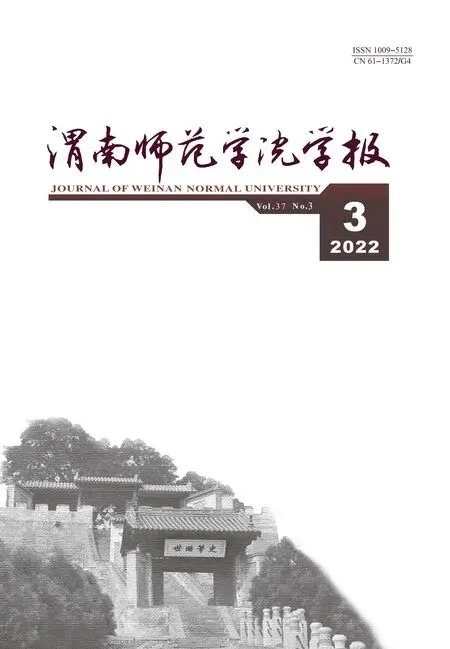《史记》二家注本起源新探
马 英 杰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一般以为,《史记》三家合刻本的形成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北宋单《集解》本上附刻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形成《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本,这种形式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1171)建阳蔡梦弼刊本;第二阶段是在二家注本上再附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形成《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本,现存最早三家注本是南宋建安黄善夫本。
这种基于现存实物文献的看法存在三点不准确之处:第一,《史记》合注家注始于合抄,而不始于合刻;第二,《史记》二、三家注的合抄始于北宋,而不始于南宋;第三,现在已知最早的《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本并非南宋乾道七年(1171)建阳蔡梦弼二家合刻本,而是一种更早的蜀刻本。本文将就此三点加以论证。
一、《史记》二家注本形成的三个阶段
通常认为,《史记》二家注本的编纂和刊刻,是由南宋前期建阳书商蔡梦弼以当时的单《集解》本《史记》作为底本,再将单行本《史记索隐》散入正文合刻而成。这种看法,无异于认为《史记》二家注本是在书坊中一蹴而就的。
实际上,二家注本的编纂面临着大大小小的难题:例如何者有资格成为《集解》之后的第二家注?《史记索隐》底本与《集解》本产生冲突该如何处理?《索隐》注文与《集解》重复的是否收录?类似的问题可以说数不胜数,而且每一个都会影响编纂的质量。处理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严谨的编纂技术,更需要高超的学术眼光。把这些问题的解决全部归功于建阳书商蔡梦弼,恐怕是不合适的。
今天所见《史记》二家注本的形式是在历史的筛选中逐步调整,缓慢形成的。从现有材料来看,《史记》二家注本的形成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零星材料补充《集解》本。这是二家注本的萌芽期,其遗存即附有两条《索隐》的日本高山寺藏《殷本纪》。此卷中的两条《索隐》,在明末汲古阁刻单行本《史记索隐》中分别注“汤”及“色尚白”。张玉春以为,由于在宋本《史记》中“汤”下原有《集解》注文而钞本阙,“色尚白”下原无《集解》,所以就此二条来说不可谓之合抄。而且就全篇来说,此卷可能是底本偶阙《集解》,不得已而用《索隐》补之而已。[1]207
张玉春的“偶阙”说在证据和推论两方面都不无可商之处。日藏写本的《索隐》“汤”注较今本《索隐》最大区别,就是写本注文在司马贞注文之末全文引用了裴骃的《集解》。由于日藏本不易检得,兹录此卷“汤”注如下:
贞曰:汤名履,《书》曰“予小子履”是也。又称“天乙”者,谯周云:“夏、殷之众,生称王,死称庙,主曰帝。尊乙神,不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曰汤,故天乙者。”从契至汤凡十四代,故《国语》曰“玄王勤商,十四代兴”。玄,契也。张晏曰:“禹,汤,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从高阳之质,故夏、殷之王皆以名为号。”谥法曰:“除虐去残曰汤之(按,“之”字衍)。”[2]1
写本《索隐》“贞曰”之下与今本《索隐》有些许差异,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此钞本不录《集解》的原因是“张晏曰”以下实为《集解》之文。换句话说,高山寺藏本“汤”之下并非阙漏了《集解》,而是由于这一条《索隐》原比《集解》更加全面。至于“色尚白”,《集解》原本无注,以《索隐》补之更无法说明原本有所阙漏。因此,张玉春所谓高山寺藏本阙《集解》而偶用《索隐》补充之说是不成立的。相反,我们可以看到此卷有意使用《索隐》来补《集解》之不足。虽然高山寺藏本并未将《索隐》全文散入《史》,但这种吸纳后人成果的做法与后来的二、三家注本的编纂思路如出一辙。因此,高山寺藏本或许不能被称为最早的《史记》二家注本,但视之为《史记》二家注本的萌芽是十分合适的。当然,高山寺本《殷本纪》在面对“汤”之下《集解》与《索隐》重复之时,选择删掉了《集解》而非《索隐》,也表现出二家注本出现伊始时在体例上的不成熟。
第二阶段,二家注本在钞本时代的探索期。《史记》二家注本的形成并非在《集解》本上附《索隐》这么简单和直接。对于宋人来说,何人有资格成为第二家注附入史文是需要仔细考虑的。实际上,面对唐代诸多《史记》注本,宋人有许多学者依据各自的学术眼光编出了形形色色的《史记》集注本。下面简单举两个例子。
第一,裴骃、陈伯宣二家注本。《崇文总目》中有八十七卷陈伯宣注《史记》写本残卷(全本百三十卷),此书著录于一百三十卷《集解》本之后、徐广《史记音义》十九卷和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之前。可见,陈伯宣注本是正文附注本,而非单注本。[3]43迄今所见唐以来《史记》写本、刻本未有不附《集解》的,所以陈伯宣注本是附在《集解》本之上的《集解》《注义》二家注本。至于这种二家注本失传的原因,可能是《崇文总目》所说的陈伯宣“多取司马氏《索隐》以为已说”而为学者所不屑。
第二,宋敏求编四家注本。北宋范镇在《宋谏议敏求墓志》中说,宋敏求曾经“以刘伯庄《史记音义》、司马正(避仁宗讳)《索隐》、陈伯宣《注义》分注入太史公正史”[4]16卷5a。宋敏求所用的三种注本中,刘伯庄《史记音义》二十卷作于贞观年间(见司马贞《史记索隐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陈伯宣《史记注义》作于贞元年间(见《新唐书·艺文志》)。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刘、陈之书,都是唐人的单行注本。若宋敏求所用的底本是《集解》本,那么散入刘伯庄、司马贞、陈伯宣三家之后,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四家注本。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宋敏求纂本的史料价值很高。或许是由于注文篇幅过大导致合编本的形式不方便阅读,也可能是因为各个注本之间存在不少无法解决的冲突,宋敏求纂本早已失传。
由此可见,北宋时已经出现合注的《史记》钞本了,只不过此时位居裴骃之后的注家尚未最终落定于司马贞和张守节,体例可能也不那么成熟。
第三阶段,二家注本的成熟期。前两个阶段的二家注本皆为钞本,至此时则进入了刻本时代的稳定阶段。由于在《集解》本上散入《史记索隐》会面临散入位置、重复和冲突等问题,最初《史记集解索隐》合注本的刊刻只能是以体例上已经成熟的二家注钞本作为底本,调整行款后直接上板的。一旦合刻本出现,对于初版的完善则不再需要对版式问题或《索隐》和正文之间的重复、矛盾进行调整。现存最早的两种二家注本——蔡梦弼本和张杅耿秉本文字多有不同,但在注文的位置、注文的增删、解决《索隐》和正文冲突三方面大体相同,就是因为它们都来源于某种更早的、体例成熟的二家注本。
二家注本的编纂难度远大于基于二家注本编纂三家注本。原因是黄善夫本由蔡梦弼本增入《史记正义》而来[1]252,而《正义》本身对《史记》正文、《集解》和《索隐》的影响都不是很大,主要是删去了《正义》和《索隐》重复的部分。由于三家注本的编纂难度较低,所以仅在蔡梦弼本出现不过约二十年后,黄善夫本就已经刊出第一种三家注本。
总得来看,《史记》二家注本的编纂,是从援引零星材料补充《集解》本开始的。经过对唐代《史记》注家的筛选及合注体例的探索,形成了形色各异的合注本,其中《集解》《索隐》二家注本在编纂体例成熟之后被刊刻成书,流传至今的有建阳蔡梦弼本和稍晚的张杅本。黄善夫本是在蔡梦弼本的基础上增添《史记正义》之后略作校勘而成,使得二家注本成为了《史记》版刻史上的重要节点。
二、最早的二家注本非蔡梦弼本辨
张玉春的《〈史记〉版本研究》出版已近二十年,至今仍是《史记》版本的研究中最全面、系统的著作。此后讨论《史记》版本的论文层出不穷,但在二家注本出现时间上,并未出现不同意见。
《史记》二家合注本的出现时间,张玉春指出有三说。[1]207第一,贺次君的晚唐说。此说张玉春以为根据不足,因为《史记》写本中只有日本高山寺所藏的《殷本纪》中抄入了两条《索隐》,材料较少,很难看作是成熟的二家合注本。张玉春看法是谨慎的。如上所述,日藏《殷本纪》不是二家注本,只能视为二家注本的萌芽。第二是“杭州刊本”说。“杭州刊本”即刘燕廷百衲本《史记》中二家合注的十卷残本,张玉春认为此十卷残本晚于蔡梦弼本和张杅刊本。有学者对张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杭州刊本”刊刻时间难以考订。[5]41其实难以考订的原因仅仅在于原书不易得见。张兴吉在详细考察刘燕廷百衲本中的二家合注本之后,指出“杭州刊本”实际上正是比蔡梦弼本晚出五年的宋淳熙三年(1176)刻八年重修的张杅耿秉本。[6]86-90故此说亦非。最后一说即张玉春支持的宋乾道七年(1171)蔡梦弼本说。将蔡梦弼本视为最早的二家注本的依据是很明显的,即它是现存最早的《史记》二家注本。
张氏的看法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蔡梦弼本刊刻五年之后的宋淳熙三年(1176),张杅在桐川(今安徽广德市)刊刻二家注本《史记》。据此本之前跋,张玉春指出:“张杅当时并不知蔡梦弼已创二家注合刻之例,以为将《集解》《索隐》合刻为其首创。”[1]215此后研究《史记》版本的学者对这一点皆无异议。张玉春的看法,前半部分是正确的,但后半部分有些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现引跋文相关部分如下:
惟唐小司马氏用新意撰《索隐》,所得为多,至有不可解者,引援开释明白。每恨其书单行,于披阅殊未便。比得蜀本,并与其本书集而刊之,良惬意。意欲重模,与南方学者共,未暇也。朅来桐川年逾,郡事颇暇,一日与友人沈伯永语及前代史,则以为先秦古书以来,未有若太史公之奇杰,班孟坚已不逮,况其余乎。搜笥中书,蜀所刊小字者偶随来,遂命中字书刊之;用工凡七十辈,越肇始四月望,迄六月终告成。[7]
跋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意欲重模,与南方学者共,未暇也”中的“重模”二字。“重模”意即根据原书重新制版,印出与底本版式不一定相同但文字上保持一致的版本。这说明了 “蜀本”与张杅本的源流关系。张杅翻刻的方法,是以“蜀本”为底本,放大字号,“命中字刊之”。这种办法在版刻史上屡见不鲜,如南宋王叔边刻建本《后汉书》,牌记云“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证,并写作大字”[8]。再如南宋建本《南史》牌记谓“此书本宅刊行已久,中遂漫灭。今将元本校证,写作大字,命工雕开”[9]。“重模”并且“命中字刊之”印出来的版本,文字与底本是相同的。至于张杅“重模”其所得“蜀本”与“南方学者”的原因,只能是“蜀本”已将《索隐》并入本书而成为《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本,在当时比较少见。
张玉春之所以认为是张杅本人将《索隐》合于《史记集解》,是因为张玉春对跋文的引用出现了错误。《〈史记〉版本研究》引用这段跋文,“重模”引作“垂模”,标点也有所改变,此句作“比得蜀本,并与其本书集而刊之。意欲垂模与南方学者,其未暇也”[1]215。对比原文与引文,可以看出语义和语气都发生了变化。语义上,翻刻之意消失,并且使得后文“命中字刊之”的“之”字指代不明;语气上,原文“意欲重模,与南方学者共,未暇也”,说的是与南方学者共同探讨,语气谦虚,而“垂模与南方学者”意为张杅将个人收藏称为南方学者的垂法模范,也不太妥当。
张杅得到“蜀本”的时间,是其至桐川前与“南方学者”为友时。张杅(?—1178),字戒仲,一作介仲,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出生于宋代著名的绵竹张氏家族,排行四十九,南宋名臣张浚之侄,张栻的堂兄,官至知广德军,淳熙五年(1178)七月卒于吴兴(今浙江湖州市)。绍兴十六年(1146),张浚谪居连州(今广东阳山县),张杅、张栻侍行。此后十余年间,张杅一直跟随着张浚。绍兴二十八年(1158),张浚谪居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张杅亦随之。乾道七年(1171)六月,张栻过湖州市与“广德兄”会面之时,作诗一首,题为《六月晦发霅川广德兄与诸友饮饯于渔山已而皆有诗赠别寄此言谢》,“广德兄”即张杅。虽然张杅任知广德军的具体时间不明,但乾道七年之前张杅已离开永州来到广德是可以确定的。[10]结合张杅刊本的跋文来看,“意欲重模,与南方学者共,未暇也”指的当是张杅至于广德之前在连州、永州一带的想法。所以,张杅得到“蜀本”的时间,在乾道七年之前居住在连州或永州时。蔡梦弼本的刊刻时间恰好在乾道七年,由此可见,张杅所见的蜀刻二家注本在蔡梦弼本之前已经刊出。
三、二家注本体例的成熟
在理论上,编纂一个二家注本只需将第二家注散入《集解》本即可,但实际上编纂者会面临不少问题。上文已经说过,编纂二家注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选择。唐代《史记》注本为数不少,有名者有许子儒、王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等,选择哪一家作为第二家注散入正文,站在宋人的角度,恐怕并非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是编纂问题。在确定司马贞《史记索隐》作为第二家注之后,具体的编纂工作中最常见的困难有三个:一是如何安排注文的位置,二是是否删去《索隐》与《集解》重复的部分,三是如何解决《索隐》底本与正文的冲突。对这三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纂目的和编纂者本人的文化修养,有不少主观因素。换句话说,即使以相同的《集解》本和单行本《索隐》来编纂一部二家合注本《史记》,不同的编纂者会编出面貌大不相同的版本。反过来说,如果两种二家合注本《史记》在以上三个问题上的处理大体一致,那么这两种二家注本应该是有共同来源。下面就这三个问题,分别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蔡梦弼本和张杅耿秉本的一致性。
首先,在《索隐》注文位置的处理上,蔡梦弼本选择了注文后置的原则,尽量将注文置于正文整句之末,避免打断正文。如《周本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单行本《索隐》出“流为乌”三字,注曰“按:今文《泰誓》‘流为鵰’。鵰,鸷鸟也。马融云‘明武王能伐纣’,郑玄云‘乌是孝鸟,言武王能终父业’,亦各随文而解也。”[11]1卷6b这条注文本应置于“流为乌”句下,但蔡梦弼本将注文放在了句末“其声魄云”之下。[12]4卷4a再如《项羽本纪》“项伯者,项羽季父也”,单行本《索隐》出“项伯”二字,注文作“名缠,字伯,后封射阳侯”[11]3卷1b,这条注文本当置于“项伯者”之下,但蔡梦弼本置于句末“项羽季父也”[12]7卷8b之下。又如《高祖本纪》“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单行本《索隐》所注之文为“以竹皮为冠”[11]3卷2b,蔡梦弼本的注文不仅在句末《集解》之后,而且和单行本《索隐》的下一条“求盗”注混在了一起[12]8卷3a。同样,《孝景本纪》“齐王将庐、燕王嘉皆薨”,单行本《索隐》分别出“齐王将庐”和“燕王嘉皆薨”二注[11]3卷2a,蔡梦弼本也是将两条注混在一起,一同置于句末《集解》之后[12]11卷2b。这种现象在蔡梦弼本中随处可见。如果核对张杅耿秉本,可以发现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注文后置的原则有利有弊。其利在保持了正文连贯性,其弊在割裂了单行本《索隐》出文和注文之间的联系。不论如何权衡利弊,这一原则都体现了编纂者将注文纳入正文时对《索隐》呈现方式的主观考量。在《索隐》散入正文的位置与完全一致这点上,可见蔡梦弼本与张杅耿秉本有着共同的渊源。
第二,如何处理《索隐》与《集解》重复的内容,也是编纂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对于重复,蔡梦弼本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删除《索隐》之后标明已删,如《孝景本纪》“萧何孙系”一条,蔡梦弼本在《集解》下称“索隐注同”。[12]11卷1a第二,径行删除不加任何提示的,如《高祖本纪》“入蚀中”,《索隐》注云“李奇音力,孟康音食。王劭按:《说文》作‘’,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音力也”一句中的“李奇音力”和“音力也”因涉《集解》而见删。[12]8卷10b第三,保留《索隐》与《集解》的重复,这种情况比较少,如《高祖本纪》“函谷关”下《索隐》引文颖语就被保留了下来,至黄善夫本才删去。[12]7卷8b同样,通观全书,蔡梦弼本和张杅耿秉本对《索隐》的处理,不论注明“索隐注同”、直接删去还是任其重复,是基本一致的。
第三,司马贞所注的《史记》正文,并不一定与待合的《集解》本正文相同,所以《索隐》之注有时需要改动才能置入史文。如单行本《索隐·高祖本纪》有“欲告之”一条,注文云“汉书作‘苦’,谓欲困苦辱之。一本或作‘笞’。《说文》云:‘笞,击也。’”[11]3卷2b蔡梦弼本正文即作“笞”,并且删掉了注文中的“一本或作‘笞’”。[12]8卷3b再如单行本《索隐·十二诸侯年表》“郑武公滑突”,注云:“滑,一作‘掘’,并音胡忽反。”[11]5卷2a蔡梦弼本正文作“郑武公”,所以在注文中添上了“名滑突”三字。[12]14卷12a又如单行本《索隐·刘敬叔孙通列传》“九宾胪传”,注引《汉书》作“九宾胪句传”[11]23卷2b。蔡梦弼本正文作“九宾胪句传”,所以删去了注中引《汉书》之语。[12]99卷5b此类情况,编纂者在实际的工作中有很大的调整余地,不同编纂者的选择不会完全相同。可遇到这种情况时,蔡梦弼本和张杅耿秉本仍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面对以上三方面问题,不同编纂者在处理方法上出现偶然的相同是可能的,但几乎完全一致则是不可能的。蔡梦弼本和张杅耿秉本在处理方式上的高度一致,反映出二家合注的体例在此时已经基本定型。因此,它们不会是独立的初次编纂版本。相反,它们反映出了此时二家注本在体例上的成熟。历史上真正第一个《史记》二家注刻本可能是张杅所见的“蜀本”,也有可能较“蜀本”更早。
四、结语
本文通过日藏《史记》写本、北宋目录中的《史记》写本和传世《史记》二家注刊本,将《史记》二家注本形成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又从文献记载和编纂体例两个方面重新考察了《史记》二家注。
《史记》二家注本在晚唐时期已经萌芽。北宋时,文人学者编纂过一些以刘伯庄、陈伯宣等作为第二注家的二家注本《史记》,不过这些二家注本都未能广泛流传,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种类的《史记》二家注本经过宋人的淘汰、筛选,在两宋之际以收入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和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的《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的形式稳定下来,体例也趋近成熟,并且形成了刻本。
迄今所知最早的《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刻本是南宋乾道七年之前已经刊成的蜀本,可惜已经失传。《史记》二家注本在历史上真正的第一次刊刻时间,仍有待探索。
——评林乐昌著《正蒙合校集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