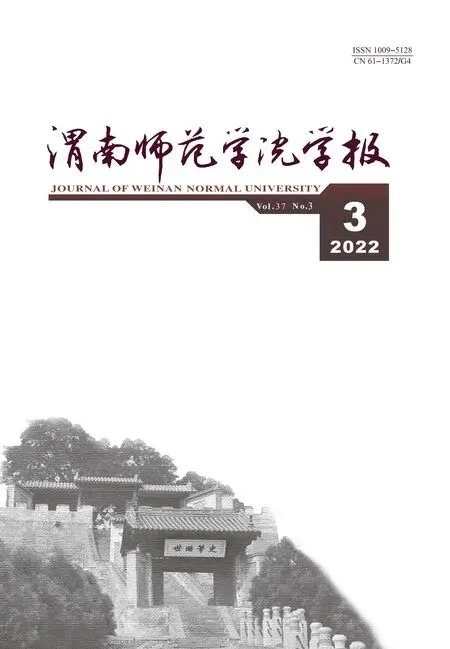论《史记》对司马相如的称病书写
姬 丹 丹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疾病作为一种“特权”符号呈现在文学作品中“便不单纯是私人的身体感知,同样也是个体生存境遇与体验的传达”[1]47,“疾病的出现既源于困顿蹇塞的人生境遇,又是抱略不展的幽怀难遣所致”[1]48。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疾病的书写遍布于本纪、世家、列传中。在这些疾病描写中,疾病更多是当事人作为一种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出现,当事人以称病去逃避事或人的行为。如《周本纪》中白起以称病为由,避免战败;《楚世家》里张仪借病逃避楚国之质问。《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对相如不同时间、境遇的五次疾病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描述为“病”“称病”“谢病”。联系两司马所处的社会时代与人生经历,作为当事人,司马相如为何要多次称病?作为创作者,司马迁又为何记录这五次疾病?
一、司马相如称病的过程
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人生轨迹做了大致的勾勒,简练地记述了其一生游梁、娶文君、通西南夷等几件事,生动地刻画了司马相如“病”的过程。
第一次是在司马相如游梁前,他以郎官的身份借病主动请免。
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2]2609
司马相如早年为武骑常侍,侍卫孝景帝。由于文学才华无法施展,一直郁郁寡欢。梁孝王入京觐见,随往的还有邹阳、枚乘等有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与他们一见如故。在汉代,任职官员若请假逾三月仍未视事,便会因病被彻底免去官职。相如正是借此病假而辞官游梁。
第二次是司马相如在临邛县,以病拒绝县令的拜访,实际上并未生病。
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2]2610
司马相如返乡后穷困潦倒,得到临邛县令王吉的接济。王吉解决了相如的衣食温饱之困,还日日恭敬拜访。相如起初还以礼相见,其后便谎称有病,回绝了王吉。王吉非但没有恼怒,反而对相如愈加谦恭有礼。
第三次司马相如“谢病”是为了拒绝参加卓王孙等富商举办的酒宴,也不是真病。
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2]2610
县令高度礼遇相如,一时被热议。卓家等富豪便举办宴会,欲一睹相如之貌。酒席当日,相如推托有病,迟迟不肯露面。再三邀请下才勉强出席,满座的客人无不惊羡他的风采。
第四次是武帝时期,相如罢官一年后被召回中央重新起用,“称病”闲居在家。
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召为郎。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2]2655
开通西南夷一事被诸多大臣反对,作为开通西南夷积极的支持者和践行者,相如被举报收取贿赂而被免官。被重新召回后虽担任官职,但他不愿论政,假病远离朝政。
第五次是相如年老之际,再次因病免官。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2]2664
司马相如风烛残年之际,养老于茂陵。武帝欲取其书,相如已死,只留下了宝贵的封禅书。武帝见之,惊诧不已。
综上所述,“称病”和“谢病”都是由当事人主动自发而产生的行为。“谢病”是以病为由而申请病假、自请辞官或拒绝见客,既包含了生病的可能,也存在没有生病的可能。“称病”意为以生病为借口,实际上并非真病,是一种托词。在五次疾病书写中,相如前四次的“因病免”“称病”“谢病”都不是单纯出于生理上的病痛,而是蕴含着复杂的政治、情感等因素,非真正的生病。只有最后一次“病甚”细致地描写了相如于临近死亡之时病痛的程度,属于真正的生病。
二、司马相如称病的寓意
称病作为一种隐晦潜在的话语,既是相如生理抱病的表现,也是他实现目的的方式之一,蕴含了深刻的寓意。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士人,他有着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怀存琴瑟和鸣的情感诉求。
(一)士大夫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
汉武帝时代,汉王朝国力增强、疆域扩展,士人普遍具有斗志昂扬的进取精神,怀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
1.称病是一种实现政治抱负的谋划
“士”是中国文化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阎步克先生认为:“中华帝国的官僚政治以学者(文人)作为官员的主要来源,这种特殊类型的官员构成了一个被称为‘士大夫’的社会阶层。”[3]465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诸侯贵族“养士”的风尚,两汉以来,入仕做官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士大夫的志向。相如的一生历经景帝、武帝两个时期,但并未受到提携重用,仕途发展不遂其意。
据司马迁记载,司马相如本名为犬子,由于“慕蔺相如之为人”[2]2609,便改名相如。蔺相如在战国时期起初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门客,后来凭借非凡的胆识和智慧在赵国官至上卿,成为当时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从改名之事可窥司马相如自小志向远大。景帝时期,相如买官任职武骑常侍。《史记索隐》张揖注:“轶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2]2609武骑常侍是陪同并保护君主安全,或观看人与猛兽格斗的武装保镖。很显然,司马相如“好读书”,其现有的官职地位与其内心出将入相的理想大相径庭,“非其好也”。出于对眼前处境的不满和对未来长远目标的考虑,司马相如意识到自己很难凭借现有的官职大有作为,这种心理的落差促使他去投奔梁孝王。
梁孝王为汉景帝的同母胞弟,十分受窦太后宠爱,被认为是大汉王朝的继位者,就连汉帝景也曾醉言:“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2]1850吴楚七国之乱,梁孝王立大功,在当时一度引发了继承王位的巨大舆论。并且梁孝王所处封地,地理位置之优越、物质之富足吸引了大量人才,梁园人才济济之势,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4]410。可见司马相如投奔梁孝王并非草率之行,“即使梁孝王‘好辞赋’,如果没有一定的政治因素,很难促使司马相如转投梁孝王”[5]114。司马相如不甘心于只做一个保镖类型的无名氏,而是欲要成为帝王治国理政的股肱耳目。因此,司马相如称病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策略,是建立在政治理想上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
2.称病是一种不得君主重用的反抗
政治清明、君臣和谐,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理想。司马相如一直渴望参与政治,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汉武帝时期,他出色地完成了两件事。首先是唐蒙在开通夜郎、僰中时滥用权利,引起巴蜀百姓震惊恐惧,于是武帝派遣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并且安抚当地百姓,司马相如圆满完成使命。其次是司马相如在多数大臣反对的情况下支持武帝开通西南夷,被拜为郎中直接成为平定西南夷的主持官员,促使开发西南夷事件顺利完成,西南的少数部族都请求成为汉王朝的臣子,武帝大喜。司马相如“两次出使巴蜀,受命于危难之际,代表朝廷,向巴蜀父老及百姓准确地宣示朝廷旨意,安定了民心,在开通西南夷的整个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使开发西南夷取得了成功”[6]138,也为我国古代边疆以及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立下了重大功劳。这次经历使他的政治理想暂时得到了实现,可是很快便破灭了,在出使时收取贿赂被弹劾。不久后,生性多疑的汉武帝便罢免了司马相如的官职。宦海沉浮、荣辱得失,只在一瞬间。正当司马相如斗志昂扬,以为终于可以展望未来的时候,却被冷水浇头,可以想象司马相如是何等的痛心疾首。
司马相如以辞赋而受汉武帝赏识,但是辞赋家在当时往往被视为“俳优”。俳优是以娱乐为外衣,以语言为手段,多指在古代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汉书·枚乘传》:“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7]1809《汉书·扬雄传》:“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7]2653扬雄在此特别以司马相如的赋作为典型,他认为赋本是用来讽谏的,但是对君主并未发挥作用,反而像是俳优之流,因此贤人君子不在作赋。可见辞赋家的地位是非常尴尬且低下的。《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了汉武帝对这些辞赋家的态度:“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7]2097可见武帝并不是看重他们的政治才干,而仅仅是把他们作为娱乐的内侍弄臣来看待。“他们一方面是皇帝依仗的内臣而受到重视,故以文采干政事,试图通过赋作来表达其匡正天下,经世致用的思想”[8]132,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仅仅是皇帝身边可有可无的内侍弄臣,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去迎合天子的口味,他们的精神和人格都是不自由的,以至于“被人与俳优等量齐观”[9]44。
个人志向无法施展,人格不得敬重,司马相如独立的自尊意识与俳优弄臣一味的附和阿谀无法共存。因此,通过称病远离朝政的行为正寓意了其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
(二)普通人琴瑟和鸣的情感诉求
在人生暗淡、迷茫之时,人往往会更关心自我的状态。政治上无法突围,兼济天下的志向难以实现,司马相如转向了对自我情感的诉求。
1.称病是司马相如自卑心理的体现
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自卑会引起心理压力和紧张,自卑感会让人感到焦虑。因此,人就会寻找优越感来补偿自己的情绪,将真正的问题掩藏起来,致力于如何避免失败。称病正是司马相如对个人的生理缺陷自卑的体现。
物质条件的贫乏和内在生理缺陷上的不足是其自卑的来源。首先,从家境方面来说,司马相如当时的处境狼狈窘困,“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2]2610。梁孝王死后,相如再回蜀地已是家徒四壁,并且失业。其次,在事业方面,司马相如在景帝时辞官后投靠梁孝王,仕途之路并无发展,还是一个不起眼的穷书生。根据刘开扬先生的说法,司马相如在与卓文君成婚时至少已经三十岁以上,李昊先生在《司马相如生平考辨》一文中认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成婚时应该是二十七岁,而汉代男子结婚往往是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最后,从健康层面来说,“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2]2655。口吃患者说话困难,在焦虑、紧张、害羞等情境下更易加重。司马相如处在人生低谷,政治追求遭遇巨大打击,又遭逢家境败落,以上几点都会加深他心中的不平感和缺失感,导致心理自卑。
卓文君优越的条件和司马相如形成鲜明对比。司马相如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大龄穷书生,而卓文君是临邛县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在家庭经济条件上远超司马相如,仅家仆就成百上千,这和司马相如室如悬磬的家境简直就是云泥殊路。此外,卓文君也不是普通女子,《西京杂记》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10]78-79虽然卓文君并非初婚,但在当时,女子再嫁或者多次出嫁是常见的事情。综上,无论是在财力还是地位上,司马相如都远不及卓文君,再加上其口吃的不足,表达上也会受到限制。试想,在司马相如当时的处境下,如果选择直接去追求卓文君,是一件何其困难之事,更不用说去面对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
因此,称病的行为正体现了司马相如由于焦虑、害怕失败,不敢直接面对卓文君的自卑心理。
2.称病是司马相如扬长避短的策略
由于自卑,人们会清楚甚至过分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与人格,要求自己克服自卑,战胜自我。在这种心理下,司马相如利用称病的方式和临邛县令王吉策划了整个过程。司马相如家境贫寒,无位无权,他便扬长避短,努力为自己营造神秘感,以人格魅力和才能去填补自身外在条件的不足。
弥补自身瑕疵,为自己建立优越感。司马相如为追求卓文君两次称病,其具体心理各为不同。第一次司马相如称病的对象表面是临邛县令王吉,而实际是为引起临邛县内卓王孙等富人的好奇,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临邛县令王吉帮助了相如,并且日日谦恭探望,相如假意称病拒绝,王吉却愈加恭谨,利用这种落差司马相如为自己建立了一个高人雅士的神秘形象,全县的百姓都觉得县令如此看重的人必定不凡。第二次司马相如称病的对象是以卓王孙为首的富人和百姓,而实际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的注意。以卓王孙为代表的富人在卓家大摆宴席,目的就是一睹司马相如神秘之身,司马相如再次称病拒绝,将个人的这种神秘感推向顶峰,在世人眼中建立了优越感,机智地弥补了自身的不足。
充分发扬优点,努力博取他人好感。在县令亲自登门的邀请下,司马相如勉强现身于众人面前,虽然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相貌没有正面记载,但是从司马相如在宴会上一出场便能“一坐尽倾”,足以见得司马相如的形貌举止必不寻常。认识到自身表达上的不足,卓文君“好音”,通晓琴理,他便扬长避短,在宴会上运斤成风,用高超的琴艺展现自己,以洋洋盈耳的琴音诉爱慕衷肠。卓文君对他一见钟情,心神荡漾,“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2]2610,司马相如以这种欲擒故纵、曲径通幽的方式成功俘获了卓文君的芳心,“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2]2610。整个事件发展中,司马相如巧妙地以病紧紧抓住了临邛县城众人的猎奇之心,增添了自己的神秘感,避免了自己的缺陷曝光于大众之下,使自身的优点和才能更为凸显。
结合司马相如政治上的失意来看,司马相如对情感的追求正是他政治追求的一种补偿,也是对自我状态的一种调适。
三、司马迁书写的深意
作为史学家,司马迁在秉笔直书的基础上对具体历史事件的选择和记录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考量,并渗透了自身的情感。从司马迁的角度来看,这种疾病的书写无疑是别有深意的,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整体情感是复杂的。
(一)疾病隐喻了对专制政治的批判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一文说:“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11]81疾病对于作家的心态和创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司马迁通过司马相如称病行为的塑造借喻现实,重点不在于表现病痛的始末与治疗,而是着重以疾病隐喻人生的流落不偶,隐喻了其抑郁、苦闷的政治困境。
疾病隐喻了汉武帝专制统治下先秦士风的消退。宋人张耒在《司马迁论》中说:“司马迁尚气任侠,有战国豪士之余风。”[12]664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了大量君主谦恭下士,君臣和谐治国的故事。如《孟子荀卿列传》:“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2]2067再如《燕召公世家》中燕昭王即位后礼贤下士,使得士人争先恐后归顺,“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2]1424,都反映了司马迁对以前士人独立自由人格的向往。但是,在司马迁的时代,士人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尚未一统,士人可以自由地在国与国间游走,士人的地位非常重要,并不受限于绝对服从于某一个君王,并且受到君主的礼遇与尊重。刘向《战国策序》记:“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13]727汉高祖时期,诸侯王养士风气浓厚,游士传统得以发扬。自汉武帝即位后,建立了严格的专制政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在大一统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士人必须以服从君王的意志为中心,他们的精神和人格都是不自由的,士人往日的社会地位和尊宠礼遇一落千丈。这和司马迁对春秋战国自由士风的追求是矛盾的。
家境普通的司马相如力争上游,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其身上同样存有浓厚的战国策士遗风。从他改名、辞官投靠梁王之事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士人通过游说权谋获得富贵显荣对他的深刻影响和巨大的激励作用。两司马皆处在专制的汉武帝时代,具曾出使西南。司马迁作为后生,应该是非常理解和尊重司马相如的。《太史公自序》中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讽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2]2873如此看来司马迁在传中大量收录相如的辞赋不仅是对其人的欣赏、对其文讽谏之旨的重视,也暗含了那个时代士人讽谏的困境。在《盐铁论·救匮》中贤良就曾公开说:“高皇帝之时,萧、曹为公,滕、灌之属为卿,济济然斯则贤矣。文、景之际,建元之始,大臣尚有争引守正之义。自此之后,多承意从欲,少敢直言面议而正刺,因公而徇私。”[14]405指出在汉武帝即位后,大臣们多奉承阿谀,少有人敢说真话,当面谏争讽刺。司马相如的辞赋虽然多用侈靡之语描摹苑囿、游猎等盛况,但最终的指向还是归于讽谏,这种讽谏方式相比春秋战国的直谏则显得委婉曲折、隐蕴含蓄。司马相如被视为弄臣之列,始终无法摆脱困境,而汉武帝独断专行、好杀伐,正是由于直谏的困难而不得不选择以委婉的方式去劝谏,“在大一统专制政治下臣子对帝王的特殊进谏方式传递出的是士子进取之心被扭曲的深层悲哀”[15]118。
司马迁对先秦自由士风的寻觅追求,与唯我独尊的王权专制格格不入。因此,疾病书写是当时士人政治理想碰壁的缩影,隐喻了司马迁对汉武帝专制的批判和对先秦自由士风的企慕。
(二)疾病隐喻了对个人心理的补偿
陈传才先生说:“所谓‘补偿’是指对人生缺憾(缺乏或失落了某些东西)的某种弥补和偿还……比如有生理缺陷的人缺乏正常人的人生生活,由此往往会生发出强烈的补偿愿望,当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便很容易借助于这种方式实现心理补偿。”[16]73对司马相如疾病的书写便是司马迁实现心理补偿的一种方式。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家庭,青年时期游历天下,视野大大拓展,也养成了他自尊自强、爱憎分明的性格。汉武帝天汉二年,李陵战败后降于匈奴,武帝大怒,群臣皆斥责李陵之罪,唯司马迁为李陵辩解不平,最后李陵全家被杀,司马迁也因“欲阻贰师,为陵游说”被定死罪。史书未成,功名未立,司马迁不想如蝼蚁一般轻死,从而在屈辱中毅然选择接受腐刑,保留性命。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的身心遭受了巨大的摧残,身体被凌虐,遭到轻视与嘲弄,被君主疏离,成为最低微的宦官。在《报任安书》中他说:“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亦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17]4323“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17]4329身心残缺的莫大痛苦,倡优般低下的社会地位,如此之处境,司马迁的身心早已悲痛欲绝、心灰意冷。作为一个史官,在现实中他已经无法有所作为,只能在文学中肆意驰骋。现实的遭遇如此不尽人意,司马迁充分利用文学的力量去补偿自身心理的缺憾。
清人吴见思《史记论文》评《司马相如列传》:“史公写文君一段,浓约宛转,为唐人传奇小说之租。”[17]3869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记载像相如与文君这样的恋爱故事,相如传记可以说是第一篇。”[17]3869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传奇的爱情故事,这在《史记》其他的篇目中都是少见的。据房锐先生所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相如所撰《自叙》为蓝本,加以增改而成。”[18]100
司马迁将这段爱情故事写入史书中,应该不只是出于其爱奇的兴趣,而是和其个人生理的缺陷、心理的失衡有密切联系,隐喻了其对个人不平的心理补偿。“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17]4328,由于钱财不足赎罪,司马迁不得不接受腐刑;遇难的时候,亲戚朋友无人帮助。生理的残缺和人情的冷漠带给司马迁的身体剧痛和情感体验在其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同时也使得他对士人寄托了更多的同情和欣赏。
在司马迁的笔下,司马相如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身为辞赋家,司马相如虽然在辞赋中寄寓讽谏,但效果甚微,他只是武帝身边的俳优弄臣。作为政治家,司马相如虽然有成为如蔺相如一样的远大政治抱负,但却辗转得不到君主的赏识与重用。作为普通人,他还有着口吃的缺陷。司马相如的一生仿佛并没有什么荣光时刻,终其一生,最后被“消渴疾”缠身,只落得了病死在家中的悲惨结局。这种不得志的遭遇和生理的缺陷与司马迁的失衡心理是吻合的。因此,司马迁将司马相如的称病与其生活窘迫、事业无成等同时书写,是和自己的经历互相牵引的,隐喻了二人巨大的生存困境。将司马相如称病琴挑文君的故事载入史书,不仅是对相如失意人生的温情点缀,也体现了司马迁欲解救相如人生困境的幻想,从而完成司马迁对个人痛苦心理的补偿与抒泄。
李长之先生说:“情感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他的书是赞叹,是感慨,是苦闷,是情感的宣泄,总之,是抒情的而已!不唯抒自己的情,而且代抒一般人的情。”[19]98司马迁的疾病书写是对时代的呼喊,充分展现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士子、平凡的文人,在面临人生的诸多困境时往往是无奈且无力的,尤其是当政治权势强力压迫于个人追求之上时。哀之、叹之,司马相如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司马迁的困境,更是那个时代无数士子、文人所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