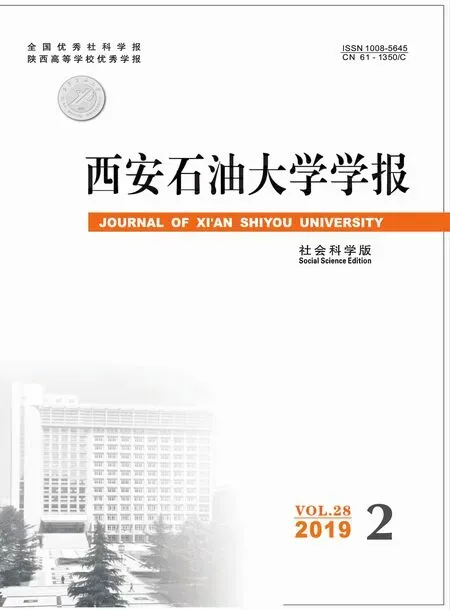《史记索隐》研究回顾与展望
王 璐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0 引 言
近现代是“史记学”研究的转折期,随着西学思想的传入,“史记学”研究在传统思想与西学东渐的碰撞下,在进一步深化考证的同时,也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从而取得了更为广泛的成绩。[1]135-139然而,相较于“史记学”的其他论题,关于《史记索隐》的专题性研究,似乎一直未能成为“史记学”研究的学术热点,有关研究成果,虽不算寥寥无几,但在数量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足。
1 相关研究专著
真正意义上以《史记索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仅有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以下简称《考实》)一部。此书将《史记索隐》中所有引文的出处一一加以考证叙录,并对比原书原文与《史记索隐》中引文的差异进行说明。程金造以为“毛氏所刻,虽标字列注、规制存小司马之旧,而实非重刊北宋秘省大字本之书”[2]3,因此《考实》一书所引《史记索隐》文字,乃是从现存最早的三家注《史记》即黄善夫本中所辑出者。[注]程金造称说本书所用《史记索隐》之底本乃是“影黄善夫本”,因为其“以校毛晋单本《索隐》,殊见完善”之故。然就此“影”字而言,此“黄善夫本”当是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中所收入影宋庆元黄善夫本《史记》,而此百衲本中文字,因经过张元济之校改,已非黄善夫本原貌,张元济另有《校勘记》说明其所有改动。因而此“影黄善夫本”大约不能径称“黄本”。作者先是考证出《史记索隐》中引文的所有出处,然后将这些书的作者与书名按照经史子集分类一一排列,其下则先列《史记索隐》中的篇名,篇名之下列本篇中司马贞所引此书之文句,文句之后有括号,内书此文句在影黄善夫本中的位置以及此文句在所列书中的篇名,文字上如若有所差异,则在此处以案语指明。每书引文全部列完后,另起一段,是作者对此书所作的提要。提要中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爬梳与考证,尽可能全面地介绍了本书的作者、成书及传播、接受等情况。尽管中华书局编辑部在《考实》一书《出版说明》中指出因为这部书稿乃是程金造生前遗著,未能来得及好好修订,致使书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但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文的学术专著,《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一书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开创性价值,同时作者辑录考订工作的细致,也很值得人们钦佩。
除过此书,便是一些学者在其有关专著中对《史记索隐》所做的专题性论述。
顾颉刚先生在其《读书笔记》中多有关于《史记索隐》的论述。如《读书笔记》卷七有《宋忠补〈世本〉系据〈史记〉》《宋忠、谯周、司马贞所见〈史记〉皆不同》,通过《史记索隐》中的有关论述,指出《世本》与《史记》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更改,以致不同时代的人看到的内容会多有差别;有《〈荆州记〉与〈史记索隐〉言齐桓所登熊耳之谬》,认为《史记索隐》及其所引《荆州记》言齐桓公登熊耳山之事实属谬误;有《白石地,〈索隐〉、〈正义〉异解》,对《索隐》《正义》解释《齐悼惠王世家》中“白石侯”之“白石”的不同有所质疑;有《“文章尔雅”,〈索隐〉误解》,指出《索隐》在解释“文章尔雅”一句时,以为“尔雅”乃《尔雅》之书,可谓“脑筋不清”;《张守节见〈索隐〉》指出《留侯世家》中《正义》有专门解释《索隐》注文的批注,由此可以判断张守节在写作《史记正义》时,乃是已读过《史记索隐》的。[3]卷七·212-287卷八有《〈索隐〉释“庸职”异想天开》,批判了司马贞对《齐世家》中“庸职”一词的解释;《〈索隐〉误释“子晣”》指出《赵世家》中简子言曰“吾有所见子晣也”,意思乃是“我是认识你的”,“晣”实为“晰”,是分明的意思,但是《索隐》以为“子晣”为人名,实在误人;《“欧代”即“瓯脱”〈索隐〉误释》指出《赵世家》中的“欧代”实际上就是《匈奴列传》中的“瓯脱”,《索隐》以“欧”为动词,“代”为代郡,又是一误,并感慨“《史记》非有一新注不可,然何易也”;《〈索隐〉引〈纪年〉证〈史〉,不如王劭》认为司马贞在《孟尝君传》中引《纪年》仅列异同,毫无自己的决断,实在不如王劭;《〈孟尝君传〉“过市朝者”“朝”为衍文,《索隐》强解》指出《孟尝君传》中“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之“朝”字实是衍文,《索隐》却强作解释何为“市朝”;[3]卷八·286-299卷九有《〈史记索隐〉与〈正义〉之关系》《司马贞与张守节》《唐弘文、崇文两馆之〈史记〉学》《古人著述用前人说而没其名》四篇[3]卷九·359-364,乃是对程金造《史记正义、索隐关系证》一文中观点的引述、评论与补充解释,顾颉刚对程金造认为的张守节在作《史记正义》时乃是看过并参考了司马贞《史记索隐》的观点,持认同态度,并进一步解释说明张守节不提司马贞名姓,乃是古人著书之通例。
其后,时哲有两类著作,对《史记索隐》的有关问题有所阐释与探讨。其一是《史记》研究的各类专著,其二是隋唐学术思想史类著作。
在众多的《史记》研究专著中,为《史记索隐》设立专章进行讨论的共有七部。[注]这里不包括在研究《史记》时对作为三家注之一的《史记索隐》所进行的常规性介绍。朱东润《史记考索》一书有《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例》一篇。[4]93这篇文章先考证介绍了司马贞的生平,后对《史记索隐》一书中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评价。朱东润指出,《史记索隐》首先指出司马贞所见之《史记》与今本之异文;其次,因司马贞“悍于立言”之故,在《史记索隐》中有《补史记条例》与《三皇本纪》之作,然而朱东润认为前者“其言多未能得史公编次之本意”,后者“殊失古人多闻阙疑之意”。尽管如此,《史记索隐》对太史公的不少论断,还是“多得其要核”和“自有卓见”的,对于司马迁之谬失多有考索,且“大体皆有条理可据”,基于此,在《史记索隐》中司马贞也有意识地在“校订《史记》或据他书改正或增补之”。除此之外,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对于裴骃《集解》、徐广《音义》等旧注有所考订。尤其是裴氏《集解》,司马贞既有攻讦,又有疏解,因此朱东润认为不可理解的是,《史记索隐》与《集解》中何以多有相似雷同的语句,此点很值得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而对于徐广“不敢妄下一字”的“专谨”态度,司马贞并不怎么欣赏,因此对徐广的保守观点多有攻击,朱东润亦举出例证,有所说明。裴、徐之外,《史记索隐》对其他各家的批驳,朱东润也举例并有所说明。而对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整体评价,朱东润所持态度较为客观,认为司马贞持论确多有极精处,然其中亦不乏讹谬,而种种讹谬,究竟是司马贞下笔之讹亦或是后人传写之讹,则难以确知了。程金造《史记管窥》一书,有《史记正义与索隐关系证》[5]169《汲古阁单本史记索隐之来源和价值》[5]218两篇文章。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一书,有《〈史记索隐〉与〈史记〉唐写本》一文[6]90。后来《史记研究集成》第12卷收入张玉春、应三玉合著《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一书,除再次收入《〈史记索隐〉与〈史记〉唐写本研究》一文外,[7]61还有一章专门对《史记索隐》的考释,[注]案应三玉又有《〈史记〉三家注研究》一书,其中亦包括“《史记索隐》考释”一章,内容与此处相同;与此同时,是书还有“《集解》《索隐》《正义》之间的疏解与承继关系”一节。包括概述、特点介绍与所引各家说例三个部分。杨海峥《汉唐〈史记〉研究论稿》中以专节对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注释成就及其对《史记》的评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8]136。袁传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一书,在考论司马迁生年时,对《史记索隐》在此问题上的有关论述进行了辨证,如“《索隐》注引《博物志》、《正义》按语在证明自身准确无讹前不能作为推算司马迁生年的‘直接证据’”“所谓日本‘南化本’《索隐》作‘年三十八’的‘铁证’实为伪证” “从由唐至宋‘三十’、‘四十’及‘世’字书体演变考察《索隐》《正义》十年之差的成因”[9]38-68;在“太史公书专题研究”一章中,又有对“《索隐》注‘臣安’为‘任安’搅起的大波”的论述[9]204。王涛《元前〈史记〉诠释文献研究》中,有专节对“注释类《史记》诠释文献——《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从作者生平、文献征引、训释内容及方法、考辨正误、校勘、目录、辨伪、辑佚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10]105
《史记索隐》作为唐代司马贞批注诠释《史记》的代表性著作,也得到了少数学术思想史研究者的关注。张岂之、刘学智编著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编年 隋唐五代卷》以年代为序,介绍隋唐五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事件,其中“玄宗开元二十年壬申(公元732年)”部分有“司马贞《史记索隐》约撰于此一时期”条[11]365。孔德凌、张巍、俞林波所著《隋唐五代经学学术编年》一书中“玄宗开元二十年壬申(732)”部分亦有“司马贞撰《史记索隐》”条[12]508。由此可知,此二部思想史编年著作,皆认为司马贞《史记索隐》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
2 专题研究论文
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史记索隐》的专题研究论文渐次发表;而21世纪以来,则有数篇以《史记索隐》研究为选题的学位论文发布。
2.1 单篇专题研究论文
有关《史记索隐》的专题研究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史记索隐》展开研究。
一是对单行本《史记索隐》版本问题进行探讨。程金造《汲古阁单本〈史记索隐〉的一些问题》一文“认为毛本《史记索隐》一书,实在不足推重。并且毛晋所谓北宋刊版之言,也是欺人之谈,不足凭信”。[13]151-160何以言此,乃是因为程金造通过比对毛晋单行本《史记索隐》与现存最早三家注合刻本南宋黄善夫本《史记》发现:一者单行本《史记索隐》较之黄善夫本中的《索隐》条目,少了百数十条;二者较之黄善夫本中的《索隐》注文,单行本《史记索隐》中的讹误“为数不下几百条”;三者单行本《史记索隐》中有专门解释《集解》中文字的大字条目,其体例是于被解释的《集解》中文字前标一“注”字,以区别被批注的《史记》正文文字,“但毛本往往脱去注字,有似注文为《史记》正文,致使人误认小司马所据之本,殊多异字,或有据以改易《史记》者,迷误读者,为害甚大”[13]155-156。此外,程金造还指出,毛晋称其所刻单行本《史记索隐》所依据的是“北宋秘省大字三十卷本”,然而这个本子在书目著录中鲜见踪迹,他认为毛晋所据以刊刻的当是经过展转流传下来的一个抄本,尽管声称北宋秘省刊本,有高其声价之嫌,但是其卷帙规模却保留了小司马之旧面目,因此也有其价值所在。张玉春《论单行本〈史记索隐〉的唐写本特点》一文,[注]案此文与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一书中的《〈史记索隐〉与〈史记〉唐写本》一文,张玉春、应三玉《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中的《〈史记索隐〉与〈史记〉唐写本研究》一文,内容略有小异。通过比对单行本《史记索隐》与传世唐写本的卷次,与传世唐写本、《汉书》以及类书中所引《史记》的文字,认为“此本无论在体例、篇次上,还是在文字内容上,均可证其非毛晋所伪造,其同于唐本的特点是明显的,而其多异于诸宋本,即可证毛晋所说据北宋秘本并不可信。此本完全可能同于现存的唐抄本,毛晋正是以流传下来的唐抄本,或以唐抄本为底本的宋抄本上版的”[14]35-40。同时,张氏虽称程氏所论“毛氏所说据北宋秘本为‘欺人狂语’”之言实属过激,但在对于毛晋单行本《史记索隐》来源问题上,张氏与程氏的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此本所据底本乃是唐代流传下来的抄本。
二是对《史记索隐》及其所引文献的考证与探讨。[注]此处有潘铭基《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用〈汉书〉颜师古注研究》一文,未能得见。苏兴《李斯〈上书秦始皇〉的李善注和司马贞索隐的问题》一文,指出《史记索隐》对《李斯列传》中所收入的李斯《上书秦始皇》即《谏逐客书》一文的批注,多与李善在《昭明文选》中的批注相类,且在《司马相如列传》中亦有直接征引李善之注,“因而可证《索隐》在后,参考、抄掇了李善注”[15]47。吴汝煜《司马贞〈史记索隐〉与〈竹书纪年〉》一文[16]73-81,认为司马贞著《史记索隐》时大量引述《竹书纪年》中的材料,一则在时间、人物、事件等许多方面充实了《史记》的记载,在人名谥号上对《史记》中的记录作了补录;二则在很多具体的历史问题上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错误,也对《史记》中记载的历史事实进行了补充;此外,司马贞对于无法确定的问题,也没有盲从《竹书纪年》,而是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同时,大量引述《竹书纪年》材料的《史记索隐》也为《竹书纪年》佚文的留存做出了贡献。李步嘉《〈史记索隐〉引韦昭〈汉书音义〉考实辨证》一文[17]247,是在作者全面整理唐前《汉书》旧注的过程中,因辑得韦昭《汉书音义》七百八十余条,于是和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所考韦昭诸语,两相比对,详加考辨,对《考实》书中有关韦昭《汉书音义》诸条目的论述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文中以《史记索隐》的篇目为序,共计考察出《考实》中17处疏漏,并以作者所辑到的韦昭原文及他书之外证加以论证。牛巧红《〈史记索隐〉引书体例考辩、述补》一文,乃是在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研究基础上,“考察《史记索隐》具体的引书体式,探究其取舍规律,并据此为《史记索隐》续补引书凡例,正其‘规律未严’之名”[18]46-50。文章先分类列举《史记索隐》的4种11小类引书体式,后总结补述了《史记索隐》的引书凡例四条,明确了司马贞作《索隐》时的引书体例。
三是对《史记索隐》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加以辨证。丁忠义《〈史记索隐〉“贱之征贵”条质疑》一文,对《史记索隐》在批注《货殖列传》“贱之征贵”句时称“征者,求也。谓此处物贱,求彼贵卖之”者,提出了疑义。作者认为若释“征”为“求”,不但无所本,也讲不通,当“释作征兆、预示比较妥当”[19]107。施丁《〈史记索隐〉注“太史令”有问题》一文,对《史记索隐》引《博物志》注《太史公自序》中“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条颇有疑义,作者首先指出南宋黄善夫三家注合刻本《史记》、南宋耿秉两家注合刻本《史记》、元中统二年三家注合刻本《史记》等《史记》的早期版本,此条《索隐》注文“《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中“司马”二字下皆无“迁”字,因而不能断定《索隐》所补“迁”字就一定正确。其后,又举例证明此条批注中的“三年”乃是指汉武帝三年,因而推测“司马”后所夺之字并非司马贞所补之“迁”字,而应当为“谈”字。从而得出结论,“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注处有误”,此条批注“写的是汉武帝三年除司马谈为太史令之事”,“而且既可由此推知司马谈的生卒年(汉文帝十五年至汉武帝元封元年,即前165-前110),也可旁证《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之注本来无误,肯定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前145)毫无问题”。[20]42-49萧文《〈史记索隐〉辨误》乃是一篇读书札记,其文指出《史记索隐》在注释《十二诸侯年表》“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条时,所言“宋有公孙固,无所述。此固,齐人韩固,传《诗》者”,误也。作者以《汉书·艺文志》中有关著录与注解,辅以梁启超《诸子略考释》中言,指出“此非韩固,而是公孙固”,《索隐》之注有失。[21]76王永吉《〈史记索隐〉“【臬阝】县”地名校议》一文,指出《史记索隐》批注《黥布列传》“兹乡”条时所谓“鄱阳【臬阝】县之乡”者颇误,首先“【臬阝】”的正字当作“鄡”,其次此处“鄱阳【臬阝】”三字当为“鄡阳”二字之讹[22]121-124。苏芃《司马贞〈史记索隐〉“王师叔”正讹》一文,探究论证了《史记索隐》中所征引的旧注称曰出自“王师叔”者,乃是“王叔师”即王逸之讹误。其理据有二:一是《史记索隐》中5处“王师叔”的旧注除1处外,其他皆能在王逸《楚辞章句》中找到相同的文字;二是这5处“王师叔”的旧注,有2处在《史记集解》中也被引述,《集解》指其出处为“王逸”。最后作者还举例证明王逸之字为“叔师”无疑,故而《史记索隐》中的“王师叔”必为王逸之字“叔师”之讹误。[23]68-69孙利政《〈史记索隐〉“淖葢”是人名吗?》一文,认为司马贞《史记索隐》对《货殖列传》中“蜀卓氏之先”句的注解“淖亦音泥,淖亦是姓,故齐有淖齿,汉有淖葢,与卓氏同出,或以同音淖也”,其中“淖葢”并非如中华本《史记》专名线所标与“淖齿”俱为人名,而是在“淖”下脱一“姬”字,此句当作:“故齐有淖齿,汉有淖姬,葢与卓氏同出,或以同音淖也。”[24]70
四是游尚功对《史记索隐》中所涉及的音韵问题的探讨。其论文主要有两篇:《司马贞〈史记索隐〉声类》[25]63-68和《〈史记索隐〉中的“浊上变去”》[26]14-15。第一篇文章通过摘录出《史记索隐》中的所有2 244条音切,去其重复者得1 854条,从而整理出《史记索隐》的声类,共得三十六类,并且指出“它所反映的声类系统非常接近《广韵》,所不同的只是唇音分化出非奉两纽,神禅合并,云以独立”。[25]68第二篇文章通过对司马贞《史记索隐》中注音资料的分析,指出在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已出现了“浊上变去”的音变现象,这比其时所发现的反映“浊上变去”现象的最早文献——韩愈的《讳变》要早出近100年。
五是对《史记索隐》作者司马贞个人有关情况的考证与论述。李梅训《司马贞生平著述考》一文,通过对各种文献史料的爬梳考证,认为司马贞“生年在高宗仪凤间,武后后期为求学期,仕宦于中、睿、玄宗之世,历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等职,官终润州别驾”,而“《史记索隐》成书时间约为开元二十年左右,他也在成书不久去世,年约五十余岁”[27]109-111。牛巧红《司马贞籍里考辨》一文,以毛晋单行本《史记索隐》、南宋黄善夫刻本《史记》中《索隐》注文“藩离既有其地,句吴何总不知?贞实吴人,不闻别有城邑曾名句吴,则系本之文或难依信”者中“贞实吴人”一句,加之《浙江通志》有关于司马贞女许配董思述,未嫁而董思述亡,司马贞女得知亦绝食而亡,于是两家便将他们合葬在珠湖山这样的记载,可知司马贞女居于浙江,因未嫁之女一般会居于父母之家,因此左证司马贞亦居吴地为吴人。而《史记索隐》中署名“河内司马贞”者,乃是唐人常以郡望代籍里之故。[28]6-7又牛巧红《司马贞生平考辨》一文,在前贤时哲对司马贞生平的考订基础上,深入挖掘新的文献资料,“考证出司马贞出生于唐高宗显庆六年与咸亨二年之间(660-671年),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为国子博士,开元七年(719年)为弘文馆学士,开元八年(721年)出任润州别驾,不久后辞世。《史记索隐》成书应在开元之初,不晚于开元八年”。[29]117-120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年新修订)第二十二条规定,“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或者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单位、个人,应当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第二十四条对发证权限进行了明确规定,“申请取得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向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依法决定是否发给生产经营许可证。其他种畜禽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放,具体审核发放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六是对司马贞补《史记》思想及《史记索隐》批判精神的探讨。王裕秋、张兴吉《论司马贞中止〈补史记〉写作的原因——以司马贞笔下的炎帝为例》一文,通过对司马贞所补《三皇本纪》中涉及炎帝内容的分析,认为“司马贞虽然多方收罗炎帝的史料,但是他所收集到的史料还是无法超越前人,因之他无法缝合自战国至唐千余年来关于炎帝的各种传说中的矛盾”,因此“最终知难而退,最终放弃了《补史记》的想法,最后改为补注《史记》,即只完成了《史记索隐》”[30]63-66。王涛《司马贞补〈史记〉及其对〈史记〉版本的影响》一文,先提出司马贞“补《史记》和写作《史记索隐》是关系密切却又应该清醒地辨别开的两件不同的工作”,但是学界对司马贞补《史记》工作的关注度尚且不够,因此作者便通过对有关资料的梳理,详细交代了司马贞补《史记》工作的来龙去脉。作者在比对了殿本系统与中华本系统《史记》对于《史记索隐》原书中《补史记序》《三皇本纪》及诸条关于改定篇目注文的收录情况后,得出结论:由于刊刻者对司马贞补《史记》工作认识的不同,使得不同版本系统的《史记》在刊刻时,对于《史记索隐》中带有补《史记》意味的篇章与注文,在取舍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31]35-37刘璐《论司马贞补〈史记〉意识在〈史记索隐〉中的体现》一文,通过举出具体例证,来说明司马贞“补《史记》虽然‘未遂’,但在《索隐》中却经常体现着‘补史’意识与残迹”。[32]91-93范景斌《略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批判精神》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司马贞的批判精神出发阐释其补史精神。文章指出司马贞《史记索隐》一书,“直接指出司马迁之疏略错误、与他书之不同者,达五六百余处。其中明确提出攻驳者,达一百五十多条”,包括指出所记史实疏略、质疑所记之史实、指出司马迁之引史错误、指出司马迁叙史错乱、指出司马迁评议失当、指出记史前后矛盾、指出司马迁所见史料未备、指出《史记》文字错误等八个方面[33]84-85。
七是还有一些文章或是类比《史记索隐》与其他著作,或是以《史记索隐》为主要研究材料,来探究其他著作的有关问题。前者如程金造《〈史记正义〉〈索隐〉关系证》一文,通过比对《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二书内容,发现《史记正义》中的注解不单有针对《史记》正文与裴骃《集解》者,更有针对司马贞《史记索隐》中语词的解释,因而推断张守节作《史记正义》一书时,不但见过司马贞之《史记索隐》,还对其中的内容有所阐释,而正因为《集解》《索隐》《正义》这三部书——裴氏《集解》解释正文,而《索隐》在解释正文之外,还有时疏通裴氏《集解》;《正义》在解释正文之外,又有时疏通裴氏《集解》和小司马《索隐》”——有着这样的承继关系,可能也是后人将此三注与《史记》合刻的原因之一。[34]28-36后者如牛巧红《刘伯庄〈史记音义〉考评:以〈史记索隐〉、〈正义〉所存佚文为例》,在朱东润《刘伯庄〈史记音义〉辑佚》的基础之上,再对《索隐》《正义》进行翻检,比朱氏多辑出佚文23条,共计256条,再针对这256条《史记音义》之佚文加以考察,从而对刘伯庄之《史记音义》的成书、内容与价值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研究。[35]27-30石风、马志林《牛运震〈史记评注〉纠驳旧注辨析——以司马贞〈史记索隐〉为主》一文,详细考察分析了牛运震《史记评注》一书针对《史记索隐》的有关论述,发现其对旧注的批驳态度十分明显,而从其批驳的具体内容来看,牛氏十分反感旧注对《史记》权威性的质疑,其评注方法多样并以文学手法为主,但在考证方面并不擅长[36]16-19。
2.2 专题研究学位论文
新世纪以来,以《史记索隐》为核心内容进行研究的学位论文共有7篇,另有2篇以《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为共同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注]此是通过检索CNKI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读秀等学术资源数据库,将结果整合而得到的数据。其中以《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为共同研究对象的论文有一篇为1988年的硕士学位论文,这里也一并论述。下面逐一介绍评析。
首先是以《史记索隐》为核心内容进行研究的7篇学位论文。[注]此处有2001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赵昌文《〈史记索隐〉佚文探索》一文不得见。
2004年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蔡先锋的《关于〈史记索隐〉的几个问题》。这篇论文乃是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史记索隐》进行研究。文章先对司马贞其人、《史记索隐》的创作与流传、刊刻及后人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简单的考证与介绍,其后则分别从训诂、校勘与文献考证三个方面详细阐述《史记索隐》的成就。在训诂方面,《史记索隐》的训释包括音训、训释词语、按断词语、诠释句子、训释名物与典制等多个方面;在校勘方面,《史记索隐》不但对《史记》及《集解》注文中的衍文、倒字、异文、脱文、讹文等进行了校勘,还对其他注疏《史记》的文字进行了校勘,并对后人窜补《史记》的情况进行了考校,凡此种种,不但对《史记》的校勘工作,对校勘学本身而言,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文献考证方面,《史记索隐》对《史记》正文及《集解》注文中的有关地名、典制、史实、书目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考证,同时对《集解》中的引文及司马迁的生平也有所考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06年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王勇的《明毛晋刻〈史记索隐〉研究》。此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研究部分,下编为校读札记部分。上编以毛晋汲古阁刻单行本《史记索隐》为研究对象,先介绍毛晋其人及《史记索隐》的刊刻、流布与翻刻,然后探讨了毛晋刻《史记索隐》在版本、校勘以及研究合刻本《史记》中《索隐》注文删改情况时的重要价值,并且详细梳理了司马贞关于《史记》体例的论述。其后,作者对毛晋刻《史记索隐》的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阐述了对毛晋刻《史记索隐》进行重新整理的几点设想;下编为毛晋刻《史记索隐》校读札记,以中华书局1982年版《史记》作为底本,校以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明毛晋汲古阁刻《史记索隐》、四库全书本《史记》,指出同异,并加以考证。
2007年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范景斌的《略论司马贞〈史记索隐〉对〈史记〉的驳正》。这篇论文是对司马贞《史记索隐》具体内容的研究,作者选取《史记索隐》中对《史记》进行驳正的部分进行讨论。首先,作者探究了司马贞对《史记》加以驳正的原因,乃是为使《史记》更加完善。其次,作者从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对《史记索隐》中对《史记》驳正的有关文字进行分类与归纳,认为在内容方面,司马贞主要对《史记》的体例、原文与旧解三个方面进行驳正;而在方法上,司马贞主要通过实地考察、《史记》本书之内证、其他文献之外证及合理推理等方法对《史记》进行驳正。再次,作者又举例指出,司马贞对《史记》驳正的不当之处。最后,则总结了司马贞以《史记索隐》驳正《史记》的重要作用,包括校勘文字、考证史实、补充史料与疏解史文四个方面。
2013年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牛巧红的《司马贞〈史记索隐〉研究》。这篇论文诚如作者所言,乃是目前为止“对《史记索隐》较为系统的专门的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七个方面。其一为司马贞其人与《史记索隐》的成书,其中考辨了司马贞的籍里与生平,论述了《史记索隐》成书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动因。其二为《史记索隐》的版本研究,这一部分不单介绍了单行本《史记索隐》的著录与刊刻流传情况,还介绍了包含《史记索隐》注文的《史记》几家注合刻本的有关情况。其三为《史记索隐》引书研究,这一部分在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研究的基础上,对《史记索隐》的引书体式与规律进行了详细探讨,并补充了《史记索隐》的引书凡例。其四为《史记索隐》注释体例及注释成就的介绍,作者先归纳出“更改舛错、裨补疏遗”“意有未通、兼重注述”“探求异文、采摭典故”“释文演注、重为述赞”“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五方面注释体例,其后又指出《史记索隐》在版本与校勘、音义训释、惩妄补阙等方面的成就。其五为《史记索隐》的注释特点,作者认为《史记索隐》的注释特点有四,分别是“精于校勘、详于训诂”“勇于立言、长于辩驳”“引书广博”“以裴注为本”。其六为《史记索隐》对《史记集解》的继承和发展,主要对二书之关系进行了讨论,认为《史记索隐》对《史记集解》有所继承、有所疏解、有所增补也有所不从。其七为《史记索隐》对后世《史记》考释类著作的影响,主要分析了《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史记笺证》三部书对《史记索隐》的继承与接受。
2013年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龙向平的《〈史记索隐〉训诂内容研究》与韦琳的《〈史记索隐〉词义训释方法研究》。龙文从现代语言学的视角,采用例举、比较互证、义素分析、同源系联、图表展示与数据统计等各种方法,对《史记索隐》中校勘、文字、注音、词语与训释、语法与修辞等多个方面的训诂内容进行了十分全面的整理与分析,从而对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所表现出来的训诂成就有了一个更为公允的认识。韦文同样是以训诂学的角度来研究《史记索隐》,但与龙文的全面研究有所不同,韦文主要是通过整理与总结《史记索隐》中的训诂材料,归纳出其中的十种词义训释方法,重点探究与论述。最后总结出《史记索隐》在词义训释方面的特点与成就。
其次是以《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为共同研究对象的2篇学位论文。
1988年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龙异腾的《〈史记〉索隐正义反切考》。这篇论文通过系联《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中的注音材料(主要是反切材料),得到《索隐》有声类38个,《正义》有声类39个,并将结果与《切韵》音系的代表著作《广韵》进行比对,得出结论:《索隐》《正义》的声类,“唇音除明母外轻重唇分立;舌音分为端知两组,泥娘分立;齿音分为精庄章三组,其中索隐从邪不分,船禅不分,正义船禅不分;喉牙音匣云、云以都各自分立”。但由于材料较少且分布不均,无法得到完整的韵类系统,通过考察,作者发现在韵类方面《索隐》《正义》与《广韵》存在一定差异,即“索隐正义真谆、寒桓,又索隐歌戈都各为同一韵系的开合口。索隐脂之微三韵开口已混并为一;殷韵并入了真韵开口;尤幽两韵混并;覃谈两韵入声已混并,咸衔两韵舒入声都已混并;严凡两韵不分。正义东一等与冬、东三等与钟有混并迹象;脂之两韵开口已混并,歌韵开口与脂之开口界限不清;有相当数量的宵韵字并入了萧韵;庚韵三等开口舒声并入了清韵,严凡两韵不分”。[37]
2017年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陈亚茹的《〈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的训诂比较研究》。这篇论文先从训诂体例与术语、训诂内容和方法几个方面系统总结归纳了《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中的训诂文句,然后比较分析了《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的关系与二者词义训释方面的不同。其中,在对《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关系的探讨中,作者举出大量具体的例证,包括《正义》直接解释《索隐》者、《正义》直接用《索隐》中解释者、《正义》补充《索隐》内容者,用以证明张守节作《史记正义》极有可能是见过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承继了早年程金造先生所持观点。
3 《史记索隐》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近现代以来对《史记索隐》的研究,尽管也可以说是多视角、多维度,既有针对《史记索隐》本身内容及其中所体现的司马贞思想的研究,也有以《史记索隐》中的材料进行音韵学或训诂学的研究,更有《史记索隐》与其他《史记》注文的比较研究。然而,在考察这些研究成果时会发现,学者们在研究《史记索隐》时所称说的“《史记索隐》”乃是作为《史记》三家注中的《史记索隐》,而只有极少数专门性的论文,是在对单行本的《史记索隐》展开探讨。例如现今唯一一部研究《史记索隐》引书情况的专著——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亦是从所谓黄善夫本中辑出《史记索隐》的内容进行研究的。《史记索隐》作为《史记》三家注中唯一一部有单行本存世的作品,尽管后世对汲古阁所刻此单行本颇有微词,不甚满意,甚至怀疑毛晋所称说的版本来源并不真实,然而就其问世后被众多的藏书家收集,被多个学者所批校,并又被翻刻来看,单行本《史记索隐》亦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很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而就此单行本《史记索隐》而言,尚有许多论题未被学人所深入讨论。
其一,汲古阁单行本《史记索隐》的刻印与流传。汲古阁单行本《史记索隐》在刻印之后,无论是其时还是现今,收藏者或者收藏单位都甚富。考察各家书目,仅称说“明末毛晋汲古阁本”。而民国一些鬻卖书目却常常有“初印本”“原刻原印”的标识。而通过目验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中所藏汲古阁单行本《史记索隐》,则可以发现这部书的所谓不同副本,在大小、纸张与印刷质量上都多有差别,尤其是从其中的书板断裂情况来看,此书绝对不止刷印过一次。而所谓初印后印的信息,不见任何一家图书馆著录。因此,迫切需要对汲古阁单行本《史记索隐》的刻印与流传情况详加研究,厘清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区别,使现存的初印本不致于淹没于后世。
其二,汲古阁单行本《史记索隐》之后,以此汲古阁本为底本,又先后有了四库各阁本《史记索隐》、广雅书局本《史记索隐》与丛书集成本《史记索隐》。将后面产生的各本与汲古阁原本《史记索隐》进行通校之后,发现其中差异颇为不小。尤其是四库各阁本,目前得见的乃是文渊阁、文津阁与文澜阁,首先三者之间就优劣不侔,其次馆臣对据以清抄的汲古阁底本进行了大量的改动。而对于此数种汲古阁本之后的单行本《史记索隐》,除过在介绍版本时简单提及外,尚未有人进行系统的校勘与研究。
其三,留存至今的汲古阁《史记索隐》,在《中国古籍总目》里著录有五个批校本,北京国图三部,上海图书馆一部,复旦一部。这五个批校本如今都被收藏单位作为善本珍藏。观过之后,也发现不少问题,很值得进一步探究,同时对后世学者对《史记索隐》批校内容的研究,也可以辅助研究此学者的学术思想与学术经历。
其四,上述诸学者在研究《史记索隐》内容时,大都忽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司马贞为《史记》每一篇所创作的《述赞》。司马贞以四言诗的形式为《史记》每一篇作赞,将其从史书中抽离,其实可以看做是一组针对《史记》而作的咏史组诗。然而仔细阅读司马贞之《述赞》则会发现,司马贞在作此《述赞》时的取材并不局限于《史记》本身,《史记索隐》在为《史记》作注时,常常会有史事的补充,而《述赞》当中就有对司马贞自己所补内容的吟咏,从而也可以体现出其补史之思想。通过对司马贞《述赞》的研究,可以从史学与文学等多方面对司马贞其人有更深入的理解,因此也很值得学界关注。
《史记索隐》一书在承载了司马贞补史的思想的同时,彰显着唐代恢弘历史背景下自由的学术气息。解读《史记索隐》,不仅可以体味太史公的微言大义,更重要的是能体会后人在《史记》上留下的强烈的主观色彩与时代印记。期待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关注《史记索隐》,更深入地研究《史记索隐》,从而进一步完善《史记》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