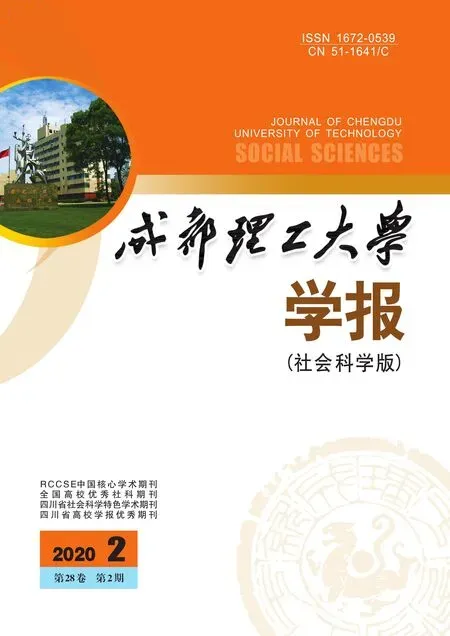苏辙《诗集传》中的心性之学
刘 茜
(深圳大学 饶宗颐文化研究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北宋初年,“心性”之学逐渐兴起,经学开始出现义理化趋向。这一思潮也影响到了宋代《诗经》学的发展。苏辙的《诗集传》蕴含了丰富的“心性”思想,显示了宋代《诗经》学的义理化特征。
一、 《诗集传》解诗所蕴含的心性思想
苏辙《诗集传》在对《桧风·鸤鸠》《卫风·淇奥》《小雅·小宛》《大雅·旱麓》等篇的疏释中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心性”思想。首先,苏辙认为“人性”即“仁性”,具有德善具足的特点,是人达到君子理想人格所应具备的条件。苏辙《诗集传》注《淇奥》曰:“君子平居所以自修者亦至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日夜去恶迁善,以求全其性。”[1]309此句是说,君子应不断修行,去恶迁善,以求保全自己的本性。可见,在苏辙看来,人的本性应是尽善无恶的。又《诗集传》注《小雅·小宛》云:“君子之不为不义,出于其性,犹窃脂之不食粟,虽欲食而不可得也。特以其居于乱世,而填尽寡弱无以行赂,则其陷于岸狱也固宜。曷不握粟而往试之?彼桑扈何自能食谷哉?”[1]436苏辙在此阐述了相同的观点。他指出,君子之所以不为不义之事并非是由外因所至,而是由君子至善之“本性”所决定的。无独有偶,苏辙《诗集传》的这种“人性尽善”观点也可在他的《论语拾遗》中得到印证。《论语拾遗》曰:“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尽也,火必有烟。土去则水无不清,薪尽则火无不明矣。人而至于不仁,则物有以害之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非不违仁也,外物之害既尽,性一而不杂,未尝不仁也。”[2]1538苏辙在此指出,“人性”即“仁性”,即便人有时会表现出不仁的方面,但这并不表明“人性”就是恶的,而是由于人在外物的影响下蒙蔽了他的“人性”,倘若去除这些外在的影响,人仍旧会恢复美好的人性。那么,人在外物的驱动下所表现出来的趋利避害的行为,又是不是“人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呢?苏辙在阐释孟子之语“天下之言性者,则故而已矣”时对此进行了回答。他指出:“所谓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故非性也。无所待之谓性,有所因之谓故。物起于外,而性作以应之,此岂所谓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谓故。方其无事也,无可而无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则性灭而故盛矣。”[2]1206苏辙指出,人的“本性”是静一恒定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会在外物的干扰下而表现出趋利避害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所谓的“故”。苏辙将“性”与“故”作了严格的区分,实际上也确立了他的“性善”本体论思想。
确立了“性善”的前提,苏辙又指出人的言行要达到君子的人格标准,做到不违“仁义”、均一恒定,就必须依靠长期的修养以保全尽善之人性。这一思想见于《诗集传》注《卫风·淇奥》中,其文曰:“君子平居所以自修者亦至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日夜去恶迁善,以求全其性,然亦不可得而见也,徒见其见于外者瑟然僴然、赫然喧然,人之见之者皆不忍忘也,是以知其积诸内者厚也。”[1]308苏辙指出,君子通过长期的修养,使日常言行不断地得到完善,旁人虽仅看到他的行为表现,但却会为他的行为所感染、不忍忘怀。原因何在呢?苏辙指出,这是因为旁人感受到这些言行并非出自于偶然,而是人在经过长期的内在修行之后,使得“人性”达到了德善具足的境界,从而外化为日常的行为,故常人虽只看到他的所作所为,却会为他的内在德性修养所感动。《诗集传》在对《桧风·鸤鸠》的注解中表述了相似的观点:“君子之于人,其均一亦如是也。仪,其见于外者,有外为一而心不然者矣。君子之一也,非独外为之,其中亦信然也,故曰:‘其仪一兮,心如结兮。’……君子之行,无不充足者,故周旋反复视之,而无不如一,譬如丝带而充之琪以耳。夫无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能一,不可得也;既已充矣,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1]376可见,在苏辙看来,“德性”是决定人之行为处事的根本前提。
既然“人性”对人的行为规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人就应当保全自己的本性,不要使“本性”在外物的影响下迷失;如果人的“本性”失落了,人也要试图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因此苏辙讲究君子要“求全其性”。那么通过怎样的方式来保全或者是恢复自己的“本性”呢?苏辙在《诗集传》中提出了渐修的主张。《诗集传》注《卫风·淇奥》曰:“君子平居所以自修者亦至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日夜去恶迁善,以求全其性,然亦不可得而见也,徒见其见于外者瑟然僴然、赫然喧然,人之见之者皆不忍忘也,是以知其积诸内者厚也。子贡问于孔子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欤?’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告之以贫而乐、富而好礼,而子贡知其自切磋琢磨得之,此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如卫武公所谓富而好礼者欤?”[1]308苏辙在此指出,要“养性”,就必须通过长期的内省与反思的过程,不断去除恶的思想与言行,代之以善的德性。只有这样,人之“本性”才能得以恢复。人如果具备了这样深厚的内在修养,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其外化于日常的行为举止之中,并深深地感染他人。孔子赞扬子贡“可与言诗”的原因,正是在于孔子感到子贡明白了要提升人的思想与精神境界,就必须通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修养工夫的道理。苏辙在《论语拾遗》中再一次论证了他的观点,其文曰:“若颜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尽去,薪未尽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违仁’矣,而未能遂以终身也。其余则土盛而薪强,水火不能胜,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颜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学未及究,其功不见于世,孔子以其心许之矣。……使颜子而无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将造次颠沛于是,何三月不违而止哉?”[2]1538苏辙认为,颜子的德性较为纯一,但不幸早亡,因此没有历经长时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修养工夫,这也使得他的德性未能达到圆满的境界。
那么是否通过长期的内省工夫就可以使自己的“性”恢复到至善的境界呢?苏辙认为还必须以“诚”贯穿于始终。《诗集传》注《淇奥》云:“《记》曰:‘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1]309苏辙指出,要使“人性”得到修养,生命因此而受到润泽,就必须去除偏邪之心,怀抱着诚心去修养。苏辙认为,诚心是洞悉道的根本。他在《诗集传》注《大雅·旱麓》中论述了这一观点,其文曰:“道在我而物无不咸得其性,鸢以之飞于上,鱼以之跃于下,而况于人乎!或曰:天之髙也,以为不可及矣,然鸢则至焉;渊之深也,以为不可入矣,然鱼则跃焉。夫鸢、鱼之能至此也,必有道矣,岂可以我之不能不信哉?君子推其诚心以御万物,虽幽明上下无不能格。小人不能知而或疑之何以异,不信鸢、鱼之能飞跃哉!《记》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1]490苏辙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运行之中必定有一个“道”存在,倘若我们洞察到了“道”的奥秘,就能明白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它的本性,且在本性的支配下运行的道理。那么如何能洞察“道”的奥秘呢?苏辙指出,必须秉着诚心来求索,只要有诚心,即使是玄奥难测的道理也可以被洞悉。
“诚”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历代儒者对它均有阐发,但各自的理解却不尽相同,苏辙的“诚”又具有怎样的内涵呢?他在《孟子解》中对这一概念作了明确的阐述,其文曰:“孟子学于子思,子思言‘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子思言‘至诚无敌于天下’,而孟子言‘不动心’与‘浩然之气’。凡孟子之说皆所以贯通于子思而已。故‘不动心’与‘浩然之气’,‘诚’之异名也。‘诚’之为言,心之所谓诚然也。心以为诚然,则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动而其气浩然无屈于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为师弟子也。子思举其端而言之,故曰‘诚’;孟子从其终而言之,故谓之‘浩然之气’。一章而三说具焉:其一论养心以致浩然之气,其次论心之所以不动,其三论君子之所以达于义。达于义所以不动心也,不动心所以致浩然之气也,三者相须而不可废。”[2]1200苏辙认为,孟子与子思在思想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孟子所谓的“不动心”与“浩然之气”即是子思所说的“诚”。只有心诚,才能做到行为的正直,只有心不为外物所动,浩然之气才不会有所折损。因此子思所谓的“诚”是孟子所谓“不动心”“浩然之气”的根本前提,而“不动心”“浩然之气”则是“诚”的必然结果。苏辙由此得出结论,人要使“浩然之气”充盈身心就要通过养心的工夫。而“浩然之气”又是达于“义”的根本途径,因此养心也是达于“义”的根本。反之,人若达于“义”之后又可以做到心不动,进而可以充盈浩然之气。因此,养心、充实浩然之气、达于义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苏辙的“诚”所具内涵是十分宽泛的,它应包含了“不动心”“充盈的浩然之气”,甚至也具有了“义”的内涵。
综上,苏辙在《诗集传》中阐发了他“人性善”的观点;而在修养途径上,苏辙则主张怀抱诚心进行长期的道德修养实践,以此保全人的尽善之本性。
二、《诗集传》对“思无邪”的“心性”学阐释
“思无邪”一语出于《诗经·鲁颂·駉》:“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骃有騢,有驔有鱼,以车袪袪。思无邪,思马斯徂。”[3]563孔子将它引来作为了对《诗》三百的总体评价,即《论语·为政》所载:“《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4]39孔子的“思无邪”学说对后世《诗经》学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深远,但对于孔子此语的具体含义却历来众说纷纭。
《诗序》解《诗经·鲁颂·駉》云:“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3]1627郑玄结合《诗序》之义,注“思无邪”云:“思遵伯禽之法,专心无复邪意也。”[3]1628可见,郑玄此处是将“思”字解为实词,把“邪”字与“专心”对立起来,因此所谓“无邪”便指专一、无二心的意思,故郑玄认为“思无邪”是指对伯禽勤政爱民政治的虔诚追随态度,其与《诗序》阐扬教化之义完全一致。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则作了这样的解释:“诗者,持也,持人之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5]55刘勰认为孔子此语之义应侧重诗教功用,“思无邪”即是指“义归无邪”。其中的“无邪”应有“正”的意思,可见刘勰基本将“思无邪”解为“义归正”的意思。
宋真宗咸平年间,邢邴为《论语》作疏,对“思无邪”作了新的注释:“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故此一句可以当之也。”[6]65邢邴明确了“思无邪”一语所指称的对象与范围,认为孔子是根据诗歌的社会效用立论。可见邢氏接受了汉儒以美刺言《诗》的观念,认为“思无邪”是指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应符合儒家伦理与政教规范。邢邴的阐释对后世影响极大。
苏辙在《诗集传》中则从“心性”之学的角度对“思无邪”作了创造性解释。《诗集传》注曰:“……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何谓也?人生而有心,心缘物则思,故事成于思,而心丧于思,无思其正也,有思其邪也。”[1]564苏辙指出,人的思考来自于心对外物的反应,但人的本心却常常因外物的影响而迷失。苏辙进而指出人心迷失的原因:倘若人在对外物进行思考的时候,使自己的思考为外物所束缚,那么他的思考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他的心也会丧失本来的面目。苏辙在此已将“思”有“邪”的说法提出,根据前后句意推断,苏辙所谓的“正”是指人处在“无思”的状态,保持着自己的“本心”。因为人的本心是德善具足的,所以人在无思的状态下,他的心思也是纯正的。与之相对,“邪”是指人在对外物进行思考的时候,心思为外物所束缚,因此而丧失了原有的纯正。由此可以推断苏辙所认为的“思无邪”应是指人在对外物进行思考的时候,其心思不为外物所束缚,仍然处于一种纯正的本初状态。
既然人不可避免地要对外物进行思考,又如何能做到“思无邪”呢?苏辙云:“有心未有无思者也,思而不留于物,则思而不失其正。”[1]564苏辙认为,只有在思考的时候,不为外物所束缚,人的心思才不会在外物的影响下丧失本来的面目。那么人又如何能做到思考外物而又不被外物所束缚呢?苏辙作出了这样的回答:“正存而邪不起,故《易》曰:‘闲邪存其诚。’此思无邪之谓也。然昔之为此诗者,则未必知此也。孔子读《诗》至此而有会于其心,是以取之,盖断章云尔。”[1]564苏辙指出,只要人保持纯正的本心,邪心就不会萌生。如何保持本心呢?苏辙指出,人必须使自己的心做到“诚”。他认为《周易》中的“闲邪存其诚”正可视作对“思无邪”的注释,所谓“闲邪存其诚”应指人的心思出现偏差与否在于他是否使自己的心做到“诚”。与此同理,人要在对外物的思考中保持自己的本心,就要使自己的心保持“诚”的状态。无独有偶,苏辙的这一思想在《论语拾遗》中作了更为详尽的阐释。苏辙认为,《周易》所谓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与《诗》所谓之“思无邪”之义并无二致。苏辙指出:“……惟无思,然后思无邪,有思则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圣人无思,非无思也。外无物,内无我。无我既尽,心全而不乱。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尝思,未尝为,此所谓无思无为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动,与木石为偶,而以为无思无为,则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无邪,思马斯徂。’苟思马而马应,则凡思之所及,无不应也。此所以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1]1536苏辙认为,人只有在不对外物进行思考的状态之下,才可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使自己的思考不会偏离本心所愿。这就是“思无邪”,而人一旦进行思考,他的本心与思考均会受到外物的干扰而失去本来的面目。这便是“思有邪”。圣人之所以能做到思而无邪,并不是圣人不对外物进行思考,而是圣人在思考外物的时候,能够摆脱外物的束缚和一己之偏见,做到“外无物,内无我”。如能这样,人就可以做到按照事物本身的规律去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人虽然因外物而思考,但实际又不为外物所缚。这就是“因其自然,而吾未尝思,未尝为,此所谓无思无为而思之正也”。反之,如果人在思考的时候使自己的心思为外物所束缚,那么人心也不会处于本有的纯正状态,这就是所谓的“邪”。因此人要做到“思无邪”,就必须使自己的心不被外物束缚,从而使自己的心保持“寂然不动”的状态,唯其如此,方能做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洞悉万事万物存在的奥秘。
苏辙对“思无邪”的解释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是从诗教方面而言的,但与前儒不同,苏辙更偏重于从心性学的角度对“思无邪”进行解释,这也使得此句的内涵较之前儒的解释更为丰富与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