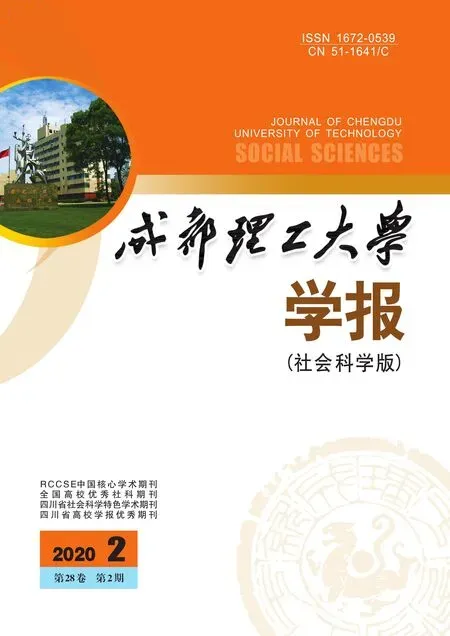骈文界定问题的再审视
陈 果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一、引言
随着近三十年来学界对骈文投入更多关注,骈文研究在形式特征、发展脉络、思想理论、文体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突破,但一路向前的同时溯源回顾,怎样的文章可以算作骈文——关于骈文的界定仍然莫衷一是,留有很大的讨论余地。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关系到对骈文产生于何时的认识,认定的标准不一则最后的见解也必然不同。
纵观诸学者骈文专著或论文,绝大多数都视对偶、用典、藻饰、声律为骈文的主要特征,或表述有别而意思无差,由此有论者通过这些特征界定骈文,如提出骈文是“一种主要由偶句(又以四六为习见)构成、多用典故和华丽辞藻、有一定音律要求的文体”[1]“骈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特有的一种主要由对偶句构成,具有对仗、用典、声韵、藻饰等四大修辞形态的与散文相对的形式华美的文体”[2]等,亦有论者认为“界定魏晋时期的文章是否为骈文,应把对偶、四字句、六字句视为核心因素,其他作为从属条件。界定刘宋时期的文章,则应在前期的标准上加上用典作为主要标准。界定齐梁时期及其以后的文章,则应再把声律要求上”[3]。那么,以骈文的形式特征去界定骈文是否合适呢?笔者认为,将骈文的形式特征与骈文的界定等同,或者引骈文特征给其下定义值得商榷,在此基础上结合前贤之论,提出关于骈文界定问题的一些思考。
二、骈文的界定应坚持“对偶”本位
《说文解字》对“骈”的释义是:“骈,驾二马也。从马,并声。”[4]465段玉裁注:“併马谓之俪驾,亦谓之骈……骈之引申,凡二物并曰骈。”[4]465骈文突出的是“骈”字,作为骈文的首要特征,对偶从一种修辞方式上升为一种文体组织形式。虽然骈文名称及理论的出现滞后于骈文创作,骈文之名正式确立已是清代,但后世至今均以此为名进而逐渐统一,可见“对偶”作为骈文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得到广泛的承认与接受。早期文章的骈化可能只有对偶这一项明显的特征,其他所用极少甚至根本没有,但此时已可以将之称为骈文。即使是“动态界定”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也只瞻前,并未顾后,因为倘若界定骈文需加上其他形式特征,则会随之带来如下相应针对性的问题。
(一)如加用典为界定标准
在隶事之风盛行下,用典与对偶走到时代的交汇点上,共同成为六朝骈文鲜明的要素。但这一时期的骈文不是篇篇见典,如《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这样的短文佳作,皆不用典,自然成对。再有后代四六名篇也并非均以六朝为范,北宋“欧苏新四六”既有骈文之美又有古文之气,一些篇目不用或极少用典故,这些对偶的文章是否属于骈文呢?
(二)如加藻饰为界定标准
谢无量先生《骈文体格及变迁论》言:“骈体至齐梁而盛,齐梁以前,行文已重偶辞,而声律未精,惟其比对姿势,多有可观耳。《文心雕龙》谓丽辞导源仲尼,要及骚赋既兴以后,文章始务以华藻为工。盖承战国之诙嘲,挟西京之闳丽,然后骈文之体格生焉。”[5]193但这只是齐梁时期骈文的“体格”,并非后世骈文均延此路线,刻意雕饰形成的浮华之风即使在当时也有批评之音。后世作文严格遵循对偶却无藻饰者多有,如盛唐时期“燕许大手笔”,尤其是其公牍文纯属白描,不事雕饰,质朴明快,已经体现出骈文散体化倾向,这些对偶的文章是否属于骈文呢?
(三)如加声律为界定标准
骈文分为有韵骈文和无韵骈文两类,谭家健先生指出:“书启、序记、论说、章表,通常可以不用韵。赞颂、铭诔、吊祭、檄移、则多用韵。凡用韵者均可自由换韵,无须一韵到底,而且不限韵,赋亦如此(只有唐以后的律赋限入韵)。”[6]24且不说齐梁以前的对偶文没有声律要求,齐梁时期的声调也只是初创,运用于骈文并不严格,后世也并未严守。那些无韵,且不求平仄的对偶文是否属于骈文呢?
以上所提及的几种情况,恐怕很难被排除在骈文的范畴之外,莫道才指出:“作为判断骈文的依据,它们最多只是从属的条件”[7]。在笔者看来,或许也不应算作从属条件,因为它们并不属于整个骈文发展过程都具备的条件性特征。大抵自陆机之后骈文由发展迈向成熟,而对偶、用典、藻饰、声律兼备的“徐庾”将骈文推向繁荣期,那“徐庾”之后的历代创作中这些特征不全具备的骈文则只能算是“成熟之后的不成熟”或者“鼎盛之后的倒退”吗?恐怕不能,而应将之视作“新变”。因而这四项特征只是在骈文极盛时期(尤其是齐梁声律由诗应用于骈文之后)才同时并且集中出现,共同推动“六代之骈语”成为“一代之文学”。
如果对偶是骈文这条大河的干流,那用典、藻饰和声律就是汇入其中的支流,为其陆续注入活水:用典“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8]614,藻饰“孚甲新意,雕画奇辞”[8]514,声律使“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9]。以对偶为中心的骈文在发展过程中将用典、藻饰、声律三种修辞形态纳入,是因为通过这些修辞分别增强了骈文的论证功能,描写功能与朗读功能。以用典为例,笔者认为六朝骈文对偶与用典的搭配组合存在着密切的双向互动关系,即“引入典故充实对偶句式的内容,对偶句式的灵活使得典故的表现手法多样,二者之间的互动是在内容与形式上为对方提供便利”[10]。
莫山洪先生指出骈文的核心特点是“形式的华美”,而“这种华美主要是由它的修辞形态所带来的,是外在的美和内在的美的结合”[2]。或可据此引申:骈文“内在的美”在于对偶,其中包含汉字的特殊性,汉语语法结构的灵活,古代阴阳对举、物生有两的审美理想等各种文化意蕴;外在的美在于对偶之外用典、藻饰、声律所带来的附加的美。“盖虽有闳文丽藻,音调则前后参差,隶事则上下不切,此未足为美也。”[5]172若把谢无量先生的话反过来说,即使不加其他修辞,仅对偶已经使文章具有美感,如再恰当用典,注重辞藻,追求音律,则会使骈文的美感进一步增强。
近人瞿兑之对于骈文中平铺直叙,不假雕饰,追求平易通畅的文章提出:“白描骈文”的概念,谭家健先生进而指出:“白描骈文并不是骈文的幼稚阶段或通俗化形式,它代表华丽之外的另一种美学追求,不仅魏晋有,南北朝、隋唐也有,中唐的陆贽可归入此类,宋四六中有白描派,但也有华丽派”。[6]101这种说法是颇有见地的。而四者多备甚至兼具,达到“内外兼修”的“形式的美”在六朝乃至初唐时期最为凸显,因为这一时期的骈文文字运用技巧最为成熟,骈文的体裁应用也最为普遍,赵义山、李修生《中国分体文学史》就将南北朝骈文的繁荣总结为四个方面:(一)骈文风行,无所不施;(二)名家辈出,高手如林;(三)名作迭见,云蒸霞蔚;(四)情文并茂,各具风姿[11]。
因此,我们可以说某篇骈文具有如“用典繁密”“辞藻华美”“平仄和谐”等某些特征,但不宜以对偶之外的特征去倒推界定。数学定理中有“充要条件”之关系,引而述之则四种修辞形态便是骈文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即具备这四种修辞形态的文章一定是骈文,但反过来说骈文却并不需要完全具有这四项,其中只有对偶是骈文所必须具备的。
三、关于对偶的几个问题
在确立对偶之于骈文界定的核心地位后,笔者想进一步进行探讨,认为骈文界定问题的重点并非在于是否纳入用典、藻饰、声律这些形态特征,而应该将问题引向对偶本身来讨论,其中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偶句是否以四六句式为主才算骈文
前文之所以未提句式,是因为句式归根结底还是关于对偶的句式,句式问题属于对偶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并不应与其他修辞特征并列。虽然到了唐代柳宗元《乞巧文》才见“骈四俪六,锦心绣口”之说,从而使得“四六”与骈文联系更加紧密,但《文心雕龙·章句》早已提及“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常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8]571,四字句和六字句不促不缓,节奏上相间互补,因而在南北朝便已作为骈文最常态化的句式,似乎可为标准。但南北朝时期对偶也存在七言“诗化”倾向,再如宋代骈文中对偶多见长句,这种对偶句式所带来的不同增强了骈文的节奏变化。张仁青先生《中国骈文发展史》言:“世多以宋人之骈语为四六,而以骈文专属之南北朝文。实则二者之主要区别,在骈文较自由,四六更工整,骈文不必尽为四六句,而四六文实为骈俪之文无疑。”[12]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各种体裁的骈文,四六句式都在文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但在种属关系下四六句式并不能够作为骈文的界定标准。
(二)对偶句应至少占全文多少比例
对偶是文人长期创作实践所形成的修辞方式,并无特定属性,因而在骈文和散文里俱可使用。莫道才定义骈文是“基本由对偶的文辞组成的文章”[7],这个说法是符合问题走向的,但此处“基本”显得较为模糊。既然对偶骈散皆有,文章可以骈散互参,那么是“骈中带散”还是“散中带骈”,区别可能就在于二者的比例问题,对偶句数的比例要如何规定才能算是骈文呢?
魏晋以前甚至早至先秦时期的文章中就已出现对偶,但至多不过零星几句,且非前人有意为之,故有骈句而无骈文。李蹊以一半为标准提出:“从数量上看,假如一篇文章的偶句没有达到全文句子的一半,就不能算是骈体文。”[13]225-226莫道才《骈文通论》谈到:“一般来说,夹用散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通篇骈句带来的文气不畅。因此,散句的使用是有限的,一般不超过全篇的四分之一,否则,就很难说是骈文了。”[14]似乎是将对偶句数认定在全文四分之三以上。于景祥则认为:“骈文中除了每段的发句、收句,以及段中的连接句、补足句可以用一至数句散行之外,通篇都以字句相对、平仄调和为准则。”[15]1进一步将散句限制在更小的使用范围内。关于对偶比例应为多少看法不一,底线为一半的标准是最起码的,笔者也较为认可,比例上的量化似乎是需要的,但确定怎样一个具体的数值标准终究是一个并不好把握的问题。
(三)对偶句是否应以工对为标准
对偶不仅是从“量”上去衡量,可能更需要从“质”上去把关。李蹊提出是否为骈文应有三条标准:“一是看偶句的数量,二是看偶句的质量。”[13]225“如果一篇文章具备了上述两条要求,但是不讲究藻饰,仍然不能算是骈体文。”[13]226偶句数量和藻饰问题前文已有论述,笔者赞同从“质”“量”两方面来看,但不太认可“质”是指“偶句的结构形式,看偶句是否讲究藻饰”[13]225,而认为“质”应着重体现在对仗是否工整。对仗有工对(或称严对)与宽对之分,谭家健指出:“早期的骈文只要求大体相对即可,南北朝以后越来越严格。能够字字相对,谓之工对。仅仅大体相对,谓之宽对。”[6]18工对要求上下两句的结构、词性都需相同,褚斌杰说:“古人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术语,但他们实际上是本着这样的语法结构和词性来做的。”[16]163严格遵循这样的规则写出来的句子当然是骈句,但如果仅仅是意义相对,词性、结构有异,恐怕连对偶本身所具有的形式美也会大打折扣。
对偶的类型可以分很多种,最早《文心雕龙》里就简要分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四种,再如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里列二十九种之多,虽为论诗,于文亦可。今人亦有详述,以莫道才《骈文通论》的对偶分类为例:从语言句法的表面形式可分4种;从语言词法形式可分5种;从音韵技巧上可分3种;从描写角度可分4种。当然由于划分角度不同,必然也存在既属此种又属彼种的情况,但不管如何划分,都应当首先建立在词性与结构上下相对应的基础上。我们从《六朝文絜》中随取一篇短文,以简文帝萧纲《与刘孝绰书》为例甄别:
执别灞、浐,嗣音阻阔,合璧不停,旋灰屡徙。玉霜夜下,旅雁晨飞。想凉燠得宜,时候无爽。既官寺务烦,簿领殷凑,等张释之条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龙之才本传,灵蛇之誉自高。颇得暇逸于篇章,从容于文讽。
顷拥旄西迈,载离寒暑,晓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鸟归林,悬孤帆而未息。足使边心愤薄,乡思邅回,但离阔已久,戴劳寤寐。伫闻还驿,以慰相思。[17]
将虚词、衬字除外,文中只有带点的句子可以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对偶句(其中“晓河未落”与“夕鸟归林”严格意义上也只是同为主谓结构,词性从严讲也并不算完全相对)。在对偶句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看对偶句的比例,但也需要注重怎样的上下句可以被归为对偶,莫道才提出“骈文的对偶一般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字数的基本相等;(二)意义的基本对举;(三)词性的基本对称;(四)结构的基本对应”[7]。也许去掉这些“基本”,以工对为标准才最为契合对偶本质。偶见有论者在涉及骈文举例时误举,易将个别看似字数相等实则上下并不相对的句子划入其中,使对偶句数比例扩大,一些可能并不能算作骈文的文章被归为其列讨论。
四、骈文与辞赋之关系
辞赋属不属于骈文?钟涛认为把辞赋列入骈文研究“表面上对探寻骈文本源与流变似乎不无方便之处,而实际上却是混淆了辞赋,骈文各自的源流”[18]。辞赋就其体裁来源于诗,所谓“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8]134,辞赋当然与骈文不同,问题的着眼点在于辞赋中的骈赋属不属于骈文?此题争论颇多,较为中和的一种观点是骈文与辞赋二者存在交叉关系,即辞赋中只有骈赋属于骈文范畴。谭家健先生对此问题的看法比较清晰:“辞赋与骈文是并存的两种文体,各自有其独具的特色和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在古代文体分类中,赋从来都是自成一家。在当代赋学研究著作中,辞赋并不隶属于骈文,骈文亦不被视为赋体。二者有交叉关系,那就是六朝骈赋。至于汉晋大赋和抒情小赋,唐之律赋,宋之文赋,都不宜算作骈文。”[6]5将骈文的外延扩大到骈赋,这个问题还存在补充论述的空间,笔者试着进一步梳理两个层面的关系。
(一)辞赋与骈文并不属于同一文体分类体系
我们需要明确:赋是一种产生早于骈文的独立文体,但骈文并不是“独立”的。褚斌杰先生归纳得好:“骈体文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它是从古代文学中的一种修辞手法逐渐发展形成的。从实地看,它并不与诗歌、辞赋、小说、戏曲等一样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与散体文相区别的一种不同表达方式。但由于它本身具有一定的格式和特点,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所以一般地也都把它看做是中国文学中的一种体类。”[16]146在这里提到了“体裁”和“体类”两个概念,我认为二者同属“文体”的下层概念,将骈文归为“体类”是十分合适的,骈文并不是具体的某一种“体裁”而是一种“体类”,与“散”相对,一种文学“体裁”既可以用骈文来写,也可以用散文来写。骈文与辞赋并不是同一个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标准,它是从语言修辞角度划分出的文体概念,具有独特的包容性,语言修辞上的“骈化”可以覆盖的是从文学体裁角度所划分出的各种文体,而辞赋的骈化甚至远早于诗和其他体裁,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云:“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19]赋跟其他诸如章表奏议、铭檄序启一样,是可骈可散的文体。或有“骈赋押韵,骈文不押韵”的观点,解释以来道理亦如是,骈文之中也有颂赞铭箴等文体与赋一样押韵。于景祥说:“魏晋六朝之赋则多为骈文之一体,也可以说是地道的骈体文。”[15]78骈赋属于骈文从文体分类上是可以说通的。
(二)骈赋分别符合“骈”与“文”的范畴
我们将骈文二字拆开来看,首先“骈”的要求骈赋毋庸置疑是符合的,问题在于另一个字“文”。《说文》对“文”的解释是“文,错画也,象交文”[4]425,视文章为“文”的标准是有文采,那么作为“古诗之流也”的“赋”可以算入“文”的范畴吗?褚斌杰认为,赋体“是属于一种半诗半文的文学体裁”[16]150,并指出汉赋中一些散中带骈的现象对于骈文已是一种胎息微萌的状态。汉赋与文实则并无严格的界限,有些虽以赋为名,内容和形式已不符“古诗之流”,亦有些虽用赋体却不以赋称。《汉书·兒宽传》载:“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20]似乎在班固时期史传,赋已可被视为“文章”。从古代“文”的观念来看,魏晋以后文学进入“自觉时代”,文体分类意识逐渐形成:曹丕《典论·论文》中认为属于“文”范畴的文体有八种,陆机《文赋》扩为十体,挚虞《文章流别集》所留存十一类,《文心雕龙》涉及文体大类三十四类(如果算上“骚体”),《昭明文选》收录文体三十九类,唐宋以后则越分越细,可见中国古代的“文”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概念,而其中“赋”均是重要一体。许梿《六朝文絜》、王先谦《骈文类纂》等骈文选本收录骈赋,孙梅《四六丛话》等也将骈赋纳入骈文理论体系中谈论。姜书阁说:“由于汉、魏之际,骈文已经形成了,赋已进入骈赋(俳赋)时期,在文章体制上,二者几乎合流;或者说,从此以后,二者的发展是同步的,故密切相关,互为影响。因此,在论述某一个个别作家时,即不再分文与赋为两类,而概以骈体文章视之。”[21]随着对“文”的概念的不断认识,“文”的外延扩大,赋属于文章自可“从宽处理”而不拘泥,骈赋也就同时符合“骈”与“文”的范畴。
五、结语
综上,我们从骈文的修辞形态,对偶内部特征,骈文与辞赋之关系三个方面讨论了骈文的界定问题。倘若工对句数超过全文总句数一半以上且其中句式多以四六为主,兼具用典、藻饰、声律的文章是最为标准和成熟的骈文,那么是否可以认定:包括骈赋在内,工对句至少超过一半的文章可以称作骈文。这里首先抛却了用典、藻饰、声律等其他修辞形态,确立了对偶本位;其次规定了对偶的工对标准与基本比例;最后还需强调是“文章”而排除诗与对联。总的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骈文的界定,但宽中仍存有严,即对偶中的工对标准。以对偶为本位界定骈文,笔者略陈管见,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