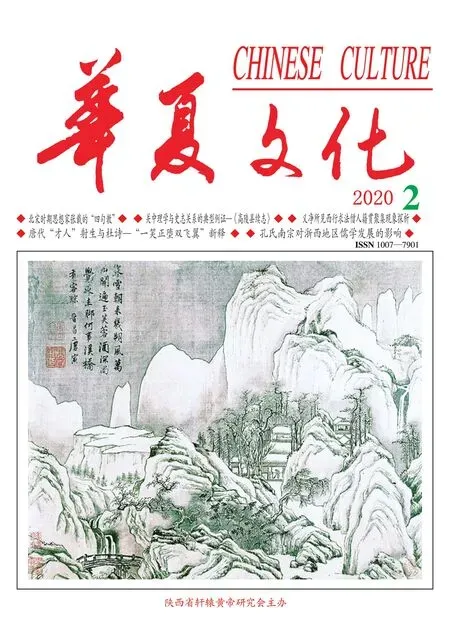经学大义与文化意蕴
——《关雎》的文化解读
□冉 苒
在中国诗歌的长河里,《诗经》不仅是最早的,而且也是最特殊的诗歌。“诗三百”不仅仅是盛开在文学花园里的奇葩,还是根植在伦理道德土壤中的药草。如“关关雎鸠”,传诗的毛公释“关关”为“和声”,暗拟男女情投意合。但千百年来,学者们对此的阐释从来都不是“和声”一片,罕有“情投意合”者,《关雎》的主旨之争更是众说纷纭。本文拟从名物角度,结合周代文化现象和儒学思想,探寻《关雎》作为“纲纪之首,王教之端”的言说进路,从中得出结论,那些把《关雎》当作民间恋曲、婚庆礼歌的解读行为,都是在“矮化”《诗经》这部文学元典。
一、《关雎》唱给谁人听
孔子在《论语》里多次对学生们谈到学《诗》的重要性,其中对《关雎》的评价最具体,赞赏溢于言表,其重视之心远超其他作品。
《论语·八佾》中,孔子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诠释《关雎》。《论语·子罕》中,孔子又赞赏《关雎》声乐上的美妙盛大:“《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聆听《关雎》这样“正”而“和”的音乐,耳朵里都是美妙又响亮的声音。
那么,春秋时期的乐工会在什么样的时间与场合吟唱《关雎》呢?
1、《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云:“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尽管没有提及具体篇名,但作为《周南》之首,季札“美哉”的赞美声中必定有《关雎》的一席之地。
2、《仪礼·乡饮酒礼》云:“乃合乐《周南》:《关睢》、《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为周代诸侯管理地方的乡大夫招待乡人耆老会举行聚会宴饮,目的是替天子举贤荐能,倡导尊长敬老社会风气。乡饮酒礼是其中的礼仪流程。
3、《仪礼·燕礼》云:“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燕礼是天子或诸侯犒劳有功之臣、聘请贵宾、宴享群臣时举行的宴会,目的是明君臣上下相尊之义。
4、《仪礼·乡射礼》云:“乃合乐。《周南》:《关睢》、《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繁》、《采蘋》。”乡射礼盛行于先秦,目的是司礼乐、观盛德、正志行。
举行以上这些典礼的场所通常在宗庙、燕寝、大学、乡学。宗庙是祭祀祖先、布政、朝见的地方。寝,是天子、诸侯的居所。大学,是古代的学宫,除供国子学习以外,也是集会、行礼、习射之所。乡饮酒礼、乡射礼则于乡学中举行。
根据这些古代文献的记载,演奏《关雎》的场合不是在贵族们的聚会上,就是在天子或诸侯的宴会里。以周公为代表的上层贵族们,他们制礼作乐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能让听者从中观德悟道。如果没有义理层面的把握,诗礼乐便只是“术”而已。诗礼乐仅仅停留在娱乐表层,那就是引导君王贵族滑向沉溺享乐危险边缘的靡靡之音,是孔子所反对和唾弃的“郑声”。因此,如果说《关雎》在原初时代曾是个人情志的产物,那么当它被纳入王室贵族的礼仪系统后,它的民间身份就已自动退隐丧失,在“王官之学”的新标签下,曾经直白的私情密语也就被集体道德意志不可逆转地改写成深远的微言大义。
《关雎》言德,《关雎》之德又为何物?仅有汉一代,便有齐鲁韩毛四家不同的解读。
《汉书》记载习齐诗的匡衡向皇帝上疏:“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
《后汉书》记载熹平元年,青蛇见御坐,灵帝问以杨赐,杨赐有“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之语。唐章怀太子李贤注曰:“《音义》曰:‘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此事见《鲁诗》’。”
《后汉书·明帝纪》记载天有日食,明帝引咎诏曰:“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李贤注引薛君《韩诗章句》:“诗人言睢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睢》,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这是韩诗的说法。
《毛诗序》云:“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前三家为今文学家解《关雎》,以周康王晏起讽刺君后失德,但这种以古史渗透的方法建构起来的言说教化模式弊大于利。因为,史实性的解释或具体视域化的场景还原,虽然强化了教化的指向功能,但也窄化和折损了诗篇中的义理,消解了文本的美学义蕴。
相比之下,从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到上博简里战国儒者的“关雎之改”、“以色喻于礼”,进而发展到汉古文学家的“而无伤善之心”的“后妃之德”,这样疏朗开阔的释义,反倒显现了先秦儒家以及毛公解诗的高明之处。他们不仅没有落入摈弃情欲的宗教禁欲主义陷阱里,反而把观念、情感以及仪式(礼)的引导,安放在日常生活的伦理和心理系统之中,在正常的人类情感的基础之上,首肯人欲的正当性,强调只要对欲求进行合理的引导,情理便能圆融合一,从而实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这样的解诗,义理上才是精微而准确的。
通过以上分析,《关雎》究竟是讽刺失德还是赞美美德,汉儒们显然有不同的阅读视角,但在《关雎》言德,而且言说的是以后夫人为代表的周代贵族妇女群体的品德,这一点上意见是空前一致的。所以,《关雎》才会成为贵族在聚会时观乐学礼的重要曲目。
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文化定位
《礼记·昏义》:“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夫妇之义”为何在此反复出现,它又代表了什么意涵?先秦古诗文中,“义”与“仪”意义相同。《诗经·大雅·文王》云:“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这里的“义”和“仪”均指文王制定的准则。由此可见,义的观念里隐含着约束力。《国语·鲁语下》中有“咨义为度”一语,这里又显示出义具有社会行为价值尺度的作用。符合义的,就是美和善。清代学者段玉裁也注意到《毛传》将诗经中的《文王》、《我将》中的“义”释为“善”,进也而将“义”训诂为“与美、善同义”。
周代贵族的婚姻倡导“同姓不婚”,夫妇之间由于没有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因此双方必须在道德的约束下形成约定,维持一夫一妻制,维持双方家族以及政治集团的利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夫妇之义的评判标准是由社会共同体约定俗成而来的,因此“义”又引申出“约定”的意思。
在先秦儒家眼里,贵族婚姻从来都不是男女之间的私事,而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大事,它决定着家庭兴衰,维系着家族绵延,影响着社会风气。婚姻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伦理意义,是“万伦之始”,是“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所以显得极为严肃而又十分重要。对于君王尤其如此,后宫坤宁祥和,方能安心治国理政,造福百姓苍生。
为什么夫妇之义如此重要?因为夫妇关系是父子关系形成的基础;其他社会关系如兄弟、婆媳、妯娌等等,均是由夫妇关系产生的。夫妇关系不稳,其他家庭关系必然不健全,甚至地动山摇,分崩离析。为了稳定与和谐夫妇关系,必须建立起协调夫妇关系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从而保障整个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当然,更为长远的目的在于稳固宗族以及背后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
由此看出,在西周贵族集团“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婚姻制度下,夫妇双方绝对不是因为爱情而走到一起的。因此,《关雎》绝对不是男子对美女一见钟情的还原,也不是对浓烈爱情企慕的吟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展示的内在意蕴就是匹配与相和,这正是那个时代里夫妇之义的真正答案,也是那个时代贵族择偶的社会标准。
与社会其他家庭相比,后妃是否“匹配”帝王,对国家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可以说是国之根本。《史记·外戚世家》:“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
通过对夏商周三代得失的陈述,司马迁论证了天子夫妻关系对国家治乱的影响,阐明夫妇是人道里最重大的伦常关系。婚姻,特别是王族婚姻,不可不慎。因为天子与后妃,乃天下夫妇的垂范,他们各修男教女顺,内外协调,使民众因之而风化,让一国上下有序,这就是王道教化,是为世间男女爱欲立法,因此王室婚姻必须符合道德,必须怀着谨敬的心情而兢兢以待。
考察典籍我们发现,春秋时期上层贵族女子的教育分为婚前和嫁后两个时期。订婚前的情形在《礼记·内则》中有记载:“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贵族女子十岁起便不再轻易外出,幽居深院,由保傅姆教习礼仪,勤学女红女功。根据这个礼制,把《关雎》解释为君子在河边遇到采集荇菜的漂亮未婚贵族女子,无疑是不通的。能让君子随随便便邂逅的她,肯定不是“淑女”,而是《汉广》里的“游女”。
订婚后夫婿亲迎前,贵族女子还有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婚前“强化教育”。《礼记·昏义》:“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祢未毁,教于公宫,祖祢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芼之以苹藻,所以成妇顺也。”意思是说,出嫁前的三个月,女子由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如果女子与国君是五服以内的亲属,就到国君的祖庙里“上课”;如果已经出了五服,就在大宗子的家里。教成以后举行祭祀,向祖先禀告。祭时用鱼作俎实,用苹、藻这两种水草作羹菜,这些祭品都属于阴性一类,可以用来表示妇人的顺从。
夫婿亲迎,女子入夫家后,称之为初昏。这时并不会立即与丈夫行合卺之礼,而是接受长达三个月的婚后教育。完成后,会举行一个叫“庙见”的仪式,祭拜夫家祖先,祝官向先祖汇报“来妇”消息,男女双方才可同房合卺,正式成为夫妇。
《礼记·曾子问》中,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女儿别家而嫁,可谓骨肉分离,父母思念不已,无法安眠,所以“三夜不息烛”;夫家娶新妇承接香火,代表母亲年老力衰、家中地位要被替代,儿子心里得为此而哀戚,所以“三日不举乐”。这和今日婚礼之热闹、铺张的场面截然相反。《礼记·郊特牲》曰:“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婚礼不贺,人之序也。”乐是阳气,阳是动散,如果用乐,便会令新娘意志动摇涣散。不用乐,可使新娘深思阴静之义,以修妇道。“序”,就是“代”的意思。人之代,就是指人世的新陈代谢。儒家认为,子女长大成人,父母年老衰颓。这有什么值得庆贺呢?又怎么忍心庆贺呢?因此,《关雎》所描述的琴瑟、钟鼓之乐场景,根本不会发生在婚礼之中,更符合发生在三个月后于夫家举行了庙见祢祖礼仪之后。
庙见祢祖是怎么进行的?《仪礼·士昏礼》中有详细的描述:“若舅姑既没,妇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庙奥,东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妇盥于门外。妇执□菜,祝帅妇以入。祝告,称妇之姓,曰:‘某氏来妇,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妇拜扱地,坐奠菜于几东席上,还,又拜如初。妇降堂,取□菜,入,祝曰:‘某氏来妇,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礼。妇出,祝阖牖户。老醴妇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妇之礼。婿飨妇送者丈夫、妇人,如舅姑飨礼。”郑玄注:“某氏者,齐女则谓姜氏,鲁女则曰姬氏。”
没有经过“庙见”仪式的女性,不会得到夫家在家族关系上的认可。《礼记·曾子问》:“女未庙见而死,则如之何?”孔子曰:“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可见,未等到庙见礼仪举行就死去的女性,不会被葬在夫家墓地,必须归葬于娘家,即使她已经在夫家居住了一段时间,但依然不算是夫家家庭成员。
《左传》中还记录了一个“未经庙见”的故事,可以佐证西周贵族婚姻中“庙见”的重要性。《左传·隐公八年》:“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鍼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隐公八年,郑公子忽迎娶陈侯之女妫氏,由于“先配而后祖”,也就是说两人先同房了,才去祭拜祖庙。送嫁的陈国大夫鍼子看到这种情形,指责道:“这不能算是夫妇。欺骗祖先,不合礼法,怎么能够繁育子孙呢?”
女性嫁入夫家,三个月不能与夫同居合卺,这种礼俗对于今人来说有些难以理解,甚至觉得不近人情。但对于刚刚摆脱原始血缘团体,建立宗族组织架构的西周贵族统治集团来说,却是合理而又男女双方必须遵守的习俗。这项习俗的根据何在?历代学者提供了各种答案,其中以“验贞说”比较合理。《公羊传·成公九年》何休注:“古者妇入三月而后庙见称妇,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必三月者,取一时足以别贞信。贞信著,然后成妇礼。”这也就是说,庙见之礼的目的在于检验新娘是否贞洁,是否有过婚前性行为。不过,这个答案并不准确,虽然已经足够接近真相。
西周春秋时期,统治阶级之间的联姻,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需求,即所谓的厚远附别,从而壮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女人的贞洁,并不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庙见之礼的真正目的,是检查新娘是否怀有别人的孩子,以确保她日后出生的子女具有夫家纯正的血统。因为上层贵族之间的婚姻多发生在宗族、国家之间,婚前慎重考察总比婚后随意出妻更有利于维护政治关系,于是“庙见”成了男女双方家族都能接受的礼制。
根据“庙见”之礼,我们再来理解《关雎》中的“在河之洲”以及“窈窕淑女”,便觉得义理上毫无窒碍。“河之洲”似乎正是隐喻新娘入夫家三个月来所居之所。“窈窕”,《毛传》释为“幽闲也”。《荀子·王制》:“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唐代学者杨倞注:“幽,深也。闲,隔也。”经受过“深隔幽居”考验的淑女才能被冠之以“窈窕”一词,唯有如此方能成为“君子好逑”。
清代刘寿曾是持庙见之说的学者,他在《昏礼重别论对驳义》中认为:《关雎》四言“窈窕淑女”,明其行祭之前尚未成婚;其特言“君子好逑”,明其行祭之后可以配匹。行祭,正是通过“验贞”的标志,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验明无孕在身。
最近,安徽大学公布了“安大简”《诗经》,其中《关雎》的“窈窕淑女”作“要翟淑女”。“要”是“腰”的本字,“翟”亦为“嬥”。《说文》:“嬥,直好貌,一曰娆也。”于是,众多媒体显得很兴奋,大呼“背了两千多年的《关雎》背错了”,淑女“身材苗条”说又添出土铁证,毛公的“幽闲贞专”说如何能够再讲得下去?
其实,稍有古文常识的人便知:叠韵连绵词,往往意思比较抽象,表示事物状态或者主观感受,记录叠韵连绵词的多是记音符号,比如“望洋”就有“望阳”、“望羊”、“望佯”等写法,具体到“窈窕”,除了“要翟”、还有“茭芍”(马王堆《五行》帛书)等写法。“窈窕”在历代诗歌里还有写成“窅窱”等10多种字形的,但读音均叠韵连绵,意思也一样。因此,毛诗所持的《关雎》“后妃之德”说,逻辑上依然自洽。
三、“参差荇菜”的祭祀文化背景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国家只有两件重大事务,就是祭祀祖宗神灵与军事战争。繁复的礼仪、揖让进退的仪容、形形色色的礼器,祭祀之礼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道德情感和现实作用?
清代学者孙希旦认为,冠、昏、宾客之礼,是“先有其事于外,而后以我之心应之”,而祭祀之礼则是“乃由思亲之心先动于中,而后奉之以礼”。从这种主观性上来说,祭祀礼仪是宗族活动中最切近人情、最能表现人的精神品质和精神需求的形式。除此之外,它也起到了客观现实作用。周代贵族集团在政权结构中的尊卑,宗族成员在血缘关系中的亲疏,是靠祭祀形式巧妙地将等级秩序情理化、法定化以及制度化的。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关雎》中的这一系列动作,展开了一幅“窈窕淑女”与众人采集荇菜,准备祭品拜神灵、飨祖先的生动风俗画。荇菜是很普通的常见的水生植物,但“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物虽微而能用,重要的是荐者心中有至诚之意,以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忠信之义。
《礼记·祭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祭祀之礼,不是借外物从表面上做样子,而是发自人的内心敬畏去依礼奉献祭物。所以我们在《礼记》中发现,贵族们祭祀天、地、山、川、社稷、先祖之神,用作祭品的酒浆饭食,要么是取自藉田的收获,要么是亲自采集的果蔬,只有尽己所能、亲力亲为,才能对鬼神表达最高的诚心和敬意。天子王后也概莫能外。“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以供斋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斋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连身上所穿的祭祀之服也得要象征性地去养蚕织就。
“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复杂的祭祀礼仪背后彰显的道德感情是“敬”。在漫长的历史中,“敬”逐渐演变为先秦儒家思想核心理念之一,它来源于祭祀与礼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儒家道德哲学的渊薮和根源。
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情感?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分析过康德哲学的“敬重”:“敬重”这个道德感情的特点便根本不是快乐,相反,它还带着少量的痛苦,包含着强制性的不快。因为它必须把人们的各种自私、自负压抑下去,在道德律令之前自惭形秽。另一方面又因为看到那个神圣的道德律令耸然高出于自己和自己的自然天性之上,产生一种惊叹赞羡的感情,同时由于能够强制自己、压抑利己、自私、自爱、自负而屈从于道德律令,就会感到“自己也同样高出尘表”而有一种自豪感。一方面压抑各种自私利己感情产生出不快、痛苦,同时又因之而感到自豪高尚,这样两种消极、积极相反相成的心理因素,康德认为,便构成了道德感情的特征。
儒家的“敬”与康德的“敬重”异曲同工,有着理性战胜情欲的相似斗争过程。于是,在揖让进退之际、雍容俯仰之间诞生了以“敬”为支撑的礼乐祭祀文化,它有着“痛并快乐着”的心理感受,有助于修炼人性,提升人格。这种文化生命力量之大,甚至可以让人产生“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巨大勇气。
当然,祭祀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取悦上天和先祖,希望上天和先祖能给子孙降福免灾。但中国人的至上神“上天”从来都不是西方上帝那样的人格神,而是道德神,向道德神献祭,最好的祭品不是精美的食物,而是祭祀者高尚的德行。这样的观念是在历史中形成的。
周以僻远小国取代中原大国商,以周公为代表的开国者们坚信商纣是因失德而丧失天命从而导致灭国的。殷鉴不远,所以姬氏的后代必须修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记载,周成王在训诫一个叫“胡”的诸侯时说了这番话。在天子周成王看来,上天是没有感情的,不会对任何人亲近,他只帮助有德的人。而民心也是无常的,只对仁爱的君主感恩和怀念。姬氏想要保有天下,不仅要用德行祭祀感动上天,还得用仁政来取得民众支持。这才是祭祀文化在周代流行的背后隐藏着的真实目的,它是姬氏一族对于王权易失所持有的惴惴不安的复杂心情,并通过节制自身权力,来打造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世界,以此换取国祚长久。
在制礼作乐的文化背景下,回看《关雎》,在“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的宗庙祭祀氛围中,如果一个秉承祖训,有着高尚操守的周朝贵族,在神灵与先祖面前,喋喋不休地倾述自己对美女如何“寤寐思服”、如何“辗转反侧”,如此“不敬”的言行举止,根本就是欺宗灭祖。
但诗篇中的“寤寐之思,反侧之哀”又如何解释?《毛诗序》的“进贤思贤”说反倒能合情合理地嵌入历史场景中。因为,妇有“上承宗庙、下启子孙”的重大责任,夫不得不慎重以求,夫之欲得贤女为妇,犹君之欲得贤士为臣。而女子贞专,男子慕贤,实为德性相匹。正如清代学者崔述在《读风偶识》说:“《关雎》三百篇之首,故先取一好德思贤,笃于伉俪者冠之,以为天下后世夫妇有用情者之准。”此言亦深得毛序义理精髓。
因此,《关雎》展现的是穆穆庙堂,礼乐谐配,庙见之仪,君子之思,此时此刻惟有求配德偶这样诚惶诚恐的心情,上天或先祖才会予以赞赏佑助;惟有持敬守节、发乎情止于礼的性情,《关雎》才当得起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赞。也惟有理性战胜情欲,这样情理合一的模式,《关雎》才会让人像孔子一样,在乐曲终章时心有感触而觉“洋洋乎盈耳”。
四、“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礼乐属性
《说文》释友:“同志为友。”凡是想要做番事业,想要取得成就,都离不开志同道合的“友”。所以《毛诗序》有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而成者也。”“友”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两只同一个方向的手相加,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惠而好我,携手同行”的意思。从“琴瑟友之”来看,在西周春秋时期,夫妻好合的标准也包括志向、志趣的相同。
志是什么?《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是先秦典籍中记载的中国最早的诗乐舞。葛天氏“八阕”近乎帝尧时期的“八音”,但“八阕”的名称已然含有政教和伦理的特征,可见“志”绝对不是单纯的心灵和情志,先天就含有敬天常、依地德等伦理之志。
儒家有“言志”的传统。《论语·先进》“侍坐”一节中,孔子令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弟子各言其志,通过他们的言行以观其志,从而进行道德砥砺和人格培养。孟子对“志”的阐发最为发扬蹈厉。在《孟子·公孙丑上》中,他以“夫志,气之帅也”起论,一路铺张,引出气、言、义、辞等范畴,哲学化地推论出“集义所生”、“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种道德情感“至大至刚”,强大到可以抵御外部环境的威压或利诱,可以修习和成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最高精神境界。
由此可见,“琴瑟友之”的“友”表现的不是情感上简简单单的友好态度,而是两大联姻的贵族集团对于恪守结盟道义的希望。
琴瑟钟鼓,代表礼乐。《礼记·礼器》:“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琴瑟钟鼓之乐,是用来观志道志的,是要引发人产生崇高的道德情感的。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由诗兴发的性情虽然“思无邪”,但天真自然中缺乏自控的节制之力,必须依靠“礼”来约束。而以“礼”而立的性情虽然高尚正大,但难免缺少温润之感和自然的天趣,还得依靠“乐”来养护陶冶,情理方能圆融为一体,意趣才能既葆有天真,又趋向高尚。从某种角度来说,《关雎》正是展现了这样一个“诗礼乐”教化的过程。
上博简《孔子诗论》曰:“曰:《关雎》以色喻于礼,……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好,反纳于礼,不亦能配乎?”
“色”“礼”之间,“礼”的节制作用跃然而出,就是“《关雎》之改”。“配”字,有学者解释为婚配,结合上文“庙见”的分析,我认为应当与《左传·隐公八年》“先配而后祖”的“配”字同义,是“男女交受”,是情欲的行为表现。因此,诗论此简的意思是说,知礼、重礼(“喻礼”),琴瑟之悦、钟鼓之乐(所谓好色之愿、□□□□好,其实就是指人的真情实感,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思无邪”)便有了“德音之美”。“真情”与“德音”相结合,于是“配”的情欲和礼乐所代表的道德情感圆融交合,达到了“乐”的最佳审美状态——“和”。“乐者,天地之和也。”“乐极和,礼极顺。”因此,诗文中的琴瑟钟鼓之乐、寤寐反侧之哀才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也只有这样的行为和情感,才能跳脱出单纯的男女之情。所以,《诗论》又有“《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之言,呈现的正是情理不断交战,精神迁善改恶的过程。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在《四书训义》中评论《关雎》说:“为君子宫中之治言也。”他的理由是“故用之而为弦歌,其声和也,则无蔓衍之音;其声幽也,则无凄惨之响。于以养人心之和,而辅之于正,美哉!无以加矣!先王以之移风易俗,学者以之调养心气,舍此,其谁与归?”船山诗论切中肯綮。《关雎》倘若非“治言之歌”,美“后妃之德”,如何可“诚比金石,声内宗庙”,又“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五、结语
阐释“夫妇之义”的《关雎》,成为《诗经》首篇之作,绝对不是偶然;《毛诗》所建立的“经学世界”能够在后世独存下来,也绝对不是幸运;毛传、郑笺对《诗经》经义的诠解和发明,也绝对不是异想天开。广大而精微的诗经经学体系,建构的基础虽然不是在信史之上,但有先秦流传下来的群经经义作为坚实的地基。本文对《关雎》的释读,只是在疑古与信古之间,尝试找到通往诗经经学本身的道路。尽管诗经文本缺少信史痕迹,但依然可以通过以诗三百为基址,群经作椽斗,传笺当泥瓦,辅之以其他古史资料,来逐步还原这个体系层累建构的过程,还原《诗经》在文学意义之外的人文表征,还原其中所蕴含的那个时代的道德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