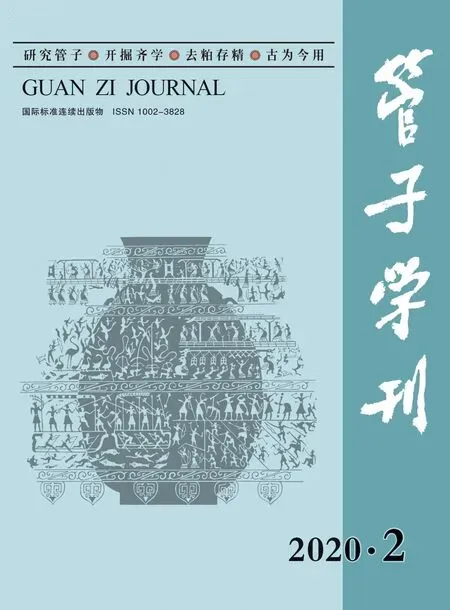朱子中和新旧说转向的再审视
——从“方往方来之说”到“识仁”与“持敬”
赵 玫
(西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朱子中和说本于对《中庸》未发已发问题的诠释。乾道二年丙戌(1166年,朱子年37岁)夏秋至丁亥(1167年,朱子年38岁)春,朱子去信张栻(号南轩)讨论中和问题,当时留存下来的书信被朱子在己丑(1169年,朱子年40岁)新悟之后汇编(1)朱子在《中和旧说序》中提到:“暇日料检故书,得当时往还书稿一编,辄序其所以,而题之曰‘中和旧说’,盖所以深惩前日之病,亦使有志于学者读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五,《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634页。),称“中和旧说”四札,它们是:《答张钦夫》第三书、第四书、第三十四书、第三十五书。关于四札的写作时间(2)对于四封书信所作的时间,历来看法不一。大致有四种见解:其一,清人王懋竑视此四书作于乾道二年丙戌(1166年,朱子年37岁)(王懋竑:《朱子年谱》,《朱子全书》(附录),第196页。)清人夏炘推测四书作于乙酉(1165年,朱子年36岁)至丙戌之间。(夏炘:《述朱质疑》卷三,清咸丰景紫山房刻本。)今人束景南先生进一步确定四书成于丙戌七月之前。(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355页。)其二,此四书成于乾道三年丁亥(1167年,朱子年38岁)。明人李默记“三年丁亥八月,访南轩张公敬夫于潭州”,并指出:“是时范念德侍行,常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卷一,《朱子全书》(附录),第116页。)据二人论《中庸》而“三日夜不能合”之说,刘述先先生遂定此次论道为“中和旧说”的形成时期。(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80页。)其三,此四书成于乾道四年戊子(1168年,朱子年39岁)。钱穆先生认为,丁亥冬朱子至长沙访南轩,首要讨论了已发未发问题,中和旧说即此次访问两个月后引起,遂定四书成于丁亥次年。(钱穆:《朱子论未发与已发》,《朱子新学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449—470页。)其四,陈来先生认为四书成于丙戌夏秋至丁亥春之间(1166年夏秋至1167年春之间)。(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170页。)上述看法中,王懋竑、夏炘、束景南、陈来先生认为四封书信乃乾道二年丙戌朱子去信南轩讨论中和问题所作(并非作于丁亥年的潭州会晤)。今从王、夏等说,具体考证,限于本篇主旨与篇幅,不及详论。凡文中涉及四封书信,皆以《文集》中的顺序“第三书”“第三十五书”等指称。和写作次序,仍存在较大争议。明人李默、清人夏炘、今人钱穆、刘述先、束景南诸先生皆确定四封书信的次序为:第三书、第四书、第三十四书、第三十五书。牟宗三先生疑第三十五书类似于第三书之“别纸”,二书前后相续,并推测在南轩回信前,两书已陆续寄出(3)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91页。。陈来先生与牟宗三先生观点一致,并明确四封书信的写作时间为:第三书(丙戌夏秋)、第三十五书(丙戌秋)、第四书(丙戌秋)、第三十四书(丁亥春)(4)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66—170页。。王新宇偏从文献考订的视角,不可陈来先生之见,仍认为“四书相承,并无先后之错置”(5)王新宇:《朱子参悟“中和旧说”考辨》,《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与此相反,崔海东偏向义理分析,以陈先生之见为是(6)崔海东:《朱子“中和旧说”发微——以“人自有生”四札为中心》,《孔子研究》2015年第1期。。
通过梳理四札包含的内在逻辑,可以证明陈来先生的考订尤其精确。然而,包括他在内的学者们似忽略了最后一书(第三十四书)中出现“识仁”与“持敬”的工夫论转向,此书已具中和新说的胚模,说明此时中和新说思想已经开始酝酿。那么,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朱子在“乾道己丑春”(1169年,朱子年40岁)与蔡季通问辨而自疑旧说之非,并以此断分新旧说的看法,需重新审视。在写作“第三十四书”的丁亥年,中和新旧说转向的苗头就已经出现了,从丁亥春到己丑春的两年间,朱子中和新说逐渐成型,中和新旧说的转变不当只视作一场顿悟。接下来,通过四札内容的梳理,看到由旧说转出新说胚模的过程。
一、未发(“寂然本体”)已发(“良心萌蘖”)的含混表达
关于四札之序,虽诸家之说未有定论,但以《答张钦夫》第三书(“人自有生”)为首札则无疑。此札首先回顾了对“未发之中”的认识历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工夫论困境。朱子言:“人自有生即有知识,事物交来,应接不暇,念念迁革,以至于死,其间初无顷刻停息,举世皆然也。然圣贤之言,则有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者。夫岂以日用流行者为已发,而指夫暂而休息,不与事接之际为未发时耶?尝试以此求之,则泯然无觉之中,邪暗郁塞,似非虚明应物之体,而几微之际,一有觉焉,则又便为已发,而非寂然之谓。”(7)《与张钦夫》第三书,《文集》卷第三十,《朱子全书》,第1315页。
朱子认为,人之念虑随事物之交侵,没有停息之时。然而《中庸》却有“未发之中”,进而追问是否存在一个不与事物打交道的“暂而休息”之时?朱子曾试图从此处下工夫,然而在泯然无觉中不见“虚明应物之体”,又时刻被接续的知觉搅扰,但凡知觉思绎出现,便是已发,如此便不能寻求到一个未发时。
由此可见两点:其一,工夫论问题是基于心性论的,朱子反思旧时以“暂而休息”为未发,以“日用流行”为已发,落实于工夫论上则求未发而不得。其二,这也是对李延平“默坐澄心,体认天理”(8)《延平答问》,《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341页。的反思。朱子提到的“暂而休息”“不与事接”是指静坐而杜绝与外物交接之时。绍兴二十九年己卯(1159年,朱子年30岁)朱子主张“上达处不可著工夫”(9)《答许顺之》第三书,《文集》卷第三十九,《朱子全书》,第1736页。,甲申年(1164年,朱子年35岁)朱子提出“未发以前天理浑然,戒慎恐惧则既发矣”(10)《杂学辨》,《文集》卷第七十二,《朱子全书》,第3475页。,皆说明“未发之中”不是“暂而休息”,而只是“天理浑然”,因此不能以静坐求之。由此亦可证,朱子在从学延平期间乃至此后,对静坐求中之旨一直存有疑虑。因此在此信一开始,便反思了这一问题。
既然不能以“暂而休息”为未发,则朱子寻求新的解释,形成了中和旧说。朱子言:“盖愈求而愈不可见,于是退而验之于日用之间,则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夫岂别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处,而可以谓之中哉?”(11)《与张钦夫》第三书,《文集》卷第三十,《朱子全书》,第1315页。这说明存在“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的道体或心体,它作为体用不二的整体,无止息地与事物相感通,流行不已、生生不息是其特点。这个体用浑全的道体或心体,其体为未发之“寂然本体”。如此,在体用浑然的道体流行中,指认出形上本体,因此“未发之中”并非是它时、它地的独立存在物(12)朱子在甲申所作《杂学辨》中就提出类似主张:“且夫性者,又岂块然一物,寓于一处,可抟而置之躯壳之中耶?”由此亦可佐证,中和旧说四札距甲申为近,当作于乾道二年丙戌,不必在甲申之后四年的戊子。。
由此可见,朱子虽未明确以性体心用来说明,但也表达类似的意思:“寂然本体”指性,其流行发用则为心体流行,这个流行统体被他称为“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然而,朱子从心性统体中指出未发之性(“寂然之本”),似从流行统体中指认出本体,存在视性与心为二物的嫌疑。
心性统体(道体或心体流行)应物而不穷,但若缺乏致察而操存的工夫,则因不能察识其流行之端而可能陷入禽兽之域。因此,基于上述心性关系的理解,朱子提出了相应的工夫修养方法,朱子言:“然则天理本真,随处发见,不少停息者,其体用固如是,而岂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虽汩于物欲流荡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尝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则庶乎可以贯乎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复,至于夜气不足以存而陷于禽兽,则谁之罪哉?”(13)《与张钦夫》第三书,《文集》卷第三十,《朱子全书》,第1316页。心性统体之流行不已,即朱子所谓“不少停息者”。性体是所以能流行者,心用是呈现此流行的端绪。因此,当人心因物欲流荡而阻隔了性体发露,则大本无法致用;亦因涵养察识之功作用于人心而使性体发见,则由发用通达本体。梏亡是此心之梏亡;萌蘖是此心之萌蘖。则“致察而操存”作用于此已发之心,便是尤其重要的工夫。
朱子此说来路分明。庚辰年(1160年,朱子31岁)延平教授朱子“唯于日用处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14)《延平答问》,《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336页。,朱子深以为然。甲申年(1164年,朱子35岁),朱子倡导“日用之间无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体”及“日用之间所以用力循循有序”(15)《答江元适》第三书,《文集》卷第三十八,《朱子全书》,第1704页。的主张与此一致。甲申十一月,朱子表达了对南轩“日用处操存辨察,本末一致”(16)《答罗参议》,《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五,《朱子全书》,第4747页。看法的极度认可。
因此,在此札(第三书)中,朱子非常赞成周子的太极本体无不在五行、阴阳之中的看法,以及误读了程子涵养、察识于已发之际的说法。同时,朱子指出一个“因事发见”的天理作为性体,并以涵养察识于已发以复天理之本然,似有视天理与心各自存在之蔽。
朱子在此书下自注云:“此书非是,但存之以见议论本末耳。下篇同此。”所言“非是”,大抵指心性为二物之蔽的几处表达,那么可以推知在下一封信中,朱子定要回应这一问题。
二、未发(性)已发(人心)的精确指称
紧接着上一札的应当是《答张钦夫》第三十五书。主要理由有三:其一,从第三十五书的措辞来看,似并非回复南轩之疑而作,其大旨与第三书相合,疑类似于第三书之“别纸”。其二,此书仍据已发而指出未发,仍存在将心性视作两物之嫌疑。第三书中朱子自注“下篇同此”即指此篇,因两书皆有视心性为二物的表达。其三,第三十五书提到“近范伯崇来自邵武”(17)《答张钦夫》第三十五书,《文集》卷第三十二,《朱子全书》,第1394页。,确定此书作于丙戌秋,而据陈来先生考订,可确定第三十四书作于次年丁亥春(18)据陈来先生的考订,《答何叔京》第八书(“熹碌碌……”)提到“夜气”正是“复见天地之心”处,此书作于丁亥春无疑。《答张钦夫》第三十四书也提到“夜气”“亦可以见天地之心”的表达,可见二书同作于丁亥春。(文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订》(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43—44页。),故第三十五书当在第三十四书前。
第三十五书的一开头提到:“前书所禀寂然未发之旨、良心发见之端,自以为有小异于畴昔偏滞之见,但其间语病尚多,未为精切。比遣书后,累日遣玩,其于实体似益精明。因复取凡圣贤之书以及近世诸老先生之遗语,读而验之,则又无一不合。盖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见洒落处。始窃自信,以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义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圣贤方策,岂欺我哉!”(19)《答张钦夫》第三十五书,《文集》卷第三十二,《朱子全书》,第1393页。信中提到的“前书所禀寂然未发之旨、良心发见之端”即第三书中提到的“寂然之本体未尝不寂然”及“良心萌蘖”之说。此两说并未在第四书、第三十四书中出现,此亦可作为第三十五书承第三书的佐证。
由于前一封信中“语病尚多,未为精确”,朱子又取孟子、周子、大程子、谢上蔡诸说来读,始自信而见得“洒落”气象,此即延平所教授的涵养纯熟后心体自然流行的工夫效验,于是在南轩回信前又将此信寄出。
为了更“精切”而又无“语病”地纠正前一封信中的措辞,朱子这样说明心性关系:“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夫岂别有一物拘于一时、限于一处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间,浑然全体,如川流之不息、天运之不穷耳。此所以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间,而鸢飞鱼跃,触处朗然也。”(20)《答张钦夫》第三十五书,《文集》卷第三十二,《朱子全书》,第1394页。这里的“天机活物”即前书所言之“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心性统体(道体或心体)。这个心性统体是体用赅贯的,性为体,心为用。而在前书中,朱子只是以“寂然之本体”称未发之中,以“良心萌蘖”为已发。所以此札中“已发者人心”“未发者皆其性”的表达即朱子所谓较之前书用语的“精确”处。但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同于第三书,皆有视心性为二物之蔽。
“天机活物”是心体流行的“浑然全体”,它与在天而言的“川流不息”“天运无穷”一致,即用即体而圆融无碍。因此,从在人而言的心体流行对应在天而言的天道流行,皆是道理的本然发见。
在这个意义上,事有本末、精粗,但皆可以由理贯穿。正如朱子所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修身是本,‘洒扫应对’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于所以然,则理也。理无精粗本末,皆是一贯。”(21)《朱子语类》卷第四十九,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10页。也就是说“治心修身”与“洒扫应对”皆形而下者之“其然之事”,但前者为精、为本,后者为粗、为末。无事不有理,则所有本末、精粗之事皆被理贯穿。又,体(本体)、静(寂然不动)是指形而上者,用(发用)、动(感而遂通)是指形而下者,则体用一贯。
综上,本末、精粗是指形而下者被理通贯而无别;体用、动静是指体用一贯而无间,则朱子在这封信中提到的“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间”,正是说明世间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理与物之间无区别与间隔,此统体便是朱子所言之“天机活物”。这是朱子对上一封信中“浑然全体应物无穷”所作的补充。
由上述心性论的理解,直接引出了工夫论:“存者存此而已,养者养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从前是做多少安排,没顿著处。今觉得如水到船浮,解维正柂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适矣。岂不易哉!”(22)《答张钦夫》第三十五书,《文集》卷第三十二,第1394页。存养的对象就是日用之间的“天机活物”,即存养此已发者的人心,因为人心直接通贯未发之性,是未发之性的流行发见处。可见,此信中朱子对涵养察识于已发的工夫进路完全认可,并体验到了“洒落”气象。
三、纠正前两书中的心性二物之蔽
随后,南轩收到了这两封书信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在接下来的《答张钦夫》第四书中,朱子一开始便这么说:“前书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兹辱诲喻,乃知尚有认为两物之蔽,深所欲闻,幸甚幸甚。”(23)《答张钦夫》第四书,《文集》卷第三十,《朱子全书》,第1316页。
这里的“尚有认为两物之蔽”即上两书中提到的在天命流行中指出“寂然之本体”(第三书)、“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第三十五书)等处。朱子对南轩的批评深以为然,为了纠正偏颇,朱子提到:“当时乍见此理,言之唯恐不亲切分明,故有指东画西、张皇走作之态。自今观之,只一念间已具此体用,发者方往,而未发者方来,了无间断隔截处,夫岂别有物可指而名之哉?”(24)《答张钦夫》第四书,《文集》卷第三十,《朱子全书》,第1316页。朱子反省前两札的内容,称之前“乍见此理”而急于言之,则有上述的失误。这封信中提到的“一念间已具此体用”则说明人的念虑一起(发者),便带出其本体的性(未发者),正如事物迎面而来,此心便体用皆具而有应对。“一念间已具此体用”便是上封书信中提到的“天机活物”。已发未发之方往方来,无间断、无阻隔,从而避免了视心性间隔的弊病。
强调一念具体用,但就一般人来说,是否都能见理无差舛呢?因此朱子接着问:“然天理无穷,而人之所见有远近深浅之不一,不审如此见得又果无差否?”(25)《答张钦夫》第四书,《文集》卷第三十,《朱子全书》,第1316页。通过日用间的察识涵养,是否便能做到“发者方往,而未发者方来”了呢?可见朱子此处疑惑又落实在工夫论问题上。
但是,此时之疑并未直接导向对“于日用之际欠缺本领一段工夫”(26)《已发未发说》,《文集》卷第六十七,《朱子全书》,第3266页。的反思,以至于他对杨龟山之“学者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验之,则中之体自见”的表述,以及对程子所言“涵养于未发之时”(27)程子的原话是:“若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0页。)诸说皆存疑。按照朱子的说法,说“际”“时”似指出未发、已发是分开的两个时段。据前所述,朱子认为已发方往,未发方来,二者在时空上无隔截,才有已发之用,当即便是未发之体。因此,不能以“际”“时”来称未发,当然也不必有未发涵养这一段工夫。可见,此时朱子疑杨龟山,即疑延平求中于未发之旨。
对于这封书信,朱子自注:“此书所论尤乖戾,所疑语录皆非是,后自有辨说甚详。”(28)《答张钦夫》第四书,《文集》卷第三十,《朱子全书》,第1316页。朱子在己丑料检故书,成“中和旧说”一编,此处之“后自有辨说甚详”当指中和新说形成后,对之前所误解的诸儒语录作出更正。故此“自注”当为己丑所添加。
四、“自有安宅”与“求仁”:新说胚模已具
接下来是《答张钦夫》第三十四书,这封书信是对之前三札的总结、批判和推进。不同于之前三札,朱子并未在此札中加上诸如“此书非是”(指第三书)、“下篇同此”(指第三十五书亦“非是”)、“此书所论尤乖戾”(指第四书)的自注语。是否说明当朱子在己丑年反观此书时,见其对于中和新说有可取的价值呢?
这封信中朱子反思了之前几封书信中的病症,他提到:“大抵日前所见累书所陈者,只是笼统地见得个大本达道底影象,便执认以为是了,却于‘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议,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为急,而自觉殊无立脚下功夫处。盖只见得个直截根源倾湫倒海底气象,日间但觉为大化所驱,如在洪涛巨浪之中,不容少顷停泊,盖其所见一向如是,以故应事接物处但觉粗厉勇果增倍于前,而宽裕雍容之气略无毫发。虽窃病之,而不知其所自来也。”(29)《答张钦夫》第三十四书,《文集》卷第三十二,《朱子全书》,第1392页。朱子以“笼统地见得个大本达道底影象”来评价之前三书的错误。“大本”即未发之性体,“达道”即由已发之心用而通达性体。在第三书中,朱子从“寂然不动”指未发之中、“良心萌蘖”指已发之和。为精确其词,第三十五书遂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但二说皆有分离心性之蔽,朱子在第四书中以一念之间具体用,方往方来之说来纠正之前的错误。诸说皆以性体(“大本”)心用、由用而贯彻性体(“达道”)为基本框架,然而这些看法是笼统而含糊的。
因此,朱子进而反思此前对“致中和”一句的忽视,这一反思意味着新说的呼之欲出。首先,据朱子中和新说,中只是性的体段,而不直接便是性(30)《已发未发说》,《文集》卷第六十七,《朱子全书》,第3266页。。说明“中和”还不是极致处。在作于乾道八年壬辰(1172年,朱子年43岁)答石墪的书信中,朱子提到“然‘致’字是功夫处,有推而极之之意”(31)《答石子重》第九书,《文集》卷第四十二,《朱子全书》,第1935页。,这说明“中和”还不是最究竟处,“致中”“致和”才能到达极处,如此,以中为性即以中为极致,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其次,中和体用各异,不能囫囵言之。乾道六年庚寅(1170年,朱子年41岁)朱子去信吕伯恭,提出“大本”指“中”“达道”指“和”,进而言:“学者须是于未发已发之际识得一一分明,然后可以言体用一源处。”(32)《答吕伯恭》第九十七书,《文集》卷第三十五,《朱子全书》,第1520页。这又说明未发、已发皆需“识得”(33)此处“识得”不是认识,求取的意思,当指涵养以见其真,如程子所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分辨二者之别,方见得二者一源。以上两点说明,之前由已发而直接贯通未发的工夫进路,不但将“中和”直接等同于“性心”,且并无在未发之中上落实工夫的意识,因此,是含混而笼统的。
当朱子转而关注于“致中和”,这无疑是中和新旧说可能发生转变的重要信号。基于对“致中和”的关注,朱子若进而对所存疑的程子语录愈加思索,一方面见得未发不是性,而是状性之体段;又见到中、和体用有别,工夫亦各异,则中和新说呼之欲出。学界往往将第三十四书看作中和旧说的四札之一,而忽略其所含新旧说更替中关键性的内容,这忽略了此札中已具的中和新说之胚模。
再来看看朱子对此前工夫及效验的评价。朱子认为之前“盖只见得个直截根源倾湫倒海底气象”,以至于“粗厉勇果增倍于前”而少“宽裕雍容之气”。这一总结同己丑新悟对旧说的反思基本一致,己丑朱子言:“以故阙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间,亦常急迫浮露,无复雍容深厚之风。”(34)《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文集》卷第六十五,《朱子全书》,第3130页。又:“其日用意趣,常偏于动,无复深潜纯一之味,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间,亦常躁迫浮露,无古圣贤气象。”(35)《已发未发说》,《文集》卷第六十七,《朱子全书》,第3268页。可见,第三十四书中所反思“笼统地见得个大本达道底影象”,进一步讲,即缺阙未发时涵养工夫,此近于己丑对旧说工夫及效验的反思,更佐证新说胚模已具,若加以推敲琢磨,便呼之欲出的说法。
基于工夫效验的反思,朱子从性心体用一源之“方往方来之说”转向寻求贯通体用的枢要,此枢要即“求仁”:“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所以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者,乃在于此。而前此方往方来之说,正是手忙足乱,无著身处。道迩求远,乃至于是,亦可笑矣。”(36)《答张钦夫》第三十四书,《文集》卷第三十二,《朱子全书》,第1392页。“安宅”指仁。孟子言:“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孟子·公孙丑上》) “尊爵”意为仁是天所赋予人之性(仁、义、礼、智)中之长善者;“安宅”是说人居于此长善者而能安身,即朱子所言之“人当常在其中,而不可须臾离者也,故曰安宅”(37)《孟子集注》卷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9页。。此时朱子将“求仁”当作“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正是从切近处求取。
此前朱子视心性全体浑然,从而方往方来,与天道之“川流不息”“天运不穷”“鸢飞鱼跃”“触处朗然”诸说一致,说明体用无间。此见虚玄高远,不似就人心上落实与具体,故朱子称此前所见“道迩求远”。因此,朱子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认识落实到作为自家主宰的人心上,以“求仁”为方,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朱子在次年(乾道四年戊子,朱子年19岁)回顾这封信,这样说到:“‘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语固有病,然当时之意却是要见自家主宰处。所谓大化,须就此认得,然后鸢飞鱼跃,触处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说个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颟顸笼统,非圣门求仁之学也。”(38)《答石子重》第五书,《文集》卷第四十二,《朱子全书》,第1923页。此时朱子总结第三十四书之得失:直指大化即安宅,似显笼统,这是所见有偏的地方;但看到大化中之安宅,不在天地处寻,而落实到具体的人心,这是合理之处。那么,接下来的工夫便以“求仁”为要,南轩早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在他收到之前三通信札,遂“教告以求仁为急”。
在朱子成熟的思想中,仁是打通天人的关窍。仁乃天地之心落实于人者,其包四德,贯四端。仁通天人、贯体用。如此,仁之体用分别关涉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因此,求仁就意味着在未发与已发上皆可以下工夫,这与此前在已发之心上落实工夫的做法不同,此即我们将朱子转向“求仁”视作其中和说的一次大飞跃的理由。
另外,朱子中和问题的进展和对仁的研讨,总是形影相随。丁亥九月(1167)朱张二人潭州会晤,二人论辨的核心问题便是“仁”。己丑(1169)朱子更定中和旧说,接着便是壬辰十月(1172)《克斋记》《仁说》的写定。由此可见,此时朱子转向“求仁”,势必为中和说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
五、中和旧说向新说的转向契机:以“敬”为工夫
“求仁”需以“敬”为主。朱子言:“学者当知孔门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间,以敬为主。”(39)《朱子语类》卷第十二,第213页。以敬为工夫,从而使得日用间接物应事由“急迫”转而为“雍容深厚”。因此,关注于求仁,便是将工夫修养转向“持敬”,二者的发生是同时的,这是中和新说形成的契机。
在写作《答张钦夫》第三十四书的丁亥年春,朱子与友人论学,多次谈到“持敬”。朱子言:“所以有此病者(40)笔者按:指上文提到“躁妄之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气有以动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临事接物之际真心现前,卓然而不可乱,则又安有此患哉?”(41)《答何叔京》第六书,《文集》卷第四十,《朱子全书》,第1808页。这里的“躁妄之病”即第三十四书里提到的“粗厉勇果”之病。也就是说,朱子将之前所主张的在日用常行间的察识涵养,进一步落实为“持敬”的工夫。惟有“持敬”才能使此心为一身之主宰,而使接物应事有条理。如此所带来的工夫效验便不同于从前。
此时的朱子对程子之“持敬”说完全认可,“持敬”说又被湖湘学继承下来,这更加深了朱子对南轩学问的认同。朱子称“《敬斋记》所论极切当,近方表里看得无疑”(42)《答许顺之》第十二书,《文集》卷第三十九,《朱子全书》,第1745页。此书作于丁亥,可见南轩《敬斋记》作于此前不久。。《敬斋记》是南轩为其友崔子霖之“敬斋”而作,由此篇可见南轩论敬之旨。《敬斋记》提出:“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谓敬’,又曰‘无适之谓一’。”(43)张栻:《敬斋记》,《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第十二,《南轩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38页。此说强调人心的重要性,它是万物的主宰者,所以能够统贯事理。既然如此,人的修养工夫要落实在人心上,一方面既要求察识此心之发动,即“致知”之功;又要持守此心不至于丧失,即“持敬”之功。
当事物纷来沓至,此心发动而有应对。在心之发动中,有一贯之旨,即谓察识与致知。识得并持守即“持敬”,因此南轩接着总结到:“其必识夫所谓一而后有以用力也。”(44)《敬斋记》,《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第十二,《南轩集》,第938页。这里的“一贯之旨”尤显重要,“一”即“不走作”(45)朱子言:“一,只是不走作。”《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六,第2467页。而专注于面前之事,即程子所言之“无适”,朱子常用“且如读书时只是读书,著衣时只是著衣”“在门前立,莫思量别处去”(46)《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六,第2467页。的例子来说明。察识之后便是持守工夫,即“持敬”,亦程子所言之“主一”。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持敬”即“主一”,不是说将敬视作一物,从而视“敬”为一物作用于心。而是常存敬畏,不放纵此心而常惺惺。故南轩言:“盖主一之谓敬,敬是敬此者也。只敬便在此。”(47)《答曾致虚》,《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张栻集》,第1159页。说明“持敬”便是“敬在此”,专注一事一物而诚敬以对。
为了进一步说明察识(“无适”)与持敬(“主一”)的关系,南轩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南轩言:“且吾视也、听也、言也、手足之运动也,曷为然乎?知心之不离乎是,则其可斯须而不敬矣乎?吾饥而食也,渴而饮也,朝作而夕息也,夏葛而冬裘也,孰使之乎?知心之不外乎是,则其可斯须而不敬矣乎?”(48)《敬斋记》,《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第十二,《南轩集》,第938页。视听言动是人们日用常行间的基本行为;饥食渴饮等是人们的基本欲求。在日用间的这些行为与欲求中,都有心的主宰作用。认识这个“不走作”的心并“持敬”以守之,即上文所提到的“识夫所谓一而后有以用力也”。
综上可见,南轩认为心地工夫可以具体分两块,一则“致知”(察识)此心之发之正当与否;二则“持敬”(涵养)而能使此心始终能如如呈现。这两块工夫皆作用于已发之心。
朱子认为《敬斋记》“所论极切当”,可见他对南轩心地工夫的完全认可。在丁亥年,关于察识与持敬,朱子提到:“因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察于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49)《答何叔京》第十一书,《文集》卷第四十,《朱子全书》,第1822页。在朱子的语境里,“察于良心发见处”即察识良心发见之端,见得其正当与“不走作”,这是已发处的心地工夫;“猛省提撕”即持敬之功,朱子尝言:“人之为学,千头万绪,岂可无本领!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语。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则于事无不见,久之自然刚健有力。”(50)《朱子语类》卷第十二,第209页。为学之方众多,然而有一个根本的为学本领,便是程子所言之“持敬”,即“提撕此心”而使之愈见光明澄澈,从而应对事物而无不正。总之,此时朱子的认识和南轩完全相符,察识与持敬以作用于已发之心,是为学的根本要领。
以“持敬”为工夫,是中和旧说向新说转变的关键点。只是此时,朱子并未进一步将“持敬”工夫再细致追究,没有看到“持敬”这一涵养工夫可以作用于动静,从而没有意识到静时的涵养工夫尤其重要,以至于他虽意识到“方往方来”说的笼统与工夫效验的“粗厉勇果增倍于前”,并关注“致中和”与“求仁”以及“持敬”,中和新说虽具胚模却仍欠些火候。
我们从己丑以后朱子与学人的书信往来及《朱子语类》的成熟之见中就能看到这一点。试举几例,《朱子语类》载:“大抵敬有二:有未发,有已发。所谓‘毋不敬’,‘事思敬’,是也。”曰:“虽是有二,然但一本,只是见于动静有异,学者须要常流通无间。”(51)《朱子语类》卷第十七,第373页。从这则语录中,可见两点:其一,朱子及弟子二人皆认可存在两种敬,一种是作用于未发,如《礼记·曲礼》之“毋不敬”,“毋不敬”常被朱子称为“浑然好底意思”(52)《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三,第546页。之所以说“毋不敬”是强调在未发所作的敬工夫,在于看到朱子亦有类似表达。朱子在辨别“思无邪”与“毋不敬”两语时尝言:“‘毋不敬’是浑然底,思是已萌,此处只争些。”(出处同此注)可见“浑然底”与“已萌”即未发与已发。,强调直接作用于浑全本体之敬。一种是作用于已发的,如《论语·季氏》之“事思敬”,强调在日用常行间接物应事间无不敬。其二,两种敬虽作用于未发之静与已发之动,但敬的工夫又是落实在动上,并直接贯穿“流通”到静。
显然,丁亥,朱子与南轩看到了上述第二点,而没有重视第一点。二人认为日用间心用直接贯彻本体,故而心用上的工夫即本体之工夫,因此他们强调了已发之敬。也就是说,二人看到了敬贯穿流通于已发未发,但没有看到动之敬与静之敬以及相应的动静工夫的区别,尤其忽略了静之敬的重要性。
又,己丑年(1169年,朱子年40岁)朱子写给南轩的信中提出“以静为本”的说法。朱子言:“来教又谓熹言以静为本,不若遂言以敬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贯通动静,而必以静为本,故熹向来辙有是语。今若遂易为‘敬’,虽若完全,然却不见敬之所施有先有后,则亦未得为谛当也。至如来教所谓‘要须察夫动以见静之所存、静以涵动之所本,动静相须,体用不离,而后为无渗漏也’,此数句卓然,意语俱到,谨以书之座右,出入观省。”(53)《答张钦夫》第四十九书,《文集》卷第三十二,《朱子全书》,第1420页。此时朱子中和新说已经形成,朱子除了提倡“敬”字贯穿动静的主张之外,亦提出“以静为本”的主张,也就是说分静之敬与动之敬,但是在这两种工夫中,尤其强调静之敬工夫的根本地位,以标明“敬之所施有先有后”。南轩亦注意到了动静皆可以由敬贯穿,在静时涵养以见得动之根本,在动时省察以见得静之所在,前者由体涵用,后者以用见体。但是南轩并不像朱子一样更强调静之敬的根本地位,因此紧接着上述引文,朱子提出南轩察识于已发与涵养于未发“二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谓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实”(54)《答张钦夫》第四十九书,《文集》卷第三十二,《朱子全书》,第1421页。的建议。可见在己丑,朱子和南轩不仅已经看到静之敬与动之敬的区别,并且,朱子尤其强调了静之敬的根本性地位。
总之,丁亥,朱子关注“求仁”与“持敬”,这意味着中和新说初具胚模却未成形。一方面,朱子仍将敬视作已发时的工夫,而没有看到在动之敬之外还存在静之敬;另一方面,朱子更没有进一步认识到静之敬是根本,以至于忽略在强调敬工夫的过程中尤其要突出“以静为本”。但是,关注“持敬”与“求仁”,是中和旧说完全转为新说的必要环节,可以说,这是新说胚模形成的重要标志。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朱子在丁亥年所作《答张钦夫》第三十四书中已具新说之胚模,在该信中,朱子反思此前缺阙的“宽裕雍容之气”,又意识到对“致中和”的忽视,并将虚玄高远的“方往方来”说转为“求仁”与“持敬”。同年朱子尤其认可了南轩“持敬”之说。这些都是中和新说形成胚模的重要标志:对“致中和”的关注,为性体心用转向心统性情提供了可能;对“求仁”与“持敬”的认识,为从已发之敬转出已发、未发皆存在动、静之敬的成熟理解做了铺垫;对工夫效验之“粗厉勇果”的反思,是“宽裕雍容之气”转变的必要前提。
总之,中和四札《答张钦夫》第三书、第三十五书、第四书、第三十四书因内在逻辑,其顺序不容紊。丁亥对于朱子中和新说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不容忽视。作于丁亥春的《答张钦夫》第三十四书中已具中和新说胚模。中和新说的提出不是己丑春的一场顿悟,而是在丁亥年便初具胚模并随后逐渐成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