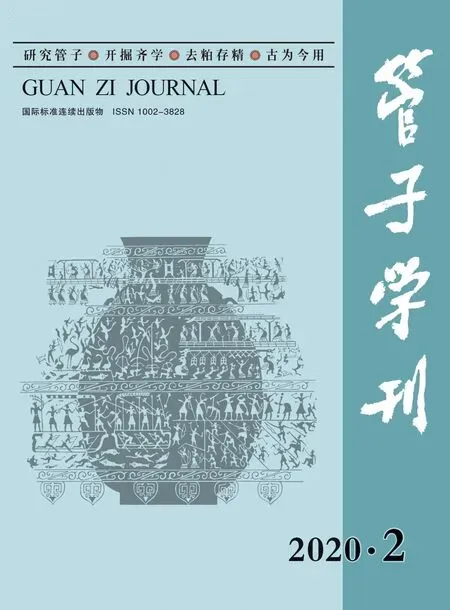论康有为的“人道”思想与其孔教观
——以《康子内外篇》为中心
郝颖婷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一、《康子内外篇》对康有为思想研究的重要意义
学界对于康有为早期思想的研究所参照的文本主要包括《教学通义》(1)参见刘巍:《〈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根据此文的考证,此稿书名应为《教学通义》而非梁启超误记之《政学通议》,《中国文化》研究集刊首次刊布时亦误作《教学通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中《康有为卷》以此为底本,亦误作《教学通议》。本文均写作《教学通义》,引文作《教学通议》者不予修改。《民功篇》《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等,然而由于康有为在其著作中常倒填年月及他对书稿的频繁修改,这些文本能否被笼统归为康有为早期思想的表达依然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将这四种文本笼统归为康有为早期思想的表达不仅仅难以解释康有为看似“同期”思想中的矛盾之处,更会错失其思想发展成熟的真正内在理路。而《康子内外篇》则是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文本。
康有为自己在对其《年谱》的修订之中,将《内外篇》与《人类公理》《公理书》并列进退(2)参见茅海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甚至还曾将《康子内外篇》前九篇刊于《清议报》1899年第11、13、15、17、28各册的《支那哲学》栏(3)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页。,非如《教学通义》般在康有为思想成熟后为其闭口不提,更没有似《民功篇》一样在《年谱》中被删去。以康有为常常以“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自诩来看,将《内外篇》系于二十九岁、三十岁之时所作,并将之于变法失败后依然发表这一行动,表明他非但并不以之为思想未成熟时作品,反而以之为他思想早熟甚而完备且具有独立性的证明。
《内外篇》成书时间虽于《年谱》中系于1886年,但在《年谱》之外首次被康有为提及则是在光绪辛卯年(1889)《与沈刑部子培书》:“所著《内外篇》,说天人之故,行且次之呈览。”(5)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192页。可知《内外篇》初作之时间不晚于1889年,早于康有为与廖平会晤之前。且考虑到《内外篇》中诸多与《万木草堂口说》《春秋董氏学》甚乎《孟子微》《大同书》等文本的相类之处,我们几乎可以推定,《康子内外篇》是康有为第一次向清帝上书建议变法失败后在思想上作出重大调整的产物,也是康有为脱离章学诚影响思想真正成熟、开始具有独立性、体系性的证明。《内外篇》集中体现了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汉学思想家在人性论及人性论背后的自然——人为之辨向度上对康有为产生的巨大影响,康有为由此得以接续荀子以降至西京经学以“血气心知”论性的思想传统,进而将之在人之为类的文明化成层面上加以重构,而最终以之为其五运转移、三世进化的孔教观奠基。也正是在《康子内外篇》定下的思想基调中,康有为才能够迅速吸收利用了廖平带来的今文经学的思想资源,因此这种吸收利用绝非全盘剿袭,而只是在其已经形成的独立框架中重构传统。
因此,尽管《内外篇》内容还未全备,甚至还颇有内在逻辑不协、说理未能圆融之处,但其所思考的根本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已经确定,故而之后康有为通过廖平得到今文经的思想资源后,才能非常迅速地加以消化,并进一步将之与《内外篇》中已经体系出的基本思路予以结合,两相叠加下,康有为的今文经思想才在之后的戊戌变法中释放出了爆炸般的力量。也正是透过这些还未全然尘埃落定的思想痕迹,我们才可能把握康有为诸多非常异义或看似浅薄之论背后的真正思想意义。
二、从“爱恶”到“仁智”
康有为在作《教学通义》之时依然秉持朱子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的人性论观念,然而在《康子内外篇》中,他却已然接受了“生之谓性”的观念,超越了理—欲对立、善恶二分的人性论格局,直接以爱恶论性。这一改变的内容与意义超越了人性论论域本身,直接影响着康有为对政治秩序何以构建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
康有为自《内外篇》始几乎全以气质之爱恶论性,同时《内外篇》基本奠定了其政治哲学的人性论基础及其处理政治问题的根本思路:
人禀阴阳之气而生也。能食味,别声、被色,质为之也。于其质宜者则爱之,其质不宜者则恶之,儿之于乳已然也。……故人之生也,惟有爱恶而已。欲者,爱之征也;喜者,爱之至也,乐者,又其极至也,哀者,爱之极致而不得,即所谓仁也,皆阳气之发也。怒者,恶之征也,惧者,恶之极至而不得,即所谓义也,皆阴气之发也。(6)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9页。
康有为从此确立了气本论统摄下的“生之谓性”式人性论思路(7)在约1891年所作《答朱蓉生先生书》中康有为重申了这一论调:“告子曰‘生之谓性’,即‘性者生之质’之谓。‘食色性也’,即圣人从其食色中指出善恶之谓,故仆有取焉。”,不再像朱子一样在理气二元的基础上以理在气先为性善之先天性作出证明,而是直接以气质为性,认为此性全由阴阳之气构成,并未先天便得天理赋予其中。因此,性也不能先天地表现为“健顺五常之德”,也就不具有可以通过理学工夫而可复之“性”。因“阴阳之气”而生的性只能通过“爱恶”有所表征:“于其质宜者则爱之,其质不宜者则恶之,儿之于乳已然也。”人与生俱来者并非天命所赋义理之性,而是“爱”“恶”二端。
以“欲恶”为论心性之大端,早见于《礼运篇》“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之说。而以“好恶”为喜怒哀乐之根源,则早见于《左传》中子产言礼的著名段落:“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康有为在《爱恶篇》中同样以喜怒分别归于好恶,不同之处在于对“哀惧”的处理以及“仁义”在这一序列的引入,更重要的是以“爱恶”与“智”相表里,而这都是经典本身所未及处。可见,康有为此论大概并非直接承袭《礼运》《左传》,而是近承自清代汉学所开之新义理学并别出机杼:
爱之征也;喜者,爱之至也,乐者,又其极至也,哀者,爱之极致而不得,即所谓仁也,皆阳气之发也。怒者,恶之征也,惧者,恶之极至而不得,即所谓义也,皆阴气之发也。(8)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9页。
康有为将七情分为两组,分别归于阴气、阳气之发,而七情最终归本“爱恶”二者。“爱”作为“阳气之发”表现为一种外向开辟、聚摄外物的意向活动,“恶”作为“阴气之发”则为一种凝敛拒斥、有所断限的意向活动。“爱”聚摄外物的倾向表征为“欲”,其进一步发展则为“喜”,更进一步则昭显为“乐”,而当这种不断向外推扩、吸摄外物的倾向被限制、削折之时则发为“哀”,由哀人方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行、立不忍人之政,方有“仁”。“恶”的逻辑亦如是,其有所断限而拒斥的倾向发展彰显则为“怒”,当其欲断限凝敛、拒斥外物而不能之时,则发为“惧”,人因惧而立下种种限制以保守自身,方有“义”。
康有为所谓“爱恶”虽能生出种种欲望情感,但却不能被简单化为现成的、具有明确形式情感、欲望或意愿,而是更近似于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活动。这种意向活动乃任何现成明确的思、行的根源,即某种“动之微”——几。它指向对象、构成对象,从而在这种活动中完成“意义给予”。“爱”在这一意向活动中代表了意向性不断聚摄外物而赋予意义、形式,因而不断开辟推拓超越意向本身的能力,而“恶”则代表了将不断推扩的意向活动凝敛为具体现成对象,给予彼我间分界、物物间断限从而将意向活动完成为分析、判断等具体意识行为的能力。
康有为认为“哀惧之生也,自人之智出也”,将“爱恶“与“智”等同,认为两者相为表里,正是其论“智”深刻之处,也是他后期《大同书》中提出人道不过苦乐、所谋不过去苦求乐观点的先声。他在《大同书》中提出:“故夫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9)康有为著,周振甫、方渊点校:《大同书》,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页。苦乐尽管可以解释为《大同书》中所枚举的种种人世间具体明确的苦乐之事,但苦乐首先是人基于爱恶的知觉感受,人基于爱恶之“几”而有苦乐之感,世间事事物物于是因此苦乐而被赋予意义,人面对世界的筹划谋虑也于是不过“去苦求乐”而已。然而这种筹划谋虑本身即为“智”,或者说,爱恶之“几”通过知觉达于苦乐之感本身即是“智”。因此,康有为所谓与爱恶相表里的智绝非某种能够脱离感性因素做出判断的理性,也并非能够为意志、感情所驱使的工具理性,而就是由爱恶达于苦乐的知觉本身,故而康有为所谓“智”本身就是伦理性、政治性的。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仁智间关系的描述清晰地表明了其思想自《爱恶篇》到《大同书》的延续轨迹:“夫浩浩元气,造起天地。天者,一物之魂质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质也。”(10)康有为著,周振甫、方渊点校:《大同书》,第3页。《爱恶篇》中对爱恶源自阴阳二气的表述,在这里被代之以“人之魂质分自浩浩元气”之说,而人之魂质即其觉知灵明,与爱恶乃一体两面,故而虽改换表述但依然是康有为以气论性的升级版本。不同之处在于康有为强调的重点从“爱恶”转向了“知觉”,这一转变不仅表明康有为起自《爱恶篇》的人性论思路在《大同书》中得到了继承,更表明了他虽以“爱恶”为篇名但知觉之为论性关键的一以贯之之处:
孔子曰:“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神者有知之电也,光电能无所不传,神气能无所不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全神分神,惟元惟人。微乎妙哉,其神之有触哉!无物无电,无物无神,夫神者知气也,魂知也,精爽也,灵明也,明德也,数者异名而同实。有觉知则有吸摄,磁石犹然,何况于人?不忍者,吸摄之力也,故仁智同藏而智为先,仁智同用而仁为贵矣。(11)康有为著,周振甫、方渊点校:《大同书》,第3页。
知觉在康有为的气论框架中被解释为“神气”,神气如同光电般无所不传无所不感,因而人的知觉根本上具有“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全神分神”的势用。而这种势用正是人之能“仁”的原因:天地皆由元气造起人生于天地间亦如是,元气分于人为神气无所不感,表现为知觉使人能感通天地万物,这种感通便是“仁”,便是“不忍人之心”。人因其能“仁”而于万物为贵,然而“仁”并非人为天所赋别有一物之性或理,而正是人之为人能知能觉本身。这就将康有为此处与理学如程颢《识仁篇》的思路区别了开来:在大程子看来仁者自然居于“浑然与物同体”的超迈境界,这种感通只需学者识得仁之理后“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便可达至。然而在康有为这里“仁智同藏而智为先”,仁境的到达并非通过“反身而诚”的内向道路,“仁智同藏”中仁是在伦理价值层面标的,而“智”才是仁的实质。因此,康有为以感通论仁的思路虽然有似于大程子以“手足痿痹为不仁”的譬喻,但其重智则正处在儒家思想史上以“知觉”“智性”为人性之主的传统之中,其中远则荀子,近则有戴震,而戴震对于“智”的强调对于康有为影响深远,其思想史意义远非一句其重新开启了知识论传统足以界定。
三、以“智”论性
戴震遵从《乐记》以“血气心知”为性,其于《原善》中论性曰:
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性之征于欲,声色臭味而爱畏分。既有欲矣,于是乎有情,性之征于情,喜怒哀乐而惨舒分。既有欲有情矣,于是乎有巧与智,性之征于巧智,美恶是非而好恶分。(12)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4页。
而康有为在1882年为其师朱次琦所作《南海朱先生墓表》中便已认为:“治血气,治觉知,治形体,推以治天下;人之觉知、血气、形体,通治之术。古人先圣之道,有在于是。”(13)康有为著,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其以血气觉知形体论人,思路与戴震极近。康有为所论形体之于戴震所言声色臭味之欲,血气之于喜怒哀乐之情,心知之于美恶是非之巧智,均可对应。其中,戴震所谓人惟能以心知—巧智而能成其性的论述,对于康有为人性论整体框架的构建起到了根本启发作用,尽管康有为最终落脚之处比戴震更为激进。
戴震在《原善》中构建的人性论基本框架在之后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中不断完善,但根本旨趣未曾改易,要而言之,其人性论旨趣不过“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14)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44页。一语。“自然”于人性而言乃欲与情,欲与情则人与物同——人物之生生皆本于“天地之气化”“阴阳五行之运而不已”,故而乃“血气之伦尽然”者:“凡血气之属皆知怀生畏死,因而趋利避害;虽明暗不同,不出乎怀生畏死者同也,人之异于禽兽不在是。”(15)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26-27页。而康有为同样以为人与禽兽之异在于“智”:“虽然,爱恶仁义非惟人心有之,虽禽兽之心亦有焉。然则人与禽兽何异乎?曰:异于智而已。”(16)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11页。可见康有为完全承袭戴震以爱恶仁义非人与禽兽之别的观点,而康有为认为人之智愈推愈广则其爱恶愈大而愈有节的观点,背后也是戴震的观点:“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17)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41页。概括而言,戴震与康有为都认为,人的知觉是人能达情遂欲、推扩爱恶而得节的根本原因,而达到道德之盛与产生政教礼义文章正是由知觉而通情遂欲、推扩爱恶而得其节的结果。
戴震论性的根本旨趣在于“归其必然,适完其自然”,在他看来,唯有“巧智”或曰“智”“知觉”“神明”,方为能“归于必然”之根本:“人则能扩充其知至于神明,仁义礼智无不全也。仁义礼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极其量也。”(18)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26页。“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无节于内,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践乎中正,其自然则协天地之顺,其必然则协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语于此。”(19)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69页。“天地之中正”或言“仁义礼智”并非“如有物焉藏于心”之物,仁义礼智在戴震看来并非如种子一般根植在人性中,人心并非先天就“具众理”。也就是说必然作为自然之极则,不可能通过“复性”的方式达到,而只有通过“智”—“神明”才能实现。智性或曰知觉,在戴震的人性论中居于根本地位。上文引文中虽有“既有欲有情矣,于是乎有巧与智”之语,但巧智—知觉并非外在于欲、情而别为一物者,亦非生于欲、情之后以对治欲情者,这一表达毋宁是在说,欲与情在人身上只有通过知觉巧智方能表现出来,生养之道由之得尽,感通之道由之得遂。换言之,智性—知觉并非人为了修仁义礼智之德、达天地中正之道所行的某种工夫或手段,而就是德性之修、中正之达本身。这正是戴震论性的根本旨趣所在,也是戴震真正影响康有为之处。
康有为论证人之“爱恶”能够发为“哀惧”而最终呈现为“仁义”之德行的思路与戴震相似,都强调这并非情感的自然发展,其根源在于“智”:“哀惧之生也,自人之智出也。魂魄足矣,脑髓卑矣,知觉于是多焉。”“智”即为“知觉”,知觉随着人逐渐生长发育特别是脑部发育完全而完备。“哀惧”自人之“智”出,表明“智”并非在“哀惧”“仁义”之外别为一物,而与“爱恶”为一体两面:“人生仅有爱恶之端……存者为性,发者为情,无所谓善恶也。”(20)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10页。“人之性情,惟有智而已,无智则无爱恶矣,故谓智与爱恶为一物也。存于内者,智也;发于外者,爱恶也。……智无形也,见之于爱恶。”(21)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11页。“生之谓性”,人生来仅有爱恶二端,据其存于身之状态一面而言则谓之“性”,据其发而现于外一面而言则谓之“情”,性情只就存于身发于外而有所区别,无所谓善恶之别。“爱恶”与“智”为一物之表里,“智”为人之性情,而爱恶则为“智”之所发。这一论述与戴震论四端之扩充本为心知之扩充的思路几乎完全一致,戴震论曰:“于其知恻隐,则扩而充之,仁无不尽;于其知羞恶,则扩而充之,义无不尽;于其知恭敬辞让,则扩而充之,礼无不尽;于其知是非,则扩而充之,智无不尽。仁义礼智,懿德之目也。孟子言‘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休惕恻隐之心’,然则所谓恻隐、所谓仁者,非心知之外别‘如有物焉藏于心’也。”(22)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29页。可见知觉之外别无所谓四端,即康有为以爱恶仁义与智相表里之论也。而康有为亦明确提出:“欲与恶所受于天也。若天地则光电热重相摩相化而已,何所谓理哉?……夫有人形而后有智,有智而后有理,理者,人之所立。”(23)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29页。反对以理为别有一物在,康有为承接戴震之说而较之更为激进,直以理为人之所立,人因其有智而能立其理。
四、“继善成性”新解
对于“人为”的重视戴震至康有为一脉相承,然而这种“人为”不能等同于荀子“化性起伪”中的“伪”,也非以荀子式“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分际为背景。戴震对“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强调正表明,他并不想完全斩断天人之间、自然人为之间的联系,因为强调天人之分固然给予了人为对秩序建构、意义赋予的根本重要性,却也将人为之法抽空为纯粹的习俗,使之丧失了其超越于习俗之上的根据与价值。但同时,他也并不赞同完全以天理为自然而贬抑人为之价值、以复性为归旨的理学式天人观。康有为明确地继承了戴震的问题意识,并在其思想体系建构中着力强调的“人道”概念,所要延续的正是戴震希望以自然—必然之论重建天人关系的努力。
在这种重建中,戴震与康有为都使用了《系辞》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作为经典资源。“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本身作为往复不息的气化过程,不断生成又不断归于混沌,表现出一种本真的生成倾向——生生之谓易,这种“生生”乃阴阳之交感之不测,此所谓“天道”。戴震所谓:“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24)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43页。这种天道乃纯粹的气化,康有为则表达为:“夫天之始,吾不得而知也。若积气而成为天,摩励之久,热重之力生矣,光电生矣,原质变化而成焉,于是生日,日生地,地生物。”(25)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28页。他虽然借助西学物理知识试图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但剥除“热重光电”的物理名词,其核心依然是天道之气化。
人道由天道所生,而不与天道同,在戴震处,“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由天道以有人物也。”(26)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43页。天道之生生不息固然表达了一种生成倾向,然而天道毕竟“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天道无谓善恶,生而不成,“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者乃人道而非天道,即所谓“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27)语见熊十力《新唯识论》《原儒》。然而此处虽用此语但与熊十力原意有别,熊先生强调“本来性净为天,后起净习为人”,然而康有为所在人性论传统并不强调人有“本来性净”,此处之所谓“因”在于人能继天,人由道之生生气化而成形而有爱恶有觉知,而非禀有某种源自于天的实存规则、形式或善性。。人身处天道气化不断的生生不测之中,而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人之为人就在于人能够“继善成性”,这种“继善成性”在戴震看来正是他一直念兹在兹的自然—必然之辨:“《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继之者善’,继谓人物于天地其善固继承不隔者也;善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一事之善,则一事合于天;成性虽殊而其善也则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天地人物之道于是乎尽。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28)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43页。人继天之气化不隔而谓之善,但此善并非天赋一种善理在人而人继承之,“继承不隔”指的是知觉感通无碍无蔽得以通情遂欲的本真状态,人由此得以达乎中正而归于必然,也真正完成其天命之“性”——性为自然,但人能继善则完成其性自然之极则,由此,人为成为了自然的完成。
康有为在《内外篇》中就对“继善成性”做出了与戴震极其相似的表述:“盖继道为善,必天生而为性,而后成之,若未有人,谓何实焉。”(29)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29页。然而康有为在继承戴震观点的同时,却在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立场背后的根本视域——如果说戴震依然在个体生活的伦常日用的视域下处理自然—必然之辨,依然在理学提供的语境下以天道—人道之分殊为一有待解决的义理问题,那么在康有为这里,个体生活的伦常日用视域只能作为一个更加宏大视域的组成部分,这个视域就是人之为类、人类之有人道的政治—历史视域。戴震通过自然—必然之辨、通过重述性善论所试图做的,仅仅是松动一个五伦尊卑次第已然确定的秩序,这一固化的政治秩序实际上是戴震一切论述的隐含背景,他的根本视域内在于此秩序,所以他依然是从一个既有秩序中生存的个体的视角出发。康有为则面对着一个已然松动甚至趋向解体的政治秩序时彻底跳了出来,不再从既定政治秩序中的个人的角度来思考,而是站在了立法者的位置直面如何制法垂教、构建某种理想政教的根本问题。因此,人性论论题在康有为这里也不再仅仅在单独在抽象层面进行讨论,转而将之从属于人之为群如何构建秩序共同生活这一根本问题进行论述,换言之,人性论论题不再是一个高于政治生活的属于“性与天道”的抽象命题,对之的探讨决定性地指向了政治生活本身并成为了为政治生活奠基的努力。
康有为之后在《中庸注》中对人性与人道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说明:“道者,非以为鬼神道,非以为木石鹿豕道,以为人之道也。道要于人所行,通于人所共行,则可以为道。”(30)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7页。康有为对“道”的定义侧重于道“通于人所共行”之“共”,道之为人人共行之道,必须将人之为类无分智愚高低皆纳入其中,然而这种纳入不同于朱子以道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朱子的侧重点在于人人皆可修习此道以启其心复其性,而对于康有为,人道之能“通于人所共行”在于其乃人得以为群为类共同生活之道:“道,犹路也,人身初入动作由之,无离乎路者,以明人性之有交接云为之者,即为人道也。自形上言之则为阴阳,自继成言之则为善性,自形下言之则为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皆人道之不可离也。若离乎道者,腾空缘壁盖有之矣,然非人所共由,不谓之道。”(31)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第189页。人道惟存于人与人交接云为的共同生活中,且人道并不体现于共同生活中的个体的孝悌节义上,而只能呈现为人之为群体的共同生活如何构成上,即呈现为人之为类的群道。以“人道”为背景,康有为对于人性论问题的处理成为了我们理解其对自然—人为、圣人—历史根本观点的关节。
因此同样是以“继善成性”为说,康有为在《答朱蓉生先生书》中明确提出:“其言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指在天之道言。‘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言善也则是圣人所继之者,性也则是人人当成之者。……且既曰成之,则人为在焉,非谓性即善也。”(32)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180页。此处强调“成性”源自“人为”与《内外篇》同,不同处在于康有为在这里将“继善”解释为“言善也则是圣人所继之者”,这并非是表述圣人与天继承不隔全善而无气禀所拘的超拔境界,结合《春秋董氏学》中的类似论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康有为是在人道之文明化成的层面解释“继天之善”:
鸿蒙开辟之始,鸟兽獉狉,山河莽莽。圣人作,而后田野、道路、舟车、都邑、宫室、服物、采章、礼乐出。作成器以为天下利,垂教义以为万世法,所谓继天也。继者,天所继而续之,天所缺而补之,裁成辅相之极则也。(33)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4页。
圣人继天成善,就在于圣人能够裁成辅相,于天之外而成礼乐政教于人道得文明化成之功,圣人成器垂教之前天地处于“鸟兽獉狉,山河莽莽”的状态,并无文明可言。换言之,戴震在个体层面描述的“形体始乎幼小,终乎长大;德性始乎蒙昧,终乎圣智”(34)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页。的过程,在康有为这里被提升到了整个人类由草昧而至文明的层面,圣人在历史文明演进中所扮演的正是“智”在人性中的角色:“天地之气,存于庶物,人能采物之美者而服食之,始尚愚也同。一二圣人少补其灵明而智生矣。合万亿人之脑而智日生,合亿万人之脑,而智日益生,于是理出焉。若夫今人于野番,其为愚,亦无以禽兽无几何,虽智且不能言,而何有于万物哉?故理者,诸圣人之所积为也。”(35)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28页。在人道演进过程起根本推进作用的并非人类整体的智慧进化、物质积累——这些某种程度上只是这一演进的结果,为康有为所真正看重的根本推动者乃是圣人,人类之智日益生的开端是“一二圣人少补其灵明而智生矣”,这也正解释了为什么在他的表述中“理者诸圣人之所积为也”与“理者人之所立”并行不悖,在普遍抽象的论述中可以说理为人所立,但当论述进入具体的历史—政治视域时,唯有圣人能够裁成辅相。故而在《万木草堂口说》中记录下了如此文句:“天理,圣人犹裁成辅相之,故圣人不以天为主,而以人为主,是天理二字非全美者。”(36)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1页。圣人之制作恰恰因其“以人为主”而得为“裁成辅相”。
五、“以人为主”的圣人观与作为“人道”之教的孔教
康有为在《中庸注》中对“中和”之为大本达道的注解更为极端化地表达了他对圣人为历史中的文明奠基这一观点:“凡礼乐政教之蟠天际地,明物治人,扬辨幽微,范围博峻,然其本始,甚微甚渺,皆因创制者之性情而生。”(37)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第190页。这在整个《中庸》的注释史上都非常奇异,因为他并没有采用郑玄注“喜怒哀乐”为“天下之大本”的思路——这也是清代汉学学者如凌廷堪等倡导“以礼代理”时的人性论根据,这一思路以性情为“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的根本,认为政教乃圣人原人之性情所创制。然而康有为却反其道而行之,直以礼乐政教为“因创制者之性情而生”。这似乎近于荀子“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之说,以礼义法度之伪起自圣人,圣人本身之“圣”成为礼义法度的根本源头。
这种论调在浸淫于现代常识的今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今人以为灵智、礼乐、政教的出现乃是人类自然进化的一个结果,圣人的作用至多像章学诚所言,乃有见于历史之不得不然而有所经纶制作者:“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38)章学诚著,叶瑛注解:《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0-121页。圣人从属于历史本身的发展,而不可能超越于历史之上,道只能通过历史自然展开:“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39)章学诚著,叶瑛注解:《文史通义校注》,第119页。历史由此呈现为道逐渐展开渐形渐著的过程,圣人只是有见于道之自然而有不得不然,不可能越过历史直接与道沟通:“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道”作为“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不能为任何人直接认识而只能表现为“万事万物之当然”——作为“道之迹”即历史而为人所知,历史是沟通道与人的唯一方式,圣人只能于史中明道,或者说圣人似乎只是道在历史中实现自身的工具——道借助圣人的“有所见而不得不然”来将自身实现为具体的历史。在这样一种更易于为今人所接受的历史主义式的圣人观的视野中,康有为对圣人的推重确实会显得是非常异义之论,而以历史主义的圣人观为依据反驳康有为之说为浅薄荒谬之说,或者认为这种推重仅仅是因为康有为试图以孔子为教主或试图树立孔子的神圣地位,就显得名正言顺、证据确凿(40)然而孔教论是康有为对“圣人”与历史本身严肃思考的思想结果及其政治实践策略,在论述中不能倒果为因,将之直接等同于康有为对圣人的思考本身。我们所要作的,就是在康有为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中尝试解释,康有为是在何种意义上推重圣人甚至提出“一二圣人少补其灵明而智生矣”的说法的。。
康有为的观点与这种历史主义的圣人观念全然反对:“自羲、轩、神农以来,中国于是有智,欧洲自亚当、衣非以来,于是有智。虽阿墨利加洲、墨西哥、秘鲁之先,亦有礼乐文章宫室舆服之盛,特其后亡之耳。”(41)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12页。当抽象的普遍人性论落实在具体文明演化的历史轨迹中,仁义礼信皆生于智的逻辑也就成为了圣人能成人之智、故能成礼乐文章宫室舆服之文明的逻辑。故而康有为认为,人之智待圣人出而补之然后成、礼乐政教皆因创制者之性情而生、理为圣人所积为。理解这一观点的关键在于理解康有为的自然—人为之辨及其重建天人关系的努力。在历史主义的圣人观念下,圣人作为道在历史中展开的媒介实际上并无主体性,圣人之不得不然依附从属于道之自然,圣人之经纶制作就成为道在历史中的呈现。因此,在章学诚式历史主义的圣人观念下,自然与人为之间不存在龃龉,圣人之所为不过自然的实现。而康有为对于“人为”“智性”价值的强调以及对圣人为文明奠基观点的坚持,似乎都在自然—人为之间划出了罅隙。然而康有为早年深受章学诚影响,他并非不知章式历史主义的圣人观念,而恰恰正是从章学诚式的天道—圣人相合的历史主义中,康有为开始向那个为他所看重的罅隙跳跃。
这一跳跃在其思想痕迹中早见于《内外篇》中的《性学篇》:
中国五帝三王之教,父子夫妇君臣兄弟朋友之伦,粟米蔬果鱼肉之食,诗书礼乐之学,士农工商之民,鬼神巫助之俗,盖天理之自然也,非人道之至也,顺人情而教之,非学而为之也,非独中国然也。何也?夫人类之始……三人具,则豪长上坐而礼生焉;声音畅,则歌谣起而诗出焉。同时而起者也,土鼓蒉桴以为乐,立章约法以为书,更其后者也。此五者,人类未有能外之者也。(42)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12页。
这段文字就表面文意看来与章学诚之名篇《原道》篇首之义如出一辙,尤其是其中“三人具,则豪长上坐而礼生焉”的表述与章学诚“三人居室……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之说非常相近。更重要的是,此处康有为似全从章学诚之说,直以人伦政教、诗书礼乐为天理之自然,甚至更进一步将讨论的视野从“中国”扩展到了“人类”,认为作为天理自然的人伦政教、诗书礼乐之发展不独中国如此,人类皆然,由此将章学诚所谓“天道之不得已”进行了更为普遍化的激进推扩。
这看似与之前所述康有为提出的礼乐政教出于圣人之智相龃龉,康有为所以为的圣人之智绝非仅仅“顺人情而教之”而已,这里的相近不过是其思想起跳的起点。他在将人伦政教归为“天理之自然”的同时,并不认为顺应天理便是“人道之至”,人道之为人道在于人之能“学”:
凡言乎学者,逆人情而后起也。人情之自然,食色也,是无待于学也;人情之自然,喜怒哀乐无节也,是不待学也。学,所以节食色喜怒哀乐也。(43)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12-13页。
康有为所规定的“学”的基本特点就是“逆人情而后起”,圣人创制政教固然“调停于中,顺人之情而亦节人之性焉”,却非“学”之至,这也就突破了戴震、焦循、凌廷堪等人“学以节性”之说所赅括出的“学”的范围。
人伦政教因天理之自然而设,是人之为类顺遂其自然所具有之食、色、情、欲所构建之不得不然者,而“学”则代表了“天”之外全然属于“人”的领域,在康有为看来佛教是为“学之至”者:“自六根、六尘、三障、二十五有,皆人性之具,人情所不能无者,佛悉断绝之。故佛者逆人情悖人情之至也,然而学之至也。”佛教因其为“逆人情悖人情之至”而为“学之至”,而“学”之为“人道”则代表了人试图突破自然下的不得不然进而赢得并全然贯彻其人道公理的努力:“人好食则杀禽兽,不仁甚矣,圣人知其不可,阴食之而阳远庖厨以养其仁心,欺矣。佛则戒杀生不食肉焉。人好色则争夺杀身忘亲,圣人知其不可,阴纵之而阳设礼教以束缚之。夫色心之盛岂能束缚?必至不义也。佛则戒淫以绝之。”(44)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12-13页。佛氏之戒杀戒淫在康有为看来实际上是仁义之至、人道之至,而圣人节人之情调停于中所出之法却只是不得已下的妥协之举。尽管康有为多次批评佛教“源于人道,人情不堪”,但他也往往承认佛教“有高神之理,卓绝之行”,只是因于时势躐等于人情太苦而不能行于世。康有为对佛教式“高神之理卓绝之行”的认同在于,佛教实质上将人道公理推至了极致。前文已述,在康有为看来人之为人其性区别于禽兽之处正在于其有“智”,因其智人方能学,方能在与禽兽同的食色情欲之外得以继善成性,方能由智而仁使其德性得到全然彰显。因此,康有为所肯定的并非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佛教,而是他认知中的佛教,一种毫不妥协调停全然贯彻人之智性而行最为高神卓绝之人道公理的教化。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康有为看来,佛教为代表的种种宗教完全外于以“孔教”为代表的人类政教,这种“外于”康有为试图以地理—历史发展之进程予以解释:“以地球论之,政教文物之盛,殆莫先于印度矣。……印度居中,于昆仑为最近,得地气为最先,宜其先盛也。至于佛,盖其末法矣。”(45)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30页。“印度文物尝大盛矣。……盛极而后,佛学出焉,阴阳互长之根也。故人民之先,未有不君师合一,以行其政教如中国者也。事势既极,而后师以异义称尊,离于帝王之以为教焉。……中国陆王之学,离政教而言心亦是也。”印度政教文物盛极而衰之时佛教才作为“末法”出现,乃“离于帝王以为教”者。就整个文明进程而言,“君师合一”式政教如孔教者为始教,“师以异义称尊”如佛教者为末法终教,两者并列为教,“终始相乘,有无相生,东西上下,迭相为经”。
这种始终之教的归纳看似是历史地理学层面的轻率结论,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康有为对于整体人类文明之历史演进的体认,而这种体认某种程度上在之后与春秋三世说相合而成为了支撑起康有为思想体系的史观骨架。康有为述二教递嬗曰:
无孔教之开物成务于始,则佛教无所澄明也。狗子无佛性,禽兽无知识无烦恼,佛不可出。人治盛则烦恼多,佛乃名焉,故舍孔无佛教也。佛以仁柔教民,民将复愚,愚则圣人出焉,孔教复起矣,故始终不能外孔教也。然天有毁也,地有裂也,世有绝也,界有劫也,国有亡也,家有裂也,人有折也,皆不能外佛教也,故佛至大也。(46)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14页。
孔教为阳教而率始,佛教为阴教而成终,人作为类、作为群体其生活必须通过孔教“开物成务”来维持,这是由人的自然禀性所决定的。佛教式的教化因其对机运与自然不屑一顾而高神卓绝得为“人道之至”的同时,却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康有为思想体系更加成熟之时被其判为“远于人道”,如此评判的原因在于,佛教仅仅能在个体层面澄明“人治”所引起的烦恼,个体生命在佛学式教化下得到了跳出天地国家己身的种种畛域限制而实现其作为个体“人道”的可能。但就作为群体的人之为类的人道而言,全然祛除种种畛域界限之后,具有食色情欲的人类在面对无常的机运与自然禀性本身的束缚之时,人类作为群体的共同生活很可能无以为继:“其苦行,大地无比之者矣,彼以炼魂故弃身,然旆于全群人道则不可行。”(47)康有为著,周振甫、方渊点校:《大同书》,第7页。
至此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之前提出的问题本身:在人之为类、人类之有人道的政治—历史视域下,康有为为何提出人之智待圣人出而补之然后成、礼乐政教皆因创制者之性情而生、理为圣人所积为的观点:
故孔子之道,因于人性有男女、饮食、伦常、日用,而修治品节之。虽有高神之理,卓绝之行,如禁肉去妻,苦行练神,如婆罗门九十六道者,然远于人道,人情不堪,只可一二畸行为之,不能为人人共行者,即不可以为人人共行之道,孔子不以为教也。(48)康有为著,周振甫、方渊点校:《大同书》,第7页。
在康有为看来,人之为类所求之人道绝非通过佛教式的“服药”可以达至,人道固然以全然实现其仁智之性为鹄的,但佛教式彻底破除天地国家己身之种种界限以求解脱的方法只会在根本上瓦解人之为类所求之人道,而倘若人之为类的群体生活无以为继,那么个体之解脱又有何意义?人道乃“人人共行之道”,是人之为类寻求真正解脱之道。人之为类的解脱之道只能存在于人之为类的文明之中,佛教之破除天地国家己身种种畛域,看似打通一切使人于天地间得其自由,但实际上将人隔绝于天地人之外沦入虚空,而这便确乎已逆于人道了。
因此,人之为类所求之人道必依托于文明而为道,正是在此对“孔教”“佛教”为阴阳二教“终始相乘,迭相为经”的判分的基础上,康有为得以最终统合二者为真正率始成终之孔教:
孔子教之始于人道,孔子道之出于人性,而人性之本于天生,以明孔教之原于天,而宜于人也。(49)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第189页。
天生人性为有“智”,然此智若为一己之私智则于人道之宜无益,人道之为道,在于“循人人公共禀受之性,则可公共互行,故谓之道也”(50)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第189页。。而能够“循”此“人人公共秉受之性”而教之者,唯有孔子之教,而《内外篇》中的“圣人”其实就是《中庸注》此处的“孔子之教”,故而就人道而言,人禀受于天之智确乎需要“圣人”补之方真正为“智”,也就是说,人之为类所求的、因其本真仁智之性所望上达的“人道之至”——绝非仅仅随顺“天理之自然”,只有通过孔子之教方成为可能。
因此,孔子之为“圣人”的位次就根本上高于仅仅随顺天理之自然而传政教文物的先王,也高过仅仅保守其灵魂以澄明解脱为鹄的而瓦解共同生活之佛氏:“最无欲者佛,纵其保守灵魂之欲;最无欲者圣人,纵其仁义之欲。我则何为哉?我有血气,于是有知觉,而有不忍人之心焉。”(51)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15页。康有为强调因“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不仅仅是他在为其政治行动的动机做出解释,更重要的是这实际上是他自然—人为分际下对政治活动本身可能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贬抑——政治生活并不是佛教式个体能够达至的完全纯粹的“人道之至”,而是在机运制约下人之为类的人道,是不得不混杂自然的人道,故而在以公理“总期有益人道”(52)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第35页。的判断原则下,政治生活的价值层级似乎被相应降低了——圣人虽彻上彻下,但按照《庄子·天下篇》的说法,圣人本身在其位次之外似乎还可以有天人、神人、至人的选择。康有为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利用经典资源对孔子之品位进行说明,《万木草堂口说》中记录其言曰:“圣人是第二等人,实则孔子神人也,孟子言神人,乃圣人加级也。”(53)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64页。这种说法在《中庸注》中得到了继承:“圣之品位,孟子以为在神之下。盖神人惟孔子,自余学之至者,则证圣也。”(54)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第195页。康有为许孔子为惟一之“神人”,高于圣人,原因正在于孔子之为血气知觉之伦以不忍人之心而施不忍人之政:孔子舍弃了作为《天下篇》意义上天人、神人、至人的可能,而成为了惟一彻上彻下者,因此尽管康有为在极大程度上认同佛学,甚至认为佛学与孔子在虚理上完全一致而只有制度不同(55)“佛制度与孔子相反,虚理无不同。”参见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54页。,但他依然认为佛学不如孔子之学宏大全备,原因正在于,只有孔子之教才能真正构建起人道所应有之政治秩序:“释氏舍弃一切,弃家学道,以出烦恼,而生天成佛者。然孔子于明伦教物,实倡此义,令天下人人乐其境遇,不复苦恼,此度人之大仁也。”(56)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