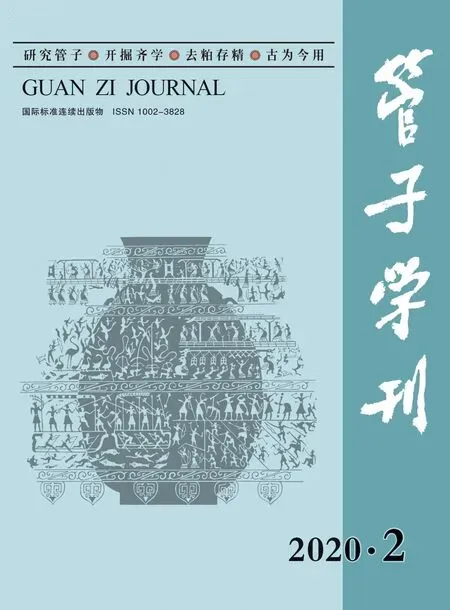化性起伪:儒家荀学派的工夫论及其取向
路德斌
(山东社会科学院 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山东 济南 250002)
以“工夫/功夫”概念来称谓儒家的修身进德之道,当然是宋明以来的事情。但若从内容或思想源头上说,毫无疑问,在儒学创立之初的孔子那里,儒家的工夫论即已奠基,粗简中已然可见其大形之正。而在其后的孟子和荀子那里,在看似势不两立、形同水火的论争中,儒家的工夫论却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建构。二子目标一致,但取径不同。从哲学上说,孟学一派秉持并依循的是唯理主义的理念与思路,而荀学一派恪守和运用的则是经验主义的原则与方法。至宋明,儒家工夫论虽然在儒者们更加自觉的建构中变得愈发精微而系统,但在哲学和方法论上,他们实未超出先秦孟子和荀子所分别拓立并给出经典示范的形态和理路。鉴于过往传统对荀子及荀学多有误读和误解,故本文在此想要梳理并澄清的问题是:同为儒家的孟子和荀子,其在工夫论上的分野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儒家荀学一派工夫论的架构和内容是怎样?其理论主旨和要义又是什么?
一、孟学与荀学:两种“人”观与两条进路
一如大家所知,就个体修养而言,成圣成贤乃是儒家自孔子以来历代儒者念兹在兹、梦寐以求的目标,孟子和荀子当然也不例外。但大家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修身进德的方法上,作为后起的儒者,荀子并没有沿袭孟子的理路,而是在对思、孟之学非难有加的同时,另辟蹊径,自成统系。即如上面所言,从哲学的视角看,孟学一派行的是一条唯理主义的路线,而荀学一派走的则是一条经验主义之路。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从孟学到荀学的这种转向呢?梳理可见,荀、孟间的分道扬镳归根结底实源于他们对“人”作为工夫主体的观解或认知的不同。
先看孟子的“人”观。其言曰: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是如此,那么荀子的“人”观又如何呢?他是这样说的: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荀子·非相》)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
凡是熟悉孟、荀思想的人都会发现,尽管两大体系间有着太多的不同,甚至冲突,但在修身问题上,却也存在着基于共同的儒家信仰而有的高度相同的理念或共识。这之中,起码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其一,圣人的标准在“仁义”,或者换言之,仁义的极致即是圣人。故孟子曰:“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荀子亦教人:“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荀子·不苟》)其二,人人皆可为圣人。故孟子有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亦曰:“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由此足见,所谓的孟、荀之争,说到底其实只是一个“道”同而“术”不同(1)路德斌:《荀子与儒家哲学》,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1-32页。,也即是说,在同宗孔子、同尊仁道的前提下,荀学与孟学间的分歧其实仅在于达成仁道和圣域的途径或方法不同。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目标相同,这路径分歧又是由何而起的呢?透过上面的文本,个中缘由和理路可谓是清晰可辨,一目了然。
在孟子,人之所以皆可为尧舜,原因无他,仅系于一点,即“仁义”内在。如其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简言之,在孟子的认知中,仁义之于人,犹如天赋的观念,生而固有,圆满自足。用宋儒的话说,即所谓:“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2)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页。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之所以会有不善或恶行,并非是因为其人天生就没有仁义之性,而完全是由后天的原因造成的,是欲望的放纵和不良环境的熏染致使其天生完具的良心与良知被遮蔽而放失。也即是说,从本然的或先天禀赋的意义上看,其实人人都是可以为善乃至成圣的,正所谓:“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所以在孟学这里,修身进德的过程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天命之性——良心和良知的重新发现并呈现的过程,用孟子自己的话说,即叫做“反身而诚”——“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人心能思,思则得之,然后存之养之,扩而充之,如是,则睟面盎背,圣贤气象备焉。所以,关于圣贤工夫,孟子有一言以蔽之,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告子上》)
在荀子,涂之人之所以可以为禹,当然亦必须有其在人自身的内在根据(3)就理解荀学而言,此点尤为关键。但在历史上,却总被学者们有意无意地无视和忽略。而宋儒对此无视的结果,就是判定荀学为“大本已失”而将其逐出了儒家道统。,正如其所言:“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那么在荀学这里,这个所谓的“可以知之质”和“可以能之具”又是什么呢?荀子的回答是“辨”和“义”。辨者,辨物析理,是知性;义者,知是知非,是德性。而二者的统一作为理性,荀子认为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当然也即是“涂之人可以为禹”之不可或缺的内在根据——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因此,就其人人生而固有且乃道德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言,荀子之说当然也是一种“义内”。但是,在此务须有一个清楚明白的概念,荀子的“义内”和孟子的“义内”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存在,荀学与孟学之所以会在工夫论上发生分歧并形成两条迥然不同的观念理路,原因正在于此。
即如前述,在孟子,作为道德之源头,“仁义”乃是一种天赋观念般的存在,人人同具,圆满自足。因此,理所当然,在孟学这里,成圣成贤,无须外求,只需反求诸己,扩而充之,即可最终完成德充四体——由“四端”到“四德”的道德呈现。但在荀子则不然,“辨义”之于人,虽亦为道德所必须,但它只是一种为人所独有的天生而来的能力,而非“如有物焉”而存在的天赋观念。因此,就其作为德性之根据来说,虽为人人同具,但却非圆满自足。是有待,而非无待。所以在荀子看来,圣贤人格之修养和实现不可能像孟学所告诉人们的那样,在一身之内,仅通过反求诸己即可完成,而实在是一个“合外内”为一道的结果,也即是一个以人心的“辨义”之能去认知和把握客观而外在的人类“群居和一”之道——仁义法正之“理”的过程。用荀子自己的话说,即是一个“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荀子·解蔽》)的过程。所以,与孟学一派以“求放心”为指归的工夫论不同,荀学一派的工夫论则完全是围绕着如何“合外内”为一道而展开。取向之不同,实乃两种哲学精神下的不同“人”观所使然。
二、化性起伪:荀学工夫论及传统之误解
概括言之,在荀学这里,所谓圣贤工夫,其实即是个体通过人心对道或理(在历史文化中显现为“礼”)的认知和把握从而实现对情欲(即荀子所谓“性”)的统辖、引导以使其合于善而归于治的过程。用荀子的话说,即叫做“化性起伪”。而“化性起伪”之极致——“性伪合”,即是圣王理想或境界之达成,故荀子曰:“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礼论》)
分析说来,荀学的圣贤工夫实质上是一个两“合”的过程,即由“外内合”到“性伪合”的过程。所谓“外内合”,即“合外内”为一道,一如上述,是人心以其独有的“辨义”之能在认知和把握“道”或“理”的同时,将其认定并确立为人行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是即荀子所谓的“知道”与“可道”;而所谓“性伪合”,亦并非是“去欲”“寡欲”、以理灭欲之谓,而是以道制欲,以礼养欲,也即是将人基于自然生理之质而有的情欲追求限制在合“理(礼)”的范围之内而不至导致偏险悖乱之恶,是即所谓“守道以禁非道”。在荀学,“外内合”乃是实现“性伪合”的前提和基础,而“性伪合”则是“外内合”所要达成的境界和目标。因此就个体修养而言,“合外内”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因为没有“外内合”,“性伪合”便无从实现。故荀子有言:“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荀子·解蔽》)
由上述可见,荀学工夫论的架构和理路其实并不复杂曲折,并非难以把捉。然而,回首以往,我们却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诧不已的事实:两千年来,荀学及其工夫论确确实实一直在被严重地误读和误解着!为什么会这样呢?追根溯源,所有的误读和误解其实最终都源于荀子哲学或荀学工夫论的两个核心概念,这就是“性”和“伪”。故在此,我们不得不略作疏解和澄清。
首先,我们来看传统对“性”一概念的误读和误解。
简单地说,在“性”概念问题上,传统于不经意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以孟解荀”(4)路德斌:《荀子与儒家哲学·自序》,第1-8页。,也即是在解读荀书文本时,不自觉地、想当然地由孟子而不是荀子的“性”概念出发、并以之为标准去理解和论断荀子的“性”概念。不错,从文本或概念上看,孟子言“性”,荀子也言“性”。但传统一直混淆不清的是,虽然同谓之“性”,但对孟、荀来说,事实上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如大家所知,在孟学,“性”一概念被赋予的基本涵义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具体内容指的是人先天而有的仁义礼智之“四心”或“四端”。但大家可能并不清楚的是,这一在今天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和运用的“性”概念,在先秦时期却并不是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而是一个属于孟子自己的创见和新说,是孟子通过“性命之辨”,对传统的“性”概念进行了一次“旧瓶装新酒”改造的结果(5)《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而在荀学这里则不然,作为后起的儒者,荀子并不赞成孟子的做法,而是坚持“约定俗成”的原则,非常自觉地在传统的“生之谓性”的意义上使用“性”一概念(6)牟宗三《孟子讲演录》:“‘生之谓性’是古训,它是一个老传统,根据古训来。”。也即是说,在荀学这里,所谓“性”,非但不具有“人之所以为人”之内涵或规定性,而且恰恰相反,它指的是而且仅仅是人与禽兽之共通属性——自然生理之质及其欲望(耳目口腹之欲)。至于“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一如前述,荀子并非没有觉解,但按照“约定俗成”的制名原则,荀子认为决不可象孟子那样用“性”一概念来称名之,而须“稽实定数”,“有作于新名”。所以在荀学的概念体系里,关于“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荀子所使用的名称并不是“性”,而是另外一个,那就是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概念——“伪”。
由此以见,孟学中的“性”与荀学中的“性”,实乃同名而异实,是两个“意义”完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的概念。但遗憾的是,过往的传统并没有理会到这一层,以致两千年来一直为“名”所蔽,深陷在“以孟解荀”的思维误区而不自觉。结果呢,可想而知,荀子的思想倍遭曲解,荀学的精神湮没不彰。仅以“人之性恶”一命题为例,是从荀子自己的概念出发还是由孟子的概念出发,解读的结果完全不同。如果我们是严格按照荀子自己定义的“性”概念去解读,那么这一命题的涵义只是在说,人的属性当中属于人禽共通属性的部分——“性”,是导致偏险悖乱之恶的最后根源。质言之,“人之性恶”并不意味着人的本质是恶,因为在荀学的概念体系中,“性”之所指只是人的属性之一,而不是全部;在“性”之外,人的属性还有另外的部分,那就是“辨”和“义”,依荀子之见,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之本质所在。但若是“以孟解荀”,由孟子的“性”概念出发去解读,结果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在孟学当中,“性”概念的涵义或规定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者”。那么由此出发去解读荀子的文本又意味着什么呢?要言之,有两点:第一,“人之性恶”会在不自觉间毫无障碍地转换成另一个命题——“人性本恶”,即谓人的本质就是恶;第二,荀子关于“人之所以为人者”的所有论述则会被充耳不闻、视若无睹。因为“人之性恶”既然就是“人性本恶”,那么在人的属性当中当然也就不会有另外所谓“人之所以为人者”存在的空间或余地了。如此一来,尽管荀书中一再强调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在“辨”和“义”,但在“以孟解荀”者眼里,说了等于没说,存在如同不存在。故二程有言:“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朱熹亦说:“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荀、扬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朱子语类》卷一三七)误读和误解竟如此之甚,那么在过往的传统里,与“性”概念密切相关的荀学工夫论又如何可能获得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呢?
其次,我们再来看传统在“伪”一概念上的误读和误解。
不客气地说,关于“化性起伪”的“伪”字,过往的传统并不比他们在“性”概念上所犯的错误更小或更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且看传统到底是如何解读的。
梳理可见,在“伪”字问题上,自唐宋以来,学者们沿着两条解释路径形成了两个传统:其一是以宋代的二程和朱熹为代表,将“伪”字解为“真伪”“诈伪”之“伪”。沿着此一路径,荀子人性论的基本命题——“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在理学家们那里,则被解读成了一个与其本义甚相乖离的命题——人性本恶,善乃伪为。其二则是以唐代杨倞为代表,释“伪”为“为”,即“人之作为”之义。曰:“伪,为也,矫也,矫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皆谓之‘伪’。”
不消多言,第一种解读与学者们在“性”字上的“以孟解荀”交相呼应,更加坐实了理学家们关于荀子“人性本恶”“大本已失”的认知和判断,并在事实上确实左右了其后很长一个时期荀子与荀学的际遇和命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清代以来,在学术上黜宋崇汉的背景之下,学者们关于“伪”字的解读大都又回到了唐代杨倞的解释路径上来,一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杨倞)其说亦合卿本意。后人昧于训诂,误以为‘真伪’之伪,遂哗然抨击,谓卿蔑视礼义,如老、庄之所言。”以至今天,理学的传统已鲜再有人附和,学者们的读荀与解荀悉依杨倞的路径以展开。但现在的问题是,杨倞对“伪”字的解读真的就完全符合荀学的本义吗?其实非也。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自己对“伪”字的表述。《荀子·正名》曰:
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
在这里,如果我们可以做到不先入为主的话,就应该能够清晰地看到,荀子所谓的“伪”其实有两层涵义或两种存在状态:一是作为先天“能力”而存在的“伪”;二是作为实践“过程”而存在的“伪”。具体说,在荀学这里,“伪”首先必须是人心固有的一种能力,因为这是后天“过程”之所以可能的内因和根据,否则,“过程”之“伪”便无从产生和展开。至于“能力”之具体内容,毫无疑问,就是荀子所谓的“辨”和“义”。其次,“伪”还必须有后天之“过程”,否则,先天的“辨义”之“伪”亦无由实现和完成,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天赋或潜能而已。而这个过程,就是荀子所说的“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荀子·解蔽》)的过程,当然也即是一个“心择能动”“虑积能习”的过程。
如此而然,我们再回头看杨倞的释读,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诚然,与程、朱释“伪”为“真伪”“诈伪”之“伪”相比,沿着杨倞的解释路径确实可以更加接近荀学的本义,但遗憾的是,杨倞将“天性”与“人为”对置起来的做法,却又在不经意间为一睹真相或全貌设置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所以我们从杨倞的释读中可以发现,他只是道出了“伪”字的后天“过程”义蕴,而未见甚至否定了“伪”作为先天“能力”的存在和意义。于是乎,在自清代以至今天的解读中,荀学中的“伪”一直被看作是一种与人的本性无关因而缺乏内在根据的、完全后天和外在的工具性行为。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清儒一再诟病宋儒在“伪”字释读上的荒谬并试图给予矫正,但却并未因此从根本上改变宋儒以来对荀子人性论的错误认知和判断。因为在清儒这里,“伪”同样是外在的,故而荀子的人性论也依然还是“人性本恶”,依然还是“大本已失”。
否定了“伪”的先天属性——在这一点上,杨倞与程朱是一样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否定了荀学工夫论本身,因为在荀学当中,所谓圣贤工夫就是一个“起伪”以“化性”的过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试想,一个纯由外铄、与心无干从而没有主体性的“伪”,又哪来“工夫”之可言呢?
当然,事实上即如前述,荀子、荀学的“伪”决非如宋儒程、朱之所断,亦非全如杨倞、清儒之所解。确而言之,“化性起伪”的“伪”有两重义涵且缺一不可:其一,从先天的意义上说,“伪”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植根于人心并以“辨义”为基础而趋向于善的能力;其二,从后天的意义上说,“伪”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起伪”以“知道”“可道”以“化性”从而实现由“外内合”到“性伪合”的过程。
由此以见,在儒家荀学这里,“伪”之一字是何其关键和重要,不仅关涉到了荀子、荀学过往之际遇,而且亦攸关荀子、荀学未来之命运和发展。而单就工夫论来说,毫无疑问,“伪”之所在其实亦即是荀学圣贤工夫之所在。
那么,作为先天固有之能力或禀赋,“伪”在现实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而其作为圣贤工夫之担当,具体的方法和路径又是如何?
依荀子的表述,在现实生活中,人之“伪”大致有两种表现或发挥作用的方式,用笔者的话来概括,一种可以称作“伪”的消极表现,另一种则可称作“伪”的积极表现。具体说,所谓“消极表现”,指的是“伪”在人的道德行为呈“他律”状态下的表现。即如荀子之所言:“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在此一状态下,“伪”并非不在,也并非没有表现,但其作用仅止于对礼法规范之消极的、被动的接受和遵从,用荀子的话说,即是所谓的“法而不知”。在荀子看来,“消极表现”乃是“伪”在现实生活中最为普遍的状态,大多数人之所以不能进德成圣而不免为众人,原因即在于此。而相反,所谓“积极表现”,指的则是“伪”在人的道德行为呈“自律”状态下的表现。与“他律”状态下的消极表现不同,在“自律”状态下,人作为道德的主体,对其天生而有的“可以知之质”和“可以能之具”有充分的自觉,故而能够在破除内外之蔽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发挥人所独有的“辨义”之能,“知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其结果当然就是儒家人格目标的达成——或为君子,或为圣人。
如此说来,在荀学这里,所谓“工夫”,其实不是别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起伪”以成就其“积极表现”的问题。具体说,也就是一个如何发挥人心所独有的“辨义”之能,在“性”与“伪”的关系框架下,“知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从而最终达成“性伪合”之圣人境界的问题。
那么,在荀学这里,人究竟如何才能“起伪”,如何才能达成“圣伪合”的境界呢?为此,荀子从“心”与“行”两个层面,双管齐下,构建起了一套独具特色、明显不同于儒家孟学一派的修养理论和方法,用荀子的话说,即叫做“治气养心之术”。即此,稍作梳理如下:
(1)“心”上工夫——“虚壹而静”
依荀学的理路,“辨义”之能作为“可以知之质”和“可以能之具”是人皆有之的,因此从先天的或本然的意义上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能力成圣成贤的,都能够“知道”“可道”,然后“守道以禁非道”,此即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然而,一个显而易见、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自古迄今,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或者事实上并没有成圣或成贤。应然与实然间,落差竟如此之大,原因又何在呢?这显然是一个需要给出解释的问题。依荀子之见,造成此种落差的根本原因并非其他,而是“天君”(即人心)易受蒙蔽所使然。他这样说:
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乱国之君,乱家之人,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妬繆于道而人诱其所迨也。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所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是以与治虽(离)走而是己不辍也。豈不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荀子·解蔽》)
“天君”虽有“辨义”之能,但在蒙蔽之下却无法发挥其本有的作用。故在荀学这里,圣贤工夫的第一步就是“解蔽”。而解蔽之方法即是所谓的“虚壹而静”。故荀子曰:
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两)也,然而有所谓一(壹);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壹)。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荀子·解蔽》)
虚者,虚怀若谷,勿以自满;壹者,以道观尽,勿滞一隅;静者,仁知清明,勿令智昏。臧而能虚,两而能壹,动而能静,此乃人心本有的功能,也是人心“知道”“可道”之前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心却很难保有这种本然的状态,而总是相反,是普遍的、经常性的处在被遮蔽以致功能丧失的境地——能臧不能虚,能两不能壹,能动不能静。故在荀学看来,若想达成圣贤境界,务须做到“虚壹而静”。因为唯其如此,人心才能够跳脱“蔽于一曲”的心术公患,才能够恢复并发挥理性本有的能力,知“道”可“道”,“守道以禁非道”,而最高的成就便是“辨义”之能发挥之极致——“大清明”的圣人境界:
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荀子·解蔽》)
(二)“行”上工夫——“学而成积”
人创造了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了人。在生活中,没有人会怀疑或忽略环境与习染在人格塑造过程的作用,但在哲学上,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重视和强调的程度确实有很大不同。而在荀学这里,基于“习俗移志,安久移质”(《荀子·儒效》)的认知,荀子对此一人格要素尤为重视故多所思考,并由此形成了其哲学最具特色的部分。即此,荀子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及概念叫“积靡”。其言曰: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荀子·儒效》)
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荀子·荣辱》)
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荀子·儒效》)
“积靡”不只是“成己”,亦在“成人”。王天海释云:“积,有积久渐成之义;靡,有习染、影响之义。”(7)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32页。其说甚然,无庸赘解。在此最为紧要的问题是,人们究竟该如何去做才会收“积靡”之效呢?由荀书的论述可知,“积靡”最基本的形式正是荀子所谓的“学”,曰:“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既如此,那么在荀学这里,何谓“学”?内容是什么?方法或途径又如何?关此,《荀子·修身篇》有一个纲领性的表述,曰:“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而围绕此一纲领的阐述和表达,在荀书中可谓俯拾皆是,如曰:
礼之生,为贤人以下至庶民也,非为成圣也。然而亦所以成圣也,不学不成。(《荀子·大略》)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
学之径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荀子·劝学》)
学莫便乎近其人。……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徧矣,周于世矣。(《荀子·劝学》)
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荀子·性恶》)
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荀子·劝学》)
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为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荀子·劝学》)
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儒效》)
“不学不成”,学以致圣。很显然,“学”在荀学中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从诵经读礼到求师择友,从择乡就士到近好其人等等,凡后天习养及所得,皆在“学”的范畴之下。而且在此尤须看到并注意的是,“学”的过程其实即是一个“起伪”以“化性”的过程,同时在很多人那里还呈现为一个由“伪”的“消极表现”向“伪”的“积极表现”转变和提升的过程。也即是说,虽然从生活经验上看,“伪”在不同的人那里确实有“消极”与“积极”之别,但就个体修养而言,在“消极表现”与“积极表现”之间却并不存在一个截然二分、不可逾越的界限和鸿沟。任何人——无论工农商贾、智愚贤不肖,皆可以通过“学”的工夫,由凡入圣,“下学而上达”。故荀子曰:“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荀子·性恶》)
三、心:圣贤工夫之枢纽
在工夫论或伦理学上,因“以孟解荀”而给荀学带来的最严重的误解就是对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否定。的确,依孟学的理路,一个“以性为恶,以礼为伪”因而“大本已失”的荀学,又哪来主体性之可言呢?但稍览荀书却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荀学,涂之人之为禹,固然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从根本上说,却并不是一件被动无为、纯属偶然的事情,而是相反,在现实生活中,你最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为君子还是为小人,是成了圣人或者只是一介凡夫,归根结底其实是完全可以由人自己做主的,用荀子的话说,即取决于每一个体的肯与不肯、为或不为。荀子的话讲得很明白,其言曰:
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荀子·性恶》)
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豈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荀子·儒效》)
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然而跛鳖致之,六骥不致,是无他故焉,或为之,或不为尔!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
孔子尝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荀子的认知和理念显然与孔子一脉相承——圣凡在己,孰禁我哉!所以在荀学这里,人于道德活动中的主体性其实是毋庸置疑的。既如此,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人的这种道德主体性又是由何而来的呢?从《论语》看,孔子对此似乎尚缺乏理论上的自觉和阐述,但到荀子这里就不同了,已然是思索孰察,清晰了然。荀子的回答是“心”,是“心”作为“天君”的独有属性所使然。荀子是这样表述的:
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荀子·解蔽》)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荀子·正名》)
很显然,荀子是“自由意志”论的拥趸。纵览整个中国思想史,对“意志自由”的表述,恐怕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的任何一个概念能够比荀子的“出令而无所受令”来得更加贴切和明确。依荀子之见,与禽兽及万物相比,人心作为“天之就者”,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存在,它不仅固有禽兽所无的“辨义”之质,而且还具有根据个人意愿而对自身行为作出自由取舍和予夺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虽同为天之所生,但人却能够超然于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能起伪,能化性,能生礼义而经纬天地,故最终能够与天地跻立为三而同其伟大。
善恶由乎心,圣凡由乎心,甚至就连具有本根意义的“道”,对人及其社会来说,其行与不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也都是而且也只能透过“心”来展开和实现。难怪荀子会说:“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心”乃圣贤工夫之枢纽,由此足见,毋庸置疑。所以,就荀学工夫论而言,最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让具有“主宰”(自由意志)能力的“心”始终是运行在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轨道上。用荀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如何保证“心之所可中理”?如何避免“心之所可失理”?(《荀子·正名》)荀学工夫论的全部建构及努力如“虚壹而静”以“解蔽”,如“学”而“积靡”以致圣,等等,归根结底其实都是围绕着此一问题而进行、而展开。而这也正是荀学中的核心概念——“伪”的真正主旨或要义之所在。故于荀学工夫论,荀子有一句话讲得极为中肯和切要,他说:
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
在以往的解读中,这句话常因理解问题而引发疑惑和不解,这难道是说圣人之“伪”与众人之“伪”先天就是不同的吗?当然非也。因为在荀学中,所谓“圣人”,并不是一个先天的而是后天的概念,一如所言:“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荀子·荣辱》)。依荀子之见,天之生人,除了“性”即自然生理之质及其欲望是人人相同之外,“伪”作为成圣之能力(即“辨”和“义”)同样是生而固有,无人或缺,故其言曰:“涂之人可以为禹。”因此,此所谓“异而过众者,伪也”,决不是就先天之“能力”说,而是就后天之“过程”说。质言之,圣人与众人之区别,并非源自先天,而完全是“伪”的能力在后天的伦理生活中发挥作用或实现程度的不同所使然。至于这种能力在个体那里究竟能发挥几何、实现几何,不消多言,全看他们的“工夫”用到了几何。如此而然,对于荀子的表述,我们不妨稍作改易,直白但不失准确,曰:“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材性知能也;所以异而过众者,工夫也。”工夫到了,即为圣人;工夫不到,便是众人。这就是儒家荀学派的工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