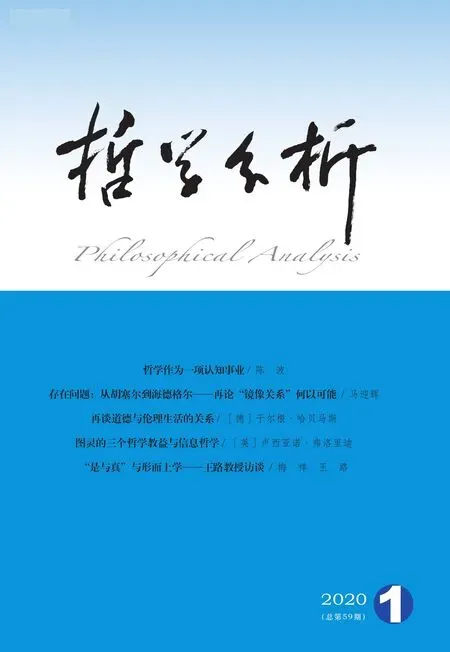存在问题: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
——再论“镜像关系”何以可能
马迎辉
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关系问题之所以受到学界的持久关注,笔者认为,首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尝试解决的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比如思与存在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为现象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在《镜像关系》①参见马迎辉:《镜像关系中的海德格尔与胡塞尔》,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一文中,笔者曾初步探讨了海德格尔各个时期的存在建构与超越论现象学之间可能存在的镜像关系,但这仅仅是理解他们之间关系的第一步,因为我们并未解决既然存在镜像关系,他们之间何以还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这一更为关键的问 题。
本文将尝试通过对如下问题的探讨解决这一难题:首先,从描述心理学到超越论现象学,存在问题先后被胡塞尔理解为完满的充实状态以及被思的多维存在,后者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建构的镜像;其次,在跟随胡塞尔学习现象学之前,海德格尔就已经明确了单义的最高存在与超越的一(及其所建构的存在)之间的根本差异,但他对超越论现象学的存在论“改造”却使他实质性地放弃了这一差异;再次,通过对“无”的重新诠释以及对环形存在之内在因素的揭示,海德格尔返回了单义存在,他对尼采的解读以及对神人关系的看法在此基础上都可以得到恰当的理解;最后,本文将指出,海德格尔对四方域的构想可以看作在更高的存在层次上对体验流形或者连续统的表达,新形态的哲学仍然有赖于思的范式上的突 破。
一、绝对存在
按照海德格尔本人的说法,他对存在问题的兴趣发端于布伦塔诺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而胡塞尔的探索则是他对此问题的现象学研究的前史,他评述道:“胡塞尔本人在《逻辑研究》中——主要是在第六研究中——已经切近于本真的存在问题,但在当时的哲学气氛中不能将其贯彻到底。”①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孙周兴修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3页。针对他与胡塞尔在存在问题上的关联,我们可以提出两个问题:首先,海德格尔是如何继承并推进胡塞尔对存在的理解的?其次,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之后对存在是否有新的探索,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建构与胡塞尔的新探索之间是否有某种关 联?
学界较为关注第一个问题。倪梁康先生曾将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推进”归结为将胡塞尔的意向性改造为敞开性,进而将存在规定为揭示和去蔽。②倪梁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笔者在此尝试要追问的是,如果海德格尔的“推进”是内在的,那么存在的先行敞开是否也以某种方式隐含在胡塞尔的思考中,它又是如何被“耽搁”的?这些思考会指向第二个问题:被“耽搁”之物对胡塞尔的超越论转向有何影响?它与超越论现象学中的新的存在又有何关联?如果考虑到《观念》对绝对存在以及各个区域存在的建构远早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建构,那么这些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了。
传统经验论认为,直观只能容纳并作用于感性材料,存在是不可能被直观到的。胡塞尔提供了新的可能,他将存在理解为“在相即性中同时被意指和被给予的对象的同一性”,以及“在相即性中被感知之物”。③胡塞尔:《逻辑研究》II/2,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A598/B2126。对存在的直观是现象学的新直观理论的最佳范例,正是在此基础上,胡塞尔开始将感知规定为“以此证实的自身展示之方式而充实着的行为”④同上书,A614/B2142。,而直观的本质就在于具有范畴形式的含义的“现实的和自身被给予的显现”①胡塞尔:《逻辑研究》II/2,A615/B2143。。胡塞尔的发力点是充实意义上的自身被给予性,范畴形式落实在奠基性行为的共形变异②同上书,A632/B2161。,或者说,行为质料的相合统一的可能性 上。
是否存在一种先于充实意义上的自身被给予的、更原始的存在概念?胡塞尔并未提出这一问题,因为他以充实和代现为基点对直观的扩展确实将本已超出感性领域的自身被给予性拉回到了感性行为的某种形式的变样中。在此意义上,认定胡塞尔的存在概念也只是存在者的存在确实有其合理性,而海德格尔随后向揭示和去蔽的扩展也确实隐含了激活被代现论“压抑”了的范畴的绝对性和原初性的意图,大致上也是可接受 的。
但人们很容易完全接过海德格尔接下来的想法:既然存在的揭示和去蔽含义超出了存在在实显意向中的自身被给予性,那么就不应该再局限于感性行为及其变样中,而应该另寻出路,比如寻找一种其唯一特性就在于建构其存在的存在者。但这种理解对胡塞尔及其所代表的哲学传统并不公平,因为在《逻辑研究》之后,胡塞尔很快意识到从充实和代现角度对范畴形式的限制是不恰当的,现象学还原随之而 起。
现象学还原最早出现在内时间意识研究中③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65、184页。,这不是偶然,因为这项研究要求以体验的延续为基础建构延续的体验,这首先就要求悬隔现存的体验,进而揭示其被建构的可能,而感知立义是一种瞬时性的意识行为,它根本无法揭示体验的延续,立义模式必然会受到彻底批 判。
胡塞尔将还原的产物称为绝对给予性④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现象学剩余⑤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以及纯粹意识⑥同上书,第90页。。但这些说法并不清晰,一定程度上甚至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绝对被给予什么?与纯粹意识一样,“绝对”容易让人联想起意向行为的绝对性,仿佛只需剥离意向行为中的实项内容,行为便自然会成为绝对和纯粹之物,而“剩余”的说法更容易让人觉得现象学还原缩小了存在范围,绝对和纯粹之物只是一点剩余物而 已。
根据胡塞尔,以时间意识为构架的纯粹意识展现从活的当下对横、纵意向性,或者用贝尔瑙时间手稿中的说法,从一维流形到二维连续统的构造。⑦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肖德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2页。在他不同时期的探索中,纯粹意识的多维建构所敞开的绝对存在为超越论构造奠定了不同层次的基础:简言之,《观念》时期的习性和人格研究建基于体验流的纵向维度,而《沉思》之后的本性现象学则奠基于活的当下。⑧对此问题的初步探讨请参见马迎辉:《意向性、绝对流与先验现象学》,载《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由此,超越论的思并非一种无深度的表象意识,而是有其习性、历史以及本性维度的存在关联。现象学还原揭示的是一种全新的、建构性的存在领域,而描述心理学由于局限于行为现象分析,从而遮蔽了这一存在建 构。
从对象意义上的完满的被充实状态到由多维的纯粹意识所建构的绝对存在,存在问题在胡塞尔那里有其独立的发展脉络,相对前者,绝对存在不仅更为本源,从建构性上看,它甚至具有了海德格尔所要求的先行敞开的特性。这里存在两种具有竞争性的存在理解:一种是胡塞尔式的内含时间和历史维度的被思的存在,它以数学理性所建构的观念关系为基础;另一种则是海德格尔的以此在之存在的样式展现出的存在一般。海德格尔的存在领会与胡塞尔对存在的超越论建构又有何关联,差异何 在?
二、平行关系
在1927年的通信中,海德格尔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地告知胡塞尔他们之间存在分歧。与胡塞尔坚信只有通过现象学还原,超越论自我作为绝对存在之构造源点的地位才能被确立不同,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生存已经是超越论的了,现象学还原乃至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都应该建基于他的生存论建构。①海德格尔:《致胡塞尔的信》,靳希平译,载《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8—79页。
笔者认为,他们对彼此的理解存在错位。首先,此在无论如何不是心理或物理意义上的存在者,作为在世存在者,他已经是现象学还原的产物了;其次,当海德格尔坚持此在的生存论建构是现象学还原的基础时,他的现象学立场已经超出了《观念》第一卷。第一卷的现象学还原最终揭示的是纯粹意识与超越论自我之间的构造关系,但其中的超越论自我被刻画为纯粹体验的一种极化形态,它本身无内容,也正因为此,胡塞尔在《观念》第二卷开始探讨身体动觉对自我的构成意义,在此基础上,笔者更倾向于将海德格尔的批评同情地理解为对这种极化自我的不满,而他本人揭示的“主体”在世界中建构世界,实际上就是《观念》第二卷所展示的习性现象学的主 题。
纯粹意识构造的是意识自身的存在,还是存在一般?如果是后者的话,这种构造又何以可能?海德格尔当然认为纯粹意识建构的只能是它自身的存在,是区域性的。但有趣的是,尽管海德格尔坚称胡塞尔忽视了存在问题,但他本人对存在的追问一开始也陷入了对一种区域性的存在,即此在之存在的追问,因而并未真正超出胡塞尔,而是更多地从存在一侧区别于后者,如何看待这些奇特的现 象?
首先,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并不相同:胡塞尔着眼的是巴门尼德—柏拉图的思的传统,存在是被思的,思与被思的存在之间具有一种先天的平行关系;从海德格尔的视角看,存在何以能成为思的对象这一更原初的问题并未先行得到追问。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笔者认为,原因即在于确实有存在是不可思的,譬如神学所探讨的存在就具有这一绝对的超越性。当然,我们也可以为胡塞尔做点辩护:在德语“Bewußtsein”(意识)中,存在(Sein)就是被意识到的,意识现象学就是对意识如何先天地建构其存在的研究。但海德格尔仍然会说,存在一般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被意识的存在只能被限定在“被意识性”的范围内,同样,在思的范式中,存在的意义也只能在“被意识性”上得到区域性的规定。由此,必须寻找新的、不同于胡塞尔的建构存在的起 点。
其次,当海德格尔将此在视为其建构存在的起点时,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在于,作为存在于此,此在与存在具有一种先天的内在关联,此在之所以被认为能够先天地建构其所领会的存在原因即在于此。这一关联的数理原型可回溯至胡塞尔在其内时间和空间构造中已揭示的连续统的构造。①这里还可以提及外尔的工作,作为希尔伯特的继承人以及胡塞尔的编外弟子,他对连续统的建构与超越论现象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对此问题的讨论,请参见倪梁康:《二十世纪数学基础论争中的现象学——从胡塞尔、贝克尔与外尔的思想关联看》,载《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向来我属性在习性现象学那里同样存在。在胡塞尔那里,习性自我总是在其习性关联中意识到并建构其周遭世界,世界总是为我所属。从存在角度看,胡塞尔的确“错失”了此在及其对其自身之存在的原始建构,但这种超出了被思的存在的存在本就不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主题。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就此忽视此在的生存论建构与习性现象学之间的平行关系,海德格尔的批评甚至就建立在他对胡塞尔的超越论构架的平行移置之上。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一方面将现象理解为“就其自身显示其自身者”②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7页。,在此意义上,现象学的存在论探究的应该是就其自身显示其自身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他却又从形式上将现象学规定为“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③同上书,第44—45页。,即是说,将“就其自身显示其自身者”规定为存在者的存在,另一处说得更清楚:“因为现象学所领会的现象只是构成存在的东西,而存在又向来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以,若意在显露存在,则先须以正确的方式提出存在者本身。”④同上书,第47页。存在“就其自身”显现被替换为从 “存在于此”,即此在出发,从人格现象学来看,海德格尔继承并贯彻了超越论现象学的“主体性”原 则。
笔者愿意进一步指出,即便从此在出发,也是不够的,因为海德格尔并未先行考察何以能从“存在于此”出发,强调此在对存在的向来我属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向来我属性本身仍需辨明:存在何以就必然为此在所属,而不能不为其所属?本真与非本真之辩是无法解决此类难题的,因为它们都已经是存在,并且都已经为此在所属了。实际上,无论遗漏对此在与存在之内在关联的先行考辨,还是在起点上以此在替换存在本身,这些都与海德格尔从存在一侧对胡塞尔的习性现象学的无批判的挪用有 关。
通过对存在之原始显现的可能性的追问,海德格尔看似“超出”了超越论现象学的被思的存在,将存在一般的意义问题提升为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从而在赋予现象学运动以新的问题维度的同时,也隐秘地取得了一场类似基督教神学“取代”古希腊理性式的胜利,但我们同时也不难看到,尽管海德格尔指出了存在问题的根基性,但由于他未能真正找到建构存在的立足点,而是以此在的去—存在取代了存在就其自身的显现,从而保留了胡塞尔式的主体性哲学的“残余”,超越论现象学的因素仍然潜在地作用着生存论建构时期的海德格 尔。
三、存在差异与本己的开端
上文已经指出,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兴趣并非源自胡塞尔,而是布伦塔诺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但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在跟随胡塞尔系统学习现象学之前,他在对司各脱的诠释中就已经明确了单义的最高存在与超越的一之间的根本差异。①笔者学力有限,无力对海德格尔存在之思中的亚里士多德因素与司各脱因素的关系进行深入讨论,这里仅满足于提出这一问题。笔者感兴趣的是,当他从现象学角度建构此在之存在时,存在的根本差异这一“前见”起到了何种作用?②笔者曾批评海德格尔在对思的哲学的批判中错失了柏拉图等人已经揭示的存在的内在差异(参见拙文:《存在抑或善的存在——论海德格尔对存在之“思”的曲解》,载《学术研究》2017年第9期),在引入单义的最高存在与超越的一所建构的存在的差异后,这里需要做一个补充:思的哲学中的存在的内在差异是基于思的各种形式间的差异得出的,它们都属于超越的一所建构的存在,而单义的最高存在在整体上是超越思的。但笔者无意收回这一批评,因为海德格尔批评柏拉图时仍然处于思的哲学的镜像中。
在解读司各脱时,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在每一种明确的范畴形成过程中,我们都把握了一种先行存在的东西。‘存在’因而就意味着对象领域本身的整体意义,意味着在对象性东西中的那种贯彻性的因素,‘存在’乃是范畴中的范畴。”③海德格尔:《早期著作》,孙周兴、王庆节主编,张柯、马小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25页。“其他的超越性,如一、真、善等等,可以被看作是存在的‘近似—特性’,但并非在同等意义上的如同作为对象性本身的存在那般源始。”④同上书,第227页。他与思的哲学之间的分野清晰可见:柏拉图主义将善的存在(一或太一)视为最高的理念,它是智性的对象,而海德格尔则视之为存在的近似物,因存在而存在,对单义的最高存在之思是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海德格尔何以一开始就对胡塞尔持保留和批评态度了,因为后者从未隐瞒他的超越论的理念与柏拉图以来的思的传统的内在关 联。
当海德格尔指责胡塞尔的形式化仍然受困于事质区域时,其最终的根据可归为他沿袭自司各脱的对存在与一的层次区分。思的哲学聚焦的是一对经验领域的建构,最终是“数字”的一,而非“超越的一”。①海德格尔:《早期著作》,第233—234页。在海德格尔看来,似乎正是量的关系加入“超越的一”才使得数学理性成为可能。由是,思的哲学似乎最终只能作用于实在的经验领域,单义的最高存在是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思及的。据此,当海德格尔试图从胡塞尔那里提取出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时,笔者认为,这样做恰恰是危险的,因为这种带有类比色彩的做法很可能使他再次失去他早已获得的与胡塞尔的根本差 异。
但是,海德格尔必须面对一个基本事实,被胡塞尔视为现象学之数学原型的流形论就是一门无量的数学。在《逻辑研究》第一卷的开篇,胡塞尔专门提到:“将形式算术普遍化,或者说,对形式算术进行改动,使它在基本不改变其理论特征和计算方法的同时扩展到量的领域以外,这种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必定会唤起这样一种明察,即量这种东西根本不属于数学之物的‘形式之物’的以及建基于它们之中的计算方法的最普遍的本质。”②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一卷),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AVI/BVI。实际上,就超越论现象学的具体建构而言,无论在空间感知对动觉之流形结构的探讨,还是内时间意识对连续统的构造,抑或《观念》对显相的流形以及意向作用的流形的揭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体验的延伸构型一直被胡塞尔视为了超越论建构的基础。超越论现象学已经突入了“超越的一”的层次。在这里,一是纯粹意识的延伸构型的一,多不是与一对立的外在存在,而是连续统的一的内在性质,一中的每个多都有一的性质。这也从侧面解释了超越论现象学何以能成为海德格尔生存论建构的原像,因为胡塞尔从现象学角度提供了他建构存在所必须的一种“近似”物,但不无悖谬的是,这同时也解释了他的生存论建构何以无法触及存在一般,因为这种“近似物”始终无法消除超越的一所建构的存在与单义的最高存在之间的根本差 别。
胡塞尔的确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确认一种超出“一”并使之存在的存在,因为这种超越的存在的理论背景是传统深厚的中世纪神学,胡塞尔坚持的是柏拉图主义的思路,他要求在超越论的一中建构存在。据此,存在是使“超越的一”成为可能的,还是“超越的一”所建构的,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一开始就存在一种根本无法消除的对 立。
那么,海德格尔又是如何一步步“超出”作为“原像”的胡塞尔的?或者说:他是如何融合其“前见”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原像”,从而在获得其本己的哲学形象的同时“超出”胡塞尔的?我们之前将这种“超出”简化为从存在一侧对胡塞尔习性现象学和内时间意识结构的平行移置,而研究界一般也将此“超出”的文本群确定在《存在与时间》之前的几次关于时间问题的讨论,尤其是《时间概念史导论》中对此在与时间性的关系的分析上,但现在看来,将“超出”单纯确定为“平行移置”,一开始就将其定位在了存在一侧,它展示的是如何以“存在于此”为基点借助思的镜像来建构存在,而没有揭示从思到存在的范式转变的现实可能 性。
实现范式转化至少有两个要件:一是指出胡塞尔从思出发建构存在这一研究范式的内在困难,在这一方向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海德格尔对思(noein)的哲学的简化甚至曲解,譬如将柏拉图传统下的思以及与此相关的艾多斯直观理解为表象和静观①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2页。,将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理解为描述心理学的实显意识;②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1页。二是说明归入存在理路的可能性,这一点非常关键,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他对数学理性的贬抑,比如他告诉我们:“数学是最不严格的科学,因为它最容易通达”③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8页。,在谈及存在者及其存在方式与感性知觉的关系时,他明确说:“我无法知觉到几何关系。”④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笔者无力对此可能性做出全面的研究,这里仅满足于提出一点: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的核心观念在存在一侧似乎同样能得到说明,譬如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中世纪对“形式的存在者之概念”(conceptus formalis entis)与“客观的存在者之概念”(conceptus objectivus entis)的区分已经实质性地赋予了胡塞尔的能思—所思的先天平行关系以存在内 涵。
形式的存在者之概念“是在actus concipiendi(构思的活动)或者conceptio(行构思)意义上的概念能执”⑤同上书,第103页。,是“对存在者的能执,或者说的更普通更小心些,是对存在者的把握。它正是我们标为存在领会以与其他相区别的东西……”⑥同上。而客观的存在者之概念与“存在领会”不同,它就是“那在把握和执着中作为可执着者,更确切地说作为被—执着者的objectum(客体)被对抛的东西,作为在能执中的所执本身,概念内涵(又被称为含义),被対置的东西”⑦同上书,第104页。,其中,“Conceptus(理解到的)、concipere(被理解)属于logos ousia(存在之逻各斯),存在之概念,属于raito(理性)甚或intentio intellecta(智思的意向性)。这里必须将Intentio(意向性)更确切地理解为intentum intellectum(被理解到的意向者),也就是在能执意向中被意指的东西”⑧同上。。
能思—所思的平行关系是纯粹意识的意向构架,根据超越的一建构存在的观点,体验流形建构的就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绝对存在。平行关系不同于对称性,后者预设了关系项的现实存在,而平行关系则特别地与建构相关。形式的存在者之概念意味着在存在领会中把握存在者,而客观的存在者之概念就是被把握者,或者简单地说,构思活动在存在领会中建构被理解之物,这不难让人联想起胡塞尔在探讨能思时对其存在设定的强调。①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02页。从海德格尔角度说,超越论的思的结构早已在存在上得到了述说,因并非胡塞尔的专属物。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则,如果我们完全接受这一类比,那么超越论现象学所展示的这个时代的整体知识状态就很难看到了,这也是笔者最为担忧的;二则,这一类比其实并未使海德格尔完全走出胡塞尔:他强调的是思的结构隶属于思中的存在的逻各斯,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还是表现为在思的存在设定中建构被思的存在,还是从存在领会中谈论能思对所思的建构,存在此时仍然是被思 的。
超越论现象学究竟为海德格尔带来了什么?从单义的最高存在与超越的一的差异来看,我们不难体会到他此时在哲学处境上的被塑造和被压抑的状态以及突破的可能方向:首先,海德格尔有信心在“存在领会”的基础上指责胡塞尔乃至整个西方哲学错失了存在问题了,因为他已经表明,既然超越论的思对所思的建构本身即蕴含了存在关联,那么对此存在关联的先行领会和建构便自然成为了可能的研究方向,更何况这一方向直指他早已明了的从中世纪延续而来的存在问题的框架,当然,这里应该把中世纪神学排除出他的批判范围;其次,本质直观的确为海德格尔提供了描述此在与存在的建构关系的绝好方法,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因为本质直观本身即蕴含了存在关联,但是,一旦采取这一方法,他便会陷入思的哲学镜像,由此不但会遮蔽单义的最高存在,而且必然陷入所谓主体性哲学的窠臼,因为胡塞尔提供的是以流形的延伸关系为基础对“超越的一”及其存在的建构,后者与单义的最高存在具有绝然的区分,此在尽管与存在具有先天的关联,但它无法成为建构单义的最高存在的起点;最后,海德格尔与思的哲学的关系也可以获得更深入的说明,对坚持存在之单义性的海德格尔来说,思的哲学所蕴含的存在的内在差异,譬如柏拉图传统中的智性(noesei)与理性(noesin)的存在之间的差异根本不是挑战②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吴天岳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350页。,甚至完全可以不出现,因为它们都归属于“超越的一”所建构的存在,但对那个在生存论上建构此在之存在的海德格尔来说,错失这种存在的内在差异绝对是问题,人们甚至可以基于其原像指责他错失了善的存 在。
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的方向也是确定的,他无需像胡塞尔晚年所做的那样借助什么根本性的还原,再去更深入地探索主体性的秘密,因为思的哲学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提供建构单义的最高存在的方法,而应该放弃思的镜像,或者套用他生存论建构阶段的术语,尝试揭示某种或某些特殊的“存在者”,它或它们应该具有与领会着存在的此在完全不同的存在特征,以此真正揭示并建构单义的最高存 在。
四、返回“存 在”
单义的最高存在何以可能?对此时的海德格尔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问题,在他系统学习现象学之前就已明确,对此问题的探讨因而意味着回归,同时,它还意味着彻底告别超越论现象学,因为后者确实无法提供建构最高存在的现成方法。但告别超越论现象学是否意味着告别整个思的哲学的范式,尤其是使之成为可能的数理基础?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涉后海德格尔哲学的可能方 向。
笔者认为,海德格尔“回归”以及建构单义的最高存在大致有如下关键步骤:首先,重新解释“无”,从《存在与时间》的作为对世界之否定的“无”和不之状态到“转向”时期揭示创生此在之在世的无之无化的“无”;其次,探索单义存在的内在结构,在对环求积分和环状存在的哲学意向上将单义存在的最终形态展示为天地神人四方 域。
在思想转向前,“无”对此在在世的建基作用就已经显现了。在谈论此在如何见证其本真能在时,海德格尔说:此在的愿有良知意味着“在其罪责存在中从它自身出发‘让’最本己的自身‘从自身中行动’。这种‘让在自身中行动’在现象上代表着在此在自身中所见证的本真能在”①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61—362页。。使此在获得了“‘让’最本己的自身‘从自身中行动’”的是此在对良知呼声的领会,这是此在在其自身中被构造的问题,自身何以能原始地具有其本己性?相对此在之在世,良知的本真呼声已然是一种“多余”了,它具有的这种建构本真能在的力量源自何 处?
良知的生存论建构围绕良知作为操心的呼声以及作为对良知之领会的罪责存在这两个环节展开,海德格尔在这两个关节中都谈及了世界之“无”或“不”的问题:就前者来说,此在在畏的现身情态中被摆到世界之无面前,“此在就在这无面前,在为其最本己的能在的畏中生畏”②同上书,第340页。,作为良知之被呼唤者的此在就存在于世界之无的根基处;后者意味着非现成存在意义上的不之状态,罪责存在就是“由‘不’规定的存在之根据性的存在”③同上书,第348页。。在这两个构造环节中,海德格尔都标识出了无以及不之状态与本真能在的关联:良知的呼声以及呼唤者就存在于它们的根基处。但可惜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并未循此道路继续前行,而是将此在对其本真能在的建构封闭在此在对良知呼声的领会之上,由此错失了通向此在之最终根据的道路,即是说,在生存论建构中仍然呈现出否定性特征的无是否可能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建构性的存在特 征?
海德格尔已经逼近中世纪神学的存在生成于无这一基本立场了,说“逼近”,是因为他此时还没有进一步将之揭示为创生性的存在,对于依然处在思的哲学镜像中的生存论建构来说,存在一般只能是无。但尽管如此,在他对“愿有良知”和“罪责存在”的分析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无”与此在之生存的建构性关系的影子,笔者愿意将之视为对中世纪神学的基本教义的现象学表达。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同时已经逼近“超越的一”所建构的存在的边界,这里的“无”可以看作单义的最高存在与“超越的一”所建构的存在之间的绝然区分在生存论建构中的显示,尽管是隐晦而间接 的。
在从1928—1929年开始的“转向”中,无的创生性开始真正得到展示。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海德格尔指出,与生存论对畏死经验的分析不同:“在畏中,并不发生任何对整个自在存在者的消亡,……无是与脱落着的存在者整体‘一体地’照面的。”①海德格尔:《路标》,第131页。无不再意味着对在世存在的否定,而是对存在者整体的有所拒绝的指引:“使一般存在者的可敞开状态成为可能。”②同上书,第132页。随后,在《论根据的本质》中,海德格尔进一步从存在学上将这种本源之无的创生视为向存在者整体的超越的根据,正是对此根据的建基使此在嵌入无这一事态成为可能,他告诉我们:“唯存在之被揭示状态才使存在者之可敞开状态成为可能”③同上书,第153页。,无之无化被确定为创生此在之生存的存在之无蔽状态。无就此具有了存在的特征,它是本源存在的一种可敞开状态,在自由中的建基。在生存论建构中缺失的良知的存在论基础得到了揭示,正是这种本源存在的无之无化最终“让”此在的最本己的自身行动成为可 能。
由此,海德格尔的所谓“转向”的实质就是经由“无”在两种存在之间实现跨越。与《存在与时间》谈论生存论之边界的“无”不同,他此时已经初步揭示单义的最高存在构造超越的一所建构的存在的可能,此时的“无”意味着一种本源的存在。如何看待这一存在差异?在生存论建构中,对此在的本真与非本真状态的区分中仍然隐含了知性之思与智性之思的镜像,而一旦将创生此之在的“无”确定为本源的存在,那么建立在思的镜像之中的存在差异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存在范式的根本变化。海德格尔似乎彻底告别了胡塞尔以及思的哲 学。
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他告别的其实是胡塞尔式的以超越的一的延伸构型构造存在这一现成的镜像,而没有彻底告别数学理念本身,在随后的探索中,他令人惊讶地试图以他一贯不屑的数学形式,比如对环求积分和环形所折射出的哲学意向来刻画新的存在。换言之,他已不再从连续统的当下化的因素,即存在于此出发来建构“此”的本真的自身性,而是直接就环形的内在存在来看诸存在因素之间的存在关联了。以此范式出发,海德格尔后期哲思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就可以得到较为简易的理解:比如他何以要长时间解读尼采,何以要回溯前巴门尼德哲学,何以如此理解四方域中的各存在因素,尤其是神与人的关 系。
对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于,尼采不仅比海德格尔更早地对思的哲学传统予以了激烈的批判,而且也更早地以一种类似环形的方式展示了权力意志的存在形态,即永恒轮回。在思考方向上,海德格尔对思的哲学的表象性的批判几乎与尼采完全相同:只要思是表象性的,那么表象行为与被表象物的差异必然生成存在的差异,柏拉图据说就是以此将世界一分为二,区分为经验世界与理念世界。要克服柏拉图主义所带来的虚无主义,就必须诉诸某种新的存在。这种新存在当然不可能再以任何类似感性、知性和智性的方式被建构,因为它们首先意味着区分。尼采据此提出了强力意志的永恒轮回的学说,这一点在学界人所共知,同样不陌生的是,海德格尔批评尼采仍然在尝试建构一门在场的形而上学。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一存在形式本身仍可被视为基本的思想平台,他要强调的是思考者以何种思的姿态与存在的永恒轮回关联:“只有当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在虚无主义和瞬间意义上得到思考之际,它才真正得到了思考。而在这样一种思考中,思考者本身就进入了永恒轮回的圆环之中了,但却是以这样的方式,即:思考者也参与了对这个圆环的争取和决断。”①海德格尔:《尼采》 (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36页。海德格尔甚至强调:“尼采哲学返回希腊思想的开端,以它的方式采纳这个开端,并且因而使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追问进程所构成的那个圆环闭合了起来,这样一来,尼采哲学就成了形而上学的终结。”②同上书,第454页。即是说,巴门尼德的持存、在场与赫拉克利特的存在者生成在永恒循环的圆环中被联结起来了。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胡塞尔之后,尼采一度成为了海德格尔探索存在之新形态的镜像。
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海德格尔以其尼采批判为起点,开始揭示原始存在的存在形式。在他看来,“作为在遮蔽中的无蔽,存在更容易遮蔽这一基本特征……但这一对它的本质和本质来源的遮蔽乃是存在原初的自行澄明的特征,虽然这一来,思想恰恰并不追随存在。”③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06页。存在不再以持续在场和生成的方式显现自身,它首先隐匿并为真理抑制自身,继而因自行抑制而解蔽,从而进入存在者,真理之自行发生源自存在的自身抑制。在此,思者对环形存在的“争取和决断”这一在尼采那里仍然带有传统形而上学基调的说法被海德格尔拒绝了:“思想恰恰并不追随存在”,用他在《形而上学导论》中的话说:“所有的意志都植根于让予(lassen),而理智对此却一无所知。”④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因术语统一需要,引文略有改动。存在的抑制与解蔽建构了原始的时间之本质,正是由于与“存在之时代特性的应合”⑤海德格尔:《林中路》,第308页。,此之在的绽出才是可经验的,“存在之时代本质居有着此之在的绽出本质。人的绽出之实存忍受着绽出因素,因而保持着存在的时代因素;而存在之本质包含着这个‘此’,从而包含着此之在。”①海德格尔:《林中路》,第308页。这里存在双重让予:首先,原始存在自身在自行抑制中自行敞开,这种自身敞开就是让予;其次,对存在自身在自行抑制中自行敞开这一运作本身的让予,这是建构此—在的让予。在1943年《论真理的本质》的“作者边注”中,海德格尔明确了这一双向让予结构:“让(予)—存在:1. 不是否定性的,而是允诺——保藏;2. 不是作为以存在者状态为定向的作用。对作为存有(Seyn)的存在的尊重、照管。”②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自行抑制中的自行敞开不是否定,而是创生性的允诺、保藏,而建构此—在的让予则意味着对存有的尊 重。
在对“物”的追问中,海德格尔指出:“物化之际,物居留统一的四方,即大地和天空,诸神和终有一死者,让它们居留于在它们从自身而来统一的四重整体的纯一性中。”③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四方域在纯一性中相互居有、共在互生:“映射在照亮四方中的每一方之际,居有它们本己的现身本质,而使之进入纯一的相互转让之中。以这种居有着一照亮着的方式映射之际,四方中的每一方都与其他各方相互游戏。”④同上书,第187—188页。天地神人的四方域不仅在原始的空间化中,同样也在原始的时间化中以相互游戏的方式存在,按照海德格尔1962年的说法:“时间三维的统一性在于各维之间的传送。这种传送证明自身为本真的、在时间之本己因素中游戏的端呈,就仿佛是第四维——不光仿佛是第四维,而且从实事而来就是第四维。本真的时间是四维的。”⑤海德格尔:《面对思的事情》,第23页。本源存在的运作即是时间—空间的自由游戏,它们都呈现为四维存在者之间的交织运动,相互端呈与创生。在生存论建构时期,此在与存在之间似乎隐含了一种制宰关系:存在创生并制宰着作为其生成物并内在于其中的生存因素,而对神的超越性的体验也被时间化为此在的体验瞬间的到时,但在此原始的圆形存在中,神不再高于有死者,它们相互居有、相互端呈,在笔者看来,这种思考的根据就是存在的单义性,天地神人创始于本源的存在并分有了同样的存在 性。
结 语
“另一个开端”,还是既有的开端?从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来看,笔者倾向于认为,所谓“另一个”实质上就是既有的,它一早就隐含在单义的最高存在中,“返回步伐”因而就意味着“返回”最高的存在,但与中世纪的范式不同,单义被他演化为了四维存在者之间的自由的时—空游 戏。
在此问题域中,海德格尔在其生存论建构时期曾探讨过的经典问题:“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①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6页。是否还有其合理性?海德格尔此时很少再主动以现象学家示人了,这一命题似乎也就变成了伪命题。笔者之所以愿意重提这一老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笔者对“游戏”这类说法始终心怀疑虑,因为哲学的严格性应该随人类理智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我们在海德格尔的新探索中的确重新看到了新的现象学的可能 性。
在1927年左右,胡塞尔曾要求将现象学的存在论建立在超越论的体验流形之上②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6、338页。,从海德格尔的尼采批判来看,胡塞尔晚年揭示的涌流的—持立的活的当下所表征的问题也完全可以被视作一种融合了巴门尼德的持存在场与赫拉克利特的生成流变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超越”了胡塞尔的思的哲学及其形而上学的可能?笔者之所以始终对“超越”的说法持谨慎态度,不仅因为“镜像”本身就包含了不同范式的建构以及思想发生的不同路径的意思,也不仅因为海德格尔的所谓“超越”最终可归结为中世纪神学在存在问题上对柏拉图主义的超越,这种“超越”因而更合乎神学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即便海德格尔后期的存有建构也可以部分地从数学意向上得到理 解。
本有、四方域以及双重让予体现的是多种存在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海德格尔也从不讳言环形结构对此本源存在的建构意义,从数学原型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此举相当于在更高的存在维度上重塑了连续统或者超越论的延伸构型。但是,一旦着眼于存在的连续统及其构造的可能性,我们又将不难发现,在后海德格尔时代,德里达、德勒兹、拉康等人其实已经在本源存在的维度上提出了比互隐互显、相互端呈更为丰富的哲学意向。如何看到这些探索与经典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其中是否蕴含了思的新范式,对哲学本身的发展又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已经成为了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问 题。
——兼论现象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评介
——论胡塞尔对布伦塔诺时间观的继承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