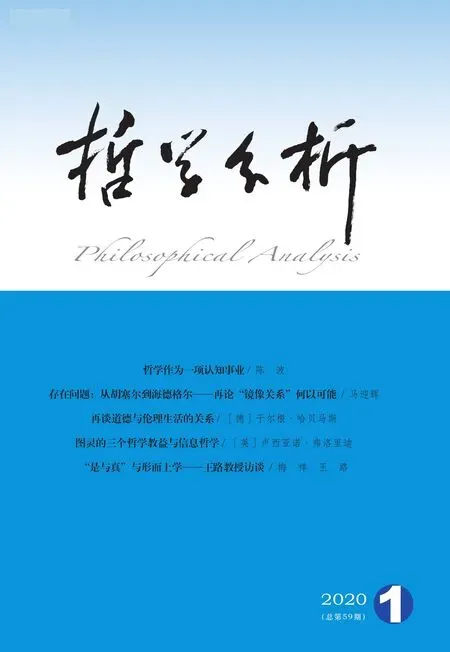哲学作为一项认知事业
陈 波
一、引 言
美国哲学家蒯因断言:科学与常识是连续的,哲学与科学也是连续的。“正如科学是自觉的常识一样,哲学力求将事物阐释得更加清楚明白,就其目的和方法的要点而言,应无异于科学。”①蒯因:《语词与对象》,陈启伟、朱锐、张学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在蒯因那里,“科学”一词有两种含义:狭义仅指自然科学,广义指由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知识所构成的整体。将蒯因的上述论断展开来说,就其目标和使命而言,哲学像常识和科学一样,是人类认知这个世界的总体努力的一部分,它应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就其方法论而言,正像科学方法是常识方法的精致化一样,哲学方法也是对常识方法和科学方法的提炼和总结,没有独一无二的哲学方 法。
牛津哲学家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继承和发展了蒯因的上述思想。他从两个方面严厉批判如下的哲学例外论:哲学研究只是由哲学家在扶手椅(armchair)中完成的,其方法论与评价标准与其他各门科学有实质性区别。首先,他论述说,哲学与科学在研究对象上是连续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中发生的所谓“语言转向”和“思想转向”是错误的,已经过时了。哲学家并不只对语言的性质和结构感兴趣,也不只对有些人所认为的优先于语言的概念、思想、心灵感兴趣,而是相反,像其他科学家一样,哲学家所关注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本身。例如,当形而上学家研究“时间”“空间”时,他们所关注的是这个世界中真实的时间和空间的性质及其结构。当认识论家研究“知识”“真理”时,他们是在探究如下至关重要的实质性问题:究竟什么是知识?如何获得知识?如何证成知识?知识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知识如何在社会共同体中发挥作用?等等。其次,哲学和科学在方法论上也是连续的,只不过有自己的特点。哲学更像数学,两者主要是在扶手椅中完成的,其方法首先不是实验,而是溯因(abduction)和演绎推理。但这并不妨碍它们都是科学。哲学也要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并且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哲学进展主要在于构造解释力更强的更好模型,而不是提供更多有信息量且无例外的普遍概括。我们不应该过多地考虑哲学究竟是先验的还是后验的,因为这个区分在认识论上是表面的和肤浅的。②参 见Timothy Williamson, 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New Jersey: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威 廉 姆森:《溯因哲学》,刘靖贤译,载《哲学动态》2017年第7期;Timothy Williamson, Doing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Timothy Williamson, “Armchair Philosophy”, Epistemology &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56, No.2, 2019, pp.19—25。
我同意蒯因和威廉姆森等人的总体哲学倾向和立场,也同意他们对哲学例外论的批评,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我将进一步提出和论证一个核心论题:哲学是一项认知事业。这个论题旨在强调:哲学与其他各门科学是连续的,它是人类认知这个世界的总体努力的一部分。哲学要帮助人们更好地认知自然界,更好地认知人本身,更好地认知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更好地认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个论题显然是针对关于哲学的其他看法的,例如只把哲学理解为对先贤学说的整理,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对思想传统的继承,对异域思想的引介,对哲学教科书的编撰,等等。这些活动当然是哲学的内在环节和必要部分,但绝对不是哲学研究的全部。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应立足于当代生活现实,在先贤思想成就的基础上,以哲学问题为导向,以论证、对话、质疑、挑战为主要形式,去撞击已有的思想边界,去展开对新领域的开拓和对新理论的创制。一句话,要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由此确认中国哲学家的身份并赢得中国哲学家的尊严。①参见陈波:《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载《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陈波:《哲学研究的两条路径:诠释与创新》,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1期。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上述核心论题做详细展开和论证:就其研究对象与目标而言,像其他各门科学一样,哲学的使命也是帮助人们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就其方法论而言,哲学和科学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哲学与哲学史之间既有连续也有断裂,哲学对哲学史的特别关注并不构成对该核心论题的严重挑战。本文最后回应了对该核心论题的另外两个挑战,认为它们都是想当然的说法,似是而非:科学依赖观察和实验,哲学诉诸诠释与理解;科学重点关注“实然”(事情实际上怎么样),哲学重点关注“应然”(事情应该怎么 样)。
二、哲学的使命:帮助人们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
(一) 人类的利益和需求是人类认知的出发点
在我看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倡导“从人或人类的视角去看世界”。我们生存于斯的这个世界,纵无际涯,横无边界,在时空上都是无限的。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因此,我们对这个世界无法做镜像式的全面透彻的认知,我们认知我们需要认知的,我们认知我们能够认知的。我们的欲望、需求、利益、关切决定了我们要去认知这个世界中的什么;我们所具有的认知和行动能力以及认知资源,决定了我们将如何认知。这两者的结合划定了我们的认知边界,即把这个世界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人化的实在”(humanized reality),即人类认知和行动能够达到了现实世界中的那一部分;“原生的实在”(brute reality),即当下的人类认知和行动尚不能达到的现实世界的那一部分,相当于康德哲学中的“自在之物”(things in themselves)。
有必要强调指出,设定一个“自在之物”的世界是充分合理的,也是绝对必要的。首先,这是对人类先前世代的认知经验的归纳总结和合理外推。当“人猿相揖别”时,早期人类的认知和行动范围很小,只局限于他们当下的生存环境、附近的山川河流,他们重点关注在哪里去获得生存资源以及如何获得,偶尔也抬头仰望星空,看到他们用肉眼能够看到的东西,这构成了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最初认知。随着人类认知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增强,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人群与人群的相互交往越来越多,经验、信息、知识的传播速度加快,他们的认知空间随之大大扩展,从前科学认知,到古代科学,到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他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中很多他们先前不知道的东西。他们也知道,不是他们的认知创造了这些东西,而是这些东西本来就在那里,只是对他们来说先前静默无声地存在着。此类经验积累多了,人类通过归纳总结,由此合理外推出一个论断:有一个原生的、本然存在的世界,它独立于我们当下的认知,超越于我们当下的认知,却构成我们的认知对象。其次,承认有一个“自在之物”的世界,也为人类的未来认知扩展留下了足够大的空间。显然,人类的认知能力在迅速增强:人类遨游太空,潜入海底,探究物质的微观结构,一本本陌生而神奇的“自然之书”正在被我们打开。我们必须承认:它们本来就在那里,只是由于人类先前认知和行动能力的局限,它们不被我们所知,作为“自在之物”在那里存在 着。
虽然哲学和各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以这个世界为认知对象,但它们之间既有分工也有合作。各门具体科学通常以这个世界的某个局部、侧面、维度为认知重点,探究其中的结构、秩序和规律。哲学则要在各门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绘制这个世界的整体画面,探究这个世界的一般性的结构、秩序和规律,因此哲学在抽象程度和普遍程度上远高于各门具体科学。哲学还要质疑或证成各门科学的基本假设,质疑或证成各门科学的价值维度,撞击或推展已有的认知边界。但哲学仍然要在常识和科学理论的框架内活动:利用科学的发现,使用科学的方法,去反思、质疑、甚至挑战常识和科学,去挖掘和质疑科学理论背后所隐藏的根本性假设,去构想做别种选择的可能性。不能据此就断定哲学与常识和科学是断裂的,就如同不能说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现代科学与近代科学是完全断裂的一样,尽管前者否定和抛弃了后者的许多理论断言,但仍有一些关键性要素贯穿其间: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诉诸科学证据,使用科学方法,进行科学验证,最后还要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 可。
(二) 哲学和哲学家如何看待这个世 界?
追求真理是我们的使命。这是因为:真理是我们生存于世的基本凭借。如果一个个体或种群对这个世界及其周围环境常常做出不真实的认知,经常做出错误的决策和应对,大自然就会通过自然选择机制,通过各种途径,让他们的基因从大自然基因库中消失,逐渐把他们这个种群从这个世界上淘汰掉。要对这个世界做出正确的认知,首先必须弄清楚,这个世界中究竟有什么:What is there? 这就是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研 究。
很显然,这个世界中有很多的物理个体,如恒星、行星和卫星,山川河流,果木菜蔬,它们占据时间和空间,有其时空边界,能够被我们的感官所感知。但它们不是孤零零的存在,而是有很多的属性,相互之间发生复杂的关系。由于这些性质和关系,不同物理个体形成不同的自然种类,不同的种类处于不同的层次,受制于不同的结构、秩序和规律。它们相互发生因果作用,由此产生变化和发展。把自然种类进一步抽象化,变成了集合。集合有元素,对集合的元素以及物理个体都可以计数:一个、两个、三个……,由此产生了数。因此,物理个体、性质和关系、自然种类、时空、层次、结构、因果关系、规律、集合和数等等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只不过采取不同的形式,相互之间还有依赖关系:有些是基础性的,有些则是派生 的。
这个世界中还有很多人造物品。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干的种群,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新物品,小至钟表手机、桌椅板凳,大至高铁、摩天大楼、海底电缆、跨海大桥、航天飞机。这些东西与自然物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有物质形态,存在于时空之中,能够被我们所感知。它们与自然物的不同之处在于:里面都灌注了人的思想、观念、设计、制作,甚至情感。没有人的设计和制作,它们就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发挥其作 用。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社会实在”,亦称“制度性事实”,例如,国家、政府、军队、警察、货币、银行、大学、学术研讨会、婚姻……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指出,制度性事实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涉及如下五个要素: 功能赋予、集体意向、构成性规则、语言和背景,其中集体意向是关键性的。在构成性规则“在情境C中,X 被当成 Y”中,X 是原生的事实,Y 是制度性事实,把 X“当成”Y 是由社会集体意向通过语言赋予并确保 Y 有一定的身份和功能来实现的。拿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来说,就其物质形态来说,它就是一张纸,尽管是一张特殊制作的纸,使得它在当代社会中变得如此重要的,显然不是它的物质形态,而是在其背后支撑它的一整套社会制度,是这套社会制度赋予和保障了它发挥神奇的功 能。
还有很多文化构造物,例如神话、民间传说、文学作品、电影、戏剧、动漫游戏等等中的角色,如“女娲”“龙”“孙悟空”“林黛玉”“哈姆雷特”,以及由人所创制的概念、命题、理论、学说,如“区块链”“人是万物的尺度”“实用主义”,等等。这些东西是由现实世界中的人利用各种物质性手段(例如笔墨纸张、电脑和其他器材)创造出来的,又存在于某种物质形态(例如书籍、影像制品、网络文件等等)之中。关于文学人物,我们可以说两种意义上的真话:“孙悟空是唐僧的大徒弟”,这是站在小说《西游记》里面的角度说的一句真话;“孙悟空是吴承恩所创作的一位虚构人物”,这是超脱于《西游记》、站在现实世界立场上说的一句真话。这些文化构造物在我们的理智生活和情感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各种群体、组织、社会、民族、国家等等,他们各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需求、愿望、观念和行为模式,他们对“我”的生存来说构成合作与竞争关系,是“我”必须认知的这个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 分。
如上所列的所有这些“实在”,对于我们的个体生存和类生存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因而都是我们的认知对象,也是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如果“实在”中包括如此歧异的元素和类别,那么,究竟什么是“实在”?如何去说明、刻画、甚至定义“实在”?这对于哲学家来说构成一个严重的挑战。通常的说法是,“实在是独立于人的意识和心灵的存在物”。若考虑到人造物品、社会实在、文化构造物、人类社会等等,这个说法显然不成立,因为没有人的意识和心灵的参与,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或许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C. S. Peirce)所言:“实在并不必然独立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而只是独立于你或我或任何有穷数量的人关于它可能持有的想法……”①C.S. Peirce, The Essential Peirce(Vol.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39.
(三) 哲学和哲学家如何有助于促进或改善对这个世界的认 知?
可以从多方面去回答这个问题,由于篇幅关系,下面只谈两 点。
(1)哲学可以拓展新的认知领域,展示新的思维空间,达至先前未及的认知深度。以前的形而上学家大都只关心自然界中有什么,而约翰·塞尔促使我们注意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除了自然物之外还有什么?哪些东西对于我们作为人的社会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他提出还有“社会实在”,如政府、军队、警察、钞票、婚姻和大学等等,并探讨了如下一些问题:这些社会实在是如何形成的?发挥了哪些作用?如何发挥其作用?等等。显然,这些探讨是非常新颖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形成了“社会本体论”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并对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等等产生重要的影 响。
休谟分别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休谟问题”,一个关涉归纳推理和因果关系,另一个关涉“是”与“应该”,也就是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从事具体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大都使用归纳推理,相信因果关系,据此做出规律性概括,并进而做出对未来的预测。休谟进而追问:这么做的基础和理据是什么?归纳推理能够确保从真前提得出普遍必然的真结论吗?我们凭什么断定事物和现象之间有因果关系?他的这些质疑是深刻的,至今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以致有这样的说法:“归纳法是自然科学的胜利,却是哲学的耻辱。”②施太格缪勒:《归纳问题:休谟提出的挑战和当前的问题》,参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57页。休谟还注意到,有许多作者依据关于“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陈述,得出了“应该做什么或怎么做”的断言,前者是描述性陈述,后者则是规定性或规范性陈述,这两者的差别是巨大的。如何从前者推出后者,或者说,如何从“事实”进到“价值”或“规范”?这就是“是—应该”问题。①参见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9, p. 521。它在当代哲学中以“规范性研究”特别是“规范性之源”的形式被重新复活。什么是规范性?有哪些种类的规范?例如认知规范、伦理规范、法律规范,以及各行各业的规范?这是关于规范性的初步研究;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必须遵守那些规范?或者说,我们为什么“必须”或“应该”?这涉及规范的基础和依据,在追问“规范性之源”,是关于规范的形而上学研究;如何获得和证成我们的规范性信念?这是关于规范的认识论研究;规范如何发生作用?如何确保规范得到实施?实施某些规范会有哪些或好或坏的后果?这是关于规范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规范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合理性问题,是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热点之 一。
(2)哲学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给我们的认知发展提供永不衰竭的动力。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实际上,这个断言可以推广到一般哲学。哲学的特点就是试图穷根究底,不停追问,从多方面质疑和挑战,构想新的可能性,这导致哲学研究的批判性色彩十分浓厚。批判常常采取两种形式:内部批判和外部批判,前者是一个哲学理论派别内部的相互切磋和相互诘难,暴露或揭示该理论的内在冲突和理论困境;外部批判是持有不同理论观点的人去反驳该理论的根本假定和主要论题,试图挫败该理论。在这两种批判中,起最大作用的常常是内部批判,从而导致该理论的演变和发展。例如,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早期分析哲学,具有非常狭隘和刚性的立场,提出把(在感觉经验中的)“可证实性”作为区分(认知上)有意义与无意义的标准,由此把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等都归于“无意义”之列。在内部压力之下,“可证实性”被进一步区分为“直接的可证实性”和“间接的可证实性”;卡尔·波普提出以“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蒯因批判“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质疑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提出整体主义知识观;斯特劳森和蒯因等人证明,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只是有不同的形式(如修正的形而上学和描述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承诺等等);麦金泰尔、罗尔斯、帕菲特等人把伦理学、正义论、规范性研究等重新纳入分析哲学的怀抱;普特南、塞尔、戴维森等人则使心灵哲学成为分析哲学的热门领域……由于内部批判,分析哲学从早期的一些学派、一场运动,演变成一种研究风格,即一种做哲学的方式,没有固定的边界,也没有固定的立场。③参见陈波:《分析哲学的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陈波:《分析哲学内部的八次大论战》,载《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据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是这样,其成员至少可以分成四代:第一代的主要代表是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库斯;第二代的主要代表是哈贝马斯和韦尔默,第三代中最知名的是霍耐特,还有第四代。甚至在第一代中,也可以区分出四个不同的阶段……①参见Nicholas Joll, “Metaphilosophy”, UCL= < https://www.iep.utm.edu/con-meta/ >。
通过学哲学和做哲学,我们可以培养怀疑和批判精神,理性论辩的能力,清晰表达和写作的能力,这显然有助于我们的认知能力的提 升。
三、哲学与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连续性
在哲学中,可以利用的方法论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像在其他各门科学中一样,哲学也要求助于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实验(特别是思想实验)、直觉和常识、数据和证据、思考和反思、想象和思想实验、溯因—最佳解释推理、模型建构、猜测性假说、逻辑推理、证成与反驳、证实与证伪,如此等等。正像科学方法是常识方法的精致化一样,哲学方法也是对常识方法和科学方法的提炼和总结。在方法论上,哲学与常识和科学之间没有实质性区 别。
下面仅讨论三种最具特色的哲学方法,它们只不过是相应科学方法的延伸与扩 展。
(一) 溯因—最佳解释推理
皮尔士在演绎和归纳之外,提出了一种新的推理形式——溯因(abduction): 令人惊奇的事实C被观察到,如果A为真,C就会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有理由猜想A是真的。他认为,“溯因是形成一个解释性假设的过程,它是产生任何新观念的仅有逻辑运算。”②C. 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5, p.189, p.17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35.哈曼(G. H. Harman)最早提出了“最佳解释推理”(缩写为IBE),它是从解释反常证据E的多个可能假说中,选出关于E的最佳解释性假说的一套程序和方法。③G. H. Harman, “The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74, No.1, 1965, pp.88—95.利普顿(Peter Lipton)后来对IBE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其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潜在合理的解释”和“最可爱的解释”等概念。④彼得·利普顿:《最佳说明的推理》,郭贵春、王航赞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我倾向于把溯因推理与IBE看作一套统一的方法,记为“溯因—IBE”,并用一个四元组模型 〈E, B, {H1, H2, ……,Hn}, C〉来刻画它:
待解释的反常现象E
背景信念B加上可能假说H1, H2,……,Hn中的某一个,都可以合理地解释E根据选择标准C,Hn是比其他可能解释更佳的解释,并且是最可爱的解释因此,有很强的理由接受假说Hn
再做几点必要的说 明:
(1)E是被观察到的新奇且令人惊讶的证据;B是一组背景信念,主要包括具有高接受度的已有理论,或许还要加上常识信念。E与B不相容:仅从B出发,可以推出E的否定,即
(2)H1, H2, ……,Hn是用来解释证据E的一些可能的假说。根据迪昂—蒯因的整体主义论题,对E的解释并不单纯依据H1, H2, ……,Hn中的某一个,还要加上一组更新过的背景信念B。
(3)C 是选择最佳假说的一组标准。我愿意采纳蒯因所给出的标准:(a)保守性:在同等条件下,一个假说对先前的信念摒弃越小就越合理。(b)谦和性:除非必要,不要构造离奇的假说。(c)简单性:在逻辑结构上越简单的假说越好。(d)概括性:一个假说所覆盖的经验证据越多,它的适用范围越广,就越合理。(e)可证伪性:一个合理的假说必须有某种可设想的事件将构成对该假说的反驳。①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 (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9—389页。或许再加一条:(f)精确性,主要来自逻辑和量化手段。一个假说越精确,它被无关原因而巧合证实的概率就越小,由预测成功得到的支持就越 强。
(4)根据利普顿,对E有解释力并且与B相容的假说是“潜在合理的假说”;与已有证据吻合度最高的假说,构成对现有证据的“最可能为真的解释”;不仅能够解释现有证据、而且能够解释其他已知的类似现象、并且能够预测未来的类似现象的假说,构成对现有证据的“最可爱的解 释”。
(5)根据利普顿,在得到“最可爱的解释”的过程中,有三次认知过滤:从“可能解释”到(不必为真)的“潜在合理的解释”;从“潜在合理的解释”到“最可能的解释”(最可能为真);从“最可能的解释”到“最可爱的解释”(最佳解释),后者最可能为真并且解释力最大:能够解释最大范围的类似现 象。
毫无疑问,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广泛使用了溯因—IBE方法,只不过先前被包裹在“假说演绎法”的名下,涉及其中的三个重要环节:如何提出假说,如何评估和选择假说,以及如何证成假说。威廉姆森近年来大力倡导在哲学研究中使用溯因方法:“哲学应该使用广义的溯因方法论。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这样使用了,但它应该以一种更大胆、更系统和更有自我意识的方式使用。”②Timothy Williamson, “Abductive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Forum, Vol.47, No.3—4, 2016, p.268.下面以我本人近年关于事实、证据、真理的研究为例,说明溯因—IBE在哲学研究中的使 用。
“事实”是一个在哲学中被频繁使用的概念,被作为真理符合论的基础性概念,哲学家们先后提出了本体论的事实观和事实—命题同一论等。前者认为,事实存在于世界之中,是使得命题为真为假的东西;后者认为,事实与命题特别是真命题是同一的:事实就是真命题,真命题就是事实。但前一理论面临很多严重的困难,例如:难以厘清命题与事实的关系,如命题与事实究竟谁先谁后、谁依赖谁、谁说明谁?“事实”与命题之“真”是否相互定义、从而导致恶性循环?如何把事实个体化?例如是否有原子事实、否定事实?能否对事实进行计数: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事实的边界条件在哪里?是否所有事实都相互关联着,从而形成了“唯一的大事实”,“事实”因此蜕变为像“实在”“世界”“真相”这样的大词,从而在定义命题的真假时不起实质性作用?同一论把“事实”与“命题”相等同,会带来更多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如果它们都是客观的,或者都是主观的,怎么能够用“事实”概念去说明和刻画一种主观认识(用句子或命题表达)的真假?由此,我提出一种认知主义的事实观:“事实”是我们从世界母体上一片片“撕扯”下来的。究竟从世界母体上“撕扯”下什么,既取决于我们“想”撕扯下什么,即我们的认知意图和目标;也取决于我们“能”撕扯下什么,即我们的认知能力;还取决于我们“如何”撕扯,即我们所使用的认知手段和方法。如此刻画的“事实”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混合物,在科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起“证据”作用。①参见陈波:《“以事实为依据”还是“以证据为依据”——科学研究和司法审判中的哲学考量》,载《南国学术》2017年第1期;陈波:《客观事实抑或认知建构:罗素和金岳霖论事实》,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陈波:《没有事实概念的新符合论》,载《江淮论坛》2019年第5—6期。
在关于“事实”的研究中,我的工作模式是这样 的:
起点:“事实”概念在哲学上很重要,已有事实理论遭遇严重困难,需要重新解 释。
进程:本体论的事实观面临诸多困境,可以断言其不成 立;
事实—命题同一论面临更严重困境,可以断言其根本不成 立;
……
认知主义的事实观是更好的解释,甚至是“最佳的或最可爱的解 释”。
结论:认知主义的事实观是成立 的。
(二) 想象、思想实验与模型建构
1. 想象与思想实验
爱因斯坦指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①爱因斯坦:《论科学》,载《爱因斯坦文集》 (第一卷),许良英、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84页。例如,从1911年卢瑟福所提出的原子结构的行星模型(原子的大部分体积是空的,电子按照一定轨道围绕着一个带正电荷的很小的原子核运转)中,我们感受到想象力的巨大跨越和瑰伟神奇。哲学研究也需要有想象力,“想象是我们了解诸种假设的可能性的基本方式”②蒂莫西·威廉森:《哲学是怎样炼成的:从普通常识到逻辑推理》,胡传顺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版,第85页。,后者主要通过思想实验来发挥作 用。
思想实验是在研究者的头脑中进行的,不借助任何物质手段,只是一套纯粹的概念推演或逻辑操作。它只在类比的意义上是“实验”,通常包括以下步骤:(1)确定目标:为了挫败或证成某个哲学论断,或者构想一种新的可能性;(2)展开想象:假如怎么样,就会怎么样(what if ...)?这里主要用到反事实条件句及其推理;(3)设计情景:该情景含有目标哲学论断的某些要素,但没有另外一些要素;(4)逻辑推演:从所设计的情景中,分析和推演出一系列结论;(5)做出最终结论:该哲学论断成立或不成立。思想实验亦被称为“心灵的实验 室”。
有的学者正确地指出:“在17世纪,伽利略、笛卡尔、牛顿和莱布尼茨都是思想实验的最杰出的实践家,他们全都致力于‘自然哲学’的方案。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没有思想实验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创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其中大部分实验都与这些科学理论所产生的重要哲学问题有关。此外,伦理学、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的许多内容以思维实验的结果为基础的,其方式看起来与科学中的思想实验非常相似(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质疑这一点),包括塞尔的中文屋、普特南的孪生地球和杰克逊的色彩科学家玛丽。如果没有思想实验,哲学甚至会比科学遭受更严重的伤害:变得更为贫乏。”③参见J. R. Brown and Y. Fehige, “Thought Experiment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9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forthcoming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9/entries/thoughtexperiment/。这里补充一点:在中国先秦哲学中,也有很多很好的思想实验,如“庄周梦蝶”和“濠梁之辩”。但在现当代中国哲学文献中,却很难见到想象与思想实验的踪影,都变成了从文本来到文本 去。
思想实验在哲学研究中主要被用作论证手段,用于挫败或证成某个哲学论断或学说,其作用常常是破坏性的。例如,塞尔的中文屋实验旨在反驳如下的强人工智能观点:人脑不过是一台数字计算机,人心只不过是一种计算机程序,心与脑的关系就是程序与计算机硬件的关系;普特南的孪生地球旨在表明:(词项的)意义和指称不在人的头脑中,而是由外部世界的状况决定的;盖提尔反例旨在表明:知识不仅仅是得到证成的真信念;富特的电车难题则挑战了关于道德的后果主义或功利主义观点;“庄周梦蝶”在质疑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至少是我们如何证明这种实在性;“濠梁之辩”在挑战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相互理解的可能性。不过,沃伦的“道德的太空旅行者”思想实验却力图表明:堕胎有可能不是谋杀,因为只有人才能被谋杀,而胎儿并不具有完整的人格。汤姆森的“生病的小提琴家”的思想实验进一步表明:胎儿是不是一个人或潜在的人跟怀孕的女性是否有权堕胎根本没有关系,因为即使胎儿是一个人,怀有这个胎儿的女性仍然有权决定是否终止妊娠,就像那位被强行连接其身体以拯救那位患病的小提琴家的人有权终止其连接一样。①参见小西奥多·希克、刘易斯·沃恩:《做哲学》,柴伟佳、龚皓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44—47、54页。
关于思想实验,有很多问题尚待回答和研究,其中最主要的有:思想实验有哪些重要特征?如何对思想实验进行分类?有哪些主要的类别?如何可能在没有新经验数据的情况下,仅凭在头脑中想象、思考、推演(思想实验),就能够获得关于外部实在的新知识?能够把思想实验分成好的和坏的吗?根据什么标准去评价和区分?能够反驳某些思想实验吗?从哪些方面去反驳?如此等 等。
2. 模型建构
所谓“模型”,是我们描述或构想的一种假定性结构,希望用它们去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现实世界中更复杂系统的运作。模型方法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数理科学特别是逻辑学中使用得十分广泛,例如,用水流经沙盘的模型,模拟一条河流侵蚀河岸;用彩色的圆柱体和球体的结构模型,模拟DNA分子结构;用沙盘推演,模拟战争中各方的策略应对及其结果。在理论科学特别是逻辑学中,模型是一种更为抽象的理论结构;现代逻辑有一个专门的分支,叫做“模型论”。在现代逻辑中,我们先用无意义的符号语言去建构形式系统,然后为该形式系统寻找模型(满足一定条件的对象域),在模型中对该系统内的各个要素做出解释:给它的词项确定指称,给它的公式确定真值条件,给它的推理形式确定有效性条件,最后再证明该形式系统的可靠性(系统内可证的公式都为真)和完全性(在相应对象域中为真的公式都可证)等等。还可以去寻找使得某个公式在其中为真的“正模型”,也可以去寻找使得某个公式为假的“反模 型”。
在哲学中也可以甚至更需要运用模型建构,因为哲学研究复杂现象背后的一般结构及其规律。由于所研究的现象过于复杂,我们需要做必要的简化,撇开其他不相关要素,凸显我们所关注的要素,研究其中各要素的关系,这就适合使用一种简单的结构模型。一旦简单模型获得成功,我们再尝试逐渐添加更多的复杂细节,以逼近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即使如此也仍然比现实生活系统简单得多。如果一开始就事无巨细全都考虑在内,我们的思维就无法起飞,什么也做不成,达不成任何有意义的哲学结论。由于模型所展示的是一般的结构关系,而不是全称判断式的哲学结论,它们就能很好地经受住反例的考验,而不会像波普所说的那样,那么容易被证伪。威廉姆森指出,“取代一个模型的是另一个更好的模型。它的部分优势在于,它能更充分地处理旧模型的反例,但它也应该再现旧模型的成功。”①蒂莫西·威廉森:《哲学是怎样炼成的:从普通常识到逻辑推理》,第85页。他自己用一千张彩票抽奖的模型,根据数学概率去说明其中隐藏的认知不确定性。②参见Timothy Williamson, “Model-Building in Philosophy”, in R. Blackford & D. Broderick (eds), Philosophy’s Future: The Problem of Philosophical Progres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7, pp.163—164。
(三) 认知分歧、哲学论战与反思的均衡
1. 认知分歧
由于人们在立场、背景知识、认知方法、认知能力、所获得信息和证据的质与量,特别是陈见和偏见、利益冲突等因素的影响,相互之间很容易发生分歧(disagreement),对于哲学来说,最重要的是认知分歧。什么是分歧?如何界定分歧?分歧有哪些种类?认知分歧如何发生?如何解决?通过什么程序和方法?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认知分歧在人的认知发展以及社会文明发展中有什么积极或消极作用?这些问题在21世纪初才进入哲学家的视野,成为他们研究的课题。③参见B. Frances & J. Matheson, “Disagreement”,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9 Edition),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9/entries/disagreement/。
以往的认识论着重研究个体的认知行为:一位认知主体,或者说一位理想的认知主体,凭借什么样的过程、方法、程序和规则等等才能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认知?它们严重忽视认知的社会维度。不同认知主体之间的交流、对话和论战等等,对他们最后所持的认知立场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甚至有某种权力分配结构:认知权威的意见会受到更大程度的关注和重视,而处于弱势地位的认知同伴的意见则很容易被忽视或轻视。着重研究认知的社会维度的叫做“社会认识论”,它目前集中关注两个话题:一是信任(trust),特别是对他人证言(testimony)的信任,二是认知同伴之间的认知分歧(epistemic disagreement)。
关于如何看待和处理认知分歧,目前形成了两种主要立场:一是折中调和论,主张在面对认知分歧时,各方应该等量齐观各自的立场及其理由,从而都后退一步,对自己的立场做出重要的修改或调整;二是固执己见论,它批评对方在理智上不真诚,既然自己的认知立场是在仔细权衡证据、认真思考之后得到的,即使面对分歧也应该严肃坚持自己的立场,努力去说服对方,这样做的依据是:各方在认知证据、认知德性和认知能力等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距。④参见Diego E. Machuca (ed.), Disagreement and Skeptic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1—7。
2. 哲学论战
哲学家的认知分歧只能通过对话和论战来解决,就像其他各门科学中的情况一样。不过,很多时候,哲学论战不仅不解决分歧,还制造新的分歧。那么,这种论战究竟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哲学家们为什么要投身于这样的论战中去?我曾撰文指出,哲学论战有如下的积极意义和价值①参见陈波:《分析哲学内部的八次大论战》,载《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第一,哲学论战有助于揭示已有理论观点的问题和缺陷。例如,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弗雷格、胡塞尔等人的反心理主义在逻辑学和哲学领域几乎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一些当代学者揭示出这种反心理主义的诸多问题:(1)它基于早期实验心理学的不成熟,认为只要一触及心理现象,其研究结果就必然是私有的、个人的、主观的和不稳定的。但当代心理学已经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成为一门值得尊敬的严肃科学,很多研究结果具有相当程度的客观性。(2)它的不少关键性前提只是被假定为真,并没有得到严格论证,其成立依据值得严重怀疑。(3)它把推理和论证的有效性完全与人的实际思维过程分离开来,从而使逻辑的规范性得不到合理的说明和辩护。(4)随着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求我们去研究人的实际认知过程、思维过程和决策过程,从中提炼出认知的模式、程序、方法和规则等 等。
第二,哲学论战有助于激活思维,发展新的理论观点。例如,为了回应克里普克对语言哲学的质疑,维护如下三对重要哲学概念之间的密切关联——必然和偶然(模态)、先验和后验(理性)、分析和综合(意义)——一些当代哲学家发展了二维语义学,后者的“中心思想是一个表达式的外延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依赖于世界的可能状态:一是认知依赖,这是指表达式的外延依赖于现实世界的呈现方式;二是指虚拟依赖,这是指在现实世界的特征都已经固定的情形下,表达式的外延还依赖于世界的反事实状态。对应于这两种不同的依赖性,一个表达式就具有两种不同的内涵,这两种内涵以不同的方式将表达式的外延和世界的可能状态联系起来。在二维语义学的框架中,这两种内涵被看作是体现了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或内容的两个不同的维度”②蒉益民:《二维语义学及其认知内涵概念》,载《哲学动态》2007年第3期。。
第三,哲学论战有助于防止哲学领域里的盲从、独断和专制。如果说,政治或军事领域的独断和专制还可以找出一些理由的话,例如为了政府机构的高效运转,为了保证军队能打胜仗,那么,学术领域特别是哲学领域的独断和专制绝对是有害无益的。有一种说法:哲学史就是一种“学术弑父、思想弑父”的历史,后来者推翻其前辈,并超越其前辈。想一想当年维也纳学派是何等风光,“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是如何响遏行云,维特根斯坦和蒯因如何在很长时期内居于领袖地位,如今却物是人非,其影响日渐式微 了。
第四,哲学论战有助于凸显哲学追求智慧和真理的本性。有的学者鲜明地指出:“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①麦基编:《思想家》,周穗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页。
3. 反思的均衡
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最早提出和使用了“反思的均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这个方法的核心就是追求最大程度的“融贯”(coherence),并且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一个人自己的观点相互融贯,一个人的观点与其理由和证据相互融贯,他的观点与其他学者的合理观点相互融贯。这必须通过前思后想(forth and back)、左思右想、“上穷碧落下黄泉”,付出极其艰辛的理智努力,才能达 到。
罗尔斯论述说,即使处于原初状态的人类个体也都具有理性思考能力,但他们的思考能力还是有差别的;现实的个体在其知识教养、生活经验以及所处的认知地位等方面更有差别,由此会形成有关公平、正义和道德等等的不同直觉和各种各样的“慎思判断”(considered judgments),甚至导致相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包括来自内部的和来自外部的:一个人自己的道德直觉与慎思判断不一致,他所持有的多个慎思判断彼此不一致,他的直觉和判断与社会生活现实不一致,他的直觉和慎思判断与别人的类似直觉和判断不一致。这就使得有必要对他自己的观念进行反思:它们各自有哪些理由?这些理由都成立吗?哪些观念得到较好的证成?哪些则得到较弱的证成?是否需要放弃或修改某些观念?如何放弃或修改?由此达成自己观念内部的协调和融贯。这叫做“狭义的反思平衡”。“广义的反思平衡”还要求认真思考别人的不同道德观念及其理由:在什么地方有分歧?为什么会有这些分歧?对方持有哪些理由或根据?它们都成立吗?其与社会生活的吻合程度如何?回过头来再对照思考自己的观念及其理由,如此往复,权衡比较,不断调整、修改和完善自己的观点,直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这个人已经考虑了我们哲学传统中那些最重要的政治正义观念,已经权衡了其他哲学和其他理由的力量”,他的观点“是在范围广泛的反思和对先前众多观点加以考虑的情况下产生的”。②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2页。这样的反思平衡凸显了“多元”“开放”“宽容”“理解”“对话”“审慎”等关键词语的价值,并且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
从关于帕菲特(Derek Parfit,1942—2017)写作《重要之事》一书的报道性文字中,可以看出他认真践行了“反思的均衡”,由此亦可看出他的理智诚实,治学严谨,以及对自己学术观点的忠诚,真的是让人肃然起敬:“帕菲特想要这本书尽可能地接近完美。他想回答每个可设想的反驳。为此目的,他把手稿几乎送给了他认识的所有哲学家,寻求批评,有超过250位哲学家给了他评论。他辛苦多年,修正每一个错误。随着他对错误的纠正与对论证的澄清,书也变得越来越长。他原本的设想是一本小书,然后是一本长书,再然后是一个非常长的书加上一本甚至更长的书——总加起来有1400 页。人们开始怀疑他最终是否还能完成这本书。”①拉里莎·麦克法夸尔:《如何为善——帕菲特小传》,葛四友译,载《政治思想史》2017 年第1 期。
四、哲学与哲学史的连续与断裂
对“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这个论题,最有可能提出的一个异议是:哲学史在哲学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甚至“哲学就是哲学史”,而历史研究在其他各门科学中的地位远不如在哲学研究中那么重要。下面我来回答一下这个异 议。
(一) 哲学与哲学史的连续性
1. 哲学史关涉文化与文明的传承
连动物都知道向下一代传承其生存技能和生活经验:去哪里寻找食物和水源,用何种技巧去捕猎,如何避开危险物,特别是其捕食者,等等。人类更重视技能、经验、知识的传承,更重视后代的智能培养。人类远胜于其他动物之处在于:发明了文字和印刷术,因而有了书籍,人类先前的经历、经验和智慧被记录在书本里,使得知识的隔代传承有了可能。既然哲学是人类关于这个世界的总体知识的一部分,先前世代的哲学思考和哲学智慧当然也在需要传承的“薪火”之列。哲学史家以其严肃的学术工作,给我们清晰、扼要且系统地展示了先前的哲学家是如何思考的,其理论要点是什么,其各要点之间又是如何关联的,受到他的同代人和后代人的哪些批评,给我们搭建了进入他们的思想世界的阶梯,当然功莫大焉。由于哲学是一个文化和文明的核心要素,在传承一个民族的哲学史的时候,也就在传承那个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并且在塑造后来者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例如,在学习和研读儒家经典时,我们就在懂得和理解何谓中国人,同时也在学习怎么做中国人。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无根”的,一个没有某种形式的哲学的民族则是“无魂”的。研读哲学史,就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民族或整个人类“寻根”“找 魂”。
2. 哲学史是训练思想和人格的媒介
历史无情,大浪淘沙,很多喧嚣一时的作品都被后代无情抛弃,只有通过了很多世代的无数双挑剔眼睛的严格检视,少数优秀人物及其优秀作品才流传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先贤大哲”和“经典文本”。优秀人物及其作品必有其优秀之处,也必有值得我们学习、模仿、改进、发展之处。我们研读孔孟著作,体会其“推己及人”的运思方式:首先认清自己,然后对他人做同情之理解,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研读庄子,透过其汪洋恣肆的文字,体会其瑰伟奇丽的想象,恢诡奇谲的思想,更着迷于其所描述的真人境界:“古之真人,……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庄子·大宗师》)“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逍遥游》)我们读笛卡尔,感受其彻底的怀疑,奇特的想象,步步推进的哲学思考。我们读康德,感受其沉郁的人格特质、系统而严谨的理论思考、对人类认知能力的严格审问、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极度推崇(“人为自然立法”),以及令人着迷的感悟:“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①I. Kant,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ranslated by Thomas Kingsmill Abbott, First published in 1788,网络版http://ebooks.adelaide.edu.au/k/kant/immanuel/k16pra/part2.html#conclusion,读取日期2019年11月5日。我们读维特根斯坦,感受其有点偏执的人格,惊人的创造力,怪异而深刻的运思方式和写作方式,对哲学和自己人生的忠诚。我们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读黑格尔和马克思,读尼采和叔本华,读海德格尔和胡塞尔,读弗雷格和罗素,读蒯因和威廉姆森,……我们从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学习和感受做哲学的不同方式,然后我们自己开始学习做哲学,如果足够幸运和有才能,也许能成为某种类型的哲学 家。
3. 哲学史是激活创造的资源
关于优秀哲学家的优秀作品,必须强调两点:第一,体现在这些作品中的那些思想、智慧和运思方式并没有完全死掉,它们仍然以某种方式活着,可以成为我们新思考的参照和向导。因为哲学家探究有关自然、社会、人生的大问题,隐藏在这些事物之后并统御它们的大道理,与当时情景的关联并不那么紧密,具有某种普遍性,例如哈姆雷特的人生困惑和艰难选择“to be or not to be”,每个时代的人都会遭遇到和感受到,只是以不同的方式。第二,先前的哲学家并没有把话说尽,我们遭遇新的情景和问题,必须自己找到解决方法。套用爱默生的表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是新的,是尚未被触碰过的处女。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深入观察和独自冥思,获得和展示我们自己关于当代现实的新观念。但我们的思考不能平地起高楼,而是要站在巨人的肩上:通过批判性思考他们的思考及其理论,我们逐渐认识到:他们在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弄错了,哪些地方虽然是对的但还不够……,由此改进他们的思考,发展他们的思考,以致完全超越他们的思考,提出我们自己的新思考和新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愧为那些先贤大哲在理智上合格的后 嗣。
(二) 哲学与哲学史的明显断裂
人们常常把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连续性夸大了,强调得太过分了,以致提出有点怪异的论断:“哲学就是哲学史”,并不断重申这一论断。如果对该论断做弱解读:通过学习哲学史来学习哲学和进入哲学,通过批判地研究先前哲学家的思想来研究哲学和发展哲学,那么,它就是明显合理的。如果对它作强解读:研究哲学就是研究哲学史,研究哲学就必须研究哲学史,哲学研究等于哲学史研究,那么,它就是明显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威廉姆森谈道:“我有时被问到在研究哪个哲学家,仿佛那是任何一个哲学家必须做的事情。我用牛津风格回答道:我研究哲学问题,不研究哲学家。”①蒂莫西·威廉森:《哲学是怎样炼成的:从普通常识到逻辑推理》,第144—145页。他还谈道,既然哲学史是哲学的一部分,那么,研究哲学史也是在研究哲学,但是哲学却不只是哲学史,他论证 说:
“哲学就是哲学的历史这个观点是在自掘坟墓,它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哲学选项,我们没有义务必须接受它。它没有证据的支持。在哲学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是自己写哲学史的。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解释其他哲学家的理论,或者甚至是他们自己的理论,而是首先建构这样的理论。例如,关于心灵及其在自然中的地位。这与科学理论并无本质区别。这同样适用于今天仍然在发展的大部分哲学理论。而且,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有很多在诸种理论之间进行合理决断的方法。把哲学与哲学史看成是一样的,这是一种极其不历史的态度,因为它违背了历史本身。虽然研究一个哲学问题的历史(例如自由意志)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但还有许多研究问题的方式并不是研究其历史,正如对数学和自然科学问题的研究,就典型的不是研究它的历史。幸运的是,哲学史可以被研究,但并不是以让它接管整个哲学的帝国主义的野心来研究。”②同上书,第145页。
对威廉姆森的论证,我再补充一个重要证据:哲学史上分为明显不同的阶段、派别、风格,存在明显的断裂:后一代哲学家在研究不同的论题、使用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哲学立场。例如,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西方哲学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和两次转向: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侧重研究本体论问题: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它们有什么性质(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关系、层次、结构和规律?西方近代哲学转向认识论研究:人能否认识这个世界?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经验论和唯理论是其主要派别及其理论成果。19世纪末至20世纪,西方哲学却发生了“语言转向”:我们实际上是透过语言的棱镜去看世界,也就是通过语言去认知这个世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严重受到我们语言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先仔细审查语言本身,研究它们的结构、意义及其关系:语言是否对世界有遮蔽作用?是否扭曲、误导我们的认知?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又开始了对20世纪哲学的反思和纠偏,被20世纪分析哲学家们贬得一塌糊涂的形而上学、心灵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等又重新回到哲学的怀抱,甚至成为其研究热点。如果没有一次一次的转向、背叛、反思和纠偏,就没有哲学的发展,也就没有丰富多彩的哲学史可供研究 了。
所以,通过哲学史来学习哲学和进入哲学,通过批判地反思先前的哲学理论来发展哲学,从先前的哲学遗产出发,通过开拓新的领域、使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理论来推进哲学,这才是看待哲学和哲学史之间关系的正确态度和做法。不能所有中国哲学家都研究哲学史,并且只研究哲学 史。
五、对另外两个异议的答复
异议1:科学关注知识和真理,哲学关注理解和智慧;科学重视观察和实验,哲学重视直觉和体验;科学有累积性进步,哲学几乎没有什么进 步。
例如,苏德超认为,“科学更依赖于外在观察。外部世界独立于观察者,因此也就在观察者之间保持着中立。不同观察者的内在体验虽然难以比较,但他们对被观察者的描述却是可以比较的,这些描述不但有高下,而且有对错,从而就可以获得累积性进步。”相比之下,“哲学的目的并不是形成新的科学,而是通过回答当时科学所回答不了的问题,满足人天生的好奇心,构建起生活世界的整体,从而为人的生命寻找意义。……这部分哲学问题,依赖外在观察是无论如何都得不到回答的……,实际上主要靠内在体验来回答”。①苏德超:《问题、经典与生活——哲学教育的三大支点》,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答复:关于苏德超的上述说法,我做以下回 应:
苏德超所说的“科学”似乎仅指自然科学,其中是否包括数学?按照常识,当然应该包括数学。我所说的“科学”更为广义,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所以把它们都叫做“科学”,是因为它们都关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只是关注不同的部分或侧面;都力图发现和揭示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象底下的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规律和规则,最后以理论化的形式呈现出来;都力图揭示和把握这个世界的真相,都以追求真理(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认知)为目标,还要以对真相和真理的把握为基础,去努力在这个世界获得更好的生存;其理论成果都具有某种形式的客观性,至少是主体间性,因而不同的认知主体有相互交流、对话、理解、评价的公共平台。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性事业。苏德超也承认,“哲学活动主要是一项认知性事业而不是一项审美性事业。”②同上。
当把量子力学、相对论、宇宙物理学、分子生物学、生态学、宏观经济学、文化人类学、政治科学、管理科学等等都囊括进“科学”之后,各门科学就呈现为一个复杂程度和抽象程度明显有别的等级序列,科学与哲学还存在如下所说的明显的方法论分野吗?自然科学主要靠观察和实验、数据和证据,而哲学主要靠“思辨”(speculation),也就是说,坐在扶手椅里,靠理性思考来提出理论和反驳理论,不怎么使用证据。这些说法有太多明显的反例:与哲学家一样,数学家也不怎么做观察和实验,主要坐在扶手椅里工作,难道数学不是科学?各门具体科学家真的不做思辨吗?否!在设计实验、思考数据的准确性和证明作用、由数据和证据中概括出理论原理等等,他们也要诉诸想象和思想实验,后者就是某种形式的“思辨”。一门科学所研究的对象越复杂,一门科学越抽象,其从业者的工作方式与哲学家的工作方式就越少区别,例如牛顿、爱因斯坦和霍金的工作方式与康德、蒯因、威廉姆森的几乎是相同的。有很多大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罗素等人)本身就是某种等级的哲学家,难道在他们作为科学家和作为哲学家的身份之间存在某种分裂吗?他们在思考科学问题时用一种思考方式,在思考哲学问题时用另一种思考方式?否!在他们那里,他们所研究的问题构成一个抽象等级相互连续的序列,其所使用的思考方法也是相互连续的。此外,哲学家也并非不需要证据,他们的证据来自常识、直观、思想实验以及各门科学,根据威廉姆森的“知识就是证据”这一论断,所有被确证为真的东西都可以被哲学家拿来当作证据,用于证成或证伪某个哲学命题。一个哲学理论要成为可以分享的公共性资源,它应该越来越多地依靠明晰的概念和观念、可靠的理由或证据、明白晓畅的说理、严格的推理链条,而越来越少地依赖私人化的直觉、体验、印证,甚至是某种形式的“密码”“呓语”“当头棒喝”……哲学中也有进步,哲学的进步首先体现在方法论上:把能够说的尽量说清楚,暂时说不清楚的尽量往清楚方向去说。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当代哲学中涌现出许多新的哲学分支:语言哲学、心灵哲学、逻辑哲学、数学哲学、政治哲学等等,它们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比先前的哲学更细致也更深入,提出了更合理的洞见或理论,这就是哲学中的进步。至于哲学中很少有达到完全共识的“真理”,这是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理论概括的抽象性造成的,在其他各门类似的科学(如生物进化论、分子生物学、量子力学、宇宙学、理论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等)中情况也是类似的,其中共识稀缺,分歧是常态,但不能说它们不是科学。
异议2:科学重点关注“实然”,即事情实际上怎么样;哲学重点关注“应然”,即事情应该怎么样,涉及规范、价值、理想、愿景等 等。
这个异议是2019年11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如何做哲学——元哲学与哲学方法论”研讨会上,袁祖社教授在私下交流中向我提出来 的。
答复:这个异议以休谟的“是与应该”问题中所隐含的事实与价值和规范的分裂为基础,但我认为这个分裂是不存在的,是一种误解和虚构。我们为什么“必须”和“应该”?这是“规范性之源”问题;我们的“理想”或“愿景”是否需要某种事实性基础?有必要回到我在本文前面所述及的思想:我们对这个世界无法做镜像式的全面透彻的认知,我们认知我们需要认知的,我们认知我们能够认知的。我们的欲望、需求、利益、关切决定了我们要去认知这个世界中的什么;我们所具有的认知和行动能力以及认知资源,决定了我们将如何认知。按照这种思路,“事实”是我们带着一定的认知意图、使用一定的认知手段,从世界的母体上一片片撕扯、扒拉下来的,带有明显的认知主体的印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认知建构,没有纯客观的事实。我们为什么“应该”和“必须”?这是由以下三个要素共同决定的:一是我们的需求、意愿和目标,其中意愿和目标产生于需求,意愿的强度往往取决于需求的强度,而需求有客观基础;二是当下的实际状况,常常与我们的需求和意愿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意图改变现状,造成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和意愿的某种另外的状况(愿景);三是相关的科学原理:面对当下的状况,根据相关科学原理,我们“应该”或“必须”做什么和怎么做,才能满足需求、达成目标、让愿景变成现实?所以,有一条共同的纽带,即我们的欲望、需求、利益、关切,把“事实”与“价值”和“规范”关联起来,由此架通了从“事实”到“价值”和“规范”的桥梁。科学理论会派生出相应的规范,也有它们自己的价值追求;哲学理论也需要有事实性基础,由此建构出“价值”“规范”“愿景”。在这一点上,哲学与科学之间没有明显的断裂。由于篇幅关系,我这里只能概述相关想法,以后将另外撰文将它们详细展开,提供系统性的论证和答 辩。
最后,我以威廉姆森的断言来结束本文:“哲学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有序的探究形式,它是一门科学,但不是一门自然科学。”①蒂莫西·威廉森:《哲学是怎样炼成的:从普通常识到逻辑推理》,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