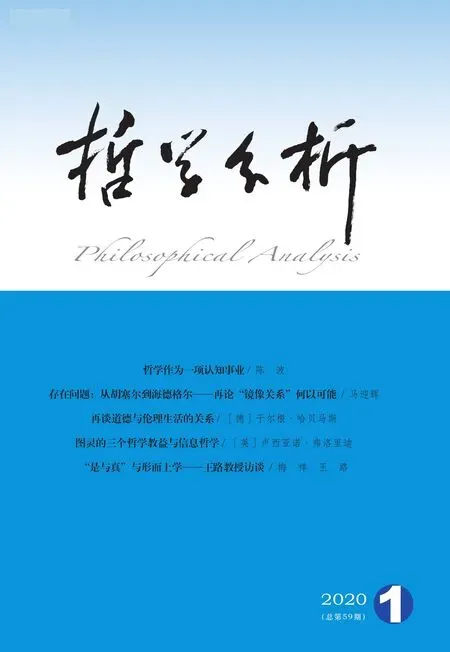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①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文
童世骏/译 姜锋/校
今晚这个一点不新的演讲主题①对此问题作者此前曾多次讨论,如Jürgen Habermas,“Über Moralität und Sittlichkeit—Was macht eine Lebensform ‘rational’?”,in Rationalität, Herbert Schnädelbach (hrs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84;“Moral und Sittlichkeit: Hegels Kantkritik im Lichte der Diskursethik”, in Moralität und Sittlichkeit, Wolfgang Kuhlmann (hrs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6,该文以“Treffen Hegels Einwände gegen Kant auch auf die Diskursethik”的题目收入了Erläuterungen zur Diskurseth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1)一书,并经作者建议,被加入了Moralbewuß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3)一书的英文版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0)之中。此外还有“The Moral and the Ethical: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Issue of 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 in Pragmatism, Critique, Judgement. Essays for Richard J. Bernstein, Seyla Benhabib & Nancy Fraser (ed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译者,让我想起那个在斯图加特召开的难忘的黑格尔大会②此次会议于1981年6月在斯图加特召开,哈贝马斯在会上作题为“Die Philosophie as Platzhalter und Interpret”(《哲学作为替代者和阐释者》)的报告。——译者上的一段轶事。在这个会上,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邀请了美国哲学的一些分析进路的先锋来做系列演讲,除了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伊安·哈金(Ian Hacking)以外,还有蒯因(W. V. O. Quine)、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和普特南(Hilary Putnam),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会议的高潮。在我的报告之后,罗蒂朝我走过来,边友好地摇头边说道:“你们德国人总是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来回摇摆。”我尽力向他解释,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说是在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之间来回摇摆,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些历史地传承下来的论证当中,总还能找到对一些系统性问题的回答。顺便说一句,那个会议设置的问题是:康德抑或黑格尔?这个问题至今仍具有其两极化的效力,也包括在那些共同提及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人们当 中。
从字面上说,道德(Moralität)和伦理生活(Sittlichkeit)③“Sittlichkeit”一词直接的意思是“伦理”,英文通常译为“ethical life”,中文通常译为“伦理生活”。——译者这两个表述的意义并无区别。“道德”听起来有古罗马习俗(altrömischemores)的意味,而“伦理生活”则是对希腊语“Ethos”的翻译,意为一城邦之居民的生活方式,与“Nomos”或实定法律相区别。“道德”这个概念是通过康德才第一次具有其与“良好伦理”(gute Sitten)相对的那种“古韵”(阿多诺语)的,因为它此后表达的是“自主”概念的另外一面。从关于个人意愿与理性引导的自我立法之间关系的这种颠覆性的新观念出发,形成了要求无条件遵守的道德律令(moralische Geboten)这个概念。黑格尔虽然要保留从理性当中产生出其法则的那个自由概念,但是在他看来,一个无力地面对着流行习俗的抽象的应当太不现实了。最终的分歧在于,在黑格尔所关注的国家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是否能既考虑伦理生活的现实主义,又同时不剥夺道德批判(die moralische Kritik)之异议的最后发言权。我想先讨论自主性(Autonomie)这个根本不算困难但实在是整个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三四个创新之一的概念(一)。然后我将回顾黑格尔的伦理生活概念,并且回顾康德可能对此提出的一个异议(二)。从这种讨论当中将形成一个暂时结论,对此我将作一个概述(三)。政治理论如果不考虑到马克思所发现的那种具有政治影响的社会的权力关系的话,就仍然只能受困于软弱无力的规范主义(四)。从康德到马克思的这样一番曲折讨论最后会得出一些观点,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可能会更好理解当前一些现实挑战(五)。
一
众所周知,康德用以定言命令为形式的伦理法则与自爱原则相对立:“要这样行为,即你的意志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同样地被视为一种普遍立法的原则。”(KpV, AA 05: 30)①中译文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载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 (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译者因此,道德的行动规范之合乎理性,在于它们因为符合所有相关者的利益而具有普遍有效性。有意思的是,康德放弃了对这条基本法则的繁琐论证,因为它自动地产生于先验哲学的语言的语法之中。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对理论理性作了施为的概念把握,也就是把它理解为一种自我立法的主体性的运作;就此而言,“实践理性的批判”是由“纯粹理性批判”滋养而成的。因此,随着理性从理论性运用转到实践性运用,认知主体用来确立经验杂多性之统一性的那种普遍的综合规则,被代之以无强制的普遍的实践法则。借助于这样的步骤,康德当然就在一条“法则”之“普遍性”这个概念当中,引入了卢梭在讨论政治立法时所引入的一些涵义。对于“法则普遍性”(Gesetzallgemeinheit),他不是从语义学上将其理解为法则之表述的普遍性,而是从语用学上理解为在该法则可能运用的所有情形中其内容的同等对待。我们从道德的视角出发应该证明,一条行动规范能否被设想为一个——总是已经默默地被作了共和主义理解的——立法过程的着眼于程序正义的结果。这个程序要求,在所有可能的相关者都得到包容和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这样一种合理的普遍化操作,这种操作使得只有那些可能为所有人所意欲的准则,才可能成为法 则。
但这样一条普遍法则,只有在所有人都行其所应当行的时候,才是同等地对每个人好的。如果说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对应的是其理性方面的话,道德法则的应当性对应的是意志自由方面。关键是,这两个方面在自主性这个概念中,是相互交叉的。被康德作为出发点的是这样一点,即对普遍伦理法则的事实,从而对刚才提到的程序,我们已经直觉地意识到了,但只有依照严格的“应当”才认识到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即在自爱准则与实践理性之间作出决定。我们居于自然之物的躯壳之中,尽管也是被赋予理性的。依照我们之偏好的这种完全是自然的、在康德看来也是不可忽视的利己主义,我们领悟到,当我们让自己的意愿(Willkür)受那种我们出于自己的实践洞见而自己制定的法则约束的时候,我们的行动是出于自由意志(freier Willen)的。因此我们必须把理性洞见的认知层面,与在所有情形下遵从这种洞见之决断的意志层面,区别开来——两个层面都是自由的层次。也就是说,实践理性是无法把好的理由简单地强加给一个理性主体的。当然,理由会对一个理性之物有强制作用,但它们所强制这个无法推卸“表达是否之能力”(Jaoder-Nein-sagen-Können)主体的,是采取一种立场。因此,仅在理性方面,自由的一个软弱环节就已暴露出来(这一点,比方说,在对行为责任进行刑法审理时就要加以权衡)。此外,我们的意愿(Willkur)还必须能够让自己受约束于这些自己认识到是正确的理由。在这双层意义上,自主性意味着明智的自我约束(einsichtige Selbstbindung)——让自己的选择自由(Willkürfreiheit)受到我们出于实践理性的理由而被认为是正确的理由的约 束。
康德是法国大革命的同时代人,已经能够根据这个历史事件来对他的卢梭进行诠释;在对法国革命的状况(Verfassung)的论证中,他已经感受到一种实现道德内容的行动。但是,基于其先验哲学的前提,他为其开创性的理性自由(vernünftige Freiheit)的观念保留了一个理智之我(intelligibles Ich),所以,那个新的法权秩序的合法律性(Legalität)只是道德(Moralität)的苍白镜像——只是理智的目的王国在现象世界中的一个阴影。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发生了变化,他第一次用他的伦理生活(Sittlichkeit)的概念赋予康德的“伦理共同体”(ethisches Gemeinwesen)概念以清晰轮 廓。
二
黑格尔不仅仅是比康德年轻了一代,而且作为同时代人,他既看到了来自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欧洲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也看到了早期工业主义中人们生活关系受经济搅动的效果。与此同时,他关注到历史的人文科学的崛起和政治经济学的起步。在大哲学家当中他是第一个重视“历史”思维的人。他在社会、文化和历史中看到了客观精神的符号形态的内在意义。他是在法哲学中研究伦理生活的这些领域的,而他的法哲学包括其社会理论和国家学说。由此,他一方面把康德的理智世界(Welt des Intelligiblen)从空间和时间的彼岸拉回到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之中;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对这种非超验化过程的思辨的反动,他又把由符号体现的理性重新推向了一种“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动态过程。不管怎么样,道德判断和道德行动的单个主体现在是从其生活史的教养过程加以理解的。这可以说是非超验化过程的现实主义成果。这种个人主体在一种强势的客观精神的动力机制面前,因此就失去了其康德意义上的自主性。那种在被伤害的个体的抗议中表达出来的道德正义标准,把它们的权威让位于呈现在社会生活形式的伦理生活之中的那种超个人精 神。
当黑格尔在论述道德和伦理生活的关系的时候,他可以说是相对于康德在方法论进路和问题提法方面都进行了一个转换。康德采取的是一种参与者的视角,他要证明哪个规范是有效的,并且把这规范运用于一个既定的冲突,而黑格尔则又把自己拉回到理论观察者的角色;也就是说,他要在一个规范的视角下面判断一个实存共同体的伦理构成(sittliche Verfassung)。但是他采用的是一个进行理性重构的观察者的态度,他要知道的是,那些参与者自己在完成其社会实践时能否把他们自己的和他们的共同体的生活或多或少视作“好的”。就此最终判断公民可以在哪种情况下感觉良好,是哲学家的事情。从这种改变了的视角出发,黑格尔提出了一个与康德所提出的全然不同的问题。他所关注的不是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共同体之成功的社会整合的条件。黑格尔感兴趣的不是对何为道德上正确的论证,而是把道德(Moral)根植于一个相互承认的可靠关系的网络之中,它采取的形式要么是——其样本是原本的家庭生活——非正式地适应的和构建信任的生活形式,要么是那种自足的政治共同体(恰好是国家)的法权的—正式的关 系。
对这种成功的共同生活的现象,黑格尔事实上进行了比康德更加尖锐的考察。他对政治共同体的观察,带有尖锐的历史敏感性,带着对个体人的独特性(亦即个人的历史生活形式的特定结晶)与社会交往的道德的和法权的、规范的抽象普遍性之间的交替结合方式的诊断性眼光。只有单一、特殊和普遍之间的一种平衡关系,才有可能使现代社会形成一个“伦理”总体。从黑格尔那时开始了这样一种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它围绕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用资本主义方式动员起来的、以加速度变得更加复杂的社会的框架之中,如何稳定维持以下两方面的脆弱的平衡:一方面是习以为常但变得松懈的原初世界的世界中的团结,另一方面是经济运行机制的功能迫令。因为,根据黑格尔对“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①这个词亦可译为“资产阶级社会”。——译者)的分析,经济运行动态过程连同增长着的社会不平等会同时促进异化和个体化,所以,只有国家的有组织暴力所具有的和解力量,才有可能在越来越个体化和利己主义化的个人之间维护社会纽带——但这样做又并不是依据其个体公民的抽象正义标 准。
康德可能提出异议说,一种成功的社会整合之高要求条件并没有解释,一旦私下的法权人承担了以民主方式共同发声的国家公民的角色以后,有良心个人的道德声音为什么就要沉默下来。而黑格尔从他的观察者视角则完全正确地认为,经验地来看,公民们的平均的道德行为和守法行为只有在共同生活形式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稳定。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必须以一定的基本信任彼此相对。但对于参与者本人来说,从这个事实出发并不意味着亲历的伦理生活对于政治正义具有规范上的优先性。由此我们到达了一个决定性的节点。在这之前,康德和黑格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教导,并且可以相互学习,但康德无法同意让正义的主张适应于社会关系的要求——除非有一种这样的适应不仅符合功能性的要求,而且本身也在道德的观点之下得到辩护。但在康德看来,这样一种检验不能仅仅由知识更多的哲学家来进行,而必须由公民自己来进 行。
为什么现代社会的公民在愤怒地面对不正义的时候,要把那些已经随着轴心时代宗教和形上世界观而出现的普遍主义道德标准,盲目地置于一种特殊善之下,或使之适应于后者,认为它在他们的生活形式之中据说已经实现了?为什么政治社会化的公民,对其“伦理的”生活关系的基本结构,亦即其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生活关系的基本结构,应该不再把它们放到道德眼光下来批判为不正义的,并且是作为参与民主立法者可以加以改变的?但是黑格尔在他的君主立宪制的构想中否认公民所拥有的就是这种权利;而且,他这样做不是出于纯粹的识时务的理由,而是出于成问题的系统的理由。也就是说,这里起作用的是一种对于臣民的自我授权的不信任,这种自我授权从经院哲学盛期(Hochscholastik)开始就表达于主观权利的概念之中,并且在直到卢梭和康德为止的现代理性法的发展过程中最终体现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当中。黑格尔的倾向于亚里士多德而反对康德的选择,暴露出他与这样一种古代正义观念和解的努力,根据这种正义观念,一种根植于形而上学的、剥夺公民之判断的自在自为的法律秩序,让每个人“各安其位”(“jeder das Seine”)。
三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必须强调康德和黑格尔之间讨论的这样一个中期成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黑格尔所重视的历史思维推动了康德的自主概念的非超验化,它剥去了理性道德和理性法的抽象性质(1)。另一方面,黑格尔为什么把支持他自己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诊断的道德的特性,置于总是已经存在于国家之中的伦理生活之下,这个问题揭示出他的观念论色彩强烈的“历史中之理性”(“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的观念中,有一个现实主义核心(2)。
(1) 借助于客观精神形态的发现,黑格尔引入了对康德的理智世界(Welt des Intelligiblen)的非超验化过程。恰恰是为了把握康德的划时代洞见的实质内容,我们必须把实践理性对于孤独的理智之我(intelligibles Ich)的内在论坛的运用,转变为诸多通过交往而社会化的主体的公共的自我立法。理性道德的这种非超验化过程解释了,道德法则所要求的、基于理智之我进行的那种普遍化操作,是如何可以变成相关主体之间的商谈性理解过程的。参与者如果具备了一种相互采纳视角的能力,并且服从更好论据的非强制性制约,就满足了这种论辩实践和协商实践的高要求语用前提条件。在对实践理性作这种处于历史语境中的运用时,参与者们必须始终留意的是,把按要求包容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反事实要素。因为只有这个要素才能够让他们不仅想到其判断难免的可错性,而且想到道德普遍主义的这样一种预期意义:只有自由才能充填自主这个概念,而从自主概念我们知道,除非人人自由,否则无一人自 由。
康德的理性法(Vernunftrecht)的非超验化——它也与理性道德的非超验化相一致——不再是来自一种哲学上构思的宪法。从18世纪后期的宪法革命以来,哲学反而只能局限于对宪法论证的历史成果和实践方式进行理性重构。哲学要考察的是,一个未来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或他们的代表如何在其立宪实践中追寻这样一个目标,即借助于现代法手段为一个自由和平等的法律人的自决共同体“提供基础”。以这种方式我们看到,民主法治国的宪法拥有这样一个康德主义的观念,即要用法律确保所有公民都拥有平等的私人自主和公共自 主。
(2) 黑格尔没有看到,在民主立宪国那里,康德自主性概念已经具有了法的形式,并且从理智之物的领域(die Sphäre des Intelligiblen)进入了历史。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拿破仑法典,也就是民法的实质内容,而不是共和国的宪法。另一方面,他有充分理由用伦理生活的概念去关注这样一个有规范相关性的向度,它在对于立宪实践的理性法重构中并没有得到明确考虑,而只是隐含地预设了。作出自我立宪之决定的并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一个实存共同体的居民,他们决心要把政治统治放到自己手中——参与者们绝不是偶然相逢的诸多个人的集合!因此,在每个宪法当中也可以找到一定的历史情形和历史挑战的沉淀物。尽管如此,一个先已存在的参与者们非正式社会化过程这个事实,只能在小册子的宣言性语句中找到,而绝不存在于宪法的原则纲要本身之中。因为,对于那些要全面确保政治统治运用的正义性的建制的奠基来说,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一些现存的社会形式,不管是伦理的、文化的还是宗教的方面,被固定为宪法规范的等级,确保政治统治运用的正义性的意图从一开始就被证伪 了。
当然,对于立宪实践的决断来说,对于宪法论证行动中的“我们言说”(Wirsagen)来说,一种相互的信任预设是必要的。所有相关者的公民、所有未来的公民,都必须有可能感到是有共同归属的(müssen sich zugehörig fühlen können)。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但它肯定并不足以拒绝黑格尔自己曾经欢庆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的道德威力。因为没有这种对政治正义之标准的源自自然法和理性法的哲学论证,对于政治统治之运行的合法性,是无法提供与神圣论证相匹敌的世俗论证的。如果我们把民主法治国之公民的自主性之得到确保理解为民主法治国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黑格尔用批判眼光看待的民主法治国的“道德负荷”,就完全是不可避免的。道德的原则不仅(根据黑格尔的法哲学)在刑法中,而且首先在公民权和人权的形式中,通过采取实证法的形式而获得一种社会有效性。借助于(如在德国,当然只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渗透进整个法的系统中的基本权利,规范与现实性之间的一块全新紧张区域被嵌进了社会现实本身之中。这种规范性反差释放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动力,因为对于现存关系中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之匮乏的批判,现在是可以援引那些不饱和的基本权利和正义主张的尚未耗尽的规范内容的。道德实践的学习过程,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它当然不再(如在康德那里)发生在单个主体的头脑之中,但也不是发生在以交往的方式社会化的主体们的头脑之外。这种理性在历史偶然性之中蹒跚行进,恰恰不是通过一个辩证地活动着的绝对精神这样的至高形式,而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如同田鼠①马克思1856年4月19日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演讲时说:“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译者,也就是以社会化的主体们自己在认知的、社会认知的政治—道德方面的可错的学习过程的形式。这种可错的学习过程的成果,不仅在基础层面体现在可在组织、技术和经济上应用的生产力上面,而且体现在平等自由之建制化的艰辛的、时时有倒退危险的进步之 中。
四
从今天的视角出发,我们能够从康德和黑格尔的相关讨论中拉出来的中期报表,大概就是这样。当然,马克思已经给了这种讨论另一个转向,因为他把黑格尔的社会理论视角转向加以激进化。与黑格尔相悖,他批判性地发现了这样一种社会权力的事实的痕迹,它被包裹在伦理生活的核心当中,并且以这种方式转变为政治暴力。从时间上说,马克思紧随着黑格尔,处在黑格尔与康德相分开来的那同一个年代阶段。作为七月革命的同时代人,尤其是作为失败了的1848年革命的同时代人,马克思成为了社会阶级斗争和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批判性参与的观察者。你们可能感到吃惊的是,在批判黑格尔对古代人的形而上的法权想象与现代人的法权想象作相互调解的不幸努力的时候,我会求助于马克思。因为马克思追随他的老师去推崇亚里士多德而贬低康德,并且把他自己的资本主义批判的规范性基础,说得客气一点,弄得既混乱又晦暗。但是,在对“绝对精神”进行清算以后,马克思是最坚定不移地接过黑格尔的问题提法,并同时对黑格尔提出最尖锐批判的那个人。由于他的青年黑格尔派同事的宗教批判已经促使他从原则上不信任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的社会整合力量,整个伦理生活的领域现在都落入了意识形态怀疑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把黑格尔作为“第二自然”来把握的客观精神形式,从民族精神学说的历史性理解,转译成了社会理论的语言。因此,对以交往的方式社会化的、从事生产的诸多主体与其社会生活形式的关系,他们不再按等级高低理解为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关系。因为主体在与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遭遇的时候,后者不是作为一种提升性的“第二天性”,而是作为一种“自然化的”社会史的压迫性和诱导性的暴力。这种视角转换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要把对于阶级社会之现存的不正义的道德愤慨的冲动,而不是道德,作为反对伦理关系之假象的解放斗争的力量来加以信 任。
黑格尔之所以把伦理生活领域称为第二自然,是因为那些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是带着其具有语义特性和规范特性的经验而与认知着的精神相遭遇的。但他把它们称为另一个或第二个自然,又是因为这些语词、文本和作品,这些做法和建制,这些制度和传统,它们所具有的隐晦一面,都不像第一自然那样具有物理对象的不透明的客观性。这种隐晦性得到澄清的程度,取决于对理由之主线的诠释者,在多大程度上深入理解符号对象的内部、理解它们的意义。在黑格尔看来,客观精神用来与主观精神相遭遇的,就是理由的理性力量(die vernunftige Kraft von Grunden)。从这个立场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黑格尔把主观精神置于客观精神之下,并且在谈论主观精神时不提以交往的方式社会化的诸多主体彼此之间的、它们与主体间分享的生活关联之间的对称关系;同时我们又看到,为什么政治共同体的伦理生活状况会免予公民的道德异议——黑格尔完全无法想象,自身就是由理由之结晶所构成的客观精神,居然会用理由让主观精神受骗。直到马克思,意识形态才得到了理解,它是可以用理由让公民受骗的,因为那种掌握生产方式的人们的社会权力,会以一种不透明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和文化的生活形式向来透明的教养力量之中。政治权力是公开的,但掩盖在社会和文化之中的社会力量,则用以下方式施行一种不公开的统治,即限制好的理由的自由流动,并且以此悄悄地阻碍政治行动主体运用其理性自由。黏着在社会权力运用中的、一定程度上包裹在硬壳中的这些理由,会使得自由的公共交往之流变得凝固。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尔的“第二自然”那里发现了一个“自然化”(Naturwuchsigkeit)的向度,这个向度能在明显的不正义面前为现存关系提供稳定性。这种思想的要点是,那种以意识形态方式凝聚起来的理由,是可以通过批判性的理由来加以把握的,因为意识形态就是要在理由之空间本身之内设置边界。马克思用关于“自然化的”统治关系的意识形态启蒙所要剥去的,据说是“伦理的”生活形式的面具,这种生活形式如果要稳定阵脚,只能通过掩盖社会事实维持那种公正性很勉强的社会关系的有效假相。阶级社会的自然性就表现在这一点,即把政治统治呈现为经过意识形态点缀的所有公民之共同利益的代 表。
如果我们把对于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解读放在有关先前讨论的哲学理解当中,并且不把社会过程的自然化误解为具有自然法则性质的,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就发生了逆转——要反抗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不正义,首先必须为推翻分裂的社会、为政治共同体的真正凝聚创造经济基础。但是,对这种政治斗争发生兴趣,马克思是作为政治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而不是作为理论家,尤其完全不是作为政治哲学家。作为研究者,他在不列颠图书馆捡起的只是黑格尔法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线索。到头来,他就像黑格尔那样,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确信,最终会导致资产阶级社会瓦解的那同一种经济危机,也将释放出导向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形式的力 量。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其早期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之后,没有回到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的思考。他同样也没想到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福利国家的那些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青年马克思,连同其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已经走偏到另一个轨道。像黑格尔一样,他没有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宪成果,其核心是人权和公民权。他希望把国家的上层建筑消解在一个完全从法权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之中,而没有看到,即使在一个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也必须有一种确保私人权利的社会自主,如果人们作为国家公民要能够行使其确保公共权利的政治自由的话。这自然不是要反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借助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提问题的提法是正确的,至今仍然是真实的。当然,他可能受到他那个时代政治的阶级统治的规范上可恶的自然性的误导,低估了这样一种事实性的自然性的抵抗力量,这种自然性使得一种世界范围内交织一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复杂性,与民主驯服的种种努力,处于相互对峙的状 态。
五
上述对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复杂讨论的回顾,有助于我们考察以下三个相关因素在今天仍占主导地位的相互关系——即使在今天,为资本的充分运行提供条件的旨在避免危机的国家政治(Politik der Krisenvermeidung),必须在这样的双重条件下运行,它不仅要满足一种具有充满道德内容的宪法的合法化要求(Legitimationserfordernis),而且要满足社会凝聚或“伦理生活”的功能性要求。一方面,20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必须在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视角之下满足更广泛阶层有关其政治自主和个人自主之法律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兴趣;另一方面,福利国家自己也必须依赖于其公民的团结,从而一方面多数决定会被处于下风的少数派所接受,另一方面他们所选择的决定不仅仅是满足短期的特殊利益的。足够比例的公民,以及公民中有代表性的那部分,必须是愿意把参与民主立法者的角色也作为取向于共同福利加以理解。而对共同福利的这种期待,即使只有小幅提升,也要有足够程度的社会整合与之相适应。而今天还有一个因素发挥作用——现在社会融合虽然也依赖于,但不仅仅依赖于社会正义意义上的那种包容;政治包容现在也逐渐延伸到了种种文化生活方式和亚文化氛围之间的区别。对于那些古典的作者来说,这还不是一个问 题。
当然,对被排斥的或处境不利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容纳,过去和现在都已经带来这样的结果,即彼此陌生的文化氛围相互开放,以使得有可能在相应扩大的民族文化框架之中出现一种以“我们”来言说的国家公民们共同的意志形成过程。但是,只是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那些对其文化认同的特性提出政治承认之集体主张的地区独立运动,以及整个宗教的、语言的和文化的少数群体的斗争,才出现了它们的前提条件。在我们的语境中,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即这些冲突以一种不同于社会经济冲突的方式考验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共同体之公民之间的团结。他们也要求社会的和政治的平等正义,但仅仅这一点他们并不满足。彼此都想维护其认同的那些生活形式之间的冲突潜力,最终只能通过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才能加以缓解。在通常情况下,与文化歧视相联系的,还有一种社会压制。但那些在规范上受到保护的文化隔阂要得到沟通,迄今为止决定了该国政治文化的那个历史地形成的多数文化,就应当作创造性的扩展。否则,所有公民平等地在其中得到承认就无从谈起。一个彻底含糊的例子是欧洲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由各种民族运动引发、由行政力量推动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统一的省份和“领地”的地区意识和乡土意识,融合为一种由学术精英们表达出来甚至设计出来的民族意识。在许多场合,在19世纪,一个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动员起来的族群,是凭借其在民族史方面激发活力的公民意识,来给一些王侯领土国家的在一定程度上还精神空虚的架构充填内容的。这种由国家本身来推动的意识转变过程的人为性质,对民族主义释放出来的那种不仅对外而且同时也针对内部的少数群体的好战暴力,或许有所解 释。
但是,在现成的民主共同体之内,在(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日益增长的文化多元主义的紧张过程中不断进展的政治文化之自由化,是一些具有道德核心的政治上的学习过程的成果;因为基本法权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的普遍主义,是通过这样的学习过程才对一种具有功能必要性的政治包容之扩大(但并非强行进行一种不顾规范上得到论证的必要性的同化),起到先导的作用。哪里缺少共同的文化背景,哪里的国家公民的平等地位,亦即法律包容的“道德”,就要求有政治文化容纳的“伦理生活”的补充,也就是促成所有人都可能参与的相应扩展了的政治文化上的自我理解。随着这种建构性转向(Wendung zur Konstruktion),“伦理生活”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一种围绕已得到正式确保的对于政治包容的基本权利主张而非正式形成的政治文化,不再是以一种历史地成长(gewachsen)的氛围的形式存在了;相反,它必须——这是新的地方——是结晶而成的(herauskristallisieren),但不能借助于法律的行政的手段而促成(erzeugt)。一种以自由方式扩展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有丰富历史内容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宪法爱国主义构成物,它是无法刻意形成的(das nur beilaäufig entstehen kann)。它至多能出现于(hervorgehen)一种所有公民都已经共同从事的国家公民实践之 中。
上面我对从康德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直到右翼民粹主义当代的讨论进行了回顾,下面是我的这个极其概略的回顾的要点:在上述情形下,一种会给国家公民之团结以足够支持的自由的政治文化,其自身必须来自公民们在为创造性地解决其共同问题而进行的民主斗争中已经创造出来的经验。这样,对于社会不正义和政治不正义的道德愤慨,才能为一种支撑跨越社会隔阂以及文化隔阂的公民团结的新型的政治的伦理生活的扩展提供先导。在文化多元的社会中,这种动态机制表现了这样一种道德和伦理生活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走在前列的是对基本权利遭受损害的批判声 音。
这种乍看是文化主义的思考,绝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支持全球化的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奢侈品;也就是说,它绝不回避资本主义危机动力机制当中产生出来的那些棘手的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因此首先要评估欧洲各国人民(europaische Volker)今天必须解决的问题的严重性,以便在一种世界范围蔓延开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迫令面前,在跨国层面上赢回他们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丧失的政治行动能力。他们如果要拯救摇摇欲坠的福利国家模式,并且不再是为了一种抽象地追求的国际竞争力而屈服于日程增长的社会不平等趋势,就必须以一种并非完全是没有代价的方式进一步加深在欧洲层面上做到一半的建制化合作;他们必须把在民族国家建设中已经多次形成的那种政治外壳先构筑起来。只有当各国人民破除了其民族国家文化的狭隘意识,他们才可能克服其国家的民族利己主义,尤其是经济上的民族利己主义。他们必须相互开放其民族的公共领域,并且准备超越其民族边界彼此交换他们的视角;因为,只有在关于如何解决其共同问题的超越边界的争论过程中,他们才也会意识到他们的政治文化的共同根源。上述命题是以虚拟语气提出的。因为实际上,支撑团结的民主实践之源今天在各国都已经干涸。政治精英们,除了少数例外,都因为一种被人在意识形态上大做文章的社会复杂性而丧失斗志,失去了进行一种形成性政治(gestaltende Politik)的勇气。与此同时,几乎抽干了所有真正重要议题的民族国家公共领域,则不是变成了相互煽动民族主义怨恨的平台,就是变成了消遣和冷漠的舞 台。
我们如果不想陷于一种阴暗预测的话,可以在一种受过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康德思想那里有所学习——理性的田鼠只是在以下意义上才是盲目的,即它知道自己撞到了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否会有一个解答。它不顾一切只顾往前拱,确实是够固执的。我们得到这种看法是受了康德的影响——同时连同他的种种洞见。可以说,他的哲学就是要为这种思想搜集好的理由。就他的如此了不起的启蒙的哲学而言,这难道不是最了不起的事情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