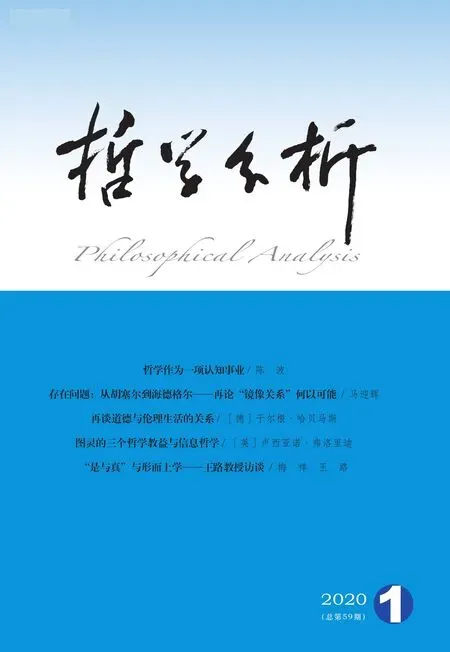实验哲学:一个尴尬的概念
费多益
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是近些年来比较流行的运动或趋向。它抛出的主张是用实验调查的方法来进行哲学研究。①从概念和表述看出,实验哲学可以理解为“以实验为根据的哲学”或“以实验的方式从事哲学”,而非“以实验为对象的哲学”(英译为“Philosophy of Experiment”),后者则是科学哲学的重要内容。实验哲学的口号是:让哲学家离开“扶手椅”走向实验和实践,为古老哲学问题的研究带来新的力量。①Robert Frodeman, Adam Briggle and J. Britt Holbrook, “Philosophy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ism”, Social Epistemology, Vol.26, No.3—4, 2012, pp.311—330.其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实验哲学声称它借助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了解到普通公众对“理性行动”基本概念(如“相信”“责任”“道德的客观性”②参见Jonathan Haidt, “Invisible Fences of the Moral Doma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28, No.4, 2005,pp.552—552。和“自由意志的可能性”③Shaun Nichol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 Will”, Science, Vol.331, No.6023, 2011,pp.1401—1403.)的看法以及形成这些判断的神经机制,发现了不同人群以至跨文化群体的直觉差异,从而使哲学研究建立在更为有效的经验基础之上。如斯蒂奇(Stephen Stich)所言,“如果继续得到同样的结果,那么整个20世纪乃至之前的哲学家所使用的核心方法(依赖躺椅直觉)就出现了问题。”④Edouard Machery, Ron Mallon, Shaun Nichols and Stephen P. Stich. “If Folk Intuitions Vary, Then What?”,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86, No.3, 2013, pp.618—635.于是基于实验哲学的思路,遍布哲学领域的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重新讨论,正因为如此,实验哲学宣称自己引发了一种哲学变革。
通常把温伯格等人的《规范性与认知直觉》一文看作实验哲学诞生的标志。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太长时间以来,认识论研究者严重依赖认知直觉,于是提出和辩护了如下两个主张:(1)如果关于认知直觉的经验假设中的一个或多个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一个相当大的认识论研究群—— 一个包含了分析传统认识论中所做的大部分工作的研究群——将会遭到严重破坏;(2)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这样的一些经验假设的确是正确的。这些证据大部分来自正在进行的一系列关于认知直觉的实验研究。因此,那些从事有关认识论研究的人有责任解释为什么假设的真实性不会危及他们的结论,或者为什么根据实验证据仍然可以认为这些假设是错误的。⑤Jonathan M. Weinberg, Shaun Nichols and Stephen Stich, “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 Philosophical Topics, Vol.29, No.1—2, 2001, pp.429—460.
近二十年来,在“实验哲学”的旗帜下汇集了一个活跃的军团⑥Christopher Shea, “Against Intuition”,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55, No.6, 2008, B8—B12.,它的拥趸包括弗洛德曼(Robert Frodeman)、诺布(Joshua Knobe)、费尔茨(Adam Feltz)和克科利(Edward T. Cokely)⑦Feltz, Adam and Edward T. Cokely, “Do Judgments About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Depend on Who You Are?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in Intuitions About Compatibilism and Incompatibilism”, in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Vol.18, No.1, 2009, pp.342—350.、尼科尔斯(Shaun Nichols)、凯利(Sean Kelly)、玛歇利(Edouard Machery)⑧David Colaço, Wesley Buckwalter, Stephen Stich and Edouard Machery, “Epistemic Intuitions in Fake-Barn Thought Experiments”, Episteme, Vol.11, No.2, 2014, pp.199—212.等人,而他们的每一项实验又几乎可以衍生出新的实验方案。那么,实验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吗?它对已有哲学的批评是否成立?它所给出的方案能否真正解决它的诉求?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试图由此启发人们思考:在学科高度分化却又不断交叉的今天,哲学的作为是什么?
一、实验哲学:做哲学还是做科 学?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实验哲学的工作分为两类:一类是数据采集,即设计哲学场景,进行问卷调查,收集被试者关于某个哲学直觉p的信念状态(相信p/不相信p)的实验结果;另一类是数据分析,即通过呈现实验结果与“传统哲学”的直觉差异,表明哲学家的直觉不具普遍性,这种研究属于元认知(metacognition)①John H. Flavel, “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 A New Area of Cognitive-Developmental Inquiry”,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34, No.10, 1979, pp.906—911.范畴,即对认知的认知。就前一种情形而言,实验哲学从取样到实施与依赖调查和测试量的实验心理学没有区别;就后一种而言,实验哲学跟认知心理学进行的部分工作是重叠 的。
回顾一下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实验哲学的主张延续了40多年前实验心理学对只注重内省的传统心理学的声讨,其中可以窥见心理学家布罗德本特(Donald Broadbent)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布罗德本特在谈到如何看待心理学的前景时,不无忧虑地说道:“没有人能坐在扶手椅里抓住事实的本质。而且,在新的实验进行之前,我们不会知道结果如何。”②Donald Broadbent, Behavio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1, pp.200—201.作为对这一担忧的回应,之后不久,认知心理学之父奈瑟(Ulric Neisser)就开启了运用调查法去探寻真实生活中个人记忆的新阶段。
然而这样的声讨并不适用于哲学。把两者做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首先,研究对象和探索目标不同。实验心理学虽然涉及广泛的人的客观行为和心理现象,但它的研究对象必须满足“可检验性”标准,它的进步也是通过研究可解的实证问题而取得的。相比之下,哲学的对象无所不包,各种现象都被认为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哲学家不以直接的方式思考这个世界,他们所思考的是思考这个世界。哲学以超越实证和经验的思考以及前提性的反思而区分于科学。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问题可以通过经验的方式得到解决,即通过感官知觉或做实验得到解决,那么它就不是哲学问题。③John Hospers,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Analysis, 4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Prentice Hall, 1996, p. xi.所以,科学能回答的问题,不是哲学问题。
对普遍性的执着追求,无法满足于特定领域的知识。哲学史上,人们不断地提出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并未由于科学的发展而得到回答或因此而被消除,因为哲学“不同于任何一种各部类的科学,没有任何别的科学普遍地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而是从存在中切取某一部分,研究这一部分的偶性”④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当所有的科学都只关注各自的领域时,哲学关注的却是普遍意义上的存在。科学不去回答本质的终极问题,而是将概念建立在可观测的现象基础之上,通过对概念进行操作性定义获得进步。哲学的思考则超越已掌握的事物和已看到的现实,关乎我们所做判断的辩护,关乎对可能性的敏锐捕捉和把握。哲学作为一种理性的活动,其所操作的对象是理性实践本身。这一区别从各自的提问方式即可看出,例如,认知科学更关注心智是如何运作的 (How does your mind work?),它涉及表征、计算、识别、模拟、信息加工等等这些偏重认知结构和机制层面的东西;而心灵哲学更多关心的是,我们所说的心或心智究竟是什么(what is the mind or mentality?),涉及心理内容及其根源、心理现象的本质、特征、其存在和变化方式、心身关系等等形上层面的东 西。
与目标不同相伴的是方式上的差别。哲学的态度通常表现为:在探求知识之前,关注术语或概念的界定,即“某概念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它的关切集中于理解和澄清“一阶”学科的概念表述。这种理念意味着,当一个词被当作理论中的概念使用之前,必须对这个词的使用所涉及的潜在语言问题有清晰的理解。与此相反,在科学领域里,某概念的意义确定,发生于与该术语有关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研究之后;一个精确的概念性术语来自科学过程中数据和理论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在对物理世界展开研究之前,物理学家不会花费气力讨论如何使用“能量”一词;在讨论物质的基本组成时,不会去追究“粒子”一词是否真正表达了他们要表达的本质含义。对于“生命一词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生物学家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含义,它只是足够好地满足我们生物学家工作需要的一种用法,并不是争论或辩驳的主题”①Peter Medawar, The Strange Case of the Spotted Mice and Other Classic Essays on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66—67.。科学家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其进步的关键在于放弃本质考查,接受操作主 义。
即使在与人相关的科学领域,情形依然如此。以心理学为例,心理学家必须经常接受被试者给出的言语报告,以此作为建立他假设的材料依据。这些报告常常包含诸如“知觉”“意象”“观念”“记忆”等术语,它们是关于被考察现象的完整知识结构所必需的。对这些术语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术语的性质,例如“什么是意象?它如何与外部世界相联系?它能否作为证据被接受?”但实验者所关心的是:“被我们称为意象的那种东西在什么环境下发生?它的功能是什 么?”
二、实验:哲学的“助探工 具”
关于实验的地位,或者哲学命题需要经验支持的论断,在一个世纪前已被逻辑经验主义讨论,并从理论上得到确立,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逻辑经验主义为了清除无意义的概念和命题,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工具,进行概念澄清和语言分析,而实验作为人工控制的经验过程,对于理论的确认或驳斥都给出了有价值的暗示,并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一次实验就是向自然提一个问题”、“有想象而没有实验的检验,只会通向空泛的思辨”①汉斯·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0、130页。,关于这些主张我们只要读读赖欣巴赫(Hans Reichenbach)、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石里克(Moritz Schlick)、纽拉特(Otto Neurath)、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费格尔(Herbert Feigl)等人的著作,就很容易知道。实验研究也为当代实在论提供了最有力的手 段。
哲学研究的持续和深入,当然离不开科学的发展。借助科学就其内容来说并不新颖,之所以宣称新颖就在于实验哲学家没有把借鉴科学成果作为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哲学本身就需要运用其他学科所提供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资源,但哲学通过自身独特的方法探寻隐藏于现象的实质以及事物背后的终极原因,而不是依附或混同于其他学科的方法。“在与一阶事实保持距离的地方工作,正是哲学的特色”②杰伊·F.罗森伯格:《哲学是做出来的》,张家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21页。——分析事实所依据的合理基础或理由,以及对“一阶”学科的预设及前提条件进行深入的探究。哲学试图去理解“最广意义上的事物如何在最广意义上相互联系起来”③Wilfrid Sellars, “Science and the Philosophical Image of Man”, Science, Perception, and Reality, Atascadero:Ridgeview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1.,去理解这类理解的限度。哲学家并不像具体学科研究者那样具备判断“一阶”断言真假所需的专门知识;这些断言如何被认为是对的或错的,不是哲学所解决的问题。不过,哲学家坚持这些问题作为思考的背景需要先得到解决,而他们的工作建立在此基础 上。
也许有人会说:关于世界的图景和世界的本源,科学提供给我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系统,这样,所谓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就会逐渐消失——20世纪初,实证主义不是就举起“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拒斥基于思辨虚构的宇宙本体论吗?科学的发展的确如此,不过,以范畴和先验原理为探究内容的范畴本体论不仅形成了悠久深厚的哲学传统,而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当代哲学家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的描述形而上学试图通过对语言用法的分析来揭示我们实际的思维结构,这些努力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并深化了范畴本体论。除此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形态的形而上学:“意义本体论”。“意义”具有认知、评价(如伦理、审美)、语言分析等多方面的涵义。在语言的层面,意义被理解为与之相对应的“所指”(事物、事态或事实等),并根据不同的命题类别拥有相应的标 准。
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立法者,其魅力和不朽在于思想能力的创造。哲学家的训练和专长是概念分析和推理思辨,他们的训练和贡献体现在运用逻辑发现疑点以及构想新的可能性方面,而不是自己去充当实验者或科学普及者。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就不以为然地说:“这种或者那种民间哲学的所谓许多发现很有趣,但对于传统哲学家来说并不是新闻,哲学也不是实证问题,我不觉得实验哲学对哲学研究有什么影响。”①Timothy Williamson, “Replies to Kornblith, Jackson and Moore”, Analysis, Vol.69, No.1, 2009, pp.125—135.路德维希(Kirk Ludwig)则坚持,我们必须最终通过第一人称途径(躺椅上思考)来追求我们在哲学上为自己设定的目标。②Kirk Ludwig, “The Epistemology of Thought Experiments: First Person Versus Third Person Approaches”,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31, No.1, 2007, pp.128—159.对他而言,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通过思辨的创造,打开一个为日常思维和经验思维所遮蔽、封闭的思想空间,使人们能够获得一个更合理的想法。在这个意义上,哈克(Susan Haack)认为实验哲学“甚至也算不上令人鼓舞的跨学科交叉”③Susan Haack, “The Fragmentation of Philosophy, the Road to Reintegration”, in Julia F. Göhner, Eva-Maria Jung(eds.), Susan Haack: Reintegrating Philosophy,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pp. 3—32.,因为实验只是哲学工具箱里的助探工 具。
三、方法论自然化中的“解释鸿 沟”
实验哲学认为它的一大优势是充分借鉴和运用了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关于精神和心智活动的神经机制的发现,无疑扩展了人们对感觉、知觉、记忆、情感和意志的认识界限,让我们探知人在行动时大脑中发生了什么。但它们无法对日常心理(如理由、意图、目标、价值、习惯等)做出解释,也不能通过论及脑或脑某些区域的感知或思考来解释人如何感知或思考。科学家自己都谨慎地承认,作为解释而提出的认知模型仅仅构成对所考虑问题的重新描述④Maxwell R. Bennett and Peter M. S. Hacker, “On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Behaviour”,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67, No.4, 2015, pp.241—250.,因为,进行感知和思考的是人,而不是他的脑或脑的某些区域,脑的活动使人(而非脑)得以感知、体验和思考。更重要地,心智、意识、体验最重要的特征是其主体性,它不受物理世界因果规律的支配:对人的内在状态、事件和过程的解释既关系到神经生理学各种理论主张的意义(这些主张意味着什么),也关系到采用这些主张的合理性及其理由,不能仅仅通过诉诸物理解释而获得成 功。
如今先进的脑成像技术可以反映脑在完成某个认知任务时的重复性变化,这些图像及其数据不是对大脑活动的直接呈现,而只是揭示出与该任务相关的较活跃脑区的局部特性。例如,功能磁共振成像检测的是流向特定脑区的血液变化状况,后者与神经活动的确有线性关系,但我们需要借助其他一些相关信息做出判断,并在相关语境中进行解释⑤Christian G. Huber and Johannes Huber, “Epistemological Considerations on Neuroimaging—A Crucial Prerequisite for Neuroethics”, Bioethics, Vol.23, No.6, 2009, pp.340—348.,因为大脑的活动是高度复杂的,涉及各部分结构的具体功能、神经系统整体的运转以及个人的兴趣、价值取向等等。一方面,我们的感受质与外物刺激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另一方面,同一脑区可能与许多不同的心理状态都有关,没有一个单一的区域承担特定的心理状态的表现,例如,内侧额叶前部皮质激活是焦虑程度加剧的标志,然而,这一区域也可能因兴奋而变得活 跃。
大部分对意识的科学和哲学讨论聚焦于“感受质”(qualia)——我们的经验的质性方面,比如所感知到的西红柿的红色、柠檬的酸味等等。神经科学家已经建立了这些质性与特定大脑状态的紧密关联,并且能够通过直接影响大脑来操纵我们的经验。可是,我们至今无法用大脑活动或其他任何物理过程解释感受质。我们甚至难以想象这种解释会是什么样的。且不说一些心智现象(诸如“嫉妒”之类的复杂心理状态)在目前还未找到直接的神经基础,即使绘制出所有瞬时意识的脑活动准确模式,我们也无从得知心智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精神背后的生理过程是体验的生理联系而不是体验本身,呈现在意识中的是感觉而不是生理运动的机械变化。经验是以第一人称方式出现的。一个特定的物理系统何以拥有作为主体的感受呢?科学在这个问题上无力回答。
对于人的经验来说,我们所关心的不仅是停留于实证层面的真假,而且关乎“有意义和无意义的领域”,后者属于概念和逻辑方面。①贝内特、哈克:《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张立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8—429页。当一个人抬起手来指向远方时,生理学家对此的研究集中于从抬手到指向手势的发生过程,他试图弄清抬臂动作的一般性机理和形成指物动作的精细运动。在他看来,只要能够解释指物动作所有可见的运动,就了解了全部过程。所有这些关于运动的神经生理学描述与我们所见的指物动作的外在表现完全对应起来,但它并未能告诉这种对应所表达的意思,没有对该运动何以成为一个指物的行为(action)做出解释。只有当了解了所关注的运动在什么背景下发生,我们才可以说明某一个特殊的动作,换句话说,“只有在我们知道特定的同一关系时才能对特定的心理事件做出说明”②唐纳德·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牟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63—264页。。这样,为何想要或者打算去指某物,可能是问题的关键,比如你或许是希望明确事物所在的方向,也或许在表示惊讶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指物动作的意图。判断一项运动是否可被描述为有意要去做的动作,显然须将该运动的语义和语境构架考虑在 内。
这里需要澄清两个不同层面的解释。在个体(personal)层面上,当我们对经验进行描述时,这一经验属于作为整体的个体,他被视为具有理性的主体,其行为间的相互关系受各种规范支配,因而关于他的知觉、意图、信念和想象的描述是以一种具有整体性和规范性的方式得到理解。与此相对照,在对经验所依赖的神经活动进行描述时,我们所描述的是亚个体(sub-personal)层面上的现象,其内容缺少整体性和规范性特征。例如,我认为你的内心很愉快,我是在个体的层面上做出这一归属的,这一归属判断是否有意义,部分地取决于愉快的概念以及你对愉快的理解等。与此形成对照,你的某一脑区具有某种电磁活动模式,这是从亚个体层面上做出归属的。个体层级关注的是个体的行为,即某人为什么会在特定时刻做出某种行为,这样的理解有时是猜测的或粗略的;而亚个体层级则倾向于去了解与预测普遍的人类行为,即个体如何能够做出某种行为,它专注于寻找现象的机制性解释。①Martin Davies, “Interaction Without Redu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and Sub-Personal Levels of Description”, Mind and Society, Vol.1, No.2, 2000, pp.87—105.这两个层级的理论具有各自所针对的目标及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它们共同构成关于人类行为的更加丰富合理的图 像。
但心理谓词的对应主语只能是作为整体的人,而非身体或其组成部分。例如当我们说“眼睛在看”时,实际上是表示“人用眼睛看”;同理,当我们说脑有无意识时,表达的是具备脑的某种生物拥有或丧失意识;只有人和行为表现上与人相像的东西才能被看作心理谓词的主语。其原因在于:(1)它涉及个体独特性的词汇(distinctive vocabulary),即个体层级包含信念、欲望等涉及意向状态的语词,而在神经活动层次,意向性是无法得到解释的;(2)它涉及在个体层面可以进行区分的规律(distinctive laws),即个体层级能够辨认出其他层级所无法辨认的行为规律性;(3)特殊的限制(distinctive constraints),指在个体层级,我们要根据理性原则归属对于对象的意向状态,并且假设持有信念的个体是理性的。②José Luis Bermúdez,“ Personal and Subpersonal: A Difference Without a Distinction”,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Vol.3, No.1, 2000, pp.63—82.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差异决定了个体层级的解释无法被其他层级的解释取 代。
方法论的自然化使得实验哲学家从关于被考察对象的感觉印象直接得出观察陈述或观察命题,然而这不正是塞拉斯所批判的所与神话吗?事实上,没有任何给予经验的东西能够独立于概念能力的获得而对我们的信念提供确证。心智的奥秘尤其如此,它关联着与特定感受相连的生命过程的奥秘——大脑的神经回路随着生命的展开被赋予了个体性和独特性,反映了特定机体的生命历史。同时,每一人类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并不简单地由个体心智所决定,而是内化了许多体现为社会文化传统的一般性行为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内容不可能直接地经验到,而关于某个直觉的经验叙述更不足以成为对一个哲学命题的证明和反 驳。
四、直觉作为证据的确证困境
实验哲学针对的是哲学家的直觉作为证据的合理性与限度。但传统哲学家也倾向于拒绝将表面直觉作为证据,并且通过直觉得出的结论从未停止接受发展着的科学的检验。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认知与道德直觉上具有明显差异这一点,人类学早在19世纪就开始关注和探讨,认知科学领域近几十年来也出现了大量、丰富的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都不断地融入了哲学论证的素材。从这个角度看,实验哲学并不构成它所声称的对哲学传统的挑 战。
与反对专家直觉相应,实验哲学强调以群体共同发生的直觉为研究基础。那么,大众直觉或不同文化群体的直觉可以作为哲学判断的可靠证据吗?我们知道,证据是指在论证中能够使人相信某一命题为真的理由,直觉要成为基本的哲学证据,就需要满足作为真理由的基本要求。而直觉并不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优先地位。对此,索萨(Ernest Sosa)就曾问道:“直觉之于哲学能够如同知觉之于经验科学吗?”在他看来,直觉分为“经验的”直觉和“理性的”直觉,后者才是信念所依赖的东西,从而关涉到哲学中使用的那种抽象的扶手椅思想。①Ernest Sosa,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Intuition”,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132, No.1,2007, pp.99—107.也就是说,作为命题态度的直觉本来就不是支持或者确证某种理论的证 据。
直觉这种心理状态或信念倾向,是建立在经验的规律性强化之上的,尽管由于它是一种具有进化根源的潜能,但直觉运行的机制是依靠情感刺激诱发灵感,从而建立起本能与感觉、情感和对象之间的关联,因此离开了规律,直觉也就失去了意义。直觉的有效性取决于过往的积累与训练水平。人们相关的经验越丰富,直觉的准确度越高。因为大脑只能给出与之相对应的自觉反应,当积累增加时,才可能产生更准确的直觉。②Arie W. Kruglanski & Gerd Gigerenzer, “Intuitive and Deliberate Judgments Are Based on Common Principles”,i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118, No.1, 2011, pp.97—109.只有环境具有足够的规律性,并且这些规律在判断时已被人们掌握,联想机制才会识别情景并做出预测和抉择。③David G. Myers, “Intuition’s Powers and Perils”, Psychological Inquiry, Vol.21, No.4, 2010, pp.371—377.以上条件得到满足,我们有理由相信某个人的直觉。相反,如果本能拥有的事实经验匮乏,或本能从事实经验中觉察到的联系较差,直觉给出的结果将可能使我们误入歧 途。
退一步讲,即便承认直觉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我们如何能够真切地获得或呈现直觉?实验者采取的方法是:安排不同条件的情境,通过谨慎地只改变情境中的一个变量,考查这一因素是否导致目标行为的产生。那么,怎样确定实验中不同情境人的行为差异是由特定因素造成的?其关键是保证较高的内部效度,后者被定义为确保除自变量以外的其他变量的一致性,也就是当且仅当自变量对因变量造成影响。这要求控制所有无关变量,并且被试者是随机地被分配于不同的实验情境。但如此一来,情境可能变得虚假而不像实际的生活。被试者知道自己在参加心理实验这一事实,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这就是心理学实验的外部效度危机,即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推广到其他情境或其他人身上?此处所说的推广包括两种类型:(1)从研究构建的情境推广到真实的生活情境(情境的推广性);(2)从实验被试者推广到一般人(人群的推广性)。
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冲突:如果提高内部效度,就要随机将人们分配于不同实验条件并严格控制情境,以此保证没有无关变量对结果产生影响;而这样一来,外部效度也就必定受到损害,因为这样的情境与日常生活相差很远;外部效度的提高可以诉诸增加实验的心理真实性,这使得实验中激活的心理机制接近于现实生活激发的心理机制,或实验所引发的心理过程接近于自然情境的心理过程,但如此将使控制所有无关变量的操作变得相当困难。①埃略特·阿伦森等:《社会心理学》,侯玉波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与此同时,实验的可重复性也饱受质疑:心理学实验中,自变量具有多样性,它们在许多情况下几乎同时起作用,而且通常往往以相反方向起作用(例如个体的内部条件和环境条件),而一方的稳定性始终伴随着与另一方的可变 性。
除了操作层面的困境外,实验哲学还面临着实验结果与量化修正之间的裂缝。实验所提供的是相关性数据,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联。实验的目的和意义恰恰体现在基于可理解性进行因果分析,以及从观察结果中发现因果性的规律,否则我们只能停留于现象。而从相关推导因果的困难是:对于一个现象的数据及其解释非常多,我们如何找到最接近真相的那一个?无疑,我们关心的是有效数据,这些数据间存在逻辑关系,但无论数据集有多大,因果结论不会仅仅从观察到的统计规律中得出。相反,哪些数据是有效的取决于因果结构,我们不得不利用我们所有的线索和想象力来创建合理的因果假设,包括诉诸干预和构造反事实假设②Judea Pearl, “Conditioning on Post-treatment Variables”, Journal of Causal Inference, Vol.3, No.1, 2015,pp.131—137.。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剔除伪相关或随机相关,即从无穷的相关与混杂中,选取既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又与误差项不相关的变量(即工具变量),然后分析这些假设,看看其是否合理以及如何通过数据来检验它们。也就是说,实验获得的数据不能直接拿来就用,而是首先进行数值分析。用样本指标估计总体指标,必须接受显著性检验和证实。为什么?这是为了消除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第一类错误(α错误)是零假设(原假设)为真却被误拒绝的概率;第二类错误(β错误)是零假设为假却被误接受的概率。简言之,运用小概率反证法,在假设的前提下,估算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如果该事件是小概率事件,在一次研究中本来不大可能发生,但却发生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推翻之前的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反之,若该事件不是小概率事件,我们就找不到理由来推翻之前的假设,即接受原假 设。
假设检验需要明确:问题是什么?证据是什么?判断标准是什么?然后才能得出结论。检验方法有很多种,例如 T检验、T′检验、U检验、χ2检验、Z检验、方差分析等,究竟该用哪种好呢?这就要求我们对总体的特征做出某种假设,比如它符合离散变量概率分布还是连续变量概率分布?离散变量概率分布可能是二项分布、伯努利分布或泊松分布;而连续变量概率分布又包括均匀分布、正态分布、指数分布、伽玛分布、偏态分布、贝塔分布、威布尔分布、卡方分布、F分布等等。在对分布做出假设的时候,实验者依托已有的背景知识,预设了想要探寻的总体样本的特征,那么,这是否同样构成了实验哲学所批驳的“认知成见”呢?无论如何,对于“直觉在多大程度上可靠”的判断需要诉诸经验,而对这种判断的判断仍然依赖于直觉,如此就陷入了一种自我支持或循环论证,但实验自身却无法解决这个问 题。
以上是本文针对“把实验哲学当作哲学方法或哲学变革”观点的批判。行文至此,不得不强调,笔者所要批评的并非跨学科研究本身,而是被作为学术发展方向提出的“实验哲学”口号。如果仅仅是某一学科所研究的问题,“跨”到了另一学科的传统领域,但元假设或方法论却依属原学科的,那么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充其量是不同学科的拼接,而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或超越。造成这种软肋的原因可能在于实施交叉的研究者还未能了解所涉及学科的样态与精髓,更缺少对其间差异及其意义的深刻理解。结果那些魔幻般变化出的眼花缭乱的成果,就像不断扩展的“积木”,缺乏内在的联系和逻辑。事实上,无论跨越哪些学科,也无论以何种方式交叉,对于一名严肃而审慎的跨学科学者来说,首先需要做到的是弄清楚自己学科的现状是什么、瓶颈在哪里,以及是否不能被已有学科替 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