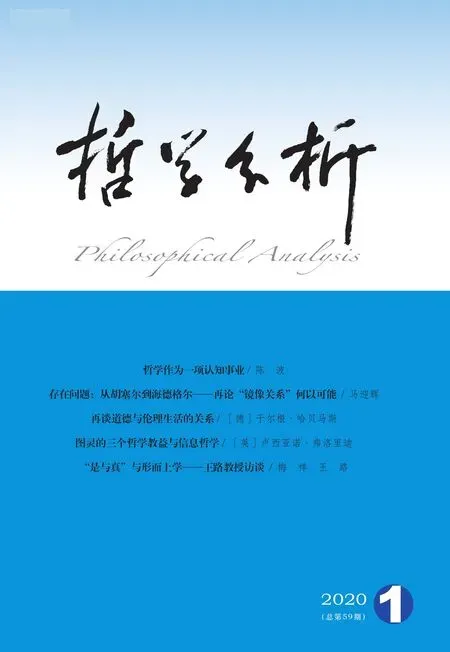韩国性理学对黄榦人心道心说的批判
邓庆平
众所周知,人心、道心作为道学讨论的重要概念,其原出于《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此,朱子有非常详细丰富的讨论,他最重要的弟子黄榦(字直卿,号勉斋,1152—1221)在讨论心性论问题时的一个亮点就集中于人心道心问题。真德秀在《西山读书记》卷三《心》中抄录了勉斋黄榦与李道传、李方子之间讨论人心道心问题的几段书信材料,这些材料不见于现存《勉斋文集》,但这些书信展示的只是勉斋讨论的一部分。现存《勉斋文集》中保留了一些真德秀未抄录的勉斋相关讨论的书信,展示的是勉斋讨论的后续部分。对于勉斋与友人围绕人心道心展开的讨论,有学者曾予以关注①王宇:《人心道心之辨与后朱熹时代朱子学方法的奠定》,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但可惜的是其所见材料仅为真德秀所抄录部分,而不见于《勉斋文集》中的部分。就勉斋思想在后世的影响来说,《勉斋文集》所保留的后续辩论材料非常重要,曾在韩国性理学当中引起重要反响。本文就侧重于这一后续讨论及其引发的韩国性理学家们的批判意见,于此既显示出当时朱子学派内部在性情论问题上的理解差异,同时也展示了韩国性理学讨论相关问题的深入程度,更具体地揭示出人心道心问题的复杂 性。
一
现存《勉斋文集》收录了黄榦的一封书信即《复李公晦书》,黄榦在信中明确提出:
来教谓喜怒哀乐属于人心为未当,必欲以由声色臭味而喜怒哀乐者为人心,由仁义礼智而喜怒哀乐者为道心,以经文义理考之,窃恐不然。……发于此身者,则如喜怒哀乐是也;发于此理者,则仁义礼智是也。若必谓兼喜怒哀乐而为道心,则理与气混然而无别矣。故以喜怒哀乐为人心者,以其发于形气之私也;以仁义礼智为道心者,以其原于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对而言,犹《易》之言器与道,《孟子》之言气与义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复微而难明,故当精以察之,则喜怒哀乐之闲皆见其有当然之则,又当一以守之,使之无一念而不合乎当然之则,然后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①《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602页。下引该书均为此版本。
李方子,字公晦,朱熹重要门人。他以为不能统言喜怒哀乐即人心,应该是由声色臭味而发的喜怒哀乐为人心,由仁义礼智而发的喜怒哀乐为道心。黄榦在信中对李方子的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人心之人是指身,道心之道是指理,发于身者喜怒哀乐等,发于理者则仁义礼智。若一定要说喜怒哀乐是道心,那就是理与气混淆而无分别。故以喜怒哀乐为人心,是因其发于形气之私;而以仁义礼智为道心,是因其原于性命之正。人心道心是相对而言,就如同易之器与道,孟子之气与义。人心既危而易陷入其中,道心隐微难明,因此要精以察之,在喜怒哀乐当中见其当然之则,然后一以守之,使得每一念头都合乎当然之则,然后信守之而不失 去。
在此信中,黄榦坚持以仁义礼智作为标准对危殆的人心进行严格精密的审查与对治,这样的态度无疑是标准的道学立场。黄榦侧重从人心、道心的概念构成上来解释问题,这是黄榦“看文字”的一种常用技巧。他将“人心”之“人”理解为“身”,道心之道理解为理,而人心乃是身之发,道心便是理之发。这种解释是有渊源的。朱子曾曰:“道心是义理上发出来底,人心是人身上发出来底。是圣人不能无人心,如饮食、渴饮之类;虽小人不能无道心,如恻隐之心是也。”②《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11页。这里也把人心理解为人身上所发,而道心为义理所发,但朱子认为人心乃是饮食渴饮之类,道心则是恻隐之心,而黄榦则把身之发解为喜怒哀乐,理之发解为仁义礼智。喜怒哀乐之发总是以耳目口鼻等身体器官相关,这里的身之发为喜怒哀乐好理解;但理之发为仁义礼智,此发具有两层意思,一是仁包四德意义上的逻辑上的蕴涵,二是现实意义上的由未发之理而成为已发之四端之心;这两种理解在理学体系当中都是被认可的。如果从理论内涵来说,黄榦的这个人心道心观具有更强的概况力,不仅涵盖了未发已发的论域,还蕴含了道与四德之间的关系问 题。
就道心为性的讲法,在《朱子语类》中也有相关的两条材料,一条即是黄榦所言,即“直卿云:‘不谓性命’章,两‘性’字,两‘ 命’字,都不同。上面‘性’字是人心;下面‘性’字是道心。上面‘命’字是气,论贫富贵贱;下面‘命’ 字是理,论智愚贤不肖。学蒙”①《朱子语类》卷六十一,第1462页。。另一条为李方子录朱子之语:“‘性也,有命焉’,此性是气禀之性,命则是限制人心者,‘命也,有性焉’,此命是气禀有清浊,性则是道心者。”②同上。此外,朱熹另一重要弟子陈淳也有类似的观点:“人之所以贵于物者,以其有道心,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是也。”③《与黄寅仲》,《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45页。明代中期最重要的朱子学者罗钦顺也明确提出与黄榦类似的观点:“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④《困知记全译》,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版,240页。道心与人心乃是性与情的关系,有动静之分与体用之别,这与黄榦的理解大体一致。冯友兰在解释朱熹哲学时,也认为“性为天理,即所谓道心也”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这里都将道心理解为 性。
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按朱子一般的观念,喜怒哀乐为情,仁义礼智为性。在《朱子语类》当中有不少将道心理解为四端之心而非性的讲法,如“饥寒痛痒,此人心也;恻隐、羞恶、是非、辞逊,此道心也”⑥《朱子语类》卷六十二,第1487页。。朱子明确将四端视为道心,而四端是已发,这样道心便不能是未发之性。如此一来,黄榦以道心为仁义礼智之性的观点就与朱子的这一类观点存在差异。这一差异在后来为韩国性理学者所注 意。
二
朝鲜时期,性理学者都具有强烈的朱子学立场,朱熹的语境成为判定学术争议的最高权威,且伴随着对四端七情的长期论争,人心道心、未发已发、性与情等概念得到充分讨论与细致辨析,其中李退溪(1501—1570)认为“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非有两个道理”①李滉:《答李宏仲问目》,《退溪先生文集》卷三十六,《韩国文集丛刊》 (第30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310页。的观点影响巨大。黄榦以喜怒哀乐为人心、仁义礼智为道心的观点在朝鲜时期就受到性理学者的较多批评,其中权尚夏(1641—1721,号遂庵)及其弟子韩元震(1682—1751,号南塘)都撰有专文。
权尚夏是韩国性理学史上第一个专文讨论勉斋思想的学者。他所作《勉斋集辨》②权尚夏:《勉斋集辨》,《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杂著》,《韩国文集丛刊》 (第150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386页。下引该文不再标注。虽然不到三百字,但观点清晰。他首先就提出自己关于人心道心的看法:无论是发于形气之私还是性命之正,皆有喜怒哀乐之情。在这里喜怒哀乐本身是中性的概念,因其所发不同而分属于人心与道心。而黄榦认为发于身的才是喜怒哀乐,发于理的不是喜怒哀乐,不可谓之七情。对此,权尚夏提出三点批 评:
其一,“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是人心也。今以发于耳目口鼻者为人心,发于声色臭味者,不可谓人心,亦未可晓也”。这里的分歧在于对“发”的理解上。黄榦所谓的发于声色臭味,是指声色臭味乃是发之主体,喜怒哀乐是其所发,这自然不通,应该是耳目口鼻所发为人心。而权尚夏则认为人心是耳之对声,目之对色,鼻之对臭,口之对味的感知,这种感知即是人心。权尚夏这里“发于声色臭味”是指因声色臭味而引发,即声色臭味是发的诱因。
其二,“圣人之于声色臭味,事事中节而已,今曰圣人未免于逐物,亦不可晓”。圣人同样也会遭遇外界的声色臭味,也会因之而发心,但圣人之发心乃事事中节。这种“发”被黄榦以为是逐物,而权尚夏并不认同。
其三,“以人心道心,拟之于易之器与道,亦甚不然。”对于黄榦的这个类比,权尚夏也不认同。就朱子本意,道心人心应该都是属于人的意识范围,应该没有形上与形下之区分。黄榦这样的比拟意在突出道心对人心的基础意义,但若将人心道心比作器与道,则有形下与形上之分,这个比喻应该说是有问题 的。
三
权尚夏主要是就黄榦论证过程中的观点提出质疑,但并未详细讨论。其主要弟子韩元震在老师的基础之上,作成长篇专文《黄勉斋性情说辨》③韩元震:《黃勉斋性情说辨》,《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杂著》,《韩国文集丛刊》第202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74—75页。下引该文不再标注。对黄榦答李公晦书信中的言论一一进行详细辩驳。该文不仅详细辩驳了勉斋的性情观,而且还涉及对勉斋之学的一些重要认识,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代表了韩国性理学者对勉斋之学的最高研究水 平。
为讨论方面,下面将该文分为几段一一分 析:
勉斋答李公晦书,深非喜怒哀乐由声色臭味而发者为人心,由仁义礼智而发者为道心之说。李说本自无病,攻之殊不可晓,况其为说,又多可 骇。
韩元震一上来就直接亮明自己的态度,认为李公晦之说本没错,勉斋“攻之者殊不可晓”。其实正如本文前面所分析的,勉斋的批判乃有一整套论证思 路。
南塘为证明勉斋之说有“多可骇”,首先提出自己对于未发已发的理 解:
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朱子解之曰:“喜怒哀乐情也,未发则性也。”然则喜怒哀乐之情未发者为仁义礼智之性,仁义礼智之性已发者为喜怒哀乐之情。大本达道,一理相贯,而人心体用,尽于是矣。盖五性之外无他性,七情之外无他情故 也。
韩元震认为,未发为性,即仁义礼智信五性;已发为情,即喜怒哀乐等七情;五性之外无他性,七情之外无他情;性情的关系即未发与已发的关系。接着,他对人心道心作出解 释:
所谓人心道心者,以其喜怒哀乐之感于食色而发者谓之人心,以其感于道义而发者谓之道心。何为而有感于食色而发也,以其有耳目鼻口之形,具于身故也。何为而有感于道义而发也,以其有仁义礼智之理,根于心故也。故曰生于形气而有人心,原于性命而有道心也,非谓人心七情不本于仁义礼智,而道心却在喜怒哀乐之外 也。
人心道心都是已发,都属于七情。人心乃是感于食色而发出来的七情,其根源在于耳目鼻口之形,道心乃是感于道义而发出来的七情,其根源在于仁义礼智之理。因此,并非人心之七情不本于仁义礼智,也并非道心在七情之 外。
上述未发已发观与人心道心观便是南塘性情论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他对黄榦以喜怒哀乐为人心、以仁义礼智为道心的观点展开批评,指出黄榦的观点将导致一系列错 误:
今曰:“以喜怒哀乐为人心者,以其发于形气之私也;以仁义礼智为道心者,以其原于性命之正也。”如此则喜怒哀乐不原于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不发为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无理以为本,仁义礼智,无情以为用;而大本达道分为二致矣。七情,总举人情之目;人心,偏指食色之情;而今以七情专属于人心,则是又以人心侵过食色之外矣。仁义礼智性也,人心道心情也,而今直以仁义礼智为道心,而曰原于性命,则是又昧于性情之分,而仁义礼智之上,又有性命矣。七情之发而中节者为道心,而今以道心为在七情之外,则七情之外,实无他情,而道心终无发见之地矣。人心不原于性命,而道心不在于七情,则是又人心无与于大本,而道心无与于达道 矣。
南塘推导出勉斋的错误有:(1)将喜怒哀乐与仁义礼智完全割裂开来,势必导致喜怒哀乐没有以仁义礼智为根本,仁义礼智也不会发为喜怒哀乐,人心与道心完全割裂。(2)七情乃是人情之具体种类,而人心乃是偏指其中食色之情,勉斋将七情等于人心,这样人心概念的外延就出现不当拓展,以包括食色之情以外其他种类的情。(3)人心道心皆是情,仁义礼智乃是性,勉斋以仁义礼智为道心,势必性情混淆;而且道心原于性命,这样仁义礼智之上势必还有性。(4)道心本是七情当中发而中节的那部分情,而勉斋以道心在七情之外,但七情之外并无他情,这样道心势必没有发见处。(5)人心不原于性命,道心不在七情之中,那么人心与大本没有关系,道心与达道也没有关系。
接着,对于黄榦在信中的论证过程,韩元震也一一进行有针对性的驳 斥:
又曰:“人心道心,相对而言,犹易之言道与气,孟子之言气与义也。”如此则言人心而遗理,言道心而遗气,从人心道心之分者而言,则理气分开,各自有用而不相交涉也。从道器理气之合者而言,则人心道心,发必俱发而不得相舍也,二者无一可 矣。
这里是对黄榦用易之言道与气、孟子之言气与义来类比人心与道心的观点进行驳斥。如勉斋所言,则无论是就人心道心之分而言,还是就道器理气之合而言,或者人心道心各自有用不相交涉,或者人心道心必须同时一并发出,这都是说不通 的。
其破李说,则曰:“人心发于形气之私,形气在我,如耳目鼻口是也,声色臭味在物,岂得以发于声色臭味者为人心乎。”夫谓人心发于形气之私者,谓其有耳目鼻口之私,故食色之心,因是而发也云尔,非谓耳目鼻口自发得知觉之情也。耳目鼻口,是不思之物,则固不能自发得情,而又无耳目鼻口之视听啖嗅者,则食色之心,何从而生乎。故谓之人心发于形气,然则李所谓人心由声色臭味而发者,亦谓由声色臭味之感而有人心云尔,非谓人心直就在物之声色臭味上发出也,今乃反其意而攻之,则其果服李之心 耶。
韩元震这里对“人心发于形气之私”提出正解,认为食色之心是由声色臭味之感而有人心,并非如勉斋所理解的是直接在物之声色臭味上发出来,因此,勉斋对李公晦的这个批评是不成立 的。
又曰:“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今以由声色臭味而喜怒哀乐,则是圣人未免于逐物也。”夫人情之发,莫不由于外感,则声色臭味感于外,而食色之心发于内者,又安有逐物之嫌乎。若以是而为逐物,则恻隐之心,因孺子入井而发者,亦将以为逐物耶。盖其以李所谓由声色臭味而发者,为即声色臭味而发者,则自所谓人心七情发于形气者,亦为即形气而发。此情与性命而分对出来也,此其所见根本之错,而无处不错 也。
黄榦也承认圣人有人心,但若人心是在外物上发,则圣人逐于外物,这是黄榦的质疑。而韩元震认为人情皆由声色臭味这些外在诱因而发,但其食色之心乃是发于意识范围之内,并非有外在诱因就一定会逐于外物。若由外因而发便是逐于外物,那么因外在的孺子入井而发于内心的恻隐之心,难道也是逐于外物吗?韩元震通过这个反问,进一步证明李公晦所谓由声色臭味而发乃是即声色臭味而发的意思,所谓人心七情发于形气者也是即形气而发的意思,这本是情与性相对而发见出来。勉斋之错根源在 此。
又曰:“由仁义礼智而喜怒哀乐者为道心,则《乡党》一篇委蛇曲折,焕乎其文章,莫非由仁义礼智而发也,曷为而以道心为惟微乎。”夫《乡党》一篇所记,莫非天理流行,则此非道心而何,此非仁义礼智之发而何?其记饮食衣服动静起居之节,无不中理者,即栗谷所谓人心即道心者也。夫孰非仁义礼智之发见也,人心虽本危动,道心虽本微妙,在夫子盛德至善,动容中礼者,则固若是其安且著矣。所谓危者安、微者著者也,恶可以其著而谓非道心乎。若以其著而谓非道心,则孟子所谓仁义之端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果是虚张诳人之说耶。圣人之动容中礼,焕乎其文章者,亦全在于人心,而道心一任其微昧耶。朱子答黄子耕书曰:“盖以道心为主,则人心亦化而为道心矣。”如《乡党》所记饮食衣服,本是人心之发,然在圣人分上则浑是道心 也。
勉斋以《乡党》篇圣人显著的饮食、衣服、动静与起居之表现与“惟微”的道心不合,因而反对道心亦可以表现为外显喜怒哀乐之情的观点。韩元震认为《乡党》篇所载圣人表现就是道心,正是仁义礼智之性所发,并引朱子与黄子耕书信中人心亦可化为道心的观点,应该说是正中勉斋的疏忽之 处。
又曰:“若兼喜怒哀乐而为道心,则理与气混而无别矣。”夫理气虽曰有别,而实无分开各行之时,况七情道心,只是一情,则又安得论理气之别乎。若必以七情道心为二情然后,方免于理气之无别,则子思之以喜怒哀乐为达道者,亦将归于混理气而无别耶,抑书之道心。《中庸》之达道,其名物色相,亦有不同者 耶。
若道心兼喜怒哀乐,则如将理气混而无别,勉斋这里的逻辑本是以道心与喜怒哀乐分类比理气关系而分属不同范畴。韩元震则指出,道心与喜怒哀乐等七情都是情,道心与七情的关系和理与气的关系并不相同。如果一定要认为七情和道心是两种情,这样才可避免理气相混的话,那么子思所谓喜怒哀乐皆中节而为达道的讲法,也是将理气相混的讲法,“道心”与“达道”完全不同吗?至此,韩元震对勉斋信中的论证过程作了异常详尽的一一反 驳。
接着,韩元震对勉斋《复李公晦书》中表达的性情观进行了总结,他总结出五个谬 误:
大抵一书中所论种种丑差,不胜爬栉。提撮其要而言,则以人心道心分道器,一误也;以喜怒哀乐为不发于仁义礼智,二误也;以七情之总人情者专属人心,三误也;以仁义礼智之性直为道心,四误也;以道心为在七情之外者,五误也;此皆系义理之大原,关问学之极致,而一切迷错如此,则其于道也,不啻重关复岭之隔矣。如是而犹承朱子之嫡传者,诚有可 疑。
总体来看,韩元震的反驳异常详尽有力,其所总结的五点也是可以成立。更为难得的是,韩元震对勉斋之学的认知不止于此,他敏锐地发现,勉斋此信中的观点乃是其早年思想,到后来勉斋自己对此有所反 省:
然细考之,此其初年之见,而非为一生定论也欤。其《答胡伯量书》曰:“人心道心,恐如契兄所云者为是,李所云人心气也,余所谓性之正者,皆未精确。”人心气也者,即与前所论人心为易之器孟子之气者同一说也。所谓性之正者,亦似是指前日之论以道心为性发而不干于气,又以仁义礼智直谓道心而不分其性情者也。据前说以人心道心分道器,则其必不以此说为非。而今其所驳人与自驳者如此,则其改正前见之误者必矣。夫既改正人心道心分道器之误,则其他七情专属人心等一般说话,亦必在所一例改正 矣。
这里提到勉斋答胡伯量书中对李公晦与自己观点的反省,“皆未精确”①可参见《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六,第597页。。由此,韩元震在性理学的概念体系当中,推测勉斋必定改过前见之误,完全推翻前 见。
最后,韩元震对勉斋之学作了一个整体上的评 价:
盖观勉斋之学,专以苦思得之。故其于朱子说,始疑而卒服之者多矣,非独此一说也。如《洪范》五行说,《论语》浴沂章说,皆系造化之源道体之妙,而始皆深疑朱子说,费辞多辨,卒皆以朱子说为正而弃其旧见,岂非所思益深,所见益精而然耶。昔之疑之也非强异,则后之从之也非苟同,而必有洒然融释者矣。然则朱子之传之道,勉斋之受其传者,夫岂有可间者哉。勉斋全集,前不东来。顷年权副使尙游之自燕还,始行于东方。
信中提到《勉斋文集》传入韩国比较晚的事实。②完整的《勉斋文集》传入韩国应该是在1713年,参见拙著《朱子门人与朱子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17页。韩元震还以黄榦早晚思想变化的两个例子——洪范五行说与《论语》“浴沂”章说,以证明“盖观勉斋之学,专以苦思得之。故其于朱子说,始疑而卒服之者多矣。”勉斋之学专以苦思得之,这是合乎事实的。但对于洪范五行说,黄榦之疑主要针对朱子的两种五行次序说而言,其最终思想如韩震所论回归朱子,但这最后的回归朱子也并非完全信服朱子。③可参考王小珍、邓庆平:《黄榦〈太极图说〉解》,载《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关于《论语》“浴沂”章说,黄榦存在一定的思想变化,而且黄榦早年之疑并非没有价值,这一质疑直接促使朱子对《论语集注》该章进行修 改。
再回到韩元震对勉斋人心道心观的推测,事实是否如其所推测的回归朱子,我们需要结合勉斋《答胡伯量书》来看。该信指 出:
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说恐如契兄所云者为是,李所谓人心气也,余所谓性之正者,皆未精确也。道体之说此更宜讲究,谓但指隐而言者,岂所以为道体之全耶。体字不可以体用言,如今所谓国体治体文体字体,亦曷尝对用而言耶。所谓道体者,无物不在,无时不然,流行发用,无少间断。如曾 者,真是见得此理,然后从容自得,有以自乐。今之局促迫狭,寻行数墨辄拘碍者,岂亦于此有未洒然者邪?主敬、致知两事,相为经纬,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见者,恐亦于此有所未思耳。④《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六,第597—598页。
胡泳字伯量,南康人,朱子重要门人,与黄榦交往密切。这里的李应是李公晦。就信中语意,李所谓人心气也,指向的是李公晦所言人心观,“余所谓性之正者”,应是指向自己所持道心观。李公晦以为人心发于形气之私故皆为恶,这点黄榦已经有过批评。而对于自己的道心观这里仅说不够精确,具体内涵却没有明言。虽然黄榦认同胡泳的人心道心观,但胡伯量的信件现在不可见,我们只能从《朱子语类》当中大略推测胡伯量的立 场:
问:“先生答余国秀云:‘须理会得其性情之德。’”曰:“须知那个是仁义礼智之性,那个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始得。”胡泳。①《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第2909—2910页。
问:“心存时也有邪处。”曰:“如何?”泳曰:“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谓‘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个无拣择底心,道心是个有拣择底心。佛氏也不可谓之邪,只是个无拣择底心。到心存时,已无大段不是处了。”胡泳。②《朱子语类》卷十二,第220页。
这里将仁义礼智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四端分别为性与情,又把道心视为具有道德判断功能的道德意识。这与朱子将道心视为四端的讲法是一致的。从胡泳所接受的性情观来看,黄榦以所谓道心为仁义礼智之性的讲法应该是受批评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受胡泳的影响,黄榦最终将道心为性的讲法修改为道心为四端是可能的。这点从黄榦此信中对道体的反省也可以印证。他的反省并未从已发未发、性情问题开始,而是从对道体之隐的思考开始的。之所以从道体开始,勉斋并未明言,但就其常用概念拆分方法来看文字的为学方法,“道心”概念自然包括“道”与“心”两部分,对“道”的认识最为关键,“心”则与发相关,因此,他对道心的理解思路还是从道之发来理解,所谓道体便是道与发的合体。他认为道体之隐并非道体之全部性质,此处体字并非体用相对而言当中的体,乃如国体治体文体字体之体,是类型、体裁的意思。所谓道体之全并非仅指隐而言,应是既内在隐微又外向显著,遍及一切事物与场合,具有时空上的普遍性。勉斋这里反省的实质是对自己前见当中以为道心的特征只能是隐微这一点有更进一步理解,故其将自己的失误归结为“今之局促迫狭,寻行数墨辄拘碍者”,即过于拘泥于文字,这里所指应是“道心惟微”这句话。由此可见,勉斋这里还是将道心与道体紧密联系,这与勉斋一贯重视道体认知的为学特点是一致的,而与韩元震在韩国性理学长期四端七情、性情论争的历史当中所熏陶发展起来重视概念辨析的反驳思路还是存在一定差 异。
因此,黄榦最终关于人心道心的理解可能是,喜怒哀乐为人心,四端为道心。黄榦最终有可能如韩元震所推测的那样改变自己的观点即“夫既改正人心道心分道器之误,则其他七情专属人心等一般说话,亦必在所一例改正矣”。但关于未发已发、四端与七情的关系等心性论的其他问题,我们并不能就此判定黄榦最后的定见如何,是否会与韩元震的观点一致。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黄榦对性、对未发的理解与朱熹没有太多差异,对于已发之恶也有关注,但他对情、对已发的理解则侧重于四端,对四端与七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讨论。
关于未发向已发转化,黄榦最终还是坚持两种发动机制的观 点:
其为说则心之所发,必乘于形气,抑不思《中庸序》之言曰“或发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则不皆乘于形气矣。惟其以为皆乘于形气,所以合人心道心而为一也。①《舜禹传心周程言性二图辨寄黄子洪》,《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六,第14页。
此信作于1221年黄榦去世前不久。对黄士毅(子洪)所作《舜禹心传之图》中将人心道心合为一,黄榦提出质疑。在这里,黄榦批评黄子洪以为心之所发皆乘于形气的看法,并引《中庸序》的原话来论证心之所发的机制“不皆乘于形气”。可以看出,黄榦在晚年最终坚持对人心、道心的发生机制依然坚持两种发动机制的观点。这一观点在韩国性理学的四端七请论争中发挥了重要影 响。
心在道学领域通常既代表修养工夫的主体,也代表修养工夫的对象,还会用来描述修养之后的境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作为工夫主体的心,侧重的是其功能与本性,因此与性有密切关系;作为对象的心往往是具有危殆属性的现实人心,而道心则一方面可以作为修养工夫的主体而属于未发,另一方面又将作为修养工夫之后的境界而属于已发。对于朱子而言,对人心道心的解读有两种模式,一将人心道心视为理气式的理气论解读,侧重的是作为工夫主体的道心,道心是性,而人心是情,这样的解读强调了道心作为修养工夫主体的一面,将道心与性合一,但未能将性与性之端倪区分;另一种是将人心道心视为已发状态的心性论解读,侧重于将道心视为修养工夫的境界即作为已发的情,这样的理解将性与性之端倪区分开来,将道心理解为性之端倪,这在对未发已发之“发”的概念使用上更具一致性。黄榦关于人心道心的辨析及其引起的后来包括韩国性理学家在内的学者的讨论给我们清楚地显示出这两种解读模式之间的理论差 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