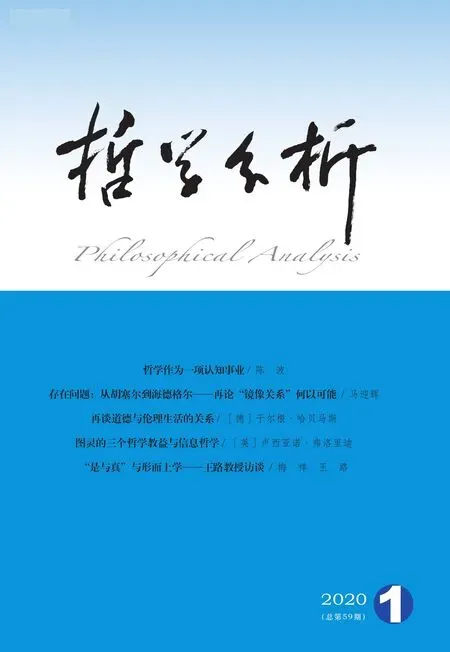“是与真”与形而上学
——王路教授访谈①
梅 祥 王 路
一、关于几本书
梅:在2003年出版《“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之后,您于2007年出版了《逻辑与哲学》。您在该书序中说,有关being的研究可以暂告一个段落。该书最后一章的题目是“真与是”,似乎恰好与《是与真》一书相呼应,也显示出该项研究大致完成的意思。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我看到您后来又写出《读不懂的西方哲学》 (2011年),《解读〈存在与时间〉》 (2012年),以及《一“是”到底论》 (2017年)。这是为什么 呢?
王:“是与真”这个问题是我考虑了许多年的问题。我在中国社科院的时候,一些朋友对being问题感兴趣,每周二见面的时候我常给他们讲being问题。每次谈的时候他们都很清楚,回去之后又不清楚了。后来他们说,你干脆把它写下来吧。《是与真》写完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发表是在2003年我到清华以后。这本书主要是从语言层面对“是与真”进行讨论。你把being看作外文当中的一个词,翻译成中文的时候首先你得把它翻译成一个词,这个词要表达它本身所包含的许多思想。我当时提出要把它翻译成“是”,主要是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它,并且觉得应该把这种理解贯彻始终。这是一个基本观点。那本书在语言层面上对being谈得比较多,并且从这个角度讲了很多人的相关思想。这本书写完后,我觉得“是与真”这个问题仅仅从语言层面上来谈还不够,还应该从学科上来谈。所以后来我在清华申请了一个项目“逻辑与哲学”,谈的还是“是与真”,但是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谈。我认为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是being,但是西方哲学的基础或者它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是逻辑。逻辑中所说的“S是P”的那个“是”,being,是个常项。所以,being不仅是哲学的基本概念,也是逻辑的基本概念。两者在字面上是相通的,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与逻辑这两门学科是相通的。我当时认为,这样就从语言层面和学科层面把“是与真”谈清楚了,而且我当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给国内一些搞西方哲学的朋友们提供一个思考的视角,所以我在2007年出版的《逻辑与哲学》中讲“这个研究可以告一段落了”。这两本书出来以后,我听有人说,“王路是搞逻辑的,他不懂”。我确实看到一些人在文章中或明或暗地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是”这个翻译反映了一种逻辑主义的理解,与“存在”的哲学理解是相悖的。在他们看来,“存在”是哲学的理解,“是”是逻辑的理解。我当然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得继续讨论。于是我又写了《读不懂的西方哲学》 《解读〈存在与时间〉》,明确地指出从“存在”理解来being是有问题的,直到2017年出版了《一“是”到底 论》。
梅:我发现,您在《是与真》中提到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在《逻辑与哲学》中专门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在后来的著作中,您虽然也谈到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似乎都不如前两部著作那么强调。这是为什么 呢?
王:本来我认为谈“是与真”一定要把哲学与逻辑结合起来,一般而言,人们说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逻辑分析,可是到具体分析的时候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在我的观点出来之后,有的人说你把being理解为“是”,你是一种逻辑的考虑。有人甚至认为你这里有一种倾向,就是要把形而上学的考虑给割裂出去。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怎么办呢?那就不谈逻辑吧。我的意思是说,即使不谈逻辑,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西方人谈论的being是“是”,而不是“存在”;西方谈论的truth是“真”而不是“真理”。但是这样一来,就要做文本分析的工作。我不得不说明,being翻译成“存在”,现有译文是读不懂的;我将它修正为“是”,文本就好读了,就容易懂了。这样也就避开谈论逻辑,没必要非得强调逻辑,但结果还是一样的。being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系词意义上的东西。谈逻辑能帮助你理解它,不谈逻辑理解起来也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不谈逻辑并不意味着里面没有逻辑。即使不谈逻辑,我们仍然能看到“being”表达的东西就是“是怎样”的东西,与它对应的词就是“是”。
梅:《是与真》从巴门尼德谈到海德格尔,谈到许多人,唯独没有谈柏拉图。《逻辑与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维特根斯坦,您又谈论了许多人,但是最后专门用一章谈论柏拉图。这样的讨论方式我觉得有些奇怪。这两本书的人物思想都是按照历史顺序谈的,唯独对柏拉图不是这样——一本没有谈,另一本放在最后。后来在《读不懂的西方哲学》中就正常了——您把柏拉图列为第一章。请问您这样做是随意的还是有意的?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呢?
王:顺序不一致肯定是有问题的。我最早读柏拉图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因为要做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后来我研究弗雷格之后,就把柏拉图放下了。再后来作“是与真”研究,我又重新读柏拉图。对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研究是不能写的。
梅:您说的“足够”是什么意 思?
王:我指的主要是我对二手文献研究得不够。谈论“是与真”当然会涉及柏拉图,但是他在许多著作都讨论了being,比如《理想国》 《智者篇》 《泰阿泰德篇》 《巴门尼德篇》,等等。换句话说,选点很难。所以一开始我回避了柏拉图。巴门尼德就比较好谈,因为他残篇内容集中,而且他的论题非常出名。谈论being问题可以不谈柏拉图,但一定要谈巴门尼德。所以一开始我没有谈柏拉图。后来我觉得我对他的晚期著作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和研究以后,也就可以写他了。《逻辑与哲学》有两稿,第一稿没有写柏拉图,后来加了这一章。因为我认为,把柏拉图加上去会对我们思考逻辑与哲学有帮助。柏拉图的讨论肯定都是哲学的讨论,因为他那里还没有产生逻辑。假如柏拉图的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没有任何联系的话,柏拉图的思想就是孤零零的东西,这对于逻辑的产生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有思想来源的。它不是花果山上的石猴,不是凭空蹦出来的,它的思想来源一定是柏拉 图。
梅:为什么不会是其他人 呢?
王:也许其他人那里也有它的思想来源,但是我们看不到,因为没有文本,我们只看到柏拉图的对话。从柏拉图的对话可以看到,比如《泰阿泰德篇》,他那里是没有逻辑的,但是有与逻辑相关的考虑,我们可以把这些考虑看作具有逻辑倾向性的考虑。比如他关于“是”“不是”“真”“假”的考虑与亚里士多德形成逻辑的考虑是相关的。如果这样去理解柏拉图著作,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视角。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前面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要把这部分内容加到前面,后面就得重新写,整个体系就都打乱了。于是我就“偷了个懒”,在全书不做改动的情况下,把它放到最后一章。到了写《读不懂的西方哲学》的时候,我对柏拉图有了许多研究,这时候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把柏拉图的东西放到第一章去谈。最近我还写了一本书,叫《逻辑的起源》,不只是谈论《泰阿泰德篇》,我主要谈的是《智者篇》,以《智者篇》为文本谈论“是”,谈论柏拉图的相关思想。当然,这是后来的工 作。
二、关于“是”与“真”的问题
梅:在《是与真》的导论中,您提到了关于being和truth的翻译错误的问题,您提出正是因为错误的翻译导致我们难以读懂西方哲学。之后您又单独写了一本《读不懂的西方哲学》来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发现在《读不懂的西方哲学》中您只谈了关于把being错译为“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再谈把truth错译成“真理”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王:你是对的,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第一次谈being是在1992年,我写了一篇论文《论“是”的逻辑研究》,在那里我谈了being有多种含义,也有一种“存在”的含义,而且我谈到being要与“真”联系起来。1996年,我发表了《论“真”与“真理”》这篇文章,明确谈到把“truth”翻译成“真理”错了,应该把它翻译成为“真”。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谈了应该把“真”与“是”的理解和研究联系起来。那时我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以为being难谈,truth好谈。所以要先谈truth,然后谈being。现在truth谈完了,所以可以开始谈being了——因为从传统哲学来看,being问题的影响太大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其实being的问题好谈,而truth的问题难谈。因为being可以是一个句法概念,我们可以从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很多支持,比如关于系词的论述,关于举例的说明,比如“风是冷的”“天是蓝的”;还有很多跟逻辑的联系,比如being是一个逻辑常项。所以从句法的角度来理解being,我们至少可以找到许多西方哲学家提供的支持论证。我认识到,being好像难谈,实际上却好谈,而truth却不是那么好谈。truth是语义概念,人们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带有对它的理解。当人们把它当作一个对象来谈的时候,它的基本意思就是“it is true”,这是在一种语义的角度上说的。那么如何对这个语义概念进行理解,这反而成为了一个问题。最近我又开始谈这个问题,这你是知道的。①参见王路:《为什么是“真”而不是“真理”》,载《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为什么要区别真与真理——回应邓晓芒教授的批评》,载《河北学刊》2018年第2期;《再论真与真理》,载《求是学刊》2018年第3期;《真、真理与真相 》,载《湖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是”与“真”这两个概念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因为being可以从句法角度理解,而truth无法从句法角度来理解,只能从语义来理解。所以谈论它们的时候既要把它们联系起来考虑,又要把它们区别开来。通过讨论语言哲学,我们有个明确的认识:就是现代逻辑使得真这个概念得到凸显,用波普尔的话说,由于塔尔斯基的工作,我们敢谈“真”了。应该看到,弗雷格的逻辑使得我们可以从句法的角度,比如他说的那个函数结构来探讨问题,但是他的这种函数结构却是基于真来考虑的。比如弗雷格说“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概念是一个其值总是一个真值的函数”,“句子的意谓是真值”,等等,以及其他许多这样的论述。人们可以从真的角度去谈句子的含义。因此我们认识到真是一个语义概念。在传统哲学中,being确实谈得多。当然关于“真”这个概念的讨论也有,它依然是一个语义概念,但往往是按照常识性的理解来谈论的。比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说是者是,就是真的;说是者不是,就是假的。康德说的,真乃是认识与对象的符合。这些都是常识性的认 识。
梅:您的意思是说把being译为“存在”和把truth译为“真理”都有问题,但是前一个问题更明显,影响更大 吗?
王:其实都是很大的问题,但是从文献上说,我们会感到把being翻译成“存在”问题更大一 些。
梅:为什 么?
王:因为being是一个核心概念,在整个西方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讨论中,它一直是一个核心概念。因为它是一个句法概念,人们可以在句法的意义上讨论它,它到处出现。反过来,你看在西方哲学中人们也会谈真,但是谈论真却不是贯彻始终的,不是连篇累牍的,给人感觉好像是时隐时现的。如果说把being翻译成“存在”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或认识,把truth翻译成“真理”也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或认识的话,那么当然前一种错误比后一种错误的影响要大。比如我们把海德格尔的Sein und Zeit翻译成《存在与时间》;把亚里士多德说的“有一门科学,它研究being qua being”翻译成“有一门科学,它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把笛卡尔的名言cogito ergo sum翻译成“我思故我在”,等等。虽然把being错译为“存在”比把truth错译为“真理”的影响更大,但是我觉得实质是一样的,因为being与truth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谈同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西方哲学家在谈认识的时候,谈being和谈truth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角度不同而 已。
梅:我的博士论文与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有关,所以我对真这个概念有比较多的认识和理解。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应该将truth译为“真”,而不是译为“真理”。但是我仍然想问,是不是要像坚持一“是”到底论一样,将truth译为“真”,并坚持一“真”到底 呢?
王: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一是到底”是别人的说法,不是我的说法。我的说法是:应该把西方哲学中的being理解为“是”,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并且把这种理解贯彻始终。别人后来把这种观点称为“一是到底论”。“一是到底”,字面上给人的感觉是,凡遇到那个being,都把它翻译为“是”。这就很容易把一个理解的问题变成一个翻译的问题。关于truth这个问题也一样。我认为应该主要在“真”的意义上理解西方人所说truth。为什么?因为truth是is true的名词形式,所以要在“是真的”的意义上理解truth,并且把这样的理解贯彻始终。但是如果把它变成一“真”到底,我觉得就麻烦了。这样就相当于说,凡是看到这样的表达,你都把它翻成“真”。这又把一个关于理解的问题转换成一个关于翻译的问题了。当然问题就比较多。举个例子,特朗普说“people must know the truth”,如果把它翻译成“人民必须知道真”,这就显得荒唐。truth这个词,你把它搁在句子图式①句子图式指一种刻画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图式。它有一个最基础的形式:(语言)句子:谓词 /专名(含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思想的一部分(意谓)真值:概念 / 对象在这个基础形式上可以构造更多的句子图式,句子图式能帮助我们认识到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是不同的。(参见王路:《语言与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三行理解,就是真值;搁在第二行理解,就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了。特朗普说的显然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应该是第二 行。
梅:您的意思是说,哲学讨论与日常表达是有区别的 吗?
王:是的。塔尔斯基的论文②指 的 是A. Tarski,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Formalized Languages”, in Logic, Semantics, Metamathematics,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56。说的是“the concept of truth”,明确地说探讨的是“is true”这个表达式的意思。哲学家在谈truth的时候,有加复数和不加复数的区别。多数情况不加复数,这时候指的是真。比如康德说,truth就是认识与对象相符合。这个truth,放在句子图式中看应该是第三行,或者,你如果把它理解为第三行的话,它显然应该是真。当给truth加复数的时候,这时候指的不是第三行而是第二行的东西,这时候就要考虑它表达的是什么。我的观点是,哲学家们在谈a truth或truths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很多东西,比如可以谈sentence(句子),可以谈proposition(命题),可以谈judgement(判断),可以谈statement(陈述)。在不同的上下文里,可以把truths翻成比如真句子、真命题、真判断等。在没有参照物的时候,把它翻成“真理”也可以。但是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说truth的问题比being要复杂,因为它是个语义的东西,它只能依据理解,没有句法支持,不像being有句法支持。所以我说句子图式是有帮助的。你要把truth理解为第二行的,翻译成“真理”是可以的;而如果理解为第三行的东西,就一定不能翻译为“真理”。也就是说,将truth理解和翻译为“真”还是“真理”,是有根本区别的。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按照我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哲学家们都是在第三行的意义上说的。所以truth不是第二行的东西,不是真理,它是 真。
梅:您能举个例子说一下 吗?
王:好吧。比如“2加2等于4”或“雪是白的”。这句话本身是第一行的东西,我也可以说它是真的。当我谈论它的真的时候,这个“真”应该是第三行东西。这句话还表达了一些东西,无论是什么,都应该是第二行的。因为我说出这句话,我表达了一个意思,你听到我这句话,你理解了这个意思。我们都承认它是真的。这样就有了三个东西。我们可以谈论这个句子,可以谈论它所表达的东西,也可以谈论它的真,或者谈论它所表达的东西的真。对于理解西方哲学家的谈论也是同样。将他们说的truth如果翻译成“真理”,就是将其理解和表达为第二行的东西,如果翻译为“真”,就是理解和表达为第三行的东西。这当然是有区别的,而且是重大的区别。所以哲学中才会有the truth of a proposition 和the proposition of truth 这样不同的表达和关于它们的不同的讨论。前一句谈的是第三行,后一句话谈的是第二行(或也可能是第一行),当然是不同的。刚才说到康德谈论真是认识与对象的符合。我们说从理解的角度你可以把他说的truth解释为第二行东西,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第三行的东西,但这是不一样的。你还可以看到,康德没有我们今天这样关于第三行的认识,所以他的论述并不是那样的清楚。反过来,我们今天区别出第三行和第二行,以此来进行说明,我们可以说得更加清 楚。
三、关于形而上学
梅:在关于“是与真”的研究中,您提到了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奎因、达米特、戴维森等人,我发现他们更多的是研究形而上学或者语言哲学的哲学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经常听到其他一些人被称为哲学家,比如尼采、叔本华、萨特。罗素曾把尼采称为“文艺性哲学家”,认为他对本体论和认识论并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他们在大众中非常受欢迎,我国也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我发现您从来都不谈论他们,这是为什么呢?您对这些哲学家做哲学的方式有什么看法,您赞同罗素的说法 吗?
王:你如果读过我近几年写的一些文章的话,你会发现最近我明确谈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形而上学,一个是加字哲学。加字哲学是我一种谈论形而上学的方式,就是把形而上学与其他哲学区别开来。所以我近年来明确谈论的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学。我认为形而上学与逻辑是相通的,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先验的。而所有加字哲学我认为都是与经验相关的。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点达成共识或者认识到这个区别的话,你可以认识到我谈的这些人都是形而上学家。反过来你说的那些人,我认为他们都不是形而上学家,也许有些人会认为他们是。比如你刚才说的尼采、叔本华、萨特,他们可以谈对生命的体验,谈对理想的追求,谈对上帝的感悟,这些东西都是和经验相关的。所以它们与形而上学的区别很清楚。至于说大众的认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哲学应该是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古希腊是如此,今天也应该如此。柏拉图还说过国家应该由哲学王来管理。这话其实不难理解,因为那时学科没有分化。柏拉图说的哲学王,指的是社会上最有聪明才智的人。哲学发展到今天,很多东西都从哲学分离出去了,才有了我们今天这样的哲学专业。假如今天仍然还把哲学理解为比如像终极关怀、人文精神这样的东西,甚至理解为谈天说地、风花雪月这样的东西,当然你可以把许多人都看作哲学家。但是我不这样看。因为哲学是专业,我喜欢的哲学家是专业哲学家。所以最近这些年我谈论形而上学和加字哲学。我说我们可以有两种对哲学的理解,一种是宽泛的,就是认为哲学涵盖所有加字哲学,一种是狭隘的,就是认为哲学是形而上学。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可以。就我个人而言,我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理解哲学,或者说我研究形而上学,我认为哲学是先验的,所以我不谈刚才你提到的那些哲学家。我绝不反对别人对哲学有宽泛的理解,涵盖加字哲学,但是我认为那样的研究是经验的,是与形而上学不同的,而且持这种看法的人至少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不反对大众喜欢加字哲学家。罗素说的没有什么错,你看“文艺性哲学家”不也是给“哲学”加字了吗?只要一加字,就会与经验相关。加字是可以随意的,但是谈论哲学是不能随意的。或者最保守地说,我们总还是可以以专业哲学家的方式来谈论哲学 吧。
梅:那海德格尔呢?我看到您也经常谈到海德格尔,而且还专门写了《解读〈存在与时间〉》。您在课堂上明确说过,您不喜欢海德格尔,您为什么不喜欢他呢?既然不喜欢,您为什么还要谈论他呢?另外在《是与真》中您谈了许多哲学家,但是谈到海德格尔就结束了,《读不懂的西方哲学》您也是谈到海德格尔就结束了,这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比如为什么不是谈到罗素或者维特根斯坦就结束呢?
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平时一起聊得比较多,所以你知道我是不喜欢海德格尔这个人的。但是你注意了吗,我一般是在谈being的问题时谈他的。在当代哲学家中,海德格尔是非常出名的,而且他出名是以谈being起家的,或者说他是从谈being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由于他名气大,所以他关于being的讨论就非常重要。他的书《存在与时间》,国内读者都知道。所以你谈being问题不谈海德格尔是不行的。为了讨论being问题,我认真读了海德格尔。但是我只读了他早期的东西,比如《是与时》 《论真之本质》 《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等。晚期的东西我大致翻了一下,没有读,我也没有时间去读那样的东西。因为我的目标是谈being,而不是其他东西。虽然海德格尔是个现代人,但他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他讨论问题的方式基于传统逻辑,所以being问题对他很重要。而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这些人是现代逻辑产生以后的分析哲学家。在分析哲学里,being这个概念不重要了,“真”这个概念才是核心概念。所以我们谈being的时候可以不谈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谈“真”这个概念的时候才要谈到这些人。这是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所导致的哲学上的差 异。
就海德格尔而言,我觉得他早期确实是在形而上学传统上展开论述的。比如他的《是与时》一上来就谈being,他说传统关于being的观点可以分为三类。尽管他认为这三类观点都是有问题的,他不同意,但是他仍然把它们归为三类。第一类说being是最普遍的概念,第二类说being是不可定义的概念,第三类说being是自明的概念。在关于自明性的说明中他说,在一切命题中都要用“是”这个词,他还举例“天是蓝色的”来补充说明。他这样的谈论当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是在形而上学这条线上的。所以讨论being问题,海德格尔必须要谈,而且也是可以谈的。不喜欢海德格尔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的哲学是与研究认识相关的。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表达方式,我认为哲学就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由此形成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我们谈的哲学与其他科学有一点很相似的地方,就是它的科学性。这也是我强调的。很多人认为哲学不应该做得那么科学,不应该那么具有科学性。我不这样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们是关于事物的认识。一门科学就是关于某一类事物的认识。哲学与它们不同,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但是就认识这一点而言,哲学与其他科学是一样的。所以,科学有科学性,哲学也应该有科学性。最简单地说,科学讲究证明,那么哲学也同样,如果说哲学的证明与科学的证明不同,那么我们可以说哲学讲究论证。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谈的哲学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而海德格尔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没有论证,许多地方只是一个陈述或者一个描述,或者他的东西充其量是一种修辞性的。无论别人怎么看,这绝不是我理想中的东西,所以我排斥海德格 尔。
梅:您的回答让我对being和truth、对是与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领悟,也让我明白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与哲学,以及在继续学习和研究逻辑与哲学的过程中的重要性。谢谢王老 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