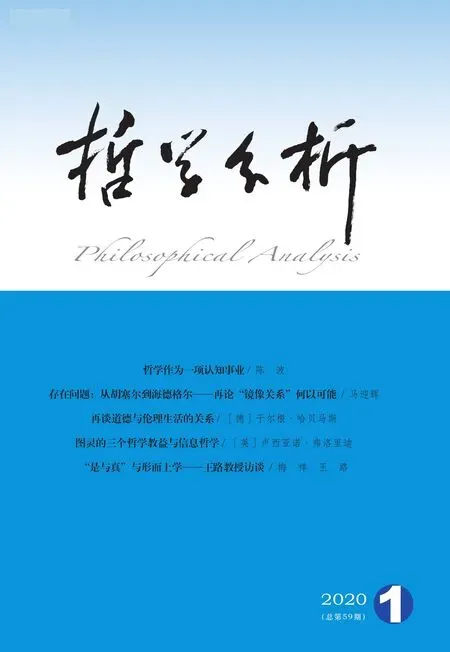先秦哲学的别样叙事
——读牟复礼先生的《中国思想之渊源》
张 朋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先生的经典作品《中国思想之渊源》①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王重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二版。本书的第一版为王立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西方学界享誉已久,在中国却影响不大,至今罕有学者专门对之展开评述。牟复礼先生的这部《中国思想之渊源》虽然不以“哲学史”命名,却是一本简明扼要的中国先秦哲学史研究专著。由于牟先生精纯的文化修养、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宽广的学术视野,其关于中国先秦哲学史的研究必然大有可观。下面就以牟复礼先生《中国思想之渊源》对中国先秦思想的分析脉络为主线,把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的先秦部分作为主要对比内容,集中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增进对先秦时期的中国学术一些新的认 识。
一、“中国思想”与“中国哲 学”
“中国哲学”是在20世纪初中西文化对接时产生并被接受的一个概念,在被使用近百年之后其之所以会遭到合法性的质疑,一方面是当代学术进步的体现和学术反思思潮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概念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和观念冲突。所谓的“中国哲学”究竟是“在中国的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从多种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并存的现状来看,似乎是二者兼备,其中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要 点:
1. 由于近现代以来哲学观念的巨大变更,“中国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得以不断凸显。按照欧洲经典哲学的立场和观点来看,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鄙薄当然是有道理的。“属于哲学的应是关于实体、普遍的东西、客观的东西的知识”,所以以这种西方哲学为标准,他认为中国无哲学,有的只是一些常识性的道德教训:“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①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 (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8页。。虽然这种评价可能给了一些以救亡图存或民族振兴为学术使命的中国学者以深深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还会因为20世纪初中国深重的民族苦难而被放大并最终导致中国哲学创造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一系列冲动和越界,但是按照现当代西方哲学观念来看,特别是按照海德格尔晚期的哲学观念来看,中国“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这不仅不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不足和欠缺,而且很可能恰恰相反,这是中国传统学术足以面对后现代解构思潮冲击的难得一见的优势和长处。当年大力反对“哲学”入侵中国学术的傅斯年先生早就断言: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而且庆幸我们民族有“这么健康的一个习惯”②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的影响》,载《汉学研究》 (第14卷),第309—332页。。所以在欧洲、美国以及日本都没有“中国哲学”这一学科设置的国际学术潮流之下,即使我们不按照“东亚系”或“汉学系”这种学科划分来安置中国哲学,那么我们也必须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来的看待中国人所使用的“哲学”或“中国哲学”概念。当然这里隐含着的一个重要判断是:就中国传统学术而言,使用“思想”和“中国思想”要比“哲学”和“中国哲学”具有更大的适用 性。
2. 按照欧洲经典哲学的观点和立场来研究中国哲学史,或者说“依傍”西方哲学来构建中国哲学史,这种研究方法产生了很多问题,在整体思路上可以说是非常牵强。胡适、冯友兰等前辈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已经证明,照搬西方哲学观念和思路来梳理中国哲学史是不恰当 的。
胡适在其1929年6月3日日记的手稿本中就表达了对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否定意见:“哲学的根本取消——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而1958年胡适说他在1929年写《中古思想史》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③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台北版自记”。。以上两点可以充分说明胡适先生早在1929年就放弃了“依傍”西方哲学来建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任何努力。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标志性人物,冯友兰先生一生虽然四次书写“中国哲学史”,但是其对哲学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前现代,其大作并不能担负其所理应担负的时代使命。俞宣孟先生明确指出,冯友兰先生把出于西方哲学“是论”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当作衡量哲学资格的标准,把中国哲学史上许多与之无关的观念纳入普遍与特殊关系的筐子,不免掩盖和歪曲了那些概念的本意。他在‘是论’的方向上接续中国哲学的发展,是生硬的,与传统脱节的。其所显示出来的不适,正说明‘依傍’的道路是走不通的。”④俞宣孟:《写中国哲学史要“依傍”西方哲学吗?——兼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观》,载《南国学术》2017年第3期,第2—13页。甚至可以说,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百年困局,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精神困 局。
3. 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相对照,西方历史学家牟复礼先生的《中国思想之渊源》实际上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更加切近中国先秦时期学术思想原貌的典范,而且由于其着力于“理解奠基于文明底下的思想根基”,以期“可以轻易发现思想和更为宽广的文化的互动”,因此具有更加深远的学术意义。比如就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而言,牟先生的这本著作堪称是“离开完整的哲学,回归到他们曾经拥有的思想传统中去……努力为一个朴素的理性,在历史时间轴上超越二元对立”。其中的关键是对于传统思想本身的坚持,即不必为富强、救亡、适者生存之类的时代理想而牺牲传统内容或忽视传统价值,最终得以在这一个过程中离开“无家状态”而进入每一个自适自足的精神家园。①比利时鲁汶大学戴卡琳教授所言,参见葛兆光:《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的争论》,载《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可见牟复礼先生使用“中国思想”这一概念而不是像冯友兰先生那样使用“中国哲学”,这实际上具有深刻的学术考虑,也说明他对中国哲学史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先秦部分具有深刻而独到的见 解。
二、关于中国思想(哲学)的起源
中国思想(哲学)的起源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有多种阐释。从《中国思想之渊源》中可以看出牟复礼先生对中国思想(哲学)的起源问题有非常深刻的见解。牟先生首先对冯友兰所秉持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表达了否定意见,虽然这种观点在当时曾经非常流行;其次牟先生慧眼独具地发现了《易经》,对《易经》中的有机世界观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加以阐释;最后牟先生提出并使用了伟大传统(Great Tradition)这一重要概念,为探索中国思想(哲学)的起源这一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总体解决方 案。
1. 牟先生彻底抛弃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并指出冯友兰在应用此方法来解释中国哲学起源中的逻辑困难。具体就是在第一章里牟复礼先生对冯友兰在解说中国哲学起源时所使用的趋向于极端的环境决定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冯的观点虽然饶有趣味,但作为整体的解释却失于简单。在一个循环的发展中因和果难以甄辨,以此很难解释结果何以又成了原因”。②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第15页。极端的环境决定论对地理环境和民族思想文化作出了非常简单的归类和机械的捆绑,比如以希腊作为海洋文明而以中国为大陆文明,以此来作不同文化的对比分析框架。实际上,中国地理的气候多样性赋予中华文明以很多不同的生产生活内容,除了农耕文明、渔猎文明之外还有畜牧文明和贸易文明。当然,如同牟先生所说,思想通过对生产生活的制约和改换也会对地理环境产生或大或小的作用,并很可能产生思想与环境之间一个循环的互动机制。此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冯友兰先生对哲学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关于中国哲学的环境决定论:“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习惯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这些就构成这个哲学的特色。就个人说是如此,就民族说也是如此。”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4页。就思想与环境的互动而言,环境对于思想是可以有巨大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决定性。思想诚然“常常”受到环境的限制和作用,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必然发生的。或者说环境的影响往往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但这个因素的古今变化巨大,其对于思想的作用力之大小是很难估量的,就一个人而言是这样,就一个民族而言就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哲学的背景而言,无论是“中华民族的地理背景”还是“中华民族的经济背景”都不足以给中国思想(哲学)的起源及其特质以充分的说 明。
同样,冯友兰先生以不同职业作为各家学派起源的见解也有非常类似的逻辑问题。以刘歆对九家学术起源的猜测为基础,冯友兰先生再进一步,他认为司马谈所说的六家思想是在官学到私学的历史转化过程中从六种不同职业的从业者中产生的:“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②同上书,第32页。仔细揣度这种职业对思想的决定关系,与其说“儒”“侠”“辩者”“方士”“法术之士”“隐者”这六个职业分别是各家学术的起源,还不如说各家学者更加趋向于选择这些职业。除了这种因果分辨不清的逻辑困难之外,冯友兰先生的这些猜测(冯友兰先生保留了“盖”字)实际上也缺乏先秦史料的具体支持。比如先秦典籍中“以武犯禁”的“侠”往往是荆轲、聂政之类快意恩仇的独行剑客而不是刻苦力行、团队协作的墨者,所谓的“辩者”应该还包括口若悬河的纵横家而不是专指研究名相的名家,而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方士”“法术之士”和“隐者”都很难说是先秦时期的某种特定职业。老子和庄子虽然可以说是“隐者”,但是他们也都出仕过,他们的思想更绝不是仅仅依靠那种隐居无闻的生活状态就能够得到充分说明的,这一点只要把动机和思想都多种多样的汉代隐士拿来作对比就很容易看清楚 了。
2. 牟先生发现了《易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基础意义,并对《易经》中的有机世界观进行了高度评 价。
牟先生特别重视中国哲学产生的独特文化土壤,凭借着西方历史学家对于中华悠久文明的敏锐直觉,他注意到了《易经》作为中国思想的基础意义:“《易经》伴随中国文明成长、臻熟,作为哲学,它成为后世历代思考和创见的源头活水。”牟先生以极大的热情集中阐释了《易经》有机世界观的重大意义和独特价值:“《易经》作为古代文献对我们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传达了一种最早的世界观。”受到心理学家荣格的启发,他进一步论述了《易经》贯通宇宙和人生以及揭示人体潜能的重要意义:“《易经》昭示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宇宙观,一种关于人的潜能的哲学:人在宇宙运化之中拥有主动创造和自由的潜能。”所以牟先生“把《易经》看作中国人心智的最早结晶”①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序”,第46页。,也就是当作最早、最为基础的中国思想或中国哲学,而《易经》也就是最能够代表“中国特质”的思想内 容。
《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牟先生的观点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其相关阐释也非常精彩。但是需要补充说明以下两点:第一是关于“《易经》”的含义问题。从上下文来看,牟先生所说的《易经》是成书于西周初期的《周易》经文,不包括《易传》。对比于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始终对《易传》的属于战国时期的哲学内容进行大力阐发而完全忽视成书更早的《周易》经文的重要意义,我们才能够真正发现牟复礼先生见解的深刻和卓异。以《传》代《经》,或者说只看到《易传》而看不到《易经》经文,这种传统经学的研究思路限制了冯友兰对《易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定位。现在看来,对《周易》经文和蕴含在其中阴阳思想的忽视,这可以说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失。第二是《周易》经文之中蕴含着阴阳思想,或者说阴阳思想是《周易》经文的核心,这个关键点牟复礼先生没有点明。正如张祥龙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牟先生没有“能深入理解《易经》的阴阳观及其在主流哲理和历史实际中的决定性影响”,“言《易》而未及阴阳,殊为可惜。”②同上书,第19页。诚哉斯 言。
3. 凭借着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敏锐感觉和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牟先生提出并使用了伟大传统( Great Tradition)这一重要概念,为探索中国思想(哲学)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具有多向展开可能的切入 点。
首先,牟先生提出的伟大传统这一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论及中国人没有“创世和超越的造物主的观念”的时候,牟先生认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则以圣贤传统之名成为各家各派的共同财富。”③同上书,第48页。中文译者王重阳在页下对 Great Tradition添加的注解是:“此处指高级的学术文化和精英传统。”在接下来的阅读中可以发现王先生对 Great Tradition一词的翻译进行了多样化的处理,最为常见的一种翻译是“圣贤传统”,类似的翻译还有“中国的圣贤传统”“中国圣贤传统”“中原圣贤传统”,相对比较少见的两种翻译是“中国文明传统”“传统”。④同上书,第65、75、131、111页。在“译后记”中王先生总结道:“用 Great Tradition指商周以来上层阶级的文化传统,以区别普通百姓的风俗传统。但‘大道’‘道’‘圣贤传统’‘文武之道’等文献中现成的古语都不能完全对接,求教了数位方家,也不能钤定,只好因地制宜,不强求一致。”⑤同上书,第239页。即使有了以上这些解释,Great Tratition的丰富含义仍然是意犹未尽,它会随着我们对夏商周三代文明认知的不断加深而加 深。
其次,通过概念对比和文献检索,我们可以进一步厘定Great Tradition的含义。首先,虽然具有丰富内涵,但是Great Tradition的基本意义是区分于草民传统、民间文化、众庶文化、大众宗教的“中国思想之莫基”。①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序”,第239页。笔者认为可以这样概括:Great Tradition是先秦学术思想的渊源,也是思想生命力、思想创造力的活力之源。第二,就Great Tradition的核心内涵而言,可资参照的先秦文献之中似乎唯有《庄子·天下》中作为天下学术之总源的“道术”与之相仿佛。如果《庄子·天下》中对先秦学术的总体图景是对先秦学术的一种真实叙述的话,那么由此就可以确认牟先生所说的Great Tradition具有很高的历史契合 度。
第三,Great Tradition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也是一个连续的概念,其中包括已经发掘的内容和尚未发掘的内容。夏商周三代思想文化是老子、孔子等诸子思想的主要渊源和生成土壤,而《易经》就是夏商周三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夏商周三代之前,伏羲时代还是一个接近于神话的传说时代,而黄帝时代则是一个仍然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的时期,无论是文献的可靠支持还是逻辑的合理展开都远不能够令人满 意。
三、关于中国思想(哲学)的特质
冯友兰先生对中国思想(哲学)的特质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素,比如他很早就提出了“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一概念。牟先生则对早期中西思想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没有创世的神话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并且认为只有在中西比较的视野内才可能对中国思想(哲学)加深认识,避免很多因为不自觉地因循西方思维而产生的误解。以冯、牟二位先生的研究为基础,我们可以对中国思想(哲学)的特质进行进一步的讨 论。
1. 冯友兰对中国思想(哲学)的特质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 索。
冯友兰对中国思想(哲学)的特质进行了很有意义的多向探索,其中很多观点都具有创造性。比如有可能受到辜鸿铭先生关于“中国人的精神”专题论述的启发,冯友兰提出了“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一概念:“中国哲学的历史中有个主流,可以叫做中国哲学的精神。”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灌注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独特内涵,他认为“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照中国哲学家们说,那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总体上看,冯友兰先生的这种概括是普遍适用于儒释道三家传统学术的。此外,冯友兰先生还提出了“入世的哲学”和“出世的哲学”这两个界定,并以佛家、道家为例对“出世的哲学”进行了特别的说明,以宋代新儒家为例说明“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哲学的精神”。由此不难发现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还是以儒家为本位的,尽管他用以概括中国哲学的“内圣外王”一词来自道家著作《庄子·天下》。但是很可能受到“依傍”西方哲学来构建中国哲学史这一根本思路的限制,冯友兰先生对中国思想(哲学)的特质还是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比如他始终没有回答“西方哲学的精神”是什么这类直接相关的问 题。
2. 牟复礼先生在早期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中发现了中国思想的特质,并在更加广阔的学术背景下对此进行了阐 释。
牟复礼先生敏锐地注意到“中国没有创世的神话”,“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这正是一个本然自生( spontaneously self-generating life)的宇宙的特征,这个宇宙没有造物主、上帝、终极因、绝对超越的意志,等等”。在这种中西思想文化深层次比较的基础上,牟先生指出“没有比西方人误解中国世界观的基本性质的过程,更能说明一种文化理解其他文化的方式,以及一个人在理解其他文化时所运用的自己的文化元素的尺度。现代欧美人坚持一种未经检验,而且也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假定:所有民族都认为宇宙和人类是外在的造物主创造的产物。由于把假定的基本类比当成事实,西方人在翻译中国典籍时依赖的是用我们自己文化的表达,进行似是而非的比附,并且以此机械地解读中国典籍,这满足的不过是西方人喜欢在其他文化中听到回声的癖好。”①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第47页。需要补充的是,不仅仅是西方学者容易犯以上错误,很多受到西方文化熏染的中国学者也会经常不自觉地按照西方哲学的观点来讨论中国思想文化的很多问题。
3. 以冯、牟两位先生的研究为基础,我们可以对中国思想的特质展开进一步的讨 论。
冯友兰所说的作为人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圣人”,进而“与宇宙的同一”,这虽然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却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质有着很深刻的揭示。这里所谓的“与宇宙的同一”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原话来讲实际上就是“道”的境界,这一点在冯友兰晚年所提出的人生四种境界的理论,特别是最高级的天地境界的思想上得到很大验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如牟复礼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生”的,那么中国人会把自己的终极问题归结于哪里呢?从逻辑上来说,如果不归结于上帝,那么就只能够归结于人自身和人与生俱来的潜在力量;进一步来说,就是归结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关于个人心灵提升和自我修炼的系统思想,可以简称之为“修道”思想。所以,在这里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中国思想的特质而言,“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概念,“修道”是儒释道三家学术的共同主题。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论证 了。
四、先秦哲学(思想)的大势分野
《中国思想之渊源》中先秦学术的总体架构是:先秦儒家、先秦道家、墨家、墨名道儒的论战、法家的成与败。这种分析框架具有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准确的历史考虑,而《论六家要旨》就是《中国思想之渊源》中先秦学术总体分析架构的根本依 据。
汉代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列举了六个主要学术流派: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其中的儒、墨、名、法、道德五个部分基本上都被牟复礼先生直接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进一步论述各家学说的要旨与短长时,这六个流派被司马谈进一步界定为“阴阳之术”“儒者”“墨者”“名家”“法家”“道家”。很明显,司马谈非常精确地使用了“术”“者”“家” 这三种不同称谓来对六种学术流派进行命名并借之以对六种学术流派进行准确区分。第一,就“术”而言,其强调的重点是某种思想的应用,而且这种思想具有久远的渊源。《周易》占筮就是自古流传的阴阳思想的一个应用之术,所以其具有“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的鲜明特征。当然就其本身而言,阴阳思想是一种具有深刻内涵的宇宙论,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部分,具有“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的重要意义。所以牟先生盛赞其为“一种卓越的有机世界观”,并把关于《易经》的讨论作为中国思想开端的主要内容。牟先生对《易经》的这种处理可谓是与司马谈所做的“阴阳之术”的区分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就“者”而言,其主要强调的是一些人物的群体或集合,而不是强调其思想的连贯和一致。司马谈认为当得起“者”的是“儒者”和“墨者”,所以司马谈很可能已经认识到孔子、孟子、荀子以及曾子、子思等学者只是一群自称为儒的人,墨子和其后学也只是一群自称为墨的人,而在每群人中的某些人的思想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差异。当然,就积极入世乃至于汲汲于救世的使命感而言,“儒者”和“墨者”二者之所以都被称为“者”还可能是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那一种政治抱负和经济情怀。遗憾的是,牟、冯二位先生都把“儒者”和“墨者”当作“家”来做简化处理。第三,“家”是指具有连贯和一致的学术思想的一些人,强调的是此“家”与彼“家”之间的边界与区别。而“家”这种称谓应该是以周代礼仪制度中大夫之“家”所具有的血缘亲性和政令一致以及后代承继等特征为文化背景。很明显,司马谈认为可以称为“家”的只有“名家”“法家”“道家”这三家学术流派。牟先生接受了“法家”“道家”这两个学派界定,却对“名家”进行了放大处理,即在《中国思想之渊源》的第六章“何为真知”中对墨名道儒的关于“知识论”的论战进行了集中讨论。对于这种“知识论”的处理办法,冯友兰先生的意见无疑是非常中肯的:“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因为“认识者和被认识的是一个整体。”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22页。此外,墨名道儒各家论辩的角度不同,内容各异,很多都不是纯粹的逻辑问题。像牟复礼先生那样将其当作逻辑问题来讨论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些问 题。
当然牟复礼先生所设计的这个先秦学术总体架构也并非尽善尽美,还是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讨 论。
1. 按照汉代学者的思想观念而不是按照先秦史料来建构先秦时期的学术体系,现在看来这恐怕还是有些问题。按照汉代的学术观念来划分先秦时期的学术流派乃至于考察其起源,这一思路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体现得非常突出。根据《庄子·天下》 《吕氏春秋·不二》等先秦学术史料来看,汉代学者司马谈、刘歆对先秦时期总体学术面貌的理解与先秦时期学术体系的实际状况差距甚大,特别是以刘歆的学术观念为基础来讨论六家起源,这也就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明显失误。比较而言,牟先生在《中国思想之渊源》中对冯友兰著作中汉代学术观念的过度使用有很大纠正,但是整体而言仍然有所阙 失。
2. 继承了冯友兰先生的观点,牟复礼在《中国思想的起源》中仍然把孔子当作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这种看法并不妥当。冯友兰先生具有鲜明的儒家立场,而这种思想倾向被其带入到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的写作之中,其中最突出一点就是始终坚持把孔子当作中国哲学史第一人来叙述,即使遭到胡适等学者有理有据的批评和反对也一直没有改变。实际上根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掘,老子先于孔子,《老子》是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部诸子著作,这是一个世纪以来越来越见其正确的一种学术观点。特别是郭店竹简《老子》出土之后,老子在先秦诸子中的首要地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牟先生没有接受胡适等学者对老子和《老子》的思想考察和历史定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 憾。
3. 先秦时期而言,以儒家为主流而以道家为支流,牟先生所秉持的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就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史而言,关于儒道关系学界已经多有争议,总体而言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儒家主干,二是儒道互补,三是道家主干。冯友兰先生一直秉持第一种观点,牟先生继之。但是仅就先秦时期而言,以儒家为主流而以道家为支流这种观点是不合适的,因为儒道之间的区别和互动不是先秦时期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根据《庄子·天下》 《吕氏春秋·不二》等先秦学术史料来看,子学是当时学术的基本面貌——无论是发表个性飞扬的观点还是进行互相攻驳的争论,儒道诸子所发表的首先都是个人观点,抑或是对于敌手个人的批评,其中并没有明显的学派归属和儒道区分意识。如果说先秦时期学术有所统一或归类的话,那么《庄子·天下》则体现出以“道术”统摄先秦学术的意向。而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在总结先秦学术时则明显有着对道家而不是对儒家的偏好和欣赏,其主要原因就是其兼收其他五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参照,牟复礼先生在《中国思想之渊源》中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先秦思想进行了重新梳理,进而给出了一个迥然有别的先秦学术面貌,这使得“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的光辉能够更加耀眼,直照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