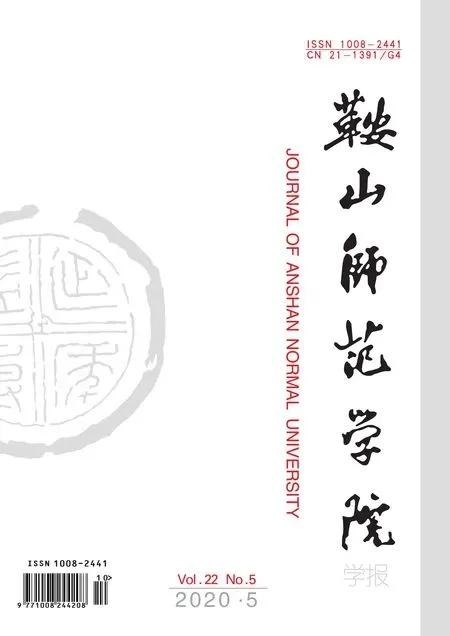从介系词语义功能看汉韩空间关系概念化差别
王楠楠
(鞍山师范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一个完整的句子除了有语调,一般由名词和动词(包括形容词)构成。然而,在一个句子中,名词需要一定的语法标记才能实现其语法功能。用来标注名词语法功能的语法标记在不同的语言中类型是不同的,如声调、词缀、词尾、语序、词等。汉语除了可以靠语序实现名词的语法功能外,介词也是其实现名词语法功能的一种手段,而韩语主要靠在名词后添加助词来实现其语法功能,只不过汉语的介词为前置词,而韩语的助词为后置词。本文将这种在句子中用来标注名词或其同等语与句中其他成分之间关系的单词形式统称为“介系词(adposition)”。
空间关系指的是现实世界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物体间形成的位置关系,用来描写这种关系的语言表达式可称为“空间关系表达”或“空间关系构式”[1-2]。从语言类型学来看,虽然汉语和韩语分别属于孤立语和黏着语两种不同语言类型,但在表达空间关系时,“处所”“起点”“方向”“终点”等语义角色的实现基本需要借助介系词的帮助,汉语中这样的介系词主要为“在,从(由),往(向),到”等方位介词,韩语中这样的空间介系词主要为“e,eseo,(eu)ro”等位格助词,为了平行对比需要,这里将它们统称为“空间介系词”。
从前人研究来看,关于汉韩空间介系词的对比主要集中在个别介系词用法及语义扩展的比较上,很少有研究将汉韩介系词放在空间关系这一语义范畴下来考察,而揭示其概念化方式的研究就更少了。此外,就汉语来说,虽然与空间关系相关的讨论和研究涉及语义范畴[3]、表达方法和手段[4-5]、认知基础和构式语法基础等诸多方面[6],但从汉语与其他语言对比的角度研究空间关系的只有少数几篇,主要集中在汉俄和汉英之间的对比[7-9]。本文以汉韩空间表达式中的空间介系词为研究对象,通过这些介系词在空间关系这一语义范畴中所表现的语义功能对比,揭示汉韩语言使用者对空间关系进行概念化方式的差别。
一、空间关系的类型及空间成分的语义角色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空间关系的语言表达是语言使用者对客观事物间方位关系的概念化。因此,空间关系表达式所描述的空间关系与其说是客观上真实存在的,不如说是语言使用者对空间场景进行主观性识解的结果。例如:
(1)a.他的大衣掉在阳台围墙的下面。
b.外环路的南面和东面是工业区。
c.这里左边是悬崖,右边是深沟。
(1)分别描述了“大衣”与“阳台围墙”“工业区”与“外环路”“悬崖”和“深沟”与“这里”之间的空间关系。但在确定具体空间方位上,所选择的“参照点(reference point)”并不相同。(1a)中,“围墙的下面”这一空间方位通过“围墙”便可以确定;而(1b)中,“外环路的南面和东面”这一空间方位除了需要“外环路”的位置,其“南面和东面”是由地球这一参照点决定的;(1c)中,“这里”及“左边”和“右边”这一空间方位只有通过观察者的实际位置才能确定。这说明在对空间场景进行概念化时,我们只有通过某些参照点,才能确定目标物体的相对空间方位。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把空间关系图式化见图1。

图1 空间关系的构成要素[10]
图1中,四边形表示由两个参与者形成的空间场景,其中一个参与者为需要确定方位的“目标物(located object)”,另一个参与者是用来决定目标物方位的“参照物(reference object)”。它们之间用虚线连接是因为这种关系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这个空间场景“观察者(viewer)”的概念化结果。我们可以把图1看作一种跨语言的空间关系图式,作为汉韩空间关系表达式比较的参考基点。
根据图1中的“目标物”和“参照物”之间是否发生位置变化,可以将空间关系划分为“静态性空间关系”和“方向性空间关系”两大类型。这两种空间关系的表达式可以通过下面示例说明:
(2)a.20多名儿童在操场上载歌载舞。
b.在书桌上有一本打开的书。
(3)a.他从上海出发。
b.一位白发男人正从中南海红墙外走过。
c.两个女工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
d.水往低处流。
(2a)中的目标物“儿童”和参照物“操场”之间,(2b)中的目标物“书”和参照物“书桌”之间没有发生位置变化,即“目标物”和“参照物”之间形成的空间关系是一种“静态性空间关系”;其中,(2a)的空间成分“操场上”是事件“载歌载舞”发生的场所,标注“操场上”这一“背景”的语法标记为“在”;(2b)的空间成分“书桌上”是物体“打开的书”存在的场所,标注“书桌上”这一“处所”的语法标记也为“在”。可见,汉语中,无论是“相对静止性空间关系(2a)”还是“绝对静止性空间关系(2b)”,用来标注静态性空间成分的语法标记都是“在”。(3a)中的目标物“他”和参照物“上海”之间、(3b)中的目标物“男人”和参照物“红墙”之间、(3c)中的目标物“女工”和参照物“凳子”之间,(3d)中的“水”与参照物之间发生了位置变化,即“目标物”和“参照物”之间形成的空间关系是一种“方向性空间关系”。(3)中,空间成分“上海”“红墙外”“凳子上”“低处”分别是目标物“他”“一位白发男人”“两个女工”“水”移动的“起点”“路径”“终点”及“方向”,用来标注这些空间成分的语法标记分别为“从”“在”“往”等。可见,汉语里,在“出发移动(3a)”“通过移动(3b)”“到达移动(3c,d)”等空间关系中,用来标注方向性空间成分的语法标记各有不同。
在汉语和韩语的空间关系表达式中,除一些特殊的空间关系表达式外,“背景”“处所”“起点”“路径”“方向”及“终点”等语义角色的实现基本上需要在指示参照物的名词上标注空间介系词。如(2)和(3)所示,汉语介系词“在”具有标注“背景”“处所”及“终点”的语义功能;“从”具有标注“起点”和“路径”的语义功能;“往”具有标注“方向”的语义功能。下面我们将通过这几种空间关系类型的汉韩具体表达式对比,寻找汉韩空间介系词语义功能的对应关系。
二、汉韩空间介系词的语义功能与对应关系
按照上述空间关系的分类,我们可以发现汉韩在表达空间关系时,除存现句、省略句等一些特殊句式外,空间成分基本上都需要由空间介系词标注。
(4)a.20多名儿童在操场上载歌载舞。
b.在书桌上有一本打开的书。
c.两个女工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

我们决定在图书馆见面。

你打算从首尔出发吗?
从(4)和(5)可以看出,汉语方位介词“在”和韩语位格助词“eseo”在表达动作行为的“背景”上具有相同的语义功能,如(4a)和(5a)。但汉语“在”还有标注物体存在“处所”和物体移动“终点”的语义功能,如(4b、c);而韩语“eseo”则具有表示物体移动“起点”的语义功能,如(5b)。
(6)a.一位白发男人正从(由)中南海红墙外走过。
b.他从(由)上海出发。

犯人从后巷逃了出去。

来这边吧。

爸爸回家了。
从(6)和(7)可以看出,汉语介词“从(由)”和韩语助词“(eu)ro”在表达物体移动的“路径”上具有相同的语义功能,如(6a)和(7a)。此外,汉语“从(由)”还可以表达物体移动的“起点”,如(6b),而韩语“(eu)ro”还可表达物体移动的“方向”或“终点”,如(7b、c)。
(8)a.史迪威逃往(向)印度。
b.水往(向)低处流。

弟弟回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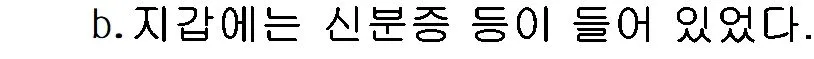
钱包里装着身份证等。
(10)我们走到了湖北省黄冈市。
从(8)和(9)可以看出,汉语“往(向)”标注的是物体移动的“方向”,韩语“e”可以同时标注物体移动的“终点”和物体存在的“处所”。此外,汉语的“到”也可以标注物体移动的“终点”,如(10)。
根据上述空间介系词的对比分析,可将汉韩空间介系词语义功能及对应关系绘制成图2。

图2 汉韩空间介系词的语义功能及对应关系
三、空间介系词语义功能差异的概念化原因
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不仅要进行充分的描写,还要对这些语言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找到其背后的根据。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汉韩都存在同一个空间介系词标注多个空间方位成分或同一个空间成分由不同的空间介系词来标注的情况,这说明语言的形态和意义并不是单纯一一对应的符号体系。究其原因,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使用者在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同时,由于心理、文化、社会、生态等因素的影响以及为了减少记忆负担量,同一个形态基本上可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义。实际上,语言中真正意义上的单义词很少,大多是以多义词的形式出现的。上述的汉韩空间介系词除了在标注空间成分上具有多个语义功能之外,还可以用在时间、心理等抽象的概念上,这一共同特征充分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但不同的是,汉韩的这些空间介系词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交叉对应的,下面将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它们之间这种交叉对应关系产生的因素作出回答。
(一)概念化的视角差异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范畴象征概念范畴,从汉韩都存在用同一个空间介系词标注几个空间成分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在汉语中,“在”所标注的“背景”“处所”和“终点”为同一个概念范畴;“从(由)”所标注的“起点”和“路径”为同一个概念范畴;“往(向)”所标注的“方向”和“终点”为同一个概念范畴。在韩语中,“eseo”所标注的“背景”和“起点”为同一个概念范畴;“(eu)ro”所标注的“方向”“路径”和“终点”为同一个概念范畴;“e”所标注的“处所”和“终点”为同一个概念范畴。为了能同时满足以上概念范畴的划分,可以设立这样的假说:汉语按某一动作行为执行后目标物是否存在于某一特定空间,将空间概念化为不同范畴;而韩语则按某一动作行为执行前目标物是否存在某一特定空间,将空间概念化为不同范畴。下面,我们对这一假说进行验证。
(4′)a.20多名儿童在操场上载歌载舞。
b.在书桌上有一本打开的书。
c.两个女工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
(8′)a.史迪威逃往(向)印度。
b.水往(向)低处流。
(4′)中的“在”分别用来标注“背景”“处所”和“终点”,这三个语义角色可以用同一个形态“在”来标注必然存在范畴化的相同点。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它们的相同点就是在空间关系中,“目标物”执行相应的动作后都存在于由“参照物”所确定的空间范围内。即,“载歌载舞”“有”“坐”的动作执行后,目标物“20多名儿童”“一本打开的书”以及“两个女工”在参照物所确定空间“操场上”“书桌上”“凳子上”的范围内。(8′)中的“往(向)”分别用来标注“方向”和“终点”也是同样的道理。
(6′)a.一位白发男人正从(由)中南海红墙外走过。
b.他从(由)上海出发。
(6′)中的“从(由)”分别标注“起点”和“路径”,各句中相应的动作执行后,“目标物”不在空间成分所指示的空间范围内。即,“走过”和“出发”的动作执行后,目标物“一位白发男人”不在“中南海红墙外”和“他”不在“上海”的空间范围内。

(5′)中的“eseo”分别用来标注“背景”和“起点”,两者范畴化的相同点就是在空间关系中,“目标物”执行相应的动作前存在于由“参照物”所确定的空间范围内。即,“mannada (见面)”和“chulbalhada(出发)”的动作执行前,目标物“uri (我们)”在“doseogwan (图书馆)”和“听者”在“seoul(首尔)”的空间范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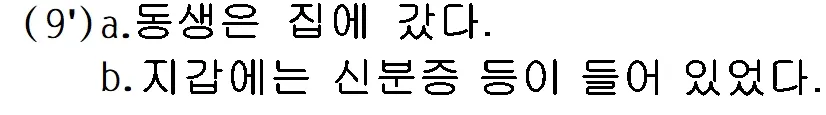
(7′)中的“(eu)ro”分别标注“方向”“路径”和“终点”,各句中相应的动作执行前,空间成分指示的范围内目标物是不存在的。即,“ppajyeo-nagada(逃出)”“oda(来)”“dolaoda(回来)”动作执行前,目标物“beomin(犯人)”“听者”以及“abeoji(爸爸)”不在参照物所确定空间“dwisgil(后巷)”“ijjok(这边)”“jip(家)”的范围内。(9′)中的“e”分别用来标注“处所”和“终点”也是同样的道理。
可见,汉语按动作执行后目标物是否在空间成分指示的范围内将空间范畴化。动作执行后,有目标物存在的空间成分用“在”或“往(向)”来标注;动作执行后,没有目标物存在的空间成分用“从(由)”来标注。韩语也是同理,只不过韩语按动作执行前目标物是否在空间成分指示的范围内对空间进行范畴化。动作执行前,有目标物存在的空间成分用“eseo”来标注,没有目标物存在的空间成分用“(eu)ro”或者“e”来标注。也就是说,汉语对空间场景进行范畴化时,将观察点放在动作行为执行之后;而韩语对空间场景进行范畴化时,将观察点放在动作行为执行之前。这个假说放在位移事件中时也可以理解为汉语的观察视角在位移事件的“终点”,而韩语的观察视角在位移事件的“起点”。
图3(a,b)描述的是相同的移动事件。如(b)所示,概念化主体从“起点”观察移动事件时,移动体向着“终点”移动的每一瞬间所经过的位置均可以看作为移动的“方向”和“终点”,这些位置一起构成移动的“路径”;但如(a)所示,概念化主体从“终点”观察移动事件时,移动体向着“终点”移动的每一瞬间所经过的位置除了一起构成移动的“路径”这一点相同以外,各个位置只可以看作为移动的“起点”,这与从“起点”观察移动事件正好相反。由于两个不同的观察视角,汉语中的“起点”和“路径”重合,韩语中的“方向”“路径”和“终点”重合,分别被概念化为同一个范畴,用同一语法标记来标注。实际上,在一些汉韩空间关系表达式中,汉语“从”标注的是“起点”还是“路径”,韩语“(eu)ro”标注的为“路径”“方向”还是“终点”,如果没有上下文,就会如(11)一样,难以区分。

图3 位移事件
(11)a.他这次从北京去美国。(“北京”可以是出发的“起点”或途中经过的“路径”)

他从桥上走了过来/他向桥走过来/他走到了桥(这儿)。
(“桥”可以是“路径”“方向”和“终点”)
(二)概念化的突显差异
认知语言学认为,不同的民族对相同的对象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其外部表现就是同一对象用不同的语言范畴来表达。前文虽然说明了汉韩的同一介系词可以标注不同的空间成分与概念化的视角有关,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介系词可以同时用来标注相同的空间成分。如,汉语的“在”和“到”可以同时标注“终点”,韩语的“e”和“(eu)ro”也可以同时标注“终点”。本文认为不同的空间介系词虽然可以标注同一语义角色,但在使用上会受到不同的句法语义制约,这体现了汉韩在对空间场景进行概念化时对同一空间场景突显不同。
(12)a.他跑到了学校。
b.*他跑在了学校。
(13)a.他坐到了椅子上。
b.他坐在了椅子上。
(14)a.他把画挂到了墙上。
b.他把画挂在了墙上。
(12)~(14)中的空间成分均表示“终点”。(12)用来标注终点的空间介系词只能选择“到”,而(13)和(14)却可以选择“到”或“在”。这种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到”在语义上可以同时突显位移的过程和终点,而“在”只能突显位移的终点。“到”和“在”的这种语义差别可以通过动词的“体(aspectual)”加以验证。如果给动词进行体的划分,(12)的动词“跑”属于“非终结动词(atelic verb)”,而(13)和(14)的动词“坐”和“挂”属于“终结动词(telic verb)”。因此,“跑”的论元结构不要求结果位置,即“终点”论元;而“坐”和“挂”的论元结构需要有“终点”论元。此外,“跑”行为的实现,需要一定时间的持续,而“坐”和“挂”行为的实现是瞬间性的。(12)的事件本身包含一定的过程,其语言表达需要对这个过程进行突显;而(13)和(14)的事件本身包含结果位置,其语言表达需要对这个结果位置进行突显。因此,只能突显结果位置的“在”不能用来标注需要突显过程的事件上,所以(12b)为不合乎语法的句子。

顺女回到了家里。

顺女回到了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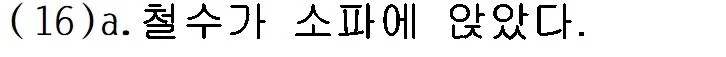
哲秀坐在了沙发上。

哲秀坐到沙发上。
(15)和(16)的空间成分均表示“终点”。(15)可以选择“e”和“(eu)ro”来标注,而(16)只可以由“e”来标注。这种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e”的语义只能突显位移终点,而“(eu)ro”突显的是到达终点前的过程。(15)中,“dolaoda (回来)”这个动作不仅要有终点,回来之前还需要一定的距离。此时,如果需要对位移终点“家”进行突显,我们可以选择“e”;而如果需要对与家逐渐接近的过程进行突显,我们应选择“(eu)ro”。而“anjda (坐)”这个动作,如上所述,这个动作是瞬间发生的,只有结果位置具有突显性,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不能由具有突显移动过程的“(eu)ro”来标注,所以(16b)为不合乎语法的句子。
从(12)~(16)可以看出,虽然汉韩都可以用不同的空间介词来标注相同的空间成分,但两者对相同空间场景突显的侧面并不完全相同。以到达移动事件为例,汉语可以用不同空间介系词分别突显“终点”或同时突显“终点”和向终点移动的过程,而韩语用不同空间介系词突显的只能为“终点”或向终点移动的过程。
本文从空间关系这一语义范畴出发,通过对空间关系的分类,探讨了各种空间关系表达式中用来标注空间成分的空间介系词所表现的语义功能,并从认知语言学角度阐释了汉韩空间介系词在语义功能上存在的不同之处与语言使用者对空间关系进行概念化时采取的视角和突显有关。此外,在表达空间关系上,汉韩方位词、存在动词、位移动词以及存在句等特殊句式在句法语义上也存在诸多的细微差别,这些都是与空间关系这一语义范畴相关的重要语言现象,亦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