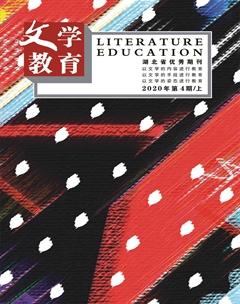从郭沫若的《女神》看“自由体新诗”的嬗变
内容摘要:作为中国新诗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郭沫若对新诗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本文从《女神》的角度入手,具体阐述中国新诗由“以物观物”向“以心观物”的转变、在“表现自我”中的“象征主义”移植、最后创造出以浪漫主义为主色调的“自由体新诗”的嬗变过程。
关键词:《女神》 表现自我 象征主义 自由体新诗
按照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1]的界定说,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他把中国新诗从“摹仿自然”阶段推向“表现自我”阶段,并借助泛神论加强了新诗“表现自我”和反封建力度;使“二十世纪的动荡和反抗精神”成为新诗艺术的精魂和生命线。他的《女神》一问世,就急遽地结束了五四诗坛上的“胡适开一代诗风的时代”,引领中国新诗走上新的里程。
一.从“以物观物”向“以心观物”的转变
作为五四新诗的重要成果之一,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早期诗歌创作,一直被普遍视为现代新诗史的真正开篇。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反复谈论《女神》中充满理想光彩的自我抒情形象、大胆叛逆精神以及渗透在内容和形式中的彻底解放感,为的是说明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成就不仅支撑了整个创造社诗人群,面且照亮了整个五四新诗坛。他不仅是“代表五四以后最早也是突出的浪漫主义诗潮”,而且也是中国新诗第一个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中国新诗坛、
参与诗歌创作的。
众所周知,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诗体大解放中,冲破了一切旧体诗词格律的束缚之后,明确地提出“情绪说”或“自我表现说”。他认为,诗的主要成分是“自我表现”,“情绪”高于一切,“情緒的律吕,情绪的色彩便是诗”。[2]在1920年1月18日写给宗白华的信中激情地宣称:“我想我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的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hain(曲调),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旋律),生的颤动,生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醇,慰安的天国。”[3]他的这个理论追溯起来是导源于卢梭、歌德、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大家。英国的华兹华斯就给诗下过这样的定义:“所有的好诗,都是从强烈的感情中自然而然的溢出的。”[3]一定的程度上,郭沫若对新诗理论及创作来说显然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和反叛,创造了和“摹写自然”迥然不同的“表现情绪”的诗歌。在他的诗歌中,复沓、排比手法的运用不仅使句子读起来琅琅上口,有时还直接起着结构篇章的作用,这一种手法的使用,可以说是郭诗的一个创造。一方面有助于造成一种奔腾流荡的气势,将诗人喷泻而出的激情径自地融入富于节奏感的诗行中,既能彻底将早期白话诗从半文半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又能表现出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更能比较容易地获得新的韵律感,昭示了“摹写自然”的逐渐消退。
郭沫若笔下的自然已经在自然景观中流溢着诗人心中的诗意、诗境,是诗人情绪中的自然,或者说是诗人在自然中的情绪。因此,在他的诗中,有了更多的“自我表现”成分和较为分明的主体形象,诗歌观及其创作标志了中国新诗由“以物观物”向“以心观物”的转移。中国新诗到郭沫若才真正塑造了主体形象,才真正具有审美意识的主体性,中国新诗才真正跃进到现代化的行列。郭沫若的这种特点最清楚不过地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女神》中。
二.在“表现自我”中的“象征主义”移植
对郭沫若而言,表现主义似乎比象征主义更具吸引力。他曾多次引述表现派的观点与概念,并表达了与表现派的“共感”。但他所推崇的是那种与其自我表现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原则一致的表现主义,按他的阐释,这种表现主义“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把自我的精神运用客观的物料,而达到自由创造”。[4]对表现主义的其他重要方面,如“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语言、价值和式样,表现人格的最深层次,并利用得自现代工业世界的象征”以及运用抽象或变形手法“创造幻象世界的尝试”等等[5]并未给予特别关注。换言之,表现主义只是他用来表述其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另一个概念,它消融于这种浪漫主义,而不具独立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的诗歌还是以浪漫主义为主导的,同时也与现代主义有若干的联系。在《女神》中,可以看出郭沫若是怎样把激情、想象、联想与象征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以致富于激情与想象的诗篇,几乎都有象征的意义在,或象征某种精神,或象征某种情感,或象征某种意愿。《风凰涅槃》就是象征诗,还带着神秘的色彩。在诗中,郭沫若把象征与狂幻想的激情、奇丽的联想结合起来,构成了象征“美的中国”再生的神话的诗。长诗的《序曲》抒写凤凰集香木燃火、群鸟间“冷淡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以及在漫长的历史中“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灭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接着《群鸟歌》展示了对宇宙人生的不同层面的理解,以及精神宇宙的主体性。群鸟对宇宙人生的体认与凤凰处在不同的精神层面,说明凤凰的黑暗、冷酷、荒谬的环境中的自焚行为充满了孤独的悲壮感。再如《炉中煤》、《晨安》、《匪徒颂》等诗作以及《星空》、《瓶》、《前茅》中的部分诗作,也具有象征的意蕴。同时,郭沫若还善于运用象征性意象以扩大诗的内蕴和强化诗的情感,其中贯穿的意象,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丰富了诗歌的精神内涵,展示艺术魅力。
应当指出,郭沫若诗中所运用的象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象征主义,他对西方象征主义诗艺并没有作过认真研究,而是取其“类比”方式。其中的重要的观点是:“真正的文艺是极丰富的生活由纯粹的精神作用升华过的一个象征的世界”[6]。正因为文艺都是“象征的世界”,所以《女神》几乎是在力求“创造一个类比的大网”,这个“类比的大网”,并不体现为对象征主义的诗艺(符号)的着意经营,而是体现为对象征精神意蕴的关注与探索。象征主义作为浪漫主义运动以后兴起的一种新的潮流,被郭沫若专注于西方象征主义的移植,由于他的传统诗词的深厚功底,使得他得其精义。
三.创建浪漫主义为色调的“自由体新诗”
郭沫若早期的与浪漫主义共生的那种象征主义,为其“自我表现”和“自然流露”提供了诗意的支撑。在这里,主体情感借助外在物象和情境呈现着自身,这种主客体的统一,使激情的宜泄得到了诗意的升华,因而这些诗都具有所谓的“具体性”,又由于主体的介入而有了某种超越性,给郭沫若的“自我表现”以形体,使其避免了一泻无余。郭沫若的诗就吻合了“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个性解放精神,保持了诗人奔腾不息的个人风格,又不失诗的境界与意趣。这种借助“融会贯通”而产生的象征意蕴,在《女神》之后的创作中发挥着浪漫雄浑的热情和撼人的艺术光泽,却又在自然的冲淡中保持了郭沫若那种淋漓的元气和独特的诗意。
闻一多说:“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7],卞之琳在《新诗与西方诗》中也说,郭诗出现以后,“新诗才真像新诗”。事实上,郭沫若的诗歌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色调的,而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则是其诗歌的精义所在;他在把象征主义纳入了浪漫主义的总体框架中,创造了被称作“女神体”的真正的自由体新诗,充分显示了五四“诗体大解放”的实绩。《女神》的问世,把旧诗词的限制一扫而光,把一切羁绊统统推倒了,中国诗歌从这里真正得到了解放,为青春的热情寻找恰当的语言和形式,创造出了完全合于自己诗歌内容的崭新的多姿多彩的新形式。连郭沫若自己都说:“我所著的一些东西,只不过尽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乱舞罢了。”[8]然而正是这种乱跳乱舞的诗,很好地倾泻出五四时期人们胸中那“大波大浪的洪涛”,完美地反映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精神。
《女神》以自己的思想情绪支配诗行,以情绪的旋律表现诗的旋律。郭沫若不愿局限于一个格局,而是徘徊翱翔在所有叙述性、抒情性、戏剧性的形式之间,来回于散文与诗歌风格之间。突破了那风格之一律的旧原则,诗人以“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力量和气魄去推倒一切旧形式,重建一种新形式,这种新形式再也不是一种束缚人们手脚的镣铐,而是自如地抒写自己的激情和想象的自由的形式。从郭沫若开始,新诗不再存在固定的格律规范,诗中的激流随着内在情绪的节奏而起伏;读者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对音韵形式美的品味和感知,而主要是以联想的方式投入情绪的体验,从而获得美的享受。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他的自由理论,即“艺术的自由”的审美观念,这种观念要求每个诗人都成为他自己,冲出狭小的空间,走进广阔的艺术天地,而实际是唤起每个诗人的艺术的觉醒。
因此,郭沫若黄钟大吕般的高亢歌声,无疑是表现自我、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逐步嬗变。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潮借助郭沫若的《女神》,闪现出强烈而短暂的美学光辉,而郭沫若的文学地位也借助浪漫主义得以奠定。我们看到,五四诗歌革命只有到了《女神》才“异军突起”,才充分显出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威力,新诗阵地才有了主将。《女神》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恢宏的诗歌创造才能,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为中国新诗开多拓了主体精神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427
[2]郭沫若.生命的文学[J].学灯,1990(2)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4]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607.
[5]理查德·谢帕德.德国表现主义-现代主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249
[6]刘增杰.云起云飞[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311
[7]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N].创造周報,1923-06-03(4)
[8]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3.
(作者介绍:王秀芹,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从事现当代文学,影视传媒,广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