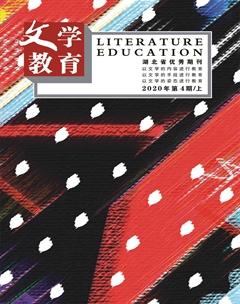路遥小说民俗叙事研究
内容摘要:路遥对黄土地上民俗生活样态的书写,反映了陕北独特的生活面貌。作家通过大量的民俗元素构建了小说人物的活动空间,以陕北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为原型,塑造了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借用民俗场景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立体交叉桥”和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生活。路遥是一个对史诗性追求非常自觉的作家,将宏大的历史问题表现于琐碎的民俗生活中,蕴含着深刻的现实精神。
关键词:路遥小说 民俗叙事 现实精神
民间风俗既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又对个人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恰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言:“我们必须看到,风俗习惯对人的经验和信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它的表现形式又是如此千差万别。没有人会用不受任何影响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人们总是借助于一套确定的风俗习惯,各种制度和思维方式来观察这个世界。”[1]路遥生于陕北,从小深受乡土生活熏陶。在民俗文化书写中,路遥并没有停留在对陕北民俗元素活化石般的记录和复现,而是体现出自觉的审美取舍和艺术关照,使之与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融为一体。
一.路遥小说民俗事象的呈现
路遥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关于世态人情、风土习俗的描写。小说中的民俗元素,主要体现在物质民俗、人生礼仪民俗、节日民俗等三个方面,展现了陕北的历史生活面貌。
1.物质民俗
路遥小说中的物质民俗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老羊皮袄、白羊肚毛巾、羊皮大氅等服饰多次出现在小说之中。“民以食为天”,小说中描写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吃食,如馍馍、钱钱饭、面片、荞面饸饹、油糕、猪头肉、大烩菜等。关于建筑,小说中最常见的是窑洞,分别有土窑、石窑、砖窑。在出行上,小说中最常出现的是马车、架子车。它们既是交通工具,又是生产工具。路遥小说中的物质民俗体现了陕北以农耕文化为主,糅合了游牧民族文化的多元特征,蕴含着陕北人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小说中出现的羊肚子手巾等服饰、大杂烩的饮食文化以及对羊肉、揪面片的喜好,可以隐约窥见游牧民族文化的遗风。
2.人生礼仪民俗
路遥小说中还涉及生育、结婚、丧葬等众多的人生礼仪习俗。在陕北诞生习俗中, “谁家要是生了男孩,要在月子窑的门楣上别一块扎着弓箭样的小红布,告诉世人,这家生了个小子。路遥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郑重地把绾好弓箭的红布挂在了门楣上。”[2]外人见到弓箭样的小红布则主动回避的习俗被路遥用到了《平凡的世界》孙少安的媳妇坐月子的时候。关于婚俗,小说《人生》详细介绍了刘巧珍与马栓的结婚盛况,尤其突出了热闹的娶亲场面。陕北地区婚俗沿袭了古代六礼的许多仪式,婚姻的缔结大致需经择亲、定亲、商话、迎亲等四个环节,其中最为隆重的便是迎亲。关于葬礼,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绘金老太太的葬礼,细致展现了“撒路灯仪式”、“游食上祭”仪式、“商话”等礼俗。除此之外,路遥还表现了生日当天小孩挂“锁线”、本命年系避邪的红裤带等习俗,暗含着陕北人祈求无灾无病的文化心理。
3.节日民俗
路遥小说中还描绘了春节、元宵节、端阳节、打枣节等众多的节日民俗。每一传统节日,包含着独特的民俗习惯。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以大量的笔墨表现了农历正月十五闹秧歌、“转灯”等过年的习俗。双水村人为迎接春节的到来,积极准备吃食,制作道具,彩排节目。节日当天,各村秧歌展开激烈的竞赛,本村人、外村人挤在一起,汇集成人海。打枣节是路遥小说中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这一天全村老少纷纷出门打枣,场面热闹非凡。路遥的故乡盛产红枣,并逐渐形成一项民俗节日。路遥将这一熟悉的物产所形成的民俗节日融进他的小说之中,作品显示出故乡特有的“土”味。路遥小说中的民俗事象丰富多样,它们共时存在又相互渗透,共同勾勒出一幅幅具有陕北特色的农耕文明图景,展现了陕北城乡宏阔的社会生活。
二.路遥小说民俗叙事的构建
1.作为环境描写辅助要素的民俗文化存在
在小说创作中,路遥将富有陕西特色的黄土高坡、川道、马兰花、红枣树等自然之物运用到小说的叙事之中,并进一步挖掘了窑洞、信天游、陕北方言的文化内涵,塑造了典型的陕北环境。
窑洞是黄土地独特的居住环境,亦是其独有的风景。在小说创作中,路遥笔下的窑洞是一个温馨的话语空间。孙玉厚一家只有一眼土窑,可尽管这七口之家一直生活在一个狭小破旧的土窑洞里,家庭人际关系依旧和谐。双水村的人们利用开会前的一点空余时间,常聚集在窑洞里拉家常,增进邻里关系。高原城的揽工汉挤在一口破窑洞里,喝酒,唱酒曲,讲述过往经历。路遥通过窑洞营造出了一幕幕温馨的生活情景,并进一步挖掘窑洞的隐喻功能,点出窑洞是贫富和贵贱差距的象征。在《平凡的世界》中,一条河将双水村分割成两个区域,田家圪在双水村的南边,金家在双水村的北边。“从住宿方面看,金家湾一带的窑洞明显比田家圪这面强……而且许多人家的土窑洞都接了石口……可细细一瞅,就可以看出当初做工的精细,并且还有雕镂的花纹,说明这门面曾经有过一时的显赫。”[3]在田家圪和金家湾隔河相对的自然景观中,暗含着两个不同姓氏家族居住条件的差异。孙玉厚一家在田家圪中穷得出了名,全家只有一眼土窑。少安开转窑获利后,重建一处院落:“一线三孔大窑洞,青砖砌口,还在窑檐上面戴了砖帽。”[4]孙家窑洞的变化,即孙家生活的变迁。孙少安新建了一处气派的院落,还成为双水村中第一个用砖接窑口的,意味着他从此和过去的屈辱诀别,自豪平等地站到人前。
在路遥的小说中,民歌始终贯穿小说的始终。信天游、陕北民谣、儿歌、链子嘴、唱酒曲等成为了表现生活、表达感情的手段和工具。路遥用民谣表达情人的悲欢,以信天游悲戚地呼号自然灾害,用链子嘴委婉讽刺“儿子养鱼不救父”。陕北民歌成了路遥小说中的诗意成份,营造出了诗意的氛围。陕北的信天游《冰冻歌》在《平凡的世界》中共出现五次,每次的出现都与田润叶有关。在初春的原西河边,润叶与心上人孙少安坐在草地上闲聊,一首信天游飘荡在原西河上:“正月里冰冻呀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5]这首信天游真实地映衬了润叶爱情萌动时羞涩而又着急的心情。润叶与少安相坐在双水村的河畔边,《冰冻歌》再次萦绕在山间。润叶得知少安结婚后独坐于原西河岸边、润叶的婚礼上以及婚后再次听到少安的消息时,这首信天游也都出現过。《冰冻歌》反复出现于小说中,映衬了润叶从甜蜜到痛苦的心路历程。
方言是地方民俗文化的载体,是民俗文化传承的活化石。路遥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具有黄土高原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作家用“圪”、“塄坎”、“山茆茆”、“跌水哨”、“崖坬坬”等大量方言词来呈现陕北的地形地貌;用“锅台”、“窗掌”、“脚地”、“灶火旮旯”来突显窑洞的建筑特征,以“脑畔、”“硷畔”、“门楼”来描述农村院落的特点等等。在艰难的环境下,孙玉厚老汉常感慨光景烂包,类似的俚语词如“穷家薄业”、“牺惶”、“受苦”等也较高频率地出现在小说中,贴切地反映了陕北人贫瘠的生存环境及艰苦的生活。除此之外,路遥还把陕北家庭成员关系的称呼运用到小说创作中,二爸、三爸、大爹、干大、二妈等地方性色彩的称谓增添了亲切可感的乡村气息。这些富有陕北地方特色的方言俗语营造出了浓郁的陕北生活气息,揭示了陕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精神。
2.作为人物塑造辅助要素的民俗文化存在
陕北民间文学历史悠远,神话传说样式丰富。县文化馆和新华书店里的杂志、画报,以及民间说唱艺术成为了路遥最初学习文艺创作的重要资源。陕北民间传说中的舜禹治世、赵连甫负薪孝母、韩世忠精忠报国等故事中的民间人物形象,成为路遥艺术创作的原型,由此塑造了一系列“当代英雄”的形象。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人物所具有不向挫折低头、勇于奋斗进取的精神与陕北英雄传说中英雄人物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路遥还巧妙地将民间传统故事中“英雄美人”的表现模式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中篇小说《人生》中所塑造的高加林形象与传统文学中“卖良心”的形象相比较,命运轨迹大致趋同:出身贫寒——公子落难,淑女钟情——情意缠绵,一朝得势——声名显赫,弃旧迎新——另觅佳配,公堂受审——前程断送。“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模式同样还出现路遥小说的其他作品中,孙少安与田润叶、贺秀莲的婚恋也存在类似的三角关系的模式,孙少平、郝红梅、顾养民之间的情感纠葛亦包涵着同样的原型。
路遥运用民俗文化塑造了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一系列典型形象,并以民俗心理来揭示“人”如何在极度生存困境与思想冲突中坚持理想主义精神和高贵的品格。高加林和刘巧珍打破传统的婚恋习俗,引来村民议论纷纷,而顺德爷爷的宽容和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深层民俗心理的评判,体现出自由爱情是陕北人民集体无意识中认同的心意民俗。高加林进城工作后,抛弃了巧珍,后因“走后门”被告发后,被迫再次返回农村。走进村子,对面山坡上传来了孩子唱的信天游:“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6]。这首古老的歌谣是陕北人对卖良心人的强力谴责,高加林的灵魂在自我谴责中获得了强烈的美感力量。《平凡的世界》亦通过民俗心理展现了陕北青年的内心活动。孙少平虽不迷信,但对新宅修建时的禁忌习俗却十分敏感;郝红梅在丈夫死后仍严格遵守一系列禁忌习俗;“逛鬼”王满银每到春节都要赶在除夕到来前回到家。小说透过民俗细节凸显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展现了转型时期青年的精神面貌。
3.作为故事情节展开辅助要素的民俗文化存在
在小说的结构上,风俗活动常常成为情节陡转的叙事信号。《走西口》是一首山西的爱情民歌,情感基调悲凉。在《人生》中,这首悲凉的民歌成为小说的结构框架,通过顺德老汉的反复吟唱,进一步烘托了高加林和刘巧珍复杂的心境,为二人的爱情悲剧埋下伏笔。路遥还充分利用“大马河桥”充当小说中城乡故事架构的连接纽带,将“大马河桥”设置于城乡的临界点上,进而将《人生》的整个故事情节展开于“大马河桥”上及其两侧的城乡场域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大马河桥”具有超越时空的象征意味,桥的一端象征着城市现代文明,另一端象征着农村传统文明。“大马河桥”在小说中共出现了七次,具有重要的意义,见证了高加林由“教师——农民——干部——农民”的身份转换,更是映衬其“回到农村——走进城市——回到农村”的人生转折。
路遥将陕北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元素巧妙地运用到小说的叙事之中,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感。他以大量的民俗元素来构建小说人物的活动空间,并以陕北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为原型,塑造了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借用民俗场景来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命运,凸显了改革开放初期陕北的城乡变化。
三.路遥小说民俗叙事的现实精神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旧的正在消失,新的正在建立。消失的还没消失,建立的也还没建立起来”,“不论生产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意识都处于过渡、转折、斗争、矛盾的状态”。[7]路遥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通过现实主义写作文本化了“历史”,在“交叉地带”建立起一种基于共同文化的新的生活想象。他用“社会书记官”的眼光和历史学家的笔墨,将国家大事转化为小说背景,“点穴式”串联起了故事情节,营造了宏大的时代氛围。路遥小说创作既从宏大的历史层面对生活进程展开全景式呈现,也从微观层面记录了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生活细节。小说通过描摹改革中民俗风情的“常与变”,展现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心态史。
路遥出生于陜北榆林清涧县,陕北的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及历史文化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家以物质民俗、人生礼仪民俗、节日民俗等构建起了典型的陕北生活环境,展现了陕北人的精神世界。小说中村庄院落、服饰衣着、饮食习惯、方言俗语、民歌民谣等民俗事项构成了一幅幅明净鲜明的陕北民俗画,镜照着陕北人的品质性格、生活习俗、思维特点、感觉方式。路遥还将社会的变化寓于民俗元素之中,以日常饮食、居住环境等物质生活的变迁进一步映现出“改革”中陕北人生活水平的提升,显扬了陕北人积极乐观、热情淳朴的精神品格。此外,路遥进一步以民俗仪式、民俗心理等塑造社会转型时期陕北青年的精神世界。《平凡的世界》中,少安与秀莲的婚礼凝聚了双水村中孙氏、田氏、金氏等多个家族,汇集了农民、村干部、汽车司机、教师等多种身份的人物,揭示出农村完成婚事的艰巨,显现了双水村互帮互助、互相体谅的文化传统。这些陕北民族的优良传统蕴藏于小说的民俗细节中,体现在人物的行动上。润叶深爱少安,得知少安结婚心如刀绞,萌生了让少安“把那姑娘打发走”,甚至想着“寻死上吊闹腾一番”,后而却让父亲代送贵重的“杭州锦花缎被面”作为礼物。仪式是小说表现人性美的重要契机,润叶的痴心和善良也通过少安的婚礼得到了深刻的表达。路遥通过民俗叙事表现了陕北青年的精神世界及人物情感关系中的困境,体现着路遥对陕北人精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
路遥继承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将个人化的生活经历提炼为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时代命题。“文学再现着人类的生活,折射着社会的发展历史,而民俗恰恰是人类生活以及社会发展历史中最深层、最隐蔽,也是最稳固的部分。”[8]路遥在个人生命体验的基础上,注入“罗曼蒂克精神”,以民俗叙事塑造出典型的社会环境和人物形象,表现出陕北广阔的社会变革。面对当前小说创作对现代化进城中的矛盾揭示力度不足,存在小说生活细节浮虚失真,底层形象呈现出扁平化、概念化等问题,回望路遥的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2
[2]张美兰.路遥故乡书写研究[D].赣州:赣南师范大学,2017:18-19.
[3]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6.
[4]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41.
[5]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3.
[6]路遥.路遥文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0.
[7]杨晓帆.路遥论.[M].作家出版社,2018:138.
[8]宋欢.民俗与小说的邂逅——论路遥小说中的民俗书写[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32.
(作者介绍:李静静,广西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