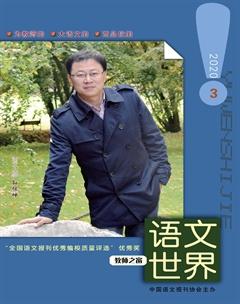诗缘情
叶水涛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对诗歌本体的不同认定。“志”与“情”紧密关联,但侧重点不同。在中国诗论的传統中,“诗言志”先于“诗缘情”,这或许与孔子的删诗有关。经他删定的“诗三百”成为“经”,它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与伦理期待,突出诗的教化作用。诗根植于“礼”,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伦理道德,“言志”说由此应运而生。但实际的诗歌创作和鉴赏中,诗比“情”的亲和性更强,《诗经》中大多数诗篇为抒情性作品。孔子也注重“情”,他提出诗歌的“兴观群怨”,“兴”便以情感因素为主。对此,朱熹从“感发”和“志意”两个方面作了阐述。“诗缘情”可以追溯到《毛诗序》,尽管它所说“情性”主要是指诗人的政治性情感,但这一命题毕竟指出了“情性”是诗歌创作的根本。
“缘情”说的首倡者是晋朝的陆机。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强调诗是缘情而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有情才有诗,无情便无诗,这是从诗歌写作的角度看。“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是从读者对诗歌接受的角度看。诗歌鉴赏主要不在接受道德教化,而是让自己的情感得到寄托。陆机所说的“绮靡”是指诗的审美特征,意即华美而悦人耳目。诗的特征在于美,不美就不是诗。不能给读者以美的感受,诗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因此,美对诗来说,同样具有本体的意义。“诗缘情”从“缘情”和“绮靡”这两个方面阐释了诗的发生与功能,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诗歌本体论的进一步发展。陆机所说的“诗缘情”之“情”与《毛诗序》的“吟咏情性”的“情”有很大的不同。陆机所说的“情”主要是诗人丰富复杂的审美感情,不是“止乎礼仪”的政治化感情。“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是为自然景象所感动的情,与《毛诗序》“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所包含的感情是不同的,前者是审美的感情,后者不是。
在中国古代,诗与乐是连在一起的,诗歌的合称正是体现了这一点。音乐是直接传达情感的艺术,因为声音的律动最为契合情感的律动乃至生命的律动。对此,《乐记》一书阐释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触动人心,人心动而形于声。如果赋予这种声音以美的形式,并演奏出来,这就是乐。乐之结合于言,这就是诗。诗合于乐的节律,能吟唱,这就是诗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诗缘情”更合于诗歌诞生的自然逻辑。诗缘情与诗言志,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情与志相同都是人的主体精神,孔颖达《五经正义》说:“情、志一也。”但情一般是指人对外物的感受和态度,志一般是指志向,或对某一目标的追求。前者审美感性的因素居多,后者功利的因素居多。邵雍《伊川击壤集序》云:“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由此可见,志在理性思考,情在审美感受。
“诗缘情”强调诗以抒发审美感情为本,这更符合古代诗歌的实际状况,大大扩展和丰富了古代诗歌本体的内涵,标志着一种新的诗歌美学原则的诞生。“诗缘情”这一命题在古代诗歌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就诗歌创作而言,缘情文学日益发达。魏晋时期,陶渊明、鲍照、庾信等均以抒情作品称著。宗白华先生说:“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鲁迅称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由晋陆机提出“诗缘情”说,绝非偶然。陆机之后的诗论家,大多都提倡“缘情”的诗学观。唐代以降,“缘情”说更是迅猛发展,成为诗坛的主流。“缘情”说预示着诗歌的发展方向,构成了后世诗歌创作发展繁荣的巨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