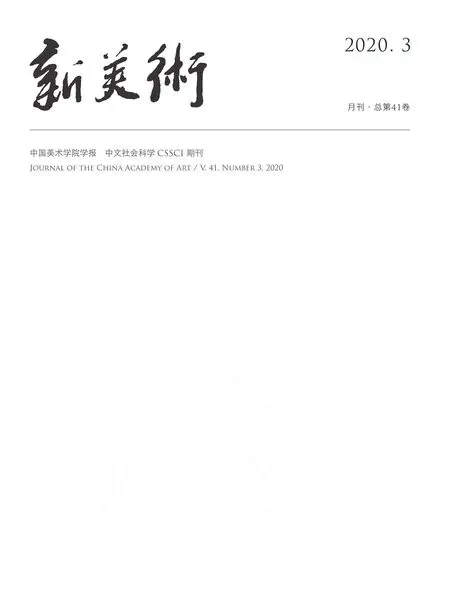徽宗朝官方的绘画史观 基于《宣和画谱》的考察
李方红
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记载:“自崇宁始命宋乔年掌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而继以米芾辈。殆至末年,上方所藏率举千计,实熙朝之盛事也。”1[宋]蔡绦撰,《铁围山丛谈》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78页。蔡绦文中所称颂的盛事即指徽宗内府所收藏的历代书画。这些内府收藏的历代书画在徽宗朝被著录成书,为后世留下了《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明代藏书家、刻书家毛晋(1599―1659)在回顾唐宋时期公私收藏的状况时,对《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评价到:“数百年来,惟宣和二谱足以当之。”2[明]毛晋撰,〈隐湖题跋〉,载丁福保、周云青编,《四部总录艺术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66页。毛晋的评论可谓精妙。徽宗以上古三代“圣王”之治为政治理想,追求在礼乐文化方面重现三代之盛况。在此政治理想下,内府收藏成为了徽宗朝文化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徽宗的主持下,内府古物、书画收藏的规模蔚为大观:“及宣和后,则咸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若岐阳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礼殿之绘像,凡所知名,罔问巨细远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储阁,咸以贮古玉、玺印,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尽在。”3同注1,第80页。保和殿是徽宗朝内府收藏的主要陈列场所:“藏祖宗训谟与夏、商、周尊、彝、鼎、鬲、爵、斝、卣、敦、盘、盂,汉、晋、隋、唐书画”4[宋]王明清撰,《挥麈后录·余话》卷一,中华书局,1961年,第278页。,徽宗亲自作《保和殿记》一文记录其用途:“左实典谟训浩经史,以宪章古始,有典有则。右藏三代鼎彝俎豆、敦盘尊罍,以省象制器,参于神明,荐于郊庙。东序置古今书画,第其品秩,玩心游思,可喜可愕。西夹收琴阮笔砚,以挥毫洒墨,放怀适情。”5陈均撰,《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中华书局,2006年,第709页。以上说明了徽宗朝在古物、书画收藏方面的规模。此外,徽宗敕令编撰了《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文献,入选的皆是内府古物、书画收藏中的精品。
《宣和画谱》是徽宗朝重要的绘画文件。其在《叙目》中论到:“因门而得画,因画而得人,因人而论世,知夫《画谱》之所传,非私淑诸人也。”6《宣和画谱》之《叙目》,元大德本,第3页。可知《宣和画谱》不仅是徽宗朝内府历代绘画收藏的目录清册,而且是徽宗朝藉以构建画史正统与谱系的重要载体,代表了徽宗朝对于绘画史的官方立场。因此,通过分析《宣和画谱》的编撰体例、画科分类标准、入选画家与品评等方面,可以较为深入的探讨徽宗朝官方的绘画史观。
一 《宣和画谱》的版本与作者
关于《宣和画谱》的版本问题,谢巍总结为古今版本二十二种7谢巍著,《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刘昕童对谢巍的总结逐一作了考证,并认为谢巍文中的宋刊本实为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吴文贵刻本。8刘昕童著,《〈宣和画谱〉校勘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4年,第22―27页。因此《宣和画谱》目前见存刻本、抄本、整理本等古今版本二十一种,散藏于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昌彼得认为《宣和画谱》历史上共有四个刻本,初刊于高宗时,今已不存,次刻于元大德六年(1302)吴文贵,三刻于嘉靖十九年(1540)杨慎,四刻于崇祯中毛晋,学津讨原本为清张海鹏翻刻的毛晋刻本。9昌彼得编,《跋元大德本〈宣和画谱〉》,台北故宫博物院,1971年,第 4页。韩刚认为《宣和画谱》共有五个刻本,分别是宣和二年(1120)成书后的刊本,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被昌彼得等人认定为元大德本;建炎、绍兴年间的次刻本,今已不见;三刻于元大德六年吴文贵版本,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认为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本的翻刻本;四刻于嘉靖十九年(1540)杨慎;五刻于崇祯中毛晋津逮秘书本。10韩刚撰,《〈宣和画谱〉宋元版本考》,载《美术与设计》,2016年第4 期,第1―6页。谢巍、刘昕童、昌彼得、韩刚等学者关于《宣和画谱》的版本问题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讨论,但就各版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目前还没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就目前所见《宣和画谱》的诸多版本中,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刻本时代最久、内容最精,也最为珍贵,被广泛选为《宣和画谱》的标准底本。毛晋所刻津逮秘书本,对于以前的刻本有所补益,但不知其所依底本为何。张海鹏的学津讨原本翻刻于津逮秘书本,只是对于其中的文字偶有校补。四库全书本以高拱刻本为底本,四库馆臣也进行了校勘增补。因此,对于《宣和画谱》的版本问题,我们认为现存最早的版本应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刻本,至于此本是宋刻本,还是元代大德年间吴文贵刊刻本,目前还无法做出明确的结论。
关于《宣和画谱》的作者问题,阮璞梳理了古今学者的论述总结为十种说法,而他自己则认为《宣和画谱》的作者是徽宗和其内臣。11阮璞著,《画学丛证》,上海书画出版,1998年,第160―165页。余绍宋认为《宣和画谱》:“与《书谱》同,当为宣和内臣奉敕编集者。”12余绍宋著,《书画书录解题》,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200页。阮璞认为余绍宋的结论“实为有识有据,自能成立”13同注11,第163页。,但是也批评“所惜余氏辨难两书撰人问题,无一字涉及姚大荣,似于姚氏之说未知闻见,对于相传两书撰人为宋徽宗一说,绝口不加可否。”14同注11。虽然余绍宋的考辨有诸多问题,但是余氏之说对后世学者影响颇深。昌彼得否认了周中孚、王毓贤、四库馆臣、余嘉锡等人的说法,并且从书中文词的应用和称谓等方面分析,得出结论:“自古帝王御制之书,固不必出自亲撰,大抵由臣工修纂,呈之乙览,而统观此书,前后辞气如一,悉出徽宗笔削点定,殆无疑义。”15同注9。在昌彼得看来,《宣和画谱》由徽宗朝群臣修撰,最终由徽宗修改定稿。金维诺认为“《宣和画谱》它实际上是在宫廷主持下,集中人力集体编撰的。”16金维诺撰,〈宋元绘画收藏著录〉,载《美术研究》,1980年第9 期,第69页。相比较于余绍宋、阮璞、昌彼得等学者的说法,金维诺肯定了《宣和画谱》为朝廷官方文献的性质,但是扩大了编撰人员范围。扩大编撰人员范围,可以为《宣和画谱》中文辞不一的现象做合理解释。倪根法认为“《画谱》的编撰很可能由徽宗挂名,内臣编定。”17倪根法撰,《〈宣和画谱〉的成书年代及与米芾的关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8 期,第82页。此说依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二中所记载中《画谱》前有“天子云”,并最后推测徽宗所作之序遗失。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 把《宣和画谱》的编撰归结为秘书省[Palace Library] 相关人员的本职工作:“They were also the ones who did much of the work on the catalogues of Huizong's collections.”18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8. p131.[ 他们还承担了徽宗藏品著录、整理的大部分工作。] 韦宾和张其凤对于《宣和画谱》的作者问题进行了学术争鸣。韦宾认为现存的《宣和画谱》只是宣和之前的御府绘画账目,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19韦宾撰,《〈宣和画谱名出金元说——兼论〈宣和画谱〉与徽宗思想无关〉,载《美术观察》,2006年第10 期,第103―107页。张其凤撰文20张其凤撰,《倡新说覆旧说当慎之又慎—就〈宣和画谱〉一文与韦宾先生商榷》,载《美术观察》,2007年第4 期,第97―103页。针对韦文的三条论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认为《宣和画谱》的作者是宋徽宗本人。此后张其凤又专门撰文21张其凤撰,《〈宣和画谱〉的编撰与徽宗关系考》,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年第4 期,第63―68页。,详细论证《宣和画谱》的编撰与宋徽宗的种种联系,用来夯实自己的结论。此外,还有多位学者22可参考陈传席撰,《〈宣和画谱〉的作者考及其他》,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 期,第89―91页;李永强著,《〈宣和画谱〉中的缺位―米芾》,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5―12页;陈谷香撰,《〈宣和画谱〉之作者考辨》,载《美术研究》,2008年第4 期,第42―47页。对于《宣和画谱》作者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论证,其结论皆有可参考之价值。
综上所述,关于《宣和画谱》作者问题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考据学派的学者,注重版本、文献等问题;一类是现代理论派学者,关注的焦点是绘画理论、用语、思想等问题。我们认为《宣和画谱》成书于宋徽宗时期,其作者未必是徽宗本人,但是其编撰目的、动机、准则和框架等则出于徽宗本人无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是宣和内臣、宣和群臣、秘书省文臣、宋乔年、米芾或者其他具体撰写,都只不过是徽宗思想的忠实记录者而已。
二 《宣和画谱》的内容与性质
《宣和画谱》共二十卷,卷首有《叙》和《叙目》共两篇。《叙》论述了绘画的历史、意义与功能,并在最后交代了构成本谱的主要内容:“晋魏以来名画,凡二百三十一人,计六千三百九十六轴,析为十门。”23《宣和画谱》之《叙》,元大德本,第2―3页。《叙目》论述了各门分类原则和画家入选标准和绘画数量,具体分为:道释门四十九人,一千一百七十九轴;人物门三十三人,五百五轴;宫室门四人,七十一轴;番族门五人,一百三十三轴;龙鱼门八人,一百一十七轴;山水门四十一人,一千一百八轴;畜兽门二十七人,三百二十四人;花鸟门四十六人,两千七百八十六轴;墨竹门一十二人,一百四十八轴;蔬果门六人,四十二轴。在《宣和画谱》二十卷中,各门的具体分布卷数如下:道释门第一至四卷,人物门第五至七卷,宫室门、番族第八卷,龙鱼门第九卷,山水门第十至十二卷,畜兽门第十三至十四卷,花鸟门第十五至十九卷,墨竹门、蔬果门第二十卷。
具体到每一门,基本的编写顺序是:首先是本门《叙论》,主要论述本门的意义和画史谱系;接下来是按照历史顺序,以朝代为单位罗列历代画家名称;最后是具体的历代画家小传。在画家小传部分,主要包括画家籍贯、师承、技艺、品评、内府收藏画目等内容。在已有的著作中,以四库馆臣和谢巍所作《提要》最为详细,四库馆臣考察《宣和画谱》画家排列顺序有不同的情况,认为是由“作谱之时乃分类排纂其收藏之目,则以时代先后为差”24四库馆臣《宣和画谱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致,谢巍对于《宣和画谱》画家小传的史料价值,认为“颇有前人画史不载之资料,宋代宗室诸家之传,犹可征信”25同注7,第164页。,以上都是中肯之论。综合考察《宣和画谱》的内容,可知其画史知识有两部分来源:其一是已成书的画史,如《历代名画记》《圣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等;其二是宋代宗室资料,如赵宗汉、赵仲佺、赵令松、宗妇曹氏等人的史料。
关于《宣和画谱》的性质,一般认为是徽宗内府绘画收藏的目录清册。但是《宣和画谱叙》中对此有所阐述:“乃集中秘所藏者晋魏以来名画,凡二百三十一人,计六千三百九十六轴,析为十门,随其世次而品第之。”26同注23。可知在编撰者的构架中,《宣和画谱》具备两个基本的功能:一是内府绘画收藏的目录清册,即“中秘所藏”;二是构建画史与谱系,即“世次而品第”。后人对于《宣和画谱》这两个功能的认识并不统一,如吴文贵在《宣和画谱》大德本跋中认识到此本“乃当时秘录”27[清]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载《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九),中华书局,2006年,第600页。,这侧重于目录清册的功能。明人对于《宣和画谱》的认识较吴文贵有所进步,如《内阁藏书目录》中记载:“《宣和画谱》六册全,宋徽宗编次,有御制序。自孙吴以至赵宋共二百三十一人,人为一传,总十家,工道释者四十九人,人物三十三人,宫室四人,番族五人,龙鱼八人,山水四十一人,畜兽二十七人,花鸟四十六人,墨竹十二人,蔬果六人。”28同注2,孙能传、张萱撰,《内阁藏书目录》卷七,第166页。这表明晚明的孙能傅、张萱等人意识到《宣和画谱》并非单纯的内府绘画收藏著录,并且注意到其中“人为一传”的特色。《宣和画谱》的这一特色明显不是单纯的绘画收藏清册,而是具有画史意义的著作。
美术史进入现代学术体系后,学术界对于《宣和画谱》性质的认识更加丰富。郑午昌认识到《宣和画谱》“关于画品及画学者”29郑午昌著,《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第243页。的历史价值。但是,从郑午昌著作《中国画学全史》中“宋代画迹”30同注29,第190―204页。一节可知其主要侧重于《宣和画谱》的史料价值,更确切的说是其中宋徽宗内府绘画收藏清册的史料价值。郑午昌对于《宣和画谱》的使用和认识具有典型性,其对于《宣和画谱》中画迹采用统计学的方法也启发了后来相关的学术研究31参考伊沛霞撰,〈宫廷收藏对宫廷绘画的影响:宋徽宗的个案研究〉,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3 期,第105―113;刘昕童著,《〈宣和画谱〉校勘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4年,第64―68页;张钫撰,《画者的博物学:基于〈宣和画谱〉的考察》,载《美术与设计》,2017年第4 期,第9―13页。。伊沛霞认为: “ Much like the antiquities and calligraphy catalogues,thePainting Cataloguewas a select list,not a full inventory of the paintings in the palace.”32同注18,p260.[ 与《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相似,《宣和画谱》也只是一个经过选择后的内府绘画收藏的部分藏品名目,而不是全部藏品清单。]伊沛霞在认定《宣和画谱》是内府绘画收藏的部分清单后,试图进一步从所收录的各门类绘画作品的数量差异中探讨徽宗本人的绘画观念和政治文化意图。即便如此,伊沛霞仅对《宣和画谱》中的画迹作统计学上的分析,并没有解决徽宗本人的绘画观念和政治文化意图与《宣和画谱》中各门类绘画作品的数量是否存在对应关系。陈韵如把《宣和画谱》看成是徽宗朝官方绘画活动的指导准则,讨论官方对于绘画所持有的观念。33陈韵如著,《画亦艺也:重估宋徽宗朝的绘画活动》,台湾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21―55页。虽然陈韵如关注到《宣和画谱》的画科分类意义,但是并没有分析其中所涉及的画史观念的重构。刘昕童观察到《宣和画谱》中的叙目、每一门类前的叙述模式与宋代官修《崇文总目》有相似之处,认为“《宣和画谱》作为艺术类著录书,能够继承同时期目录书体例的精华是非常难能可贵的”34同注8,第65页。。但是刘昕童仍把《宣和画谱》作为宋代官方的绘画著录作品,只是认识到其在编撰体例中借鉴了目录学的知识。
《宣和画谱》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宋内府绘画收藏的名单清册,而是宋徽宗藉以重塑画史传统与谱系的工具和载体。徽宗在继位之初具有雄心勃勃的政治追求,锐意恢复神宗时期的新法,更是在崇宁三年(1104)批准新法领袖王安石配享孔庙,在颁布《故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廷诏》中论到:“其施于有政,则相我神考,力追唐虞三代之隆。因时制宜,创法垂后,小大精粗,靡有遗余。内圣外王,无乎不备。”35《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584页。徽宗努力营造的三代圣王气象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也涵盖了文化领域。他继承了王安石新法中关于学校教育的改革,掀起了“崇宁兴学”风潮。徽宗藉由学校改革把画学纳入到“崇宁兴学”的体系中,有意识、有系统地提升绘画的地位,使之成为“六艺”之一,并成功跻身于徽宗朝的文化领域中。在徽宗的政治理想中,绘画是其恢复三代圣王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兴办画学是从审美风尚、绘画实践的层面贯彻徽宗的绘画思想,而编撰《宣和画谱》是从画史传统、师资传授谱系的层面彰显官方立场。因此,画学和《宣和画谱》是徽宗朝绘画改革中相辅相成的两面,最终服务于徽宗朝在绘画领域所确立的权威地位。
三 《宣和画谱》的画史观念与谱系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宣和画谱》是徽宗朝重塑画史正统与谱系的工具与载体,体现了徽宗朝官方的绘画史立场。因此,《宣和画谱》具有重要的画史意义,是分析徽宗朝画史观念与立场的重要文献。《宣和画谱》的《叙》《叙目》、各门《叙论》及对入谱画家的品评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徽宗朝官方绘画史观提供了分析文本。
《宣和画谱》在开篇的《叙》中述说绘画之源流,其论述方式、基本观点和用语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源流》相同:如关于绘画起源的传说,都是河出图、洛出书;又如《叙画之源流》中的论述“周宫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36[唐]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卷一,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120页。,在《叙》中变为“至周官教国子以六书,而其三曰象形,则书画之所谓同体者,尚或有存焉”37同注23,《宣和画谱》之《叙》,第1页。;再如在论述绘画的教化功能时,《叙画之源流》中的论述是“成教化,助人伦”38同注36。,《叙》中的表述为“明礼乐,着法度”39同注37。,所论述的含义完全相同。即便如此,《叙》中还是点明了编撰此书的现实目的,即:“今天子廊庙无事,承累圣之基绪,重熙浃洽,玉关沉柝,边燧不烟,故得玩心图书,庶几见善以戒恶,见恶以思贤,以至多识虫鱼草木之名,与夫传记之所不能书,形容之所不能及者,因得以周览焉。且谱录之外,不无其人,其气格凡陋,有不足为今日道者,因以黜之,盖将有激于来者云耳。”40同注37。这充分显明了《宣和画谱》所服务的政治目的以及蕴含的文化意义。
接下来的《叙目》具体处理《宣和画谱》的编撰事宜。首先是各门的分类标准,《叙目》中明确是依照司马迁《史记》“先黄老而后六经”41同注6。的传统,解释了道释门列为诸篇之首的原因。在一一论述完十门意义后,《叙目》总结了编撰原则:“凡人之次第,则不以品格分,特以世代为后先,庶几披卷者因门而得画,因画而得人,因人而论世,知夫画谱之所传,非私淑诸人也。”42同注6,第4页。以此表明《宣和画谱》的权威和意义在于“非私淑诸人”的绘画正史传统和“因门而得画,因画而得人”的绘画师资传授谱系。《叙目》再次显明了编撰《宣和画谱》的政治目的以及蕴含的文化意义。
既然徽宗朝编撰《宣和画谱》的目的在于重塑画史传统和谱系,那么入谱画家的选择就具有明显的画史意义。《宣和画谱》各门《叙论》中都涉及到了本门画家的谱系和优劣品评,其重塑画史的意图非常明显。本文以《叙论》中所涉及的画家为标本,按照门类逐一分析,用以论述徽宗朝官方的绘画史观。
《宣和画谱·道释叙论》中论述:
自晋宋以来,还迄于本朝,其以道释名家者,得四十九人。晋宋则顾、陆,梁、隋则张、展辈,盖一时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矣。至于有唐,则吴道元(玄)遂称独步,殆将前无古人。五代如曹仲元,亦骎骎度越前辈。至本朝,则绘事之工,凌轹晋宋间,人物如道士李得柔,画神仙得之于气骨,设色之妙,一时名重,如孙知微辈,皆风斯在下。然其余非不善也,求之谱系,当得其详,姑以著者概见于此。若赵裔、高文进辈,于道释亦籍籍知名者。然裔学朱繇,如婢作夫人,举止羞涩,终不似真。文进蜀人,世俗多以蜀画为名家,是虚得名,此谱所以黜之。43《宣和画谱》卷一,元大德本,第1―2页。
道释门画史追溯至晋宋时代,在所涉及到的画家中,按照朝代顺序,依次是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展子虔、吴道玄、曹仲元、李得柔、孙知微、朱繇、赵裔、高文进,其中褒扬了本朝(宋)的道士画家李得柔,贬低了朱繇、赵裔、高文进三人。
《宣和画谱》对道释门的画史传统和谱系进行了重塑。就五代以前的画史传统,《宣和画谱》更多的是继承,只是重塑了入宋后的这段画史。在入宋后的画史中,道释门重点突出道士画家李得柔,认为是本朝第一。《宣和画谱》卷四中对于李得柔的介绍充满了神怪色彩,重点突出了他的道士身份,具体到其绘画技艺,被称为是“不学而能”44同注43,卷四,第20页。的天才,这与论述吴道玄“六法俱全,万象必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45同注36,第124页。的语法非常相似。《宣和画谱》在专门叙述李得柔生平的具体条目中特意把吴道子关涉其中,体现了其延续画史谱系的意图。因此,在道释门重塑的画史传统中李得柔传承自吴道子,在此唐宋谱系得以接续。
从道释门贬低的画家中,亦体现出了《宣和画谱》的画史意图。道释门中把朱繇、赵裔、高文进列入贬低的行列,其中对高文进的贬低最为严重。虽然同受贬低,朱繇还是入选了《宣和画谱》,并且对其绘画评价颇高,认为其画艺“妙得吴道元(玄)笔法”46同注43,卷三,第5页。,达到了“妙造其极,而时出新意,干变万态,动人耳目”47同注43。的高度,同时引用武宗元的评价进行左证。赵裔作为朱繇的学生,也在此处提及:“(朱繇)弟子赵裔,亦知名一时。”48同注43。由此可见,朱繇、赵裔只是道释门贬低高文进的引子。
高文进在北宋初年即名声显赫,随蜀主孟昶降宋,后进入翰林图画院,其画深受太宗赏识,后被委以“搜访民间图画”49[宋]郭若虚撰,《图画见闻志》卷三,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479页。的重任。高文进的师承在《图画见闻志》中有清楚的记载:“工画佛、道,曹、吴兼备。”50同注49。郭若虚文中的曹、吴具体指曹弗(不)兴、吴道玄。曹弗兴、吴道玄是《宣和画谱》构建画史谱系中的重要成员,高文进画艺传承曹、吴,足以说明其画史谱系的正宗。况且太宗又十分赏识高文进的绘画,屡屡委以重任。高文进在主持重修相国寺期间亲自绘制相国寺大殿后璧及殿西的壁画,并且成为“画院学者咸宗之”51同注49。的精品,这也足以说明高文进绘画技艺的高超和在画院中的影响力。虽然从画史师资传授谱系、画艺、影响力等方面来看,高文进都十分优秀,但是《宣和画谱》却罢黜不录,并且作为贬低的典型。这其中的原因,即是“文进蜀人,世俗多以蜀画为名家,是虚得名,此谱所以黜之。”52同注43,第2页。由此可知,贬低高文进意味着《宣和画谱》不承认道释门画史中的西蜀传统,目的是破除“世俗多以蜀画为名家”的旧有画史观念。
《宣和画谱·人物叙论》中论述:
故自吴、晋以来,号为名手者,才得三十三人。其卓然可传者,则吴之曹弗兴,晋之卫协,隋之郑法士,唐之郑虔、周昉,五代之赵岩、杜霄,本朝之李公麟。彼虽笔端无口,而尚论古之人,至于品流之髙下,一见而可以得之者也。然有画人物得名,而特不见于谱者,如张昉之雄简,程坦之荒闲,尹质、维真、元霭之形似,非不善也,盖前有曹、卫,而后有李公麟,照映数子,固已奄奄,是知谱之所载,无虚誉焉。53同注43,卷五,第2页。
人物门《叙论》中所构建的画史脉络中,李公麟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宋代人物画的高峰。《叙论》甚至把张昉、程坦、尹质、维真、元霭等人不能入谱的原因都归结为李公麟的艺术光芒掩映其中,使上述五位画家黯然失色,故不入谱。
《宣和画谱》人物门把李公麟置于如此重要的画史地位,基于两点:其一是其绘画技艺之高超;其二是李公麟的士大夫身份。关于李公麟的绘画艺术,《宣和画谱》对其描述的最为详尽,说他学画初始即临摹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并且集众家之长为己所有,然后自成一家,这从画史师资传授谱系方面中完成了构建。至于李公麟具体的画艺:“尤工人物,能分别状貌,使人望而知其廓庙、馆阁、山林、草野、闾阎、臧获、台舆、皂隶。至于动作态度,颦伸俯仰,小大美恶,与夫东西南北之人,才分点画,尊卑贵贱,咸有区别,非若世俗画工,混为一律,贵贱妍丑,止以肥红瘦黑分之。大抵公麟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其成染精致,俗工或为学焉,至率略简易处,则终不近也。盖深得杜甫作诗体制而移于画。”54同注43,卷七,页11―12页。上述引文重点突出了李公麟画艺中的两个特点:其一是精准把握物象形似之后突出表现物象的神似,即以形写神的能力;其二是把诗歌与绘画有机联系起来,重点表现画中的诗意,即“作诗体制而移于画”55同注43,第12页。的能力。
李公麟的士大夫身份亦是《宣和画谱》关注的重点。《宋史》中记载:“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第进士,历南康、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用陆佃荐,为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测款识。”56《宋史》卷四四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25页。从正史的角度来看,李公麟具有北宋士大夫身份所具备的一切文化因素,进士出身、有官宦经历、博学、能作诗文、好古物、精辨识。《宣和画谱》中也注意到这一点:“文臣李公麟,字伯时,舒城人也。熙宁中登进士第。父虚一,尝举贤良方正科,任大理寺丞,赠左朝议大夫,喜藏法书名画。公麟少阅视即悟古人用笔意,作真行书,有晋宋楷法风格。绘事尤绝,为世所宝。博学精识,用意至到。”57同注54,第 10―11页。从中可知《宣和画谱》在叙述李公麟的身份中与《宋史》的关注点是一致的。
北宋中期以来,士大夫逐渐参与到绘画创作和理论构建领域,深度影响了绘画的发展。士大夫阶层借助书画收藏、鉴赏及创作不断地重构画史传统与观念,并以此推动绘画风格的更新。徽宗在潜邸时因王诜、赵令穰的原因深度接触了士大夫绘画的观念,并且对此观念有相当程度的认可。李公麟作为士大夫画家,其画艺远承魏晋正统,又符合北宋晚期的绘画审美趣味,这正是人物门把其列为画史传统中重要一员的根本原因。另外,人物门推崇李公麟也侧面说明了徽宗朝认同士大夫关于绘画的观念和实践。徽宗朝借助于李公麟入谱,把相关的绘画观念上升为国家正统,以此建构皇室在绘画发展中的权威,并达到重塑人物门画史正统和师资传授谱系的文化目的。
《宣和画谱·宫室叙论》中论述:
粤三百年之唐,历五代以还,仅得卫贤以画宫室得名。本朝郭忠恕既出,视卫贤辈,其余不足数矣。…自唐五代而至本朝,画之传者得四人,信夫画之中,规矩准绳者为难工,游规矩凖绳之内,而不为所窘,如忠恕之髙古者,岂复有斯人之徒欤?后之作者,如王瓘、燕文贵、王士元等辈,故可以皂隶处,因不载之谱。58同注43,卷八,第1―2页。
宫室门画史传统中以卫贤、郭忠恕为中心,尤其是郭忠恕。另外还特别贬低了王瓘、燕文贵、王士元三人。
在宫室门构建的画史正统中只有卫贤、郭忠恕两人。《宣和画谱》中对于卫贤的论述十分简略,只是说明其为江南李氏朝廷的内供奉,南唐君主曾在其绘制的《春江图》上题《渔父词》。59同注43,第6―7页。从其绘画与词相配这一点中可知卫贤的绘画有诗意,这种创作风格符合北宋晚期的绘画审美趣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卫贤是京兆人。60详情参考[宋]刘道醇撰《五代名画补遗》;[宋]郭若虚撰,《图画见闻志》中的相关记载。京兆即是长安,是唐代的核心地区。虽然卫贤事南唐,但是其绘画传统亦可以看成是唐代传统,加之卫贤的画艺符合北宋晚期的审美趣味,因此宫室门把其收录其中,只是评价上要稍逊本朝(宋)的郭忠恕。《宣和画谱》中记载郭忠恕以明经科中第,太宗迁为国子博士,擅篆隶,喜画楼观台榭。郭忠恕符合北宋晚期对于画家身份与修养的标准,加之其画艺高古,足以比肩卫贤。更为重要的是《宣和画谱》认为郭忠恕的绘画“如韩愈之论文”61同注58,第9页。,这种论述与评价李公麟的绘画有杜甫诗体制如出一辙。
至于王瓘、燕文贵、王士元三人,皆因皂隶出身而不得入谱。检索整本《宣和画谱》,发现王士元出现在山水门。考察《宣和画谱》对于王士元的记述,可知他是王仁寿的儿子,画艺兼学诸家之妙,人物师周昉、山水师关仝、屋木师郭忠恕,最后评其山水画是:“其风韵则高于关仝,其笔力则老于商训”62同注43,卷一一,第26页。。王仁寿、周昉、关仝、郭忠恕都是《宣和画谱》所录之人。单从画艺的角度考察,王士元家学、师承都符合《宣和画谱》的要求,因此被录入山水门可谓得当。至于王士元的身份,《宣和画谱》记载其为“郡推官”63同注62,第25页。。推官在宋代的品位为从八品64参考龚延明编,《宋代官制词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544页。。从官品上看,《宣和画谱》把其归为“皂隶”行列是合理的。宫室门对于入选画家有身份要求,因此王士元被罢黜宫室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王士元因着师承关系符合《宣和画谱》的画史谱系要求,而被幸运选入山水门。
王瓘、燕文贵则没有王士元那么幸运。纵观《宣和画谱》之前的画史记载,王瓘“家甚贫困”65[宋]刘道醇撰,《圣朝名画评》卷一,载卢辅圣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447页。、燕文贵“隶军中”66同注65,第452页。且无任何职务,可知二人皆出身贫贱。但是《圣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对于王瓘、燕文贵的画艺评价颇高:如对于王瓘人物画的评价是:“观其意思纵横,往来不滞,废古人之短,成后世之长,不拘一守,奋笔皆妙。诚所谓前无吴生矣,故列神品上”67同注65,第447页。;再如对于燕文贵山水画的评价是:“不师于古人,自成一家,而景物万变,观者如真临焉。画流至今称曰燕家景致,无能及者。”68同注65,第453页。从中可知二人的画艺高超,但是没有具体的师承谱系,因此不能像王士元一样归入《宣和画谱》的其他门类。
综上可知,宫室门入选的第一标准是画家的师资传授谱系,第二标准是画家的身份,其中画家谱系最为重要。郭忠恕完美符合第一、第二标准,因此可以作为本朝(宋)代表,王士元只符合第一标准,因此根据其画艺高低,相应录入山水门。至于王瓘、燕文贵,二人不符合上述两条标准,即使画艺再高超,甚至达到了“自立一家规范”69同注49,卷四,第482页。的高度,同样不被纳入《宣和画谱》所构建的画史中。
《宣和画谱·番族叙论》中论述:
今自唐至本朝,画之有见于世者凡五人。唐有胡瓌、胡虔,至五代有李赞华之流,皆笔法可传者。…后有髙益、赵光辅、张戡与李成辈,虽驰誉于时,盖光辅以气骨为主而格俗,戡、成全拘形似而乏气骨,皆不兼其所长,故不得入谱云。70同注58,第11页。
番族门重点强调了李赞华,点出了其“系出北虏,是为丹东王”71同注58。的身份,并评价其画艺是“笔法可传”72同注58。,以此树立其番族门画史正统的地位。至于本门贬低的画家,主要是从画艺的角度出发,要么是格调不高,要么是缺乏气骨。
北宋在与辽代的对峙中,始终具有优势地位的是文化事业,《宣和画谱》专门设置番族门,并且把李赞华列为正统,说明徽宗朝在绘画领域把辽代纳入到自己的话语体系中,进一步强化宋王朝的正统地位。因此,《宣和画谱》专门设置了番族门,并且把丹东王列为此门的画史正统,表明徽宗朝放弃以前“陋蛮夷之风,而有以尊华夏”73同注58。的历史观念,力图实现“古先哲王未尝或弃”74同注58。的文化事业。
《宣和画谱·鱼龙叙论》中论述:
本朝董羽,遂以龙水得名于时,实近代之绝笔也。…五代袁嶬,専以鱼蟹驰誉;本朝士人刘寀,亦以此知名,…若徐白、徐皋等辈,亦以画鱼得名于时,然所画无涵泳噞喁之态,使人但埀涎耳,不复有临渊之羡,宜不得传之谱也。75同注43,卷九,第2页。
鱼龙门在构建画史谱系时强调了本朝(宋)董羽和刘寀。关于董羽的记载,以《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最为详细,两书的记载内容相似,可以肯定《宣和画谱》的内容来源于《图画见闻志》。
董羽江南毗陵人“事伪主李煜为待诏,后随煜归京师,即命为图画院艺学”76同注43,第8页。,专门画龙,画艺传自吴曹弗(不)兴,达到了“实近代之绝笔”77同注75。的高度。因此从画史谱系和画艺上考虑,董羽入谱是合适的。至于刘寀,则是构建画鱼谱系的关键。《叙论》强调了刘寀的士人身份,对于其画艺并没有涉及。考察其后的徐白、徐皋,《叙论》贬低的原因是“不复有临渊之羡”78同注75。,足以说明刘寀的士人身份是其入谱的关键。鱼龙门如此处理,也呼应了其对于“鱼龙之作,亦《诗》、《易》之相为表里”79同注75,第1页。的总体认识。
《宣和画谱·山水叙论》中论述:
至唐有李思训、卢鸿、王维、张璪辈,五代有荆浩、关仝,是皆不独画造其妙,而人品甚髙,若不可及者。至本朝李成一出,虽师法荆浩,而擅出蓝之誉,数子之法,遂亦扫地无余。如范宽、郭熙、王诜之流,固已各自名家,而皆得其一体,不足以窥其奥也。其间驰誉后先者凡四十人,悉具于谱,此不复书。若商训、周曾、李茂等,亦以山水得名,然商训失之拙,周曾、李茂失之工,皆不能造古人之兼长,谱之不载,盖自有定论也。80同注43,卷一〇,第1―2页。
北宋是山水画发展的高峰,郭若虚甚至评价北宋李成、关仝、范宽三家山水是“三家鼎峙,百代标程”81同注49,卷一,第469页。。不同于郭若虚的“三家山水”的画史构建,《宣和画谱》山水门独尊李成,北宋其他山水名家则被评价为“皆得其一体,不足以窥其奥”82同注80,第2页。的下李成一等。
山水门构架画家谱系的原则是:“自唐至本朝,以画山水得名者,类非画家者流,而多处于缙绅士大夫。”83同注80,第1页。即以“画家者流”和“缙绅士大夫”来分类,属于身份界定。如此一来,不难理解《宣和画谱》中把李成描述成一个儒者,而非画家。在山水门《叙论》中李思训、卢鸿、王维、张璪、荆浩、关仝、李成皆属于缙绅士大夫行列。这些从事绘画的缙绅士大夫“人品甚高”84同注82。,且“胸中自有丘壑”85同注43,卷一二,第10页。,因此才能达到“画造其妙”86同注82。的境地。
至于次李成一等的范宽、郭熙、王诜等人入谱,从构建画史的角度而言甚为合理。《宣和画谱》认定范宽“山水始学李成”87同注62,第10页。,郭熙“取李成之法”88同注62,第19页。,从师资传授的谱系考察,范宽、郭熙皆是李成传派。虽然二人身份在画史中界定的不慎明显,但是二人画艺高超,范宽被以往的画史认定为“三家鼎峙”之一家,并且郭熙服务于神宗朝画院,其绘画深得神宗喜爱。至于王诜,其身份画艺皆符合入谱之标准,关于王诜的身份,《宣和画谱》有详细的介绍,其画艺“皆李成法”89[宋]邓椿著,《画继》卷二,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706页。。在《宣和画谱》构建画史的标准中,王诜具有完美的身份,但是其画艺没有达到一流的水平,故此以李成之一体的面目入谱。在《宣和画谱》的画史观念中,专门从事绘画的“画家者流”,如商训、周曾、李茂等人自然没有资格进入这个新构建的画史传统和谱系。
《宣和画谱·畜兽叙论》中论述:
粤自晋迄于本朝,马则晋有史道硕,唐有曹霸、韩干之流;牛则唐有戴嵩与其弟戴峄,五代有厉归真,本朝有朱嶬辈;犬则唐有赵博文,五代有张及之,本朝有宗室令松;羊则五代有罗塞翁;虎则唐有李渐,本朝有赵邈龊;猫则五代有李霭之,本朝有王凝、何尊师。…而包鼎之虎,裴文睍之牛,非无时名也,气俗而野,使包鼎之视李渐,裴文睍之望戴嵩,岂不缩手于袖间耶?90同注43,卷一三,第2页。
畜兽门所涉及到的画家皆是马、牛、犬、羊、虎、猫等科,其在画艺上具有一定的传承性,符合画史构建的谱系要求,至于包鼎、裴文睍被排除,则因为其画艺“气俗而野”91同注43。。这里没有强调画家的身份,而是看重其师资传授的谱系。
《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论述:
自唐以来,迄于本朝,如薛鹤、郭鹞、边鸾之花,至黄荃、徐熙、赵昌、崔白等,其俱以是名家者,班班相望,…若牛戬、李懐衮之徒,亦以画花鸟为时之所知,戬作《百雀图》,其飞鸣俯啄,曲尽其态,然工巧有余,而殊乏髙韵;懐衮设色轻薄,独以柔婉鲜华为有得,若取之于气骨,则有所不足,故不得附名于谱也。92同注43,卷一五,第2―3页。
花鸟门构建了一个从唐至宋“班班相望”的画史谱系,即薛稷、郭干晖、边鸾、黄荃、徐熙、赵昌、崔白。在《宣和画谱》的画史顺序中,薛稷、郭干晖、边鸾皆属于唐代,黄筌属于五代,徐熙、赵昌、崔白属于本朝(宋)。至于被贬低的牛戬、李懐衮,则被认为徒有其名,其画艺缺乏气韵,格调粗俗。
考察鸟门所构建的画史,基本呈现了一种由名家过渡到师资传授谱系的趋势。薛稷、郭干晖、边鸾、黄荃、徐熙皆是名家,赵昌、崔白这过渡到风格谱系上。在这个名单中,黄筌最为特殊,从风格谱系上看,黄筌的花鸟画风格继承薛稷等唐代名手,风格谱系纯正,且其子黄居寀事其家学,其画法成为“自祖宗以来图画院一时之标准”93同注43,卷一七,第3―4页。。花鸟门《叙论》只字不提黄居寀,直接过渡到赵昌,说明了徽宗朝对于黄筌所传承的风格谱系并不认同。徽宗朝认为黄筌的风格谱系是:“祖宗以来,图画院之较艺者,必以黄筌父子笔法为程序。”94同注43,卷一八,第15―16页。显然,徽宗朝对于翰林图画院花鸟画中充斥的黄筌风格程序化的现象十分不满。至于黄筌本人的画艺,《宣和画谱》的论述是:“用意为至,悉取生态”95同注43,卷一六,第7页。。这是一个较为中肯的评价,也是决定黄筌位列花鸟门“班班相望”名单的关键因素。
花鸟门《叙论》把赵昌列为本朝(宋)风格谱系的真正开端。赵昌擅折枝花鸟,郭若虚认为其画“传彩旷代无双”96同注49,卷四,第484页。,《宣和画谱》更是认为其画“不特取其形似,直与花传神”97同注94,第2页。。可知赵昌的花鸟画风格不同于黄筌、徐熙,而是在二人的基础上自成一格。《宣和画谱》花鸟门把赵昌列入重要地位,一方面是其画艺具有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是为崔白、吴元瑜风格谱系的构建提供了合理基础。崔白、吴元瑜对于北宋花鸟画风格的发展有革命性意义,《宣和画谱》认为“自(崔)白及吴元瑜出,其格遂变”98同注94,第16页。。崔白的风格探索建立在赵昌的基础之上,并且教导出了一位出蓝之与的徒弟-吴元瑜。《宣和画谱》记载:“(吴元瑜)善画,师崔白,能变世俗之气所谓院体者。而素为院体之人,亦因元瑜革去故态,稍稍放笔墨以出胸臆。画手之盛,追踪前辈,盖元瑜之力也。”99同注43,卷一九,第6页。同样,吴元瑜也有一位出蓝之与的徒弟—宋徽宗。蔡绦记载徽宗“时亦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100同注1,卷一,第6页。,而徽宗的画艺则是“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101同注89,卷一,第704页。这说明了徽宗在崔白、吴元瑜的风格谱系中取得了高超的进步。
综上所述,花鸟门风格谱系的构建主要体现在本朝(宋),即赵昌、崔白、吴元瑜、徽宗。至于黄筌、徐熙,虽然不承认其风格谱系,但是肯定了他们的画史贡献,并在构建画史传统中给予了他们一席之地。
《宣和画谱·墨竹叙论》中论述:
画墨竹与夫小景,自五代至本朝,才得十二人,而五代独得李颇,本朝魏端献王頵、士人文同辈,故知不以着色而专求形似者,世罕其人。102同注43,卷二〇,第2页。
墨竹门不见于之前的画史,是《宣和画谱》首创的门类。对此,墨竹《叙论》的解释是:“(墨竹、小景)往往不出于画史,而多出于词人墨卿之所作,盖胸中所得,固已吞云梦之八九,而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故一寄于毫楮。”103同注43,第1页。从中可知,在《宣和画谱》的观念中,此门是词人墨卿的专属领域。因此,墨竹门的画史构建集中在画家的身份,而不在于画艺,贬低画家自然也无从提及。作为《宣和画谱》首创的绘画门类,由于其绘画历史短暂,《叙论》甚至都没有构建其画家谱系。
《宣和画谱·蔬果叙论》中论述:
且自陈以来至本朝,其名传而画存者,才得六人焉。陈有顾野王,五代有唐垓辈,本朝有郭元方、释居宁之辈。…如侯文庆、僧守贤、谭宏等皆以草虫果蓏名世,文庆者,亦以技进待诏,然前有顾野王,后有僧居宁,故文庆、守贤不得以季孟其间,故此谱所以不载云。104同注102,第18―19页。
蔬果门的情况与墨竹门相似,也是《宣和画谱》首创的绘画门类。与花鸟门相似,蔬果门被认为是“诗人之作”105同注102,第18页。,因此强调画家的人文素养。顾野王“七岁读五经,九岁善属文,识天文地理无所不通”106同注102,第20页。,说明其有深厚的人文修养。蔬果门以画家的人文修养为标准构建画史,既没有强调画家的身份,也不关注画家的画艺,甚至都没有提及画家谱系,这是《宣和画谱》画史构建中的特殊情况。
结论
通过对《宣和画谱》十门《叙论》中所涉及到的画家分析,《宣和画谱》入谱画家标准基本遵循以下三条原则:其一是画家的师承谱系;其二是画家的身份;其三是画艺的高低。除了蔬果门之外,上述三条原则贯穿于《宣和画谱》整个的画史构建中。在画家师承谱系方面,以承接魏晋以来的画史师资传授传统为宗旨,力图在画家师承谱系中构建一个魏晋至唐宋的画家名目。绘画在北宋中后期成为士大夫自身文化修养的重要部分,经过宋迪、文同、李公麟、苏轼、米芾等人的努力,人们对于绘画的认识从偶尔的自娱活动,变成了堪比建功立业的不朽之事。徽宗朝注意并认同了这种绘画观念的转变,因此在重构画史传统的过程中格外重视画家的身份属性。在画家身份的界定中重点关注画家的王公贵胄、文人士大夫身份,甚至画家的画艺都要让步于这一原则。具体到画艺的高低,其评判以高古、气韵生动、形神兼备、表达诗情画意为标准。需要指出的是,《宣和画谱》所构建的画史并非完全符合画史史实,而是在上述三条原则的指导下,根据绘画门类的特征和以往的画史做了相应的调整和侧重,这重点体现在各门《叙论》中所贬低的画家名单中。
在《宣和画谱》十门《叙论》中,另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对于各地方割据政权的态度。《宣和画谱》的编撰以树立徽宗朝画史正统为宗旨,并且有选择地把五代各割据政权的画家纳入其中,重新构建魏晋以来的画史传统和谱系,以此彰显徽宗朝在文化传承上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在画家谱系的选择中,能够比较客观的看到五代各割据政权的绘画成就和杰出画家,并且有意识的把北方契丹族画家纳入其中。总体来说,《宣和画谱》肯定南唐绘画风格,并把其画家纳入本朝(宋)谱系中,但是对于西蜀绘画风格,却是有意贬低,导致许多西蜀名家惨遭罢黜。不管是肯定南唐传统、贬低西蜀传统,还是接纳契丹族画家,甚至是专辟日本国一节,都是为彰显北宋中央王朝的文化正统和权威服务的。
通过编撰《宣和画谱》,徽宗朝重构了画史正统和师资传授的谱系,确立了官方的绘画史观和审美倾向。从北宋晚期的绘画发展的历史视角考察,《宣和画谱》不仅代表了徽宗朝官方的绘画史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北宋晚期私人的绘画观念。考察后世的画史著作,《宣和画谱》中的某些编撰标准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公私画史的写作。
——《宋代徽宗朝宫廷绘画研究》评介
——以《诗馀画谱》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