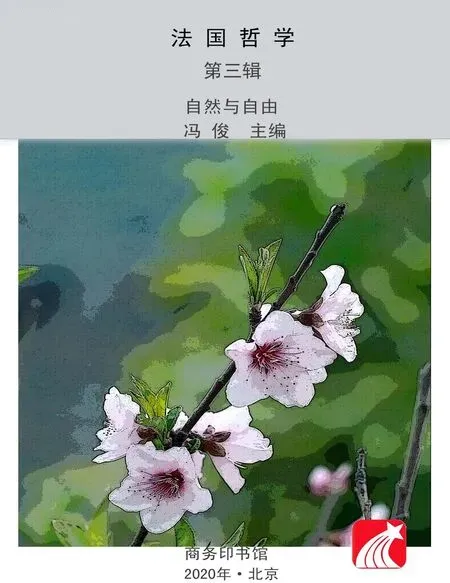亨利生命现象学中的被动性概念*
崔伟锋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被动性概念是法国精神哲学传统的重要概念,米歇尔·亨利批判性地继承了并以现象学为基础发展了这一传统。通过改造曼恩·德·比朗(Maine de Biran)等人的被动性概念,亨利提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被动性,并且通过把被动性与现象学的自行给予概念结合起来,发展出自己的生命现象学理论。亨利的生命现象学是在批判性继承和发展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上完成的,围绕着胡塞尔的质素(Hyle)的意向性构造问题,亨利提出一种以非意向性感受为基础的生命自我感发现象学。
一、作为“非我”的“质素”
感觉材料或质素概念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最早在《算术哲学》和《逻辑研究》中,胡塞尔便已经开始使用“patimäre Inhalte”(第一性的内容)来讨论原初给予的感觉材料的意义。他使用“‘Stoff’(材料)、‘感觉材料’、‘Empfindungsinhalte’(感觉内容)来指代纯粹意识中发生的对诸如颜色、触觉、声音一类的素材(Daten)以及愉快、疼痛和瘙痒一类的感觉(Empfindungen)的感性体验(sinnliches Erlebnis)”①方向红:《时间与存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1 页。。由于这些概念包含着意向性体验与非意向性体验意义的混淆,所以胡塞尔用质素概念专门表示“不带有意向性的纯粹的感觉材料……而带有意向性特征的一切感觉材料或内容被归于感性(Sinnlichkeit)”②同上书,第104 页。。这一区分在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中极其重要,由此可以划分“质料现象学”和“意向活动现象学”。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感觉”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在狭义的“感觉”意义上,“感觉”概念对应的是外感知的感性材料或感觉材料,“感受”对应的是内感知的感觉材料。两个概念具有结构性相似,都是作为感知的构成部分或展示性部分在起作用。“外感知是统觉,因而概念的统一性要求内感知也是统觉。…… 这间房屋显现给我—我以某种方式对现实地被体验到的官能内容(感觉内容)加以统摄。……与此完全相同,我统摄地感知我的心理现象,感知那激动着‘我’的喜悦,心中的悲哀等等。它们都叫做‘现象’,或者更好是叫做显现的内容,也就是统觉内容。”③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第237 页。作为内感知的“感受”与外感知的“感觉”具有类似的结构:“每一个感性感受,如灼热的疼痛与被灼,……感觉在这里是作为感知行为的展示性内容而起作用,或者感觉在这里经历了有关对象性的‘立义’或‘释义’。因此它们自己不是行为,但行为是用它们构造起来的。”④同上书,第431 页。在《逻辑研究》阶段,感觉和感受的展示性结构是相同的,都是行为的组成部分或组成内容,作为“材料”都要被“形式化”或“立义”。
在《观念一》阶段,胡塞尔把感觉材料看作是“纯粹体验”的“材料部分”,即感知体验的实项(reell)组成部分,感觉材料本身是不带有意向性的,它与意向相关项、意向活动一同构成了现象学还原之后的剩余物。在《观念一》第85 节,胡塞尔区分了两种意义的体验:第一种是作为“初级内容” 的不具有意向性的感觉或感受材料。例如,外感知意义上的颜色感觉材料、触觉感觉材料和声音感觉材料等“感觉内容”;内感知意义上的感性的快乐感、痛苦感、痒感以及“冲动”范围的感性因素等,它们都属于初级内容这个属。需要注意的是,在《观念一》中,胡塞尔把外感知意义上的感觉材料和物自身的显现因素或客观特性严格区分开来,不像在《逻辑研究》中那样,对感觉材料的处理比较含糊,把感觉材料既看作一种主体状态,又看作一种事物的客观特性。这样就可以避免自然态度的前设。第二种是带有意向性特征的体验或体验因素,这些意向性的体验是使“初级内容”的感觉材料“活跃化”或“给予意义”的附加层次。①崔伟锋:《原初给予与内在生命—米歇尔·亨利的生命现象学》,载高宣扬主编:《法兰西思想评论·2016(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8 页。可以看到,感觉材料需要通过意向体验的激活才能显现自身,它的给予方式也没有得到直接的说明,对它本身的认识也必须通过反思的抽象考察,即在反思中才可以被具体化。所以对质素的分析始终面临着陷入无限倒退的危险。②在《时间与存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方向红详细分析了在《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之前胡塞尔的质素概念所面临的问题。参见方向红:《时间与存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第106 页。
质素概念构成了胡塞尔时间现象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到《C 手稿》,胡塞尔开始专门对质素难题进行研究。在《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中,质素是“以未变样的方式为纯粹源初给予性意识(原在场所意识到的)所意识到的”③关于质素问题的详细分析,参见上书,第97—114 页。。但是在质素的给予过程中,质素的给予并不在自我的可控范围之内,质素的给予以一种“强加”的方式给予自我,这是一种“非自我性的”(nichtilichlich)或“对自我陌生的”(ich-fremd)①关于此问题,参见方向红:《时间与存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第109 页。。作为一种“非自我”之物,质素如何又是“被意识到的”呢?或者质素如何内在于体验并且隶属于主体?“自我”和“非我”似乎构成了一种主客二分的对立。胡塞尔通过“原活当下”(urlebendige Gegenwart),即原印象、滞留和前摄的时间意识构造活动,以及原素本身的构成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胡塞尔并不把非我与自我看作是毫无关系的对立存在,非我仍然是一种“主体”,是一种自我不曾察觉到的自动完成的构造,这一过程“处于不清醒状态(Unwachheit)中,处于完全的‘无意识’(Unbewusstsein)中,处于无主动性(Aktlosigkeit)中”②同上书,第113 页。。通过区分不同位阶的自我或主体,胡塞尔把这种“非我”看作是自我的“匿名形式,史上未被唤醒的、最低阶的状态”。③同上。可以看到,自我的存在样式有主动性自我和被动性自我两种,“非我”是一种主体的被动性存在样式,而不是超越于主体的外在存在者,否则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就会陷入自然态度或经验主义心理学的困境。
如果胡塞尔把主体划分为不同的层次,那么这种最低位阶的主体(“非我”)如何显现或构造自身?或者质素作为一种“原活当下”的内在体验,它的显现方式具体是如何显现的呢?是反思的方式或者抽象的方式,亦或是意向性地被构造为对象而显示。亨利进一步追问这种原初体验的显现方式,最终发现了一种绝对内在性的自行给予,一种作为最低阶主体的生命。亨利的探讨在批判胡塞尔的意向性现象学的基础上完成,但是更多的是受到了胡塞尔的启发。亨利对胡塞尔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前期的《逻辑研究》、《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和《观念一》阶段,如果亨利有幸读到胡塞尔后期的《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等文本,便会发现他的思路和胡塞尔后期思路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差异性。
二、 以根本被动性方式进行自行给予的生命
亨利认为生命的本质是一种自行呈现(auto-révélation)或自行给予(auto-donation)的根本内在性,生命的自行呈现是一种自行感发(autoaffection),即一种根本的被动性(passivité)。亨利指出被动性是一种不超出自身,不变成非自身,从而设定他者的一种自行给予、自行呈现的本质。生命的存在形式便是这种最根本的被动性,生命的原初存在和显现不超出自身。同时,生命还构成了显现的本质,是显现得以可能的先天条件。亨利所理解的生命自身的自行呈现、自行给予不单纯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同时还具有身体主体的实践行动意义—生命是一种内在于肉身的主体性存在。通过身体主体的自行显现,亨利赋予被动性一种本体论含义:主动性和被动性没有任何本体论差异,二者只是身体主体原初存在的两种模式。
1.肉身生命
在《身体现象学与哲学》中,亨利区分了三种意义的身体:
(1)主体性身体的原初存在,即在运动的先验内在体验(expérience internetranscendantale)中被呈现的绝对的身体。这个原初身体就是主体性的绝对生命;在这个原初身体中,我们生存,我们运动和感觉。
(2)器官的身体。它是承载主体性身体运动的运动者,即身体的某个部分,也可以说它就是运动得以进行的所有肢体部分的整体。
(3)客观化的身体。它是外在知觉的对象,并且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传统哲学所能认识到的唯一的身体,正是这种独断的客观性概念带来了身体与精神统一的困境。①Michel Henry, Philosophie et phénoménologie du corps: 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 Paris: PUF,pp. 179-182.
主体性身体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原初自行呈现,它是一个内在性意义上的先验主体,而不是超越性或者意向性意义上的先验主体,也不是经验主体。主体性身体是一种能够自行显现的生命主体,生命的显现方式不同于存在者的显现方式。前者的给予方式是内在的,后者是超越的。①亨利区分了两种现象:世界的现象和生命的现象。两种现象的显现方式是不同的,前者以超越的方式完成,后者以内在的方式完成。
在《显现的本质》序言中,亨利指出他对身体的理解不同于胡塞尔和梅洛—庞蒂。他认为肉身生命不是一种意向性和超越性的对象:“身体性是一种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当下感受(pathos immédiat),它在身体朝向世界之前就已完成。正是这种原初的身体性保存了身体的各种基本的能力,如作为一种力量(force)或行动(agir),习得各种习惯,自我记忆—正是以这种方式,身体摆脱了各种表象”②Michel Henry, Philosophie et phénoménologie du corps: 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 p. V.。在《观念二》中,胡塞尔把身体看作是一种“我能”意义上的感觉构造的中心,身体是感觉定位或行动的支撑者,它通过被动给予的方式构成了意识自我的构造性背景。亨利认为身体在胡塞尔那里还未获得本真的主体性意义。梅洛—庞蒂已经认识到身体的特殊性,并赋予身体主体性的地位,肉身性主体构成了一个精神与物质的辩证交织的存在领域。但是亨利认为,梅洛—庞蒂没有从根本上澄清身体主体自身的绝对内在性本质。③亨利没有像梅洛—庞蒂那样把身体主体的本质看作是一种意向性的身体,而是看作一种非意向性的根本内在性。
在亨利看来,真正的主体性身体理论拒斥传统的身体与心灵的二分,它是“主体性的普遍本体论的最初应用”④Michel Henry, op.cit., p. 308.。从胡塞尔到梅洛—庞蒂再到亨利,一种内在性的身体现象学理论被建立,主体不再被单纯看作是“纯粹意识或者抽象的主体性”⑤Ibid., p. 268.。通过一种内在性的身体性现象学,亨利才可以说“我就是我的身体的生命,自我是身体机体的实质”⑥Ibid., p. 174.。
在生命主体的存在论意义上,绝对身体与器官身体的区分是一种现象学的区分,而不是实体性的区分。器官身体“在一种绝对知识中被给予。因为它是我们绝对身体意向性的非表象的严格对象,它一直是被整体呈现给我们,并且我们在一种排斥所有限制和所有错误可能性的知识中拥有它”①Michel Henry, Philosophie et phénoménologie du corps: 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 p. 269.。所以器官身体不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表象对象,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整体给予,是同一性意义上的自我的物质承担者。自我的具体化(concrétisation)在身体的运动或行动中呈现,这是一种属于主体性的绝对内在性的领域。器官身体从属于主观身体,而主观身体通过器官身体的运动得到具体的呈现。这种关系就像是斯宾诺莎的实体与样态之间的同一两面的辩证关系。绝对身体拥有绝对的自由,即使是受外界刺激的被动性反应也是一种自由的样态,因为绝对身体完全依赖于自身而存在,并且在自身的绝对性中完成自行显现。②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指出“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反之,凡一物的存在及其行为均按一定的方式为他物所决定,便叫做必然或限制”。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 页。
亨利关于器官身体与主体身体关系的思想来源于比朗。亨利认为,比朗那里不存在行动哲学与思的哲学的区分,比朗的哲学是一种行动的本体论理论,他的原创性和深刻性不在于把我思看作是一种“我能”,而是看作一种行动或运动。行动和运动的存在便是我思本身。通过这种方式,行动和运动的存在便属于主体性的绝对内在领域。③Sébastien Laoureux, L’immanence à la limite: recherches sur la phénoménologie de Michel Henry,Paris: Cerf, 2005, p. 124.或者说,身体的运动即是身体对自身的认识,运动不是一种介于自我与世界的中介,也不是一个工具。在笛卡尔那里,我思只能认识我思对象的观念,因此“我思的笛卡尔式特征迫使我们只能承认观念的现实性,即欲望的观念、行动的观念、运动的观念”④Michel Henry, op.cit., p. 71.。不同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把身体的观念看作是主体的现实性存在,比朗把身体的现实性存在看作是主体性的存在。借助于比朗的身体哲学,亨利尝试把身体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统一起来。①在一定程度上,思想和广延两种属性截然区分的传统框架,特别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对意识对象的观念性存在的偏重,限制了胡塞尔对身体主体性内涵的进一步发掘。在胡塞尔那里,是否存在一种纯粹意识的现象学本体论,以及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进行具体分析。
在胡塞尔那里,现实的我思是一个意识体验流,一种内在知觉。胡塞尔在讨论内时间意识问题时,已经注意到纯粹意识体验流的原初存在性。但是亨利认为,胡塞尔的滞留概念预设了一个时间体验与主体性的现象学距离(distance phénoménologique),因为对自我的把握一直是一个被意向性指向的对象,纯粹主体一直被遮蔽。相对于这种可见的意向性主体,生命主体是一个不可见的绝对内在性。生命以自我感发的方式自行呈现,并在这种显现中不预设任何显现与自我的分离。相对于客观性身体在视域中的偶然性的给予方式,主体身体构成了一种摆脱视域给予方式的绝对给予或绝对存在的领域,即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绝对内在性给予或存在。绝对身体“不以侧面的方式给予,因为它绝不是超越的,也不是通过现象学距离与我们分离”②Michel Henry, Philosophie et phénoménologie du corps: 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 p. 269.。所以,主体身体是主体性的现实性:“主体性是实存的,身体是主观的。”③Ibid., p. 261.在胡塞尔那里,作为“非我”的质素始终面临着如何通过原初“绝对意识”被构造的难题,无论是在其早期《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等文本,还是后期的《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中,这一问题一直是十分棘手的问题。但是可以看到,胡塞尔越来越关注一种前—自我的领域,即一种被动流逝的原过程的意向性领域④关于这一问题,参见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肖德生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81—483 页。。亨利也是聚焦于此问题,实现了对胡塞尔的继承和发展。
生命自我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而是通过器官身体的实存性存在,成为具有实项性内容的肉身性生命。在身体主体的意义上,主体的现实性与自我实现了统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器官身体才可以避免被还原掉,最终只剩下纯粹意识。身体与我思都属于绝对主体性的存在领域,二者一同构成了一个先验内在领域。用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的同一两面论来理解,前者是一种实存性的实现方式,后者是一种观念化的实现方式①亨利的硕士论文(Le bonheur de Spinoza)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开端,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一些思想家的解读(特别是L. Brunschvicg),他认为斯宾诺莎的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关于亨利与斯宾诺莎思想的关联,参见Jean-Michel Longneaux, Le bonheur de Spinoza suivi de Etude sur le spinozisme de Michel Henry, Paris: PUF, 2004。。
我的身体性在身体意向性之前存在,这不同于胡塞尔的意向性主体,也不同于梅洛—庞蒂的身体的当下意向性(intentionnalité immédiate)。在亨利看来,“身体的本体论现象学,主体运动的理论和它与器官身体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行动的理论,以及身体性行动的理论”②Michel Henry, Philosophie et phénoménologie du corps: 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 p. 204.。身体的原初给予在其行动或运动完成,并且这种给予是一种原初的内在性给予,而不是超越性的给予,身体通过自身的运动构成了一个原初的存在领域。
生命现象的显现方式是一种自行显现,自行感发(auto-affection)是生命自行显现的本质结构。在亨利看来,生命是一种绝对主体,生命的自行感发不预设任何条件,它本身便是自行显现的可能条件。所以在自身为自身显现奠基的意义上,生命就是显现的本质。生命构成了一个可以自行呈现的原初可感性(passibilité)领域,这种原初的可感性不是纯形式上的,而是具有现实性内容的感受性。亨利特别批判了把生命的给予方式解读为一种意向性给予,提出构建一种非意向性的现象学的构想。③关于亨利的《非意向性现象学》,参见米歇尔·亨利:《非意向性现象学:未来现象学的一个任务》,崔伟锋译,《世界哲学》2016年第4 期。
2.生命自行呈现的被动性
亨利区分了两种被动性:
(1)与主动性对立的被动性,实存(ontique)意义上的被动性;
(2)原初本体论(ontologique)意义上的被动性,即主体的自我认识。④J. Leclercq, “Éditorial”,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Michel Henry, n°2: Inédits sur l’expérience d’autrui,Presse Universitaire de Louvain, décembre 2010, Ms A 5-10-3071.
亨利认为原初本体论被动性是一种更高位阶的被动性,它为实存意义上的主动和被动的对立统一结构进行奠基。主体的存在领域并不是行动(action),而是一种采取行动(agir)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在面临抵抗(résistance)的限制中努力(effort)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亨利把生命自行感发意义上的原初感受性看作是一种根本的被动性(passivité),即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被动性。这种根本的被动性是生命自行呈现本质的根本特征,是生命在自行呈现中自我创造、自我扩展的一种可能性。原初被动性意义上的自行给予是生命存在的本质或者生命存在的必然性①亨利的“被动性”概念受到从比朗开始的法国精神哲学(spiritualisme français)传统(Cousin,Ravaisson、Lachelier、Paul Janet 和Bergson)的影响。参见Grégori Jean, “Habitude, effort et résistance: Une lecture du concept henryen de passivité”, in Bulletin d’analyse phénoménologique VIII 1,2012 (Actes 5),pp.455-477。。作为一种根本被动性的能力,生命的自行感发表现为一种“我能”(je peux)。作为一种肉身的“我能”,它包含了自我不同层次的行为,如布伦塔诺意义上的表象行为、判断行为、情感或意志行为。肉身性的“我能”便是意识行为和身体行为的统一体,但是意识行为和身体行为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二者还有交织在一起的难以区分的区域。所以在“我能”的意义上,自我便是它的各种能力,即一种实践意义上的我能。作为一种实践,生命的自行呈现是生命自身意志能力的体现,这种意志能力根源于生命在原初被动性中的自我保存、自我发展。
被动性是生命自身存在的本质,我们不可以拒绝这种自行感发意义上的生命感受。例如某些痛苦的体验以一种“强迫性”的方式呈现,即使我的理智性的我思不断“拒斥”它,想要停止这种强迫式的给予,但是仍无济于事。这是由生命自行感发的自行呈现本质导致,所以主体性在亨利那里又具有了被动性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主体的“我能”感受是一种理性我思的“我不能”拒斥这种感受,但是在亨利那里,生命主体和理智主体不是同一层次的二元主体,理智主体的“我不能”是一种意向性意义上的,是一种外在性的“我不能”,其中存在着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离。理智主体只是生命主体的一种存在样态,后者构成了前者的本质或者可能性条件。
这与胡塞尔的先验我思的主动构造性意义上的主体性不同。在发生现象学中,胡塞尔已经注意到意识原初发生的被动性结构,“觉醒在于对某物的观看。被觉醒概念要表达的是:实际地经受一个感发(affection)”①Edmund Husserl, Expérience et jugement, tr. fr. D. Souche-Dagues, Paris: PUF, 1991, pp. 92-93.。在《被动综合分析》中,胡塞尔把感发看作是被动性中的否定性的注意(attentionnégative),在被动性中,我们完成了对象性的重构,被动性构成了自我主动性的背景,“从背景的被动性出发,感发指向了自我,它们是观看意向的前提”②Edmund Husserl, De la synthèse passive, tr. fr. P. Jean-François et M. Richir, Grenoble: Millon, 2004, p. 12.。胡塞尔指出原素和作为绝对先验自我的“自我极”之间存在一种“绝对的接近”关系,这种“绝对的近”(dieabsolute Nähe)使得“我们在‘原素’节中把‘原自我’和‘原非我’看作是原活当下中彼此交织无法区分的两个源泉”③方向红:《时间与存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第131 页。。被动感发构成了一个原初给予的领域,胡塞尔那里的作为背景的被动性给予被亨利理解成生命主体自身的存在。
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为我们进一步分析主体性问题或自我意识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理性主体与意识主体的同一性在胡塞尔现象学中被建立,或者说理性主体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自身的意识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在胡塞尔那里得到了说明。斯宾诺莎把自由看作是人运用理性对情感的控制和引导暗含了理性与自由的“联姻”。在这个意义上,情感主要构成了人的被动方面的性质。但是也需要指出的是,斯宾诺莎区分了主动情感和被动情感:“对于这些情状中的任何一个情状,如果我们能为它的正确原因,那么我们便认为他是一个主动的情感,反之,便是一个被动的情感”④引自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 页。。被动的情感“是当人的心灵具有混淆的观念或被外在的原因所决定而引起的情感”,主动的情感是“当人的心灵具有正确的观念、心灵是主动时所出现的情感”⑤同上。。如果在身心二元论的意义上理解情感,把情感看作是一种从器官身体发生并阻碍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存在,那么情感就构成了理性主体的被动性存在。
亨利关于世界的现象和生命的现象的区分是一种实存论和本体论的区分。存在者的显现只能在一个视域中实现,存在者的显现构成了对我们的感发,但是这种显现是一种实存论感发(affectionontique),它预设了一个本体论感发(affectionontologique),并且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基础。在亨利看来,意向性意识现象学不能从根本上澄清生命的自行感发的情感性本质。情感性构成了生命自行显现的各种样态(modalité),感发性决定了主体各种情感的现象学样态。
三、生命自行显现的本体论意义
在《物质现象学》中,亨利批评了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的印象性(impressionnalité)概念。他认为胡塞尔的印象概念缺乏一种真正的现象性(phénoménalité),因为它预设了一种意向性去实现自身,为了澄清时间意识的主观性本质,胡塞尔把原初意识(conscienceoriginaire)看作是印象并且赋予滞留一种优先的地位。相对于印象和前摄,滞留的特殊性在于在主观时间内意识中解释了时间的起源,并且滞留可以解释对象意识的同一性如何在被动联想(associationpassive)中实现。同时,为了解释时间意识的延展性特征,胡塞尔提出了纵意向性概念(l’intentionnalité longitudinale)。亨利认为,在这种解释框架中,印象作为现在(maintenant)的原初意识被给予,但是它在自身中包含了一个即将消逝的过去,它不断远离自身。
在亨利看来,印象的自行给予便是生命自身不间断的在活的当下(présent vivant)的自行显现。理解意识的印象性本质的困难内在于静态的描述现象学,这也是胡塞尔转向发生现象学的原因之一。同时,亨利认为印象的本质不是由出离的时间性(temporalité extatique)所规定,而是由生命自身持续的当下自行给予所规定,否则会用作为被构造者(constitué)的印象替换原初意义上的作为构造者(constituant)的印象。在出离的时间性结构中,印象变成一种滞留,而不是原初的印象,印象也丧失了自身作为绝对存在的含义。印象原初给予性的丧失也让其成为意识形式的质料性内容。
在亨利看来,生命是在时间流中的持存自身的在场,生命在自行显现的原初印象中持存。生命在持存的自身存在中自我体验和自我感知,它绝不脱离自身,不与自身设定任何距离①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matérielle, Paris: PUF, 1990, p. 53.。在持存但又不断消逝的当下(présent)体验流中,生命以一种自我转化和自我发展的方式实现了自身本质②在胡塞尔那里,先验自我是否内在于时间意识流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此问题的分析,参见方向红:《时间与存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第126—127 页。。同时,亨利认为身体在原初存在的意义上“逃脱了时间”,身体“与自身的分离不是通过前摄和滞留”,即“主体身体的原初存在不是建基于记忆”,相反是身体构造了“这些心理能力的基础”,因此身体是作为一个构成者而不是被构成者存在,身体的统一性“内在于我们的本体论知识”。③Michel Henry, Philosophie et phénoménologie du corps: 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 pp. 138-140.
作为绝对主体的肉身性生命,生命的自行显现表明了一种“绝对认识”(savoir absolu)。绝对认识指的是“肉身绝不与我们脱离,并通过我们时刻感受到的各种形式的痛苦与快乐的印象与我们的皮肤紧密结合”④Michel Henry, Incarnation: une philosophie de la chair, Paris: Seuil, 2000, p. 9.。在Incarnation中,亨利指出身体的知识是一种“绝对认识”,在其中“不存在知识和行动的分裂,因为在它的自身本质中,它就是自身,即一种知识”⑤Michel Henry, Philosophie et phénoménologie du corps: 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 p. 276.。在亨利看来,“我拥有一个身体”这个命题并不是把身体看作一个工具或对象,而是“我就是我的身体”,这种身体与自我的同一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一个必然的事件。在理智主义哲学中,身体的行动主要被理解成为实现“目的”的“方法”概念。这与理智主义哲学偏重理论性知识和表象性知识有关,同时也与它主要把主体理解成意识或精神意义上的理智主体有关。如果把身体行为或行动看作是一种“绝对知识”,那么知识与行动之间就不会存在一种绝对的分裂。任何行动都构成了一种“主体性的本质”,即行动是“一种绝对主体性生命的模式”①Michel Henry, Philosophie et phénoménologie du corps: 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 p. 279.。
亨利把身体看作是一种绝对知识与他的本体论现象学思想有关,他把关于“自我的结构的理解看作是本体论知识的存在和结构;本体论知识的存在特征,即自我的存在特征,便是身体的存在;最终,实现了本体论知识与身体自身的本体论本质的同一”②Ibid., p. 79.。通过把主体看作一种肉身意义上的生命,亨利建立了精神与物质的辩证法,两种不同的属性在生命主体的原初存在中实现了统一。精神与物质就像是生命这一实体的两种属性,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
亨利尝试建立一种绝对主体性的本体论现象学去澄清主体作为一种生命的本质。他认为“主动性和被动性不是别的,正是同一个身体主体原初存在能力基础的两个不同的样态”③Ibid., p. 226.。在后期,亨利把现象学与基督教结合起来,根据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区分了大写的生命(la Vie)和小写的生命(la vie),两种生命对应强的意义上的自我感发和弱的意义上的自我感发。在有限性的意义上,人的生命来源于上帝的自行显现,人的生命被大写的生命创造。大写的生命作为上帝的自行显现,是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得以生成或显现的最终依据,整个世界都是上帝大写生命的自行显现,所以整个宇宙都是一个具有生命的宇宙。亨利把意向性意识对世界的物质性的形式化显现拉回到了物质性的自身存在,让世界的物质性重回到自身④亨利明确提出“物质现象学”的概念,主张把“现象学问题彻底化”,追问物性自身显现的方式。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杨大春:《现象性与物性》,《哲学研究》2013年第11 期。。在生命现象学的意义上,生命主体的自行显现是一种质料与形式的统一。主体的自行显现便是一种对自身被动性有所领悟的绝对知识,也是一种不通过自我异化来实现的必然性认识。根本的被动性构成了生命存在的必然性,生命在自身存在的必然性中发现了自身存在的自由。生命自己为自己设定界限,自己规定自身,使界限或规定转化为自身存在的本质,而不是外在于自身的限制性因素。
四、小结
如果用本体论、认识论的框架分析亨利的生命主体概念,可以发现生命作为一种原初显现,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使得显现得以可能的先天条件,而且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正是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性条件使得生命的自行显现不落入直观现象学的对象化、外在化困境。
由于生命主体表现为自我的不同层次的行为,所以亨利认为胡塞尔把自我完全还原成纯粹意识是存在问题的。在胡塞尔的意向性现象学中,意识的意向性本质结构制约了胡塞尔对意识的存在本质的讨论①需要指出的是,在《逻辑研究》之后,胡塞尔认识到直观代现理论在解释体验流的统一性或无限性时所面临的实显性困境,所以他尝试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时间体验的绝对存在性特征,“即一个在时间体验的关联相位的流逝综合中被刻画的前感知立义的体验流”。关于此问题的详细分析,参见马迎辉:《胡塞尔与柏拉图:一门思的哲学何以可能?》,《学海》2017年第4 期。。不同于心理学等其他科学对现象的探讨,现象学是一种对现象给予方式进行探寻的科学,即对主体性自身进行探寻的科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是一门主体性哲学。从笛卡尔开启以“我思”为核心或基础的现代哲学开始,哲学把“我思”和“我在”联系起来。亨利尝试通过建构一种本体论现象学,澄清生命作为显现的本质如何完成了现象学与本体论的统一。
如果说生命的自行显现是一种根本的被动性,那么这种被动性就是生命自行显现的必然性本质。在自身的现实性中,生命主体建立起思想、行动的辩证法。对行动而不是对作为行动的概念重视是亨利从谢林那里继承来的,亨利所理解的生命自行感发意义上的自行呈现也与谢林的“绝对同一性”思想相关。
在生命的自行感发结构中,感发者和被感发的内容是同一的,不存在任何“现象学的距离”和“外在性”。生命的自行显现便是显现的本质,它的自行显现不会需要任何可能条件。它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内在显现,因为“内在的本质与它的内容是同一的”,也就是说“内容的存在论现实性与本质自身的存在论现实性既不分离,也没有差异” 。在感发性(affectivité)中,感发者与被感发者的同一性找到它的实存的、实项的,而不是理论的可能性,以及它的现象学实现的现实性(effectivité)。在它的根本内在性的绝对充分条件下,感发性把事物与自身联系起来,并把这种自我联系区别于其他外在性的联系。感发性是同一性的本。通过建立感发自我与被感发自我的同一性,亨利提出了一种绝对主体性的自我本体论,而这也正是生命主体的现实性。
亨利把人的主体性扩展到生命性主体,主体的本质性规定也不再是单纯的理性,而是包括情感、意志、欲望等规定性内容,这些非理性的规定性内容的本质性显现方式是生命的自行感发。人的主体性成为包含各个层次的精神性内容的人格主体。亨利所理解的自由不是主体突破被动限制的行动,而是一种在原初的本体论和根本的不自由(被动性)中发现主体本身存在的持久条件。每一个人格主体情感性的感受或体验是伦理道德规范实现的基础,并且不同人格主体的感受也存在差异,但是每一个主体的生命体验的自发性结构具有普遍性。所以在纯形式的普遍理性框架下,对社会伦理规范的客观性考察是一种与规范保持距离的超越性考察,规范作为被考察的对象还未达到与作为考察者的主体的同一,规范还未完全内化于主体的行动中,主体的自由还未完全实现,仍然受限于道德法则的强制性规定,理智主体和情感主体存在对立。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力量施加于主体,规范就必须能够以内在性的方式转化为主体的感发性力量,即在对规范的情感性认同中,让生命在自身的感受中实现规范的内在化,并进一步现实化为主体自身行动的力量。
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分别对应着以感觉经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必然性和以道德行为为研究对象的自由。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对必然性做了区分:自然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和历史必然性(Histirienotwendigkeit)。黑格尔把民族国家的诞生和现代法律的形成理解为历史必然性,而把自由理解为对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和遵从①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分析,请参见俞吾金:《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 期。。斯宾诺莎区分了两种必然,“一种是内在的必然,即他所谓‘自由的必然’(libera necessitas);另一种是外在的必然,即他所谓的‘强制的必然’”②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第161 页。。与此相对应便有出于外因的必然和出于自身本性的内在的必然或者自由意义上的必然。所以必然不仅仅指的是自然界存在的因果必然性,也包括社会历史领域规则意义上的必然性和宗教领域的永恒形式下的必然性。而人的自由也主要是后两者意义上的自由,是一种从由外因决定的自然状态到由对必然性规则的认识的社会状态的提升。所以自由不单纯指的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也包含对社会规则的认识和遵守。在康德那里,是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转化,是一种从认识论到本体论转化意义上的自由。自由因此就具有了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领域的自由意义。从必然性到自由是一种人对对象的认识提升到人对自身的认识的过程,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人的主体性或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核心内涵。
——专栏导语
——论列维纳斯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及其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