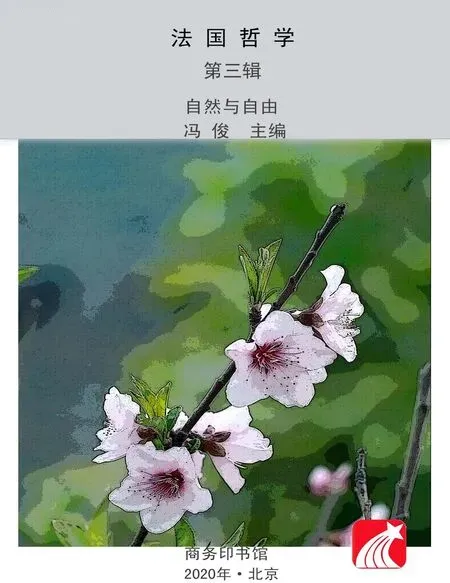历史书写的自由与限度:罗兰·巴特眼中的米什莱
庄 威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事实上,巴特①罗兰·巴特,国内也译为罗兰·巴尔特。本文采用巴特这个译名,当引用其他汉译文献时,则沿用译著者的称呼。的第一本书是《米什莱》,而非《写作的零度》;它是根据1945年前后他在位于瑞士莱赞的疗养院里所做的关于米什莱作品的笔记和卡片而完成的②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车槿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6 页。。米什莱著述宏富,相较之下,巴特只是做了非常少的摘录和评论。但在我看来,巴特从一开始就没有怠慢过自己的作品,在这部书里,他的诸多思想特征和写作特点已经显露出来了。
法国是个文学和散文的国度,文学的熏陶显然构成了巴特气质的一部分。当然,理解法国的“文学”,还真的不能够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从蒙田、帕斯卡尔那里已经可以见到的缠绕着丰富感性和微妙精神的法国思想,文学一开始就与此无法分开。
在对那些摘抄进行评论之前,巴特在书的第一部分安排了关于米什莱生平和著述等方面的评价。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巴特有一段引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的话(有点长不便引述);他是借用马克思的话视米什莱为资产阶级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特点是把民主共和制视为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手段,而不是取消它们。后面我还会提到马克思在这部书中的作用,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在巴特那里实际上是如影随形的。这里不妨事先给出我的判断:各种思想资源,如马克思、符号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当然还有文学)……巴特一旦理解消化,就成为他思想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些前后累积如地层般的思想,会溶解在巴特的作品中,他用“文学—写作”来统合这一切。
一、历史写作的现象学
题记之后就是《米什莱》的第一个“正式”篇目:“吞噬历史的米什莱”。巴特讲到这位历史作家患有偏头痛,看起来身体不太好,然而随风雨不断迁移(巴特提到他一生迁居上百次)的身体总是自认为濒于死亡,但却不断开始新生,如50 岁时迎娶了小自己30 岁的新娘。对于写作的人来说,要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这种孱弱的身体“似乎最适合承受最粗暴的束缚—工作的束缚”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 页。。偏头痛和其他病痛与工作相结合成了一种自主选择的创造性的活动,和米什莱的身体融为一体,任何一位作家都会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巴特既不描述也不评论米什莱作品的具体内容,他站在外围,在身体和写作的层面上来看待米什莱,这成了他今后一切作品的一个基本的水平线,“工作—请按历史学理解—既然是一处安身立命的栖所,在此任何弱点必定具有某种价值。偏头痛于是被移入,即获得了救赎,被赋予了意义。米什莱的整个身体变成了自身创造活动的产物,并且在历史学家与历史之间建立起一种令人错愕的共生关系。……1792年9月国民公会的创立,恐怖时期,这些都跟牙疼一样,是动辄发作的具体的病痛”②同上书,第17 页。。对于米什莱和他笔下历史的关系,巴特把米什莱确立为“历史的啖食者、教士和拥有人”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17—18 页。。“而且这个基督学的主题还在继续:米什莱把历史当作食粮接受下来,反过来,他也把生命交给了历史。不光是工作和健康,连死亡也交出去了。”②同上书,第18 页。
如何理解巴特的写作呢?这位不评论作家作品内容的巴特如何进行针对米什莱的写作呢?我想这里借助一个概念的帮助将会是恰当的—现象学。巴特的写作和视角天生就有一种现象学天赋:对作品内容的悬置,转移目光,紧盯着作家的行动甚至起居,关注作家的语言和风格……这些似乎都是在内容和意义的表面或外围,但巴特将它们制作成了主题,他找到了适合他自己的切入点和写作内容,这是一种在意义和写作边缘的写作,现象学式的写作,或者说巴特的写作内容就是写作如何呈现。抓住写作这一点就意味着必然的学科交叉,哲学、文学、历史、摄影、电影……但凡需要诉诸语言去把握的领域都是写作的领域。写作构成了对一切现实的抽离,现实也呈现为现象学式的写作—语言结构,一句话:巴特通过写作拥有了一种现象学的眼光。
在这种眼光之下,米什莱的身体和历史还有写作融为一体:米什莱在“吞噬历史”,“他在啃草,即边咀嚼,边扫视,同时进行”③同上书,第19 页。。这里用到了比喻:扫视、啃草,意味着米什莱对于时代的观察、理解和消化,他的写作就是行走和凫水一般穿过事件的旅行。巴特从米什莱那里挑选出与自己具有亲缘性的段落和句子,例如米什莱的:“我荡过路易十一,荡过路易十四。我艰难地划水,奋力当过黎留塞和投石党。”④同上书,第20 页。这种荡桨的姿态也是现象学式的处理。
巴特直接关注了米什莱的话语风格,这里引用一段巴特的原文可以看出他的角度:
米什莱的话语—也就是我们常所说的风格(请注意此处风格这个词—笔者)—正是那种彼此挨靠着的协同航行,历史及其讲述者犹如一条鱼及其捕食对象。米什莱属于吞噬型作家(如帕斯卡,兰波)一类,如果不随时吞噬自己的话语,他们就写不下去。对于米什莱来说,这种吞噬活动意味着取消高文典册的演说式节奏,代之以突如其来的插入语,以及例如“您不妨假定,您会看出,这点我回头再谈,我相信,我会这么认为,非得这么说不可”一类的招呼语。此外,序言、注释、跋语等跟整个话语的关系,与插入语跟句子的关系并无二致。这样的孔隙在米什莱的著作里频频出现(正如普鲁斯特就米什莱本人所说的“他那些音乐家的节奏”)。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22 页。
巴特将米什莱与夏多布里昂相区别,后者属于“滑动型作家”:“铺开话语,从旁陪伴而不予以打断,不知不觉地把语句引向平稳安逸的结尾。”②同上。米什莱的吞噬型顺应了历史学家和历史之间的随时交流。
“掠影”等同于夏多布里昂式的滑动型作家,而米什莱所属的吞噬型作家想避免滑动型所带来的精心雕琢的艺术效果,因为“艺术把历史摆入橱窗,使历史学家成为作家”③同上书,第23 页。。不过,我非常怀疑米什莱是否能够完全非艺术地处理历史,巴特也并未认真认定这一点,摆脱艺术,米什莱只能“勉强”做到这一点。
身体与历史的结合,米什莱将历史变成了食物:“因为,历史只有形成一个有两个端点或极点的实在客体,才是一次占有过程的对象。只有像鸡蛋或织物一样饱满厚实,历史才能成为一道食物。所以,米什莱充实了他的历史,给它配上了两个目标和一个方向:他的历史著作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历史哲学,历史被服用了;也就是说,既结束了和完成了,也被吞咽和摄取了,正好可以让历史学家恢复元气。”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24 页。
但是,我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哪个历史学家不是将历史视为一道食物呢?巴特借对米什莱的描述侧面回击了针对历史的客观、严肃的观点。巴特的论述看似古怪,其实有一种难得的诚实。从话语和风格出发,看似无关内容,但是却抓住了包括历史在内的一切以话语为媒介的作品的内在特征。只要写作,只要借助话语,就必然要涉及对内容的吞噬方式。话语—写作的角度由表及里,无比犀利。
二、历史与虚无
《米什莱》的第二部分的标题叫作“荷兰航船”,这有点难以理解。按照巴特的解释,荷兰航船中空而满载物体(仿佛承载着事件和故事的历史),“像一只悬浮在平滑水道里的实心鸡蛋”,在水的冲刷和空气的流动中交替,这是“一个未经剪裁的世界”。②同上书,第25 页。未经剪裁的世界,有点类似道家的味道,巴特讲道:
请看例如中世纪的法国国王:他的力量来自于虚空—请按“光滑”理解,来自于一种高高在上的状态,数以千计的势力世袭贵胄在此互相抵消,从而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怡然自得的无意义……理想地说,他只是虚空而已,是裹在白鼬鼠皮裙里的谦卑,他吸纳了一切:人民,资产阶级,教会。③同上书,第25—26 页。
这的确有些老庄的意味,不同于人们一般所了解的进步的或者马克思式的历史观,但却并非意味着米什莱或者巴特(尤其是巴特)不了解这些历史视角,这里巴特和米什莱的界限很难分清;之前说过,巴特从米什莱那里选择出了自己。
这种空无的历史观配合着巴特所形容的自我和历史的相互吞噬与交错,这一切又被写作所吸收。如果能够明白这一切,就很自然地会懂得下一段所说的无意义与散文的联系:“无意义的所有品性可以归结为一个元素:散文。”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26 页。米什莱也说法兰西是散文的国度(见书中巴特的亲自摘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米什莱来说,散文是匀质的标记……米什莱本人似乎生不逢时似的面临诗歌的威胁,好像亟盼彻底解放一般渴望着散文,因为散文使他能够吞噬历史并与之融为一体”②同上。。后于诗歌产生的散文,没有韵律和剪裁的痕迹,这是散文的优越性,“这就是虚空,因而也是完美的光滑”③同上书,第27 页。。这些性质配合着历史的虚无视角,历史和散文在匀质和虚空的交点处融合了,从这个角度再看事物、事件的联合与自由,祖国、革命被视为“化学的凝固作用”④同上。,“法国因而只是一种无限的化学作用,它只存在于在各部分的护持下的一种虚空当中”⑤同上书,第28 页。。在这种历史眼光之下,虚无中的生成(例如一切以西岱岛为中心的法国历史的生成)也要一种动力,米什莱选择了“作用力”,这是一个近乎尼采的“既属生机论,又属伦理学”的概念,而且这同样也意味着世界的不断再造。对于米什莱的历史书写计划来说,借助于这种作用力加上拉马克的进化论,就能够使他流畅地排列各种形式,“让它们彼此溶解,从一个等式到另一个等式地推进,直至最末一项成为起始的隐喻,直至生命体和物体之间、自然界和伦理之间不再有根本的区别”⑥同上书,第30 页。。例如巴特就此说道:“自然界诸范畴之间没有根本性的阻隔:矿物也是植物,动物身上也有人类的遐想。……位于动物底层的水母,不过是‘关于无法实现的命运的一场梦呓’”⑦同上书,第32 页。。
巴特写道:“有没有千真万确的历史呢?没有。历史其实是一个用各种身份组成的连续体,正如植物或物种是同一块织物的延伸那样。……在历史中前进的米什莱好像一个潜入水下的遨游者,周身被织物般的历史严严实实地裹起。”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34 页。历史与米什莱的身体结合为一体。所以这样的历史哪里还有因果性可言呢?起作用的是伦理性的东西,例如道义上不可或缺的东西,或一些纯属心理学的提法;对米什莱来说,由于之前提到的匀质与虚无,历史最终可以视为等式或者转换,“一言以蔽之,历史只是正义的各种形象之间的一连串等式”②同上书,第37 页。。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视为正义形象之间的过渡和转换,这种转换的驱动力(根据巴特的描述)依然是尼采式的:“驱动自然界和历史的原理这一次依然相同。一个事关存亡,一个事关道义,但两种情形都要求一种生存意志。”③同上。根据这种意志的驱动,自然界道德化了,“自然界是沿着真正的公民解放的道路实现从一个王国到另一个王国的进步的”④同上书,第37—38 页。。
巴特最后总结了米什莱历史写作的特点:“归根结底,恰恰是米什莱的道义感—也就是那种让我们觉得难以置信的修辞风格—把历史写成了一团温情暖意,不但有滋有味,更精要深邃;这是因为,米什莱像一只聪明的寄生虫那样,把自身机体放入了密封而饱满的历史所产生的热量里。”⑤同上书,第38 页。
巴特的米什莱采用了一种全身浸入式的主观具身式的写作,甚至修辞风格(按上述文本引述,道义感正是由它体现)决定了历史的面貌。我想可以说,由其笔记构成的第一部出版物就表现了巴特的主观自我的趣味。这种趣味千万不能理解为主观的以及简单的虚无主义,这种主观可以说是一种后真实。因为,“没有千真万确的历史”,那么与自我身心融为一体的主观性就成了真诚与真实的替代物。
应当充分评估巴特借助米什莱所传达出的准尼采式的历史观点。但是,巴特从不激烈。书写和文学作为屏风,挡住了虚无主义以及激烈的措辞。问题是巴特的这种后虚无主义是什么呢?是什么让他能够平心静气地书写呢?我想,这当然是一种强力意志的变形,非暴力背后的静心的意志。
三、仁慈与正义作为历史的动力
现在,读者就来到了米什莱历史的开始处,巴特将进入到米什莱历史的具体内容中—第三部分:“被我们愚蠢地归入阴性的历史”。最终归于虚无的历史还是有其内容和动力的,动力是仁慈与正义,而“内容”就是这两个塑型因素作用下的事件、人物与现实的显现。在塑型作用之下的内容同时被巴特称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畸胎学”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52 页。。
仁慈和正义仿佛阴阳、阿尼玛与阿尼姆斯,二者永远伴随,“仁慈跟自然法则(共和制度的法律)的规律性截然对立,仁慈与正义组成一对,它有半道义、半生机论的性质,二者引起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二元对立,因为历史中的一切都是仁慈对正义、宿命对自由、基督教对大革命。历史不过是二者的角力,是一个停滞与奋起的悲剧性连续体”②同上书,第53 页。。巴特说仁慈在米什莱那里是万恶之源,具有多样性,仁慈仿佛是化解一切的阴性,老子所说的众妙之门,如烟草和麻醉品,烦恼,还有小说,都被视为“仁慈”的因子:“许多国家和时代都深受其苦,它们在梦幻中沉沦,忘记了孕育生产的义务,只挂念着吸烟饮酒,丢开了历史,它们从丰饶能产的织物层中消失了:土耳其就是一个例子。”③同上书,第54 页。“小说有一种吸收的功能,它背离历史,也就是背离正义;这是一个任意性、仁慈和幻觉的典型范畴;塞万提斯和罗耀拉的西班牙便沉迷于小说、沉迷于神迹的幻象,因而让历史的线索从指缝溜走,西班牙从运动中消失了。”④同上。这里尤其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小说作为一种仁慈的吸收因素,它背离历史的阳性驱力,它是停顿与吸收的阴性。巴特与小说的关系我们将会放在后面论述,其实他早有关注。这种仁慈是一种停滞和昏睡,例如中世纪,米什莱称之为“抄袭者的文明”,之后的君主时代也是非生产性的,“中世纪的抄袭者此时正变为正人君子,都是不结果实、晦涩和孱弱的人物,例如蒙田;懦弱而被动的人物,例如末流贵族,他们是莫里哀、费内龙和卢梭等古典时期的教育家培养出来的,与之截然对立的是,英雄豪杰和公民,一如正义与仁慈之间的对立。”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55—56 页。这里顺带可以看出米什莱的历史仍然以大革命为重要的分水岭。
女人和英雄是仁慈和正义的表现形态,“女人世界是那些摆脱了雄性的正义原则的国家、人民和世纪,它们因而注定过着一种寡居生活,不是枯燥,就是放荡,总之不结果实。这一点能够解释女人世界的歧义性:有时软弱和放纵,处于颓靡状态,属于这种情形的有原始叙利亚、各路狄俄尼索斯教派、莫利诺斯圣宠派和寂静主义;有时冷漠无情,声色俱厉,坚硬如石头和利刃,例如圣书之民(犹太人和穆罕默德的信众)”②同上书,第56 页。。
正义的形象和仁慈的一样多,第一个形式便是撒旦:多产、富有创造力。英雄则是正义的第二个主要形式,是“把正义放入历史中的人”,路德、拉伯雷、莱布尼茨,还有18世纪便是其表现。巴特说米什莱把自己变成了双性人,因为他是“在仁慈的怀中孕育正义的人”③同上书,第58 页。,这种能力不是随时具备,只在某些时刻,对米什莱来说是一种时断时续的能力。
仁慈和正义的主要形象,或者说,它们的一种现象学变更的尽头便是基督教和法国大革命,“前者是一种环境,后者是一股力量……犹如两种性别,互为补充:它们是两种角度,一个凹陷,一个突出。历史就是一场爱情纠葛”④同上书,第59 页。。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正义通过行动构成历史的受精行为,18世纪正是最伟大的英雄和行动的世代,“革命是正义的本质所在,它始终存在,只是在流动中像胎液一样多少受到阻碍而已”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60 页。。米什莱根本不严格遵守“基于时序的历史逻辑”,革命是“剧情的巅峰,解释了整个过去的历史”②同上书,第60—61 页。。革命折断了时间,甚至不参与时间。巴特评论道:“他领悟到革命的全体性,历史的每一分钟都被它滋养,因此可以把它置于任何一个时间点上,而不会破坏事件深刻的内在秩序,只因革命永远适得其所。米什莱把革命写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时,没有半点踌躇。”③同上书,第61 页。
但是如果记得仁慈和正义的互为阴影,那么革命还不止步于上述形象,巴特评价道:“任何爱情纠葛都不过是一种延迟的身份。同理,法国大革命其实只是一个基督教的篡位者的形象”,米什莱如同教皇,为大革命授权,“米什莱的全部叙述都是缓步前行的仪仗”④同上书,第62 页。。米什莱生活在大革命的影响余波之下,在他那里,这就是终点,大革命之后包括米什莱自己生活的时代都只是“一部后历史而已……正如从耶稣之死到末日审判,耐心的上帝为基督徒提供的那段光阴”⑤同上书,第63 页。。
巴特很清楚,米什莱自己仅只是历史中的共和派,他没有参与那个世纪的行动,总在关键时刻逃之夭夭,“他的勇气只有次要的、装饰的意义(其诚意却不容置疑)”,他作为末代遗民有一种孤独感,“他只能让19世纪作为世界末日进入时间进程”⑥同上书,第64 页。。
到这里,读者能理解米什莱的论述和巴特的评述了么?巴特实际上站得很高(还记得开头提到巴特引用马克思吗?),但他不轻易表达和介入,仿佛只是在论述对象的表面滑动,但这需要一种天赋的耐心和敏锐的理解。这一点也向每一位巴特的阅读者提出了要求,怎样阅读巴特呢?我们真的“懂”他吗?应该识别出巴特浑然天成的现象学式的写作,但这种悬置的写作是需要相当的理论储备和支撑的,而且绝不等同于轻浮,绝不等于巴特没有观点,在论述《写作的零度》时我们会看到巴特的观点和态度;与大多数人预测的不同,我们将会再次与马克思相逢,应充分重估马克思在巴特那里的分量。
四、死亡与历史
在米什莱那里历史的基本动力和运作已经看到了,这种历史是怎样的历史呢?巴特停顿了片刻,他没有直接表态什么是历史学的真正重要的工作,他只是问是否是泰纳和科学学派所要求的涉及细节的点彩式的秩序,以及指出对米什莱来说,“大量的历史素材并不是一场要求严丝合缝的拼图游戏,而是一个必须紧紧拥抱的躯体。历史学家仅仅为再现某种热量而存在”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80 页。。在我看来,这种热量就是在巨大的虚无背景下,仁慈和正义之下,人的行动、激情等可以称作生命表征的东西,但这表征是曾经的生命表征,是对往日身躯的记忆。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在处理死亡,“他重新组织历史,但不是在思想、力量、肇因和体系的层次上,而是针对每一次肉体的死亡”②同上书,第81 页。。死者不会明白他的死,塑造他的死亡成为历史学家的魔法,历史学编织生命的线索,颠倒时间,为死者返回原路,“他从死者那里拿走他们的行为、痛苦和牺牲,在历史的普遍记忆中给他们确定一个位置”③同上书,第82 页。。“米什莱的整部历史就是这样一套用于接近死亡的仪式”④同上书,第83 页。,这是一种巫术,接近死亡,为死者招魂,又使其复活。不是每种死亡都能进入米什莱的复活体系,如假死、貌似死亡、半死、不死不活,巴特没有说明这是怎样的死,在我的理解里,这或许可以称作一种阴性的死,非生产性的死,窒息了历史含义(正义与英雄、行动与受精),所以米什莱寻找的死是光明和太阳般的死法,就他而言这并不神秘和带有美学意味,“尸体腐朽是他喜欢的主题”,“再诱人不过的题目”。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85 页。
米什莱那里没有原则性或抽象性的人物,人没有无限的永恒性,“若想成为历史的猎物,他们就必须死去,必须在有生之年就显示出某种关键的、脆弱的品质,某种多血的情绪,也就是可以改变的,已经是阴郁的情绪。说到底,整个历史都建立在人的躯体之上”②同上书,第86—87 页。。米什莱笔下的人物具有强烈的躯体性和世俗特性,“饮食最终占据了其他一切因果关系的地位”③同上书,第87 页。。“肉体是独一无二的,但绝不会是超自然的,因为它毕竟是土地、牧草或水的对等物。”④同上书,第88 页。甚至米什莱还想把每一个历史人物都统一在某种特殊的情绪之下,“人的身体只是情绪而已,而且情绪从来不会不偏不倚,它一定会引起历史学家的某种喜恶情绪”⑤同上书,第90 页。。所以说,米什莱的人物不是原则性的,因为他是根据自己的好恶与否去判断人物;“米什莱的人物根本不需要一套个人的心理活动;他们的心理全是米什莱本人的:国王,王后,士兵,各部大臣,远古神灵和市井妇女,历史上民众一律操米什莱的父亲—印刷所小老板,前圣殿护卫,等等—的语言,或者是米什莱及其妻子阿黛娜伊斯的语言”⑥同上书,第91 页。。当然这些人物也吸收了米什莱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理解;如果剥开这一层语言和之前的个人好恶,“如果从米什莱身上拿掉存在的主题,剩下的将只是一个小布尔乔亚”⑦同上书,第92 页。。
五、血液、历史与女人
米什莱的对人物的情绪化的赋予与好恶由什么串联起来呢?—血液。如果还记得米什莱荷兰航船的形象中对水的喜好,以及历史的动力学,那么就很容易把水看作是未经剪裁和生生的前历史状态,水就是环境,生命的根源。而血液生成于水,“是历史的关键物质”,“水是一种流动的、自由的、良性的、乳汁般的元素,它能够转化为血液”。血液品质的差异造成了历史现象的特征,例如“新的德国,充盈着多血、伟大和繁殖的力量,欧洲的子宫和大脑”,“俄国是个无特定形态的世界,她永远呈现为漂浮、流淌、完整无隔的水的状态,尚未形成血的性格”,“凡是封建大家族没有不因为血液而衰落的,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不过是病态的血和愤怒的血之间的冲突……”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111—115 页。血液是历史的见证。
当然,血也有其对立物,“仿佛是血液的嘲弄者”,第一是石块,米什莱用这一矿物形象隐喻来描述可归之于“生硬、荒凉、虚空的”人物和现象。另一对立物是神经系统,象征和指向着“苍白、纯净、智性的生命”②同上书,第112—118 页。。
血液是宇宙元素,“一种独特的、匀质的物质;它在偶然性的个体化过程中流经所有身躯,但丝毫没有丧失其普遍性。它本身亦从土地转化而来……它拥有元素的无限性。……归根结底,血液的最高形式是海洋。作为最原始的生殖元素,海洋是血液和乳汁的原型”,这种重要的历史关键物质因而毫无疑问具有母性孕育和女性气质,是“创造活动的终极物质”披着肉质外衣的生命:只是一个“思想的沉重体现,充满乳汁、血液和诗意”。③同上书,第119—121 页。
米什莱谈到血液必定要涉及女人,在“女人陛下”这一节中,巴特评述了这个问题。女人及血液也是米什莱组织世界的一种方式,米什莱提到月经使得女人浑然天成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正像来到希望之乡的门口那样,男人站在大自然的门外;只有通过历史,通过心甘情愿地投入正义和仁慈之间的世俗的战斗,他才能在天地之间找到一个角色。女人超然于历史之外;她掌握着时间的钥匙,是先知、仙女和宗教”④同上书,第137 页。。仁慈和正义之演进下的历史是线性的,而这种阳性的线性仍不完美,“星辰、海洋和女人式的循环时间是休憩,是永恒的时间。……从构成方面来说,从周而复始的节奏中诞生的女人是成熟的历史、胜利的历史”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138 页。。这里不是详尽描述米什莱以及巴特有关女人的话题与思考的地方,总而言之,在米什莱那里女人的主题频繁宣示,“风格之豪放、抒情和细腻,都说明女人血液的意向是他的一道真正的心理创伤—在物理或存在的意义上”②同上书,第137 页。。巴特从米什莱那里读出的有关女人的内容,也是他自己的敏感所能触及的内容,因为巴特的风格和作品里都散发着一种非暴力的非论辩性的女性或者雌性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巴特对此领域的敏感,例如他说到要懂得爱情的艺术,要求一种特殊的风流倜傥,要取得女人的信任,不是要愉悦其身体而在于赢得信任,这需要的是说服而非征服的技巧,“因为他(指米什莱—笔者)要赢取的是一个秘密”③同上书,第141 页。。“米什莱本人既非男,亦非女,他只是一道目光;他接近女人的方式不要求有任何雄性特征。……米什莱于是把自己也变成了女人、母亲、姐妹、乳母和妻子的女伴。……在米什莱看来,理想的爱情活动不是插入,而是延伸,因为能够充分展现爱情的并不是性,而是眼神。”④同上书,第142—143 页。所以为了接近女性、给出整个完整的女性神话,米什莱也得掌握一种特殊的语言,巴特说这是一种“乳母的语言”,“米什莱在谈论女人时不得不使用一种极为矫揉造作的语气,也就是小说的语气”。⑤同上书,第147 页。这并不值得惊讶,正因为如此,米什莱才将自己的感官带入正式拥有了女性的特征。
六、超越性别的“人民”
前面一节已经论及女性,这是历史的仁慈一面,另一面则是阳性的,是此前已经提到过的正义一方,这是让历史得以受精的任务及运动。雌雄同体是米什莱理想中的性别;尽管巴特是这么评价米什莱的,他自己其实也是朝此看齐。这当然是一种古老的对立,“心理与理性,即本能与思考,宗教与哲学”主导的角色并非雄性,“只有孵化的元素,雌性的威力,才能引导婚配。……凡属高级生物、国家和元素总是以雌性为主,只有具备了孵化的天赋,即把观念转化为情感的雌性力量,它们才具有能产性”;“归根结底,米什莱笔下的英雄均为雌雄同体的生命,他们靠着从女人移借来的一种重自然的直觉,孵化出智性的能力”。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167 页。例如圣女贞德(我此刻想到了尼采,若不是掌握了女人的心理,尼采的思想绝不会如此阳刚)与之相对照,充满贵族气的批判性和观念性的思考,只能恰好代表一种“亚性”,“而且凡是属于纯观念的东西都患有不育症”。②同上书,第168 页。相反,“本能、民间智慧和直觉都是雌性环境的原初形态;我们知道,跟观念的不结果实的震撼力相比,雌性环境保持着真正的能产性”。③同上书,第169 页。
掌握的雌雄同体的奥秘,也就能够对历史有所把握。对于米什莱而言最为重要的雌雄同体物乃是“人民”(le peuple),人民是“超性”(l’ultrasexe),即对性别的超越:“超性的定义是人民”④同上书,第171 页。。哲学家主宰了法国大革命的单一精神性别(雄性与正义),但是法国大革命却不能理解为由这些精神肇因和影响构成的历史学体系,“而是人民,亦即一种绝对性,大革命的参与者反倒具备双重的、完整的性别,雌雄兼备”⑤同上书,第165 页。。巴特评论说:“脱离了民众这一卓越的孵化环境:它(指观念—笔者)导致一连串罪孽,也就是恐怖时期。”⑥同上书,第168 页。观念与精神具有一种光明的品性,因为它具有精神的高冷明细;而热量乃是民众的符号,孵化行为所具有的品格,“请看人民:由于位于社会阶梯的最底端,他们才是完整的热量,是一切皆诞生于此的孵化层”⑦同上书,第171 页。。历史学家实际上也属于从事脑力的不育的雄性,“撰写历史的并不是他,而是人民在向他口授历史……同样道理,法国的建立并非产生于她的统治者:是人民的力量构思了法律,立法者不过把人民的决定以法律的方式誊写下来,它们不过是人民的记录员”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172 页。。巴特这里谈到人民与历史的关系,这是明显的马克思思想的印迹。
巴特注意到米什莱的“人民”并非明确的社会阶层的集合,“而是一种被双重性别和孵化功能所规定的元素……实际上,它没有把任何人排除在外,连富翁也在某种意义上隶属于人民;不过,他们的热量微乎其微,近乎高空大气层的不结果实的寒冷”②同上。。我把“人民”理解为米什莱那里的一种写作元素,巴特没有提到“写作元素”,只提及“元素”:“人民既然是元素,不是社会群体,逐个描写每个阶层的伦理学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贯穿米什莱的历史著作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米什莱本人的生活方式:整个人类生活被置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背景之下,这与巴尔扎克的小说完全不同;在后者那里,社会依照各个阶层的占有方式极度分化;金钱无孔不入地决定着如何讲话、吃饭、居住和恋爱。”③同上书,第172—173 页。可见巴特对于“人民”的理解特色和关注,也表明了马克思的因素对于巴特思考的指标性意义,虽然是评米什莱但也是说自己,“在米什莱笔下为基础的人民逐渐变成一条获取知识的坦途。人民犹如女人,方向也基本一致,超然于历史之外”④同上书,第173 页。。巴特讲“人民”还意味着“和谐的人性”“一个光滑无痕的世界”⑤同上。这种和谐与光滑无痕,也是巴特紧接着在《写作的零度中》所提出的写作的乌托邦;《米什莱》时期巴特的这种马克思底色式的文学思考还未臻于完备,但基本的风格与思考点已袒露大半⑥巴特的传记作者卡尔韦指出,在疗养院读米什莱的时候,他通过友人已经接触到了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阅读了《神圣家族》(参见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车槿山译,第74 页)。此处不妨引用一条《神圣家族》里马克思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话,可以对比巴特对于米什莱那里“人民”问题的理解,马克思的德文用的是Masse(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批判的历史认为(指鲍威尔的观点—笔者),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相反,在“这些活动中”,“重要的”仅仅是“一种思想”。(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 页)。
“人民”究竟是托词还是真实,实际上难以考究,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是思考和现实的水平线,“在米什莱眼中,人民是关键性的实质、生命的实质”,能够克服人类的矛盾:“例如,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既活跃又沉思,既信奉宗教又喜欢推理,既睿智又孩子气……既老又年轻”,“因此,投身于人民之中,与之打成一片,使自己成为人民,这等于服用了长生不死的神药”。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174 页。
与米什莱类似的是,巴特自己也属于小资产阶级。米什莱无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眼光、语言(“我生来属于人民,人民始终在我心中……可是,语言啊,他们的语言,却非我力所能及。我没能做到让他们开口说话”,“因此,米什莱的话语—即他的著述—压垮了他自己,迫使他痛苦地远离天堂;也许在现代作家当中,他是头一个不得不用一种说不出来的语言吟唱的人”②同上书,第175 页。),巴特非常清楚这一点,“人民”问题带来的挑战巴特是否克服了呢?巴特在出版在先、写作时间在后的《写作的零度》当中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正如整个现代艺术一样,文学的写作既具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作为一种必然性,文学写作证明了语言的分裂,后者又是与阶级的分裂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种自由,它就是这种分裂的良知和超越这种分裂的努力。尽管不断为自己的孤独感到歉疚,文学的写作仍然是对语言至善的一种特切的想象,它仓促朝向一种梦想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清晰性,借助某种理想的预期作用,象征了一个新亚当世界的完美,在这个世界里语言不再是疏离错乱的了。写作的扩增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当此文学仅是为了如下的目标才创新其语言之时: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③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 页。
然而《米什莱》就止步于这里:对于古典时序般的历史的不感兴趣、语言的问题、写作的问题、马克思与写作的问题,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这构成了巴特独特的个人风格。但还有一点需要补充。
七、主题批评及其超出
全书的最后有一节标题为“阅读米什莱”,这一节相当于一个后记,同时也相当于一个方法论的概要,巴特喜欢在前言或后记中介绍他的某部作品的思想渊源,这些都很重要,但同时也不能完全信任巴特的说法,因为作品的内容总是比他自己介绍的要丰富许多。
在这一节里,巴特论及在米什莱作品中常常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一特点,《米什莱》中的每一节都是围绕着某一主题来行文的,巴特关于每一节的笔记也是围绕这些主题而摘录的。这种“主题批评”很明显是受加斯东·巴什拉作品的影响的,后者正是围绕一些主题或元素开展其极富特色的想象力的现象学思考的,如《水与梦》《火的精神分析》等等。不过在我看来,巴特在《米什莱》时期实际上已经对巴什拉的主题批评有一种超越的企图了,他展开了针对“主题”这一批评或者写作设置的元批评。巴特注意到主题的重复出现具有几个直接后果。“首先,必须把米什莱当作一首复调音乐来阅读,不光用眼,还要用耳、用记忆来阅读。”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187—188 页。,这就意味着一种对于作品的摆脱和超出,因为“主题”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阅读的自主选择与自信,读者是主动的,并且自行设计。“其次,必须理解,主题抵制历史”;从巴特对米什莱的整个阅读看,米什莱自己是按照一种明显的个人趣味甚至偏好来写作和理解历史的,真实性在米什莱这里是不起主要作用的,巴特牢牢握住了这一点。可以说,主题阅读抵制线性的求真相的历史,而直接彰显了个人意趣(“主题支撑起一整套价值体系;没有一个主题会不偏不倚。”①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第189 页。),这一点会在今后巴特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第三点后果是更值得注意的,“主题重复特性之所以有效,还因为它在米什莱笔下具有一种语言固定性:主题总是通过同一个词语或同一个意向得到彰显”②同上书,第188 页。,“主题”通过“语言”得以固定和彰显,这就意味着—巴特自己在《米什莱》中没有明确说及但的确暗含着—“语言”是对“主题”的摆脱与超出,这一点在《写作的零度》中有着令人印象深刻地发挥。所以巴特对于巴什拉在语言这个层次上进行了超越,尽管此时还未明说,但是从对主题的评述,以及主体部分最后对于米什莱绊倒在“人民的语言”这一问题的强调上,可以看出对于“主题”的超出对巴特来说已经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