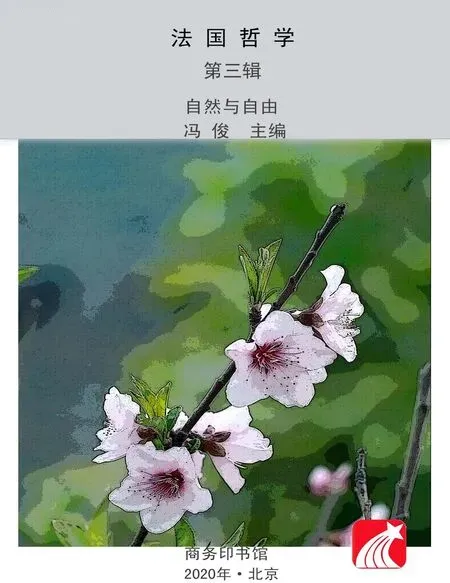自由的悖论与存在的本真:萨特与庄子
姜丹丹
(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
在法国现代哲学家萨特(1905—1980)①关于萨特的作品与思想在中国的接受,早自1943年(在1943—1947年间《墙》曾三次被译成汉语),但对他的接受经历了高潮与低潮期,与历史语境的具体情形相关。曾有两个阶段,萨特在中国被猛烈地质疑与批判: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萨特与新中国1952—1956年间的短暂的“蜜月期”(萨特与波伏娃1955年访华)过去之后。20世纪80年代,萨特的著作被一度禁止后,被重新介绍、翻译和研究。这也是“文化热”与“新启蒙”的时期,强调以西方的人道主义对抗传统,而这个阶段的“萨特热潮”也掺杂许多猛烈的批评,围绕异化与人道主义的问题的纷争与辩论。在这个阶段,萨特在中国被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所崇拜,但同时很快在《存在与虚无》的中译本发表后也曾一度被斥责为传播“精神的污染”。的思想里,自由的观念占据核心的地位。实际上,在其早期代表性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1946)里,萨特在思考“自由”的问题时,首先对所有本质主义、决定主义与唯心主义进行了层层剥离的质疑与清理,因此,自由的构想先于任何大写的谋划、命运、情感(情绪、感情)甚至包括价值,因为萨特对于任一具体的企划与个体的自由之间的“间距”保有清醒的意识。明确地讲,对于萨特而言,这指的是以选择的自由来反对在任何层面上的个体需要做出的奴役或者屈从。
从这个视角来看,在当代汉语语境里,关于萨特的一些研究中,尤其在80—90年代,有些文章将萨特与中国先秦道家思想家庄子相靠拢,似乎在对于自由的探求中建立深度的比较与沟通,尽管在这两位作者的思想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与距离。然而,这些间距也需要去提问,或者说构成与这两位思想家一起去重新思考存在与自由的跨文化的问题场域,尤其在新的语境里重新反思存在与自由的关系的悖论。还要提到,早在20世纪60年代,庄子已经与萨特的名字在论文中相提并论,但在当时其被批判为“主观唯心主义”①参见胡道静主编:《十家论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在这种有关萨特研究的跨文化对话的视野里,自由被设定为终极性的,由其引发的如下问题,或许也解释了萨特在中文语境的接受过程中出现的某些误读的现象。当自由的选择摆脱价值的限定,它应如何实现,依据怎样的方向,这是否会引向某种意义的虚无主义?或者对于存在的荒诞的认同?或者一种任意的个体主义,并伴随自私主义的所有风险?或者可能会与共同利益以及共同体的价值相对立?这又提出价值论层面的问题,比如如何避免自由的运用朝向恶的演化或者过渡?因此,在涉及自由观的思考中,亦需要探讨在存在与意义、私人与公共伦理、自由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在早期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里,萨特给出了一些不同的、具体的、实践性的情境的个案的例子,也包括对于存在选择的困境的分析。在其中,个体在情境中选择的困难以尖锐的方式提出,在一个时代的情境里,个体是否应该选择介入,在个体的生活里可能变得极具问题意识,比如在二战期间面对抵抗的挑战,为了正义的事业,等等。个体的选择不断地面对与主要的结构、必然超越自我范畴的一些价值相碰撞。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危机处境里也曾遭遇近似私与公的冲突。比如,在对《庄子》的阅读中,现代思想家章太炎(1869—1936)表示,要对于以公共伦理为名的介入有所保留,因为有可能牺牲个体的自由;平等被构想为非整全式,而是用“齐”的理想提倡尊重和保留个体之间的差异。但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并不是用同样的方式思考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萨特希望探讨的是选择的条件,比如,他区分两种类型的行动:其中一种是具体的、即刻的,但是只指向个体;另一种则指向一个无限大的整体(更宏大的,比如民族的集体性)①Jean-Paul Sartre, 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 , 1996 (1946), Paris: Gallimard, p. 42.。人应当在整体上是自由的:最终,困难在于“本真性”的探求。因而,在一个偶像、一种情感、一种道德价值的影响下所进行的选择,都反而有可能营造出非本真的状态,无知又盲目的状态。
在先秦时代,庄子反思儒家所预设的种种价值,包括仁义、忠孝,等等,他的立场并不是反道德,而是力图摈弃过于执意于道德标准或者在其运用中的过度的倾向,而提倡实行一种本真性存在的伦理,以避免让道德价值的抽象标准的过度化以及化成教条的危险。难道这不正是在摈弃推向极端的外在价值的基础上趋向对于本真性与自由的意识吗?为此,庄子也呈现所谓“整体化”的介入情境,或为了声名、荣誉、财富竞争与斗争;这种类型的介入可能掩盖潜伏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存在的自由追求所冒的潜在与真实的风险。
萨特提出著名的论述“存在先于本质”,则是在二战之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视野里与从柏拉图到康德论述的所有“本质”(essence)加以清理。事实上,在此论述中也可以隐见开启了关于“诞生”、开端、关怀当下(现在)的现象学的前奏;关键在于其中的“存在”的概念是需要在每个时刻、瞬间去体认、实验的概念,即需要在实际的选择、实践的行为里不断地重构的“存在的根底”,而不是本质化的、固定不变的“根底”(fonds)。而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亨利·梅尔蒂尼(Henri Maldiney)、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等人延续了由萨特和他同时代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用不同方式开拓的道路。在最强烈、最本真的意义上重构的存在,“如是”的存在,其出现也有赖于克尔凯郭尔与海德格尔开拓的现象学道路。
依据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的表述,自由的获得与“平静”相反,他这样写道:“平静主义,这是说这种话的人们的态度:其他人可以做我所不能做的事。”他认为,不应该把自我放弃到平静主义、无所行动的状态,即“被抛在世界之中”的自由人的状态。在行动中实现的自由是否背离通常被称作庄子所谓的“消极自由”呢?刘笑敢先生在他的比较研究的重要著作《两种自由的追求:庄子与沙特》①刘笑敢:《两种自由的追求:庄子与沙特》,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里提出,在这两个思想家—庄子与萨特—之间有彻底的差异,并指出在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之间有截然的对立,而这种解读受到以塞亚·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因而,在这本汉语著作里,萨特被放置到现代自由即所谓“积极自由”的范畴,甚至是在靠近新共和派视角里对柏林的“浪漫”自由的理解,即在认为一切都引向自由化的自由,在公民与公众的共同体的意义上。而与此相反,庄子的道家式的自由观则被当作被动的、消极的、前现代的自由。此外,这反映出在从中国现代时期以来对于《庄子》作品的精神的足有、抽象的自由的一些看法或误解。比如,在五四时期(1919—1925),反传统的激进派比如胡适以全盘西化的名义,激烈反对传统思想中的这种消极和被动,并把这个方面看作是那个时代新涌现的关键词“进化”“效率”的阻碍,在当时,进化被认为对当时把中国从濒临四崩五裂的古老帝国的“封闭”滞后的危机处境里拯救出来,建设民族国家,是有必要的。
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庄子》古典文本的重新诉求,是在两种不同范畴内展开的,一方面是从提倡对于古典的创造性转化的自由主义出发,另一方面则是忠于古代重新诠释的文化保守主义。但无论如何,在那个时代,庄子都依然被解读为消极的自由。在以塞亚·柏林的思想中,“消极的自由”提供个人自由的基础,如果说在萨特或庄子的观念中并不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在萨特与庄子那里都呈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实现方式,而在柏林的作为自由的行动可能性里是缺少的。在这两种类型的自由观的对立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呢?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萨特与庄子所关怀的问题之一,因为他们希望面对如是而在的生命存在本身,而自由的选择不应由外在的因素所制约,而应通过对自我与存在的觉悟出发开始实现。这种意识的采取召唤要面向个体的“生成”的可能性,召唤把存在当作不断在运动中的“过程”来领会。因而,存在的意义即是通过“选择”的取向(在法文中的Lesens 兼具方向与意义的意味)为存在确立方向来建构的。
在庄子思想中的“无为”,时常被误解为静止不动、无所行为,甚至被做如下负面判断:“庄子解决机械必然和绝对自由的方式,就是通过‘无己’而与‘道’同体,在自己头脑幻造‘无何有之乡’的绝对自由。这一点就决定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是阿Q 式的,并具有滑头主义、混世主义的特点。”①胡道静主编:《十家论庄》,第285 页。但与这种误读相反,《庄子》提倡的“无为”“无己”有可能以悖论的方式引向一种行动的自由。“唯道集虚”②《庄子·内篇·人间世》,参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7 页。,以“心斋”的状态体虚,“虚而待物”,意味着向万物敞开、可以接纳万物的状态,并且保证在自身与万物之间的自由往返运动,关键在于实现这种过渡或者根本性的转化。归根结底,这指的是一种祛除主体意识可能造成对于行动的阻碍的看似负面的过程,可以使行动祛除意向性、目的论,如此有可能使主体更自由地转化和过渡到行动。
那么,我们将要碰触到自由的问题意识的核心之处:如何在本真自由的意义上重新界定主体性,又如何避免在自由中的主观主义?或许,在不限于字面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庄子所提倡的自由观:这首先指的是做自己的一种自由,以典范的方式通过活动的想象来证实自身,这即是在《逍遥游》的开篇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所要达到的。鲲奋起而飞,转化成巨鸟,从而自由地漫游,“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拓展了存在与视见的视域,在眼前展开的场景,是在地面上的有限视域里所不能看到的:“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①《庄子·内篇·逍遥游》,参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册,第24—28 页。鲲的变形是以“怒而飞”而冲破“顺应主义”会造成的任何障碍,突破有局限性的视域,实现了自身的转化,并穿越种种疆界的限制。庄子所提倡的也是一种“不为物所役”的自由,因而,主体丝毫不是浑世、无原则的,但既不是要把握,也不是要统领、宰制万物,而是通过平淡、退隐的方式重新营造淡泊的主体性,在材质、空间的空隙里自由过渡的自由。比如在实践的活动中,在“庖丁解牛”的例子里(“以神会之”),经过十九年的习练,技艺纯熟的庖丁,可以轻松自由地破解事物的内在障碍,“游刃有余”②《庄子·内篇·养生主》,参见同上书,第207—208 页。,如此实现如瑞士汉学家毕来德所描述的在不同机制之间的过渡,抵达创造性自由的机制。或许这也如同在与世界的“际遇”里—作为创造性的情境的构想—实现与“跨现象性”(transphénoménal)的世界的沟通、贯通的可能性,如同庄子在“以神会之”的状态中所体会到的经验?或许在具有创造性的、引向贯通性的自由观的潜在问题意识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尝试把萨特与庄子相联结,把他们看似迥异的自由观重新做一深层的沟通。萨特在《自我的超越》③萨特1934年撰写《自我的超越》(Essai sur La Transcendance de l’Ego),1936年首先在《哲学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杂志上发表,1937年在巴黎维兰(Vrin)出版社出版,1966年再版。里提出“贯通”式的意向性的说法,“意识正是在自身之上统合,具体是由意向性的贯通的游戏开始,构成过去的诸种意识的具体而真实的“持留”(rétention)”。萨特因而有意识地抛除了“超验的自我”,将意识与意向性转化为贯通性,而由“跨现象性”(transphénoménal)的真实世界来穿越。
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还将道德的选择与一部艺术作品的构成相比拟,他对此做出如下的表述:“当然没有预先存在的美学价值,但是,有一些价值在画面的一致性里可以看到,在创造的愿望与结果之间的关系里……究竟这与道德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都处在创造的同一情境里。”①Jean-Paul Sartre, 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 pp. 64-65.选择的过程与融入创造的生命,艺术作品的创作,与道德的选择与形成一样,都与生命的诸种转化的动能不可分离。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对应瑞士当代汉学家毕来德对《庄子》文本中体现的完美的内在活动的诠释,即作为身体与精神、意识与潜意识的诸种才能的“协同”作用,由完美的内在活动整合为一体从而转化为自由无滞的行动。毕来德通过“庖丁解牛”的范例的解读,指出其中发生的从外在行动到内在活动的转化:“[庖丁]他不局限在用灵巧的技术解牛,而在于他在行业中实现了一种活动的高级形式,并由此深入到了事物的运作之中。宗旨在于通过这个行业,找到内在活动的高级形式,并由此进入‘事物的运作’之中。从一种有用的活动,发展为一种艺术,从艺术而成之为认知的方式。”②Jean-François Billeter, L’art chinois de l’écriture, Genève: Skira, 2005 (1989), pp. 270-272.正是在“虚己”的内在状态中悬置可能造成阻碍的意识活动,从而才有可能在习惯成自然的过程中进入“官知止而神欲行”的浑然整全的动能状态,而获得进入事物内在的运作机制的行动的自由。庄子选择“忘我”“虚己”的过程为途径来抵达生命的本真、淡泊的状态,这可以对应自然的道路,以获得创造性的自由。毕来德先生在《庄子四讲》里这样论述《庄子》中另一种主体性的具有揭示性的重新诠释:“庄子的范式获得一种补充性的维度,当我们感知到空无的,或者混沌的地点,……可以成为已知与未知的才能、资源与力量,可以供我们调用,或者决定我们的行动……,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往往是令人困惑的方式,他让我们懂得正是通过让这样构想的身体自身去行动,我们才能确保自身的自主性。对我们来说,这个道理是悖论性的,因为我们通常如此地习惯于在我们的行为中寻求自主性。”③Ibid., pp.145-146.
在萨特对于自由问题的思考中,难道不是也有一种针对主体性的负面劳作的过程吗,我们或可将那种过程几乎领会为祛除占有性的主体化的过程?比如,他这样写道:“我既不能在我身上探求引我引动的本真性状态,也不能去问道德要一些概念来允许我行动。”①Jean-Paul Sartre, 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 p.45.剥离意愿控制的一种身心整合的状态,构成一种纯粹的、敞开的状态,以抵达朝向现实、现象本身敞开的这种自由。而在萨特那里,世界之谜如同奇异性(陌生性)—事件展开,用一种全新的目光看到的事物的冲撞,是一种揭示,引发恶心感,是在从未如此看到的这个世界面前的不自在感,不再作为对象-物件来观看的世界,却作为令人惊诧的主体涌现,在一种“毫无意义”的非逻辑里,但与此同时却具有构成一种跨现象范畴(trans-phénoménal)的通道?
在萨特所描述的自由的经验中,可谓诉求于一种深沉的主体性,而不要停留在自动、自发主义的层面,不囿于封闭的、自恋的、属于自我中心的意识范畴的主体性的限制。或者更明确地说,这里所质疑的正是主体与自身之间的等同性。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在对于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接受过程中,将之看作一种没有限制的、任意所为的自由的论断,是多么片面、可笑的误解,甚至萨特也被当作当时阅读他的著作的一些年轻读者犯罪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在法国、中国或其他地方,萨特的所谓存在主义的一些表述都被孤立起来做相当有限的理解,也就是说,那些表述(比如“存在先于本质”)缩减为“孤儿式”的表述,对于问题的误读与误解也造成一些悲剧。如果我们完整地阅读萨特的命题,就会发现他强调对人们所是的存在、依据自身选择而将要生成变化的存在的责任感。这一点也接近海德格尔论述的l’ek-siter(出窍)的理念,走出自身,置身在自身的前方,来生成为自身,来承担作为存在的责任。因而,这种面向自身存在的责任感将拓展到他人、人类,而并不相互矛盾。萨特对于“自由”的界定颠覆常规的道德性,在生命责任感的伦理层面上具有深刻的、悖论的意义。
的确,无论是庄子还是萨特,都并没有特别表现出对于他者的关怀或操心,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中国先秦儒家思想家孔子或注重他者伦理的法国现代哲学家列维纳斯的差异很大。相反,不如说庄子与萨特拒绝以牺牲自身的方式成就他人,因为,若不如此,自身存在将不会是本真的存在,而在这种观念的图景里,甚至连他者的自由也都不能实现。这就是如保罗·利科指出的,在列维纳斯的思想里,在人际关系层面的绝对无私,可以构成面向自身的一种不公正,因而,他更倾向于对待自身宛如对待他者,反之亦然。我们可以说,萨特与庄子都用悖论的方式理解在自身的自由与他者的自由之间的关系。为他者的自由所触及,这是萨特用戏剧化的方式在他的表述“他者即地狱”所呈现的未觉醒的状态。一种真正的自由与他者的自由并不相悖,这指的是在从本真的选择到共存的可能的伦理意义层面,因而,人就成为共存的网络中的一个存在的个体,“在世界-中-的人”。通过选择“平淡”作为存在方式的生命伦理,庄子在自身与他者之间确立一种平衡的可能。“忘我”的表述经常被认识为一种漠然、对他人的不关心,然而,这却在悖论的层面上可以构成穿越边界、疆界的条件,在生命伦理的意义上,让并不令人窒息的“共存”成为可能的条件。这也同样映亮一种不治而天下自治的无为状态(指的是不要用太多人为的方式介入、干预自然的状态或过程),或许这也可以理解为在一种自由治理的层面上的“消极的自由”?换言之,是否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些倾向在庄子的思想中隐现,以不介入作为可能的介入方式,而另一方面,在萨特的介入思想里也同样在字里行间提示出自由选择的不介入的方面,两者的思想中具有的悖论性是不容忽视的。庄子与萨特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明智的精神,他们首先希望不要面向“真理”苏醒,而是面向正在生成之路中的存在的自由、本真的过程;否则,正如萨特在《真理与存在》里所提到的,真理也有可能成为“枯死的真理”。
这种主体性创造自身、不断重新创造自身,保证了个体的有尺度的自由,也意味着要与自我保持一种距离。如果没有这种自身的习练,自由也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个体也会被封闭、局限在主观主义的盲目之中。这也是力图重塑生命哲学与伦理的法国当代哲学家弗里德里克·沃尔姆(Frédéric Worms)向我们重新揭示的萨特的自由观的悖论性质,并不是与“自在”与“自为”的对立之中,而相反在“自在”与“自为”之间①Frédéric Worms, La Philosophie en France au XX è siècle, Moments, Paris: Gallimard, 2009, pp. 230-241.可能蕴含一种机体性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可对应在庄子的思想里的“自然的范式”里的“天”与“人”的不同机制之间的非对立的关联性。
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里,“自在”与“自为”的关系,并不等同于毕来德在《庄子》文本里重新诠释的两种不同活动机制(借用主体性的物理性作为基础)之间的过渡关系。因此,这种关系不是两种活动状态之间的等级关系,而可以看作是彼此之间的交织、一种可流动的循环的关系。具有创造性的、转化可能的活力,在由具体行为实现的关系中诞生,因此,把“自在”与“自为”的两种层面彼此联结,为了让两者之间的通道成为可能,为了让自身与世界彼此沟通。而弗德里克·沃尔姆正是在萨特的思想里重新诠释出这两种力量的悖论性的逆转,而庄子可以说是在另一种语言里思考了在内敛与拓展自身、平等与差异、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联。
如何保持本真性的伦理,而不妨碍自足自主的自由的实现呢?如何维系共同体的理想,但又在其内部保存如庄子“天籁”中的“吹万不同”的千差万别的差异,而促使世界的可能的“自行生成”,并包容差异的多样性,或者说没有等级的多元呢?如何在一种“无意义”的祛魅的图景内部重新奠定生命的意义呢?如何重新确立创造的主体性,以创造性的部署作为隐喻,与在取消差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网络中的“没有个性的人”的形象背道而驰,当新的“野蛮”取消生命意义时,如何重新塑造平衡而又具有创造性的生命体?或许在一读再读例如萨特与庄子这样的哲学家后,在非二元化的自由观的视野里,可以促使我们在“全球的流动性”时代里去反思这些问题。
我们也可以借用毕来德在重新解读《庄子》的著作《范式》结尾处的一段表述来归结,似乎它可以作为在某种方式上汇拢这两位思想家的恰切表述:“我们不是生来自由,我们是逐渐生成为自由的。”②Jean-François Billeter, Paradigme, Paris: Allia, 2012, p.126.萨特与庄子关于自由的观念的思考也呈现出存在的风格或者态度之间的差别,萨特用他强调的“选择”的自由所代表的“乐观的坚硬”来与庄子选择的虚静、淡泊的姿态有所区别。这种乐观的、积极的存在观也向我们传达了不断开始、重新开始的一种存在姿态与创造性的可能性,亦需要与趋向自然而然的道家式“无己”的自我转化的吊诡的思想相结合,方有可能实现与“跨现象性的”世界的贯通性沟通,打开创造性生命通道的自由,而在当今时代里的“文明的新野蛮”的情境下,这也是需要在跨文化反思的对话视野里去重新营造的生命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