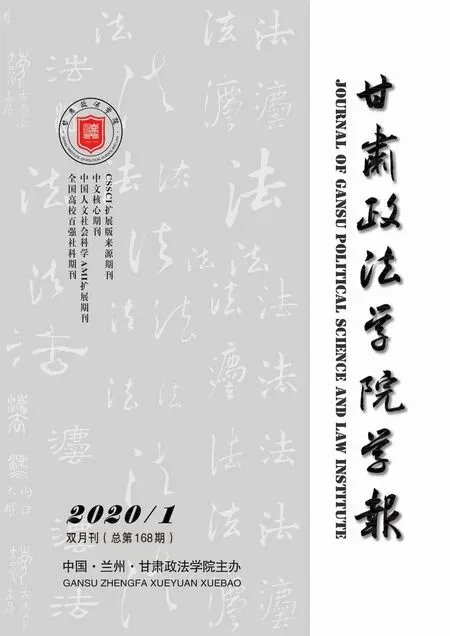技术侦查行为的“概括性否定”
祁亚平
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严禁”应该是对欺骗性侦查及其所获证据的一种“概括性”否定;该“严禁”与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至154条规定的“技术侦查措施”之间存在内在逻辑的一致性。(3)蒋鹏飞:《刑事诉讼法第50条欺骗性取证部分的学理解释》,载《东方法学》2016年第1期。但“概括性”否定的含义,仍需进一步阐明:“概括性否定”不是对欺骗性侦查行为的禁止,也不是对欺骗性侦查行为所获证据的禁止,而是对欺骗性侦查设立了一种“违法性前提”,控方需证明取证方式的合法性。“概括性”否定假定侦查行为本身不具有合法性,其主要目的就是阻断法官对特定控方证据的合法性推定。
在实践当中, 秘密侦查和“技术性侦查手段”一直被理解为一种秘而不宣的侦查方式,或者偶尔“惊鸿一现”,实则隐藏在侦查阶段从不示人的“冰山”下。(4)侦查机关以秘密措施为由,拒不出示秘密侦查卷宗成为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惯例。习惯中通过“情况通报”以保证侦查员的安全,但是这种文书内容极为简化,并不能防止可能存在的证据失误问题。由于侦查案卷移送等方面的原因,技术侦查措施中的欺骗性问题比欺骗性讯问等一般侦查欺骗行为具有更加迫切的研究必要。因此,本文主要集中研究秘密侦查、技术侦查手段中的欺骗性取证的证据合法性问题。如果“概括性否定”概念不能涉及技术侦查,那么“以审判为中心”制度将难以真正实现。同时,“概括性否定”意味着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所获证据的证据资格取决于具体案件中的司法审查结论,这就使得侦查所获证据的资格审查与侦查行为审查出现一定的程序混同。也就是说,对于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概括性否定”也隐设了司法事后审查程序。
一、“概括性否定”的实际涵义
(一)“概括性否定”与“违法性假定”
“概括性否定”的第一重含义,就是规定欺骗性技术侦查所获证据具有违法性。侦查法治化的目的,是为了规范技术侦查措施行为的实施范围及手段;技术侦查措施法治化的主要实现方式包括侦查前的程序许可及审判阶段的证据审核。“概括性否定”就是假定欺骗性侦查所取得的证据本身具有违法性,即使没有被告人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法庭也应当依职权主动进行证据合法性审查。“概括性否定”意味着这类侦查方式在本质上具有更应当被质疑的特点。这种证据“否定”,并不是对于证据手段的一概否决或排除,证据是否有效,取决于司法审查的结论。因此,警方应随卷移送技术侦查方面的真实证据,不能一概以“危害侦查秘密”为借口或以“情况说明”取代证据来源,否则这种假定不能被推翻。
(二)“概括性否定”与司法事后审查
“概括性”否定必须伴随证据资格审查程序,这是“概括性”否定的第二重含义。控方必须证明特定证据方式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不能将“概括性否定”解读为“概括性肯定”,或者成为价值优势选择的道德判断途径。(5)龙宗智:《欺骗与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界限》,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所谓“实际允许”,是指实践中并没有谁指责这类行为系违法,也还没有发现因此而排除口供的案例,更不存在对于这些措施的具体核实、评判。技术侦查措施程序的合法性控制主要有两大程序:技术侦查措施前的许可程序与司法审判中的审查程序。对于刑事指控所依据的所有证据,审判法官必须能够对于侦查移交的证据进行来源审查。对于具体案件中的欺骗性取证所取得的证据是否有效,应当在具体的案件条件中,依据明确的程序和明确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主要表现为合法性审查和必要性审查,合法性审查是指所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必要性审查是指所取得的证据是否符合侦查行为的比例性原则。
审判机关在证据调查中,需要得到具体侦查行为实施的过程性材料的支持,才能够进行实质性的证据审查。“审判中心主义”必然包含对于侦查程序中欺骗性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必要性审查,这就必然需要实质性的的司法审查机制。现有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司法审查的具体规定,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中(6)如《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特情侦查案件进行了一定规定,特情诱惑不判处死刑;“双套引诱”下实施毒品犯罪的,处刑时可予以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罚或者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对不能排除“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却对欺骗性技术侦查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审查要求。
(三)“概括性否定”与证据禁止
“概括性”否定并没有禁止类似取证手段。“概括性”否定实质上是允许控方举证推翻的一种证据非法性假定,所以与“证据禁止”含义并不相同。证据禁止是绝对不允许使用。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a)条规定,禁止用非法的方法取得被告人口供,这些被禁止的方法包括: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后来又增加麻醉分析和测谎鉴定)。“德国刑诉法第136(a)主要采用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讯问方法,限制讯问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对其宪法权利的侵犯,从而保障犯罪嫌疑人决定和确认自己意志的自由;明确了禁止的讯问方法在讯问过程中适用的强制性效力,即使犯罪嫌疑人同意使用,讯问人员在讯问时也不得使用禁止的讯问方法;如果控诉方是以违反禁令获得证据材料,即使犯罪嫌疑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7)兰跃军:《论言词证据之禁止——以〈德国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分析》,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1期。
赛猪最早开始于联邦德国。每年,全国都有不少城市和地区举办规模盛大的“赛猪运动会”,吸引着数以万计的观众。如今,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风行着赛猪。美国海诺德生猪公司首先举办赛猪,通过宣传来开拓生猪销路。赛猪的跑道是椭圆形的,铺上锯末,全长28.3米。参加比赛的“猪选手”,因为经过训练,再加上放在终点的食物特别鲜美,所以跑起来毫不懈怠,个个争先恐后。冠军的纪录是4.48秒,一直保持了多年。现在,赛猪已经扩展到中西部八个州。比赛项目也在刷新,如举行“猪儿跳远赛”、“猪儿游泳赛”等,真是别开生面。
“概括性否定”,则是在证据取得禁止与证据使用禁止之间设置了适度的法官裁量范围。一方面,刑事案件涉及的社会利益众多,警察在办案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也并不相同,在法律禁止的方法以及法律禁止之外的方法实施中,都应当赋予法官一定的酌定权力;另一方面,证据的使用禁止实际存在对于证据取得方式禁止的包容关系,所有警方按照取得方式获得的证据,最终必然经过法庭的证据审查。侦查方式的批准程序,尤其是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程序如果被过分强调,自然就会出现对于司法事后审查的实际效果的过于忽视。最终导致,法庭审判时只能凭借简要说明式的“情况说明”来直接决定证据是否适用。法律必须赋予法官在证据使用禁止中根据“利益权衡”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力,这与“审判中心主义”具有天然密切联系。这种证据排除的规定,实际与英美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具有基本相同的含义。(8)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第2款规定:“在任何公诉方计划将被告人供述作为本方证据提出的诉讼中,如果有证据表明供述是或者可能是通过以下方式取得的——(a)对被告人采取压迫的手段;或者(b)实施在当时情况下可能导致被告人的供述不可靠的任何语言或行为,则法庭应当不得将该供述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被提出,除非检察官能向法庭证明该供述(尽管它可能是真实的)并非以上述方式取得,并且要将此证明到排除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参见《英国刑事诉讼法(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19页。
二、“概括性否定”的否定效力
(一) 欺骗性取证手段的否定方式
侦查手段的合法性问题与侦查所获证据的容许性问题,实际存在一定的区别。侦查手段的合法性来自于法律的授权,或者事先审查条件的满足;侦查所获证据的容许性,实际是审判程序中证据资格审查问题,指向的是司法事后审查,依据的是相关的证据规则。欺骗性讯问,并没有如同刑讯逼供一样在刑事诉讼法第56条中被直接规定为非法证据,实际就是隐含了审判法官的证据考量权力:依据被讯问人能否明确知晓侦查人员所用方法或所出示证据以及欺骗方式是否具有引起虚假供述现实可能,最终判断欺骗性措施所获证据是否应当排除。例如侦讯人员将与作案工具相似的一把小刀放在桌子上,让犯罪嫌疑人主观认为这就是他所用的作案凶器。这种方法可以属于欺骗性讯问,但是不具有证据排除的可能性。因为无论被讯问人是否作案,总能清楚判别犯罪工具是否被讯问者收集到。但是如果侦讯人员向犯罪嫌疑人出示了虚假鉴定报告,那么这种讯问结果应当属于非法证据,应当被排除。因为这些虚构的证据所具有的专业性,存在对被告人的强势压力,具有使其产生难以质辩的权威性。如果足以吸引无辜者暂时选择做出虚假供述,以求得量刑上的好处的欺骗方式就应当被法律所排除。(9)对于欺骗性取证的范围界定,必须考虑到“欺骗性”自身的逻辑涵盖范围,采取极度威胁、指明问供、过度欺骗等方式获取的口供,严重违背任意性自白规则,应属于刑讯逼供范围,所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二)技术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
在技术侦查措施方式的讨论中,学者均假设了“系统外监督”所具有的效果,但是问题在于,依靠检察官或法官掌控的事先批准程序并不能够真正有效地限制技术侦查措施程序的“欺骗性”问题。目前检察院和法院均不具有技术侦查权,如何审查技术侦查措施行为实施的合法性?检察官、法官在技术侦查措施方面所具有的事先审查权力都是有限的、表面的。权力制衡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决定者的权力最少在部分案件范围内具有足以取代被决定者的职权;实践证明,检察院难以对公安机关进行有效的立案监督。另一方面,实践中必须赋予警察在实施技术侦查措施时一定范围内的自主性权力。检察官或者法官,往往远离侦查一线,判断是否实施必要侦查手段的信息来源于警察,事先审查的正确性与及时性均无法保障。即便是在已经实现侦查法治化的德国,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了侦查前的决策程序与侦查后的事后审查程序,但是为了保证侦查及时性,警察仍然具有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较大自主性,司法审查实际上更多依靠庭审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来实现事后审查。(10)谢佑平、邓力军:《德国的秘密侦查制度》,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可见,过分关注技术侦查措施的事先审查程序,可能会夸大刑事法律对于警察的实际约束力。系统外监督可能更多依靠的是权力制衡制度,难以保证决定本身的准确性。“(证据)开示程序能使诉讼各方在审判前对证据作仔细的调查和认真的审查思考,因此而能在审判中针对那些貌似真实的情况进行提问和检验从而获得案件的真实。……禁止提出未经开示的证据,是最有力、通常也是最严厉的制裁措施。”(11)龙宗智:《证据开示与诉讼公正》,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
(三)技术侦查措施证据的否定
国内学者对于卧底侦查的实施,还局限在概念讨论阶段,或者习惯于使用“必要的恶”这种比较模糊的语言论证措施的必要性,并没有直接明确卧底侦查等侦查措施的“必要性”“界限”到底应该止步于哪种程度的行为。也就是说,目前的讨论还没有具体到技术侦查行为的规范问题,以及是否因卧底等行为不当而对侦查获取的言词证据或物证进行排除的问题。因为实践中只有少数的案件公布了技术侦查的特定实施过程,其余具体侦查行为被隐匿在法庭卷宗之外,无法了解卧底的具体细节。
基于对有组织犯罪的应对,警察真正实施卧底侦查时,必然表现为一种有组织协同的侦查行为:卧底警察会有相应的情报收集、后勤保障、调度指挥、资金支持等多个要素的支持。同样,涉及到卧底侦查的取证行为,也并不会局限于某种单一的取证手段,必然是集口供、证言、物证等多种证据收集方式于一体的组合证据收集方式。所以,卧底侦查取证问题,是一种“组合”取证手段。卧底侦查所针对的案件范围,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以避免社会运行规范受到破坏。法官对卧底所获证据的合法性、必要性进行审查判断时,不能基于特定结果进行简单的道德判断,而必须考虑到更加广泛的法律规范的组合和个案中诸多现实价值的平衡问题。如,卧底侦查的法律规范部分至少会涉及到卧底程序启动、卧底侦查行为规范、卧底证据排除原则、卧底警察证言、卧底所获其他证据、卧底警察保护、卧底所获证据的质证、善意第三人利益求偿、卧底侦查的国家赔偿等多个制度的规定。基于刑事侦查行为的不可诉特点,法官的证据审查表面上局限于决定警察侦查行为的有效与否,实际还间接决定了技术侦查所涉及人员的利益保护问题。司法事后审查的结论,既是对特定证据的取舍决断,也可能涉及到个人权利保护问题和社会良好秩序的保护问题。简言之,卧底所获证据的“可采性”问题,难以通过“合法”或者“非法”进行简单的立法划定,而需依赖于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进行综合判断。
是否违背比例性原则是判断欺骗性取证措施是否导致正当性缺失的核心标准。隐匿身份人员采取的秘密取证行为必须与所侦查罪行的严重程度及当时的具体情势相当。在事前审查或事后核准时,审查主体必须结合相关情况作综合判断。隐匿身份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先实施秘密取证行为,但应坚持比例原则,以合适的强制手段对付犯罪行为,能采取较少强制的行为就没有必要采取较强烈的强制行为获得证据。若违背了比例原则,该取证行为即丧失正当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2条对侦查人员在实施隐匿身份侦查中采取的方法做出了具体要求,即不能使用可能引发重大人身危险和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更是禁止采用“犯意诱发型”侦查方法,诱使本无犯意的人犯罪(12)《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对特情介入侦破的毒品案件,要区别不同情形予以分别处理。对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行为人在特情既为其安排上线,又提供下线的双重引诱,即“双套引诱”下实施毒品犯罪的,处刑时可予以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罚或者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世界各国(13)《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75条第1款规定,所有违反该法典要求而获得的证据,不允许在诉讼中使用。该法第235条还补充规定,控辩双方有权从法庭出示的证据清单中申请排除任何证据。如果辩方提出排除证据申请的理由是该证据的获得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则在审议时,证明推翻辨方所提理由的责任由检察长承担。参见《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179-180页。此外,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6条第3款规定:“被告陈述其自白系出于不正之方法者,应先于其他事证而为调查。该自白如经检察官提出者,法院应命检察官就自白之出于自由意志,指出证明之方法。”转引自兰跃军:《论言词证据之禁止——以〈德国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分析》,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1期。根据本国实际纷纷对秘密取证方式、方法和手段作出了相应规定,综合各国规定,这些秘密取证方式、方法和手段具体包括:卧底侦查、诱惑侦查、控制交付、通讯拦截、秘密拍摄、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力量、秘密搜查、秘密辨认、秘密逮捕以及运用其他技术侦查手段和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等。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再一次规定了特殊侦查手段,该公约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允许法庭采信由特殊侦查手段产生的证据,解决了特殊侦查手段所产生的证据的许容性问题。
但是需要明确的问题是,技术侦查措施的资料是否应当移交给审判法官,目前尚不清楚。从理论上讲,在每个刑事案件中,向被追诉人公开指控涉及的证据材料十分重要,只有这样,被追诉人才能够有效地进行辩护。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过程以及所获取的证据,既涉及到本案证据资格判断,也涉及到侦查行为实施合法性审查。所以应当有一定的标准,规定适度公开的范围。在不危及侦查人员安全或者能够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地公开技术侦查措施行为过程。一概不予公布,则可能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公正实施和案件本身的公正审判产生不利影响。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必须向辩护方披露其掌握的有利于或不利于被告方的所有重要证据,包括技术侦查措施所获证据以及技术侦查措施实施过程。为确保被告人得到公正的审判,由于权利限制而对辩方造成的劣势处境必须通过救济程序予以平衡。
三、几种技术侦查措施行为的违法性假定示例
(一)卧底侦查与“Mr.BIG技术”
“卧底侦查”是国家针对有组织犯罪进行的特有侦查方法,一般认为“卧底侦查是指经特别挑选的侦查人员隐藏其原有身份,潜伏于所调查的犯罪组织或环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暗中收集犯罪的证据或情报的一种侦查方法”。(14)杨明:《论卧底侦查》,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就其侦查的实际运作方式来讲,“卧底侦查”与早期国家针对政治案件进行的“暗探”“密探”侦查,除却案件性质上的巨大区别外,在侦查手段方面实际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密探”与“卧底”只有案件性质的不同,并无手段上的不同。(15)米镝:《德国的卧底侦查制度及启示》,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卧底侦查的司法启动程序,实际就是要将卧底侦查限制在特定的案件范围内,避免卧底侦查的滥用。
从卧底侦查的实施行为来讲,卧底侦查的欺骗性主要表现在侦查人员“隐匿身份”以及“秘密取证”(或者“秘密获取情报”)两个方面。“隐匿身份”的欺骗性主要表现在,作为社会正常交往的基础,人们必须能够信赖自己身边的朋友或者亲人,但是“隐匿身份”使得人们可能无法充分信任自己身边的人。“隐匿身份”并没有直接侵犯所有的公民隐私权,也没有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所有内容;“隐匿身份”所侵犯的只是公民社会信赖感这种权利。国家在隐匿侦查人员身份方面的巨大优势,所带来的不是针对公民自己的个人隐私内容是否会被国家得知的不安,而是国家是否会滥用这种信息从而获得侦查中的某种便利所带来的不安(比如说“Mr.BIG技术”(16)一种警察非法获取被告人口供的侦查技巧。See Kirk Luther δBrent Snook.Putting the Mr. Big technique back on trial: a re-examination of probative value and abuse of process through a scientific lens,JOURNAL OF FORENSIC PRACTICE,2016年第2期。“Mr.BIG技术”是指警察组织面对某些重大犯罪,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或者自认时,警方可能会进行精心策划的卧底行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规避羁押讯问中的证据规则。2014年加拿大最高院裁决,对于“Mr.BIG技术”进行更加苛刻的使用规则。“Mr.BIG技术”主要包括“智能探头”(intelligence probe)、“冷介绍”(cold approach)、“方案推进”(credibility-building)、“证据方案”(evidence gathering) 四个步骤。)。“秘密取证”和“秘密获取情报”的欺骗性主要在于取证方式的秘密性所带来的个人隐私泄密风险,以及这种秘密证据能否得到法庭上的“交叉询问”机会。也就是说,公众无法确知与案件无关的个人隐私是否正在被他人窥知以及侦查人员收集的案件证据是否能够在法庭得到公正的评判。(17)龙宗智:《欺骗与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界限》,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对犯罪的侦查是一种极具对抗性的活动,为有效获取证据、查明案情,有时需要采用带有欺骗性要素的侦讯谋略。但另一方面,刑事司法机关对待犯罪嫌疑人的态度与方法,涉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理界限;同时,国家刑事司法行为具有一种社会示范作用。侦讯谋略设计与使用不当,可能损害公民权利,败坏国家形象,损害社会善良风俗,而且也会损害刑事司法效益尤其是长远效益。虽然我们认为在刑事司法中过分强调国家司法行为的“道德洁癖”并不能完美解释和规范具体的司法行为,但是在卧底侦查方面进行一定的法律制度规范,确实可以防止国家司法行为的“过度”问题。
“Mr.BIG技术”存在的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如何提高自认的可靠性和避免偏见。在女王诉哈特一案(18)R v Hart, 2014 SCC 52,大概的案情及侦查经过。2002年8月4日,Nelson Lloyd Hart的双胞胎女儿被溺身亡。警方怀疑是Hart谋杀了这一对双胞胎姐妹,但是因没有充分的指控证据,于是在2004年决定进行“Mr.Big”侦查计划。当时Hart正处于失业期,离群索居。警方卧底将其介绍加入一个非法组织,警方卧底人员在该组织与Hart成为好朋友。在此期间,警方给予大量的经济资助,Hart获得额外15000元收入,多次在全国旅游,出入高档宾馆。Hart视警方的卧底为知己好友,甚至兄弟。最终,Hart分别三次向警方卧底交代自己杀死了双胞胎女儿。一审期间,Hart的这些自认被视为有效的证据,但是上诉审中法官认为其中的两份应当视为无效,一份有效。加拿大最高院认为三份自认全部无效,Hart被无罪释放。中,虽然加拿大最高院并没有限制警察使用Mr.BIG措施进行案件侦查的权力,但是为了保护被告人权利,规定了两项规范要求:所获自认必须保证具有可靠性以及警方已经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预断。其中“自认的可靠性”认为,所有“Mr.BIG自认”必须被预先假定为普通法证据中的“不具可采性”证据,所以刑事案件的控方负有证明Mr.BIG口供的真实性的责任。加拿大最高院同时提醒使用“Mr.BIG自认”的法官,Mr.BIG操作在本质上是暴力性的和强制性的,因而违背了自白任意性规则。
卧底侦查的欺骗性主要表现在,警方所实施的侦查行为一定意义上存在对社会基本道德规则的破坏,或者对人们社交基础性的共识的破坏。这种欺骗性会因为具体卧底人员的操作过程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等级的破坏性。所以对于卧底侦查的实施行为不能秘而不宣,而应在保护卧底人员安全情况下,尽可能的进行法庭盘查。
警察在卧底侦查措施中利用了人们的善良习俗,存在取证行为的欺骗性。警察利用了任务目标的各种心理或者癖好,在其未予防备的情况下“投其所好”,利用了每个人的“互惠”心理,从而获得之后的侦查行为便利。“方案推进”和“证据方案”利用了犯罪组织中的考核晋升方式和群体内部“相互不再设防”的群体心理,取得犯罪集团首犯的“自白”。虽然警方行为针对的是某些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但是这种对有益的道德习俗的利用,总会令人反感。如果这种侦查行为再被滥用于普通犯罪的侦查,国家侦查行为具有因此引起社会跟风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与政府建立法治社会的正常善良习俗的法律目的背道而驰的。
警察利用目标在被警方采取措施期间或者监禁期间进行卧底,可能会滥用警察的各种职权和便利。卧底警察在这个阶段的行为以及“目标”的行为均违背社会交往“一致性”的常规习惯,其行为实际上就是这种社交规则的实际破坏。卧底警察在之前的观察时间就已经基本掌握了目标的各种心理、癖好,自然会对目标产生比较大的“吸引力”,但是这种经过精心布置或者训练的“表现”并不是卧底警察的真实面目、性格。警方利用了被采取措施的人的感情,同时也会涉及到对第三人的感情问题,这其中存在一个度,所有的过度行为取得的证据应当被宣布为无效。
(二)隐秘探话措施及其欺骗性
根据目前发表的“隐秘探话”文章来分析,这种措施也具有类似卧底侦查的欺骗性。“隐秘探话”的措施并不仅仅局限于毒品案件,一些无法找到证据的案件也会使用这种措施。隐秘探话通过“线人”或者化妆侦查员在犯罪嫌疑人不经意间探听犯罪的细节问题。实施的空间大多集中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期间。“化妆”警察或者是受警察指令、指示的“线人”,甚至是出于“立功”目的的同囚室的人,在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信任后,进行“探话”,也就是通过言语刺激、撩拨,使其谈及案件的重要情节或内容,帮助警察查清案件的行为。隐秘探话的实施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投入和警方的组织行为,有时候急于“立功”的其他囚犯自会“自告奋勇”。但是在本质上,隐秘探话依旧是一种特殊的卧底侦查措施,因为这种措施具有卧底侦查的主要要件,即“欺骗性”,其主要的实施目的也是为了获取特定证据。
隐秘探话的欺骗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信任、同情以及悔过。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善良习俗。这些习俗就如同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其中就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其是人们之间形成协作关系的重要内容。基于信任,我们可以与别人进行交流,甚至是对那些“陌生人”也会进行适度的相互关照。隐秘探话的侦查行为,会对那些被囚禁起来的人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隔阂,当然会导致囚室中的压抑气氛。怜悯之心,人皆有之。利用他人不备之时,进行言语撩拨,进而获得自己减刑的机会,实际上是对对“怜悯”善意的破坏。如果囚室中出现一例成功案件,则对其他同囚室的羁押人员产生比较恶劣的“示范效应”,如果群起而效,囚室中就没有人再去同病相怜。在正常社会交往中,悔过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基本要素。人们对于自己的过错真诚悔过,意味着对于过往的错误的真实认识,也意味着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一种重新选择。现代刑罚的减刑制度、假释制度,其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鼓励他人告发,而是为了鼓励有过必改,鼓励罪犯能够正确认识过往的错误行为。隐秘探话实际给被囚禁的人做了一种错误的“捷径”示范,不论是卧底警察实施,还是暗示其他人实施的“隐秘探话”,均是告诉被囚禁的人,告发他人的罪过可以减轻自己的刑罚。
(三) 线人及其欺骗性
“线人”是警察侦查案件时的情报网络中的有效组成之一,也是一些行政执法机关进行某些社会管理工作时所广泛使用的一种情报来源。(19)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关于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卷烟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其中第5条规定“对于举报、协助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卷烟活动有功的单位或个人,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可见,国家机关的行政行为、刑事司法行为中实际是广泛使用“线人”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于“线人”的法律规定并不明确,甚至连“线人”的概念都难以概括。“线人”广泛存在于社会各界,他们可能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与“被举报人”素昧平生,只是基于“义愤”或者基于“奖金”进行举报;也可能是“被举报人”的生意伙伴、竞争对手或者与“被举报人”存在其他社会利益争端而进行举报。但是在毒品案件中,还存在一种情况,即警察通过奖金引诱或其他方式,使得一些吸毒人员汇报情报,极端案件中甚至存在警察与吸毒者勾结在一起,伪造情报来源,制造假案的情况。线人在现行刑事侦查情报来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相关法律漏洞也是极为明显的。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线人的法律地位等问题,(20)吕志祥、王凤涛:《法律视野中的“线人”及其制度构建》,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但是笔者认为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对线人提供情报的行为进行法律规范。因为从行为意义上来讲,线人的某些特征是与卧底侦查完全一致的。“线人”提供线索的行为虽然不是警察正式的侦查行为,但是往往“事先接受警察资助”或者“事后接收奖金”,从而构成为警察侦查行为的“延伸”,故应当与警察侦查行为等同视之。虽然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基于“义愤”,并不以经济报酬为目的所进行的举报,但是依旧应当视为警察有效促成之侦查行为。因为,这种行为的结果是由警方获利的,所以应当视为警方组织的行为。
“线人”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鼓励告发和质证权困境。告发不法是国家用来与犯罪作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这种手段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国家的初衷是鼓励所有知情人告发不法行为,但是当告发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威胁工具。比如,为获取不法利益甚至出于犯罪目的的告发,就不能认为是合理的。因为这种告发实际使得国家成为告发者的权力背书人。一般来讲,线人是无法出庭作证的,这就会导致刑事审判中被告人的质证权无法实现。理论上讲,当线人所做的证言成为案件定案的依据时,线人就有必要出庭接受辩方的证据质证。但是线人的取证行为,不论是基于经济利益还是基于其他目的,只要国家使用了线人提供的情报,即意味着国家应当保证线人的安全以及线索来源的隐秘性。如果要求线人出庭,无疑又破坏了国家与线人之间的先期“承诺”,存在国家违约责任。
四、欺骗性取证行为的审查途径
隐匿身份侦查之所以能够在刑事侦查中奏效,就在于其隐秘性可以有效抵御有组织犯罪等反公开侦查的能力。警方总会千方百计地防止秘密力量的身份和取证行为的泄密。但这也意味着被追诉方很难在事后知悉隐匿身份侦查的情况,从而无法针对证据收集的过程寻找隐匿身份侦查所获证据的瑕疵。在英国,有关隐匿身份侦查情况或资料的开示可以适用于公共利益豁免规则。尽管在1993年的Ward案中,英国法院宣称应开示所有侦查记录,当然包括技术侦查措施等手段在内的所有使用情况,以便于对侦查机关所获证据在公开法庭上予以质询。(21)Chrisje Brants&Stewart field. Legal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e and Procedural Traditions: Towards a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avertand Proactive Polic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and The Netherlands, in Nelken, D. ed. Contrasts inCririminal Justice. Advances in Criminology,Aldershot: Ashgate Dartrnouth,2000.p.101.但后来在《刑事程序与调查法令》中又恢复了公共利益豁免的范围,对辩方知悉秘密信息的权利进行了限制。在大陆法系国家,即便存在针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情况记录,侦查控诉机关通常也会将技术侦查措施手段的使用情况排除在案件卷宗记录之外。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是,隐匿身份侦查有时只是提供获取证据的线索,而不直接提供证据,不产生证据的隐匿身份侦查没有必要记录在卷宗中。在有些国家,如荷兰、许多隐匿身份侦查措施开始于侦查阶段启动之前,根据2001年之前的法律,这些行为无须记入卷宗。但是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荷兰2001年立法时开始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必须在侦查报告中完整地记录秘密取证的实施情况,并要求详细记载侦查取证的收集以及获取的证据信息。
(一)“概括性否定”与证据来源审查
从卧底侦查的实施过程来看,欺骗性取证主要包括伪装潜入、骗取信任、收集证据及情报三个步骤。按照这样的顺序,卧底侦查等技术侦查措施行为的主要危害可能存在以下几种可能性:第一,没有经过批准程序或违反批准程序的某些要件而实施的技术侦查措施行为可能导致的危害,即卧底侦查的“出界”问题;第二,技术侦查措施行为在实施方面存在问题,可能因此导致的社会危害,比如卧底打入犯罪组织时所实施的手段以及打入犯罪组织后为博取信任所实施违法行为问题,技术侦查措施行为对第三方的伤害问题,即卧底的“代价”问题;第三,卧底在进入犯罪组织后,主要目的是负责收集犯罪组织的证据和情报,其行为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度”,如果超出这个度,卧底侦查所导致的伤害超出犯罪组织的原罪问题,即卧底侦查的“失控”问题。卧底侦查的启动程序所担忧的主要问题是将技术侦查措施行为可能会被滥用于一般案件,不但浪费警力也会导致社会治理方面的负面作用。以笔者所见,欺骗性取证的主要法律问题就是证据的合法性审查问题,因为无论是警察还是检察官、法官进行事先审查,主体虽然有所变化,但据以裁决的侦查线索必然是不十分充分的。排除对于系统内监督的不信任感,法官、检察官的开启决定,在实体真实性方面未必会绝对优于侦查机关决定;但是系统外监督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对于侦查一线办案自主权的完全剥夺,倘若因此丧失相应的侦查时机,整个社会为权力制衡目的所付出的实际代价就比较高昂。概括性否定无法向公众解释卧底侦查的必要性以及卧底侦查的具体约束内容。所以欺骗性审查的主要内容应该集中于卧底侦查行为的“度”和“失控”问题。因为这实际上涉及到卧底所获证据的效力以及这些法律证据在庭审中的可能适用范围问题,就本质上来讲也是证据资格问题和证据排除问题。证据排除在这里既是司法所实施的技术侦查措施的事后监督,也是法庭所进行的非法证据排除,即审判权运行的内容。卧底侦查所获证据并不仅仅是指卧底警察的证言,更多地应该包括卧底所获信息、卧底期间秘密提取的证据以及非警察身份的人卧底所获证据等非常现实和具体的问题。
(二)“概括性否定”与取证行为审查
事实上,卧底侦查等措施的存在合理性是与特定案件中欠缺有效事实发现手段和侦查取证手段密切联系的,正因为如此,卧底侦查只能严格限制,不能完全禁止。完全禁止实施窃听、卧底侦查等具有欺骗性侦查手段的国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很多国家对欺骗性取证采取一定程度的“容忍”,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侦查手段具有明确的“现实性”和“必要性”。“现实性”是指在法律规范侦查手段之前,这种侦查行为就早存在且广泛实施,警察机关并不会因为没有法律的具体授权就不进行技术侦查措施,“实践先行”是秘密侦察问题中比较敏感但又实际存在的问题;“必要性”是指国家必须具有这种侦查手段和途径,非此不足以应对特定的犯罪,所以法律不可能建立起对于技术侦查措施手段的全面禁止或者全面司法审查,只能规范实践中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错误或者违法侦查行为,但仍需要部分保留警方一线侦查人员的办案自主权。
(三)技术侦查措施行为合法性审查的条件
卧底侦查的法律规范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卧底侦查的程序控制,主要是指卧底侦查实施前的审批程序;其二是卧底侦查所获证据的司法审查。这种审查,既表现为对卧底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也表现为对卧底所获依据的合法性审查。技术侦查欺骗性问题是司法审查的重要内容。卧底侦查的程序控制主要包括警察内部的启动程序控制与司法事前审查两种。警察内部程序主要是按照警察部门内部的层级,需由一定级别的上级警察批准后方能进行卧底调查或者“潜入”“化妆”“线报”等特殊调查程序,为警察内部的控制、掌控;司法事前审查主要是规定特定的司法机关进行这种特殊侦查程序启动的控制,主要表现为程序外控制。基于对警察行为的不信任感,人们更倾向于对警方行为进行系统外控制,但是这种思路实际忽略了侦查及时性的要求且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司法所审查的准确性,甚至可能忽视了对于卧底侦查所获证据事后审查的实际效力。在卧底所获证据审查方面,对那些严重违反现行法律,有违宗教传统、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或者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威胁、引诱和欺骗性取证,应视为非法证据并予以排除。这对于实践中规范卧底侦查具有特殊的效力。
笔者认为,我国刑诉法第52条禁止的只是那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威胁、引诱、欺骗性取证,而非禁止所有带有威胁、引诱、欺骗性因素的侦查谋略。国家实施带有欺骗性因素的侦查措施,主要原因在于特定案件存在的证据收集难度。欺骗性侦查措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或者在侦查一定范围内案件时存在,其合理性主要在于这些案件对于国家社会秩序的巨大威胁以及国家侦查机关在了解实际案情、收集特定证据时的巨大困难,出于维护整个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必须要容忍一定范围的“欺骗性侦查手段”。
结 语
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其中第43条提出:“落实和完善技术侦查证据的随案移送和法庭调查规则,确保庭审发挥实质性作用。”这就需要在理论研究中进一步明确技术侦查行为以及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是否应该受到法院的司法审查。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不得不依托特定的国家机构,但是这些国家机构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自己的职责,往往并不仅仅决定于权力归属,而决定于权力的具体行使。司法审查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行为所获取的证据能够记载并反映整个执法过程的合法性。欺骗性取证方式的 “概括性否定”意味着法律对于行为性质的既定质疑态度,但是并不是证据排除的具体程序和判断标准。审判中心主义决定了所有进入法庭的证据,都必须依靠庭审的全面审查。
单纯模糊性的证据资格标准和作为某一类证据是否可以在审判中适用的“一刀切”态度,容易导致司法在证据审查时局限于证据形式性审查。如果法律规则、证据规则的设置存在模糊或者不明确的地方,这些案件中的证据审查会流于形式,最终导致社会秩序维持的失效,伤害国家的现实掌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