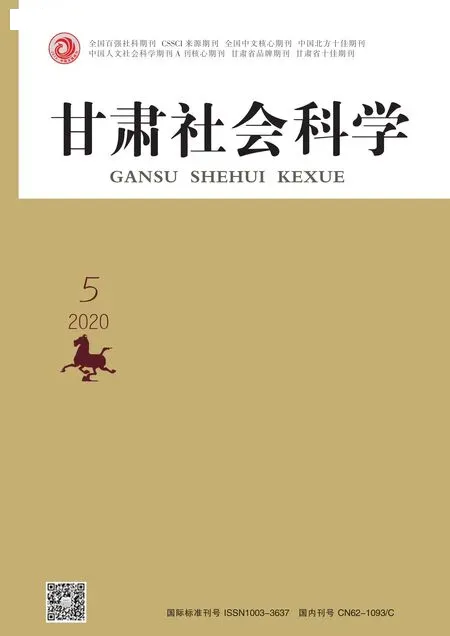永嘉学派对程学话语体系的突破
冀晋才 曾振宇
(山东大学 a.历史文化学院;b.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 250100)
提要: 南宋初,因掌控儒学话语权的程学难以解决强国御辱、恢复中原等现实需求,儒学界兴起了一股谋求突破程学的学术思潮。永嘉学派以情欲论为突破口展开了尝试,程学话语体系本身的局限性也为其提供了突破的缺口。在对“情”和“欲”的概念诠释上,摒弃程学用“气”来诠释“情”和“欲”的方法,否定了程学将“情”和“欲”割裂于人性的观点,直接从现实生活中观察“情”和“欲”及其善恶,并将二者视为人性之固有内容;在对以治欲为中心的修养论和治国论的认识上,否认程学“万事以修身为先”、修身即“穷理、去欲、复性”的观点,指出圣王之道蕴含于其实政实德之中、以保民养民为要。由此,永嘉学派对程学之天人观、“道”和“道统”进行了系统地批判和重构,基本实现了突破程学话语体系、重构儒学的学术意图。
程学,或称洛学,由北宋思想家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所创。二程学识渊博、思想深邃,长期讲学伊洛,弟子门人遍布大江南北,使程学广播天下。北宋末、南宋初,程学因暗合了朝廷将国难罪责归咎于王安石(1021—1086)及其所创之荆公新学①而被扶持,逐渐掌控了儒学学术话语权。然程学长于修身,在强国御辱方面内容不足,难以应对危局,引起了部分士大夫对其价值的怀疑,因此在南宋时期兴起了一股突破程学、开创新的儒学思维的学术潮流。永嘉学派正是其中的一支。因永嘉学派主要代表学者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叶适(1150—1223)等皆为永嘉人(今温州地区,从东晋至隋朝曾称永嘉郡),因而得名。
情欲论在二程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钱穆先生曾指出:“二程再不从宇宙无生命界转入生命界,来纡回这一条漫长而无准的路。他们主张直从生命界教人当下认取。他们只想从生命界再推扩到无生命界。”[1]此语道出了二程思想体系建构的思路:从对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的考察,向人性论、宇宙论领域推扩。蒙培元先生指出:“只有情感,才是人的最首要最基本的存在方式。”[2]而论及情感,就不能忽略欲望,这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可以说,情欲论是二程思想体系建构的基础,也应当是反程学学者能否从根本上突破程学的关键。以往对永嘉学派的研究很少涉及其情欲论畛域,事实上情欲论是薛季宣在思想上与程学分道扬镳的起点,也是永嘉学派“事功”思想建构的依据,更是永嘉学派谋求突破程学话语体系而选取的“突破口”。
一、程学与永嘉学派对“情”和“欲”概念的认识
(一)共识:“欲”分善恶、修身治国以治“欲”为旨归
程学与永嘉学派都肯定了“情”善,而将人之善恶纳入“欲”概念范畴进行探讨,在修身和治国理念上都以治“欲”为旨归。
二程对“情”“欲”作了概念分离,提出“情”乃“性之动”所生,“欲”乃肢体五官感外物而动所生的观点。程颢认为:“只性为本,情是性之动处。”[3]33程颐认为:“才有生识,便有性,有性便有情。无性安得情?……(情)非出于外,感于外而发于中也。”[3]204即“情”是天道、天理、天命在人之生活日用中的体现。“自性而行,皆善也。”[3]318“性”是“天理”之在人,是“仁义礼智信”。因为“性”善,所以“情”善,因此“情”以上诸概念皆全善。“欲”概念存在两面性,作为人之生物本能、生存前提,自然有其存在之合理性。然人心逐“欲”过度,又会使思虑害义、言行失礼。因此,程学的善恶之辨最终落实到了“欲”概念畛域。程颢言:“人于天理昏者,是只为嗜欲乱著佗。”[3]42程颐言:“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以至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3]319“口目耳鼻四支”容易被外界之物欲所引诱而产生“欲”,肢体追逐欲望失度,遂使“心(性)”失去了对人身的控制、对内在本性的向往,导致思虑言行失度而产生恶念恶行,故而二程在修养论和治国论上以治欲为旨归。
永嘉学派也明确地肯定了“情”善,将致人为恶之因定位于“欲”的范畴。薛季宣言:“修其性,见其情,振古如斯……情生乎性,性本乎天。……六情之发,是皆原于天性者也。……先王有礼乐仁义养之于内,庆赏刑威笃之于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欲。”[4]360薛季宣在肯定“情”善的基础上,将“欲”摘出单独立说。“礼乐仁义”养的是君子之德性,“庆赏刑威”格治的是小人之“欲”。薛季宣强调人欲之可向恶性,阐明了圣贤之道的实质是以法度治理泛滥之人欲。陈傅良十分重视《尚书·商书·仲虺之诰》中“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一言,认为“人所以相群而不乱者,以其有君父也。……苟无君父,则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5]1712。即因为有“欲”,人与人之间才会产生争斗。齐家治国之要旨,在于节制人“欲”。叶适论及“古之善政者”时言:“能防民之佚游,使从其教;节民之醉饱,使归于德。”[6]151即人欲失节为坏德之因,为政之要是对人欲的节制与调和。
(二)分歧:“情”和“欲”的概念本质、与人性之关系、修养治国论主张
程学和永嘉学派对“情”和“欲”概念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宇宙论、人性论、修养治国论三个层面。
首先,在宇宙论层面,程学用“气”来阐述“情”和“欲”及其善恶;永嘉学派则完全摒弃程学“气论”,直接从现实生活中观察“情”和“欲”及其善恶。
二程在“情”和“欲”的内容上并无创新。“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七种情[3]577。这与《礼记·礼运》中所言之“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基本一致。“欲”是五官肢体之本能欲求。但二程将“情”和“欲”纳入“气”的范畴,深化了二者的内涵。二程将谈论焦点集中于人身上,认为人体由阴阳二气聚合而成。体内存“清(阳)气”,故人能与天理、天命相通;体内存“浊(阴)气”,故人心易为外界之物欲所诱而嗜欲。
程颢通过人体之气的动静来阐明“情”和“欲”的生成。天地随机地将清浊融合的一团团气分配给每一个人,即人之禀气。程颢以水喻之:“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夫所谓‘继之者善’也者,犹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3]10-11人之后天生长发育过程中呈现出的有善有恶的人性,即“气质之性”,正是根源于清浊混杂之禀气。“性”只能与“清气”相通相融,媒介为心。程颢言:“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3]56“性”通过“心(清气)动”澄现出来,便是“情”。“欲”之生是人体内之“浊气”动,具体说是五官肢体之气感应外物而动所生。
程颐将人体之气分为“真元之气”与“外气”两部分。“真元之气,气之所由生,不与外气相杂,但以外气涵养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气,但真元自能生气,所入之气,止当阖时,随之而入,非假此气以助真元也。”[3]165-166“真元之气”在人而言是“元气”,在天地而言是“阳气”,等同于程颢所言之“清气”。“真元之气”是无纤毫杂质的清明之气,“外气”则是含有杂质的浑浊之气。程颐言:“阳气发处,却是情也。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3]184蒙培元先生论道:“这显然不是指物质性的存在,而是与人的道德精神和意志等等直接有关。”[7]“真元之气”沟通了“性”与“人”,从物质的角度解释了人性何以本善,进而解释了人情之善。“外气”与大地万物之气同质,故而能够感通外物。在人而言,体现为五官肢体等对物欲之追逐。
永嘉学派摒弃了程学之“气论”,直接从现实生活中认识“情”和“欲”。有学者言:“永嘉诸子思想中的‘欲’则更多的是对自然存在的人欲的总结”[8],“情”也是如此。永嘉学派不承认程学之“七情”说,提出了“六情”说:“六情之发,是皆源于天性者也”[4]360。陈傅良和叶适则只言“欲”而不言“情”,他们有意避开对“情”和“欲”的概念辨析,更强调人欲之可向恶性,意在进一步阐明圣贤之道的实质是以法度治理泛滥之人欲。
其次,在人性论层面,二程思想中“性”从属于“天理”范畴,“情”和“欲”从属于“气”范畴。永嘉学派则摒弃程学之“理气论”,直接视“情”和“欲”为“性中之物”。薛季宣说:“喜、怒、哀、乐,皆性中之物也。”[4]385陈傅良强调“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事实上便是肯定了“欲”为人生而具备的本能。叶适强调人之“物性”:“人之所甚患者,以其自为物而远于物。夫物之于我,几若是之相去也,是故古之君子……喜为物喜,怒为物怒,哀为物哀,乐为物乐。”[6]731叶适认为,人只是物,能够主宰或影响人的也只有物,人之情感是肉体感物而发。更倾向于将“物性”视为人之本性。
最后,在修养和治国论上,二程主张万事以修身为先,修养的主要功夫是穷理去欲;永嘉学派则更重视实政治欲。
二程将修身置于万事之先,“欲治国治天下,须先从修身齐家来”[3]293,并基于“气论”对修养论作了不同阐述,但殊途同归,都以穷理去欲为旨归。程颢注重于在“心静”处感悟本性,修养方法上主张“节嗜欲,定心气”,即克制内心之物欲、摒弃内心一切杂念,虔诚地体悟圣贤之道,给“人心”找一个正确的主宰。程颐强调人体内之二气之分,故而在修养论上主张人心应当逐渐摆脱“外气”的影响,归依“真元之气”的主宰。道德礼义根源于“天理”,“心”循此而发令是为行“天道”,此“心”被程颐称为“道心”。人之肉体易受外物引诱而形成欲望,“心”循此而发令是为“人欲”,此“心”被程颐称为“人心”。因此,修养便是去“人心(人欲)”、存“道心(天理)”。
永嘉学派对修身之学并未深耕,重视实政治欲。永嘉诸子并不反对节制人欲,但不赞同过度地打压人欲。他们认为,圣王治国之道既包含节制人欲的礼乐刑罚,也包含保障百姓实现合理生存欲望的保民实政。薛季宣概括为“礼乐仁义”与“庆赏刑威”。陈傅良进一步强调君王的“保民之责”,“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驱猛兽,使斯人脱于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相保也,则禹、周公之责不塞。”[9]250叶适的观点更加尖锐,批评孟子之学“揠义理就血气”[10]199、“专以心性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10]207。即一味地强调去欲存理是“揠苗助长”,导致为学修身远离了生活日用;一味地主张诚心悟性,使内圣外王脱节,背离了尧舜的王道。因而提出“天子以保民为职”[6]846“先王之政,以养人为大”[6]182等观点。
从程学和永嘉学派在情欲论上的分歧来看,永嘉学派对程学已然十分不满,决心另起炉灶重建儒学体系了。促使永嘉学派产生突破程学话语体系意图的原因不仅在于国势严峻的南宋更需要强国保民的实学,也在于程学话语体系本身的局限性。
二、程学话语体系的局限性
程学话语体系存在诸多理论缺陷,尤其在“去欲”修养论方面,这既是永嘉学派突破程学话语体系的原因,也是其绝佳的突破口。
(一)“仁”与“礼”内涵难定
程颐对人所应奉行之“天道”大致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尤重“礼”。“主敬”是程颐修养论的基本精神,道德修养上敬“仁”,行为修养上敬“礼”,是去“欲”修身的前提。程颐的具体表述为:
一不敬则私欲万端生焉,害仁此為大。[3]1179
主一之谓敬。[3]1173
仁则一,不仁则二。[3]1175
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与礼非有异也。[3]322
敬即便是礼,无己可克。[3]143
即同时存在“敬仁”与“敬礼”两个概念,似乎二者之间可以等同视之,但又有微小的差异。“仁”为“礼”之本,“礼”为“仁”之用。儒家对于“仁”的阐释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并无定论。杨泽波言:“两千多年来,关于仁的争论无以计数,讨论仁的著述汗牛充栋,但始终缺乏一个明确肯定的说法。”[11]孔子兼从心与行两方面释为“爱人”“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孟子侧重论心,以人心皆存“恻隐之心”(《孟子·告子上》)为依据,将“仁”视为人性之固有内容;二程更是直将“仁”视为人性之全体,“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3]14。因此,所谓“敬仁”,依孔子之意为“敬德”,依孟子之意为“敬君子所性”,依二程之意则为“敬性”,难以有个确切的定义。鉴于此,程颐强调“敬礼”,毕竟“礼”的内容是比较具体的。但“礼”之内容也不固定,代有损益。程颐言:“古礼既废,人伦不明,以至治家皆无法度,是不得立于礼也。”[3]200又言:“‘礼,孰为大?时为大’,亦须随时。”[3]171一方面言古礼既废而致当下人伦不明、法度废弛,使人不能循古礼而修身,言下之意循古礼方是循道;另一方面又主张人们循今礼。那么到底循哪个礼方是“循道”呢?进一步言,古礼既已残缺,今礼又多有不合圣贤之意处,那么“循礼入道”便有名无实了。“敬仁”与“敬礼”二说皆根基不实,去“欲”修身的主张便存在被根本推翻的可能。
(二)“人心”与“道心”难以界分
“人心”与“道心”就“心”上说体现为从欲或从道。意念生于内心,只能自我忖度,他人难以测度。单靠人心对“仁”与“礼”的“敬”“诚”来实现“去人心”“存道心”,能做到者毕竟少数。“人心”与“道心”就事上论体现为公与私。这里需要先确立一个评判的主体,行为者自己或他人,因每个人喜好不一、对公与私的认识也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的评判标准。如果说“公”是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为他人着想,那也很难把握尺度。没有什么能比父母对子女更无私了,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认为自己在全心全意地为其子女考虑,但却常常招致子女们的批评怨恨。若评判者为他人,则不论行为主体做到如何仁义,都免不了被批评攻讦,即使是孔子、孟子、朱子乃至程颐自己,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基于此,朱熹对程学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就事上论理欲之分。他有两种解释:一是“盖做合做底事,便纯是天理。才有一毫计较之心,便是人欲。”[12]1093-1094即不论意念产生的根据为何,只要是必须做的事情就果断去做,如果做之前先思考公私、权衡利弊那便是“人欲”。二是“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12]223如“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12]224,即欲望的实现恰到好处便是“天理”,过度实现便流于“人欲”了。如此,人们只需在日常为人处世中把握一个度即可,再不需为如何静心息欲或分辨公私而为难了。因此,程学之“去人心、存道心”的修养论主张只是一种模糊的理论构想,既无明确的操作说明,也无外在的强制与监督,最终难以落实。
(三)理论的现实困境
理学家们往往不掌实权,道德亦不具备强制性,因而欲引导人们普遍地“诚”于“道”、“敬”于“礼”,对二程来说最有效的手段仍然是宣传“天人感应”:
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见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积之多者,亦足以动天地之气。如疾疫之气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见,然后为见也。更如尧、舜之民,何故仁寿?桀、纣之民,何故鄙夭?才仁便寿,才鄙便夭。寿夭乃是善恶之气所致。仁则善气也,所感者亦善。善气所生,安得不寿?鄙则恶气也,所感者亦恶。恶气所生,安得不夭?[3]224
二程将自然界的水旱灾害、人的福寿灾祸皆归因于统治者的道德修养。若统治者能节欲修身、施行仁政、教化百姓崇德向善,则国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境安宁;若统治者纵欲失德、暴政虐民、未能很好地教化百姓,则会招致日食、月食、地震、干旱、蝗虫、战争等灾祸。然就现代地理学知识来看,很多自然现象、自然灾害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不以人之贤愚善恶为转移。倘若一发生灾祸便谴责人的道德修养,难保不会出现“冤情”,由此也降低了程学的可信度。
(四)通过改变气质来实现修身目的很难实现
从“气论”层面审视,程学修养论的实质是不断地改变人之“禀气”之质,使之不断“清明”。“除是积学既久,能变得气质,则愚必明,柔必强。”[3]191“养气者,养之至则清明纯全,而昏塞之患去矣。”[3]274最终要将人体内之“浊气”根除,只留“清气”。然张载言:“(气)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13]二程也言:“地气不上腾,天气不下降。”[3]1226从“清气上浮”的特质论,若人体纯是“清气”,将何以立足于地。进一步说,即便如尧、舜、孔子那样“禀气清”的圣人,不也曾是立足大地、有情有欲的鲜活生命吗?因此,程颐所主张的彻底地去人欲、存天理在“气论”上立不住脚,在事实上也永无彻底实现之可能。若学者皆陷溺于这个漫长的、永无止境的“改变气质”过程中,则齐家、治国、平天下诸事怕是要荒废了。
总之,程学要求人们克制私欲、修养道德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引导人们将大好时光用于探索一个虚无不定的“天理”,而荒废经世致用的实学,于己于国害处极大;要求人们彻底地穷理去欲,去完成一个永无实现可能的修养目标有些荒谬;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立身处世也不近情理。程学话语体系中的这些局限性与南宋时期强国保民的迫切需要格格不入,故而遭到了永嘉学派的严厉批评。薛季宣批评其“言道而不及物,躬行君子,又多昧于一贯,不行之叹,圣人既知之矣。”[4]332陈傅良批评其“乃一切屏事,忘言后已。高沦虚无,而卑者滞物,卒不合。”[9]615叶适批评说:“议论胜而用力寡……非当世之要言也。虽有精微深博之论,务使天下之义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6]759从中也反映出永嘉学术突破程学、寻求儒学思想转型的强烈诉求。
三、永嘉学派对程学话语体系的突破
永嘉学派从情欲论出发,对程学的天人观、“道”论和“道统”进行了突破,意在全面突破程学话语体系、重构儒学。
(一)突破程学的天人观
“欲”是永嘉学派突破程学天人观的关键。程学天人观的基本观点有二:天主宰人与天人无二。首先,“万物皆本乎天”[3]1227,万物与天如同人与父母之关系。万物之生命皆来自于天,故而应当顺天而行,这也是人之为人、为官、治国诸事之正当性的来源。二程言:
动以人则妄,动以天则无妄。[3]1190
顺天而行道者,天民也。顺天而为政者,天吏也。[3]1266
王者奉若天道,动无非天者,故称天王。命则天命也,讨则天讨也。尽天道者,王道也。[3]1243
为人、为官顺从天道,方能得到天之护佑;君王奉行天道,方能永葆天命。人对天命只能无条件服从,不得有丝毫违逆。
其次,天人无二,即天命与人性无二。二程言:“元气会则生圣贤。”[3]83“圣人之心,与天为一”[3]1261,故而圣人之道便是天道,圣人之德即天德。又言:“天德云者,谓所受于天者未尝不全也”[3]1257,即天德完善无缺、大中至正,人只能诚而循之,绝不可以私意揣度。
永嘉学派则认为,天德存在不完备处。叶适言:“天德虽偏,必以人德补之……若后世治偏尽性,必至于圣而后用者……枉其才,弃其德者也。”[10]52叶适推翻了程学思想中“人”只能小心翼翼地领会“天命”、顺从“天道”的天人观,主张“人”应当通过积极的行为去弥补“天德”之不足,使“人”摆脱了“天”的控制,阐明了“人”的自我意识和事功行为的正当性。
(二)突破了程学对儒家“道”的定义
程颐从天人观的角度将儒家的“道”定义为:“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命在人则谓之性”[3]1170,“循性曰道”[3]1182。言“道”是天命,其依据为《易》,体现在人的修养上便是“循性”。永嘉学派则认为,既然天生人性存在不完备处。由此,永嘉学派逐步地推翻了程学对儒家“道”的定义,并认为圣贤用以格治人欲、平治天下的刑罚制度的内在精神才是真“道”。
首先,推翻了程学“道之体为《易》”的说法。
二程将《易》视为天道之载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之可闻。其体则谓之《易》。”[3]1170“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3]690《易》中包含着天道,人只能从中体认天道,对其中蕴含的义理只能全部无条件服从。叶适明确反对这一观点,他说:“《易》非‘道’也,所以用是‘道’也,圣人有以用天下之‘道’曰《易》。”[6]695他在解读《易·系辞》中“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一言时说:“然则天地固准易,而易非准天地也,且既已准而从之矣,又安能弥纶之乎?”[10]42李存山先生阐述说:“叶适易学的一大特色就是要解构传统的易学哲学体系,这更表现在他否认《系辞》的‘易与天地准’和‘太极’说。……叶适的意思是说,天地之变化本来是决定《周易》之道理的,而并非《周易》决定了天地之变化……既然是《周易》符合而遵循了天地之变化,又怎能说《周易》已经把至大的天地间一切的变化都囊括在内了呢?”[14]既然“体”被否定了,那么所谓的“理”“性”也便站不住脚了。
其次,以尧舜等圣王的治欲手段为依据,重新诠释“道”。
永嘉学派以《尚书》为依托,重新梳理了尧舜禹等圣贤们的“人德”,逐步赋予“道”新的涵义,即内圣外王交相成。薛季宣概括先王之道为“礼乐仁义”与“庆赏刑威”,先王行“道”最终实现的效果为:君子皆实现其修养心性之目标,小人皆满足其口腹之欲。陈傅良用《尚书·商书·仲虺之诰》中“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一言作为薛季宣“欲”论之支撑,言治国齐家之根本目的便是平息血气争斗之心、使人们和谐共处,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便是“明天子”,是圣君。
叶适进一步深化并完善了薛季宣内圣外王合一的“道”论,建构了以“皇极”“大学”和“中庸”三合一的永嘉学派“道”论体系。他说:“在唐、虞、三代之世者,上之治谓之皇极,下之教谓之大学,行天下谓之中庸,此道之合而可明者也。”[6]726
叶适阐述“皇极”为:“极之于天下,无不有也。耳目聪明,血气和平,饮食嗜好,能壮能老,一身之极也;孝慈友弟,不相疾怨,养老字孤,不饥不寒,一家之极也;刑罚衰止,盗贼不作,时和岁丰,财用不匮,一国之极也;越不瘠秦,夷不谋夏,兵戈寝伏,大教不爽,天下之极也;此其大凡也。至于士农工贾,族性殊异,亦各自以为极而不能相通,其间爱恶相攻,偏党相害,而失其所以为极;是故圣人作焉,执大道以冒之,使之有以为异而无以害异,是之谓皇极。”[6]728“皇极”是统摄、沟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之“道”。“极”是社会上每一个个人、家庭、群体、国家各自追求的欲望实现的最佳状态,“皇极”是普天下之个人、家庭、群体、国家在不相侵夺、和谐共生的前提下皆能各自实现其欲望的理想社会状态,圣人之道的主要作用或精神便是对社会普遍欲望的调和与节制。
叶适通过重新阐述“大学”“中庸”两个概念,意在将经国济世的实学、实政纳入“道”的范畴中,从而确立圣贤之道“内外交相成”。程学强调《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要求学者严格遵守。二程解《中庸》为“反本”之学,“故君子贵乎反本。……惟循本以趣之,是乃入德之要。……反本之要,吾心诚然而已。”[3]1164此“本”即“性”,也就是说圣贤之道重在穷理复性。叶适则认为:“唐、虞、三代,内外无不合……今之为道者,务出内以治外也……守其心以自信,或不合焉,则道何以成?”[6]727言尧、舜、禹三王之道,并无分内圣外王,而是内外合一。陈锐指出:“(叶适)反对那种‘各执其一以自遂’的态度,但他却不是要在两个极端之间选取中道,而是强调两者的不可分离或‘相合’,义与利、形而上与形而下、内和外都是如此,‘仁智皆道之偏也’。”[15]叶适认为的“中庸”之道,正是内圣外王的浑然一体。
(三)突破程学“道统”
永嘉学派从尧舜禹等先王的治欲理念中探索其“道”或“人德”,并以之为依据重建了儒家“道统”,同时也推翻了程学的“道统”。
朱熹弟子陈淳曾梳理过理学“道统”:“自羲皇作《易》,首阐浑沦,神农、黄帝相与继天立极,而宗统之传有自来矣。尧、舜、禹、汤、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为三纲五常之主。皋陶、伊、傅、周、召又相与辅相,施诸天下,为文明之治。”[16]即在程学话语体系中,“道”“天理”“性”内涵一致,即“仁义礼智信”,或只言仁义。圣王生而气清,道德完备,自可化育百姓,礼乐政刑等只是手段。因此在陈淳所梳理的程朱学“道统”中,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重德化,故而作为“道统”之主干;皋陶、伊、傅、周、召等重实政,故而为辅助。
永嘉学派不认同程学的“道统”建构理念,认为先王们的“人德”正体现在各自的治欲实政和实德中。薛季宣认为,圣王们“礼乐仁义”和“庆赏刑威”并重,方使“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欲”。陈傅良认为,正是圣王们肩负起了其保育、教化百姓之责,才实现了人们的群居不乱。叶适重新建构了儒家“道统”,并进一步对圣王之德进行了重新阐述。叶适主张以尧、舜、禹、皋陶为“道统”首,他说:“故考德者必先四人(尧、舜、禹和皋陶),其次伊尹,又次文、武、周公。”[10]60将皋陶、伊尹置于文、武、之前,这与程学之“道统”大相径庭。这一排序基于他对圣王之政的认识:“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佚游,使从其教;节民之醉饱,使归于德。”[6]151“先王之政,以养人为大。”他认为尧之“人德”主要体现在其敬天保民的实政上。舜之“人德”,在于“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5]1744皋陶的“人德”在于“训人德以补天德,观天道以开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皋陶始。”[5]1745《尚书》载,皋陶受命于舜而作五刑,舜、禹皆有训示。舜训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舜典》)禹训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大禹谟》)舜命皋陶制定法令以惩戒奸宄之人,既赞誉皋陶此功,便是强调舜之“道”或“德”在此。禹的训诫更是将“作刑”之目的直指人欲,以刑治欲概是舜、禹、皋陶之“人德”所在。基于此,叶适批评程朱学:“尊舜、文王而不知尧、禹,以曾子、子思断制众理,而皋陶、伊尹所造忽而不思,意悟难守,力践非实。”[10]60言其虚无、教条,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从“情欲论”的视角重新探讨“永嘉之学”,不仅使永嘉学派的思想特色得以彰显、核心精神的传承脉络得到呈现,也能澄清当前人们对永嘉学派及其思想的一些误解。如一些学者过多地强调永嘉学派不反理学、推崇二程和朱熹、师出程门,混淆了永嘉之学与程朱学的差异,如龚鹏程言:“永嘉(事功之学)又哪里是讲事功而反理学的呢?”[17]一些学者认为“永嘉之学”最终在内圣层面沿用了程学话语体系,致使其出现内外难融的尴尬局面,如陈安金等言:“传统儒家的‘仁、义、礼’三个层次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叶适承认了‘礼’(‘似以礼为主’),就必然延伸至仁、义,就要‘礼复而敬立’,终究无法突破理学话语的编码。”[18]。何俊曾言,叶适与程学“决非一般问题上的有别,而是根本方向上的相异”[19]。永嘉学派对程学话语体系的突破旗帜鲜明、理据确凿、脉络清晰,其意图十分鲜明,欲彻底推翻程学思想体系,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改造儒学、重建儒学。
四、结语
程学将人之情感和欲望排除于人性之外,主张将“尽性”“穷理”作为修身的全部内容和目的,并主张身不修则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定程度上能促使君王和士大夫克制私欲、提高道德修养。然彼时之文人大部分都将入仕,良好的道德素养只能一定程度上保证他们不为祸百姓,却难以使他们成为治国理政之干才。自宋金开战起,宋朝的文官群体中,绝大多数人除了主张屈辱求和、以良善之心感化恶敌之外,未能提出积极的抗敌御辱实策。《三朝北盟会编》载,靖康元年(1126)八月间,金军重兵合围太原,并积极备战准备大举进犯中原,“是时军期紧急遽如星火,敏不留意,方具劄子乞令学者添治春秋。又因司业杨时上言,王安石三经新义邪说聋瞽学者,致蔡京王黼因缘为奸以误上皇,皆安石启之也。又谓安石不当继十哲,宜依郑康成画壁从祀。上从其言,下太学如敏所请。时人有十不管之语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盖讥其不切事务故也。咸谓深中时病。”[20]“敏”即当时的执政大臣吴敏(生卒不详),他对紧急军情和御敌方略概不关心,反而一味地引导年轻懦弱的宋钦宗(赵桓1100―1156)去关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同时,程学门人杨时(1053—1135)也上书宋钦宗请求取消王安石配祀孔庙的资格,事实上是认为放弃抵抗、避战求和才是宋朝的唯一出路,这些见解的背后可清晰地看到程学“穷理灭欲”思想的影子。正因为在其时当政的文官群体中与杨时有同样认识的占绝大多数,才最终招致靖康之祸。虽然这并不能全归咎于程学,杨时也不能代表全部程学门人,然若程学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士大夫群体这种消极的心态必然会不断增长,长此以往,南宋难保有不虞之祸。因此,永嘉学派致力于批驳程学的“虚无”之风,使士大夫群体认识到“实政”“实德”“实学”才是儒学之主要内容。
永嘉学派只有掌握了儒学学术话语权,其思想主张和经世举措才能被士大夫群体广泛接受,进而给予最高统治集团以更大的影响。这便要求“永嘉之学”不仅在学理上彻底推翻程学话语体系,更要求其思想内容必须紧扣人之生活日用。“情欲论”正是最恰当的突破口,因它既是儒家哲学思想建构的基础,也是人之生活日用的主要内容。永嘉诸子先从人欲之恶倒推出人性有恶、“天德有偏”;继而从《尚书》关于尧、舜、禹等圣贤们的道德功业中总结出圣贤之道蕴含于他们治理天下人欲的实政中;然后通过阐述“皇极”“大学”和“中庸”三个概念,提出“内外交相成”的“道”论主张;最终突破了程学之天人观、天道说和人性论,重构了儒家“道统”,建构了较为完善的儒学思想体系。可以说,永嘉学派基本实现了在思想上突破程学话语体系、建构新的儒学话语体系的学术意图。
注 释:
①李华瑞先生曾指出:宋廷南渡以后“把北宋亡国之罪由蔡京集团追及王安石,即将北宋时期重‘事功’的荆公新学当作亡国之替罪羊,扶持作为其对立方的程学。”(李华瑞:《南宋时期新学与理学的消长》,载《史林》2003年第3期,第28-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