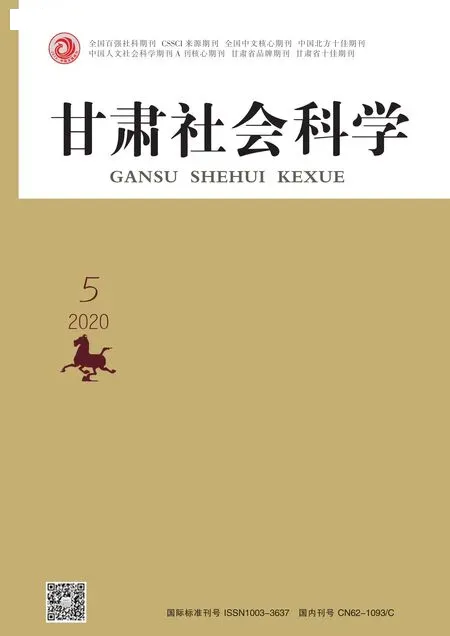《新中华报》与全面抗战前中共团结抗日的诉求
李婷婷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提要: 全面抗战爆发前,为打破国民党的舆论控制,实现中共政治理念的大众化传播,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紧紧围绕中共团结抗日这一诉求,整体论述其现实考量,详细解读其主要内容,不断丰富其传播方式,广泛报道其积极效果,以媒介的舆论力量助推中共政治理念的传播和深入,增进民众对中共的认识和了解,激发全民族的救亡意识和团结抗日情绪,筑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意基础。探讨《新中华报》与全面抗战前中共团结抗日的诉求,有益于增强当下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新时代党报媒体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持续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卓有成效地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1935年的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毛泽东提出党和全体人民的总任务为“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1]254。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2]88,便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然而,在国民党长期建构的赤色革命空间里,共产党员人人是青面獠牙、劫掠人民的匪贼,工农红军个个为杀人放火、阻碍抗日的暴徒,既有碍于中共政治理念的传播,又不利于争取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日。不过,“共产党自西安事件后地位是大大提高了”[3],获得了实施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建设的历史契机。故此,《新中华报》紧抓这一历史时机,通过对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现实考量的论述、主要内容的刊载、传播形式的丰富、影响效果的报道,以舆论的重要作用促进中共政治理念自上而下的传播。目前,学界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诉求的研究多集中于以纪念活动为中心的探讨,尚未发现从报刊的视角对全面抗战前中共团结抗日的诉求开展的研究。为此,本文尝试以《新中华报》为研究对象,考察全面抗战爆发前《新中华报》如何借助舆论实现中共政治理念的传播,达到争取全民族团结抗日的目的,力求丰富以中共党报党刊为研究对象的研究。
一、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现实考量
为什么要团结抗日?这是《新中华报》在表达中共团结抗日诉求及动员民众之先,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民众处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中,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唯有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才能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新中华报》以此为出发点,时刻关注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动态,多次痛陈日军的罪恶行径,深入揭露中国民众的痛苦生活,以营造传播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舆论氛围,引发民众的认可与共鸣。
第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1937年2月6日,《新中华报》在头版位置强调:“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略中国的行动有加无已,民族危急。”[4]华北事变后,日本军阀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野心愈加猖狂。在政治上,日本散布各种“亲善提携”,以图“炫惑中国人民耳目,来缓和燃烧着的中国抗日运动来破坏各党各派的团结抗日,来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5]。在军事上,绥东形势愈发紧张,“备战空气极浓厚,绥东战争有重新发生的危险”[6];1937年3月,日军于换防期间又增调大批军队至华北,“实数已超过原来部队一半以上”[7]。在经济上,日本加紧对华经济的垄断,拟建立一个金融银行团组织以便统治对华投资的金融周转[8],并利用朝鲜银行“努力在华中华南开辟新范围扩大在其华中华南势力”[9]。在外交上,日本和德国关系亲密,“证明着更大的侵略计划在筹备,大战的准备更加紧了”[10]。总之,国内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日大战一触即发。毛泽东便指出:“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11]报纸编辑也强调:“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经摆在每个中国人民的面前。”[12]宋庆龄亦认为:“亡国迫于眉睫,凡属血气之伦,莫不锥心泣血。”[13]显见,应对日趋深重的民族危机,成为中共强调全国团结抗日的首要考虑,也是报纸传播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最具说服力的因素。
第二,中国生灵涂炭,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九一八”之后,“失地万里,人民涂炭”[14],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杀害无比残忍。他们“开大炮,杀百姓,一刻也不停,百姓的财产,抢得干干净,百姓的性命,蚂蝗一样轻……拼命欺负人,抢去中国地,一省又一省”[15]。绥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死尸遍野,骷髅满地[16]。尤其是东北地区广大民众,遭到日军的残忍屠杀,“过着流离失所的悲惨痛苦的生活,现在的东北人民还在当着亡国奴,饱尝过了亡国奴的生活”[17]。显然,日本对中国的局部侵略就已造成中国民众的凄苦,《新中华报》借助歌谣《莲花闹》道尽日本的罪恶:“日本鬼,没好心,一心要害中国人,乱打枪,乱杀人,抢财抢地又奸淫,走私货,滚滚来,破坏中国的钱财。”[18]小调《东南西北》也唱出:“东边有个鬼子孙,日本就是他的名,横行霸道真无理,害我中国人……鬼子到处称霸王,百姓受活罪。”[19]没有比“感同身受”更能引起民众的同理心的做法,报纸恰是对日本种种罪行的控诉,对中国民众悲惨生活的揭示,以激起民众的愤慨,营造利于全国团结抗日的舆论氛围。
第三,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为唯一出路。自1935年下半年起,停止反共军事行动和建立全国联盟抗日的压力就稳步增长,特别是在军队、学生和资产阶级之中[20]。西安事变前,中共为抵御日本的局部侵略就已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21]。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新中华报》更是借助媒介的舆论攻势指出:“中国今日无论如何不能有内战,只有共同一致实行和平统一御侮救亡才是出路。”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的政策不应该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即国民阵线,中国今日的革命不是西班牙的革命,而是对外的民族革命或国民革命”[22]。所以,为着有效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为着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与复兴,报纸社论再次强调,没有统一团结,“中国人民就不能免除这迫在眉睫的大祸:亡国灭种”[23]。简言之,在日本没有停止侵华以前,中国没有国内的和平便不足以言全国性的抗战,而没有全国性的抗战就不足以图生存。
舆论环境是“一种无形而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24],舆论产生后,便会时刻影响社会,反作用于人的思维与行动。《新中华报》正是对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现实考量的深入论述,营造出益于此诉求传播的良好舆论环境,影响民众的思维与实践,形成全民皆言团结抗日的舆论效果,达到全民均要团结抗日的动员效果。
二、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主要内容
西安事变后,中共努力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强调和平统一、御侮救亡,倡导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1]255。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读者怎么想,却可以告诉读者想些什么,《新中华报》创刊之初,便连续刊发多篇以中共团结抗日诉求为主要内容的报道,实现中共政治理念与大众的“重复见面”,以刺激大众心理,引发社会舆论。
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和实行民主政治。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国内则使内战停止后,团结御侮能更快实现”[25]。故此,“本着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为人民公意”,中共“诚恳的热望南京政府及蒋介石先生”,共同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而一致奋斗。《新中华报》疾呼“要求南京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统一战线”[26],提出:“中国非消灭内战,不足以言救亡,非有坚决御侮之国策不足以言统一。”[27]但是,国民党则以各种理由与借口继续执行内战政策。为促成国共再次合作,“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28]。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一再号召停止内战,为“表示停止阶级斗争最高形式之国内革命战争”,以求“达到两党合作共同抗敌之目的”[29]。
毛泽东认为“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1]257,也就无法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张闻天甚或认为争取民主制度是国内战争停止后“一切工作的中心一环”,“只有给民众以民主的权利,抗日救亡运动才能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潜在力量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2]154。因而,“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1]256。《新中华报》直呼:“要求南京政府开放民主自由!”[30]建立“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31]。周恩来则指出:唯有国民大会“真正的民主化”,方可“建立起民主统一的政治的基础,以加紧加快的发动抗战”[32]。换言之,只有民主才能动员民众,也只有动员民众才能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力量,共济时艰。
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的团结抗日。毛泽东指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1]279。而这个战线又是极为广泛的,“包括各个阶级、各个政党、一切力量都应集中联合,来为民族生存而斗争”[33]。为此,《新中华报》指出,“实行国共合作,对日抗战”,实则“中华民族之福”[34]。“中国现在应该结一个大的团体,这个团体包括中国各阶级各党派都在内”,此乃“历史规定的神圣任务”[35]。总之,当此国难危急时刻,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更需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感[36],团结得如铁一般,才能打倒日本侵略者,实现救亡图存。
实现国共两党的团结一致、各党各派各阶层的团结抗日,对内则须打击汉奸托派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托派已是与日本特务机关有直接联系的汉奸”[2]40,他们不惜使用各种凶残手段“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之事业”[37]。托派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附属品”“最卑污的汉奸”,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必须最无情地消灭日本强盗死走狗的汉奸托洛斯基派”,在思想上“加以最明白的揭破”,在行动上“加以最无情的打击”[38]。《新中华报》也告诫“左倾幼稚病”的人士,切勿被托派所欺骗和利用,从大局着想,共同一致走向和平统一、御侮救亡的道路[39]。
对外则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团结抗日的诡计。日本帝国主义打着“亲善”“提携”等幌子,实际上却阻碍中国民众的团结抗日。故而,“随时揭破暴日挑拨离间之阴谋”[40],并加以坚决地反对,乃为当务之急。1937年3月18日,日本某实业界领袖在参加上海举行的中日贸易协会时,再次提出日本一以贯之的所谓“和平外交”“平等尊重”“经济提携”等侵略策略,《新中华报》旋即提醒全国民众勿为日本笑里藏刀似的美言所诱惑,号召“全国力量一致为实现对日抗战而奋斗”[41]。1937年5月,日本故意挑起事端,并企图转嫁给中国人民,《新中华报》积极鼓励大众以锐利的目光,密切注视日本在华的一切阴谋行径,“以最高速度的准备来发动一个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最终以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和大团结“淹没侵略者的魔鬼”[42]。
马克思把报刊比喻为驴子,而它背上驮着的麻袋,便是舆论,报纸便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43]。作为党报,《新中华报》散发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共的政治主张自然而然地浸润着报纸的全部,颇有“见报如见人”的意味。所以,它通过全面刊载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主要内容,愈加引发读者及社会各界关注的中共主张,再以舆论的力量转变大众对中共的消极态度和偏颇认知,从而在读报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接受中共的政治理念,唤醒人们的救亡意识,激发大众的抗日热情,争取全民族的团结抗日。
三、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大众化传播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民众普遍在文化修养上存有不足,陕甘宁边区的文盲率极高。毛泽东认为,做好宣传工作,“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44]。故此,《新中华报》充分考虑边区大众的实际文化水平,以曲词歌谣、诗歌诗词、标语口号、漫画木刻、谜语等为切入点,不断丰富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传播方式,扩大传播范围和受众基础,以媒体的力量影响大众认知,增强舆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曲词歌谣的民间化、通俗化。“泗州调”《救国法宝》以生活化文字解读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民众的抗日救亡,歌词说:“中华救星共产党,屡次请求国民党,合作起,共同救亡……第一停止打内战,团结御侮不可缓……第三联合各党派,救国大会快召开。”[45]“凤阳小调”《说东洋》以大众化的词句唱道:“各位同胞听端详,再不抵抗白遭殃。全国军队大联合,工农商学总武装。”[46]以陕北民歌《十二个月》改编的《一九三六年》唱道,“要求南京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统一战线”[47],“转眼又是三七年,抗日有了新局面,全国同胞联合起,中华解放在眼前”[48]。如此直白简洁的歌词,符合边区大众的文化水平,便于普通民众理解。另外,《新中华报》刊登的多首歌谣或借助于民间形式,或直接利用民歌、小调的曲谱,“或在原有的民歌曲调上进行简单改造”[49]。上文的“泗州调”“凤阳小调”,还有“张生莺莺调”《合力打日本》,“河间新调”《全民抗战曲》,“鸡腔调”《赶出中国去》,此外,仿河北民歌《小放牛》的《还我河山》等,运用大众熟悉的旋律传播抗日思想,易于为大众所理解并接受,且语气助词丰富,“救亡潮流涌涌,呀呵嗨,大家团结,嗬嗬”[50];“亡国奴!当不得,哎呀嗨!自由解放要奋斗,同胞们,快前进!”[51]这既贴近于民众生活,又有助于大众间的传唱,在激昂的歌声中,中共团结抗日的政治诉求易于深入民众,政治理念的传播空间也得以拓展。
诗歌诗词的简短性、韵律性。“诗歌,文字简短,富有韵律,朗朗上口,寓意深刻,是传递思想与情感的重要文体。”[52]洪水在《我们的生活》中写道:“抗日的任务是第一,要抗战全国人民要团结,为实现停止内战抗日而努力。”[53]《给我一枝枪》吟诵:“给我一枝枪,我要上战场:国仇家恨千万桩,那个能够再忍让。”[54]这些简洁的、富有韵律的诗词为民众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增强了前进的动力。为进行更广泛更高效的传播,《新中华报》另刊登出气势磅礴的诗篇《起来吧,中国人!》,诗中呐喊:“中国人,勇敢的战士呀!用我们的鲜血,去争取民族的解放吧!”[55]富有感染力的诗句便于记忆,容易引起大众的共鸣,激起群众的响应。而口语化、大众化的街头诗则愈加拉近中共与民众的距离,其心口相传的方式愈加扩大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传播。如:“为了打鬼子,老的少的都参加到队伍里来干,连七八岁的小娃,也举起拳头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56]这些诗歌诗句或铿锵有力,或老妪能解,将中共团结抗日的诉求植入诗歌诗词中,实现其陶冶功能与政党政治理念的深度融合,为争取全民族的团结抗日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教育武器。
标语口号的影响力、感染力。标语口号历来为中共所重视,被称为宣传工作的“小形式”[57]。《新中华报》深谙此道,以简洁醒目的文字,表意明确的词句,刊登多条富有影响力、感染力的标语口号,有针对性地向边区大众传播中共团结抗日的诉求,以影响大众的情感、态度及选择。“1.和平统一,团结御侮!2.巩固国内和平实现对日抗战!3.停止一切内战,迅速准备抗战!4.全国团结抗日援绥!5.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6.工农商学兵联合抗日!7.全国军队亲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8.全国人民武装起来,到抗日战线上来!9.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一致对日抗战!”[58]这些标语口号条条涤荡心灵,句句发人深省。青年是抵御、打击外侮的中坚力量,为加强中共在青年男女中的影响,希冀青年加入到抗战中,以扩大团结抗日诉求的传播,为此,《新中华报》刊登了针对青年的诸多标语口号。“全国青年团结救国!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御侮救亡!”[59]“勇敢的青年加入到抗日军去!”[60]毛泽东认为,“提出恰当的口号”系“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1]177;“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1]35。《新中华报》正是依托标语口号的简洁、简短、简练、简明、简单,实现政党政治理念“短平快”的传播。
漫画木刻的直观感、生动感。丰子恺曾言“百篇文章不及一幅漫画”[61],即是强调漫画在战争年代激发精神、动员民众、打击敌人的重要作用。故而,《新中华报》刊载多幅漫画、木刻,以艺术的手法、幽默的画面、深刻的寓意传播中共团结抗日的诉求。有木刻展示红军友好地伸出双手,寓意中共结束内战、团结御侮的向往[62]。有漫画描绘站在岸边的苏维埃红军扔出代表“对国民党三中全会之通电”的救生圈,抛给正在波涛汹涌大海中流浪的国民党士兵,以此告诫南京政府回头是岸,尽快结束国内战争[63]。作为呼应,有漫画展现国共两党握手言和,坚定地喊出:“现在,我们一致对外吧!”正是这种团结合作把“丑陋肥硕”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拒之国门外[64]。有漫画戳穿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他们打着“平等互惠,和平外交”的旗号,迷惑民众说:“我们是好朋友呀!”实则却是企图夺取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的钱财[65]。还有漫画揭露托派的阴谋嘴脸,他们隐藏在日本军阀身后,是日本军队的“好帮手哩”[66]。可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日不仅使帝国主义的小丑吓飞了帽子,堵住了耳朵,恐惧地跌坐在地上,又使环抱日本大腿的干枯瘦小的托派分子瑟瑟发抖,接受着中国人民的审判[67]。同时,《新中华报》激励全国民众向西班牙人民学习,正是西班牙人民以“团结”的拳头给予法西斯国家当头棒喝,使其瘫倒在地,武器尽毁,才免遭侵略[68]。显见,漫画木刻具有超越文字“成为拥有最广泛受众群的传播形式”[69]。它把高深复杂的文字转化为浅显易懂的图画,以直观生动的表达方式既启发和鼓舞着边区乃至全国民众,又使其感受到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大众可能看不懂汉字,但对漫画的含义或许知晓一二,中共的政治理念由此或可实现自上而下的传播。
谜语的趣味性、娱乐性。“猜谜”是一种颇具趣味的传播方式,《新中华报》将中共团结抗日的诉求寓于谜面中,反复出现“日本”“太平”“中国”等名字词,如“你说日本听了吓掉魂,我说妇女听了心欢喜”[70];“日本,日本,上头瞎了眼睛下头没了心肝”[71];“永远太平”[72];“中国的嘴巴”[73]等。在谜底揭晓时也寄以和平团结的寓意。例如“长安”[74]“和”[75]“国共合作”[76]“抗日”[77]“共同抗日”[78]“和平统一”[79]等,也有将“共产党”[80]“毛主席”[81]“救国大会”[82]作谜底的谜语,还有将沦陷区地名作为谜底,像“长春”“热河”[83]。但遗憾的是,由于报纸资料的残缺,无法将谜面与谜底一一对应。但以上也不难看出,报纸将寓意团结抗日的句子及词语通过“猜谜”的形式突出地反映出来,使民众在娱乐中了解、掌握中共团结抗日的诉求,真正发挥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总之,《新中华报》针对边区大众的文化现状,借助通俗易懂的曲词歌谣、朗朗上口的诗歌诗词、鲜明简练的标语口号、直观浅显的漫画木刻、颇具趣味的谜语等,不断丰富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大众化传播方式。意在将此诉求延伸至乡土社会的神经末梢,深入普通大众的心理,将各种社会力量吸收到团结抗战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将中共团结抗日的政治诉求与大众的普通诉求有效连接,使大众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中共的政治理念,由此实现良好的抗日动员效果。
四、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积极效果
中共团结抗日的诉求不仅得到边区大众的回应,边区民团、义勇队、地主豪绅也纷纷呼应,甚至白区民众、部分国民党军队亦积极响应。《新中华报》以此为报道落脚点,实证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吸引力与正确性,以助推中共政治理念的再深入,从而强化舆论的引导力,激起大众的情感共振,内化为自觉行动,实现抗日动员的最大化。
在边区,中共的抗日救亡工作获得广泛支持。广大民众“每天都像潮水一般涌入到抗日红军中来,很多人邀朋友找亲戚成群结队的来当红军,从几十里外跑来报名当红军的也是每天都有”[84]。延安民众在中共抗日怒潮的影响下,积极地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短短数日内,“原有民众救亡组织现已扩大到四百余人,前往参加报名的人数每天络绎不绝”[85]。延安市的妇女也“卷入了抗日的浪潮”,争相参加各种抗日组织[86]。在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影响下,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即将实现的消息传到三边地区后,“莫不庆祝共产党路线的胜利”,他们发动了募捐运动以“慰劳我军”[87]。中宜民众抗日热情高涨,“纷纷自动的募送抗日经费”给红军[88]。延长县“聚乐会”戏班在了解中共抗日救亡的民族统一战线后,特编一本《国破家亡身何在》旧形式新内容的戏剧,表达对中共的支持[89]。新城民众也“积极起来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已有六个村子”,且“自动的组织了‘抗日救国会’”[90]。边区民众是《新中华报》最大的读者群体,“即使不读报但和读报者交谈的人也会受到影响”[91]235。所以,报纸报道边区民众对中共抗日救亡工作的支持,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传播范围,夯实此诉求的民意基础。
在白区,中共和红军的正面形象得到建构。“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早已成为广大群众所拥护与资助的了”[92],白区民众纷纷响应,称颂中共主张的正确,传扬中共“是真正抗日救国救民的先锋”[93],赞叹其宽大、不记仇,“要联合大家一致抗日”,“这不是哄人的话,而是真的,啊呀!好得很,共产党真是为国家为民族利益的”[94]。对于红军,他们夸赞“红军真好呀!”“过去我们听说红军杀人放火,现在我们亲眼看过了才知道是造谣的,红军同我们讲的都是抗日的话,写的标语是停止内战的一些东西。”“哼!红军才是忠心报国的,各个都是岳飞。”[95]以上报道无不反映出白区民众对中共和红军的认可和赞许,表达出对中共团结抗日主张的同情和支持,而通过报纸的进一步传播,中共和红军的正面形象则愈加明晰,中共团结抗日的诉求也将随之扩大影响。
在民团里,中共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增强。清涧民团“无不称赞红军抗日爱国的忠心”,其团丁“拼命的要求参加红军去做抗日工作”,“要求红军收留,愿意抗日到底”[96]。志丹民团重新定义了共产党,认为逃跑的荒谬行为完全出自对中共的不了解[97],竞相携枪弹参加红军,“誓要收复失地,赶日本出中国”[98],愿“在抗日阵线上出一份力”[99]。部分团丁也感受到“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正确性,不仅自身潜逃参加红军,誓为实现中共的主张而奋斗到底,又写信告诉其他逃跑者,劝说其参加红军共同抗日[100]。靖边民团“也不出发进攻苏区了”,自愿地“参加到抗日工作”[101],《新中华报》表扬其“是抗日力量团结的最好表现”[102]。衡山民团决定“编入抗日义勇军,愿站在抗日最前线为祖国出一分力”[103]。红宜民团十分“同情与拥护”共产党的主张[104],又因中共“政治影响的扩大”如数归籍[105],甚至在回籍途中,被汉奸再次逼迫为匪时,“对于统一战线有深刻认识”的团丁也及时粉碎阴谋,增强红军的抗日力量[106]。延长民团听闻“共产党对目前形势与抗日主张及红军与苏维埃的新政策”后,有了“相当的认识与收获”,全数回到县城参加红军抗日工作[107]。同时,各地义勇队积极响应中共团结抗日的诉求,一方面,“缴枪不干回家种地”[108];另一方面,“专门进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109],一致表示愿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奋斗[110]。地主豪绅们也高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一致去打日本”,自愿“帮助红军抗日”[111]。总之,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传播,转变了民团等对中共的偏颇态度,增强了红军的抗日力量,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也得到国民党军队的认可。部分国民党军官们“很同情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表示愿联合各党各派,共同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汉奸亲日派,以求中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带着红星帽子和青天白日帽子的要人“交杯欢饮”,商议着“怎样打倒汉奸亲日分子”,如何实现各党各派的亲密合作[112]。在中共“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主张”的影响下,部分士兵发生哗变,认为共产党的主张“真光明、真伟大”,携带武器不断地“三五成群到红军里来”[113]。瓦市八十四师、石湾八十六师、清涧八十四师、清涧二十一师的士兵均有暴动,拖枪弹粮食主动地跑到苏区参加抗日红军[114]。中部某团的全体官兵表示愿与红军合作,“坚决抗日到底”,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115]。这充分说明国民党的部分军队,无论官长抑或士兵,那种“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共产党抗日是假的”的固有偏见转变了,“明白了共产党与红军的抗日主张”,热切地希望“全国一致联合起来实行对日抗战”[116]。衡山县石湾驻军张团长“完全同意我们的抗战主张,改变他们过去一切不良行为,他们的态度有了新的表示”[117]。国民革命军八十六师某排长,“也不打枪了,也不出击了,并且还解下武器”,亲自和红军游击队交谈,“再见,我们将来到抗日战线上去会面吧!”[118]可以说,国民党军队对中共团结抗日主张的认可,好似给各党各派、全国民众吃了“定心丸”,愈加激励和鼓舞着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推动了全国性地团结抗日进程。
综上,《新中华报》对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积极效果的大量报道,也是借大众之口获取更加广泛的公众舆论支持,以此实现抗日动员的合力效应,从而能够将中共的政治理念广泛地融入大众的现实生活,实现“一传十、十传百”的积极效应,如甘泉县民众听闻鄜县民众对中共和红军的真实评价后,均热切地“渴望红军前来”,共同团结抗日[119]。
五、余 论
报纸是一种公共的交谈,“各地分散的群众,由于新闻的作用,意识到彼此的同步性和相互影响,相隔很远却觉得很亲近;于是,报纸就造就了一个庞大、抽象和独立的群体,并且将其命名为舆论”[91]246。伴随《新中华报》读者数量的逐步扩大,舆论影响也将持续深入,继而完成“公共头脑的宏大的一体化过程”[120]。从这个意义出发,《新中华报》将中共团结抗日的政治诉求、政党的政治理念植入报纸,能在一定程度上牵引着“阅者的目光”,形成舆论的“迸发”与“共振”,从而影响大众内心深处,并外化为现实的具体行动。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的团结抗日便有了深厚的民意基础。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121]。因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22]。故此,梳理《新中华报》传播中共团结抗日诉求的大众化方式及经验,值得当下党报媒体及学者的研究和总结,从而为新时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传播提供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