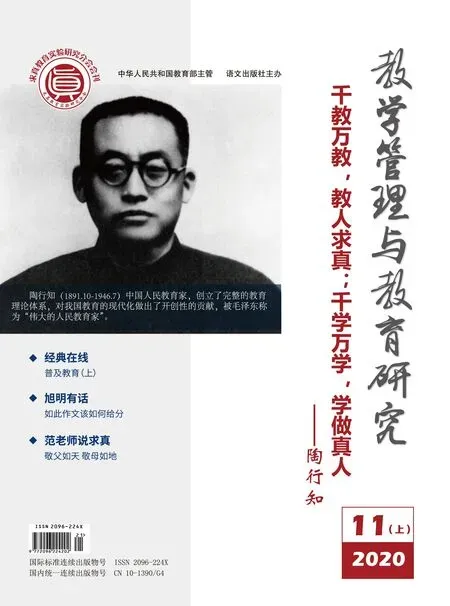普及教育(上)
陶行知
刚才谢先生介绍陶知行,陶知行已经死了,我现在的名字叫陶行知。让我先来介绍自己,陶行知出生才三个月,可以代表我的思想的转变。“知行”变成行知。陶知行这个名字,跟我已有二十四年,因为这个名字跟我太久,所以不愿改,并且有人说我喜欢花样翻新,所以终于没有改。三个月前忽然改了,改的原因何在呢?因为许多顽皮的小朋友,写信给我早就改称行知先生。还有一位德国朋友卫中先生,常常喜欢喊我“行知”,他说中国人如果懂得“行知”的道理,而放弃“知行”的传统思想,才有希望。我名“知行”,而主张“行知”,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经过许多朋友的鼓励,所以我毅然决然在苏州改名陶行知。我的朋友谢育华,看了《古庙敲钟录》之后对我说,你的理论我明白了,是“知行知”,底下这个“知”字是何等有动力,很少有人能喊出这样生动的口号。我向他表示钦佩之意后,对他说,恰恰相反,我的理论是“行知行”,所以改名为陶行知。他说,你的“行知行”不对,比如,有了电的知识,才能去开电灯厂,开了电灯厂,电的知识更能进步,这不是“知行知”吗?我说,那最初发明电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科学实验、玩科学把戏中得来的吗?法拉第(Faraday)是一个订书店的徒弟,他订书订得很慢,订一本书就看一本书,大家向老板攻击他书订得慢,老板却说他是订一本书就吃一本书。有一次,装订《百科全书》,吃到电学,他还不够,适Davy 在卖讲演,他便求人做东,给他买了入场券去听讲。他就帮助Davy 做助手,行动起来,用线接到指南针,拨动磁石,就发生了电。这就是行动。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丝,经过一千多次实验才成功,也是从行动中得来的。所以,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因此我主张“行知行”。王阳明先生主张“知行合一”,有一点却拖下一根狐狸尾巴,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们把它翻了个筋斗,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正与阳明先生的主张相反。因此,就改名“行知”。这是我对自己的介绍。
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普及教育》。这个题目,也是从行动中得来的,不然一定先要将美国普及教育是如何,法、德普及教育是如何,俄国、日本又是如何先讲一讲,再讲到中国普及教育方案。不知道中国是一个穷国,已到了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农民已连饭都没有吃了。拿富国的办法,引到中国来,无异是乡下人吃大菜。我有一首打油诗,形容乡下人吃大菜,那诗是:“乡下老吃大菜,刀儿当作筷,我的妈呀,舌头割掉了一块。”两年前,我流浪在上海,跟随我的几个学生,也是穷光蛋。穷又不安分,还想办点教育,于是四个人背了留声机,带了一点药,到宝山去。把留声机一开,乡下人就大家出来,听洋人哈哈笑,高兴得很。慢慢问他们有没有病,有病我这里有药,头痛送他一点阿司匹林,打摆子就请他吃金鸡纳霜,结了感情,山海工学团就如此办起来了。
工学团是什么,工就是劳工,学就是科学,团就是团体。如果有外国朋友问起来,就告诉他是Worker Science Union。说得清楚些,多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说得更清楚些,是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说它是学校,它有工与团,不像学校;说它是工厂,它有学与团,不像工厂;说它是民团,他有工与学,不像民团。所以,工学团可以称为“三不像”。四个穷光蛋,挂的一块大招牌是“来者不拒”。来一个收一个,来两个收一双。后来来了两百人,随后增至三百人,真有点吃不消。正如面包夹火腿,打在夹板中间,招牌既不能下,法子又想不出来,我们就在这里头打滚。有一天,看见一个小孩子教四五十个小孩子做箭,教得极好。我看了半个钟头,非常高兴,觉得这块招牌可以不下了,另外还能添上一块招牌:“不能来者送上门去。”“小孩子能做小先生。”他们是负着把教育送上门去的责任,他们把教育送到牛背上去,送到山上去。这种方法多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不是从头脑中想出来的,不是从听讲演学来的,乃是从行动中产生的。因此多想起在十一年前,我的母亲是五十七岁,我的第二个小孩子叫小桃,才六岁,她读完《平民千字课》第一册,就教她的祖母。祖孙二人,一面读一面玩,兴高采烈,一个月就把第一册读完。读了十六天,我在张家口依据《千字课》上十六天的生字,写了一封信寄给家母,她自己便看懂了。
两年半以前,晓庄师范关了门。晓庄佘儿岗的农人要想办一个小学,多苦于没有钱,请私塾先生,小孩又不愿。于是小孩自动起来办了一个农村小学,校长、教师、工人,都是小孩子。我为他们写的一幅小照:“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他们回信说,原稿第二句那个“大”字,应改为“小”字。他们反问我,大孩能自动,难道小孩就不能自动吗?大孩能教小孩,难道小孩就不能教大孩吗?从此这首诗的第二句,便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
第三个例子,我想到去年江苏淮安新安小学有七个孩子,自动出来,一飘飘到镇江,再飘飘到上海。来的时候,身边只有十块钱,他们靠卖书卖讲演过活。告别上海时,却有六十块钱了。当他们来看我的时候,他们说听见我卖讲演,所以他们也卖讲演。我叫他们先讲给我听,一听果然不错。于是我介绍几处去讲演,别人也介绍了几处,后来就有人自动请他们讲演了。他们讲三分钟,准可使听众大鼓其掌。今天我讲了很多时间,还没有博得掌声(鼓掌);我讲了二十几分钟,才博得掌声。可见我还不如他们讲得好。他们从小学讲到中学,讲到大学,大夏、光华、沪江等大学,统统去过。后来我问大夏教授邵爽秋先生讲得如何,他说几乎把我们教授饭碗打破了。当时我写了两首诗,答复他们的校长:
一群小光棍,数数是七根。
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
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
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这七个小孩子,都是江北人口。当“一二·八”后,上海人目江北人为汉奸。逮些小孩子,经过这次讲演以后,大家心理一变,至少这七个小孩子,总不是汉奸。穷孩子到大学里去讲演,这次可以说破世界纪录。这七个小孩子将金刚之锥,把时代划分为两个。
以上几个例子证明小孩子能做小先生。小孩子一个教两个极为容易。一个六岁小孩子,白天学了“青菜豆腐”四个字,晚上就会教给妈妈姐姐,一本书可供给三个人用。假如再给他一本簿子、一支铅笔,妈妈还可以画一两笔,像日记一样地交给小先生看。
小先生的数字非常伟大。一千一百万小学生,一个教两个,便是三千三百万。义务教育,就算有了大进步。还有一千万私塾生,可命每个先生带两个学生来受培养,一个假定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得意门生。这两个小先生回去,等到冬烘先生午睡、访友、上茶馆评理的时候,一定可以将新的思潮传入私塾,私塾马上就可以改良。有两千一百万小先生,六千三百万失学人问题就解决了。再按“即知即传人”的道理,另外还有八千万认字的成人在商店、家庭里,也可以每家抽出一两个人来受教育。再由这八千万人,一个再去教两个,便是一万万六千万人,成人教育就推动了。不过这确要有组织,才能共同发挥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