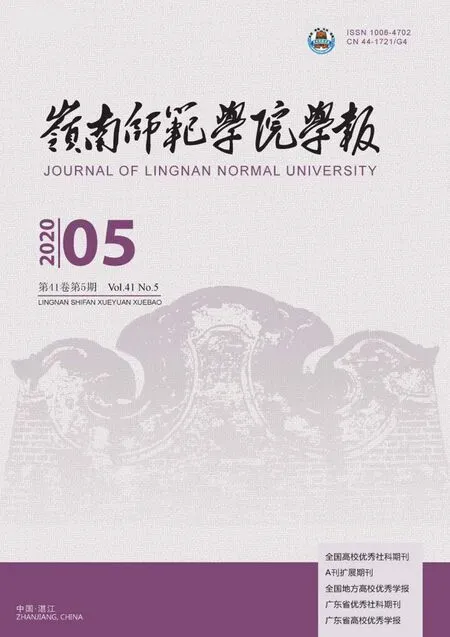从《四库全书总目》看四库馆臣的辞赋批评
孙 伟 鑫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四库全书》为清朝乾隆年间官方组织,经由四库馆臣编定的一部大型文献总集,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则为全书提纲挈领之书,反映了乾隆皇帝以及四库馆臣的文学理论。同时,四库馆臣通过提要的编纂,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文学批评体系,代表了当时文学批评的最高和最全面的水准,凝结了四库馆臣的集体智慧,体现了清代前、中期的主流文学观。
关于《总目》中所体现的文学观学界目前研究丰富颇丰,是当今四库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成果如郭英德先生《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古文观》[1]、何宗美先生发表的系列论文如《〈四库全书〉的文学批评》[2]《〈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研究的离合现象——兼谈〈批评史〉的当代书写问题》[3]《〈四库全书总目〉王士禛批评舛误辨证—兼析馆臣提要撰写体例及主观缺失》[4]、《四库体系中的曲学思想辨证》[5]等,吕双伟先生《清代骈文对辞赋的扩容》[6]文中亦有对于此阶段赋学之研究,吴承学先生也肯定了《总目》的诗文批评价值[7]。同时,柳燕著《〈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研究》[8]中有关于《总目》的文学批评研究,赵涛著《〈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9],也对四库馆臣的文学观做了相关研究。限于文章篇幅,对前贤之学术成果不作一一赘述。直言之,关于四库馆臣的文学观念之研究蔚然大观。然则关于《总目》中的辞赋批评,相关研究成果甚少,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0]1之角度看,有必要对四库馆臣对赋总集及对历代赋家赋作的评论进行梳理,以厘清四库馆臣的文体观以及其文艺理论思想,故而笔者从《总目》出发,试图整理四库馆臣的辞赋线索,抛砖引玉,以俟方家指正。
一、尊崇古体的倾向
近人余嘉锡曾言:“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11]由此可见《总目》的学术价值和成就。纵观辞赋作品发展的历史,在清代中后期以前,辞赋作品大多依附于散见于别集、史籍之中,如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大人》之作,又如扬雄《甘泉》《羽猎》之赋,皆为如此。别集之源起,前贤尚有争论,一般认为起源于西汉,经过东汉六朝之发展,至清代则是集大成之成熟期。然大多数辞赋作无专集的现象却可无疑。近人刘师培认为:“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有写怀之赋(即所谓形容言深思远,以达一己之中情者也),有骋辞之赋(即所谓纵笔所如,以才藻擅长者也)有阐理之赋(即所谓分析事物,以形容其精微者也)。”[12]据此,陈冠明先生认为:“汉代诗、赋虽无集之名,而已有集之实。”[13]汉代后,尤以唐宋为例,以诗赋取士,辞赋作为一种科举考试之文体,加之唐代以降,文人所纂别集收录范围逐步扩大,赋作并未以一种独立的文体形式集结。因而,对《总目》赋学观的梳理,眼光不应如同对诗词、骈文、小说、戏曲等文学体裁的批评范式,不可囿于对赋集的批评,而是应兼顾对著名赋家、相关文献总集、选集以及当时文艺思潮的批评,由此才可看出当时相对完整的辞赋观念。
在《总目》之中,涉及赋作之别集、总集主要有《人伦大统赋》《奇门遁甲赋》《述书赋》《画山水赋》《历代赋汇》《事类赋》等二十余种书,加之《古俪府》等总集之中涉及辞赋之内容,对于这些别集与总集,四库馆臣在《总目》中皆撰有提要,兹列数例以窥全豹。
如《历代赋汇》一则,提要言:
康熙四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赋虽古诗之流,然自屈宋以来,即与诗别体。自汉迄宋,文质递变,格律日新。元祝尧作古赋辨体,于源流正变言之详矣。至于历代鸿篇,则不能备载。明人作《赋苑》,近人作《赋格》,均千百之中录存十一,未能赅备无遗也。是编所录,上起周末,下讫明季,以有关于经济学问者,为正集,分三十类,计三千四十二篇。其劳人思妇、哀怨穷愁、畸士幽人、放言任达者,别为外集,分八类,计四百二十三篇。旁及佚文坠简,片语单词,见于诸书所引者,碎璧零玑,亦多资考证。裒为逸句二卷,计一百一十七篇。又书成之后。补遗三百六十九篇,散附逸句五十篇。二千余年体物之作,散在艺林者,耳目所及,亦约略备焉。扬雄有言,能读千赋则能赋。是编且四倍之。学者沿波得奇,于以黼黻太平,润色鸿业亦足和声鸣盛矣[14]1726-1727。
由此得见,四库馆臣对于辞赋的起源以及后世之流衍做出了简要的概括,同时肯定了元人祝尧对赋体起源变化的梳理。祝尧此书,推尊楚辞及汉赋。他认为:“……骚人之赋与词人之赋虽异,然犹有古诗之义……至于宋唐以下,则是词人之赋,多没其古诗之义。”[15]41同时他提出了:“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去其所以淫而取所以则,可也。”[15]42乾嘉学者所撰的提要,秉承朴学的治学门径,集中于文献源流、作者、史实之考证,但对于作者作品的褒贬可得见其赋学倾向。
又如四库馆臣提祝尧《古赋辨体》一则,称其“采摭颇为赅备”[14]1708,对辞赋之流变过程,如《子虚》《上林》等主客问答之作出于《卜居》《渔夫》,又如古赋以铺张扬厉、专为词者之体,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赋等诸般论断,四库馆臣认为其“言之最确”[14]1708。祝尧的《古赋辨体》,有感唐宋律赋与文赋之盛行,奋而为古赋一辩,同时四库馆臣亦对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批评祝尧之言提出辩解。
《元赋青云梯》为元人士子科举程试之作,《总目》载:“上卷赋录三十六篇,中卷录赋三十九篇,下卷录赋三十六篇,凡一百十一篇。”[15]所收之赋皆为古体赋。《赋苑》为明人赋选本,其书载:“始于周荀况,终于隋萧皇后,以时代为编次。”[14]1767所选之文亦为古体之赋。又记《古赋题》一书,言作者作其书之目的在于:“宋人有备对策论经义之书,无备诗赋题之书。至元此制不行,故钱惟善集载有乡试以罗刹江赋命题,锁院三千人不知出处之事。”[14]1767除上文举之数则外,还有《丽则遗音》《铁崖赋稿》二书,皆为元人杨维桢之作,其中《丽则遗音》“是集为赋三十有二首”[14]1462,《铁崖赋稿》则乃杨维桢未刻之书,有“赋凡四十八篇”[17],此二书皆为“其应举时私拟程试之作”[14]1462。于此,不妨将律赋与古赋的全集进行对比。《总目》中仅有《大全赋会》一则提及律体赋文:“……凡赋限三百六十字以上成。其官韵八字,一平一仄相间,即依次用。”[14]1736因此四库馆臣批评此种文体:“苟合格式而已,其浮泛庸浅、千手一律,固亦不足怪矣。”[14]1736
在有限的赋总集以及别集之提要中,四库馆臣除了推重简质典雅、清真实典的赋风外,尚有对虚怪荒诞、华而不实赋风的贬斥。在《奇门遁甲赋》条目中,四库馆臣评价道:“其于奇仪飞伏之理,词意明简,尚不至于荒诡……大抵江湖术士摭拾浮谈,无所阐发也。”[14]944-945强调词意简明的辞赋创作风格,对后世的注解,则批评其为摭拾浮谈之说,对赋论无所阐发。又如《人伦大统赋》条目中评此赋集:“惟意欲自神其术,中间不无语涉虚夸。”[14]929评价此书薛延年的注解:“宂蔓过甚,转不免失之浅陋耳。”[14]929又《历朝赋格》条目言:“骚赋之引则为骚赋一篇,骈赋之引则为骈赋一篇。殊为纤仄,古无是例也。”[14]1771
四库馆臣对于古赋之青睐,或许是受到刘勰之观点影响。《文心雕龙·诠赋》言:“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18]134此种传统观点,至四库馆臣时,可谓其来有自。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云:“将使文士学其如古者,戒其不如古者,而后古赋可复见于今也。”[19]正所谓“源流既正,识度自超”[20],汉大赋之成,已由抒发个人心绪情志转向对家国民生之忧患,主悚动人主,讽谏乎上。正如许结先生所言:“然从汉赋艺术的发展看,讽谏思想大体上经历了由个人心绪向社会历史的整体忧患的转化。”[21]此种儒家正统论及诗教传统,肇自孔子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22]又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23]及扬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24]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中设《诗赋略》,言:“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25]班孟坚云:“赋者,古诗之流也。”[26]2又曰:“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26]3王符曰:“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泻哀乐之情也。”[27]陆士衡言:“诗缘情而绮糜,赋体物体而浏亮。”[26]780刘勰《文心雕龙》言:“诗有六义,其二曰赋。”[18]134章实斋云:“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10]116至此可隐约见其脉络。今人马积高先生论述赋之源起之时认为辞赋源流之一:“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28]6中国文学历来有诗赋并举之传统,其二者之关系相互纠缠。诗具有教化风俗的社会功能自不必言,由此可见,辞赋亦是礼仪教化的理想载体,除讽谏人主外,也有社会伦理道德教化及建设文化的重要功能。故而四库馆臣推崇典核征实之赋论便可理解。
故而在《总目》中,言《朝鲜赋》:“所言与明史朝鲜传皆合,知其信而有征,非凿空也。”[14]632谈《画山水赋》:“考荀卿以后,赋体数更,而自汉及唐,未有无韵之格。此篇虽用骈词,而中间或数句有韵,数句无韵,仍如散体。强题曰赋,未见其然。”[14]955论及《会稽三赋》:“铸以当时之人,注当时之赋,耳闻目睹,言必有征。视后人想象考索者,亦特为详瞻。且所引无非宋以前书,尤非近时地志杜撰故实,牵合名胜者可比。”[14]624四库馆臣无论是在赋史的流衍考索,抑或赋予诗词文风的比较,又或赋予山川地理名物之间的勘查校正,均以朴学的学术视野出发,正是基于馆臣们实学家的学术视野,因而《总目》在赋集审择中推尊才学和见识。易闻晓先生认为:“大赋凭虚夸饰,敷张扬厉,征材聚事,都体现为辞藻的铺陈,基于作者的广博知识和深厚学养。”[29]汉赋以才学为资,才得其构成庞大的知识架构及铺陈空间,形成铺张扬厉之视觉效果和审美体验。在此逻辑之下,四库馆臣对此类具才学的作品持赞扬的态度。试举《事类赋》一则为例:“……学有渊源,又预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两大书,见闻尤博。故赋既工雅,又注与赋出自一手,事无舛误。故传诵至今。”[14]1145《事类赋》为中国历史上首次以赋体写就之类书,标志着宋初重“学”风气之滥觞。从文学史意义而言,其意义又不仅为类书所可视之,其文皆以骈文四六写就,蔚然大观。李濂在《事类赋序》中评价此书:“收罗百家,贯穿古今,可谓博学也……吴氏此书,聚博为约,最便近学。且隐括成赋,谐以音韵,诚类书之优者也。”[30]就《事类赋》涵盖的文学审美价值来说,《总目》并无过多笔墨对其赞赏,而仅就其“采摭佚书,雅致可观”的部分进行论述,遑论《人伦大统赋》专言相术,《三命指迷赋》《奇门遁甲赋》专论星象占卜阴阳术数,《述书赋》《画山水赋》叙书画之术。
至此,或可以四库馆臣对杨维桢赋集《丽则遗音》的评价概括其对古赋的推尊,其文云:
维桢才力富健,回飙驰霆激之气,以就有司之绳尺,格律不更而神采迥异。遽拟诸诗人之赋,虽未易言,然在科举之文,亦可云卷舒风云,吐纳珠玉者矣[14]1462。
杨维桢作文笔力雄浑,气势磅礴,语言刚劲。宋濂曾言其文:“……为童子时,属文辄有精魄,诸老生咸谓咄咄逼人。暨出仕与时,君遂大肆其力于文辞,非先秦两汉弗之学……”[31]215人称为“铁崖体”。就其辞赋创作而言,文体多为古赋,思想内涵方面,多涵治世之思,批判社会现实之感。赋骚之际,透露着赋家对世道倾颓,欲救世沉沦的感情。这种感情与上文中所枚举的古体赋的思想逻辑是自我洽接的。从此可见,四库馆臣对于杨维桢的评价,正是其对古体赋的推崇。
二、《总目》中历代赋学批评
(一)汉代至六朝
《总目》中对历代赋家及相关辞赋作品的评论中,可见得四库馆臣所代表“官学”的赋学思想,归根结底便是对“醇雅清真”的一贯追求。质言之,其一为感情真切,凄哀婉转,不平而鸣,发而作文,沉郁顿挫,强调气势和骨力。其二为因情书景,清新自然,典丽雅致的风格。通观《总目》中所言,对历代大赋家的文集皆有论述,如扬雄、庾信、鲍照、曹植、江淹、陈维崧等。虽汉代辞赋为一代文学之盛,然文集尚未形成,虽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辞赋大家,然《总目》中言者罕观,仅有扬雄、蔡邕、孔融等数家,且大略与赋学无关,兹略而不论。就赋学批评言之,梁启超曾言清代学术:“夫无考证学则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32]因而统摄四库馆臣进行历代赋学批评的便有二维方法论,其一为主上弘历的文学思想,其二为以乾嘉学者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宰臣文士以“朴学”学术视野观照之下,以实证为本,考辨、评探诸家赋作优劣得失,推举醇雅清真的赋学典范。而对绮丽伤骨、疲乏孱弱之赋作或持贬斥批评态度,亦或是不收入《四库全书》之内,旗帜鲜明。馆臣对于古体赋的尊崇上文已然言明,除此,还主推骈散交替,以古为韵,援古文之“气”救赋之作,以期达至文质相胜、艳丽博沉、一体浑然的审美境界。
《总目》论及文章,反对俳偶骈俪,夸饰虚华,重视气骨刚健,典雅稳重。六朝作文,浮艳绮丽,与此时所提倡的典实质重,雍容雅致的审美倾向颇有分殊,因而《总目》中对六朝文风多不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四库馆臣并没有对六朝文风完全摈弃,而是扬弃其文,给予公正的评价。自隋唐以降,尤其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33]509的古文运动以来,历北宋程颐言“作文害道”[34],缘与儒家重质轻文的批评传统,常视六朝辞赋的凭虚夸饰、声律骈偶为形式主义而摈弃于外,然《总目》却可作出公允评价。如论庾信:
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初在南朝,与徐陵齐名……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陵至所及矣[14]1275-1276。
又如评价徐陵:
陵文章绮丽,与庾信齐名,世号徐庾体。《陈书》本传称其缉裁巧密,多有新意。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为一代文宗[14]1276。
四库馆臣认为,庾信、徐陵之所以成为“一代文宗”,深层原因不在其雕声琢色,而是以情纬文,华质相见,在骈俪韵文中有云卷风舒和灏气流转,因此辞赋才雅瞻可观。以此出发,时人对于六朝辞赋的偏见得以消解,论文以六朝为尚成为是时之风。正如《总目》于《文恭集》一则云:“当时文格未变,尚沿四六骈偶之习,而宿于是体尤工。所为朝廷大制作,典重赡丽,追踪六朝。”[14]1310证据莫过于乾嘉之时出现了大批慕晋学宋的赋家,如程晋芳、袁枚、孔广森、邵齐焘等。除了徐庾赋作情文兼备外,还与四库馆臣学者的身份关系颇深,四库馆臣大多为汉学家,对宋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33]359的学风倾向不满,钱穆先生曾评戴震之学或可见得一斑:“盖乾、嘉以往诋宋之风,自东原起而愈甚,而东原论学之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35]汉学讲究考据小学,力主征引,反对空谈义理,而辞赋则是征典用事之文,关乎性情。
四库馆臣对六朝辞赋的肯定,当以醇雅为旨归,除了略有过激言论,可看作是对前代文学的反拨外,并没有全盘否定六朝文风。《宋文纪》提要云:“宋之文,上承魏晋,清俊之体犹存。下启齐梁,纂组之风渐盛。于八代之内,居文质升降之关。虽涉雕华,未全绮靡。”[14]1721馆臣们对刘宋时期文章的高度评价,还是本于文质相符、辞骨兼备的批评逻辑进行的。
(二)唐宋
清人李元度《赋学正鹄》言:“唐以诗赋取士,始有律赋之目。古赋变为律赋,犹古文变为时文也。”[36]唐人承六朝辞赋之绪,变骈为律,将至作为科举应试的文体,宋承唐制,试赋取士,然赋以文法入赋,化骈为散。祝尧《古赋辨体》言文赋:“以论理为体,则是一片之文但押几个韵尔,赋于何有?”[15]61明人吴讷亦赞同此说,分列文赋一项[37]。马积高先生认为:“赋到宋元,真可以说已是‘押韵之文’了。”[28]384基于此等事实,辞赋自后汉以来不断诗化的逆向建构已然完成。因此,四库馆臣对于唐宋两家的赋家,总体上持着“虽科举之文,无关著述,而当时风气略见于斯”[14]1300的态度,对辞赋作品多无评骘。此种态度在《祠部集》一则亦有体现:“称初为乡试举首,赋出,四方皆传诵之。既得第,耻以赋见称,乃专力六经,发为文章。有举其赋者,辄颈涨面赤,恶其薄己。”[14]1313
通观《总目》,四库馆臣对此时赋家持赞许态度的,主要有初唐四杰、黄滔、王棨等。如评王勃:“文为四杰之冠。”[14]1277论杨炯:“……炯文之最有根柢者,知其词章瑰丽,由于贯穿典籍,不止涉猎浮华。”[14]1278言卢照邻:“……大抵欢寡愁殷,有骚人之遗响,亦遭遇使之然也。”[14]1278黄滔与王棨为是时律赋大家,其人不律艺所囿,得以舒畅情感,开辟新地。《十国春秋》言黄滔赋作:“……诸赋雄新隽永,称一时绝调。”[38]《总目》言其:“集中文颇赡蔚。”[14]1303言王棨之赋:“亦足备文章之一格也。”[14]1300因而,馆臣们对此类温润雅丽,从温雅中见神气,以瑰丽畅辞气,雅而又清,丽而不淫,自然成文的辞赋是赞许的,亦可说,这种风格是四库馆臣理想中的赋学风格。具体表现为四库馆臣对《乖崖集》的评点:“其《声赋》一首,穷极幽渺,梁周翰至叹为一百年不见此作,则非无意于为文者。特其光明俊伟,发为自然。故真气流露,无雕章琢句之态耳。”[14]1306四库馆臣认为,《声赋》之所以千古称颂,正是缘于真性情的抒发,能发之于自然之心,无雕琢之气,辞赋正是需要这种审美范式为第一要义。
(三)元明清
马积高先生认为:“由唐人开创的新文赋体到宋元已走到尽头,在艺术上已难有创新;……永乐以后,可观的就寥寥了。”[28]507实则元明复古,模拟效法之习气颇重,逮至甲申国变,明清鼎易,山河变色,剃发左衽,以夷变夏,明末赋家如陈子龙、夏完淳、黄宗羲等人,反倒有激昂凄戾之作。然总而言之,作品多纤佻之习。故而《总目》中鲜有提及,偶有列出,亦以才气纵横、气骨纵横为标。
如《总目》论元人赵文《青山集》:“然其文章则时有《哀江南赋》之余音,拟以古人,其庾信之流亚乎。”[14]1425评元人程端学《积斋集》中的《四灵赋》,言其“词意高迥”[14]1445,“其文结构缜密,颇有闳深肃括之风”[14]1445,又言:“盖根柢既深,以理胜而不以词胜。”[14]1445又如四库馆臣对陈维崧赋作评为:
国朝以四六名者,初有维崧及吴绮,次则章藻功《思绮堂集》亦颇见称于世。然绮才地稍弱于维崧,藻功欲以新巧胜二家。又遁为别调。譬诸明代之诗,维崧导源于庾信,气脉雄厚如李梦阳之学杜……平心而论,要当以维崧为冠,徒以传诵者太广,摹拟太众,论者遂以肤廓为疑,如明代之诟北地,实则才力富健,风骨浑成,在诸家之中,独不失六朝、四杰之旧格,要不能以挦撦玉溪,归咎于三十六体也[14]1524。
四库馆臣认为陈维崧的辞赋取径于庾信,气脉厚远,才力富健,风骨浑成。顺康交际,陈维崧作为一代文宗,诗词文赋皆有建树,就其辞赋创作实践而言,他重视真情对于文学作品的灌注:“文章以心术为根柢,德行以藻采为锋锷。秽如扬雄,虽沉博绝丽之文,定属外篇;洁如陶潜,则闺房青致之赋,不妨极笔。”[38]扬雄之赋,徒有华丽博雅之文辞修辞,然非赋家情感之诚所作,不值所倡,陶元亮作《闲情赋》,籍男女欢爱以抒政治之思,重视情感,淳朴真挚,因而陈维崧以为此类作品可大加赞赏。同时,四库馆臣评吴绮《林蕙堂集》时论陈维崧辞赋:“维崧泛滥于初唐四杰,以雄博见长。”[14]1521四库馆臣对于陈维崧其赋作风格是把握准确的,同时陈维崧的辞赋创作亦得到馆臣们的认可,陈维崧自己的赋论也与馆臣们的赋论遥相契合,因而四库馆臣才给予他如此之高的评价。
除对个人赋家赋作进行批评外,《总目》中尚有对文学总集的批评,此类总集多收选赋作,故对文集的批评亦是四库馆臣对赋的批评。最具代表意义为玄烨敕令陈廷敬始编,及胤禛,至弘历始编修完成的《皇清文颖》,在此书中列举龙兴入关至乾隆一朝的文风演第,兹列于下,可探得赋作之风格取向:
我国家定鼎之初,人心返璞,已尽前朝纤仄之体。故顺治以来,浑浑噩噩,皆开国元音。康熙六十一年中,太和翔洽,经术昌明,士大夫文采风流,交相照映。作者大都沉博绝丽,驰骤古今。雍正十三年中,累洽重熙,和声鸣盛。作者率舂容大雅,沨沨乎治世治音。我皇上御极之初,肇举词科,人文蔚起。治经者多以考证之功,研求古义。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学,抒发鸿裁。佩实衔华,迄今尚蒸蒸日上[14]1728。
在四库馆臣对有清一代的文风梳理中,始终以经术为本,强调衔实以佩华,在文章的外在形式与内容权衡上,更倾向于追求实际的内容,对前朝纤薄轻佻、以求沉博绝丽之赋风,采取摒弃的态度,正是四库馆臣祖承诗教、尊经重学的必然结果。
综上得见,《总目》通过对历代赋家赋作的点评,建构了自成体系的赋学批评框架及赋学理念,那便是以典雅渊博、气体醇正为宗。对赋作,既需张扬赋作表情达意,又需要雅简洁质,质言之,便是以弘历一朝以雅正清真为统摄的官学的文学思想。
三、《总目》辞赋批评对创作的浸染及成因
自福临率八旗入关以来,文人们基于故国倾覆、神州板荡的历史环境,作品中常发爱国之志,寄故国之思,写亡国之恨,书英雄之绩,一扫承平颂德之作。故而顺康时,文人多发愤懑勃郁之音。至乾隆之际,承平已久,正值盛世,故而文风已转为对醇雅厚重的追求。就诗坛言之,乾隆年间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说”风靡一时,著有《说诗晬语》,编定《唐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以“温厚和平”为诗学旨归。词坛以张惠言、周济的常州词派为代表,以“传曰‘意内言外’谓之词。”[39]散文创作上,以桐城派影响最大,倡“义法”说,方苞言:“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40]一言蔽之,皆强调雅正之文。
在此文风影响之下,辞赋的创作与对辞赋的批评亦受此影响,多表现为对醇雅清真风格的手追心慕。是时,馆阁律赋竞起,虽有才学赋、骈赋等以才学与性情争之,然不逮成鼎立之势。乾隆后期,更是出现了数量不少的颂圣之作,从主题思想看,颂美鸣盛完全占据了主流,讽谕谏上的功能被剔除,工正醇雅有余而情采鲜乏,华美有余而气势空疏。承平良久的康乾盛世,使得无论是散文创作的博雅综丽,诗人的感怀寄兴,骈文的尚美对偶,经学家的经史兼备,大多无哀怨牢骚之言,都是文质彬彬的,与盛世之间的清代气象的相符的。
《总目》对醇雅清真文风的提倡,实则与统治者与总纂官纪昀的关系作为密切。弘历最为最高统治者,多次敕令《四库全书》的编修,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下旨“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41]始,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南三阁抄成终,历二十年。因而弘历的文艺思想无疑会决定着《四库全书》的摭拾准则和文学批评路径。清圣祖玄烨对文学批评已有“雅”的概念,清世宗胤禛于雍正十年(1732)七月二十八日下谕,言:“近科以来,文风亦觉丕变,但士子逞其才气词华,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是以特颁此旨,晓谕考官,所拔旨文务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备。”[42]继承与发展了先帝玄烨的“醇洁”文学思想。清高宗弘历在二位先帝的文学思想基础之上,进一步以“醇雅”作为清帝国最高的文学准则。陈水云先生指出:“‘醇雅’的实质是适应封建统治者的要求,宣扬儒家诗教传统,强调言情不轻佻,出辞不陈俗,思想醇正,不怨不怒,中正平和。”[43]弘历自己认为:“朕思学者修辞立诚,言期有物,必理为布帛菽粟之理,文为布帛菽粟之文,而后可行世垂久……国家累洽重熙之日,务学继文者。正宜沐浴教化,争自濯磨,靳进于大雅。勿尚浮靡,勿取姿媚。”[44]
弘历作为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思想是《总目》一书品评的导向,正如纪昀在《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中所言:“元元本本,总归圣主之持衡,是是非非,尽扫迂儒之胶柱。至其盈箱积案,或汗漫而难寻。”[45]309然其不可能对具体作品做出具体的评点。而纪昀作为总纂官,同时亦主持《四库全书》集部的纂编分校,故而集部的提要更多地渗透了纪昀的文学思想(1)此问题学界已有诸多相关研究,如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3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蒋寅《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歌批评》(《学术界》2015年第7期184-195页),等。。纪昀毕生心血倾注于《总目》的撰写,因而其学术、文学批评思想是渗透至《总目》中的,《总目》的提要都经纪昀削删。作为四库馆臣的代表人物,纪昀植根于经史,持雅正典则之言,主诗写性情之真,代有气运之变的文论,因而他推崇“古学”,反怪诞妄言,轻浮华无稽之文。他曾言:“夫古学,美名也,崇奖古学,亦美名也。名所集而利随焉。”[45]337以此为批评范式,对于徒饰古学之文,一概不予录用。同时他亦认为:“文章各有体,亦各有宗旨。区分畛域,不容假借于其间。故辞赋之兴盛于楚汉,大抵以博丽为工。司马相如如称合纂组以成文,刘勰称金相玉式,艳溢锱毫,是文章之一体也。”[45]336-337纪昀强调辞赋为文章一体,认为辞赋的文体特点便是形式之美,巧得博雅之长。
除此,纪昀对辞赋的观点亦体现于他本人的辞赋创作实践、论赋专文以及评点《文心雕龙》中涉赋的文字。《历代辞赋总汇》收纪昀创作的辞赋共23篇[46],就整体辞赋风格言之,多雍容典雅之言,发灵秀蕴藉之音。虽有应制之赋,然不乏清新典丽的词句,有韵律和谐、含蕴深厚之美。同时,在《清艳堂赋序》中,纪昀也表达了其赋学观点,他认为辞赋应该“撷徐庾之精华,而参以欧苏之变化”[45]371,“清思绵邈,灵气纵横”[45]371,同时将诗赋的关系比拟为书画,认为:“体格异,而运掉之关捩则同。”[45]371因而他认为:“然则世之求工是技者,反求其本足矣。”[45]371辞赋要义在于融入儒圣入世的精神同时,加强人格的修养,总而观之,则是传统的政教论文的文学批评路径。《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论赋有“控引天地,苞括宇宙”“错综古今,总览人物”“纂组锦绣,经纬宫商”[47]三个创作维度,而纪昀认为这些赋论纯就修辞而言,皆是肤浅之词,夸大其词罢了,因而有“徒张大其词耳”[45]371之论断。
《文心雕龙》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有“体大而思精”之誉,其中《体性》篇言及文学创作与作者性格之间的关系,强调:“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18]505重才学,重风骨,重神采,是四库馆臣辞赋批评的自然逻辑,具体至纪昀评点而言, 其对《诠赋》《辨骚》《颂赞》《杂文》等篇目涉赋的批评亦建构了他对刘勰的二次批评。在对杨慎、梅庆生、曹学佺、陈仁锡、钟惺、李安民、黄叔琳等前贤学人的研究基础上,纪昀提出了对《文心雕龙》文论的看法。如对于刘勰宗标自然之道,他批注道:“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48]14此处他既肯定了刘勰能结合时势,对当时文风的批判,又指出刘勰文艺批评的桎梏,指出他的局限性。
纪昀首先明辨了辞赋的起源,他认为“赋”源于“骚”:“词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辨字极为分明。”[48]24在“骚”为“赋”之源的基础之上,主张“赋”的铺张靡华滥觞于“骚”。而就辨体言之,他主张:“分别体裁,经纬秩然。虽义可并存,而体不相假。盖齐梁之际小赋为多,故判其区畛,以明本末。”[48]36作为不同文体的“体”相同,然其“用”不尽一致,对刘勰将辞赋区分为“京殿苑猎”“草区禽族”,冠以“体国经野,义尚广大”“触兴致情,因变取回”“言务纤密”“理贵侧附”的文体性征是认同的,他的这种鲜明的辨体意识,与他文各有体的文艺批评是相通的。出于对文体明辨的批评逻辑,纪昀对辞赋的文体持“兼综说”,在《诠赋》篇中,他批注道:“铺采摛文,尽赋之体,体物写志,尽赋之旨。”[48]35自汉一代以降,赋体争端,各执一词,或言主凭虚铺采,或言主情志意,莫衷一是。纪昀此论,从“体”与“旨”二维出发,指出赋兼具比与兴两个层面,揭橥了“赋”的深层性质,对后学在赋比兴的阐释之上多有启发,表现为既认同辞赋的功用,又认同其辞章与情感的表述。
六朝文风绮靡,纪昀对这种风格是批判态度的,他肯定了刘勰对于浮靡文风的批判,然而他并未因此否定整个六朝的文风。在《丽辞》中,他认为“骈偶于文家为下格”[48]118,但是又说:“然其体则千古不能废。”[48]118《声律》中认为“四声八病”自沈约《与陆厥书》而发扬光大,“齐梁文格卑靡,独此学独有千古。”[48]113纪昀作为“官学”的代表人物,有明确的文体观念意识和文学自觉性,然基于其身份,其终极追求是文学的经世致用,旨归仍然是醇雅清真,因而他对辞赋的观点是推崇文质相间的,因而在刘勰认为“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18]256之时,纪昀评为:“仍归重意理一边,见救弊本旨,所谓‘与其不逊也宁固’。”[48]54在《夸饰》篇则眉批言:“文质相扶,点染在所不免。若字字摭实,有同史笔,实有难于措笔质时,彦和不废夸饰,但欲去泰去甚,持平之论也。”[48]125均是纪昀求雅追实、救俗之弊的赋学宗旨。
综而论之,在清高宗弘历及纪昀为首的四库馆臣的引导与建构之下,《总目》形成了以醇雅清真、文质相符的辞赋批评观念。四库馆臣作为文坛的活跃力量又将此种赋学倾向运用至辞赋创作中去,又因官学的权威性,影响了大批风雅文士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双向的互动,从而推动了乾嘉赋学的兴盛,形成了体制多元、各自繁盛的局面。
四、余 论
要之,四库馆臣通过《总目》对赋集赋做出了较为系统的批评,建构了自身的赋学批评范式。通过梳理《总目》中涉及辞赋批评的提要可以发现,首先,四库馆臣推重古体赋,对于空疏的律赋、独求声律对偶的骈赋,皆是持批判的态度。其次在历代辞赋的批评中,四库馆臣们推崇抒发性情,言之有物,征实典雅的辞赋作品,对于虚妄怪佞、空谈无根、雕琢习气浓重的作品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在这其中,尤其注重辞赋中情感的灌注和抒发,由此可见,是否具有真情实意,是四库馆臣辞赋批评的第一要义。
四库馆臣大多为乾嘉时期的学术大家,同时也有文人创作者的身份,作为总纂官的纪昀更是典型人物。通过纪昀论赋的言论,发现纪昀主张诗赋同源,认为赋与诗一样具有社会教化与伦理道德建设的实用性功能,在形式美与现实美的权衡之间,他主张文质相济,这也是《总目》辞赋观的基本批评根基。清高宗弘历作为《四库全书》编纂的下令者,同时又热衷于文学创作活动,其“醇雅”的文学思想是《总目》编纂的最高统摄,“清真”是先帝胤禛的文学思想,此二者构成了《总目》的辞赋批评最高指导思想。作为最权威最官方的赋学批评准则,《总目》的辞赋观念深深影响了乾嘉时期的辞赋创作,形成了双向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