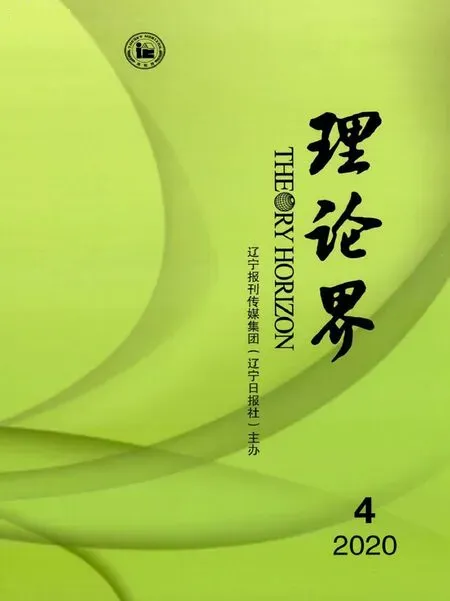《红楼梦》王际真译本西传研究
严苡丹 张秀明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的代表,赢得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他们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风俗、宗教等的重要途径。海外《红楼梦》的译文和译作很多,国外出版的《红楼梦》西文译本有几十种。在英语世界,从英国汉学家德庇时选译《红楼梦》第三回中的两首《西江月》词开始,到1991年外文出版社出版黄新渠的《红楼梦》英文简易本为止,共有15种英文译文或译本出现。〔1〕
一、《红楼梦》的西译历程与动机
《红楼梦》的西译历程跨越近160年,不同的时期社会背景不同,《红楼梦》西译的动机也不一样。陈宏薇和江帆在《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描写性研究》中把《红楼梦》的英译分为三个阶段。〔2〕
第一阶段(1830-1893) 是《红楼梦》西译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红楼梦》译文和译本主要有四个。一是1830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德庇时(John Davis) 翻译的《红楼梦》第三回片段译文,刊登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的《汉文诗解Poeseos Sinensis Commetarii.XXI.On the Poetry of Chinese》;〔1〕二是1846年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特·汤姆(Robert Thom) 翻译的第六回片段译文,题为Dream of Red Chamber;三是1868年到1869年海关税务司的包腊(E.C.Bowra) 前八回的译文,连载于《中国杂志》 (The China Magazine);四是1862年到1893年英国驻澳门副领事乔利(H.Bencraft Joly) 第1-56回译文,是由Kelly& Walse出版的单行本。陈宏薇和江帆认为,这一阶段《红楼梦》翻译的目的是提供语言资料:德庇时是从殖民者的视角对亚洲文化感兴趣,其他三位是希望在华外国居民可以阅读《红楼梦》译本更好地学习汉语。乔利译本的译者序也证明了这一点:“……对现在或将来学习中文的学生,拙译如能稍有帮助,我就感到十分满足。”〔3〕
第二阶段(1927-1958) 出现的译文与第一阶段相比,内容明显增加,基本能节译原著全文。其中英文译本有三种:王良志译本、三个版本的王际真译本和麦克休(Florence Mchugh & Isabel Mchugh) 译本(转译自德译本)。王良志译本(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于1927年在纽约出版,节译全书,共有95章,在译本序言中,史密斯博士阐释了“新红学派”的观点。此外,“译者在翻译时删除了大量与宝黛爱情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只译出了关于宝黛爱情悲剧的描写”,因此,陈宏薇、江帆主张“这一独特的爱情悲剧对西方读者有特殊的吸引力,因此,译者必须紧扣这条主线,删除其他无关“枝节”,使译本成为一部不折不扣的爱情悲剧”。王际真译本有三个版本:1929年的39回译本,卷首附有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的撰写的序言及译者自撰的导言。1958年有两个译本,一是根据程乙本和参考胡适提供的甲戌本译出的60回译本,二是译者为照顾译者阅读惯性,推出了一个40回译本,是60回译本的节略。〔4〕王际真译本同样受到了新红学思潮的影响。在1929年译本序言中,英国著名东方文化研究者阿瑟·韦利对小说在中国文学领域的地位作了阐述,他评价《红楼梦》道:“不过《红楼梦》与先前所有中国传奇小说的不同之处……这些人物(据胡适博士考证) 就是作者本人和他的家庭。所有现实主义小说自然都是现实主义小说。作者的实际知识主要来自亲身经历。红楼梦更是一部完全的自传体小说。……曹雪芹也许会很容易犯一个毛病,即把千篇一律的生活写得过于仔细。”〔5〕1958年40回译本的译者序中,王际真就曹雪芹的家世背景作了介绍,认为作者是在写他自己的家庭。
由此看来,这一阶段王良志和王际真都受到五四运动后“新红学运动”的影响。陈宏薇和江帆认为:“王良志和王际真对《红楼梦》的哲学、社会学、史学、文学和美学价值有一定认识。……很明显他们有能力,也有意图对《红楼梦》进行全译。……然而美国出版商只考虑到美国读者的大致期望,要求将小说改变成具有异域风情和传奇情节的单纯爱情故事。”〔2〕这一点在《哥大与中国》对王际真的介绍中得到进一步证明:“王际真写了一篇几十页的长文深入介绍了他喜爱的《红楼梦》。在诧异的美国人面前展开了一个奇情绚丽的感情世界,一个不同于马可·波罗描述的,也不同于传教士们带回来的那种关于中国的想象的典雅的境界。千呼万唤,王际真的文章吊起了美国人的胃口。精明的出版商适时找到王际真请他翻译这篇巨著。当时,性急的出版商无意真正介绍中国的古典,也无法理解《红楼梦》中的风流蕴藉、钟鸣鼎食之家的那种华贵富丽及其细腻深挚的情感世界。他们要求王际真尽可能地介绍故事情节来节译这部巨著。王际真却尽可能地保留了这部伟大作品的优雅风格和原始的美的风貌。”〔6〕由此得知,这一时期英语读者对充满异域风情和传奇色彩东方文化的期待是《红楼梦》西译的一个重要动机。同时,译者在中国“新红学运动”的影响下,对《红楼梦》具有科学的认识,有能力或有意愿在译文中传达这部中国巨著的文学价值。
第三个阶段(1973-2000) 产生了现在比较流行的两个全译本:霍译本和杨译本。这一时期,“产生于19世纪作为语言教科书作为语言教科书的《红楼梦》选译本和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仅仅关注恋爱情节的《红楼梦》节译本,都远远不能满足新时代读者的需要,能够充分传达《红楼梦》艺术魅力的全译本因此应运而生”。〔2〕因此,在这一时期,传达《红楼梦》不朽的文化艺术价值才真正成为这部巨著西传的目的。
当前流行的《红楼梦》英译本当属霍克斯、闵福德译本(以下简称霍译本) 和在国内出版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本)。这两个全译本对帮助英语读者深入理解和欣赏《红楼梦》,详细探究这部文学巨著的文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这两个全译本出现之前,英语读者初步认识和了解《红楼梦》的主要途径是王际真译本。王际真的三个译本,又各自衍生出了转译本。由1929年译本转译出的是博尔赫斯的西班牙文摘译;由1958年60回译本转译出了迄今为止唯一的希腊文译本;由1958年40回译本转译的是首次成书的泰文译本。〔4〕由此看来,王际真译本不仅对《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有持续性的影响,还对《红楼梦》在西班牙文、希腊文和泰文世界的传播产生了拓展性影响。
二、《红楼梦》王际真译本的运作方式
1.异域情调的传递
王际真在1929年译本译者说明的第五部分“Some remarks on the Scheme of The Present Adaption”中指出了其节译的原则:首先,基本囊括了宝黛爱情的基本情节;其次,也试图保留表现中国风俗、习惯的插曲与片段;再次,还保留了少数诗歌。〔7〕1958年译本的译者说明中,译者承认:“第一个译本中,我认为《红楼梦》主要是一个爱情故事,省略了很多看似琐事的情节。但我现在意识到曹雪芹所描述的大家庭的生活和‘琐事’,同宝黛爱情一样,对译本至关重要。因而我增加了许多女子之间零碎的嫉妒与争吵环节,这些内容在旧译中被忽略掉了。”因此,在保留中国风俗习惯,向英语读者展示异域风情方面,译者从一开始就作出了努力。在1958年40回译本中,译者特意保留具有异域风情的元素,例如涉及中国民间传说的女娲(Goddess Nügua);中国传统节日的元宵节(the Feast of Lanterns);体现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进士(Chin-shin degree)、探花(t'an hua);中国特色称谓的老爷(Lao-yeh)、姑娘(ku-niang)、姥姥(Lao-lao)、大爷(Ta-yeh)、大娘(Ta-niang)、嫂嫂(Sao-sao)、陪房(pei-fang)、太太(Tai-tai)、薛姨妈(Hsueh Yi-ma)、妹妹(mei-mei);佛教用语阿弥陀佛(Amitofo)、施主(kind donor) 等等。译者在翻译上述词汇时,使用了汉语拼音的方式,特别像太太、妹妹这样的词汇,在译语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对等词“Mrs”“sister”,译者却仍然用异化加注释的策略,平添了几分异域情调。同时,译者也有考虑到读者的理解加注。例如,译者对姑娘(ku-niang) 作的注释:“Ku-niang is an honorific for unmarried young ladies.”〔8〕
译本保留的异域情调不仅仅体现在专有名词上,对于原文中的意象和措辞译者也尽量传递再现,如:
例1,原文:平儿说道:“癞蛤蟆想天鹅肉吃,没人伦的混账东西!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9〕
王译(1958):Patience said,“A case of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the swan's flesh.’He should be made to suffer for this.”〔8〕
例1中的“癞蛤蟆想天鹅肉吃”是汉语中的特有表达,措辞有趣,意象生动,但对于西方读者这个意象是陌生的。同时,这句谚语并不难理解,通过理解字面意思,西方读者可以体会它的隐含意义。所以译者保留了这个意象,既让读者体会到了异域特色,又能通过阅读领略此谚语的含义。译者保留异域特色的同时具有读者意识,考虑了读者的接受。
2.注释
《红楼梦》王际真1958年40回译本共有脚注64个。脚注主要是对原作中的人名、称谓进行解释。对人名的解释,例如:“Chen Shih-yin” (甄士隐) 的脚注为“Homophone for‘true matters concealed.’”;“Chia Yu-tsun(贾雨村)”的脚注为“Homophonous with the first three characters of a four-character phrase meaning ‘disguised in the idiom of the uncultivated.’”。原著第一回讲:“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故曰‘甄士隐’云云。……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故曰‘贾雨村’云云。”〔9〕甄士隐和贾雨村在中文中是谐音双关,曹雪芹这样暗喻了小说的创作思想。〔10〕就如译者所译,甄士隐谐音“真事隐”,贾雨村是“假语村言”前三个字的谐音。译者对人名谐音添加注释,能让译语读者获取人名的隐含之意,更好地理解小说的创作思想。对称谓的解释,例如:“Lao Tai-tai”(老太太) 的脚注为“Honorific designation for the mother of the master of the house.”;“Mei-mei”(妹妹) 的脚注为“Younger sister.”;“Yima”(姨妈) 的脚注为“Maternal aunt.”等。王译本中称谓的翻译大多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使用了汉语拼音的方式,因此,关于称谓的注释对译语读者理解全文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此外,译本还对文化专有名词、习俗、词句隐含义等作了脚注。如:“the Red Dust”(红尘) 的注释为“The mortal world”。
这些注释有助于译语读者更好地理解《红楼梦》这部巨著和把握中国这个神秘东方国度的异域文化。这一译本脚注共64处,数量和篇幅上控制得当,作为小说文体,既提供了相关背景信息,又不影响译语读者阅读的流畅性。此外,译者还在译本正文之前提供了一个人物关系表,帮助读者理解《红楼梦》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可见译者为让读者深入理解这部小说的良苦用心,这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西译具有借鉴意义。
3.删节
王际真译本的一大特点就是删节篇幅较多。以1958年40回译本为例:32开本,一卷,共352页。而霍译本:32开本,一共有五卷,总共有2576页;杨译本(2010):32开本,共3卷,总共1886页。与全译本相比,王译本删节了大量内容。这与出版商的要求有关,出版商无心真正传达这部巨著的文化艺术价值,只是想尽快把《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展现到对东方文化充满期待的英语读者面前。在这样的背景下,译者必然侧重于故事情节的叙述,对译文进行改写,删除了很多与主要情节无关的内容。以1958年40回译本为例,原著中很多大段段落被删除,如第五回宝玉在秦可卿房内入睡,在梦中进入“太虚幻境”,看到了金陵女子的簿册,并读了十四位女子的判词,译者只选译了前三首判词;而对后文中舞女演唱的“红楼梦”十二支的原稿,则全部略去不译。究其原因,一是译者不得不考虑出版商的要求缩减篇幅;二是诗词对于译语读者难于理解,即使全部译出,读者可能也没有耐心细读。另外,第六回贾蓉借玻璃炕屏、第七回周瑞给姑娘们送花、凤姐见秦钟;第八回宝玉看望宝钗时与人对话;第九回袭人的叮嘱,宝玉拜见贾母和贾政,跟黛玉作辞等琐细情节在译文均被略去。
因受制于赞助人的要求、中西两种文化语言的差异以及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译者的删减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1927-1958年这一阶段,译本是译者意图和书商意愿所折中的产物。〔4〕
4.诗学的翻译
《红楼梦》“将诗、词、赋、楹联、诗谜、偈语、酒令、谣谚都吸收到小说的叙事中,使之成为诗性化了的小说典范”。〔11〕《红楼梦》文备众体,据粗略的分类统计,其包含诗、词、曲、赋、歌、偈、谣、谚、赞文、灯谜诗、诗谜、曲谜、酒令、牙牌令、匾额等225篇,除去匾额一共有207篇诗文。〔12〕对于原作中的诗歌,王际真在1929年译本译者说明中提到他“保留了少数诗歌”。1958年40回译本译者只译出了15首诗(包含对联)。如上文提到的金陵女子的判词,译者只译了三首(即晴雯、袭人和香菱的判词),其他女子的一概删除。还有贾妃省亲时宝玉、黛玉、宝钗等所作诗词,以及黛玉感叹自己身世遭遇的《葬花吟》等都被省略。译者译出的15首诗,大多采用意译的方式,译出原诗句蕴含的意义,却不能再现原诗的音韵。如:
例2,原文: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挂念。〔9〕
王译(1958):Clear days are rarely encountered,
Bright clouds easily scattered.
Her heart was proud as the sky,
But her position was lowly on earth.
Her beauty and accomplishments only invited jealousy,
Her death was hastened by baseless slander.
And in vain her faithful Prince mourns.〔8〕
例2是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中晴雯的判词,原词平仄交替,且前两句对仗,读起来具有节奏感;“散”“贱”“怨”和“念”押“an”韵,“逢”与“生”押“eng”韵,增加了这首判词的韵味。而译文并没有讲究格律,节奏感较弱。在押韵方面,只有“encountered”和“scattered”押尾韵,译文的诗韵较弱。
5.文化专项术语的翻译方式
《红楼梦》是一部集传统文化大成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红楼梦文化包含科举、官制、宗教、人名等各个方面。在科举文化专项术语的翻译中,译者把原著中涉及“科第”“考举人”等科举考试制度时,把科举考试意译成了“examinations”;此外,对上文提到的进士(Chin-shin degree)、探花(t'an hua),译者则采用了音译的方式,而且还对“t'an hua”作了脚注。在管制文化专项术语的翻译中,译者把将“外班”“知府”“列侯”和“巡盐御史”分别译为“magistrate”“prefect”“marquis”和“commissioner of salt”,译者主要采用的替换策略翻译官名,而对“巡盐御史”这个西方读者不熟悉的官名采用的意译的方法。宗教文化的专项术语翻译中,译者把“僧”和“道”分别译作“Buddhist monk”和“Taoist monk”;“空空真人”和“警幻仙姑”分别被译作“Taoist of Great Void”和“Goddess Disillusionment”。“僧”“道”以及僧道名号对译语读者来说是陌生的,译者对此主要采取了意译的方式,显然是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接受。
三、《红楼梦》王际真译本的不足
王际真对《红楼梦》的翻译是非常成功的。1929年译本出版后有人称道:“纵观全书,译者删节颇得其要,译笔明显简洁,足以达意传情,而自英文读者观之,毫无土俗奇特之病,实为可称。”而1958年的复译既承袭了旧译本精华部分,更有超越前作的章节,堪称承袭与超越的佳作。〔7〕
但译作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仍以1958年40回译本为例,译者对各章的取舍很不均匀,越往后越仓促,叙事节奏明显加快。译本前10章平均每章涉及1.9章的内容;11-20章每章涉及原著1.7章的内容;21-30章每章涉及原著2.3章的内容;31-40章涉及原著4.5章的内容。由此看出,译者在对原著进行选译的过程中,前半部分还能保持均匀的节奏,到最后节奏明显加快,尤其是最后3章,平均每章涉及原著7.7章的内容。译者最后部分超快的节奏,导致部分译文像是对原著的译述或概括,不利于细致地向读者传达原著的文学和文化价值。译本有些地方存在误译。例如译者对“t'an hua”(探花) 的脚注为“Title given to the second highest plac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8〕而实际上,“探花”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位列第三名的举子称谓,“榜眼”才是对第二名的称谓,译者可能疏忽了。
《红楼梦》涵盖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这给译者的翻译带来困难。因此,《红楼梦》的英译出现些许不足、误译也是正常的,瑕不掩瑜。王际真译本虽然是节译本,但在杨宪益、戴乃迭1978年全译本出现之前,是英美最流行的《红楼梦》版本。〔13〕而且在当代美国,王际真译本还在人们的视线当中,2008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弗罗斯特博士把王际真译本作为《中国女性研究》课程的基础课本。〔13〕由此可见,王际真的《红楼梦》译本是非常成功的,对于英语读者了解《红楼梦》和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西传是“中学西传”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某一时期、某一古典小说的译作,能够以小见大,窥视古典小说西译的目的。从译作在异域情调,注释,删节,诗学的翻译,文化专项术语的翻译等翻译策略方面的处理方式能够一定程度反射出中国古典小说西传的概貌。本研究以《红楼梦》王际真译本为例,透析古典小说西传的情况,发现译者对译作的处理非常成功,满足了英语读者对东方文化的期待,成为全译本出现之前英美读者了解《红楼梦》的主要途径。此外,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传播和运作的特点,我们还可以更加细致地从翻译范式、载体、文化解读等方面入手,研究某一时期的多部译作,从而发现这些作品西传的共同特点,对中国古典小说西传进行描述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