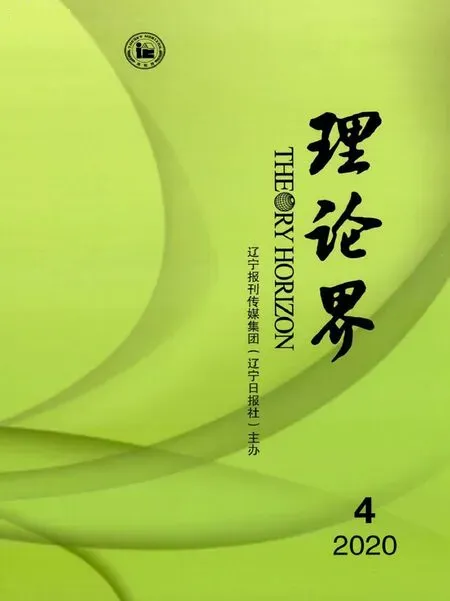“良知”的展开
——唐君毅论“宗教意识”
李占科
一、引言
在宗教本质的把握与规定问题上,吕大吉先生认为在近代宗教学研究中有三种方法最有影响:第一种是以宗教信仰的对象即神或神性物为中心,把宗教理解为以神道为中心的信仰系统,主张宗教的建制化形态,此种属于宗教人类学或宗教历史学的研究范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宗教学研究的主流,代表人物有弗雷德里赫·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ller 1823-1900) 爱德华·伯尼特·泰勒(Edward Burnet Tylor 1832-1917)、赫伯特·斯宾赛(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 等;第二种是以宗教信仰的主体即人为中心,强调信仰主体的内在心理主观活动,把信仰主体的个人神秘体验或先验意识理解为宗教的本质核心,此种是属于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代表人物是美国宗教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第三种是以宗教信仰的社会环境为中心,从宗教的社会功能与作用方面来规定宗教的本质,此种属于宗教社会学的理论范畴,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密尔顿·英格(M.Ying) 以及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宗教观也属于此类。〔1〕
正如著名宗教学者威尔费雷德·史密斯教授指出的,〔2〕人们对于宗教的抉择一般存在着两种分歧,一种认为宗教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威严表现在严格的禁忌方面,强迫着人们采取某种行为,否则就要受到神等外在力量的裁制;另一种理解宗教的思路是,其并不否定宗教外在的强制力量,但是所注重强调的是人们在面对这种外在力量时的内在情感。
唐君毅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显然他对于宗教本质的抉择倾向于一种宗教心理学式的内在的研究范式。因为作为承续宋明心学传统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儒家传统历来是强调人的主体内在性与人心的先验性的,所以唐君毅在宗教问题上完全是从人之意识心理活动方面入手着眼的。在其宗教文本中,宗教与宗教意识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是可以等同的。而对于第一种神性的信仰体系,唐君毅显然是不轻许其为宗教的本质的,因为他对于宗教的抉择从一开始就是属于一种精神性的范畴,而并非是一种建制化的宗教形态。
二、唐君毅论“宗教意识”
在唐君毅看来,人是一种综合意识的存在,具有家庭意识、经济意识、政治意识、科学意识与更高者之艺术求真与求美之意识等,此种种自决性的意识活动意识构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特质与发展方向,虽价值取向与旨归有所不同,但都是人之道德自我的分殊表现,都是自我之精神倾注、贯穿于客观者,如人之求真、求美之意识是自我之精神忘却主观心身活动与超越实用目的而求之于客观之真、美的价值诉求。虽然彼此意识之间互相有所促进、补足,例如求真与求美意识也可以促进国家政治意识与人之家庭意识与伦理的完善;科学意识可以促进经济意识的前进并带来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会造成经济之中唯科学主义的形成;此种种补充与促进是相待的,虽然有所促进但是利害相随,无异于以偏纠偏。因为在唐君毅看来,此种种意识“皆为不完足而相待者”,〔3〕即人之求真、求善与政治、社会、经济等意识的完备仍不能满足人之意识的绝对要求,仍不能安顿人之精神生命诉求。人在此种种意识之中无法实现人之自我完善,不可能获得绝对纯粹之精神自我,也无法使人在终极关怀的关照下获得道德自我的完善,以在道德要求上立于无过无愆之境地。所以唐君毅在文化哲学、理想与人文主义的理论视角与立场下对种种自然主义与功利主义予以彻底的否定,希冀建立一种人的最高意识即宗教意识,以保人文世界之长存不坠与人之道德自我的终极建立。
人作为一种自然生命,存在于自然宇宙之中,受自然生命之律则的支配,这种律则就是指人之“所消耗”与“能恢复”〔4〕两者之间的平衡。人之日常意识活动都要引起人之自然生命力的消耗,自然生命耗费的弹性恢复一般要靠物质、生理欲望的享受与满足,这种受生命律则支配的是一种常态的、自然的生命意识。然而,人之超自然的本性使人追求一种超越现实生命的解脱意识以及生理物质欲望之根绝的更高一级的精神意识,这样一种超越精神只能求之于人类更深层的意识,即是唐君毅所认定的宗教意识或谓宗教精神。
何为宗教意识?对于人类宗教意识以及超越性存在产生的源起与动机,人们一般认为,这样一种超越意识常常是由于人自觉其主观之生命精神力量的微弱,在苦痛、挫折、不公之待遇与冤屈面前常感心力不足、难以自拔而又无处申诉,自我之幸福无从获得,所以希望有一种代表着正义的完满至善之存在来主持社会公道与正义,赏善惩恶以维持人之理想的价值秩序,由此而有神之观念、有灵魂之不朽等宗教因素的存在。
但是在唐君毅看来,要想证实宗教观念存在的合理性,如果仅仅从人在苦难面前的无力、人之获得幸福的企盼以及社会正义的实现方面来理解宗教意识的产生,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从反面来讲,在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社会趋向正义、人之苦难得以拔除、人之幸福可以获得,如此种种似乎完全可以有实现之趋势,如果这样的话,宗教之源起完全可以根绝。显然,除正义、幸福等宗教产生的外在根源之外,还有基于人之精神深处的动机,这在唐君毅看来就是人之“欲求圆满之德性”,〔5〕即人之自觉向上地追求圆满、追求超越性存在的价值诉求,即基于人之精神深处的道德理性之求超越、求圆满的价值取向。
唐君毅认为,宗教意识本质上是一种“求现实自然生命之解脱而皈依于神之意识”。〔6〕一种超现实自然生命之解脱的意识必然会引导出一种超现实之存在,这种存在是一种价值存在而非一种事实存在,可以是西方观念中超现实的彼岸之神,也可以是中国文化中超越而内在的本性。这种超越性价值存在的实现即是一种“超越的我被欲望的我神化而后又被客观化,最后欲望的我使自己皈依于这超越的我的客观化了的神”的过程。〔7〕也就是说,神等超越性价值存在的产生源自于人的一种欲望之后的对于超越性的心理企盼。本质上,人的自然欲望是无限的,因为自然生命的消耗与恢复是双向的、平行的、循环的。于是,人就想求得一种解脱,希望借助于一种超越性的力量以解脱其自然欲望而实现其人生诉求。基于这种解脱意识,人就会倾向于一种超越现实自然生命与生理欲望限制的意识或者价值存在,这种存在就是神的意识或者其他形式的超越性意识。超越意识的出现是人之自然生命求解脱的诉求与表现归宿,而解脱即意味着忘却、压抑,自然生命的解脱即自我自然意识的忘却,忘却自己的财富、地位、权利等而贡献于神(或者说是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实体),压抑或抑制生理物质之欲望以尊令于神(或者说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超越诉求),乃至于舍弃生命以皈依于神(或者说是一种纯粹的道德自我、精神自我与超越自我)。由此,宗教意识的产生就是由自然生命解脱之意识过渡到对神等超越性价值存在的皈依之意识,即是一种超越性的主观心理之终极诉求。
西方文化的神本路向对于上帝的存在,一般是以先验设定与观念存在的上帝概念为前定,然后再对上帝概念予以人之思维的推理与逻辑的证明,所以西方理性主义的兴起也并没有撼动其宗教的价值取向。即使在极度标榜理性、勇于怀疑一切的笛卡尔那里最终也是没有逃离神学的窠臼而为不证自明的上帝留下了终极之席位。欧洲中世纪经院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用“五路说”解释并推导出了作为万物存在第一因的上帝。但是在唐君毅看来,依照这种证明推理或者直觉审美而建立的神的观念并不能引导出人对于超越之神的皈依意识,人的逻辑推理最终指向的并不是神的观念。“此本体或生命之神,只显为思维直觉之客观所对,而不同于宗教意识之神,为崇拜皈依之客观所对。”〔8〕所以唐君毅立足于人之观念深层的道德自我意识,继而诉诸人之求超自然现实生活中的解脱意识,引导出一种超越性存在以及对其皈依的意识,这种超越性的存在就是神(天) 之观念,这种皈依意识即是人之宗教意识。唐君毅为宗教意识的产生所给予的涵摄人文与超人文的结构阐释包括三方面的要素:即苦罪意识、解脱意识、超越意识。
1.苦罪意识
人是一种有限存在的残缺美,人的现世生活总是不尽如人意、不满人欲的。面对浩瀚无穷的宇宙,庄子感人生之行休而有“以有涯追无涯”之殆;面对波涛滚滚的江海,斯有孔子“逝者如斯夫”之叹;终将逝去,吾人也常有“化作春泥更护花”之希冀!
对于人生的有限性,徐复观有“忧患意识”一词,认为“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9〕牟宗三高度称许徐复观的这个概念,认为中国文化浓厚的道德性即是源自这种忧患意识,并认为中国文化的这种忧患意识可以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以及佛教的苦业无常意识相对显。〔10〕无论是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抑或是基督教的原罪观念还是佛教的无常、苦业意识,都可统之于张灏先生所谓的“幽暗意识”,〔11〕所谓的“幽暗意识”即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醒悟,他认为基督教对于这种源自人性罪恶而后又波及并导致社会黑暗的“幽暗意识”的认识是深入的,西方的自由民主传统以及“政府分权,互相制衡”的制度形式都受到基督教这种幽暗意识的影响。此外,张灏先生还指出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幽暗意识”的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与西方基督教有所不同。他认为,儒家文化中的幽暗意识是一种“生命二元论”的义理形态,即对人性作出成德成善的理想的正面肯定,但是同时也并不否认人性现实罪恶的间接映衬与侧面影射,只是对人性的乐观精神占了主流。因为人都有体现至善,成圣成贤的可能,所以政治权力就掌握在这些圣贤手中,由此儒家思想主导下的中国政治是一种“圣王”或“德治”的形态,让德性与智慧来驾驭政治权力。
这种种现实中的苦痛与罪恶大都源自于人之本性之欲求至善之境地而不能满足、不能自克,由此带来苦痛与罪恶感。但是人在面对种种人生苦罪的时候,自我意识深处会有一种自然生命解脱即苦痛与罪恶感自我消解的意识,这种意识就是唐君毅所谓的“解脱意识”。
2.解脱意识
如前所述,解脱意识的形成是建立在人对充斥着苦罪意识的自然生命的自觉之上的,是希冀从自然生命之中求得解脱的一种人类精神获得上升、求得圆满的意识。但是要想从现实自然生命之中获得解脱,就要对人之苦痛、罪恶等作一通观,即现实之我为何有如此苦罪?
人的苦罪感有两种亲证方式:一即苦罪感是从外在现实之中得来,是由人强加于我或者欲望之无法满足而产生;另一种即认为人之苦痛是由于自我之罪恶,人有罪恶而自当受苦。这种罪恶感是由人之自我剖析与向内求之而产生的,与其说是自我强加于己的,毋宁说是人之自我深处的一种意识原则,即有罪而自当受苦的正义原则,即苦痛是义之当受者。由此,现实之中的苦痛问题就有了一种道德的分际与诠释,获得人之内在精神道德的评判,苦罪感由此而转化为人之内心的一种自我意识,而不再是人之意识之外的问题。而这种苦罪感最终导向一种善的境地,人由此获得超越苦罪的善的意识,人之现实苦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罪恶感的现实负价值被消解,从而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善的正价值,为人之获得解脱提供了可能。正是因为人之痛苦而驱使人从现实之罪恶到精神之罪恶而进行自我剖析,意识到自我的罪恶而更加磨砺自我之人格,压抑、去除自我之现实欲望,在此种虚己意识之下由此而获得一种超越意识或谓神的意识。
3.超越意识
解脱意识是由人之苦罪感上升后而牵引出的一种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明显带有一种道德的分际,但其最终旨归却是一种超越道德意识而又被赋予形上意义的存在意识,这种意识指向的是一种自我的超越意识,是超越之我的客观化,即客观化了的非我者,也就是所皈依的神(天) 的存在。可以说唐君毅的宗教意识是一种既涵摄人文道德但又超越其上的意识,这种超越意识的获得即是真我的自觉。所谓“真我”即是指超越一切现实分际之后的真实之我。对于人的存在意识唐君毅作了双重划分,即现实之我与超现实之我(真我)。现实之我即陷于欲望之中的当下自我,是一种具体的、形而下的自我;超现实之我或真我,即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是一种希求从现实欲望之中求得解脱从而得以超拔出来的形而上的自我,是一种精神性自我。这两种自我意识的并存就像恶魔与神灵的较量一样在自我内部形成冲突而难以获得统一,难以求得自我之自觉的实现。“此二者的相互矛盾而使人产生一挣扎以求上达之意识”,〔12〕此上达、超越向上的动力即是超现实之我所指向的超越性的精神实体,是客观化了的超越性的价值存在,是超越之我的神化。
在唐君毅的宗教思想中,超越性价值存在的产生即是源自于人之欲望之后的对于超越性存在的主观指向,这种主观指向即是人之超越性信仰的逼出。于是,人笃信神之存在,信仰神而希求与之合一,由此并自觉地将自我的现实欲望予以否定并有所超化,少之又少终归于无,在神之面前虚己舍身而念念凝注于神之意志,对神产生一种真正崇拜以至皈依的意识。对这样一种意识,唐君毅解释道:“唯在此崇拜皈依之意识,所体会得之神之意识,能战胜吾人之欲望之我时,并使我于所受之痛苦不视为痛苦时,吾人方可觉神为吾人之真我,或吾人为神之子。而当吾人之欲望的我全然被克服超化而另感一道福,或一“超越自我真呈现”之乐时,吾人方觉吾人存在于神之国度之内部,以至成为神之化身。唯于此时“神为真我,超越的我为真我,欲望的我为非我之意识”方完全显出。此即宗教上唯容先知或者圣者说神与其自我合一,而不许一般人说神与其自我合一之故。而“自认为有原始罪恶,自认为灵魂为恶魔所居,为无明所缠缚,觉神圣为高高在上客观的超越者之意识,乃最先出现之宗教意识,亦由此而可得其解”。〔13〕
三、良知——唐君毅宗教世界的灵魂
一般哲学家都有两个世界的划分,此即是知识、经验的世界与纯粹、超验的世界的分际。一般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第一种世界,在其所及的研究世界内,科学把一切可能成为其对象的知识与经验全部结合起来,构成所谓的科学世界。然而,在此世界之外更有一根本世界的存在,这种世界不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假设,而是一种对人类现实存在思之甚切的结果,这就是价值世界。对于这种价值世界的探究是哲学或宗教区别于一般事实科学的分际所在。
当然在唐君毅的哲学体系里,这两种世界的分际也是明显的,“在此科学知识所及世界外,即把一切可能成为科学知识之对象全部结合起来所构成的世界外,仍然有另外的世界,即关连于人之实践理性或情意之审美活动、实际行为活动、宗教信仰活动所发现之世界”。〔14〕不过这两种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存在,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即事实世界并不是价值世界的衍生。此两种世界的分际不过是人之本性的双重显现,也就是说人本身是拥有内在与外在双重心路的,用唐君毅自己的话说就是“原自经验而由外入者”、“原自先验的理性而由内出者”,〔15〕而内、外两者以及由此所构成的是共同统摄于一本根之下,这种根本即是“超越自我”或者“道德自我”。此超越自我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具有根本的意义,是因为人之内外的两种思维显性,以及由此所生发的两种世界意义的价值承认与肯定皆有赖于此超越自我,而对此两种世界的价值肯定的判断标准,即是看此等意义的显现是否合乎超越自我的价值意识,是否合乎自我之“良知”,凡是合乎此的谓之是,反之即非,因为人之超越自我本身,即具有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的价值抉择的先天性。一切经验之活动、理性之思辨、道德之践履以及宗教之神秘体验都只能在“良知”的主宰与认证下成为可能从而显现其价值,由此“良知”或“超越自我”在唐君毅那里成为人之一切的价值之源与至高无上的主宰,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人类文化活动,皆是道德自我的分殊表现,能否真正显示道德理性的超越性,是判别它们具体价值的根本尺度。
在唐君毅的思想体系中,自然、人文以及超人文等价值性的存在都必须在人心之良知的涵摄与主宰之下才成为可能。当然作为超人文之深处的宗教也不例外。一般来说,因为宗教自身的超越性,人们在溯源宗教本原的时候往往会把这种神秘性的情感与体验连接于上帝,以天心下达人心,以天知主宰人知,以超人文涵摄人文。唐君毅并不否认这种神本的宗教形态,依然承认其宗教价值,也肯定其宗教精神。但是唐君毅之所以要遍识世界各大宗教,之所以要建立宗教哲学,其旨趣就在于为各个宗教寻求一判教之标准,以此建立新的宗教精神,并且希望世界宗教间的冲突可以在此新宗教精神的重建之后达到涵容与消解。由此,唐君毅不再以上帝为判断人间事的标准与至高无上的主宰,因为上帝不能直接说话,而只能通过承载其教义的教主等代言人说话,要证明什么才真正符合上帝的意图,那么就要有一个人间的标准,这个标准即是“人心”或“良知”。于此,唐君毅从神本的宗教走向了人本的宗教形式,把宗教从天上拉回了人间,不再强调宗教的神本性而是更加注重人的超越性,反对上帝凌驾于人之上,反对天知绝对高于人之良知从而与之分离。于是,在唐君毅的思想中,天知与人心(良知) 不再是绝对分离之二物,不再是因果关系、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本体与属性的关系,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是互相保和的关系,良知是天知之呈现于我,天知是良知之充极其量,人实际上还是必须先肯定其良知之存在,而以良知作为判断宗教信仰的标准。依良知之标准,一切高级宗教中的超越信仰皆出自人之求至善至真、完满无限的永恒的生命要求,求拔出一切罪恶与苦痛的要求,赏善罚恶以实现永恒正义的要求。虽然此种种要求是主观的,但是满足此种种要求的对象却是客观存在的,此客观存在乃是形而上性的宗教信仰,此即是宗教所当必有、所必然为一客观存在的理由。然而,宗教的反对者却说,社会政治法律文化之事业的本质也是为赏善罚恶以实现所谓之正义而存在的,所以他们注重人之认知活动,注重所认识的自然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情状,从而否定宗教的超越存在。但是此种依现实之人文价值而否定超人文世界的存在是不成立的,因为此现实世界是不完满而且到处充斥着不正义与罪恶的世界,这在人之求至善至真、永恒完满的本性要求下是必当否定的对象,人之良知为力求完满从而必当否认此当下现实世界的真实性,而认为此罪恶的现实世界的存在是暂时的,在其本性上是非真的。此非真实的现实人文又怎么能成为判定已然作为真实客观存在的宗教的标准呢?那么有些宗教家又以上帝、阿拉、梵天等形上性的超越存在作为判断宗教的标准,从而否定以良知来判定宗教。此种理论似乎是对的,因为只有上帝才可以判定人的事,而人则不能判断上帝的事,因为判断者必然在判断活动与判断对象之上,所以上帝是超越一切之上的,上帝不能成为被判断者而只能是被信仰者。但是在人们信仰上帝之时,其良知已然在判断,良知承认信仰上帝是好的。所以牟宗三先生认为:“上帝本来是绝对的存在,是超善恶的,是不可能被人间任何形容词所描绘的,但是人仍说上帝是善,超善恶的上帝必然是至善的。然而,上帝的至善也必赖人类主观方面的道德意识中之道德的善本身去证实。”〔16〕这种道德意识即是人之“良知”,所以人实际上还是必须先肯定其良知之存在,而以良知作为判断宗教信仰的标准。唐君毅先生此举实际上是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下,用人本性的宗教精神贯通融合神本性的宗教,即是通过人的道德主体性去透视、理解、诠释天的超越性,并由此拓展了人的超越性,并在人的终极意义上贯通了道德与宗教,实现了道德与宗教的内在合一。
四、结论
可以看出,唐君毅将宗教意识视为一种主观自我追求超越现实自我以体现人之无限性的意识,而作为宗教意识最高的神也即是无限自我意识的客观化,抑或是说此无限自我亦即是神等超越存在的主观化,由此人性与神性实现了贯通与统一。可见,对于宗教意识的源起唐君毅先生取径于人之内心深处之绝对纯粹的超越意识。他打破传统宗教观所采取的首先肯定神的先验存在,在得到神或者先知的启示之后才得以产生人的宗教意识及其信仰的启示进路。唐君毅对于这种神秘的信仰启示进路予以宽容的理解,但是他并没有以此种神本的方式去体验、证明人之宗教意识与信仰,而是采取一种人本或者说人文的证明路向,即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以人的意志为起点通过理性的推导上升到人的宗教意识。与传统神本宗教观肯定超自然世界存在的唯一真实性,认为神的超越性对人类现实世界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不同,唐君毅的这种宗教人文主义的证明路向消解了超现实世界对于人类世界的绝对制约,突破了传统宗教观中神人隔离的矛盾境地,从而实现了超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的上下贯通,实现了人性与神性的内在统一,深刻揭示了宗教存在的根源,即人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