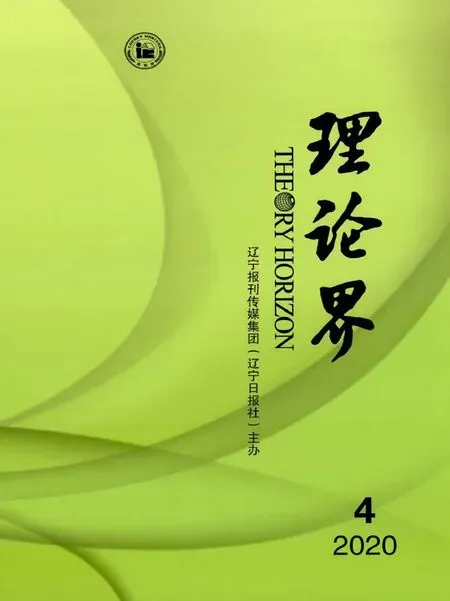破碎的新生
——从需要层次看《荒山之恋》中的自我实现
孟令军
一、前言
王安忆笔下的男主角大多具有软弱无能、堕落匮乏等缺点,不管是在现实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上,他们处处依赖女性,女性俨然成为了男人眼中的英雄,她们用女性的魅力和勇敢,令男人们依恋折服。在《荒山之恋》中,王安忆遵从她一贯的女性视角讲述了一个身体瘦弱、性格软弱的大提琴手在两段感情中的纠缠,通过第一段婚姻他认识了自我,通过另一段爱情他实现了自我。在大提琴手和金谷巷女儿这段感情中,二者的行为方式不被当时的社会环境认可,最终两人选择服药自毙于荒山之上。不少学者从文章层次分析文本,从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去看待男主人公的爱情故事。这里笔者将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分析男主人公大提琴男子的人生经历和不同阶段的自我需求,即从人性需求的角度,直接反射人性的弱点和对男人和女人在恋爱过程中的心理、生理反应的剖析,揭示出作为个体的人在自我实现和人生困境中所作出的艰难的选择。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五个方面: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并且这五方面层级是逐步提升的,也就是只有满足低层次需要之后才会有下一阶段的需要出现。因此,想要达到最高等级的需要的话,那么前四种基本需要都要得到满足。作为向善的人,在这种驱动力的作用下,才能够不断地走向整全。
王安忆的《荒山之恋》中的他——大提琴手就是一个需求层次都有所体现的例子,他在性、食物等生理需求、对家人和朋友归属与爱的需求、渴望与他人沟通的社交需求、希望得到尊重的需求甚至是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等方面都表现出来了欲求与自我实现之间存在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仅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所具有的,在当下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二、生存困境中的内心挣扎
在大提琴手的身上映射出的不只是农村与城市、物欲与精神等诸方面的冲突,更多地是在这种困顿的状态下一个人的心理历程。在《荒山之恋》的开端,哥哥带着大提琴手去求学。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十七岁的他独自面临未知的生活,长期处于封建大家庭的环境造就了他自卑、寡言的性格。王安忆在小说中并没有赋予大提琴手一个确切的名字,他是一个没有具体名字的个体,是碌碌无为的一个,同时也是万万千千的代表,是代指在面临欲求与实现之间二者矛盾对立时的所有人。所有伟大的文本的立足点都是建立在个人情感的基础之上的,《荒山之恋》也不例外,大提琴手在面对生活的问题时,如何在满足欲望与在欲望满足后的内心挣扎苦闷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点,这是他所需要面临的。
1.生理的满足与内心的痛苦
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需要是一个人能够生存下来的基本保障,生命个体想要获得生存、繁衍离不开这些最基础的物质。马斯洛所说的生理需要指的是作为物种存活下来的基本需求。对于基本的需要而言,这是整个物种所共有的现象,如果连基本的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那么对于精神层面的需要就更不用说了。
大提琴手并不是一个乐观开朗的男生,这在文本中都有具体体现:哥哥在问及他累不累的时候,“‘不累。’他轻轻地回答,乡音如歌似的掠过”。〔1〕他生性不爱言语并且还具有一颗细腻的心。在生理需要方面他也是经常得不到满足的,这在文本中时有表现: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贪馋,可是却必须抑制。他噙着眼泪,在那奶油的香味里穿行,痛苦得几乎想一头撞死在电线杆子上。可是,电线杆子在他眼前摇晃,一旦走近,却又陡然升高,擎天柱一般,他来不及的后退了。”〔2〕
在大炼钢铁、大造卫星、吃大锅饭的日子过去以后,饥荒的日子也随之而来,这对于独自在外求学,本就贫苦的他更是雪上加霜。他本是千里迢迢来求学的,可是现在连作为生活基本保障的食物,他都不能被满足。食物对于他,就像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枣过后还没尝出个中滋味就已经没有了。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甚至会产生痛苦,这种痛苦的感觉有让他“一头撞死在电线杆子上”的冲动。他不仅对同学谈论的吃食、街道卖的小吃因得不到感到痛苦,甚至还会偷吃侄子的饼干,会去操场捡几块烂铜去卖了换两个水晶包吃。在他偷吃了侄子的饼干之后,“饼干的香味顿时充满了他的全身,却转瞬即逝了”;〔3〕在他吃过水晶包之后,“吃完过后,那幸福便骤然退去,取而代之一股懊丧的心情”。〔4〕这种满足感仅仅持续了一段小小的时间,而不具有持续性,转瞬过去之后代之的是长久的懊悔愧疚。
当然,在性需求方面,大提琴手也是匮乏的:“他考上了音院附中,大提琴专业。跟了一位女老师,男人般的手,男人般的嗓音。和她比起来,他倒更像是女的了。她将他按坐在椅子上,手在他的腰脊上拍击,意思要他坐直。他坐直了,她的手却还贴在背上,热呼呼的,一直渗进了肌肤。他直直的不敢动,心里却有几分欢喜,他欢喜她是个女的,却又不像是女的。”〔5〕当老师的手贴在他的背上时,他甚至在内心会产生出“几分欣喜”,处于性压抑状态下的他会对关于异性的事件感到兴奋,因为在这之前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女性这样对过他。哪怕这是一位老师,哪怕这位老师拥有“男人般的手,男人般的嗓音”。长期生活在闭塞落后的大院里面,目睹着“长着一尊鹰钩鼻子,一双鹰隼般灼亮的眼睛”的老太爷作为家长统领着家庭,沉重缓慢在社会历史的纵线上爬行,压抑苦闷的性得不到满足,在遇到一位女老师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多少显得失态,在他与女老师性别错置的过程中更表现出大提琴手求而不得的性压抑状态。他长期生活在这种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下,并且因为这种持久性的压抑造成了他内心纠结痛苦的心理。
2.渴望被认同与内心的逃离
大提琴手生性不是一个健谈乐观的人,他与其他人显得格格不入,他喜欢一个人处于黑暗的状态下。然而这并不代表大提琴手性格孤僻,恰相反,他渴望他人理解,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但这种渴望得不到满足,他一直处于被否定、被忽略的状态,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大提琴手得不到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的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就会产生安全感;否则便会引起威胁感和恐惧感”。〔6〕这种对于熟悉环境所产生的安全感会平复他在面对未知事物时的恐惧和焦虑,“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陌生的事物,或者是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和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需求”。〔7〕大提琴手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出于安全的需要也没有得到有效满足,比如:
“这里的天空碧蓝得凛然起来,阳光璀璨的逼人,他失去了从小便习惯的黑暗的保护,好像置身在汪洋中的一叶孤舟,时时担忧着会被沉没。”
“灯光却忽的大亮起来,橱窗里的日光灯,树叶间的路灯,招牌上的霓虹灯,在同一瞬间刷地亮了。将夜晚照成了白昼,这是个不夜的城。在这突如其来的光明中,他愕然了,随即加快脚步,向学校跑去。”〔8〕
文本中的这些情节都表明大提琴手不喜欢阳光灿烂的白天,他习惯了黑暗的保护,习惯了一个人的孤独,在黑暗的状态下他才会觉得舒适自然,“暮色渐浓,他几乎有了一种醉了的感觉,忘记了一切,只是信步走着”。〔9〕即便是天气的变化也会引起他的担忧,因此,在灯光亮起来的时候,他开始变得张皇失措,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能快速地跑向学校,直到跑回学校琴房心才算安定下来。这种不安是源自他内心深处对于社会、世界产生的畏惧心理,只有在无人的黑夜中他才会觉得安心。
因为偷学校电线大提琴手被开除了,大哥到学校领他回家的时候,他感觉无地自容,这件事情如晴天霹雳在他柔弱的心灵留下了阴影。回到家里,他感觉以前的一切像一场梦,他比以前更喜欢呆在黑暗的地方了,经常窝在自己房间里一整天不吃不喝,“只有在后厢房内臭椿属阴影的遮蔽里才感觉安逸。在这个他曾经讨厌的阴暗大宅子里,此刻他比以前更需要这阴暗了,他需要这阴暗的保护”。〔10〕在黑暗荫蔽的日子里,他心中充满了悲哀、绝望,甚至觉得世界里全是无辜的不幸,没有一点儿快乐。大提琴手借助着黑暗越来越偏离其他人的生活,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在这种渴望与拒斥的对立张力下,作为主体的自我如何进行有效中和是大提琴手所面临的困难之所在。
三、情感的“失”与“得”
在感情上大提琴手是个缺乏关爱的大孩子,在家里他依恋母亲,离家上学后他依赖大哥,他渴望来自亲情、友情,甚至爱情的温暖。这里笔者将从马斯洛归属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来分析大提琴手的感情需求。对于工作已经稳定,生理需要、安全需要逐渐满足的大提琴手来说,归属于爱的需求也变得与日俱增,他急需融入社会生活中去,感受爱与被爱,学习尊重与被尊重。
1.情感的渴盼与畏惧
归属于爱的需要包括亲情、友情、性亲密三个方面。我们发现大提琴手虽然有这种需求但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荒山之恋》一开始,他就是与众不同的:“和同学们奇怪他一样,他也奇怪着同学们,竟可以一连几个小时什么也不说,什么回应也得不到地拉琴”,〔11〕同学们觉得他很奇怪,是因为他能够持续地拉琴而不去关注其他事情,一个人能够持续地拉琴,并且能够与琴进行某种交流,这在大多数人眼中是不正常的。大提琴手作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对立面而存在,他不能够做到与其他同学和谐相处,他只愿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同样认为作为人的存在物并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的人,它需要与其他事物发生联系,因此,“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2〕大提琴手也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彰显自身的价值,可是即使是在亲近的人面前他也不能很好地表达感情。比如哥哥和嫂子在诸多事情上面给予了他很多的帮助,他很想要做一些事情作为回报,他想要洗尿布作为感谢又担心保姆会来争夺,终究在内心挣扎之后作罢。他感恩他人的关心,也想作出回报,而在实际操作时又会陷入纠结。
关于归属于爱的需要,马斯洛曾经写道:“人们往往愿意冒生命危险,放弃他们的爱,失去他们的自由,牺牲他们的思想,而这一切,却都是为了这一目的,那就是使自己成为大众和统一整体之中的成员。换言之,也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同一感,尽管这是一种虚幻的东西。”〔13〕个体都有一种渴望扎入群体的冲动,这种对进入主流的强烈的求同感会让人们甚至会放弃生命乃至自由,以获得他人的认可。对大提琴手而言,他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别人不理解他的言行,他自我隔离不与外界交流,他渴望社交又心怀胆怯。
2.情感的救赎与呵护
随着家境落魄大提琴手再次走出家门被迫营生,凭借着出色的演奏技巧他成功留在了歌舞团,在这里他遇到了他的妻子(女知青)。她是大提琴手除母亲外不感到羞怯的女性,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里,大提琴手卸下负担,能够真正地回归到自我之中。妻子对于他来说既是亲人又是朋友,这使他感到自己常年的自卑、压抑终于得到了别人的理解和尊重。在她爱的滋养和鼓励下,“他开始有了朋友,一些也是从南方来的,不甚得意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他可以少一些自卑,因而也更加自如随和”。〔14〕感情在时间的推移中慢慢积累,冲刷掉了之前的坎坷和不快,这个曾经怯懦胆小的男子在爱的滋养下好像获得了新生,逐渐成长为一个健康的成年男子。在工作稳定,婚姻甜蜜,友情关爱的情况下,大提琴手渐渐摆脱了之前经历中的阴影,在幸福中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在歌舞团遇到妻子后,他得到了爱与被爱的权利,两个女儿的接连出生更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馨与幸福。在幸福的婚姻生活的影响下,他感受到了爱,感受到了来自家人、朋友的尊重,他开始变得自信乐观,只是这种场景维持得并不长久。
四、破碎中的自我实现
在面对爱情和婚姻的冲突时,大提琴手表现出感性与理性的碰撞。他不甘在平凡的生活中默默生存。当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产生了精神层面的需要。大提琴手不甘心只在物质层面得到满足,他更渴盼得到尊重,获得认可。这种认可不再是他人、社会等强加给的认可,而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自我认可,是人性最高的张扬。为了这种认可,大提琴手不惜破坏原有的婚姻,冲破道德的藩篱,在自我破碎中来加以实现。
1.婚姻与爱情的碰撞
从外表上看,“大提琴手与他妻子的结合或许被一般人认为是幸福的结合,然而这种结合模式却不是男女平等的,没有人格上的真正平等,他是她精神上的儿子,而她则是他精神上的母亲”。〔15〕虽然他们是夫妻,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性和爱在意识上并没有过真正觉醒,他们之间的结合只是性格上的契合与心灵上的慰藉。亲情不是爱情,性格决定命运。大提琴手软弱的性格造就了没有爱情的婚姻,缺乏爱情的婚姻注定在遇到真爱时变得不可一击。
金谷巷女儿是一个与他妻子截然不同的女人,她活泼、叛逆、热情、不受社会世俗的限制,由于从小受到母亲的影响,看到母亲和许多叔叔交往,她认为对男人不必付出真心,男人只是生活的调剂品,只不过是用来消遣的。金谷巷女儿和她丈夫之间像是一场战争,彼此之间更多是一种战胜、征服,这种征服欲战胜了情欲,战胜了爱情,也让他们之间缺乏爱的基础。但激情不是爱情,当征服欲望下的激情退去,他们的婚姻生活也就失去了往日的精彩与兴奋。
大提琴手和金谷巷女儿在文化宫相遇,起初她对大提琴手逢场作戏地挑逗,却不可自控地弄假成真,那种沉睡在心灵深处的性和爱的意识觉醒了,就连她自己也感到害怕了。大提琴手也被性格活泼的金谷巷女儿所吸引,但他生性是一个胆小、淡薄懒散的人。在与两个女人的感情纠葛里,他选择退缩、逃避,躲在婚姻与爱情的情感漩涡里苟且偷生,他既不想离婚也不敢私奔,以致最后酿成殉情的悲剧。
在现在看来,这种企图通过爱情的获取来证明自身价值的行为或许并不可取,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解冻不久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人的内部倾向,人竭力要完成他自己真正的本性,忠于自己的值守,成为真正的、自发的、真正表现的人,在他自己深刻的内涵中,寻求他活动的根源。”〔16〕个体渴望实现自我的本能,自我价值和归属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就成为最重要的价值体现,成为人们热望追求和实现的价值所在。
2.理性与感性的交锋
在面临爱情时,大提琴手又一次陷入挣扎撕裂的矛盾心理。每次与金谷巷女儿幽会回来后,为弥补内心的愧疚和自责,白天他加倍帮妻子干家务,晚上他会表现出对妻子加倍的爱,半夜他又会自责地揪掉自己大把的头发。一方面是有妻有女的安稳家庭,另一方面是激情四射的爱情。在平淡的婚姻与激情的爱情这二者之间该作何抉择,这是大提琴手要面对的;在感性情感与理性情感的交织下,大提琴手变得更加困顿,他明知道这样下去会引火上身,但又难以忍住对感性情感的追求,强大的感性情感会要他不断突破理性的束缚,渴望得到释放,而规训的理性情感又会反过来不断压抑感性情感,不要做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事情。在爱情与婚姻、感性与理性之间,大提琴手的人生第一次面对“甜蜜的痛苦”。感性爱情的因子不再是之前渴望他人认可的诉求,而是大提琴手作为主体的主动获取,他无需顾及外在的眼光,也不用故步自封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得益于妻子的呵护大提琴手才逐步成长为成熟的男子,大提琴手的成长进一步激发他渴望实现个体情感的自由,而在获得爱情的途中他又面临失去妻子感情的风险。这种交互复杂的情感进一步引发大提琴手内心的纠葛,他加紧了和金谷巷女儿的幽会,希望在情欲中释放自己内心的痛苦。
3.道德与人性的冲突
他们更激烈地幽会,世俗观念的约束、内心的自责羞耻全被抛在脑后,甚至在被妻子发现,被单位处分,被金谷巷女儿的丈夫殴打之后,大提琴手不仅不知悔改,反而更激烈地反抗。而金谷巷女儿为了能和大提琴手在一起甚至提出要与丈夫离婚,当她丈夫扬言:你要离婚我就杀了他。面对这种情况,金谷巷女儿心里害怕了,因为她觉得“杀他比杀她更叫她害怕。她是那么爱他,再也不能割舍了”。〔17〕面对为爱情义无反顾的金谷巷女儿,大提琴手更加陷入了道德与人性抉择的痛苦抉择中。
随着感情的加深罪恶感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本能的肯定。在向妻子坦白了一切并获得了意外的原谅与包容后,“他的心碎了,他体会到爱情的博大。比起来,那一切是多么的卑鄙与羞耻”。〔18〕在面对妻子的原谅时,大提琴手又陷入了自我纠结中,他一方面愧疚于自己的行为对家庭和妻子带来的创伤,但另一方面又因自我意识觉醒而不甘回归缺乏自我的世界里。于是,“他们又开始约会了。他们已经没有了道德,没有了廉耻,他们甘心堕落,自己再不将自己当正派人看,他们没有别的路走,只有这样了”。〔19〕世俗的伦理道德,亲情的约束,社会的谴责在爱情面前变得可有可无。在爱情与婚姻、感性与理性、人性与道德之间,他们的爱情战胜了这一切。
“就人类社会的进化史而言,‘性’早已从单纯的原始的‘生物性’功能中,转变为具有‘社会性’功能的状态。这也就意味着,愈趋近文明,关于‘性’的态度,在蒙上一层知识的理性外衣后,就会产生愈来愈多的束缚与禁忌。”〔20〕在传统习俗、文化道德、宗教、法律等各种人类文明的束缚之下,人类的本能是随着逐步屈从慢慢消失,还是会选择大胆地冲破禁锢,走向自由。从文本中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的伦理、道德,在情感、本能、自由面前的苍白无力。
从人性的角度而言,人的本能、情感、欲望可以战胜道德、传统习俗的束缚,冲破禁锢,走向自由;但是从社会现实的方面来看,人类婚姻和家庭的产生原是文明社会规训而导致的结果,这种形式一旦作为社会现象稳定存在后,就会在人类历史文明中得以延续,从一种观念、习俗发展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道德、法律来约束人类的行为,由此作为社会的人不得不在这各种风俗习惯、宗教、道德、法律的压抑甚至是阻碍下生存。不难看到,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在那个封闭的小城里有着近似不可违抗的天命。大提琴手和金谷巷女儿试图通过这大胆而热烈的爱情破除旧有文化习俗的藩篱的行为,必然不能在这落后闭塞的小城中得到认可,等待他们的是社会舆论的压迫与惩击。在长期压抑的社会氛围下他们无力与社会环境相抗衡,勇敢地为爱情燃烧后等待他们的是社会的谴责,最终死亡的方式成为成全他们爱情的出路。
在道德与人性的较量中,人对自我欲望、潜能、自由的追求最终战胜了人类文明的道德习俗,大提琴手和金谷巷女儿用死亡来捍卫爱情的自由,从而获得精神的自我肯定,实现自我价值。在生理、安全、归属与爱等需求逐渐获得满足以后,人类自觉走向对更高的自我实现的需求。这种自我实现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包括针对于至高人生境界获得的需求,“似乎有一种人类的终极价值,如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这些意味着充分实现个人的所有潜力,也就是他能够彻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充分实现他的一切可能性”。〔21〕即便是要面对妻离子散,要面对道德的审判,大提琴手第一次直面人生,正视自我,遵循心理需求,在情感的高度张扬中展现了人性之美,这种美是飞蛾扑火的义无反顾,是直视世俗的傲然不驯,在肉体被撕裂的时刻得到精神的涅槃,是真正自我需要的实现。
《荒山之恋》的结尾也颇有几分意味:大提琴手和金谷巷女儿的尸体是在七天七夜之后被几个大学生发现的。七天七夜的时间暗合了七夕的时间节点,表现了爱情的不屈;作为一个轮回,由大学生发现大提琴手的尸体,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都是青春热血的年华,这似乎又暗示了又一批的大提琴手们在成长、在恋爱,这也象征着一个周期的循环往复。开始与结尾的回环往复,大提琴手的无姓氏,生世轮回流转,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追求自己大提琴梦想的青涩敏感少年;黄粱一梦,在渴求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挣扎徘徊的纠结困顿少年又要开始新的轮回。这种命运不仅是大提琴手的命运,不仅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更是作为鲜明活泼的个体——我们每一个在自我与现实之间如何进行抉择的主体的真实写照。
五、结语
《荒山之恋》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那个政治高度紧张过后的少有松动的文学环境下,王安忆通过锋利的文笔成功塑造出一个敏感多思的少年,把当时人们对政治压迫的反抗、人性本能的绽放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是以福柯所谓最为‘疯癫’的举动,在客观上彻底瓦解了‘当代文学政治文学叙述’的正当根据,从而让人窥破了更大的历史叙事的疯癫性质”。〔22〕马斯洛的需要层次不能实现的原因不仅是外界环境造成的,更多的也有内部原因,大提琴手在不断地与欲求斗争之间进行挣扎犹豫,最终以殉情结束。以自我情感的释放作为对当时政治体制的不满,这是文学文本的时代意义;用死亡以殉爱情,这是个体在自我与现实之间作出选择的最合适方式。在自我实现和人生困境的二元冲突下,自我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获得自我救赎,这才是文本所给我们最大的意义所在。
——浙江机场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金谷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