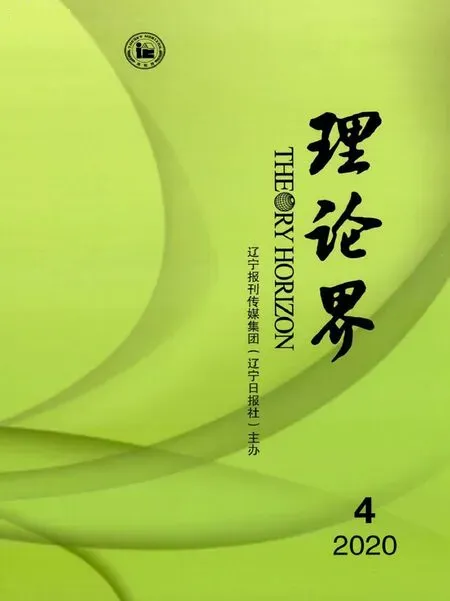论汪曾祺小说的音乐性
刘程程
叔本华说,音乐是“普遍程度最高的语言”,〔1〕他间接地肯定了音乐的多重表现意义,也说明了音乐与语言之间无法言说的暧昧。关于文学与音乐之间的联姻关系,柯克认为“一首乐曲或一首诗或一出戏剧的整体的情感组织是很相似的”。〔2〕而谈及小说与音乐之间的关系,高行健则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这样写道:
小说一旦同音乐结合,重新迸发出来的那种表现力与感染力是音诗所难以比拟的,将赋予小说无穷变化的韵味。小说家用以标明各个章节的将不再是没有生命的数目字,而是快板、慢板、行板,如歌如泣或一个明快的主题的变奏,写这种小说的作家将会发掘出艺术语言中的更为微妙的感情色彩。〔3〕
这段话佐证了小说与音乐之间不可割裂的关系。同时,也带来理解上的偏差:有人甚至以为,文学与音乐的结合是现代文学进行形式探索之时的首创。对此,笔者不以为然。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与音乐之间一直处于暧昧不清的胶着之中。战国时期,《尚书·尧典》中便载有“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的理论。从先秦时期的《诗经》 《楚辞》,再到《汉乐府》,及至宋词、元曲,文学有时甚至只是音乐的衍生品,人们无法生硬地将二者进行剥离。由此,小说与音乐之间的关系便无法说成是西方现代小说的首创。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形式多样,备受推崇。他深谙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之道,并于西南联大就读期间,汲取了大量西方文学创作的精华,深受伍尔夫、契诃夫、纪徳等人创作的启发。他敏锐地捕捉到小说与音乐之间的紧密关联,并近乎刻意地加重笔下小说的音乐性体现。他的文字中,不只充溢着戏剧元素、绘画因子,更加富含音乐的情致。他曾在文章中探讨过语言的“声音美”:
说小说的语言是视觉语言,不是说它没有声音。前已说过,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对文字训练有素的人,是会直接从字上“看”出它的声音的。中国语言因为有“调”,即“四声”,所以特别具有音乐性。〔4〕
以上文字可看作是汪曾祺对小说语言的独到见解。在他看来,文字不仅能够表达视觉意义,更应具有听觉传导的使命。因而他特别注重将音乐技巧嵌入到他的小说创作之中,并以隽永的文字中和着二者的差别。“音乐,也许是最接近情感的一种形式。音乐的流动性、抽象性、具体可感性,仿佛就是情感留给‘此岸’世界的一种身影,通过它我们真切把握了情感。”〔5〕“凡音者,由人也生也。人私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必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6〕不论古今中外,音乐都是传递情感的重要媒介。节奏变换、复调以及奏鸣曲式是音乐领域的重要技巧,汪曾祺在参悟了其中精髓的基础上,将它们应用到小说创作之中,提供着有所裨益的创作经验。他在小说与音乐这两种看似不同,实则相通的艺术种类之间实现了融会贯通,供给着一盘盘视觉与听觉并存的饕餮盛宴。
一、节奏的变换
节奏是音乐范畴的基本元素之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被喻为“音乐的骨骼”。爱德华·汉斯立克这样定义节奏:“对称结构的协调性,这是广义的节奏,各个部分按照节拍有规律地变换地运动着,这是狭义的节奏。”〔7〕节奏的规则或不规则的变换带来强烈的乐感效应: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白居易以寥寥数笔道尽和鸣铿锵的节奏带给人的强烈听觉感受,足见音乐的节奏之美带给听者的震撼。作曲家们通过节奏的不断变换,演绎出一首首荡气回肠的美妙乐章。汪曾祺深谙其道,他利用不断变换的节奏为他的文本增添着跌宕起伏的韵律美。本文从“重复”“用韵”以及“流动性的张力”三个方面着手,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节奏之美。
1.重复
重复是作家惯常使用的创作手法之一。赵毅衡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重复是意义世界得以建立的基石,没有重复,人不可能形成对世界的经验。重复是意义的符号存在方式,变异也必须靠重复才能辨认:重复与以它为基础产生的变异,使意义能延续与拓展,成为意义世界的基本构成方式。”〔8〕中国作家对“重复”技巧的运用肇始于古代时期,古典文学中便有大部分文本注重对叠字的运用。追溯至数千年前,《文选》便载有《行行重行行》一诗,叠字“行”的使用加剧了游子离家之远、路远相见之难及思妇相思之苦。乐府民歌《木兰诗》则以“唧唧复唧唧”作为小引,以机杼之声传达木兰的声声叹息,进而展开她替父从军的故事。李清照则在《声声慢》中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为始,抒发着她国破家亡、形单影只的寂寥与落寞。汪曾祺参悟了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之道,他将古典文学的精华完全吸纳,揉进文本的字里行间。
汪曾祺的小说,旨在通过对词语的“叠加”使用,为小说的人物塑造及情节走向服务,增强文本的韵律感。小说《八千岁》中有这样的文字:“……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9〕叠字的简洁强化了宋侉子行事果敢的性格特征,增强了人物塑造的立体感。句子的工整对仗颇似于魏晋南北朝之时盛行的骈文,却祛除了骈文的华而不实,留下了铿锵有力的韵律美。汪曾祺的语言一向以简洁准确著称,言简意赅却恰到好处。“重复”的运用方便了读者对句子的记忆,长句与短句的有机结合也成就了句子的抑扬顿挫,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相较于当代作家莫言、阎连科、余华等人近乎拙劣的叙述语言,汪曾祺的文字不仅带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享受,也提供了令人大快朵颐的听觉盛宴。
他在意识流小说《绿猫》的首段运用了一连串的“为什么”进行反问:
——我为什么那么钝,为什么一无所知,为什么跟一切都隔了一层,为什么不能掰开撕开所有的东西看?为什么我毫无灵感,蠢溷麻木?为什么我不是天才!〔10〕
这是一段典型的内心独白,漫溢着主人公对自我的贬低。抛开字面意思,单就小说的语言而言,一连串的追问令读者毫无喘息的空间,一直随着作者的思绪游走,快节奏的叙述方式增强了文本的动感。通过对一连串“为什么”的使用,汪曾祺不动声色地加深了句子的排比色彩,强化了小说语言的爆发力与冲击力,为主人公自责情绪的发泄提供了渠道与出口。作者对重复的使用增强了语言的气势,通过文字,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捕捉到主人公满腔的愤懑、不平与自责的情绪。
2.用韵
除了对“重复”的巧妙运用外,汪曾祺也侧重“用韵”。他说:“用合乎格律、押韵的、诗的语言来思维(不是想了一个散文的意思再翻译为诗),这是我们应该向民歌手学习的。我们要学习他们,训练自己的语感、韵律感。”〔11〕中国古典诗词讲究语言的韵律美,注意平仄韵律、对仗工整,对韵脚尤为关注。《红楼梦》中便有例证,第三十七回,众人初结海棠诗社,迎春要小丫头随口说出一字,以此限韵,小丫头倚门而立,便说出“门”字,于是众人决意限“门”字韵。又如第七十六回,黛玉与湘云于凹晶馆联诗,数得十三根柱子,便决意限“十三元”的韵,足见“韵”是诗词曲赋的根基。汪曾祺对“韵”的把握增添了他小说语言的和谐之美,为读者的听觉带来新鲜的审美享受,为文本增添了灵动的色彩。
1950年后,汪曾祺便长居北京。他受北京厚重的人文历史影响颇深,创作了大量植根于北京文化的小说、散文,《云致秋行状》是其中的典型。在这篇“京味儿小说”中,他运用地道的老北京语言,字里行间充溢着原汁原味儿的老北京风情。北京话方言特色明显,精髓在于隐藏在其腔调中的韵律感及乐感。汪曾祺笔下的文字同样极具节奏感:
戏班里的事,也挺复·杂,三叔二大爷,师兄,师弟,你厚·啦,我薄·啦,你鼓·啦,我憋·啦,仨一群,俩一伙,你踩和我,我挤兑你,又合·啦,又‘咧’·啦……〔12〕
加着重号的字都限“a”韵。韵脚“a”的文字的连续使用强化了句子的节奏性,读者读来朗朗上口。同时,老北京方言具备亲切随意、俏皮诙谐的属性,汪曾祺对北京方言的合理运用,无形中拉近了读者与主人公之间的距离。透过语言,小说呈现了老北京人慵懒、玩世不恭、油嘴滑舌的性格特点,读者轻易便可捕捉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随意与懒散。
小说《寂寞和温暖》中有这样的文字:
稻子收割了,羊羔子抓了秋膘了,葡萄下了窖了。雪化了,茵陈蒿在乌黑的地里绿了,羊角葱露了嘴了,稻田的冻土翻了,葡萄出了窖了,母羊接了春羔了,育苗了,插秧了。沈沅在这个农科所生活了快一年了。〔13〕
这段文字生动、有趣,汪曾祺将种种意象以“了”字为结尾的句子串联起来。一连串“了”字的运用,看似是作者漫不经心的写就,实则是他的匠心独具——读者读来有诗的节奏、歌的韵味。黑格尔认为,“声音不只是发泄情感的自然呼声,而是情感的艺术表现。情感本身就有一种内容,而单纯的声音却没有内容,所以必须通过艺术的处理,才能表现一种内心生活”。〔14〕音乐的变奏带给读者轻松、欢快的阅读体验,也让读者透过字面感知着主人公沈沅的内心的快意及对生活的满足。汪曾祺结合一系列生机盎然的意象,营造着春天欣欣向荣的情景以及欢快明朗的生活氛围,宣泄着主人公不为人知的喜悦心情,与后文沈沅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境遇形成反差,两相对照,强化着沈沅命运的坎坷与悲剧性。
3.流动性的张力
重复与韵律的使用为文本带来蓬勃生机,除此之外,汪曾祺的小说同样具有“流动性的张力”。即作者在文本中以一系列的动词对主人公的动作进行文字意义上的再现,使得文本在具备画面动感的同时,兼具流水一般的动态张力。徐岱的《小说形态学》一书中便提到了这一小说叙事文体特征:流动性张力。汪曾祺的小说很多情节都拥有流动性的张力,他通过对诸多动词的连续使用,刻画了主人公的活动画面,在文本中形成跳跃的场景,增强了文本的流动感,因而具有“流动性的张力”这一音乐性特征。
小说《陈小手》中有文字为证:“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15〕陈小手医德高尚,以人为本,对酬金的多少毫不在意,直接装进口袋。洗手、喝茶、道扰、上马,一串动作一气呵成,整个活动场景充满极其生动的张力与动态的视觉效应,在冲击着读者的视觉神经的同时,内蕴着主人公性格层面中流水般的从容豁达。汪曾祺以最简洁的动词还原着陈小手救人之后的一系列动作,简洁平实、不加修饰的语言中,掩藏着汪曾祺对陈小手高洁精神的感佩。
《晚饭后的故事》开篇就有这样的文字:
京剧导演郭庆春就着一碟猪耳朵喝了二两酒,咬着一条顶花带刺的黄瓜吃了半斤过了凉水的麻酱面,叼着前门烟,捏了一把芭蕉扇,坐在阳台上的竹躺椅上乘凉。他脱了个光脊梁,露出半身白肉。〔16〕
一系列动作一呵而就,读者可以通过主人公动作的悠闲,感知到他的愉悦自得。动感十足的文字的叠加运用使得整个画面充斥着流动的张力与跳跃的动感。选文中,动词的择取画面感强烈,兼具不可替代性,最平常却委实最贴切。《晚饭后的故事》是典型的意识流小说,汪曾祺避繁就简,漫无目的地讲述着郭庆春意识的游离,一切皆围绕着晚饭后主人公的“闲”展开。他以惯有的细腻为主人公营造了一个马缨花盛放、令人熏熏然的黄昏,主人公的闲情在充满流动性的语言中被一一呈现。汪曾祺以这些动词的连续使用,为文本呈现着跳动的音乐性特征。正如丹纳所说,“一个句子是许多力量汇合起来的一个总体”。〔17〕美感、画面感、乐感,好的文字总是会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心动与享受,汪曾祺的行文特色即在于此。
二、奏鸣曲式的叙事风格
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显而易见的“奏鸣曲式”叙述风格。奏鸣曲式(sonata form),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称为“显示部”,包括主部、连接部、副部和结束部四个部分。第二部分称为“展开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呈示部材料中矛盾冲突的继续发展和更加剧烈的积极展开,使情感变化更为丰富。第三部分称为“再现部”,再现的各个主题之间对比有了新的发展,乐思在经历了剧烈冲突后形成了新的统一关系,两个主题的调性彼此靠拢附合……由此发生材料和结构方面的变化。〔18〕
简言之,即引子、显示部、展开部、再现部以及尾声五个部分。汪曾祺以奏鸣曲式的音乐曲式建构着小说的框架,展开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以小说《小孃孃》为例。小说伊始,汪曾祺凭借对谢家亭台轩榭的介绍,导入故事的主人公。作为故事的小引部分,作者开始了对主人公小孃孃以及谢普天近乎素描式的介绍:漂亮大方的小嬢嬢,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谢普天,二人年龄相仿,看似男才女貌、天作之合。接下来,汪曾祺直截了当地引出了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二人为嫡亲姑侄关系——这也成为故事发展的焦点,是二人交往的最大障碍。
接着,在故事的第二阶段,即显示部部分,二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因家道衰落,谢普天停学回乡,与小嬢嬢同住在“祖堂屋”——这为二人关系的越礼提供了便利。汪曾祺借助日常琐事细述了谢普天对小嬢嬢的关照:小到吃穿用度,大到理发保养,谢普天皆亲力亲为,对小嬢嬢温柔呵护——事实上,他的行为已然违背伦理纲常,破坏了本该遵守的秩序。但在外人看来,二人的关系还未逾越伦理范畴,一切都看似合情合理。
进而,过渡到展开部部分。汪曾祺开始真正讲述这个乱伦故事。主部主题可理解为是传统的伦理纲常,小嬢嬢二人的行为是对道德伦理的大胆挑战,二人的情感发展为副部主题。“雨还在下。一个一个蓝色的闪把屋里照亮,一切都照得很清楚。炸雷不断,好像要把天和地劈碎。”〔19〕汪曾祺有意将雷声引入文本,作为情节发展的助力。雷鸣之下,他们的爱看似坚固,却饱受摧残——雷声指代传统道德、伦理纲常,更意味着主人公心中的道德枷锁。面对伦理道德的拷问与谴责,彻底跨过鸿沟的二人并不勇敢,他们恐惧、不安、焦虑、忐忑、矛盾。汪曾祺直言:“他们很轻松,又很沉重。他们无法摆脱犯罪感。”〔20〕短暂的欢愉无法带给主人公全部的满足,种种复杂的情绪交织、纠缠、充盈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渴望着自我灵魂的救赎及精神枷锁的解脱。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的交织缠绕,写尽了主人公面临的纠结。
之后,小说进入到再现部环节。故事发展到更为紧张的阶段。隔墙有耳,小嬢嬢与谢普天的秘事为外人所知,传闻纷纷。二人决意以“离开”规避各种闲言碎语,此时副部主题较为凸显,他们的逃离带给彼此的仅是片刻欢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极尽疯狂之事。在这一环节,两个主题互为上风,始终没有割裂开来。私奔的二人确实拥有一段“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快乐时光,然而他们始终处于“背离伦理道德”的阴影之下,二人的精神世界依旧被伦理道德的规约所束缚拘囿。小嬢嬢怀孕,本是喜事,却频繁做梦:
谢淑媛老是做恶梦。梦见母亲打她,打她的全身。打她的脸;梦见她生了一个怪胎,样子很可怕;梦见她从玉龙雪山失足掉了下来,一直掉,半天也不到地……每次都是大叫醒来。〔21〕
谢淑媛的噩梦源于对自我选择的惶恐不安与矛盾纠结,恪守伦理秩序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她的灵魂深处,她始终饱受着伦理道德对她的精神折磨。他们二人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整个家族的背叛,对整个亲情圈子的否定。她时常抚摸小腹,将孩子比为“罪孽”。行文至此,故事已经接近尾声。
尾声部分。小嬢嬢没能如愿顺利生产,她死于难产,带着所谓的“罪孽”离开。汪曾祺有意地将她的结局写成悲剧,伦理道德彻底战胜了情感。谢淑媛的死结束了二人的颠沛流离,谢普天将她的骨灰带回家乡,埋在桂花树下。故事以谢普天、陈聋子的飘然远去、不知所终为结局,是谢普天最终参悟了人生的关窍,还是他因谢淑媛的死产生了绝望的情绪,外人不得而知,但汪曾祺如此设置必然有其因果。笔者以为,小说是以伦理道德的完胜为终,再次强化了故事的主部主题。
三、复调技巧的应用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将“复调”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创作特征,由此提出了“复调小说”的概念。作为一种音乐范畴上的应用技巧,复调指代若干(两条及以上) 的独立意义的旋律声部的结合。作为小说技巧,复调小说更多被理解为在一篇小说之中的若干(两个或多个) 主题的统一呈现。复调小说遵循“对位法”,〔22〕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概括了小说对位法的必要条件:“一、各条‘线’的平等性;二、整体的不可分性。”〔23〕汪曾祺巧妙地将“复调”应用到他的小说内部,小说《大淖记事》便是其中一例。
通常,学界将《大淖记事》的主题理解为“人性真醇的体现”以及“纯爱的颂歌”。事实上,除此之外,《大淖记事》依然存在其他线索——女性自主意识的凸显及刘号长等军阀势利的残暴。《大淖记事》以作者对“大淖”的近乎诗意的书写作为开端,引出大淖地区的风土民情——淳朴的民风成就了善良、和美、勤劳的大淖乡民,以及主题之一的“女性的自我与独立意识的显现”——大淖的女性独立、自主、勤劳,她们“像男人一样的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24〕较之于男性,汪曾祺笔下的女性多了份果敢、坚毅,甚至支撑了整个家庭的重担,男性反而成为她们的附庸与陪衬,她们的“野性”成为“自主意识显现”的有力凭证。之后,汪曾祺正式步入“主题叙事”。
主人公巧云的出场牵引出她的不凡身世——母亲在她幼年之时,因为真爱私奔(也可视为女性自主意识凸显的有力凭证)。此为线索一。接着,汪曾祺娓娓地讲述了两个纯真青年的唯美爱情,十一子英雄救美,解救巧云于危难,情窦初开的两个人面对爱情手足无措,四目相对之间,一首关于爱情的颂歌已然开始奏响,汪曾祺所要展示的第二层线索也已完备。然而,汪曾祺却笔锋一转,为两人的爱情设置险阻——刘号长乘人之危,将巧云玷污——这是故事的转折点,也是故事的线索三,即刘号长等人的凶悍蛮横的显现。巧云爹的叹气、姑娘、媳妇的议论皆为刘号长的流氓行径提供佐证。而后,刘号长得知一切,聚集手下的“流氓”,“一人一根棍子,搂头盖脸地打他(十一子)”、〔25〕“七八根棍子风一样、雨一样打在小锡匠的身上”〔26〕——汪曾祺以最直接的语言讲述着刘号长等人的淫威高压。十一子面对刘号长等人的恐吓凶残不为所动,“不说话”、“牙咬得紧紧的”,他对爱执着而坚定,因而被打得遍体鳞伤、命悬一线。巧云听信土方,拿尿碱救治十一子,患难与共,不惜亲尝尿碱——作者以最朴素的语言、最质朴的行为颂赞着纯爱的唯美。大淖乡民不屈从于刘号长等人的血腥暴力,为受伤的十一子送去关心与问候——这是故事的又一重线索——人性真醇的体现。故事以“大团圆”式的结局为终:刘号长被调、十一子渐愈、巧云独立支撑起家庭。如此看来,多条线索在小说中并行不悖,互相掺杂却彼此独立,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说结构。很难说只有哪一项是小说的最主要线索,各种线索交织缠绕,共同发声,多种线索并存、诸多声音兼备,使得整个小说更为完满。借助这一音乐技巧,汪曾祺以惯常运用的结局模式完结了整个故事,刻画着有血有肉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物形象,建构了他意念中真爱不灭的理想乌托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靓丽风景。
小说《鉴赏家》为“复调”技巧的运用又添佐证。小说中多重线索并存:A.季匋民与叶三之间的知己之交;B.叶三为人的正直、对生活本真的体悟、对审美情趣的把握以及对艺术的热忱;C.季匋民识人知人、为人清高。汪曾祺歌咏着二人高尚的情怀,赞叹着二人品行的高超与友谊的弥足珍贵。
小说开篇,汪曾祺便直截了当地引出故事的两位主人公:画家季匋民与鉴赏家叶三。鉴赏家是汪曾祺赋予叶三的“美称”,叶三事实上并无“学院派”意义上的“鉴赏”资格。他出身寒微,靠卖水果维持生计。然而,他的生活却别致而精彩:守着四时送果子、果子个个是好的,他深谙经商之道,对儿子的抚养丝毫不马虎,儿子的孝顺侧面反映了叶三品格的高尚。儿子们劝说叶三放弃卖果子,叶三的反应异常激烈,甚至生气,情急之下表明了送果子的初衷——为给季匋民送果子,并说:“你们也不用给我做什么寿。你们要是有孝心,把四太爷(季匋民) 送我的画拿出去裱了,再给我打一口寿材”。〔27〕为了季匋民的画,叶三甘心放弃安逸的生活——事实上,叶三的儿子们家境殷实,他的养老问题不足为虑,但正是对艺术的执着热爱、对生活本真的孜孜以求,叶三始终坚持自我。进而,汪曾祺便平铺直叙,导入季匋民,讲述二人之间的交往。叶三真心赞赏季匋民的画,并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的不足与缺憾,发自于肺腑本心,绝非阿谀谄媚;季匋民对叶三的品评颇以为意,不以“大画家”身份自居,对“假名士们”的高谈阔论深恶痛绝——二人颇有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之感。叶三并不负季匋民所望,他对季匋民所赠之画也是珍之惜之,视若瑰宝。二人的友谊弥足珍贵,并未随着死亡的降临而结束,四季八节,叶三依旧到季匋民坟上供奉鲜果。季匋民的遗作价钱上涨,叶三不为所动,不卖藏画——这就包含双重旨意:其一:叶三对艺术的珍视;其二:他对友谊的看重。三重线索你中有我,我中带你,很难将三者进行区分剥离,也正因如此,构成了复调小说的审美准则。“复调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把额外的意义留给读者。读者需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话中之话,还需要调动自己的想象力。”〔28〕多重线索的共同发声为文本提供了丰富内蕴,复调小说的魅力得以显现。
严格说起来,这也可以诉诸“听觉叙事学”范畴,即听觉想象力(auditory imagination):“所谓的听觉想象力是对音乐和节奏的感觉。这种感觉深入到有意识的思想感情之下,使每一个词语充满活力:深入最原始、最彻底遗忘的底层,回归到源头,取回一些东西,追求起点和终点。”〔29〕最终“唤起与原始感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想象与感动”。〔30〕文学叙事都是一种“讲故事”的行为,这里的“讲”就是“说”,即故事要被“说”出。而“听”是“说”的对立面,有“说”就要有“听”,因而不能忽略“听觉叙事”的存在。汪曾祺的语言除了带给读者“赏心悦目”的视觉感受之外,同样具有其“听觉意义上的魅力”。
同样是叙事,老舍笔下的文字自带“京味儿”的光环,阅读老舍,仿佛置身于老北京的市井街头,感受到、触及到以及“听到”的是气息浓郁的老北京“市井气”,自有其“油滑”的特质;鲁迅的文字则略显庄重,具有“令人沉思”的特性,阅读鲁迅,是在沉痛之中思索人生及国民性优劣,冲击读者耳膜的则是沉痛、苍凉以及悲哀等种种复杂;路遥的文字听起来却似踩在结实的黄土地上,因命运的厚重感、生存的困境是路遥文字的着力点;张爱玲的文字则别具“海上风情”,为读者呈现的是迷离、有万般风情的旧上海,读者“听到”的是时间的沧桑与回忆的隽永。而汪曾祺则不然,“他的文字,整体上显得热情,饱满,像青翠欲滴的绿叶,像汁液饱满的果实,有春水般的柔滑而纯净的细腻感”。〔31〕汪曾祺的文字有着“水一样流动的特性”,具备“水”一样的音乐性与日常生活性,他的语言“听起来”生活气息浓郁,似是与读者在闲话家常,畅谈人生经历,于无意间拉近了读者与作家之间的心理距离。朴实之中透着亲切随和,同时兼具音乐的节奏感,这便是汪曾祺的语言特色。“音乐话语的在场,或使小说的叙事结构本身充满强烈的‘音乐性’,或成为指涉小说人物性别身份、阶级身份、或深层性格的‘主题动机’‘固定乐思’,对小说文本的建构、生成、阐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从纯粹的‘文学性’阅读走向‘音乐性阅读’,便能从另一个维度解读这些文本,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32〕汪曾祺通过变换的节奏、奏鸣曲式的叙事风格以及复调技巧的应用,在小说与音乐之间实现了“会通”。正因如此,他的语言更加精妙、铿锵有力、乐感十足。对小说叙事的音乐性的充分把握,也为更深层次地理解汪曾祺的语言提供了一个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