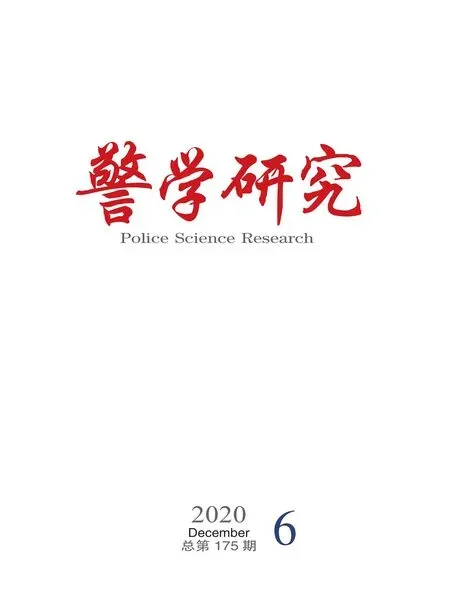论刑案材料缺失与证据筛选之关系
(四川警察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案件材料的缺失,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并不少见。在侦查活动中,案件材料的缺失往往是一种常态,必须在组织证据体系的过程中查漏补缺。而在审判活动中,大多数情况下,已经错过了查证补证的良机,案件材料的缺失就会形成一些疑难、疑罪的案件。而这些证据材料的缺失,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问题。其主观方面的人为因素,又常与证据材料的筛选存在着关联性。下面,我们就来共同面对它们。
一、筛选证据材料的必要性和缺失材料的风险性
在刑事诉讼中,即使案件材料很多,也不可能一股脑地全抛在法庭上。在法庭上,控辩双方是要展开质证和辩论的。谁胜谁负,就看出示证据材料的证明力。而要有强大的证明力,就需要筛选案件材料,组织具有逻辑力量的证据事实。但是,筛选证据材料,不是在提起公诉时才开始的工作,而是从侦查之初就开始了的。在侦查之中,案件材料不可能一开始就有很多。正好相反,侦查之初的材料是比较缺少的。在侦查过程中,也不太可能一下子就找到真正证明力强的证据,而需在许多环境材料和大量无关材料中筛选。这就需按照法律规范的案件构成要素,一边筛选案件材料,一边组织证据体系。
在侦查活动中,案件材料是一个逐渐充实的查证过程。许多时候,案件材料的缺失是一种常态,尤其在侦查初期,材料缺失更是一种常态化状况。案侦之初,确切的案件材料往往很少,追踪犯罪嫌疑人的方向,也常常不甚明确。侦查人员要在相当有限的材料中寻求案件事实,就不得不借助侦查假说,利用逻辑的力量去探寻与案件相关的事实。这就需要运用现有的少量证据材料形成一系列假设,去进行逻辑推演,从中选择与案件相关的证据,逐渐确定侦查方向。在这种选择中,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而实际的案侦情况,常常是对中有错,或是错中含对,情况错综复杂。这就需要侦查员小心地进行试错,在查证侦查假设的每一条案件线索中,理出一些案件事实的头绪。这样才能积极地去发现案件事实,谨慎地选择能反映案件事实的材料,并确定其证明方向。在查证事实中,坐实案件证据。在这些逐步接近案件事实的过程中,面对材料缺失点,侦查假说大胆地假设事实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些假设的风险,就在对有限材料的方向选择存在“局限性”。它们或局限于现有案件条件,或局限于所获材料的可能假象,或局限于现有材料的片面性,或局限于侦查人员的素质缺陷,等等。
在利用有限材料构建侦查方向的过程中,就可能隐藏着各种主客观方面的错误。尤其在筛选案件材料的过程中,人为造成一些案件材料的缺失,其风险就在侦查员的主观判断中。这些判断中的经验定式,形成了对案侦方向的一种选择。许多情况下,在大体正确的定式选择中,也包含了某些失误,甚至还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带有定式方向的判断,很可能就将一些重要的关键证据排除掉,而形成证据材料的人为缺失。因而,对案件材料的缺失风险不能小觑。侦查人员应该结合自己的案侦实际,对之进行深入的反思、考察和研究。
二、缺失材料的现实性与筛选证据的紧迫性
在刑事侦查中,案件材料缺乏是侦查员难以绕过的现实问题。这就急需要从实际出发查找和筛选案件材料。但用什么样的方法筛选,每个案件的条件不同,侦查员的素养不同,其筛选方法也就很不一样。
(一)缺失案件材料的现实性
侦查取证是公正司法的基础。但在侦查初期,面对案件材料缺失的常态,取证的现实风险性是非常高的。这时的案件材料,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差。常有与案件无关的信息掺杂其中,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信息。如果侦查员不能勤于收集事实和查证材料,而总是用眼前的表象去推测案情,总是用设想去弥补缺失材料的空缺,就存在侦查方向偏离案件事实的现实危险。人都会贪图省力便捷,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案侦人员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这种现状、提醒自己警惕出错,不把握好“省力便捷”的度,而总是偷懒怠惰,单凭想象去推测案情,以此来弥补缺失材料的位置,就可能误入侦查歧途。同样的道理,如果公诉审查人员对案情大而化之,审查证据不够严谨,就可能漏过材料不实、证据缺失、证据矛盾等较为隐形的情况。如果法庭质证和辩论走过场,法官不研究控辩双方的质证要点和论辩的关键处,也就难以排除“不合常理”的证据缺失,甚至还可能对缺失的证据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就难以依法使用相关缺失证据去排除合理怀疑,得出能够经受住历史检验的公正裁判。冤假错案,就可能顺利通过侦、诉、判的一个个关口,而成为让人难以回避的现实。而现实,就会成为最为严正的法官,把这些证据材料缺失造成的各种差错,无一例外地记入历史的案卷。
(二)筛选证据的紧迫性
在收集证据中,侦查员最紧迫的任务是筛选,需要不断地在案件材料中筛选。筛选证据材料,要在尽可能全面收集案件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1]
筛选方法有二:第一是在全面收集材料基础上,相互比较着进行筛选,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多是在侦查后期或侦查终结之时才有可能。第二是边收集,边筛选。这是破案紧迫性中的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又有两种情况:一是遵从客观逻辑方向的筛选。案件事实存在的自我规定性及其发展规律性,就是一种客观逻辑。[2]遵从客观逻辑,就是尊重事实,不带偏见,公正选择。二是侦查员已有一定的案侦经验,形成了一定的经验定式。依据这种定式,有可能迅速地找准证据,快速破案。但也可能让侦查员过于自信、自负、刚愎自用,而铸就错案。因此,经验定式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风险性。
侦查取证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要提高取证效率,就需发挥案侦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从杂乱无章的材料中,筛选法律要件中不可或缺又证明力强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受客观条件限制,一时无法找到时,只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收集较易先获得的。这就会形成一些证据的空缺。而缺位的证据,又会给案情带来不确定性。实际上,有些证据初看并非重要,但随着深入取证,关联材料增多后,便逐渐表现出了重要性。有时,又同时存在着收集若干证据的可能性,但侦查员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基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又不能同步收集,必须有所选择地分步收集,而且是边筛选,边收集。在筛选证据之中,侦查员认识能力和业务能力的有限性,又不太可能一下子就找到最佳证据,而需不断地在案件材料的选择中试错、纠错、查证和求证。这些都是一些行为筛选,是在案侦实践中的行为筛选。“行”要早于“知”,侦查要先做起来,才知道其对错。因而筛选行为最具有紧迫性。唯其如此,才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在此过程中,在同等条件下,侦查员会优选重要证据收集,或量力而行,先易后难地收集易得证据。当然,对一些重特大案件,他们又会做出巨大努力去获取关键证据。这些证据收集,要讲究效率,都不得不常与证据筛选同步进行。因而,筛选证据是收集证据中经常遇到的紧迫问题。
三、筛选刑案材料的证据标准
侦查的取证和用证,都有其证据标准。其实,这些证据标准,贯穿了侦、诉、判的整个司法过程。在收集和筛选证据材料中,侦查员都应该始终坚持这些标准,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差错。
(一)犯罪证据的法律标准
证据筛选要符合有限的侦查资源状况,最大化地发挥取证效力,就不能没有切实可行的法律证据标准。
1.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标准。刑事案件都有其法律构成要件。这种要件,是法律规定,不是具体事实。我国《刑法》规定了400多种犯罪。从构成要件上看,每种犯罪都有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四个法律要件。
犯罪主体,指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有的犯罪是一个人实施的,犯罪主体就是一个人。有的犯罪是数人实施的,犯罪主体就是数个人。而数人犯罪中,有些是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团伙犯罪等。公司、企业、机关、团体等实施的犯罪,构成单位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又有主犯、从犯,等等。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不同,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直接针对的目标,有具体的被害人。犯罪客体,指刑法保护的公民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社会关系。犯罪主观方面,指主体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心态。它们是故意,或是过失。犯罪客观方面,指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如作案时间、地点,犯罪行为方式、行为结果,等等。每个刑事犯罪,都需有满足以上四个构成要件的相关证据。其待证事实的证据材料都不缺位,才可以定罪量刑。
2.我国刑诉法关于定罪的证据标准。对于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我国《刑诉法》第200条给出的定罪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3]第55条,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这两条是一种客观标准。而“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4]则是主观标准。也就是说,刑诉法对证据的主客观标准,都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要求。这些关于证据的法律标准,也都是一种经验标准。
以上是建立在长期司法经验上的法律标准。法律是从司法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具有相当的概括性。法律概括性的优势是有较广泛的适应性,其短板是操作性不强。因而,需要充分调动案侦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去广泛地收集案件的证据材料,需要充分调动他们去慎重地筛选出“确实、充分”的案件事实,更需要充分调动他们谨慎地审查判断证据的关联性。但是,在这一系列案侦、司法工作中,侦办司法人员个人的知识结构、业务能力各不相同,对同一案件和同一些事实材料,他们的证据结论就有可能大相径庭,因此需要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能制约证据证明力的标准,来使人们的主观认识能够更加接近和统一。证据体系的逻辑标准,就是这种统一人们认识的主客观标准。
(二)犯罪证据体系的逻辑标准
证据的逻辑标准,主要是针对建立证据体系而提出的标准。无论是单一型证据体系,还是混合型证据体系,都应有确实性、完整性、一致性、唯一性四个规则。[5]其具体内容和彼此相关性如下:
1.证据体系的“确实性”,指证据材料不是逻辑推理,而是实物。它们是推理的基础物。它主要解决每个案件材料的客观真实性问题,即材料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客观的案件事实。证据事实是一种客观真实的存在,而不是一种推测、想象,更不是杜撰。在逻辑值上,证据只能为“真”,不能为“假”。在组证实践中,怎样来确定证据为“真”呢?证据本身,不能自己证明自己。这就要根据经验规则,使每一事实的证据不是孤证。而且,其微结构具有相当的质量。无论是由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共同组成的“V”字型微结构,还是单独由间接证据组成的“梅花状”微结构,[6]其证据都能够相互印证,这才具有确实性。
2.证据体系的“完整性”,指在办案件的待证法律构成要件一个都不缺少,在逻辑上符合完全归纳法。经验性司法证明,是一种归纳推理。案侦中的推理,时常是一种不完全归纳推理。侦查员很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因此,组织证据体系特别要强调完整性。构成犯罪的案件,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就指待证事实的完整性。而且,这些定案证据都需“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法定程序也是一种司法历史经验沉淀下来的取证与用证规范。一般说来,遵守了法定程序,材料查证属实了,证据的可信度也就提高了。这就又回到了确实性标准。因而,真实性是案件单个证据的质量标准,完整性是案件证据体系的数量标准。两个标准结合起来,达到数量与质量的统一,才有起码的确实性和充分性。“起码的”是一种底线标准。案件的证据体系要没有问题,还需要“一致性”和“唯一性”两个标准。
3.证据体系的“一致性”,指单个证据本身无矛盾、总体证据之间无矛盾、证据与证明对象无矛盾、证据与案件事实无矛盾,逻辑上符合不矛盾律。“证据本身无矛盾”,是单个材料的证据资格。如文物赝品,就可能露出其作伪的矛盾。但一些仿古文物,也能以假乱真。因此,有矛盾的材料本身就有问题,但表面没矛盾的材料,也不能担保其就是真的。“总体证据之间无矛盾”,是体系中的证据集合体从不同角度反映同一事实有一致性。比如作案时间,嫌疑人口供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鉴定和尸体检验等都没有矛盾。但这又同人的记忆、诚实度、鉴定水平和案侦人员取证是否得当、记录是否真实等有关系。因此,材料之间有矛盾,证据肯定有问题,但也不能说材料之间相互一致了,证据就没有问题。一些冤假错案的证据材料,从表面上看也是一致的,很难找出矛盾,但这是在筛选证据时,有人刻意去掉了那些有矛盾的材料。“证据与证明对象无矛盾”,是控罪证据的指向与其罪名是一致的,没有张冠李戴、文不对题的情况。这是个定罪量刑的恰当性和准确度问题。
以上三个“无矛盾”,都具有主观反映客观的准确度问题。而“证据与案件事实无矛盾”,则是主观服从客观,应排除合理怀疑。比如佘祥林杀妻案,十多年后,佘妻张在玉活着回来了。这一案件事实的存在,就足以推翻在案的所有材料。其实,案发之初,张家人在辨认该镇吕冲村一水塘的女尸时,就存在没有排除女尸可能不是张在玉的合理怀疑。[7]女尸的年龄、体征、死亡日期虽与张在玉吻合,但辨认不像DNA鉴定,并没有唯一性。在聂树斌案中,案件发生时,聂在上班的事实,就足以推翻聂是凶犯。因此,曾经在案,后来又缺失了的聂的考勤表和工友的证言,才至关重要。这种证据缺失的“不合常理”,就在案侦人员存在为掩盖其失误而抽取证据的合理怀疑。[8]这里抽取的,是在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在案证据之间,虽然看不出矛盾了,但是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材料表面的一致,有时还是一种现象,并不能说明案件侦办是正确的。证据筛选有主观性,证据的一致性,要服从于客观事实。证据本身、证据之间、证据与证明对象,都要围绕案件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去构建。筛选证据时,主观遵从客观,证据的一致性才是可信的。
4.证据体系的“唯一性”,指综合全案证据,其结论只有一种可能,没有第二种可能,逻辑上排除了合理怀疑,符合排中律。案件的客观事实只有一个,就是存在多人作案,其真相也只有一个。如有人驾车撞人后逃逸,后面的车辆又碾压了被撞人。通过现场勘验、尸检、目击证人、交通视频监控、嫌疑人口供等证据材料,也可还原案件事实真相,得出谁是主犯、谁是次犯,如何分担刑事责任的认定结论,而不应该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
以上四个逻辑规则:逻辑值“真”、完全归纳、不矛盾律、排中律,都是人认识事物,反映其客观现象的主观逻辑。单独而言,它们都有一定的片面性。而要深入案件事实的本质,还得有辨证思维的引导,辅以这四个形式逻辑规则,才能避免认识局限性。在案侦实践中,就是要以犯罪事实的“确实性”为共同基础,以其“完整性、一致性、唯一性”为共同条件,才能在反映案件的客观逻辑中,使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制约证据体系的形成,从而接近客观案件事实的逻辑方向。
(三)证据标准尺度的经验性误差
证据毕竟是主观反映客观的一种认识,其度量尺度与客观案件事实之间,始终存在着天然的误差。无论是侦办中的筛选证据、司法审查中的排除或认定证据,还是判决中的判断和使用证据,它们用以证明的法律事实,都与客观的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区别,并不能完全等同。司法认同它们,则是基于经验规则,将其误差忽略不计。比如,取证的刑事辨认规则①刑事辨认规则:刑事辨认是为了查明案情,让被害人、证人以及犯罪嫌疑人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文件、尸体、场所或人进行识别的侦查行为。在侦查过程中,辨认需由不少于2个侦查人员主持。刑事辨认规则,可分为混杂辨认规则、单独辨认规则、见证人规则、不得暗示规则、保密规则等。每种辨认,都需进行笔录,由侦查人员、辨认人、见证人签名。必要时,应对辨认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如混杂辨认规则有:犯罪嫌疑人不少于7人;嫌疑人照片不少于10张;物品不少于5件。而场所、尸体等特定辨认对象,辨认人能够准确描述物品独有特征的,陪衬物不受数量限制,等等。,就是一种经验规则。其辨认的准确度,与环境条件和辨认者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即使证据辨认符合规则,也会有误差,有时还是很大的误差,甚至可能是根本错误。比如,佘祥林案中对水塘女尸的辨认,就是致使案件错误的根本性差错。但人们的常识认为,这种误差多数情况是符合情理的,也就对之具有相当的容忍度。这与在筛选证据、审查证据、裁判用证中的故意歪曲事实、掩盖真相、制造冤案,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尤其那些为掩盖失误,故意伪证的行为,更不是合乎情理的误差,而是必须惩戒的行为。因此,在案侦司法过程中,就有必要分辨哪些是正常合理的证据误差,哪些是筛选证据中非正常的不合理造假;哪些证据缺失,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确实收集不到相关材料;哪些是曾经将材料收集在案,后来又在筛选证据中不恰当地排除了它们,而使证据缺失,等等。从而才能保护案侦司法人员收集和筛选证据的积极性;同时,打击那些为一己私利而造假、作伪的非法行为。
四、刑案材料的筛选与侦办方向的确定
案侦必须从证据筛选中来确定侦查方向。但材料筛选并非总是正确的,其中隐藏着种种危机和风险,它们会导致侦查方向的偏差和失误。案侦司法人员务必随时自省,高度警惕自己可能的错误。
(一)案件材料的判断,关系案侦方向的选择
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需要具有证明方向的指向性。这种指向性,既有客观的逻辑基础,又有主观的思辨方向,需要具备事实材料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案件事实的发生越是久远,它们与环境事实就越是无序地混杂在一起,其关联也就往往具有间接性、潜在性。这就使证据的关联性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有的表面上关联,实际上却可能并不关联。而明显关联的,又可能是一些表面的偶然关联性。那些实质的关联,往往又深藏于事物内部,需要案侦执法人员耐心细致地探寻。而一些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的材料,除非撞大运,还可能是案犯在反侦查中设置的陷阱,它们会误导侦查方向。在探寻案件证据过程中,侦查活动常常会面对一些庞杂混乱的案件材料。这些材料,有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其推理的方向也就各不相同,有的可能还完全相反。这就使侦查过程像探险一般,充满了走弯路、办错案的试错风险。
(二)筛选材料中的选择性危机
无论案件材料或多或少,面对案件材料,侦查员要不要对之进行判断与取舍?理论上,都应该进行判断,并在侦办中一一查证后取舍。但如判断方向不清,或判断错误,其查证必然像无头苍蝇一般乱碰,耗时费力,漏洞百出。而实践中,侦查员总会遵从省力原则,先行在判断中进行优选,在优选中进行筛查。对查证方向的选择,也是对证据线索的一种判断。随着对证据线索的查证,就可能在采信一些材料的同时,排除一些材料,这就是边筛选,边查证。在筛查过程中,有些侦查员单凭经验办事,就会先入为主,有罪推定,按照自己的设想取舍材料。这就难免主观臆断,有陷入侦查歧途之危机。因而,我国刑诉法要求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既要收集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同时也要注意收集对其有利的证据。[9]但这也会给案侦阶段造成无法认定嫌疑人、无法结案、无法完成任务等麻烦。消极应付差事的侦查员,就会对一些不利于认定的证据视而不见,甚至故意隐瞒一些先前收集到的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这在有些案卷材料中,就表现为有利于嫌疑人证据的缺失。这些证据缺失,又总是被后续的司法办案人员有意无意地忽视。在这种忽视中,便凸显出案侦方向有误的危机。
(三)控辩双方证据选择中的缺失风险
案件材料作为主观对客观的反映,需要案侦司法人员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在侦查阶段,在其后的各个诉讼阶段,都有发现真相的机遇,也充满了出错的风险。这种机遇和风险并存的选择,就是证据危机。在各个取证危险中,存在着查明案件事实的机遇。随着排除证据、认定证据与组织证据的证明活动,这种危机贯穿了整个司法过程。在强调程序正义的大环境下,为了规避冤错案件的发生,在公诉审查阶段,除了注意案件事实的真实性,还会特别审查案件材料的合法性。一些哪怕事实上出入不大,但取证明显违法或合法性存疑的材料,会被排除在诉讼之外,而去选择胜诉性较高的控罪材料。这种排除,也可能使一些证据缺失。即使公诉方不主动排除瑕疵证据,到了庭审阶段,在举证、质证和辩论过程中,辩方律师也会将它们提出来,要求法庭予以排除。这种控辩中的排除,往往造成关键定罪证据的缺失。这种时候,法官会权衡双方的庭辩材料,排除那些法律依据不足的、事实存疑的、程序违法的等问题性材料,而选取那些比较确凿和规范的材料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和依法判决的根据。这种实质性审查如果到位,就会降低缺失材料的风险,对侦查取证形成具有倒逼功效的强制性制约。有了这种司法大环境,才可能形成转危为机的侦查取证大生态。
五、刑案材料缺失的现实状况
既然刑案证据材料的缺失是常见现象,那么,它们在司法实践中是怎样存在的?这就需要我们正视其现状,分析疑难、冤错刑案的成因,探索防止它们发生的方法。
(一)刑案证据材料缺失的一些类型
法律待证事实构成要件缺失。犯罪待证事实的四个法律构成要件,在案件事实中一般不会缺失。这种事实缺失,造成证据缺失,难于组成证据体系。因此,有案侦经验的侦查人员,一般都会尽力收集它们,使之具有“完整性”。但侦查实践中,又总还是有缺失的情况。这些缺失的证据材料,通常有这几种情况:
1.经过案侦努力,侦查员没有找到这些证据。这种情况在许多案件中都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因为人的主观努力,总要受到取证条件的客观限制。这些客观条件,总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不可能只要努力了就都有尽善尽美的结果。
2.侦查员疏忽大意,遗漏了这些证据。这种情况,考验着侦查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和职业耐心。只有最具爱岗敬业精神的侦查员,才有可能完全避免这种疏忽大意。而一般人,多多少少,总难完全避免。
3.侦查员业务素质低,与证据失之交臂了。这种情况在案侦之中也不同程度地、非常普遍地存在着。因为侦查素质无止境,侦查素质的提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侦查员的业务素质中,总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与证据失之交臂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因此,需要侦查员不断地提高业务素质,包括那些经验老道的侦查员。他们要注意排除思维定式的干扰,防止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4.侦查员找到证据后,由于判断有误,又排除了它们。这种情况,也属于业务素质不够高的情况。侦查素质不够,侦查判断才会有失误。这种失误,谁都会犯。当然,如果后来发现了这种失误,也有可能被纠正过来,证据也就可能被再重新找回来。但是,如其不仅是业务素质低下,而且人品有问题,顾及个人得失,也就可能将错就错,并不会再找回证据了。
5.证据材料曾经收集在案,但侦查员为了掩盖侦查失误,也排除了它们,甚至销毁了它们,等等。毁掉证据,使之缺失,这是十分恶劣的,是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必须严格侦办案件的规章制度,将之防止在萌芽状态。最后的惩戒,则是亡羊补牢于万一。
以上诸多原因造成的法律构成要件的证据缺失,都会违反证据体系的证据完整性要求。待证事实的证据缺失,就会直接地形成疑难、疑罪的案件。
(二)刑案相关证据事实缺失
刑案相关证据事实的缺失是最常见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事实,一般是案情和案侦的诸多细节,每案各有各的不同。关联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相关证据客观上是大量存在的,尤其是以痕迹、物证等间接证据形式广泛存在。关键是它们能否为人所识别和收集,收集后能否正确地判断、筛选和运用。而且,相关证据不一定都是待证的要件事实,而多是一些与之关联的间接事实。证据体系的组织,不仅需要法律构成要件完整,而且每一案件事实,还需要有一定的相关证据数量,不能是孤证。孤证不能自证,难以确证刑案事实,也难以明确证明方向。因此,需要组织“V”型的或“梅花状”的证据微结构,使之共同指向某一案件事实。这些能够相互印证,共同证明某一案件事实的相关材料,就是一些相关证据。相关证据时常不止一个,可能是许多个。在这“许多个”之中,就存在需要优选的必要性。如果其中还有相互矛盾的材料,就不仅需要判断,更需要排查。在查证之中,排除虚假的,认定真实的。比如作案时间,它就不可能在案件发生之后。如果案件发生之时,嫌疑人有不在作案现场的相关证据,他就不太可能是真正的作案人。如在聂树斌案中①1994年8月10日上午,康孟东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女康菊花失踪。侦查认定,聂树斌是犯罪嫌疑人。1994年10月1日,聂被刑事拘留。1995年,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17时许,骑自行车尾随下班女工康菊花,至石郊孔寨村的石粉路中段,聂故意用自行车将骑车前行的康别倒,拖至路东玉米地内,用拳猛击她的头、面部,致康昏迷后,将其强奸。尔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猛勒康的颈部,致其窒息死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聂树斌死刑,以强奸妇女罪判处聂树斌死刑,决定执行死刑。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开启了中国异地复审的先河。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2017年3月30日,聂家属获268万余元国家赔偿。参见:360百科《聂树斌案》https://baike.so.com/doc/5403805-5641501.htmlhttps://baike.so.com/doc/5403805-5641501.html。,确定案件发生时间的证据事实有:被害人下班的时间、死者尸体检验推算的死亡时间等。而确定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的证据有:聂上班的原始书证考勤表、与聂同班的工人师傅们的证言等。不难通过这些相关的证据事实,确定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但是,这些关键的原在案的相关证据材料,后来却莫名其妙、不合常理地缺失了。
在证据体系中,能组成“梅花状”微结构的相关证据数量一般较多,其缺失也就往往很难直接从案卷中看出来。例如在“于英生杀妻案”中,于家梳妆台抽屉边缘的2枚外来的陌生指纹,警方却没随案移交。其缺失,只有案侦人员知晓。他们为什么要排除这一相关证据呢?因为它与侦查员认定的“于英生杀妻”相矛盾。虽然警方在于妻内裤残留物中检出了精子,其DNA比对分析表明它不是于英生的。这一关键的犯罪证据,本来可以指向真凶,也可以排除于英生作案。但它却被警方和法庭不恰当地排除了。其理由是:于英生捡拾他人丢弃的避孕套的精子来伪装了犯罪现场。直到于英生被判无罪后,警方才又通过精子鉴定锁定真凶破案。大家这才清楚,侦查员和法官都是用臆测来认定于英生作案。与之相似的,还有杭州“二张叔侄强奸致死”案。经过法庭质证和辩论后,法官排除了被害人8个手指缝中同一男人的DNA谱带的鉴定,却认定了属于二张的手机这一相关证据。[10]其结果,也漏掉了真凶,冤枉了二张。无数冤假错案说明,就是收集到了真实的客观证据,如其筛选不当,也会被人为地排除掉。这类证据缺失,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从业务到人品,它们直接地考验着案侦司法人员的各种基本素质。
(三)缺失案件材料的典型案件
案件材料缺失,更典型的是聂树斌案。众所周知,聂案的复查,源于王书金案中王供出了石家庄市液压件厂附近玉米地里的奸杀案。此案在聂案中被认定为聂树斌所为,聂因此被冤处死刑。石家庄案中的“一案两凶”,让媒体倍加关注,长期追踪报道。在王案的庭审中,王书金和其辩护律师称,石家庄案的犯罪行为是其所做,而公诉方称王并没有实施这桩犯罪行为。辩护人要求查阅公诉出示的证据,要求休庭做辩护准备。合议庭认为,这一要求符合法律规定,同意其请求,而休庭。[11]这是中国诉讼史上罕见的一幕,反映出过去的侦、诉、审间缺乏实质性的制约机制。现在,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在聂案的复查中,律师称:7年间,河北高院主要领导多次调动,他们向该院提出查阅卷宗,坚持了54次。每次遭拒的理由,都是“等等领导意见”或“还没有最终意见”。直到最高法指令山东高院复查后,2015年,律师才被允许阅卷。在复查听证会上,他们同原办案单位代表分别发表意见。律师们提出,原审卷宗中,缺失与定案有关的重要证据。它们是聂被抓获之后前5天的讯问笔录、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的询问笔录、可证明聂有无作案时间的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这些证据材料,对聂树斌有利。他们强烈要求,法庭给出明确说法。再审合议庭通过分析在卷材料,全面调查研究后,确认这些证据曾经收集在案。但对证据缺失,原办案人员没有做出合理解释。缺失证据导致原在卷聂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与在卷其他证据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最后,法官给出了对聂有利的裁判意见,形成聂树斌无罪的判决。
证据缺失的现象,不独聂案。在一些案件中,至今仍然存在。在许多疑难案件中,有些相关证据事实的缺失,虽然可能存在种种解释,而不影响犯罪构成,但是它们的曾经在案,也会像聂案一样造成不合常理现象。遇此情形,如何采信证据、认定事实,存在不同看法。聂案再审的裁判,对证据缺失的裁判规则予以了明确。在答记者问中,最高法负责人强调,在原审有关重要证据缺失的情况下,他们充分运用了“常理”这个重要的裁判理念。而在评判原办案人员的行为和事后的解释时,再审判决多次使用了“不合常理”的表述。它们都是尊重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意见的体现,也是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解决此类疑难,促进公检法规范侦办行为的要求,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12]聂案再审的判决昭示:收集证据要符合法律程序,组织证据要符合逻辑规则,认定案件事实要符合常情常理。“常情常理”,也是一种经验规则。对证据缺失情况,侦查员必须出庭做出合理解释。不合常理,就可能形成案件疑点,或让人做出对嫌疑人有利的推论。在这样的情势下,在侦、诉、判的各个环节,案侦司法人员都应该正视证据缺失现象。
六、对人为缺失刑案证据的制约方法
刑事案件材料的缺失,有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有些客观原因是正常的,有些则是不正常的人为原因。应该改善司法制度,有效地制约那些不正常的人为因素,才能改变不合情理的材料缺失现状。
(一)刑案证据材料缺失的人为原因
案件毕竟是人办的。在需快速破案的现实压力中,收集证据材料的侦查人员,其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平心而论,案侦司法人员一般都不愿意自己办错案件。但侦办压力,与犯罪严重程度和社会影响成正比。在收集材料、筛选证据,急需提高侦查效率的紧迫性中,隐藏着筛选证据可能失误的种种风险。侦办之中的刚愎自用、自负、偷懒怠惰、主观臆断、心存侥幸等弱点,会使侦查员与案件事实失之交臂。这除了正常误差的累积效应,还有因庸倦怠惰等产生的证据缺失、证据差错等负面效应。这些消极后果,常造成在案证据材料的种种矛盾。面对明显的证据矛盾,侦查人员又总是想要人为地消除它们,以利快速结案。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就会助长筛选证据中的非正常性。由之构建的证据材料,与真实案情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时,害怕承担责任的恐惧心理,又可能会促使他们对嫌疑人无辜的材料视而不见。甚至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对既成的案件材料做手脚。如抽取材料,偷换材料,伪造材料,毁灭材料,等等。而抽取材料、毁灭材料,都会直接造成证据缺失的情况。这些都是违反侦查人员法纪、职责和职业道德的行为,是法律绝对禁止、无法原谅的。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极大地损害了政法系统的司法公信力。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反应非常强烈。因此“不合常理”,就不能排除案侦人员故意抽证、毁证的合理怀疑,法庭就会得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结论。对此,一般的说服教育不足以对相关责任人起到警示作用,也难以消除其极坏的社会影响。必须完善相关制度,依法依规严厉惩治,才能让这些人不敢为,不能为,不想为。
(二)案件材料筛选与证据缺失的一般性制约
在许多冤假错案中,隐藏着筛选证据时的种种猫腻。它们是一面充满警示的镜子,非常现实地照出了收集案件材料中的负面问题,非常紧迫地折射出了筛选证据中的可怕误区。为了具体落实公正收集证据的法律条款,除了要求控方组织嫌疑人有罪的不利证据外,还应要求控方对排除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做出合理解释,并在诉讼文本中分别将其规范地记载清楚。即使刑诉法不做这样的强制性要求,作为可能出庭应诉的侦查员,也应该在案侦过程中做出这种记载,并将之归入副卷之中。即使不出庭应诉,也能为较客观地追溯案情、寻找线索起到佐证作用。同时,也为将来的案侦倒查、责任追究,提供线索和依据。这除了需完善相关结果责任的倒逼制度,还需有侦办过程的监督体制。这就要革新侦查和公诉之间的司法体制,建立独立的预审机关。在预审的强制措施审查和公诉证据的司法审查及其诉讼引导中,对侦查活动进行过程化监督。对此,笔者已经另文论述①笔者在《论中国预审的历史、现状与革新》中阐述了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和反贪侦查与其公诉职能分离,而在侦查和审判之间组建独立的预审机关来承担公诉职能。如此,预审就有条件公正地行使证据司法审查和公诉引导侦查的职能,并在审查证据的过程中对侦查活动进行过程化监督。这样,侦、诉、审之间才能实质性地建立相互制约和彼此监督的司法关系。,在此不便赘述。
如何筛选证据、取舍证据,不仅能考察一个人的侦办业务能力,更能照见一个人的职业道德和人品质量。这就同用人单位如何选择和培养侦查人员密切相关。要建设一支能公正执法的案侦司法队伍,必须有严格筛选人员的进出制度,必须使他们经受实战的磨砺和考验,必须在考验中毫不犹豫地淘汰敢于违法乱纪的人。如系为掩盖差错和怕承担追责,而对既成的案件材料采取抽取、偷换、涂改、伪造等,而造成证据缺失的误判、错案、疑罪之类的,一旦查实,就应像终身禁入股市、终身禁驾那样,坚决将此人开除出政法队伍,并将之列入社会失信人员名单,而终身禁入政法系统。唯其这样,才能维护法治的权威和司法的尊严,对侦查、公诉、审判各诉讼环节产生真正的倒逼效应。
七、结语
在刑事侦查中,侦破罪案的紧迫性、取证组证的时机性,不能不使收集案件材料和筛选证据体系的工作要同步实施,同步展开。这种同步性就含有试错的危机性、风险性。这种风险的现实情况,会造成在案证据的人为缺失。虽然,在侦查活动中,案件材料缺失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常态,但它也同非合理的证据筛选存在关联性。我们要重点防止的,就是那些案件材料人为缺失中不合常理的现象。这就要从司法体制革新中强化对侦查的过程监督,从审判结果责任倒查产生的倒逼功能去实现双重的制约。在过程监督和结果倒逼这样的双重制约中,侦查员要将其心理压力转化为工作动力。只有遵从案件客观事实潜在的逻辑指向性,而不固执于自己的经验定式,更不主观臆测,才有可能在试错中探测到正确的案侦取证方向。当然,这之中,选错证据的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现实存在的。因而需要侦查员有随时自我否定、随时回头的心理准备,将过去筛选掉的正确证据再寻找回来,而不能一条路走到黑,更不能文过饰非、将错就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即使这要将原有证据体系推倒重新组建,耗时费力,麻烦至极,也在所不惜。有勇气屡败屡战,也绝不冤枉无辜;只有无畏地屡战,才能转危为机,成功破案。这是在筛选案件材料、寻找和纠正错位证据、完善证据体系中,对侦查员业务能力和人品素质的重大考验。
——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