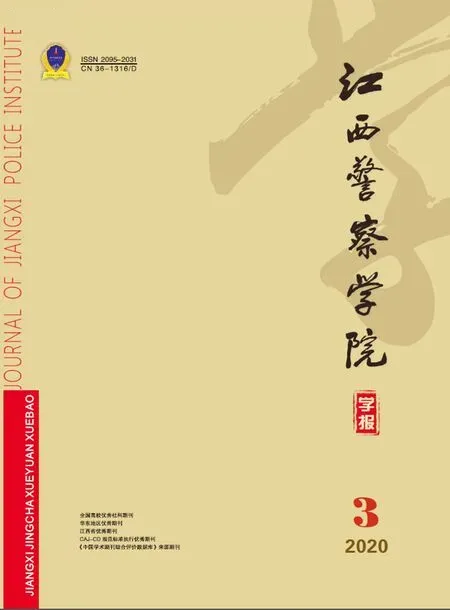抢夺罪的教义学诠释
(云南大学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6)
一、问题的提出
理论上对抢夺罪的定义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仅“公然夺取”是抢夺罪的必备要素,另一种观点则根据宣言解释对抢夺罪概念进行再定义,认为抢夺罪需要“紧密占有”和“对物暴力”两个要素①传统刑法理论对抢夺罪的定义限于“非法占有目的”“数额较大”和“公然夺取”。例如,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公然夺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5页;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使用人身强制方法,公然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参见马克昌:《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6页;张明楷教授则在界定抢夺罪概念时加入“紧密占有”和“对物暴力”的要素,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94页;张明楷:《盗窃与抢夺的界限》,法学家2006年第2期。。围绕抢夺罪爆发的争议始于张明楷教授提倡的“公开盗窃说”。有学者极力反对“公开盗窃说”,认为其混淆了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限。理论上对于抢夺罪的争论甚至上升到该罪名存废与否的地步,着实有些夸张。究其原因,在于对抢夺罪过度限制解释,为了区分抢夺罪与盗窃罪,强行将本就不是抢夺罪要素的“对物暴力”和“紧密占有”生硬地解释进抢夺罪概念中。
实践中对如何认定抢夺罪也存在不同看法。[1]“舒某伟抢夺案”②2011年2月16日21时许,被告人舒某伟在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九头鸟饭店门前附近马路上,趁被害人朱某杰下车与朋友话别时,将其黑色起亚YQZ7165E型轿车开走,后当场被抓获。经鉴定,被抢车辆价值人民币86900元。一审法院以抢夺罪判处舒某伟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11000元。参见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1)昌刑初字第467号判决书;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刑终字第3856号裁定书;参见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2年刑事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9页。能够较为形象的反应出司法实践对待该问题的态度。该案在二审期间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舒某伟构成盗窃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舒某伟构成抢夺罪。二审法院对舒某伟实行行为的认定产生了分歧,即舒某伟的实行行为是“公然的”还是“秘密的”?这就涉及对抢夺罪中“公然夺取”要素如何认定的问题。
实际上,“公然夺取”“紧密占有”以及“对物暴力”是否均为抢夺罪的构成要件要素,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在教义学的判断下,明确抢夺罪的必备要素和非必备要素极其必要。我认为只有“公然夺取”是构成抢夺罪的必备要素,“对物暴力”“紧密占有”要素的存在与否不会对认定抢夺罪形成实质性障碍,二者并非是构成抢夺罪的必备要素。我国刑法将抢夺罪置于侵犯财产罪一章中,这说明刑法规定本罪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认为“对物暴力”会有致人伤亡的可能性的观点,将抢夺罪的法益向保护人身权利方面倾斜,没有意识到抢夺罪的首要法益是保护财产权利。
对本案进行教义学解读需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问题一,被告人舒某伟开车的行为能否被评价为“对物暴力”?问题二,被害人老公赵某伟将黑色福瑞迪启动发动机后,下车与朋友们话别的行为,能否肯定其对该汽车仍是“紧密占有”?问题三,被告人舒某伟趁车里无人,上到驾驶室内开车是“秘密窃取”还是“公然夺取”?
二、“对物暴力”要素的检讨
目前较有力的观点认为,对物暴力的强夺行为必须是对财物使用了非平和的手段,整体上看具有致人伤亡的可能性。[2]对物暴力要想造成致人伤亡的可能性,就要求该财物与主人直接接触(或是被害人对其紧密占有),如此一来,行为人对财物的暴力行为才可能会对被害人造成人身伤害。也有观点认为,即便财物没有与主人直接接触,但财物只要处于被主人控制之下,行为人实施抢夺行为时,主人会通过对财物追求直接接触来防止丢失财物,也会造成“对物暴力”。[3]但是仅实施对物暴力行为还不够,必须是对物暴力的行为导致了被害人伤亡时,才能认定为抢夺罪。下文通过对“对物暴力”的解释来阐述本文认为其不是必备要素的理由。
(一)“对物暴力”的解释
首先,对物暴力的“物”在此语境下应当是指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属性且客观现实(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虚拟财产也是法律意义上具有财产属性的“物”,但是虚拟财产不大可能成为抢夺行为中暴力的对象。
其次,对物暴力的词语本身就具有模糊性,其内涵不明确,外延更是宽泛。试问如何判断作用在物上的有形力?达到何种程度才属于暴力?体型悬殊较大的人作用在物上的力是不可能一样的,比如身高一米八,体重九十公斤的人与身高一米六,体重四十公斤的人对同一物品进行暴击,物品的变形程度和受力面积不可能一样。而且,这种有形力以什么为标准判断?既然是对物暴力,作用在物上的力,就应当根据物的外观和实际状态来判断作用力的大小。但是这不具有可行性,例如,不能够看出抢夺手机和手提包时施加的作用力,也不能够判断出这种作用力的不同。在理论上不可能对这种有形力进行分类归纳,也不可能针对这种有形力制定一套供司法实践参考的标准。
再次,对“暴力”的认定,该观点认为对物暴力导致被害人伤亡时,可以认定为抢夺罪。也就是说暴力的结果要作用在人的身上,并且还要导致被害人伤亡。这种观点将会使得处罚限度最大幅度地限缩,对司法工作人员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例如,甲在菜市场,趁乙弯腰捡菜时,一把扯掉乙脖子上的金项链后逃跑。但是甲的行为并没有造成乙伤亡,甚至连轻微伤都不构成。如果事后查明金项链价值1000元以上,则可以对甲的抢夺行为定罪量刑,根本不必再讨论甲是否使用了暴力,暴力是否导致乙伤亡。并不是所有抢夺行为都会伴随暴力的发生,也不是所有抢夺行为都会导致被害人伤亡。
最后,理论上与“对物暴力”相对应的概念是“对人暴力”。但是行为属于对人暴力还是对物暴力有时候很难区分。[4]试问如何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想对物暴力还是对人暴力,或者只是想抢东西?行为人想通过对人暴力进而取得财物,适用抢劫罪的相关规定;行为人想通过对物暴力进而取得财物,适用抢夺罪的规定。这似乎是采取主观归罪的立场,认为科刑的根据是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性。难道抢夺与暴力就一定是相伴相随的吗?暴力就一定会导致被害人伤亡吗?没有人会赞同这样的结论。
实行行为不可能千篇一律,即便最终能够制定出较为明确的标准,也无法保证这些标准可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千奇百怪的问题。因为应然性解释永远无法直接代替具体案件的判断,只有面对具体案件事实,才能看出个人所理解的某个犯罪概念中到底包括哪些内容。[5]故而,不应当将“对物暴力”的特征适用于所有抢夺行为①对于转化型抢劫而言,对物暴力导致被害人伤亡是由抢夺转化为抢劫的重要因素,但是并非唯一(决定性)因素。在这些较为特殊的场合,能够适用“对物暴力”的特征。。甚至不采用“对物暴力”的特征也不会对认定抢夺罪形成实质性障碍。
(二)摒弃“对物暴力”要素的理由
首先,《刑法》第267条的条文中并没有规定构成本罪需要使用“暴力”的方法,不管是对人使用还是对物使用。其也并非属于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不采用“对物暴力”要素没有实体法上的障碍。
其次,造成被害人伤亡的原因大不相同,使用强力夺取财物导致被害人被拉拽、逃离现场撞倒被害人、被害人在追赶行为人的过程中摔倒等都可能导致其伤亡。不能将导致被害人伤亡的一切因果关系都归咎于行为人使用暴力夺取财物。
最后,如若在抢夺过程中对人使用了暴力导致人身损害,则直接适用《刑法》第269条关于转化抢劫的规定;如若对物使用暴力导致人身伤亡时,则作为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节予以考虑,但是必须是实际造成了伤亡的结果,而不是对潜在的危险性进行预先、主观推断。将预设的危险作为“已然”因素对案件进行定性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言外之意,不需要区分致人伤亡的一般危险性和较大危险性,这样的区分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根据实行行为实际客观造成的损害来判断行为的危险性是妥当的。而不是将“致人伤亡的可能性”作为认定抢夺罪成立与否的标准。因为不管是“危险性”亦或是“一般”“较大”的判断都依赖于经验,这种经验的判断也可以等同于前理解。法官依据规范裁决案件的同时,需要借助其生活经验、社会经历以及知识储备,法官自身的生活世界引导着其前理解。[6]刑事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形成自己的前理解,但是这种前理解并非贯穿于整个解释的始终。检察官、律师、被告人、被害人等在具体个案中形成的前理解也不可能全然一致。最终不能仅仅依赖于刑事法官个人的前理解(经验)对案件定罪量刑。换言之,每个人对具体概念的认识并不相似。最终得出一个普遍接纳的观点有利于司法实践,而不是将个人的前理解作为普遍观点。
回到本案,舒某伟开车的行为不论从哪一方面认定,都不可能将其行为界定为“对物暴力”。犯罪实行行为是开车,舒某伟开车采取的是平和、平稳手段。舒某伟开走车的行为客观上没有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危害。反而,被害人四人上车追赶并将黑色起亚YQZ7165E型轿车强行截住的行为,可能造成双方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
三、“紧密占有”要素的反思
“舒某伟抢夺案”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被害人老公赵某伟将黑色福瑞迪启动发动机后,下车与其朋友们话别的行为,能否肯定其对汽车仍是紧密占有?
传统刑法理论对抢夺罪的界定并不要求“紧密占有”,张明楷教授则认为紧密占有是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的重要因素。但是将紧密占有作为区分二者的重要因素不具有科学合理性,也没有区分作用。[7]而且,对“紧密占有”存在过度地限制解释的弊端,如若一定要将“紧密占有”要素纳入抢夺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中,就必须对其扩大解释,因为按照现有解释不能解决实务中的难题。要求财物与被害人身体紧密联结在一起,就相当于对抢夺罪做出比盗窃罪更要限缩的解释。盗窃罪中的财物并不要求与人的身体紧密联结在一起,比如入户窃取了一台放在桌上的笔记本电脑。电脑并没有与人的身体紧密联结,但必须要认定行为人构成盗窃罪。反而,在行为人骑摩托车瞬间夺取被害人放在自行车后座的手提包时,因为手提包没有与人的身体紧密联结,不满足“紧密占有”要素,所以就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抢夺罪。这种结论恐怕不能令人信服。
(一)“紧密占有”应当扩大解释
有观点认为,被害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必须是与人的身体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财物,具体表现为被害人提在手上、背在肩上、装在口袋等。[2]或者说,被害人占有的财物除了必须是处于被害人手中直接控制的财物,还可以是处于被害人视线控制之中的财物。[8]如若按照上述界定紧密占有概念的观点,那么本案中被害人对汽车并非是紧密占有。因为被害人并未对汽车进行手中的直接控制,汽车也没有处于其视线范围内。按照生活常识都能够明白没有人可以将汽车提在手上、背在肩上或者装在口袋。但是仅以此标准就判断被害人对汽车失去紧密占有不能令人信服。
汽车本身属于财物毫无疑问,但是汽车与能够手提肩扛的财物存在体积、重量上的差距,事物固有的属性决定了其不能与手提肩扛的财物相提并论。对某一刑法用语的解释不能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这是解释的最低限度。按照社会一般观念,停放在路边的汽车属于个人财产,即便存在无人身处驾驶室、汽车周围无人看守、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将车钥匙遗忘在车上、忘记关车窗等情形,也不能认定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完全丧失了对车辆的控制,更不能否认汽车具有权属限制的客观事实。虽然被害人背对汽车与友人话别,汽车不在其视线范围内,但是应当认为被害人主观上是充分肯定了他本人对汽车的占有和控制。此时被害人出于对社会和人们刑法价值判断的信赖,他相信没有人会认为汽车属于无人占有的财物。行为人对汽车的权属性质同样持有清晰的认识,舒某伟的供述证实了他认识到车主就在车后——有几个人在车后备厢附近站着说话,应该是车的主人和他的朋友。他已经知道被启动的车有所有权人,而且就站在车后。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形下,背对汽车的车主不能看到舒某伟的行为。
正确的解释,须永远同时符合法律的文言与法律的目的,仅仅满足其中一个标准是不够的。[9]将“紧密占有”的财物扩大解释为,处于被害人有效控制之下且能够随时使用的财物,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如若认为“紧密占有”仅限于与被害人身体紧密联结在一起或是处于被害人视线范围内,则不符合《刑法》第267条保护公民财产权的目的,没有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
(二)对“紧密占有”扩大解释的理由
第一,将“紧密占有”扩大解释为处于被害人有效控制之下且能够随时使用的财物是合理的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也没有超过公民的预测可能性。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将被害人从展示柜拿出的三部手机趁机抢走冲出店内的行为,被定性为抢夺罪①参见湖南省古丈县人民法院(2017)湘3126刑初15号刑事判决书。。此时应当肯定被害人对展示柜外的手机是有效控制,并且完全具备随时使用的可能性。如果被害人对手机是松懈占有或者没有进行有效控制,那么被告人没有必要在抢了手机之后仓皇而逃,同伙也没有必要骑车在店外等候。正是因为被害人对手机的占有过于紧密,控制有效。所以被告人需要迅速逃窜,防止“到手的鸭子飞了”。虽然对抢夺罪概念进行了扩张性的划定,但仍然是对其的逻辑解释。
第二,没有提升概念的位阶。也就是说没有将“紧密占有”的状态进行类推解释。在上述案例中,如果店铺已经打烊,店内空无一人。此时店主不能够对手机随时使用,行为人通过撬门而入等方式进到店内拿走手机的行为就是盗窃行为。因为在店铺打烊后,手机确实还处于店主有效控制之下,但是已不能够随时使用。
在本案中,应当认为被害人对汽车的占有是紧密占有。
需要特别指出,“紧密占有”的存在与否对认定抢夺罪不会构成实质性影响。正如本文开篇所言,“紧密占有”要素可以在认定抢夺罪时适用,但是必须对其进行扩大解释,否则无法解决实践中的难题。而且在认定抢夺罪时不采取“紧密占有”要素也无关紧要,因为法律条文和实务中均没有认为“紧密占有”是构成抢夺罪的必备要素。分析中国裁判文书网关于抢夺罪的判决书就可以得知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四、“公然夺取”要素的解读
“舒某伟抢夺案”要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被告人舒某伟趁车里无人,上到驾驶室内开车的行为,是秘密窃取还是公然夺取?
在被害人朱某杰的陈述和辨认笔录中对舒某伟开走车的行为做了如下描述:“其老公赵某伟将黑色福瑞迪打着,启动发动机后下车,在朱某杰、赵某伟和另外两人话别时,赵某伟发现车溜走了,后发现车是被人抢走的。”这一描述意味着当舒某伟将车开走后,并且车与被害人在空间上有一定距离时,被害人才发现车被开走的事实。即舒某伟将已经启动的车开走时,被害人并没有立刻发现“车被抢走的事实”,第一感受是“车溜走了”。行为人舒某伟到底是“偷车”还是“抢车”,从以下两方面分析。
(一)“公然夺取”与“秘密窃取”的区分
构成要件表现为“公然夺取”的抢夺和“秘密窃取”的盗窃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行为是“秘密的”还是“公然的”。[10]在刑法理论上体现为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极力主张的“公开盗窃说”(“平和窃取说”)和传统刑法理论“秘密窃取说”的激烈争论。也有观点将二者归纳为“旧说”与“新说”的对抗。[11]自2006年张明楷教授在《法学家》发表《盗窃与抢夺的界限》一文[12]至今,公开盗窃说与秘密窃取说就一直是学界热烈讨论的争点。这不仅是二分模式与三分模式①“二分模式”指在刑法中仅规定盗窃罪与抢劫罪的立法模式,例如德国、日本等。“三分模式”指在刑法中规定了盗窃罪、抢夺罪与抢劫罪的立法模式,例如中国、俄罗斯、中国台湾等。的立法差异,更是个案之间的差异。在此不深入讨论“公开盗窃说”与“秘密窃取说”的诸多分歧。主要论述构成要件表现为“公然夺取”的抢夺和“秘密窃取”的盗窃之间的主要区别——行为是否具有秘密性?
张明楷教授主张盗窃罪不需要具有秘密性,承认存在公开盗窃的行为。但是这一主张受到的批判呈现上升趋势,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坚持我国刑法认为盗窃罪是秘密窃取的传统,秘密性应当是盗窃罪的基本特征。[13]虽然这些观点对于如何界定“秘密性”尚未达成共识,但是都不否认秘密具有主观性。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是判断实行行为是否具有秘密性不可忽略的标准之一。为了确定行为人的故意,要求其必须认识到法定构成要件的事实情节。也就是说,行为人必须考虑到一些重要的具体事实情况。[14]
回到该案例,被告人舒某伟的主观认识值得探讨。舒某伟供述称:“我看驾驶车门有缝,打开一看车里没人,我趁着后面的人在聊天,就上到驾驶室内,开着车就走了。”[3]舒某伟并不想让被害人发现他上到驾驶室准备开车的事实。或者说他以一种放任(不计较)的心理实施犯罪行为,如若没有被发现,那就直接把车开走。如若被发现了,那也是等他开走车时才会被发现,这时候他对汽车已经处于实际控制中。因为他趁着被害人在聊天的时候实施犯罪行为,可以理解为他认为被害人的注意力并不在车本身,这个时候开车被害人不会发现,他只要悄悄上到驾驶室就“大功告成”。被告人舒某伟当时自认为他是在秘密窃取,而不是公然夺取。
“行为人主观上自认为没有被发觉”的表述受到学者的猛烈批判,其认为“这种观点颠倒了认定犯罪的顺序,形成了‘客观行为类型完全相同,主观认识不同,就构成不同犯罪’的不合理局面。”[15]90也就是当行为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存在差异时,如何给行为定性的问题?即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在秘密窃取,但其行为在客观上是公开的。理论上对该问题的回应各持己见,尚未达成共识。但是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认为仅依靠行为人主观认识来定性不违反罪刑均衡原则,[16]二是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应当认识到仅仅依靠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作为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限有失偏颇,这会使得司法实践过度依赖于行为人的口供。仅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作为判断标准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割裂了主客观相一致的犯罪构成要件关系。行为是否具有秘密性,要将主观判断标准与客观判断标准相结合。[17]本文采取第二种观点。
在本案中,舒某伟主观上表现出秘密窃取的目的(从他的供述可以得知),客观上舒某伟是在犯罪既遂后才被发现的,应当认为其转动方向盘时就是犯罪着手,车轮滚动时即为犯罪既遂。因为此时舒某伟坐在驾驶室内,手握方向盘,他对车已经处于实际控制的状态。他能够对车进行操作和控制,在当时也并不受人制约。后来被害人对其进行追赶的行为并不改变最终犯罪形态。
(二)“公然”的认定
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于“公然夺取”是抢夺罪的基本特征不存在争议,关键在于对“公然”需要作何解释。传统刑法教科书将“公然”界定为,采用可以使被害人立即发觉的方式,公开夺取其持有或管理下的财物。[18]学者们对“公然”的定义似乎达成了共识,例如何显兵教授认为,所谓“公然”,即为在被害人知晓的情况下,非法取得被害人的财物。[17]梅传强教授将“公然”夺取界定为明知被害人知情、当着被害人的面夺取财产。[8]也有观点对“公然”二字提出质疑,认为“公然”似乎意味着以秘密性的持续时间长短来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盗窃时秘密时间较长,抢夺时秘密时间较短。[15]93并且以司法实践中的某个案例来佐证其观点,继而认为需要对抢夺进行宣言解释,重新定义抢夺的概念。令人捉摸不透的是,即便对抢夺进行再定义,抢夺的内涵仍旧包含了“公然”的意思,即使并没有明确使用“公然”的字词。其将抢夺表述为“……当场直接夺取……”“被害人虽然当场可以得知财物被夺取,当往往来不及抗拒。刑法理论上通常说的“公然”夺取即是此意”。[2]不难发现,上述观点对“公然夺取”的界定是针对被害人(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而言。
“公然”指的是明目张胆、毫无顾忌、毫不掩饰,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公然抱茅入竹去”,再如《闲情偶寄.词曲.科诨》中的“公然道之戏场者”。这样一看,似乎是针对行为人作出的解释,要求行为人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实施犯罪行为。这就与通说相互矛盾,通说认为“公然”是针对被害人而言,要求被害人对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具有认识。
“公然”应当仅针对被害人而言,被害人必须当场知晓其财物被取走的事实。否则就没有必要对抢夺罪中的被害人作出与盗窃罪中的被害人不同的要求,即被害人有伤亡可能性。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具有致人的伤亡可能性是抢夺罪的特点。在被害人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取走其财物,按照生活常识都能够明白,这种平和的方式对被害人不会造成伤害。但是当被害人发现(察觉)自己的财物被取走,会反抗的可能性极高,此时伴随着遭到行为人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即便不要求被害人具有伤亡可能性,“公然”所指向的对象也应当是被害人。如果被害人对行为人实施“抢夺”的行为毫无察觉,行为人的行为就相当于“秘密的”。这种情况则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故而不必再讨论是否构成抢夺罪。
本案中,被害人发现车移动的第一反应是“车溜走了”,之后发现“车是被人抢走的”,被害人对舒某伟开走车的行为不存在当场知晓的情况。而且,在舒某伟转动方向盘时就应当认为是犯罪着手,车轮滚动时即为犯罪既遂。但是直至车距离被害人有一定距离时,被害人才发现车已经不属于其控制。只有在被害人知情的情况下,抢夺罪中的“公然”才兼具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本案中被害人对实行行为的认识并不满足“公然”这个构成要件要素。
综上所述,舒某伟开走车的行为是秘密行为,不满足抢夺罪“公然夺取”的要件。
五、结语
诚如车浩教授所言,法教义学的内容除了包含基本的法律解释之外,还需统筹各种材料,在法无明文规定之处创造出在逻辑上与实定法血肉相连的概念和理论。[19]法律解释在面对具体个案时才能验证其合理性与规范性,大多数时候普通民众倾向于通过犯罪概念来认定案件的性质,这也是民众朴素的法律意识最为直接的表现方式。而法律人从犯罪概念对案件进行初步判断是对经验的概括。
不论对抢夺罪采取何种概念,公然性(当场)都是抢夺罪概念中最核心最不可或缺的特征。一审法院认为:“被害人舒某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然夺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抢夺罪”。其依据传统刑法理论观点,认为抢夺罪的特征不需要具备“紧密占有”和“对物暴力”。二审法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是我认为舒某伟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而非抢夺罪。因为其行为不满足抢夺罪中最核心的要素——公然夺取。刑法学中的所有问题在解释上都有无限的可能性,观点并无绝对的正误之分,取决于选择何种立场,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除了本文中的“舒某伟抢夺案”,司法实践中对抢夺罪的认定几乎持同一观点:是否属于“紧密占有”“对物暴力”对法官认定抢夺罪没有实质性影响,最终能够决定案件性质的是“公然性”。公然性与秘密性作为抢夺罪与盗窃罪之间区分的界限,在理论上由明晰向模糊转变,以张明楷教授提出“公开盗窃说”为分界点,学者们对秘密性的认识逐渐呈现分化趋势。忽视了司法实践中仍然坚持着秘密性是盗窃罪本质特征、公然性是抢夺罪本质特征的传统刑法理论观点。可以说,“紧密占有”“对物暴力”是学者们为了将盗窃罪与抢夺罪、抢劫罪与抢夺罪进行更为深入的区分而特意提出的观点。而这两个特征原本是不存在的,是被生硬的解释进抢夺罪概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