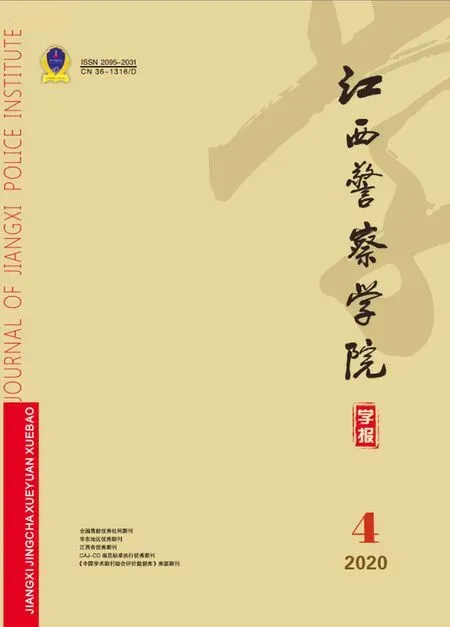论诈骗罪“处分意识”的实质与形式
——以五类典型“同案不同判”案例为切入
智逸飞,吴林生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一、问题的提出:对诈骗罪“处分意识”必要性及构造的理解不同导致定罪差异
案例一:王某1等同伙在群中担任“丢单手”、“秒单手”、“链接手”的角色,分工配合,实施网络诈骗。“丢单手”负责以出售游戏店券等名义获取被害人的支付宝余额截图,后将截图及被害人信息发给“秒单手”,“秒单手”向“链接手”获取支付金额为被害人支付宝余额的支付链接,将其中植入木马病毒,然后假装客服人员向被害人发送该链接,以需要支付小额“激活费”为由,要求被害人点击链接并安装,安装后,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支付“激活费”,账户内钱款被以购买礼品卡的形式骗取。行为人作案多起,最终被法院以诈骗罪定①参见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17)浙1024刑初498号刑事判决书。。但同为欺骗被害人点击链接,获取被害人全部余额的案件,相关被告人被法院定为盗窃罪②参见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7刑终169号刑事判决书。。
案例二:谢某等人合伙收购冶炼厂的废铅银阳极板面,商量以暗藏水箱放水的方式以减少结算重量,后谢某交代朱某将租用的货车车厢改装成带有暗水箱的车厢,使用该货车先后17次以偷放水的方式盗窃冶炼厂的废铅银阳极板面共计72.18吨,经鉴定价值二百多万,该案被告人均被法院以诈骗罪定罪③参见广东省仁化县人民法院(2016)粤0224刑初180号刑事判决书。。另一起以放空水箱盗取财物的案件中,法院认定行为人构成盗窃罪④参见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10刑终382号刑事裁定书。。
案例三:王某2在超市选购了9盒高档巧克力,将事先准备的低价商品条形码覆盖在其中一盒巧克力的商品销售条形码上,并在超市收银台通过扫描假条形码支付人民币269.5元,携赃逃离现场时被员工发现并抓获,经鉴定被盗的巧克力价值人民币1024元,虽数额不大,但行为人还有其他盗窃行为,被法院以盗窃罪定罪①参见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2刑初2064号刑事判决书。。然而,另一家法院对同类的“调换商品条形码付款案”,认定为诈骗罪②参见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2)杭江刑初字第859号判决书。。
案例四:李某于数月之间,先后多次到酒店、网吧等地,乘无人注意之机,在店家的支付宝收款二维码上覆盖其本人或由其实际控制的支付宝收款二维码,获取顾客通过支付宝扫码支付给店家的钱款共计人民币七千多元,后李某被法院以诈骗罪定罪③参见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9刑终263号刑事裁定书。。“偷换二维码取财”是近年来新兴的犯罪手段,司法机关对如何定性分歧明显,另有法院对相同案件定性为盗窃④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忻城县人民法院(2019)桂1321刑初130号刑事判决书。。
案例五:徐某使用单位配发的手机登陆支付宝时,发现可以直接登陆原同事即被害人马某的账户,于是利用其工作时获取的马某的支付宝账户密码,使用上述手机从该账户的余额中转账15000元到刘某的银行账户,然后刘某从银行取现后交给徐某。徐某归案后被两级法院终审认定为诈骗罪⑤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刑二终字第497号刑事判决书。。而同为登陆被害人支付宝账户取财的案件,有法院对行为人以盗窃罪定罪论处⑥参见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2018)豫1702刑初331号刑事判决书。。
以上五类案件,在生活中都很常见多发,案情相似却判决不同,案例一表现出司法实务会对诈骗罪“处分意识”采取不要说的立场,案例二和案例三体现了对诈骗罪“处分意识”实质内容的认识差异,案例四和案例五则体现出看似符合“处分意识”的实质内容,实则忽略了诈骗罪“处分意识”形式要件的情形,也会导致错误判决的出现。
二、关于诈骗罪“处分意识”的学说争议与“处分意识”必要性之提倡
(一)学界关于诈骗罪“处分意识”的学说争议
1.处分意识必要说
处分意识必要说的基本观点是,诈骗罪处分财产的行为,是在主观上的处分意识支配下完成的。正如刘明祥教授所言:“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应当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客观上应当具有处分财产的事实,主观上应当具有处分财产的意思,二者都不可或缺。[1]”处分意识必要说不仅是我国的通说,在日本学界也占据着主流地位,日本学者前田雅英不仅认可处分意识必要说,还对该说的内容作出了概括:“即使在外形上存在处分行为,但不是基于真正的意思时,不能成立诈骗罪……作为处分行为主观面的处分意思,是指认识到财产的占有或者利益的转移及其引起的结果。[2]”韩国的司法实务界也认同处分意识必要说,韩国大法院的判例指出:“诈骗罪是欺骗他人,使他人陷入错误,引起错误者的处分行为,以便取得财物或者财产上利益的犯罪。这里的处分行为意味着财产的处分行为,处分行为要求被害人主观上的处分意思和处分意思支配下的客观处分行为。[3]”
2.处分意识不要说
持处分意识不要说的观点认为,只要存在客观上转移财产的行为,即可认定为处分行为。代表性的观点有日本学者西田典之提出的:“只要可以认定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占有已基于受骗者的意思转移至对方,便可以肯定成立诈骗罪,有意不让对方认识到所转移的客体,这是最典型的诈骗,将此类型排除在诈骗之外,并不妥当。[4]”德国学者金德霍伊泽尔同样支持“处分意识不要说”,他指出:“财产交付概念并不以被骗者的交付意识为条件。某行为即使其与财产的相关性不为被骗者所知,一旦形成直接的财产转移,也应为构成要件的财产交付[5]。”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学界近年来有愈多学者都站在了处分意识不要说的立场,出现了诸如“盗骗竞合视角论⑦该观点主张诈骗实际上就是双边关系的间接盗窃,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就是直接盗窃与间接盗窃、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要以行为归属区分两罪,若是被告人转移财产,则为盗窃罪;若被害人转移财产,就是诈骗罪。三角诈骗与间接盗窃的区分,也要看第三人的行为归属,如果能将第三人的行为视为被害人的行为,就可认定为三角诈骗,如能将其视为行为人的行为,则为间接盗窃。”[6]、“交往沟通论”[7]、“交易信息操纵论”[8],主张以新的方式认定诈骗罪,界分诈骗与盗窃①主张盗窃罪与诈骗罪之分,主要是二者在交往形态上的显著差别,行为人采取“排除沟通”方式直接获得财产的,是盗窃罪;在有沟通交往的情况下间接获得对方财产的,就应当是诈骗罪。②主张“交易信息操纵”是诈骗罪的不法本质,欺骗人预先创设了导致交易决定的错误信息风险,并使得该风险实现,被害人在其中仅仅充当信息操纵的对象,是配合风险实现的被动工具。被害人只要是在信息操纵下实施的财产交易行为就将该财产交易导致的损失归责给行为人,无需考虑被害人进行财产交易时是否具有“处分意识”,也无需将此种交易行为界定为“处分行为”。。“处分意识不要说”似乎已经成了近来关于诈骗罪学说的流行趋势,撼动着“必要说”的地位。
3.处分意识折衷说
处分意识折衷说主张对“处分意识”要分情况对待,在一些情况下需要具备“处分意识”,一些情况则不需,这是德国实务部门一贯立场。德国法院对处分对象为财物的场合,持处分意识必要说,对处分对象是财产性利益的场合,持处分意识不要说。[9]之所以这样区分,是因为德国刑法中盗窃罪的对象只包括财物,没有把财产性利益归纳进来,若对诈骗财产性利益也要求具有 “处分意识”,就会造成刑法规制漏洞[10]。
(二)“处分意识”是诈骗罪必不可少的要素
1.诈骗罪“处分意识”是对以行为性质为基础的罪名体系的维护
我国刑法分则体系以犯罪客体的不同性质划分十大类犯罪,每类犯罪又以具体行为的不同性质创设若干罪名。可以说,在我国的刑法分则体系中,每个罪名就如同一个旗帜,统领着符合该罪的所有行为性质。对一个犯罪行为的定性,固然要考虑属于哪种性质,归属哪项罪名所统管。前述三种“处分意识不要说”的新观点,一定程度上都是对以行为性质构建罪名体系的违反。“盗骗竞合视角论”主张以行为归属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当被告人转移财产时,即定盗窃,当被害人转移财产时,即定诈骗。[6]50-56若真依此观点,则类似以链接取财、偷换包装内物品欺骗营业员等看似受骗人拱手交付的案情均构成诈骗,凡以利用财物占有人自身转移财物的行为均以诈骗论处,而不考虑行为性质,其不合理性不言而喻。“交往沟通论”以对财产决策事项有无沟通作为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标志,[7]169-181以此为区分,则行为人对无意识能力者,如幼儿和精神病患者欺骗,以及对无财产处分权限与地位的人欺骗,都将构成诈骗罪。而依照行为性质,欺骗无意识能力的人,相当于把他人当作盗窃工具利用,欺骗无处分权限的人,要么也是把他人当成不知情的工具,要么他人是具有犯罪故意的帮凶。“交易信息操纵论”也存在不周全的特点,在一件真实案例中,被害人订机票时按照行为人的指示操作,输入“电子激活码”后,账户上相应数额的钱款随即转走。该案中行为人始终掌握着信息操纵权,被害人是配合风险实现的工具,[8]240-268依“交易信息操纵论”应定诈骗,但本案同样符合盗窃的行为本质。
上述三种观点,若以行为性质分析,就会得出另一结论,如果此三种观点为适应不同情境而对自身进行完善,则势必会回到要求“处分意识”的轨道上来。对诈骗罪“处分意识”的必要性作出认可和包括实质与形式构造在内的规范构造的内容加以确定,是将诈骗罪所有行为模式涵盖在内的最佳方式,是遵循以行为性质作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标准的正确方法,若以其他标准去区分,定会引起更大的争议,并误导人们分析问题的思维。
2.诈骗罪“处分意识”是对立法目的的贯彻
在各国刑法的取得型财产犯罪体系中,盗窃罪都可作为最具本源性的罪名,其他各项犯罪都属盗窃罪的变体构成要件,似由盗窃罪的行为模式演变而来,[10]诈骗罪也不例外。当行为人料到直接取得被害人财产会遇到阻碍,想到了通过哄骗被害人使其自觉转移财产,就会出现两种情形,少数情况下被害人是被当做工具利用,没有意识到己方财物的转移,多数情况是被害人受骗后心甘情愿地交付财产。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行为已出现变质,原来是财物的转移有违被害人的意志,此时变为财物转移之时是符合被害人意志的。在这种变质的情况下,立法者想到了设立新罪名加以规制,便是诈骗。由此,诈骗行为自产生之际便具有的特殊属性即是被害人自愿转移财产的“自损型”犯罪,不同于类似盗窃罪违背被害人意愿的“他损型”犯罪,从这一角度来说,盗窃与诈骗便为排他互斥的关系。[11]诈骗行为既由盗窃“基因突变”而来,立法者将之独立设罪的目的便是发挥其特有功效。对诈骗罪进行研究的出发点也应是其对立于盗窃罪的独特之处,如果在一个案件中,盗窃罪与诈骗罪(针对同一被害人)出现了能竞合适用的情形,那一定是现有诈骗理论还有漏缺之处,需要继续完善补足。
严谨协调的取得型财产犯罪体系的构建,要求各项罪名都具有完善的构成要件,适用时严格区分、慎重把握,使其各职其能。我国取得型财产犯罪体系的各罪名具有同一的侵犯客体与犯罪目的,能区分边界之处便是各罪的行为方式,避免各项犯罪要件的交叉重叠,对财产犯罪体系的稳定有着关键性作用。[12]要求诈骗罪的受骗人对其转移的财物完全是“自愿交付”,就不可能不具备“处分意识”,这对维护整个财产犯罪的体系结构也有重要意义。
3.“处分意识” 是诈骗罪基本逻辑结构的内存蕴意
当前学界对既遂的诈骗罪基本结构的认识是统一的,均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者产生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受骗者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可见,成立诈骗罪强调“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何谓“处分财产”? 处分行为是否等同于交付行为? 在权属关系更为明确的民法中,处分是权利人对所有物依法予以处置的权利,处分权是所有权内容的核心和拥有所有权的根本标志。[13]既然是一种权利,那就不能把处分行为仅以一种肢体行动作理解,权利人要行使处分权,必定要对行使的方式、目的与结果具有一定的认识,难以想象权利人行使权利时主观意识是空的。所以,民法中的处分行为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那么刑法中的处分行为可否借鉴民法的特点?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一方面,从词汇本意上看,“处分”一词呈现出很强的主观色彩。民法中“处分行为”的特征,是立法者从汉语体系中选出“处分”这一合适的词汇,放入民法规范中熏陶侵染所体现出来的,那么剖析“处分”在语言中的本原含义,就要抛弃民法语境赋予其的特殊内涵,发掘出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用意,此时,“处分”一词就仅只处理、安排。但即使最本原的含义,也带有主观性,没有主观意识的支配,怎么对一件事物处理、安排? 另一方面,认同处分行为需主观意识,并不会造成刑法法益保护功能的缺位。如果将处分行为配以主观意识,其就不同于交付行为,后者只强调客观上的转移举动,不需考虑主体知不知情。这样,“处分”在一定层面就狭窄于“交付”,但刑法使用含义更窄的词语并不会造成法益保护的缺失,当行为人欺骗被害人“不知情而交付”时,以盗窃的间接正犯论更妥当。由此,以主客观相统一来看待处分行为,更能够突出诈骗的本质,也更能够保护法秩序的统一性。[14]
三、诈骗罪“处分意识”的实质构造
诈骗罪“处分意识”规范构造的实质要件,即实质构造、实质内容。诈骗罪的受骗者在处分财物时应具有什么主观意识,在学界未有定论。“严格处分意识说”与“缓和处分意识说”都有难以弥补的局限性,应转换视角探寻“处分意识”应具有的内容。财产有财物①学界对“财物”与“财产”未作明确区分,大多时候都通用二词,本文中的“财物”只指有体物,“财产”指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统称。和财产性利益之分,二者特征不同,法律保护二者的特点也不同,“处分意识”的内容也会因处分对象的不同性质而有差异。
(一)“严格处分意识说”与“缓和处分意识说”的局限性
关于诈骗罪“处分意识”的内容,现有“严格处分意识说”与“缓和处分意识说”之分。“严格处分意识说” 认为:“处分者除了有把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占有转移给对方的认识之外,还必须对处分财物的内容,包括交付的对象、数量价值等有全面的认识。处分意思,必须具有明确性、具体性,处分者既要认识到自己在处分一定的财物,还必须对正在处分的对象的特殊性、具体性有较为清楚的意识。[15]”“缓和处分意识说”认为,处分者不要求对财产的数量、价值等具有完全的认识。[16]1003
笔者认为,两种观点都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以“钻石案”为例来检验“严格处分意识说”,甲捡到一颗钻石,到鉴定机构去鉴定价格,鉴定人乙见到钻石,知道价值不菲,但对甲谎称说这不是钻石,只是普通水晶,自己平时喜欢收藏水晶,愿以3000元购买,甲同意成交,后乙将钻石以300000的价格卖出。依“严格处分意识说”,本案中受骗者对财物价值认识有误,不具有处分意识,只能对鉴定人认定为盗窃罪。但是,本案钻石是在受骗人的视野范围内转移的,因而很难认为受骗人对财物的转移不知情,也就不能充当“不知情的利用工具”使行为人构成间接正犯形式的盗窃罪。据此,“严格处分意识说” 会使案件陷入定性困境,既不是盗窃,也非诈骗。要求处分者对财产的所有特征都产生认识,有强烈的虚幻性,故“严格处分意识说”的立场不宜采纳。再看“缓和处分意识说”,当前最通行的“缓和处分意识说”是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其认为在受骗者没有认识到所转移财产的真实价值(价格)和数量时,应认为具有处分意识,而在受骗者没有认识到财产的种类和性质时,不宜认为有处分意识。[16]1003-1004按此观点,行为人将照相机包装盒的泡沫取出,放入另一台照相机,营业员以一台照相机的价格收取了货款,营业员具有处分意识,行为人构成诈骗罪;而行为人若将牛奶包装箱中的牛奶取出几盒,放入一个照相机,以一箱牛奶的价格支付货款的,这时营业员便不再具有处分意识,行为人构成盗窃罪。这样的观点于学理上很难讲通,同样是以商品包装为掩饰窃取货物,营业员都未认识到自己转移了该货物,为何种类不同时才评价为盗窃,种类相同时就评价为诈骗? 此外,若行为人将普通照相机与高档照相机的条形码调换后拿着高档照相机结账,营业员同时对商品的种类、价值都产生了错误,是否具有处分意识? 再有,若行为人将一台高档照相机藏入另一台高档照相机的包装盒去结账,要认定诈骗,而将普通照相机藏入高档照相机的包装盒,就认定为起刑点更低的盗窃,是否会造成量刑不公? 故该说法有自相矛盾之处,不具说服力。“缓和处分意识说”的通病在于都想找到财物自身的全部特征,然后认为对财产决策作用不大的特征在认识上可予以缓和,但在适用时往往都鬻矛誉楯,难以自圆其说,所以这并不是研究“处分意识”内容的正确角度。
(二)改换视角探究“处分意识”的实质内容
1.“处分意识” 应要求认识到行为人试图转移之财物的存在
当行为人试图通过隐瞒财物的某项特征 (数额、种类、价值等)进行欺骗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财物本身。财物的特征总有一些入眼即能认识到,一些需要通过分析研究才能了解到。财物能够出现在人的视野范围内的要素,包括财物的数量、体积、种类等,可以说是财物的外表要素;而财物不显露于外的要素,包括价值、性能、功效等,可称之为属性要素。人们通常不能仅通过观测,不假思索就认清楚该财物的价值、性能等内在属性。故此,行为人若以对方对财物价值等内在属性上的认识错误进行欺骗,对方陷入认识错误而处分财物的可能性极大;而行为人试图以对方对财物外表要素的认识错误来欺骗,只要该财物出现在对方视野范围内,对方就基本不可能出现认识错误,如果行为人将财物隐藏于包装盒内,使财物无法被对方看见,这时虽会使对方产生数量或种类等方面的认识错误,但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手段与盗窃罪的客观行为无异。由此,可以推知,诈骗罪的处分意识,处分人毋需认识到财物的价值等属性要素,但务必认识到财物的外表要素,若处分人认识不到外表要素,则一定是行为人使用了隐匿手段。同时,财物的外表要素也是认定财物存在的最基础要素,[17]可以说,处分人在认识到行为人试图转移的财物的外表要素时,就认识到了该财物的客体存在,也即“处分意识”需要认识到行为人试图转移之财物的存在。回看案例二,行为人企图放空水箱多装取冶炼厂的财物,但在冶炼厂厂主的意识里,行为人只转移了车上实际板面重量减去水重的那部分重量,对于多转移的那部分,厂主视野中并未出现该部分的体积,也即未意识到该部分板面的存在,行为人对该部分板面的转移是违背厂主意志的,因为行为人应对多转移部分的板面成立盗窃罪。
“处分意识”不要求对财物的价值有明确的认识,前述“钻石案”即是合适的例证,处分人甲虽然对财物的价值认识错误,但对财物的外表要素有清晰的认识,可认为甲具有处分意识。在案例三中,营业员同样对被调换条形码后的商品价值认识有误,但却认识到了行为人试图转移的巧克力的存在,具有处分意识,此案性质应为诈骗。
2.“处分意识” 还需认识到财物事实控制力的转出
诈骗罪中的受骗人处分财产,是将财产的何种事实状态进行处分的问题,事关诈骗罪的成立与否和法益保护效果,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过程受骗人的主观意识作出限制。对此,有三种观点:所有权转移说、持有转移说、占有转移说,需要予以评析以选择最合适的观点。
(1)过于严苛的“所有权转移说”。德国学者Backmann持所有权转移说,认为只有当被害人自己将相应财物排除出自身所有权的范围并使之成为他人所有的财产时,才能认定被害人是自我损害地进行了财产处分。否则就应当认定行为人擅自破除了被害人的所有权,不能构成诈骗罪,而只能成立盗窃或者侵占罪。[18]试举一例验证此说是否合理,甲想将乙的轿车骗为己有,便对乙说明天邻市市区车辆限号,想借车用一天去邻市办事,用完马上归还,甲借到车后占为己有不送还。本案乙处分的只是轿车的使用权,但甲若不构成诈骗罪,就会造成刑法运用的真空。乙借车予甲,甲在取得对轿车的支配控制之时是符合乙的意志的,故甲不能成立盗窃罪;乙对车的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于借车之前而不是车借到手以后,故也不符合侵占罪的要件。而乙的行为与诈骗罪的逻辑构造配合起来恰如其分,成立诈骗罪无误。由此看来,受骗人处分财物的使用权也可能使行为人构成诈骗罪,要求受骗人处分意识里要将财物所有权转移就大可不必。
(2)“持有转移说”与“占有转移说”的选择。这两种观点的合理性,可以先从两个方面探讨:一是诈骗罪财产损害的直接性方面,“被害人的作为、容忍或不作为必须导致行为人无需采取进一步的举动就足以造成财产损失。相反,如果相应行为只是造成了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机会,尤其是如果行为人还必须事后通过其他犯罪行为才能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时,就不能认为被害人进行了财产处分。”[18]从这个意义上讲,“持有转移说”达不到财产减损的直接性效果,例如,汽车销售服务4S店的店员将新车交予甲让其在店内试行,店员的主观意识只是把车在一个特定空间区域内交给甲使用,即将车的“持有”交给甲,该车仍属店内控制的财产,甲只有驾车逃出店外,汽车店才遭受了财产损失。二是刑法上“占有”的效力方面,刑法上的占有,经历了从事实性概念到规范性概念的演变过程。规范性的占有概念,是为了补足占有人与财物相隔较远的空间距离,事实上的占有关系薄弱时,对财物的占有效力。[19]但事实性的占有仍然对占有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财物上建立起新的事实上的支配控制关系时,即使是非法,也无需考虑原占有人还享有对财物规范性的占有。刑法不承认间接占有,当财物处于他人的事实性支配控制之下,即使原占有人对财物还具有民事权利,也认定其占有已被消灭。通过案例间的对比,更能认知到“占有”的效力。前述借车案中,行为人欺骗车主第二天交车的,成立诈骗罪无疑;但是,若行为人欺骗车主的内容是,想当场体验一下驾驶感受,体验后马上回来,却在驾车过程中逃跑的,还能否认定诈骗罪? 在司法实务中也有类似案情,行为人编造理由欺骗被害人想借手机打电话,却在打电话过程中趁被害人不注意而逃,法院通常以盗窃罪定罪。笔者也赞同对该类案情认定为盗窃罪。同为“借用欺骗”,为何欺骗内容是当场用后归还,就为盗窃罪,欺骗第二天归还的,就为诈骗罪? 原因就在于,后一种情形中,被害人将财物的占有转移给了对方,前一种却没有。当被害人将财物交付于行为人时,财物的占有并没有马上转移,根据占有的事实支配性,此时财物仍在被害人的控制支配下,在行为人与被害人的距离渐去渐远时,被害人对财物的事实控制力就会逐渐减弱至完全消失。但关键在于,后一种情形中行为人取得对财物占有的瞬间是符合被害人意志的,即被害人“自愿”转移了占有,而前种情形行为人取得财物占有是违背被害人意志的,是行为人自己“打破占有”,被害人只是转移了财物“持有”,两种案情性质不同。
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分析,“占有转移说” 相对于“持有转移说”是更具合理性的观点,但也不乏支持“持有转移说”,质疑“占有转移说”的声音。有观点认为,“占有转移说”混淆了“处分行为”与“占有转移”的功能、混淆了犯罪成立与既遂的关系、难以解释犯罪着手问题、有违责任主义之嫌,而持有转移说能很好地和犯罪着手理论接轨,进而妥善地处理好犯罪成立与既遂、处分行为和占有转移的关系,是更符合诈骗罪本质和构造的学说。[20]此观点站不住脚,其一,“占有转移说” 并未混淆“处分行为”与“占有转移”的功能。“占有转移说”是为了解决财产处分主观上处分意识的问题,“占有转移说”对“占有转移”的功能界定为促使诈骗罪成立的直接性要件,而处分行为具有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功能,处分行为是主客观统一的,客观上将占有转移时,主观上还需认识到财物存在这个先决条件,忽略这个条件,就会像“一包藏多物”案件那样,将盗窃看作诈骗。可见,处分行为的功能不是占有转移能替代的;其二,认为“占有转移说”混淆犯罪成立与既遂的关系更难以解释,其说法是受骗人将财物“持有”转移于行为人时,诈骗罪已成立,发生占有转移的结果时,是诈骗罪的既遂。可情况是,如汽车店试车案,行为人“持有”汽车时车店的财产权并未受到侵害,既无法益受损,何来犯罪成立? 其三,诈骗罪的着手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时无疑,但若行为人以试用(借用)为借口,骗得财物后当场逃离的,成立盗窃罪,前面欺骗行为即为盗窃罪的预备行为,该观点认为,行为人实行盗窃罪预备行为后,财物已到手,之后盗窃自己手中的财物达到既遂状态不合理。问题的关键是,行为人是从被害人的控制支配之下盗得财物(如在汽车店试行过程中驾车逃跑),不仅是从自己手中,真正取得财物之时是被害人控制力所不及的瞬间。因此,“占有转移说”与犯罪着手理论不冲突;其四,类似汽车店试车案情形中,虽然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的目的告诉店主想试车时也是一种欺骗行为,但不能解释为“诈骗”的故意,行为人驾车之后对从车店溜走一定也有清晰的计划,直接侵犯车店财产权的行为也是其驾车从车店溜走的行为,可以说盗窃的故意十分明确,所以不存在将诈骗故意解释为盗窃的故意,违背了责任主义之说。
需要注意的是,“占有转移说” 的前提是先要清晰地意识到对财物的占有。[21]例如,行为人拿商场的财物欺骗营业员说是自己带进来的,营业员相信,或是行为人帮房主修缮后院,发现埋有金币,为房主祖父所遗留,但房主不知情,还问行为人是不是他带进来的,行为人说是,便将金币带走。两案中,被害人都未意识到财物被自己占有,也就不会有处分财物的行为,对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应评价为盗窃。
最后,应使用“转出”而不是“转移”,因为强调转移,就一定要有转移对象的存在,而诈骗罪中的处分财物也可能是直接抛弃了财物,如“彩票案”,行为人明知彩票持有者的彩票中了大奖,却欺骗彩票持有者说彩票没有中奖,彩票持有人便扔掉了彩票,之后行为人拾得彩票去兑奖。本案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逻辑构造,成立诈骗罪无误,但处分人只有“转出”财物,没有“转移”财物。
3.以财产性利益为处分对象的处分意识
通过上述分析,当处分对象为财物时,处分人需意识到行为人试图转移之财物的存在与财物事实控制力(占有)的转出。而当处分对象转变为财产性利益时,处分意识的内容要基于财产性利益不同于财物的特点作出变通。作为刑法保护对象的财产性利益,是权利人应当享有的除财物之外无形的财产上的利益,[22]以财产性利益为对象的犯罪,一种情况是将财产性利益直接转为己有,如债务人欺骗债权人免除债务、第三人欺骗债权人转移债权;另一种情况则是针对利益的未实现性,损坏利益的实现可能,这种情况没有改变既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是对利益的控制支配权发生了转移。确定以财产性利益为处分对象的处分意识的内容,只需分析后一种情况即可,结论能涵盖前一种情况。而后一种情况对财产性利益的诈骗,可以认为行为人的欺骗行为使得受骗人对自己财产性利益的“当场实现可能性”作出处分,却遭受了财产损失的后果时即可成立诈骗罪。举例为证,甲等众人在豪华酒店用餐,消费数额较大,甲把其他人送出酒店后,产生了逃单的念头,于是欺骗店长说今天没带钱,明天一定来付,店长见甲是老顾客,从未欠过账,于是选择相信甲一次,但甲离开后就音信全无。本案中,在店长的意识里,并没有放弃或转移债权,债权的实现可能性也没有降低(店长认为甲第二天一定会来付款,如果其意识到债权有不能实现的风险,一定不会放甲走,债权的实现可能性降低是处分结果),店长处分的是债权当场实现的可能,但却给了甲永久逃避债务的机会。甲以欺骗行为使店长陷入认识错误,处分了债权的当场实现可能性,自己收获了经济利益却使酒店遭受了财产损失,甲构成诈骗罪,但店长处分意识的内容是“财产性利益的当场实现可能性降低①应用“降低”不应用“消失”,若行为人欺骗店主自己的家人在附近棋牌室,去取钱后马上回来,却一去不返,这是店主的意识里财产性利益的当场实现可能并没有消失,只是降低。”。
处分财物需认识到行为人试图转移之财物的存在,处分财产性利益时,当然也要认识到行为人试图获利的财产性利益的存在。例如,第三人明知债权人对债务人有多份债权,欺骗债权人向其转让一份对债务人债权,却递给债权人转让全部债权的文书使其受骗而签字。第三人就那一份债权成立诈骗罪,就其他债权成立盗窃,因为债权人未意识到这部分财产性利益的存在。
所以当处分对象为财产性利益时,处分人需要意识到行为人试图获利之财产性利益的存在与当场实现可能性的降低。
四、诈骗罪“处分意识”的形式构造
与实质构造相辅相成,诈骗罪“处分意识”规范构造的形式要件,即形式构造解决的是实质构造在什么条件下有效的问题,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所依。“处分意识”的实质内容,只有置于形式构造的框架下,才能称得上是诈骗罪的“处分意识”。诈骗罪“处分意识”形式构造的内容包含五个方面。
(一)处分人具有意识能力
意识能力是指受骗人在处分财产时正常的认识判断能力。这里可借鉴民法中关于意思能力的判断,即不满8周岁的幼儿作出的民事行为无效,8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作出的与其年龄、智力不相符的民事行为无效,精神病人作出的民事行为无效。无效的原因即法律认为上述主体缺乏独立的认识判断能力。行为人骗取不满8周岁的幼儿与精神病人的财物,或者欺骗8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作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符的处分财物的行为可认为是利用不知情的犯罪工具的行为,应视为盗窃行为。此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有可能在特殊情况下丧失意识能力,如昏醉状态下的人认清事实的能力遭受重创,这时行为人若欺骗醉酒者在纪念册上签名,实际上则是免除债务的文书,这时虽然文书出现在受骗人的视野中,但不认为其具有“处分意识”。[1]
(二)基于处分人的意志自主性产生
若行为人冒充警察扣押受骗人的某种财物,或冒充执勤交警对违章停车的受骗人开出 “罚单”,受骗人不得已而交付,这时受骗人的交付是因为形成了心理压力,而不是自由意志。“被害人交付财物或者允许行为人取走财物只是因为觉得自己别无选择,而非自愿的决定,故而应当否认其进行了财产处分。[23]”诈骗罪的受骗人应当处于完全自由的意志状态下处分财产,这一专属特质是诈骗罪与取得型财产犯罪体系中其他犯罪划清界限的关键因素。
(三)意识的产生与错误认识具有心理因果性
受骗人在错误认识的驱使下产生了处分财产的冲动,错误认识与处分意识之间有着主观心理上的因果关联,这种因果关联存在于内心思考领域,[24]虽说偶然,却也具有紧密性,体现在处分意识直接依赖认识错误而产生。以前述“钻石案”为例,鉴定人欺骗钻石持有人,其拿的是普通水晶,而不是钻石,愿以3000元购买,若钻石持有人虽然受骗,但看其带的钻石透明无瑕,不舍交付,而是拿出另一块略有瑕疵的钻石经鉴定人估价后卖与鉴定人,这时受骗人处分财产的意识不是直接依赖错误认识而产生,不具有心理上的因果关联,就不能认为是诈骗罪的“处分意识”。
(四)处分人有处分权限
诈骗罪的受骗人处分财产要求必须具有对财产的处分权限与地位,处分意识作为这一过程的主观指引因素,自然也要求具备这一形式要件。尤其是在被骗人处分的不是自己财产的场合,只有当被骗人受到被害人的委托或者根据法律规定取得了支配被害人财产的权利时,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财产处分。[25]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类似案例四的偷换二维码取财案,有些法院以诈骗罪定罪论处,就是忽略了诈骗罪“处分意识”的这一形式要件。要对“偷换二维码取财案”准确定性,第一步先要找出本案中顾客与店家哪一方遭受了财产损失,谁为被害人。《合同法》第12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本案顾客与店家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顾客因第三人的原因转错了款,店家能否以合同目的未达成为由向顾客主张违约责任? 本文认为不能,民法上的违约,是指合同债务的不履行,顾客主观上有履行债务的目的,客观上有履行债务的行为,虽然在履行过程中错把行为人的二维码当成了店家的转付了钱款,但责任不能归咎于顾客,反倒是店家没有及时审核二维码有一定的过失责任。所以,可以认为是店家由于自己一定程度上的过失而没有收到顾客的钱款,顾客不存在违约行为,店家没有请求顾客继续履行的权利。基于此,二维码案中的被害人应是店家,店家对顾客的债权受到了行为人的侵害。既然店家是受害人,那么受骗人就是顾客,诈骗罪中受骗人非处分自己财物的场合,为三角诈骗,三角诈骗的受骗人要求具有处分受害人财产的权限和地位,本案中顾客并不具有处分店家债权的权限和地位,其对店家债权的实现负有履行义务。所以,本案因为不符合诈骗罪“处分意识”的形式要件,因此不构成诈骗罪。
“偷换二维取财码” 案的正确定性应为盗窃罪,店家的债权属于店家应享有的财产性利益,刑法保护财产性利益,实际上是保护财产性利益的实现可能性。在对象为财物的场合,盗窃罪的行为模式为“以平和方式打破对方对财物的占有,建立起自己对财物的占有”;[26]对象为财产性利益时,盗窃罪的行为模式可变通为 “以平和方式打破对方财产性利益的实现可能性,使自己获得了相应利益”。“偷换二维码取财案”的行为人通过偷换二维码,使店家债权的实现可能性遭到破坏,自己取得了相应的利益,符合盗窃财产性利益的特征,构成盗窃罪。
(五)处分人存在正确认知的可能性
第三方支付方式在当今日益兴起,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侵财案件也是不计其数。案例五所示的行为人侵入被害人的支付宝账户窃取财物,在司法实务中也有诈骗罪与盗窃罪两种判决。其中认定诈骗罪的司法机关认为,支付宝平台是由人工操作的平台,而且被害人基于信任将财产托付给平台保管,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和地位,故行为人非法行为的性质属诈骗。
在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侵财的案件中,行为人作案手段通常是,进入被害人的平台账户中,输入收款人身份信息、转账数额和获悉的账户密码,待平台通过审核后,所转数额即进入收款人的银行卡账户中。在此过程中,支付宝平台只要看到所输入的收款人身份信息、付款密码正确,即通过验证,执行转账。诈骗罪的逻辑构造中,处分人因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而“陷入”了认识错误,所以,当然隐含着另一种可能,即处分人警惕意识强,欺骗人没有得逞。也就是说,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人应具有正确认知的可能性。诈骗罪的起刑数额高于盗窃罪,就是因为诈骗罪中的处分人若是警觉性强,是不会上当受骗的。联系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侵财案件,平台的财产管理者并没有这种正确认知的可能性,其只要看到输入的身份信息、密码等正确,就一定会通过审核,故平台更像是在执行一种指令,无可选择性。[27]由此看来,行为人在转账时对支付平台的操作也具有完全的可预见性,更像是把平台当作不了解真相的工具利用,认定为间接正犯形式的盗窃罪更为合适,不应论以诈骗罪。
进而言之,在三角诈骗的认定中,处分人除了应具备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与地位之外,也不能忽略“具有正确认知的可能性”这一既有的内在要素。
五、结语
坚持诈骗罪“处分意识必要说”,并不意味着对相关理论的因循守旧,不使之与时俱进。对刑法各罪理论的创新与完善,不能歪曲该罪的行为本质,也不能偏离罪名的设立目的。肯定“处分意识”是诈骗罪行为模式中“自损性”特征的本质要求,也符合立法时使之独立成罪的目的。诈骗罪“处分意识” 的规范构造要求实质构造与形式构造的有机统一,实质构造与形式构造对诈骗罪的“处分意识”同等重要,实质构造是内核,形式构造是框架,实质构造只有放在形式构造之下才会彰显价值与生命力,形式构造只有依托实质构造的存在才不至于被虚置。只要把研究重心放在对处分意识的实质内容与形式构造加以完善上,使其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就可以系统地揽括诈骗罪的所有行为方式,指引解决相关案例的定性难问题。对犯罪类型的正确区分和把握,是维护刑法尊严与谨密性的需要,对实务部门来说,又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需要。以刑法保护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不同目的为出发点,探求处分人对二者不同的处分意识,再饰以形式要件的框架,能够有效避免将一些看似“拱手交付”,直观表象为诈骗的犯罪行为定性错误,以准确会意诈骗的本真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