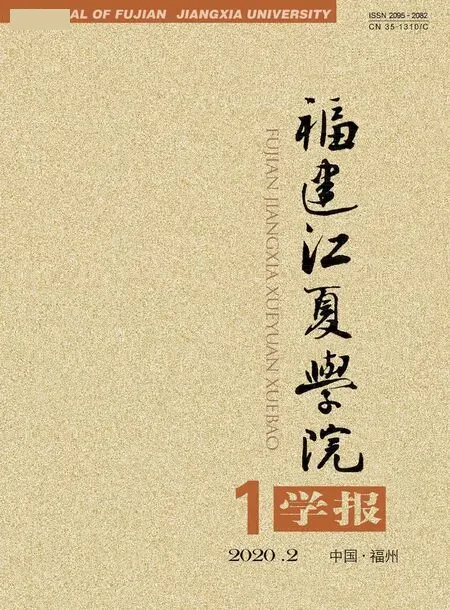庄子“道之难明”的认识论解读
王亚波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青海西宁,810000)
道,作为庄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既表现为存在的普遍原理,也构成了最终极的认知对象。围绕如何认识道以及如何得道的问题,庄子展开了丰富的论述,涉及到经验知识批判、道的认知方法讨论等内容,可以归结为庄子认识论讨论的对象。庄子在如何认识道以及如何得道的问题上,阐明“道之难明”的原因与破解之方,对一般经验知识和道的认知进行了两重形态的区分,构成了其认识论的重要特点。
一、道的内涵与道之难明
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关于道的论述在继承老子道论思想的基础上,又赋予了新的理解,使之具有多重意蕴。首先,道在庄子那里体现为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意义,这与老子思想有较为明显的继承性。庄子虽未像老子那样明确提出一个“道生万物”的模式,但是道具有生化万物的创造力是明确的。庄子在《大宗师》中指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道无为无形却真实可信,作为终极源头,自本自根先天地而存,生化天地万物。
根据庄子的论述,道不但是宇宙论意义万物化生的源头,还是天地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是人类行动的法则。日月星辰的运转、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都是以道为依据,这就是庄子之道的第二个涵义,即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的终极根据和本质。《渔父》篇有言:“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 道是万物遵循的根由,各种物类遵循了道才能得以存在,所以人伦物理莫不依道而存。道作为存在的根据和世界统一原理,不是一个具体的源头,而是自本自根没有任何规定性,是绝无对待的自足性的存在,相对于经验世界或者具体事物具有逻辑先在性。庄子将道的这种特点概括为:“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齐物论》)道不是一个具体源头,否则会陷入逻辑上的无穷的倒退,道就是超越了时间先后和有无之分的宇宙整体,无始无终。与这一特点相对应,道内在于万物,既不是一个超越万物的实体,也不是无所作为的绝对空虚。在庄子看来,道“内在于万物,但又不是以显性的方式作用于物。作为‘本根’,它不仅构成了万物的本源,而且规定着其运行的方式”[1]80。道是无始无终没有极限的,无限功用体现在万物依赖它而不自知。万物各得其所的运行中自然体现道的力量,此即是“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咸其自取,怒着其谁邪?”(《庄子·齐物论》)
庄子之道的这种本体论涵义,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老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思想,但在更多意义上,庄子弱化了老子道与物的主从关系。在庄子看来,作为终极根据的道具有无限的普遍性,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所不容,渊渊乎其不可测也。”(《庄子·天道》)道是小大精粗无所不包,囊括天地,贯穿时空,无所不在。因此,庄子用了每下愈况的方式指出,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乃至在“屎溺”。道与万物没有截然相分的界限,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和运动之中,体现的是内在性。正是如此,庄子的道物关系更多的揭示了一种“道通为一”和道通万物的关系,减少了老子道论所蕴含的主宰意味。老庄二人论道,“老子强调‘道’超越性与创生万物的玄妙作用,而庄子则肯定道遍在于万物,并已然具德于天地之中的实存性。”[2]
正是因为道的普遍性和内在性,道除了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意义,还获得了价值关照的意蕴,这就是庄子之道的第三个涵义:价值论意义上的道。庄子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世间万物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点,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合理性与独特价值。无论是巨大的房梁(楹)还是细小的草茎(莛),无论是公认的美女还是丑人,即使是各种稀奇古怪,它们都以道为内在规定性,在道的层面上无疑都是相通的。所以面对经验世界的差异性,“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庄子·秋水》)从万物普遍内含并体现道而言,万物都是相通的,无所谓贵贱差异;如果视角转换到从具体事物的个性特点看待万物,那就会呈现差异性和排他性,至于视角为流俗所左右的话,评判的标准则完全被外界所控制。在庄子看来,“以物观之”导致人执着于界限和分别,从而为变动不居的现象界所迷惑,无法获得真实的认识。“以俗观之”导致人的判断标准为成心所左右,站在预设的立场上看世界,同样也是失真的。“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庄子·齐物论》)经验世界的大小、寿夭和成毁各有其价值,且在不断转换变化,在有道之人看来这些都是内在相通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下,作为万物内在规定性的道,又具有贯通万物的作用,对于人扬弃和超越分化的经验世界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
概而言之,庄子之道内涵丰富,既有对老子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发展。但无论是宇宙生成论、本体论意义上的道,还是价值论意义上的道,在庄子思想中最终都汇聚为最高的认识真理和理想人格目标,成为人走向理想存在形态的根本遵循。庄子指出:“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庄子·齐物论》)是与非、生与死、可与不可都显示了经验世界分化和迁流变动的表象。人如果为这些表象所牵动,便会沉溺于变动不居的现象界,无法获得最高的认识真理。庄子主张人应该转换认识视角和参照系,首先破除是非和执着,超越分化和变动来审视事物;其次是“照之于天”,获得道的认识视角和精神境界,看到生死与是非的转化,进而通过彼中见此、以此明彼的全面视角,消除界限和藩篱跨越是非、可与不可;最后是体悟到大道融合、万物一体,就相当于立足在宇宙的枢纽之上因任生死、是非的变化,是者还其是,非者还其非,使天地万物的本真状态自然呈现出来,这就是“因是”。总之,从“照之于天”到“因是”,体现了人之存在从破除执着和分界,到顺应是非的转化变动,再到跳出是非、驾驭是非的真理性认识的完整过程。当然,在这个真理性认知过程中,人的认识活动与人的境界培养是相互作用的,祛除成心、破除执见、扬弃是非,既有认识视角的转换,也有对道的不断体认,需要认知主体做得道的修养工夫,摆脱名利、是非、生死等生命的负累,与道合真。如此一来,千差万别的世界自然而然便以齐通和谐的景象呈现出来,有限的生命也会完全融入大化流行之中,获得逍遥游的境界。
综上,庄子之道的宇宙生成义、存在根据的本体义和道通为一的价值义,共同构成了庄子扬弃分裂,达到理想形态的遵循与法则。因此,在庄子思想中如何获得对道的真正认识,成为人走向合理性的关键一步。那么,如何获得对道的认识,就构成了庄子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庄子认识论在表面上表现出了极大的悲观性的特点,庄子借孔子之口表述为“道之难明”。当然,关于“道之难明”的特点,庄子还有很多其他表述,如“道不可言”“道不可闻”等。此处用“道之难明”来概括庄子认识论的突出特点,在于“道不可言”等都可以理解为“道之难明”的具体表现。同时,“道不可言”在庄子那里具有多重意义,因为庄子最终还是要“言”道,只是言的具体方式和内涵有很大不同。
强调“道之难明”作为庄子认识论的突出特点,具体表现为:庄子认为,一般经验知识的认知方法在对道的把握上是无力的。一般的认知方法在于通过分别、差异等来把握具体的存在。但是,“道无私,故无名”,道是以“齐”和“通”为其内在规定性,不是有形体的具体事物,显然无法给予“名”。与此相联系,“道之难明”进一步体现为道和言的张力。“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在庄子看来,“闻”“见”和“言”都在感性对象和具体殊相范围内发挥作用,道属于无形无象的形而上存在(不形),指称有形之物的“名”,无法加诸其上。就此而言,庄子对语言能否把握道的问题上提出了责难,将主体的认识活动与道的获得,认识能力、认识方法与认识对象,能知与所知之间的矛盾揭露出来。
二、极物之知及其困境
认识活动的前提由认识主体和客体两方面要素构成,认识活动的发生就是认识主体运用一定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方法作用于客体。只有采取正确或恰当的认识能力和方法,才有可能准确把握认识对象。例如,在康德哲学中,“物自体”是隐藏于现象背后的“超验”之物,人的理性能力和理性方法无法把握和认知它。如果人类的理性能力非要超越自己的经验界限去认识“物自体”,就会产生二律背反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庄子之所以突出“道之难明”,就在于他深刻地揭示出了人的一般认识能力和认识方法的局限性,从而为超越或解决这种局限性,获得对道的体认做好前提铺垫。下面先讨论庄子对人的一般认识能力及其局限性的分析。关于人的一般认识能力,庄子概括为“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庄子·则阳》)人的语言的界限,认知能力的极致,仅仅是作用于具体的事物,极物之知“意味着经验之知无法超越经验对象”[1]100。被限制于经验世界的极物之知,在庄子看来,具有如下的特点。
从认识活动的客体即所知来看,极物之知不具备确定的内涵。极物之知以具体的“物”为认知对象,只有认识与对象相符合,才能获得确定的内涵。但现实是具体的“物”处于不断地流动变迁之中,瞬息万变,“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庄子·齐物论》),不具有确定性。所以,庄子说:“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以待者,特未定也。”(《庄子·大宗师》)认知必须要有所依赖的对象才有确定的意义,但是所依赖的对象却是变幻不定的。人的言说能力也是一样,“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庄子·齐物论》)言说不是漫无目的的吹风,必须有一个言说的对象,但是言说的对象变动不居,语言就无法表达确定的内容。庄子感慨道:“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天道》) 用眼睛看而可以看见的,是形和色;用耳朵听而可以听到的,是名和声。可悲啊,世上的人们确信形、色、名、声就足以获得事物的实情!形、色、名、声实在是不足以获得事物的实情的。形与色、名与声都是经验世界展示给人的认识材料,是呈献给“能知”的“所与”,这些感性材料是不能反映事物的实情的。庄子的上述看法,不但讨论了经验世界的不确定性,还涉及现象与实在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所与”是否是客观的呈现,二者是否一致的问题。正如《逍遥游》中“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巳矣”。天展示给人的形色是否真实地呈现了天的本然状态,九万里之上的大鹏看到的大地的形色是否也是大地的本然状态。庄子的质疑不仅揭示了经验世界变动不居的不确定性,还反映出不同的认识主体在认知过程中对认识材料有不同的感受,也无法找到统一的判断标准。
这就是庄子对极物之知特点的又一看法,即从认识主体能知来看,极物之知没有统一的标准。庄子指出:“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在经验领域,针对同样的认识对象,不同主体之间出现了完全截然相反的认知结果,难以获得统一的认知标准。不仅如此,“感知层面的以上困境,同时也制约着广义的价值判断,与何为‘正处’、何为‘正色’、何为‘正味’都无法以统一准则加以判定一样,对价值领域的仁义、是非,也难以作出确定的判断。”[1]101极物之知在认识主体方面难以形成一致的判断标准,极物之知的是与非问题也同样难以获得确定性。庄子以辩论为例:“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庄子·齐物论》)庄子认为,你我两人辩论中,各有自己的认知标准,不能明辨孰是孰非,如果请来第三者来评判“或者与你的观点相同,或者与我的观点相同,或者与你我都不同,或者与你我观点都相同,不论哪一种情况,这个第三者都不能对你我的意见分歧作出正确评判。”[3]庄子上述的看法,从逻辑层面或者认识论上来看,的确存在异类不比和标准绝对主观化等问题。但是从庄子的责难来看,庄子对认识活动成立与否的考察中,对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做了自觉性的考察,揭示出了认识活动与认识能力、认识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经验之知和主体认识能力问题的探讨,也反映了庄子对当时儒墨两大显学的认识论的批判与反思。
庄子对极物之知的讨论,不仅体现了他个人对认识活动的思考,还有深刻的时代学术背景。当时百家争鸣,“天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庄子·天下》)各学派都认为自己掌握着绝对的真理,不容质疑,相互辩驳。特别是儒家和墨家两大显学,对各自的理论都相当自信,对人类知识的正确性都表达的不容置疑的确信。儒家认为,存在“生而知之”的圣人,即使普通人也可以“学而知之”。孟子更是坚定地认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加以扩充即可培育出“智”。墨家提出判断知识对错的“三表”法则。“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认为前人的间接经验(有本之者)、当下的直接经验(有原之者)以及实际效果(有用之者)三条标准就可以判断是非。儒墨两家带有独断论意味的认识论思想,导致了两派学者固守各自的标准,相互攻讦,是非之争甚嚣尘上。这一现象在庄子看来,儒墨的是非之争,除了反映出了极物之知的特点外,还显示了极物之知还会被成见、价值观等外在因素所左右。庄子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道是如何被遮蔽而有了真伪之分?言论是怎样被遮蔽而有了是非之争?道自本自根、自古已存,如何变得不存在了?言论怎么有会有不可的呢?原来道是被小的成就所遮蔽,言论是被浮华之词所遮蔽。所以,才有了儒家和墨家的是非之争。他们各自都肯定对方所否定的,否定对方所肯定的。显然儒墨两派的纷争除了各自的所见不同之外,还附加了主观的态度、学派立场、集团利益等外在因素。用郭象的话来说,就是“各私所见,而未始出其方也”[6]71。儒墨两家都没有突破各自学派的藩篱,企图以一隅之见而涵盖大道流行,这就是庄子所谓的“成心”。“成心”即成见,成玄英解释为:“夫域情滞著,执一家之偏见者,谓之成心。”[6]68庄子认为,极物之知之所以以自我为中心,引发无数主观是非的纷争,产生武断的态度和排他现象,归根结底在于“成心”作祟。极物之知本身便有所限,现在又与人的成心结合,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的对立、冲突和界限,企图以极物之知获得对道的体认更是愈来愈疏。
因此,极物之知本身的不确定性、标准的主观性以及受“成心”干扰等特点,决定了这种认知方法对于把握以“齐”“通”为特点的道是无力的。但是世人又认识不到极物之知的特性,都以为运用自己的认识能力可以达到真理性的智慧。这在庄子看来是对极物之知的误用,不但不能真正体认大道,还会陷入困境,乃至影响生命的和谐。庄子通过“大知”和“小知”的区分予以说明。小知“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庄子·齐物论》)。秉持“小知”便是极物之知,狭隘且好辨是非,窥伺攻击对方的不足如利箭一般迅速,在守护自己的缺点时如盟誓般静待佳机。人一生中的是非之争就像这样不停地攻守变幻,以致生命的朝气与活力消磨殆尽。他们沉溺在无休止的是非之争中,无法使他们恢复生机。世人皆以为自己的“小知”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并为之不遗余力地辩驳。但是这在庄子看来,小知或极物之知不仅是对道的遮蔽,不能体认真正的道,还是对生命的戕害,既误解了“道通为一”,又破坏了“道之真以治身”。庄子感慨道:“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庄子·齐物论》)世人竭尽心智去谋求一致,而不知道本来就是相同的,无非是大家都以自己的极物之知为绝对真理,以偏概全,才造成了朝三暮四的笑话。庄子以否定性的态度分析极物之知的特点,运用能知与所知的矛盾揭示出了极物之知是对道的割裂,并非把握和体认道的正确途径。以儒墨为代表的辩者错用极物之知,秉持成心来谈论大道,不但不能澄明道,而且造成了是非难定、生命受害的困境。
庄子正是由此出发,感慨“道之难明”,在认识论上极力宣扬“知有所困”和极物之知的不可靠。一方面,庄子对极物之知的否定态度,忽略了所知与概念的相对静止所内含的确定性,割裂了知识和智慧的相关性与互动性,庄子之见有其自身之蔽。但另一方面,庄子“一再追问以何种方式才能知道、安道、得道:‘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对道的如上关切,同时也使形上之知如何可能,在庄子那里获得了优先性”[1]107。这显示了庄子通过区分极物的知识和体道的智慧二者之间的差异,为其探讨如何体道提供了逻辑起点,在认识论上深化了如何获得形上智慧的问题的讨论。
三、体道方法论之重建
极物之知和言说能力是人之所共有、共用的,但是在庄子看来,它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其无法完成体认大道、认识本真的任务。“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异便。此势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世界万物本身就是参差不齐的,从小的视角去看大的部位是看不到全面的,从大处着眼去观察小的部位是看不确切分明的。“精”可谓是微小的极限,“垺”是广大的极致,无论是小到极限还是大到极致,都是有边界限制的有形之物,至于无形无象的东西,便是数量也无法再分了;没有外围的东西,便是数量也不能穷尽了。因此,可以用语言议论的,是事物的行迹;可以用心意从推测的,是事物的无形属性;至于语言无法讨论,心意无法揣测的,那是不期限于精细粗大了。有形的可以成为语言的对象,精微的可以通过心意思虑所得,至于无始无终、无形无象、周遍万物的道,是无法为认知与言意所传达。论述至此,庄子认识论在如何体认道的问题上,发挥的是破坏性的作用,杜绝了人们企图通过极物之知和言说来体道的可能,突出了“道之难明”。当然,庄子认识论的作用不仅限于破坏,否则他本人也无法解释一方面阐明“道之难明”,另一方面又宣扬“妙道之行”的矛盾。如果说揭露极物之知的困境是“破”的话,庄子对如何得道的讨论,便是他在认识论上对体道方法论的重建。
首先,消除极物之知对体道的破坏。第一步是“知止”,限制极物之知的误用。庄子认为:“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庄子·齐物论》)古时候的至人,他们的知识有个界限,这个界限在哪里?宇宙初始未曾成形万物时,便是知识的界限,到了尽头了,不能在增加了。次一等的人运用知识只是认识到事物存在,并不区分事物间的界限差别。再次一等的人,认识到了事物的差别,但不做是非好恶区分。一旦运用极物之知划分是非,道就受到了亏损。在这里,庄子界定了极物之知的范围,强行运用极物之知类似于“理性的僭越”,必然造成错乱。因此,庄子提出“知止乎其所不知,至矣”。“知止”的观点打破了对认识能力的盲目自信和知识的绝对化、终极化。“知之所至,极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庄子·徐无鬼》)限定极物之知的界限,将是达到不随波逐流、不因成毁而变、不被议论所左右的睹道之境的第一步。
在“知止”的基础上,下一步便是弥合极物之知的分裂作用,还原道通为一的景象。用庄子的词汇来表述,便是通过“和之以天倪”“和之以是非”,达到“天均”进而实现“寓诸庸”。“‘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庄子·齐物论》)“天倪”普遍解释为自然的分际,什么叫用“自然的分际”来弥合是非?任何事物有其“是”的一面,便有“不是”的一面,有其“然”处必有其“不然”处,极物之知只是看到其部分内容而以偏概全,便造成了主观的分裂。如果摒弃极物之知的分裂,以自然的分际看待他们,“美者还其美,恶者还其恶;不以恶掩其美,亦不以美而讳恶,则美恶齐矣。是者还其为是,非者还其为非,不以非而绌是,亦不以是而没非,则是非齐矣。”[4]不过当、不违则,无所偏倚,弥合分裂,达到“天均”自然的均衡。如此看待万物,则“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人可以自由的因任驾驭是非、大小、可与不可,万物一体、道通为一的智慧之境自然显现。
其次,消除“成心”对体道的遮蔽。要想彻底革除极物之知的负面影响,还必须清理“成心”对体道的遮蔽。庄子提出:“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井里的青蛙不可以与它谈论大海的广大,这是因为受了空间地域的限制;夏天的虫子不可以和它讨论冰冻的事情,这是因为受了时间的限制;见识短浅的学者不可以和他谈论大道,这是因为被他所受的教育和观念所束缚,束于教的曲士就是被成心所遮蔽的人。人的认识一旦被成心所搅扰,则“是非判断无法脱离主观成见的干扰,都带有一定先设的立场,偏执于一端永远无法达到真理性的认识”[5]。因此,庄子认为:“如是,则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虽有至知,万人谋之。鱼不畏网而畏鹈鹕。去小知而大知明。”(《庄子·外物》)庄子要求人必须刨除成心,达到“吾丧我”和“坐忘”的境界,即荡涤心中已有的束缚和成见,心智空灵才能获得入道之门。如此便可实现“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没有成心,是非之争、割裂统一的根源就被拔除,所以郭象解释为:“未成乎心,是非何有生哉?”[6]68
无论是消除极物之知对体道的破坏,还是消除“成心”对体道的遮蔽,这样高妙的境界,庄子善于运用高超技艺的描写使之形象化、具体化,通过“技进于道”体现道的自本自根、圆融齐通、周遍万物却又真实存在的玄妙。高超技艺的实践不仅涉及技术的主体化,而且体现了对象的主体化。技术的训练过程,同样是主体逐步深入客体,客体的本性逐步敞开的过程。因此,经过反复训练和日益成熟,技术成为了自然与自由统一的活动,在“技”的沟通下,人与物、天与人达到了和谐统一。无论是“庖丁解牛”还是“轮扁斫轮”,这种能够见道的高超技艺,无不体现了对分裂、界限和成心的超越。庖丁“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庄子·养生主》)。抛弃官能的干扰,以心神领会,又完全遵循牛的生理规律,虽然有人的活动,但是主客体之间完全融为一体,当下整个世界呈现为统一的整体,没有主客之别,没有天人之分,完全一派道之流行。以“技进于道”的形式描述体道的过程,一方面,庄子为自己构建的体道之知提供了类似于实证化的证明,增强了可信性;另一方面,庄子通过寓言将自己重建的体道方法论予以具体化、形象化,为描述高远玄妙的道找到便捷门径,而这又涉及到庄子体道方法论的最后一项内容,即如何言说道。
最后,建立“三言论道”的言说方式。极物之知割裂了道的齐通,以极物之知为内容的言论同样是对道的疏离;极物之知有其发挥作用的界限,言论同样也非无所不能。“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庄子·天道》)世人所珍贵的道记载于书中,书不过是语言文字化的物质形态,语言是有其可贵之处的。可贵的是其中蕴含的意义,意义是有所指向的,却不能通过语言来表达出来,世人虽然珍贵于书,但我(庄子)却以为不足为贵。这里的“意”可以理解为道或者根本性的存在,它是无法通过语言来传递的。既然道不可言,那么庄子又是如何言说他的体道之知的呢?庄子主张通过用寓言、重言、卮言的形式来谈论道。“三言”都非就事论事,而是假托其他人与物、借重先贤和没有成见的无心之言来表述。“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①郭庆藩《庄子集释》中“终身言,未尝言”的“未尝”下有“不”字。王叔珉在《庄子校诠》中指出:“‘不’字疑涉下文‘未尝不言’而衍。古钞卷子本、道藏成玄英疏、林希逸口义、褚伯秀义海纂微、罗勉道循本诸本皆无‘不’字。”笔者以为王说为是,故从之。;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庄子·寓言》)没有语言的分割作用,万物之理是自然齐同的,自然的齐同如果加上人主观的言论便是有差别的了,把人主观的言论加之齐同之理上便是不齐同了,所以说要发没有主观成见的言论。即使是终身说话,却像不曾说过;即使终身不说话,却也未尝不在说话。庄子这番言论的意义,重在通过“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警示世人不要拘泥于语言的本身而忽视了对言外之意的把握。所以,庄子提出:“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语言只是体道所借助的工具,拘泥于语言就会忽略道之本真,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就是可以与之谈论大道的智者。
四、结语
庄子在认识论上一再宣称“道之难明”,但并没有倒向绝对的怀疑论。他虽然极力责难极物之知,对人的一般经验认识能力进行了限制,但在批判极物之知的同时,又构建了自己的体道之方。庄子在体道之方的构建中,特别突出了“技进于道”的领会方式与“三言论道”的言说方式。关于“技进于道”,庄子注意到了在高超的技艺操作中,实践主体难以用语言再现自己的操作过程。实践者对技艺的核心要领是在自己实践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其中得心应手、与物无间的微妙感受很难通过言语系统表述出来。关于“三言论道”,庄子集中探讨了“言”和“意”的关系问题,并提出“得意忘言”的观点。在言意之辩中,庄子认为,语言系统是获得意义的工具,滞留于语言本身是无法达到对“意”的认知。庄子在认识论上对言语系统无力的揭露,恰恰契合于波兰尼对默会认识形式的发现过程。庄子在认识论上区分道的认知和一般经验知识两重形态的特点,也与默会认识多有相通的内容,显示了庄子哲学蕴含的丰富内容和持久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