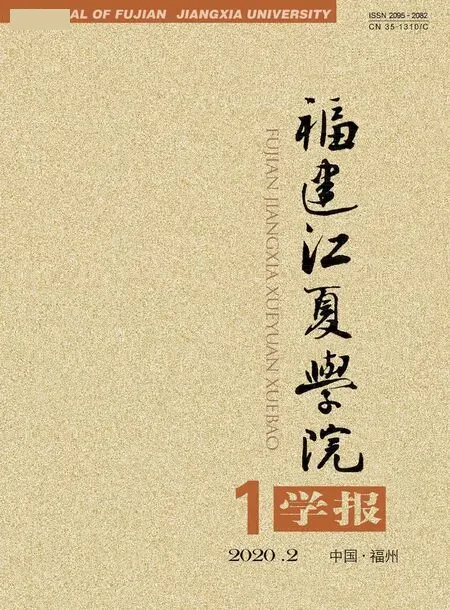郑振铎的文博思想及其贡献
陈振文,高朝华
(1.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院,福建福州,350108;2.福建江夏学院人事处,福建福州,350108)
郑振铎(1898—1958)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也是现代著名藏书家、考古学家。1949年后历任全国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是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郑振铎的文博思想集中呈现在国家文物局党史办编辑的《郑振铎文博文集》和郑振铎子嗣郑尔康编辑的《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全面总结郑振铎的文博思想,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郑振铎在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等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生态文明建设、文明交流互鉴等重要论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迎接2020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福州举办,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关文物概念、性质、价值的论述
随着近现代考古学、博物馆学的兴起,文物的概念在不断发展,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在旧时代,“古物”“古董”的把玩与收集是名士派生活之资、自娱自乐之物,它们被消极地“保存”,不能物尽其用。郑振铎批判过去有人把文物当“古玩”“古董”,或当“瑰宝”,占有了文物即占有了“学问”等错误认识。从研究对象的外延来界定对象,也是下定义的一种方式。郑振铎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对“什么是文物”划定了范围,分为“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两大类。“可移动的文物,范围很广,包括:古代刻本、抄本的图书;清末以前的绘画,著名人物的手迹(包括原稿、信札等),玉、石、木、竹、骨和象牙的雕刻,各种木制家具,各种丝、麻、棉、毛织品;古代的玉器、铜器、陶器;各时代的瓷器;各种革命文物,以及许多工艺美术品等等。不可移动的文物,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地上的,包括革命建筑物、古代建筑物和宫殿、城墙、园囿、庙宇、名人住宅、民居、牌坊、石柱、石窟、摩崖雕刻、石阙、碑碣、陵墓等纪念物;另一类是地下的,包括古墓葬和被毁、被淹、被废弃的古城、古宫殿、古庙宇等古文化遗址。”[1]239
对文物进行分类,是文物研究首要、基础性的工作。分类标准的不同,对不同学科领域研究的价值也不一样。按时代分类,对通史、断代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按功用分类,对专门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按属性分类,对人文、艺术研究有重要价值;按价值分类,对文物的保护有重要价值;按存在形态分类,对文物的保护、研究和陈列的价值比较明显。郑振铎以文物的存在形态来划定文物范围,是作为文物工作领导者、学者在文物认识上的体现。
郑振铎深刻阐述了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首先,他认为文物具有历史的、文艺的和科学的价值。[1]184历代的文物是中国人民最高的艺术创作,足以表现民族文化的最可夸耀的成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不仅可以说明先民生活的时代、历史发展的过程,通过对其分析还可以解答许多历史上的疑题。[1]79其次,他进一步论述了几种价值之间以及“文”与“物”、“文献”与“文物”的关系。郑振铎指出,过去很多学者偏重“文字”,很少想到以实物来说明历史问题,无形中就把很多艺术品埋没了。[1]124正是有了科学价值才使得文艺价值得以保存。在这里,他实际上也指出了考古发掘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也就是他在学术研究上长期推崇的重“实证”和“田野”调查。再次,他把文物的价值与创造新文化联系起来。文物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承载着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可以为我们创造现代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提供养料。文物作为先民创作的伟大成就,也是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形式。我们要通过那些文物“建立起整个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的系统来”[1]79。正如他在《保存古物刍议》一文中所指出,人类的进展在文化上表现得最为真切。每一个时代各有那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每一个民族也各有其特征。“文化是禅递不断的,像抽刀断水似的,水是永远的‘更流’着的。每一个民族文化的特征,最好的表现,便在各时代遗留下来的古文物、古文书上……凡对于人类文化、民族文化有一点爱护之心的便都会爱护这些自己民族所遗留下来的古文物、古文书。”[2]563郑振铎对文物价值的认识是全面的,也是现代的。当下,在概括文物的价值时,也仍然表述为文物“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3]585。他对文物价值、作用的深刻理解进而形成的文物意识,也深入影响到他的学术活动的方方面面。郑振铎充分意识到文物作为真切、形象、生动的信息载体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自觉将文物保护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将文献与文物结合起来研究历史、说明历史,“让文物活起来”。这在学术研究领域有着开创性意义,也正是1952年他创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时将其开设在历史系的缘故。
二、有关文物保护、发掘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论述
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注意和重视研究文物和现代考古学。他想起庚子之祸,提起《永乐大典》的散佚,心如刀绞。他读格鲁威特尔、勒·柯克、史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诸家的考古著作、报告书,对列强掠夺的经过仿佛历历在目。得悉格鲁威特尔等人先后四次从西域运走大批古壁画后,他感到痛心疾首。他感叹,这样下去“恐怕连祖宗的喜神也有保守不住”[1]36,甚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汉慕义博士所称的“渠预料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以求深造”[1]36的话,也可能迟早应验。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郑振铎在文物上的认识,还主要出自个人的研究兴趣和满腔的爱国情愫,更多的是从感性的、零星的认识而走向学院式的,那么,在他作为主管全国文物工作的学者型官员后,则站在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的大视野来认识文物,并逐渐全面、丰富而系统化。
(一)开创新中国文物管理制度顶层设计
郑振铎在文物领域的收藏之丰、保护之功、知见之广,早为中共高层所识。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际,即被周恩来总理邀请作为代表参加会议。会上,他提出了文物保护的意见。此前,他还作为即将建政的新中国的代表,去巴黎(后改为布拉格)出席“世界和平大会”,沿途访问了捷克、苏联,参观了各类博物馆,返程时写了三篇文章,“一为普特(布拉)的国立博物馆,一为苏联作家协会,一为夏宫”[4]395,可惜《郑振铎全集》没有收录。从日记推测,这些文章应该是有关文物方面的。
郑振铎对中国文物事业的贡献,首先是建立文物的法令法规。作为第一任文物局局长,他主持拟定了关于征集革命文物、关于保护古文物、古建筑等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确立了我国文物法制建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框架,使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纳入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对依法保护文物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保护我国文化遗产,防止珍贵文物和书籍流出国外,制定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1950年5月24日);为保护名胜古迹和藏于地下、流散各处的珍贵文物图书,制定了《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政文董字第十三号,1950年5月24日),并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作为经常性的文化建设工作;为征集各地区所有革命文献与实物,制定了《征集革命文物令》(政文董字第二十四号,1950年6月16日)等。这些法令、法规由中央批准,并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明令颁布,使新中国的文物保护有了可以依据的法律法规。
他还建议将各项保护和征集文物的法令加入土改学习文件中,并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在他看来,保护文物不仅是为了保存、保护先前的文化、艺术遗产,更是为了发展将来的文化、艺术。[1]274-275所以,人人都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他都给予了极大关注,不仅“缂丝”“宋锦”“南京缎”“漳绒”等工艺美术品要保护,而且包括制墨、手工纸、装裱等传统技术,“一切美好的,有用的,有益的绝技、绝活,我们都必须继承下去……发扬光大。”[1]370
(二)构建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单位”长效机制
郑振铎主政国家文物局的十年间,有关文物保护方面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一是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发掘的关系;三是“化私为公”乃保护文物之上策;四是坚持保固和恢复旧观的修整原则。[5]其中,提出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的关系,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建设如火如荼。基建过程中如果不注意文物保护,极有可能在打开“地下博物馆”之门,伴随“惊人发现”之时,让大量珍贵文物在铁锹、推铲机下惨遭“惊人的破坏”。鉴于这一顾虑,郑振铎及时沟通文物单位与基建单位的工作配合,并且从制度建设上给予保障。《基本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和作用》《考古工作与基本建设的关系》等文也集中反映了郑振铎的这些思想。
郑振铎对中国文物保护的可贵贡献,还在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单位”长效机制,使我国不可移动文物逐步走上“有效管理、有效保护”的轨道,开创了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文物事业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除了成立各级各类文物管理机构外,全面强化依法治理、保护文物。截至1954年底,国家相继颁发了十多部有关文物保护的命令、办法、指示和通知,强调、明确了保护文物的重要性和保护范围,扭转了旧中国法制缺失和长期战乱造成的文物流失、管理无序的局面。但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也面临着严峻考验,经历战火洗礼幸存下来的文物遇到了建设性破坏的新难题。该采取什么措施对各类文物,尤其是分散各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有效、安全的保护与管理就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1953年10月,郑振铎起草了《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53)政文习字24号〕,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保证了基本建设工程中文物免遭破坏和损失。1956年4月,又发布《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国二文习字第六号〕,明确提出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择其要者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推行“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制度,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管理办法。
虽然最初的“文物保护单位”主要以建筑和艺术价值明显的点状物质性建筑、遗址为主,但其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遗产保护体系,最大限度地维持了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虽然早期各级各类“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只占总量的六分之一,但集中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创造的最高成就,与各级馆藏文物、民间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五彩缤纷的“中国符号”系统。公布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对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实施有效保护的一种制度创新。从解放初实行至今,为近十万处文物古迹的生命延续提供了坚实屏障,成效显著,功绩卓卓。[6]近年来,“文化线路”作为世界遗产名录中的重要类型备受关注。虽然最初的“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并不完善,却较早在事实上涵盖了与“文化线路”有关的要素,其保护理念和保护成果惠及后世,为我们今天整合区域旅游资源,乃至中国“文化线路”申遗都奠定了坚实基础。[7]作为这一功绩最初制度的设计者,郑振铎功不可没。
此外,郑振铎还强调在文物保护上要有整体意识。“古代壁画的存在和古代建筑的存在是相依为命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许多古代壁画便是这样地被保存于古建筑,与它们显得相得益彰,同时,也放射出它自己的独特的光芒。”[1]387
在郑振铎的主持领导下,全国文物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和良好的社会影响。据统计,1949—1955年间,基本建设中出土的文物达219201件(不包括零星陶片),包括修建成渝铁路时发现了第四位更新纪晚期的人头骨化石和大量汉代文物、修筑黄河三门峡水库时发现了200多处从新石器时代到元代的遗址和建筑、地方基建工程中发现了两汉、三国墓葬等。[8]1954年5月12日—11月8日这些出土文物中的精品3760件在故宫午门大殿举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出土文物展览》得到了集中展示。之后,郑振铎还主持编辑了新中国第一本全国性的出土文物图集——《全国基本建设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这些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三)联动实施文物保护和文物发掘
作为文献学家,郑振铎在古籍鉴定上的成就和眼力,文献工作者耳熟能详,当年鲁迅就非常欣赏。在其他古文物的鉴定上,郑振铎也有着独到的识见。辨认地下有无古墓葬或古文化遗址,他以泥土的颜色、土质(灰层)、夯土等为主要特征。他认为,“一个时代的文物,都有一个时代的特征”,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最习见、最常遇到的东西”,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殷朝的饕餮、汉代的瓦壶和五铢钱、六朝的青瓷、唐代的马佣等等,依据这些有时代特征的物件去辨认古代文物的年代,相信“不会相差的很远”。[1]252-254他还提出,要“建立正确的鉴定制度”,“成立学术委员会”,“做到任何一件藏品都成为可靠的科学研究的依据与基础”。[1]320-321
对文物的发掘工作,郑振铎始终持谨慎、科学的态度,他极力劝阻定陵的发掘,就是典型一例。他强调文物发掘要在特别考虑技术条件的前提下,注意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联合起来,做有系统的,有意义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1]8这一认识是科学而积极的。时至今日,这一重要观点仍被文物工作者奉为圭臬。因为多数重要遗址由于具有占地范围大、埋藏一般较浅、可观性相对较差等特点,被破坏的危险性往往最大。科学的态度是:在不具备技术条件下,可挖可不挖的古遗址、古墓葬,首先应加强保护,暂不发掘。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近些年来,社会上仍存在一种倾向,急于对重要遗址、古代帝王陵墓进行发掘。这种脱离我国社会经济和文物保护水平的盲目发掘,实际上是一种破坏。当然,郑振铎也不是消极地对待发掘工作,他认为单靠偶然的发现是不够的,而且是靠不住的,因为:“第一,不知古物从多少深的泥土中掘出来的,因此,我们便不能断定其时代;第二,给惯于作伪的古董商有了作伪的机会;第三,同时被发见而农夫们视为不足轻重的古物,一定被毁坏了不少;第四,在许多次的偶见的发见中,其幸得为学问界所知者又百不过六七,其余的或为农夫们所随手抛弃,或辗转的入于市侩之手,或为当地官吏所夺取,从此不再见知于世。”他还动情地说:“谁要是有意于这种的工作,我愿执锹铲以从之!”[1]7-8
在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发掘的关系上,郑振铎特别强调要重视在基本建设中进行文物发掘。他提出,基本建设人员不仅是工程师、建筑人员,也应该是考古工作者。[1]231鉴于当时比起浩浩荡荡的基建队伍,考古工作队伍的力量实在太有限,为了不耽误基本建设的步伐,他提出文化部门要参加“规划”,同时,“先遣队”要走在基建工程队之前。这些认识无疑是宝贵的。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文物发掘,仍然是当下文物发掘工作的主题。在这些年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的考古发掘中,绝大多数属于配合基建,包括在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重点建设中,考古与文物保护都被纳入了工程规划。
(四)多渠道、多形式培养文物人才
郑振铎非常重视文物人才、新生力量的培养和专门人才队伍建设,来为文物保护提供有力的技术、人才支持。他提出,要“设立图书馆专修学校,并与各大学历史、建筑等系联系、合作,多培养文物工作人才”[1]75。他还主动到基建部门为工程技术人员作《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与作用》报告,特别阐明古代文物是古代的物质文化,是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可供作为“推陈出新”之用。为普及文物知识,宣传党和政府的文物保护政策,他还通过科普协会举办讲座,亲自授课。在郑振铎的倡议下,1952年北京大学设立了考古专业,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他还亲自给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上了第一课——《中国美术史》。此前,虽早在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下设有考古学研究室,但并没有作为独立的学科专业来建设。如今,这颗种子已经长成大树,成为国家该领域唯一的重点学科。1983年,考古专业从历史系独立出来,扩建为考古学系。1998年,北京大学再次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办学,成立考古文博院(后改名考古文博学院)。也是在他的协调组织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北京大学历史系,在1952—1955年的四年间,合办了4期为期3个月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参加学习者达341人。[9]1这些由各省、市抽调学习的青年干部,后来分配到各地从事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成为了文物战线的骨干、专家。在掌握专业知识上,“要专精一门,通许多门。”他是这样要求,自己也是那样的广博。郑振铎在考古、博物馆学学科建设上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值得深入探讨。
三、有关博物馆性质、功用和陈列等方面的论述
郑振铎对博物馆早有研究,其旅欧日记中20多次提到博物馆并加评论。《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也多有提及。作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郑振铎确立了博物馆的性质和主要任务,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博物馆有关文物的鉴定、修整、保管和陈列等一系列工作的原则与方法,为中国现代博物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确立了博物馆的性质、任务和工作原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已和图书馆一样,成为人们获取新知,提升自我的场所。博物馆教育对观众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博物馆的建筑环境、参观环境和人文环境这些非直接说教的方式来感染、熏陶、激励、启迪观众的。郑振铎在旅欧参观“圣特里尼礼拜堂”时就被其建筑之华丽、内部之装饰、器具之陈设所迷醉。他批评了为考古而考古、为古典文学而古典文学的错误思想,提出“让古人为今人服务”、博物馆要摘掉“闲人莫进”的牌子,让文物走向大众、服务于大众,真正实现文物的价值。
在1956年召开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郑振铎“开幕词”(提纲)的题目即“博物馆事业应该为科学研究服务”。他批评旧式的博物馆仅是“古物陈列所”,提出在新时期博物馆既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和自然标本”的收藏所,也是科学研究机关,具有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与征集保藏文物标本的特性;同时,强调这三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科学研究不能离开它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收藏文物、标本工作”“科学研究保证了文化教育工作的质量”[1]214-215。
在这次会议上,明确了博物馆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怎么为科学研究服务,他进行了具体阐述:第一,要建立鉴定制度,分辨真伪,并对考古发现加以科学的整理,使每一件藏品都成为科学研究的依据;第二,要发动群众开展搜集,丰富藏品,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第三,要建立健全保管制度和陈列方法,更好地为研究提供服务;第四,除了不能时时暴露或开阖的最珍贵的古文物之外,要充分公开各种重要藏品,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参观、参考的便利;第五,要尽量供给科研院校以藏品的照片、拓片、复制品和各种记录性的文件;第六,要成立专门的学术委员会,延聘馆内外的专家。[1]320-321在会议总结报告中,他还进一步强调,“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两项基本任务是统一的,“有着提高与普及的辨证关系,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也是为科学研究服务,而且向科学进军不只是少数专家的事,需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科学研究服务也是为了长远的人民利益服务。”[1]327-328郑振铎对博物馆性质特点、基本任务的分析和概括,直到今天还是科学且具有指导意义的。
(二)重视博物馆的文物陈列与展览
文物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发挥文化教育功能的主要途径和形式,它的实物性和直观性,展出形式上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人文关怀,是其他教育形式所无法比拟的。郑振铎重视发挥展览陈列的宣教作用。他主持举办过各类型的文物展览,来反映文物保护工作成效,包括个人文物展。他还把博物馆作为科学研究、社会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在这个指导思想下,通过改进陈列,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物的宣传教育作用。他重点推进对故宫博物院的改革,筹建了《绘画馆》《陶瓷馆》等专馆,还亲自起草了《故宫博物院改进计划的专题报告》,指出原状陈列必须选择重点,“应该原状陈列的地方尽可能保持其原状。例如,太和殿……但像坤宁宫,只表现了满洲皇帝结婚的仪式的,便没有必要原状陈列出来了。”同时,在陈列文物种类上也要考虑有侧重点,在故宫博物院“其陈列重点,应该是:中国的美术品和工艺美术品”[1]214-215。他还建议要成立若干专门委员会,来审查陈列设计。正是他精细而周到的考虑,使得故宫陈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份报告(手稿)“处理故宫文物的初步方案”中,他不仅首次提出文物“巡回展”“国际展”这些新概念、新做法,还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展览单元”这种专门化、个性化的展览方式。虽然过去了50多年,直到今天,我们在探讨这一展览样式时,仍然感觉鲜活,富有生命力。
1957年,郑振铎参观访问苏联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保加利亚记卡赞洛克市博物馆,对其独特的陈列方法、设立统一的博物馆委员会、规定修复、保护的措施等印象深刻,在其访问日记中多有记载。回国后从实际出发,吸收国外经验,对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加以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郑振铎还将其重金收购的几百件古代陶俑悉数捐献国家,并倡议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不要购卖、收藏文物。这一倡议后来成为文物系统工作人员的优良传统,并成为新时期国家文物局颁发的文物、博物馆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之一。
四、郑振铎的文博思想具现代性和世界性
郑振铎是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奠基人。从早年游历欧洲,在目睹西方文物的盛貌、扩大眼界的同时,感叹中国文物流落他乡,“楚弓不为楚得”,到后来广泛接触文物考古书籍以及对于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的深入,再到主政国家文博事业,郑振铎的文博思想日臻完善。他主管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十年,“从方针政策、指导思想、队伍建设、业务建设以及出版宣传等各个方面,都为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许多方面是开拓性的。他在文博方面的深刻论述,是“基于对祖国文物的价值和作用的深刻理解,基于对自己伟大祖国的热爱而形成的文物保护的指导思想,体现了文物保护工作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1]15。同时,也正基于他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开阔的眼界,使得他的文博思想更具现代性和世界性。
(一)郑振铎的文博思想是超前的,也是现代的
1928年,郑振铎游学英伦着手编撰《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详细介绍世界近百年来重大考古发现,明确把19世纪中叶之前的发现、发掘与19世纪中叶后的田野考古发掘,严格区别开来,并正式提出了在中国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倡议,同时呼吁“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做有系统的、有意义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1]8。这在当时中国尚无一本考古学专著的情况下,此著作的写作出版需要的勇气和具有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在80年前能提出诸多精辟的见解,更是难能可贵。比如,关于处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关系问题,他把技术条件作为发掘的前提。2002年,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九部委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对“处理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也坚持了这一认识:“必须把对遗产的保护放在第一位,一切开发、利用和管理工作,都应以遗产的保护和保存为前提。”[10]关于保护古城墙问题,郑振铎指出:“凡可拆可不拆的,都要‘刀下留人’。”遗憾的是,对他的呼吁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今“绿树城廓是扬州”的扬州城廓不见,“半城宫墙半城树”的北京画卷失色。[11]
(二)郑振铎的文博思想是广博的,也是世界的
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兴趣于文物和现代考古学。早年的游学开阔了他的视野,据其《欧行日记》记载,旅欧时陆地第一站是马赛,他参观的第一个人文景观就是“郎香博物馆”。旅法期间,他参观各类博物馆达二三十次共10余所。每到一地,他常常是“拿着目录,一个一个房间仔细的对目录看着”[1]34,以文化研究者鉴赏的目光去考察。旅英期间,郑振铎广泛接触了西方文物考古学方面的书籍,激发了他从事考古研究工作的热忱,产生了建立中国现代考古工作的愿望。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为我们揭开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面纱,第一次让国人对世界近百年来重大考古发现有了全面认识。在向国人传播世界文物考古知识的同时,郑振铎也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文化。他曾多次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赴波兰、保加利亚、印度、缅甸、印尼等国访问,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作了专门考察,特别是当地的民风、民俗、历史古迹和博物馆,尤其对印度双壁的石窟群泰姬陵和阿旃陀石窟作了详细参观记录。在保加利亚访问期间,还应主人之邀作了有关“中国文学和中国考古学”的专题报告,从“中国古代神话与传统”到“明清文学”共讲了八讲,向外国友人介绍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密切了中外文化交流。在1957年4月全国学联与国际学联联合举办的“中国古迹名胜学习旅行”班上,他作了《从考古学上所见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报告,从考古学的发现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古代文化。这份报告后来曾用俄、英、法三种文字翻译。
五、结语
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延续和进步的见证,具有不可再生的价值,只有通过有效保护才能世代相传、永续利用。郑振铎的文博思想内涵丰富,格局宏大,目光长远,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和远见卓识,并成为制订文物、博物馆工作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成为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的思想库。逝者如斯,思想长存。郑振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也有重要的论述和丰富的实践活动,限于篇幅,另文阐述。
文博事业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它不仅包括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还涉及考古、文化研究、文化推广、文化体系建设等方面内容。做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让人民共享保护成果,对提升城乡面貌品质有着重大现实意义。2020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郑振铎的故乡福州举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时,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提出了许多重要理念。重新挖掘、研究学习郑振铎的文博思想,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论述,传承、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的创新理念和重要实践,以及把握承办“世遗大会”的重要契机,向世界传播好中国风貌、中国形象、中国精神,坚持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