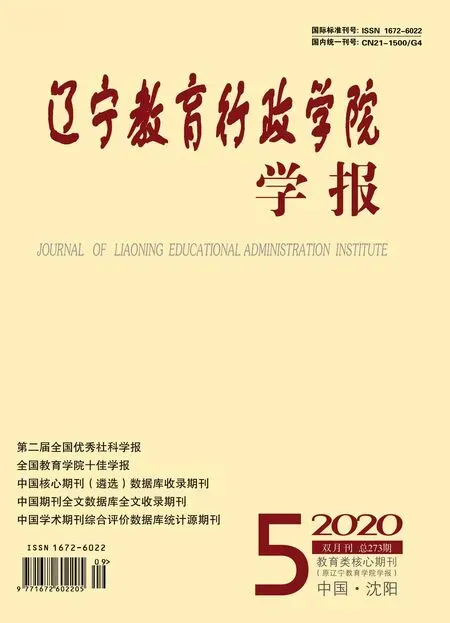人性的探索:狗儿爷生死意识探赜
侯衍楠
云南艺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对戏剧文本的研究,永远无法脱离生与死的主题,而这恰恰也是人性研究亘古不变的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戏剧危机、戏剧观大讨论背景下,戏剧艺术开始对人性进行探索的时期中,刻画出极具中国传统农民典型特点的陈贺详这一角色的《狗儿爷涅槃》应运而生,为中国的话剧史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其创作伊始,至今还没有一部作品塑造出的农民形象能完成对狗儿爷的超越。狗儿爷的悲剧命运源自他的生死意识,生死意识可以解构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物质层面,意指人作为一个生命体,其不可避免的肉身的生与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第二层为精神层面,意指肉身之外,深层意志中的生与死的观念。故本文将从这两方面对狗儿爷的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进行研究,对其命运悲剧予以探赜。
一、物质层面:肉身的生与死
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是生死意识中自然层面的两个重要部分,在对生的欢愉与死的恐惧之中,生死意识应运而生。狗儿爷一方面惧怕年老与死亡;另一方面,身为一个对土地极度热爱的传统农民,在土地与自己的生命之间,可以随时舍却生命,追随于前者,面对肉身的生与死表现出的生死意识,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成熟,已然超脱于普罗大众简单的生死观念。
(一)生命意识
狗儿爷是千百年来始终怀揣着“土地梦”的中国农民的代表,狗儿爷的生命意识,也主要依托土地而显现。地之于农民,如同水之于万物般,乃万物之源头,在农民眼中,世间的一切,都依托于土地给予的营养而得以孕育,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便可以以此孕育出一切,而没有土地,万物都将沦为虚幻。从祖辈开始一直都是农民的狗儿爷对土地有着独特的情感,尤其是村东头风水坡大斜角的二亩地,半沙半胶,经旱经涝,种一斗收八升的宝地,更是将之视若自己的生命。
农民的“土地梦”是宽泛的、模糊的,但在狗儿爷眼中,地主祁永年的“千倾牌”确是实实在在的,狗儿爷的“土地梦”就是成为像祁永年一般的地主,得到了祁家的祖产宝地,狗儿爷离自己的“土地梦”“地主梦”又更近了一步。“咱村要‘一片红’,人家都红了,你狗儿爷不能当‘黑膏药’!”狗儿爷宁愿做“黑膏药”一般的社会毒瘤,也坚决不交出自己的“大斜角”。大斜角原是祁永年家的祖产,因土改分到了苏连玉手里,后又被狗儿爷用三石芝麻换到手里。这块地不仅是狗儿爷眼中“远女儿近地无价之宝”的宝地,更是自己耗尽一生所追求,承载自己全部生命意义的“土地梦”的象征。当冯金花带着虎子与“膏药户”划清界限之时,在与李万江推杯换盏之际,“大斜角”就在迷迷糊糊之中归了堆。狗儿爷穷其一生,冒死在炮火之中收了芝麻,过上了小地主的生活,在扩大“资产”的时候换到大斜角的宝地,却于此时走投无路归了堆,不禁感慨,发出“爹,小狗儿,你白吃啦!”的呐喊,对父亲用生命换来的二亩地的人生意义的怀疑的同时,也是对自己倾注了全部生命意义的“土地梦”的破灭后的迷茫。“大斜角”没了,狗儿爷一直追寻的已然物化成一片又一片的土地的生命意义也随之消散,陷入了迷茫、混沌之中。
子嗣后代一直是中国家庭中家族传承的载体,然而当承载狗儿爷生命意识的“风水宝地”和家族新生生命于狗儿爷面前相互碰撞时,狗儿爷又将如何选择呢?风水坡归了堆之后,狗儿爷还是念念不忘,常去风水坡,而此时狗儿爷的成分也因儿媳妇是“地主”的孩子而不再“良好”。将狗儿爷置入了一个“割尾巴”的两难境地,最后还是靠狗儿爷的前妻、李万江的现任妻子金花而得以让此事不了了之。虽然狗儿爷在此似乎没有做出选择,但他的举棋不定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怀有三个月身孕的女人如果被“割尾巴”后果如何,可想而知,至少孩子保不住是肯定的,然而,即使是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狗儿爷还是无法做出选择,他将鲜活的孙辈的生命、儿媳的生命和一块没有生命体质特征的“土地”化作了等号,并且发出了“眼下还不如从前的”怒吼,可见狗儿爷眼中肉身生命的传承,还是抵不过“风水宝地”所能滋育出的“生命”,狗儿爷的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都是依土地应运而生,抛却土地,狗儿爷的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将无从谈起。
(二)死亡意识
“一根火柴划亮了,旋又被风吹灭。”[1]在这忽明忽暗的火光中,狗儿爷陈贺详出现于舞台之上,陈贺详的生命恰如这火柴一般,似生非生,似灭未灭,已然接近濒死的状态。当人们一旦认识到死亡的残酷、死亡的不可重复性、死后世界的毁灭,便会对死亡产生巨大的恐惧。艾比克泰德认为“可惧怕的事情不是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惧。”[2]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因为人们在死的那一刻,已然没有了知觉,他的人生的全部价值,也已随着知觉的消失而消失。真正引起人类恐惧的是还没有到来的死亡,尤其是当人类看到他人的死亡而引起对自身死亡的思考时,人类就会对死亡产生深深的恐惧。刘锦云也正是将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融入了其最为经典的剧作《狗儿爷涅槃》之中,将常人固有的死亡意识进行了消解、重构,构建了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一心迷恋土地的“个人英雄”。
年轻的狗儿爷展现出的死亡意识与自己的三十岁正当年的年龄相比,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成熟。战乱之中,大炮一响,老婆带着孩子跟全村人一道逃命去了,狗儿爷却坚守在村里,趁着战乱,要做一回“乱世英雄”“阎王不收,就能活着回来,要收你,一个炮弹下来,我不去炸死俩,我去了绕一个。”[1]在全村人面对死亡的来袭,包括自己老婆、儿子在内的村民们纷纷外逃至村外的当口,狗儿爷丝毫没考虑自己的死活,只是以一个商人般的眼光去权衡这次逃离,老婆和孩子要是死在炮火中,算是死了两个人,狗儿爷如果也一起跟着去逃难,一个炮弹炸下来陈家就得死三个人,陈家将面临绝后之危,利益权衡之下,狗儿爷没有逃命,而是毅然留在村中,做了一个“舍命不舍财”的土庄稼孙,处在两军交火密集之处,收了二十亩地的好芝麻,如果自己不死,陈家的家业将从自己这一代发达。从全村人的争相外逃不难看出,村里远比外面危险得多,而此时狗儿爷却毫不谈及自己的处境,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与死亡相距如此相近么?显然不是,Kübler—Ross的濒死心理反应阶段理论把将死之人的心理反应大致分为五个阶段:震惊与否认、愤怒、讨价还价(乞求将自己的寿命再延续一段时间)、沮丧到最后的接纳。[3]而狗儿爷似乎直接跳过了将死之人前四个心理阶段,他是以自己肉身的生命作为赌注,与死神进行了一场对赌,已经到达全然可以接受死亡的阶段。
鬼怪、鬼魂原本是科学不发达时期的人们,因对死亡的畏惧而衍生出的意识中的产物,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真正的鬼魂,但在《狗儿爷涅槃》的舞台上,就出现了狗儿爷眼中“死而复生”的祁永年亡魂。《狗儿爷涅槃》并不以传统的线性结构讲述故事、塑造人物,而是随着狗儿爷意识的流动,逐渐向观众描绘出了其悲剧人生的始末。伴随着忽明忽暗微弱的火光,祁永年的亡魂在第一场就已然随着狗儿爷的意识而出现。
狗儿爷(猛回头,始惊愕,继平缓地)是你?
祁永年 是我。
狗儿爷 你不是人
祁永年 ……不是人。
狗儿爷 你是鬼。
祁永年 ……是鬼。
狗儿爷 你来干什么?
祁永年 因为你想我。[1]
在这似明似暗的舞台之上,这一问一答的超现实对话之中以及“烧了,烧了,你‘了’啦。”这般暗示性的台词,都渲染出了森森阴气,意喻着狗儿爷的死亡。但狗儿爷丝毫未表现出对死亡的畏惧,都是其早已坦然接受肉身死亡的显征,狗儿爷肉身的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都是依托于土地而显现,土地是狗儿爷的命根子,也是他的全部精神依托。其早已将肉身的生死置之度外,狗儿爷并不畏惧肉身的死亡,所以,无论对于鬼魂还是象征生命的火光,都不能引起狗儿爷的恐惧,而这一切的根基,都是源自于其意识层面生命意识的死亡。
二、永生意志的承载者
人类对生命的追求,对死亡的逃避,最终将依托人类生存的原始动力即生息繁衍而实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东坡在仰观自然风貌之无垠时发出如此的感慨,惊异于人生之短暂,觊觎自然的无穷尽的生命。人都曾感叹生命之有垠,然而不论医学、科学技术如何发展,其能延续人肉身生命之长短终归是有限的,作为个体的人之生命总会是有尽头,但人本性的“贪婪”也同样激励着人不断探寻永生之法。
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亦是源自于生命的欲望,肉身是生命的载体,对生命意识的追随,首先表现为对肉身的重视,延长肉身生命成为人们追寻死亡超越的最初努力。[4]然不论对肉身之死亡如何避趋,也终究是徒劳。于是,人类试图通过其他方式追寻生命之永恒,终于,将生命永恒落脚于精神永恒之上,于是人们开始追寻个人意志之永恒不死。荣格将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三个层次。“个人无意识基础有赖于更深的一个层次,这个层次既非源自于个人经验,也非个人后天习得,而是与生俱来的。我把这个更深的层次称为集体无意识……这部分无意识并非是个人的,而是普世性的……其内容与行为模式在所有地方与所有个体身上大体相同。换言之,它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因此,具备超个人性的共同心理基础,普遍存在与我们大家身上。”[5]不论是在哪个国家刚出生的婴孩,都会寻找母亲以期寄从中获取生命的给养,这种跨越地域、文化、种族表现出对生的孜孜追求,同时也是对死亡的避趋,正是埋藏在全人类最深层的意识之中,以整个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显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使个人意志产生长久且广泛影响的哲学家,之于普罗大众,只能以人类繁衍生息的本能,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探寻一套使自身意志达到永生不陨之法。狗儿爷虽然可以坦然面对肉身的生死,但究其本质终是自身无意识状态下在精神意志层面对永生的渴求,对死亡的避趋。
纵观《狗儿爷涅槃》全篇,狗儿爷的父亲虽然始终没有出现在舞台之上,但其虽死犹生,可以通过狗儿爷看到其父亲的遗志,狗儿爷是父亲全部生命意志的承载者,并且对父亲生命意志的传承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甚至是视若英雄般地追随者。虽然祁永年因其父亲“吃狗丢命”一事而讥讽陈贺祥为“小狗子”时,狗儿爷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辩驳,但引发狗儿爷反感的并不是父亲为了二亩地生吃了一条小狗而死的行径,而是对祁永年不屑态度的抵御。
“爹,小狗,你白吃啦!”[1]狗儿爷在面对风水坡被收归之后,发出了如是感慨,人也变得疯癫起来,正是因为狗儿爷将风水坡视若自己的生命,而根源正是来自于父亲传承下来的生命意志。狗儿爷父亲当年跟人打赌,为了二亩地活吃了一只小狗,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命。父亲的这种行为正是对土地极端热爱的体现,甚至为了土地丝毫不在乎自己的生命,狗儿爷也承载了父亲将土地视若生命的意志,在战火中,全然不顾肉身的生命收着芝麻。狗儿爷在此正是将父亲视作英雄一般,不仅在行动上模仿着心目中英雄的行径,面对土地,可以抛却肉身的生命,更是在精神上沿袭着父亲的意志,将土地看得比肉身的生命更具价值。
不仅在面对土地表现出的意志是源于父亲的,让狗儿爷梦魂萦绕的地主“身份”也是在无意识状态下继承于父亲。祁永年父子因在和泥用的麦糠里放了一袋子香菜籽,在颗粒无收的大涝之年发了家,成了挂上千顷牌的地主,让狗儿爷一家羡慕不已,也要去追寻自己的“地主梦”,开始在麦糠里掺上了香菜籽、倭瓜子、西葫芦籽,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狗儿爷对祁永年的祖地风水坡、被吊着打过的门楼、象征地主身份的印章的痴迷,都是对祁永年地主身份的向往,而对这个身份的苦苦追寻,正是根源于父亲尚未死去时对祁永年一家地主身份的向往和成为地主的行径模仿。对狗儿爷父亲而言,虽然其肉身早已因打赌吃了条小狗而死,成为了全村人的笑柄,甚至拖累儿子也成为众人调笑的对象,但在其个人精神意志传承上面,他是成功的,不论是视土地远胜于生命的意识,还是期寄成为地主的梦想,都在狗儿爷身上得到了延续,他是父亲精神意志的承载者,更是将父亲视若英雄的忠贞追随者,父亲的精神意志在狗儿爷身上得到了新生,并将永生不死。那狗儿爷是否又能像父亲一样在精神上延续自己的个人意志,以期精神不死呢?
三、精神意志的殉道者
狗儿爷的命运是充满悲剧性的,而造成悲剧命运的根源正是在无意识状态下,期寄通过子嗣后代延续自身生命意志,以逃避精神陨灭的死亡意识幻想的破灭。
狗儿爷的一生都是在被否定中度过,这是其精神走向死亡的先决条件。在炮火中,冒死收芝麻想要换取更好的生活,却被老婆冠以“财黑子”的名号,风水坡收堆时,新媳妇金花也要带着儿子陈大虎坚决和“黑膏药户”划清界限,不论何时,狗儿爷的行径和意志始终得不到妻子的认可。狗儿爷用命换来芝麻以后发了家,为了继续追寻自己的地主梦,用三石芝麻换了大斜角的宝地,却因“一片红”的政策而被收归了大队,而收地的人正是替自己降服了祁永年,自己誓言要一辈子听他话的队长李万江。不论是妻子、置腹的好友还是“一片红”的政策都与自己的意志完全相悖,甚至自己一生的死敌祁永年的亡魂竟成为了唯一能倾诉的对象,这些都不能将狗儿爷打垮,因为其精神意志延续仍有希望,在这个与狗儿爷格格不入的世界,狗儿爷还能且只能将自己精神意志延续的希望寄托于儿子身上。
冯金花曾抱怨自己不能给陈家带来一子半女,本该有着“多子多福”意识的狗儿爷对此竟然毫不在意,以算命先生的“预言”为托词,对只有陈大虎这一独子的事情一笑而过,究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父亲只有自己一个儿子,在这种情况下,狗儿爷一人就已经继承了父亲的全部意志,父亲的全部人生价值都已通过唯一的子嗣——狗儿爷完成了。二是虎子已经显现出了对父亲意志传承的迹象,不论是“我是耙子,你是匣子,我的宝贝匣子”这般与狗儿爷曾对金花说过的一模一样的话语,还是对资产的不断积累,都是陈大虎已然将自身生命意志继承的体现,狗儿爷因此认定已然不需要其他子嗣继承自己的意志。
父子双方真正矛盾的爆发点集中于资产的不断积累之中,当新资产与旧资产、新观念与旧观念产生矛盾的时候,狗儿爷内心一直认为自身意志的继承得到了断裂,将自身生命意志的载体——门楼一把火烧掉,也是狗儿爷视死如归,决心走向死亡的体现。当狗儿爷面对儿子娶了世仇祁家女儿的事实时,狗儿爷再次选择了隐忍退让,随着一次次的让步,狗儿爷的意志也正不断地消磨,离死亡也越来越近。[6]
象征地主身份的风水坡、菊花青,还有那始终都得不到的刻着祁永年名字的印章都消逝不在了,唯一剩下的只有门楼了,这是狗儿爷父亲遗留的“地主梦”的最后证明,更是狗儿爷精神意志得到传承的最后一丝证明。陈大虎偏要为了工厂推掉门楼,狗儿爷将精神意志传承于儿子陈大虎身上的希望也将随门楼陨灭,最终狗儿爷被逼致死。狗儿爷以门楼代替自己肉身的生命,不论是火烧门楼还是推平门楼,都可谓“生命意志的终结”,但这种终结却分有自身主动的殉道和被迫的殉道,狗儿爷在发现精神意志得不到延续之时选择了更为决绝的前者,火把一扔,在这用力一掷之中,完成了精神和灵魂的升华,走向了崇高。
狗儿爷坚持认为生命意志已然终结才会烧掉门楼,成为一名殉道者,但实为不同时代差异导致的世界观的差异,致使狗儿爷以为自身的生命意志,或者说是从父辈、祖辈传承下来的生命意志已然湮灭,其本质只是时代不同导致的生命意志的体现方式的分歧,然而实质上,陈大虎着实传承了狗儿爷的意志,继续完成祖辈们的“土地梦”“地主梦”,只是实现这个梦的载体已然从土地变成了新时期的现代工厂,而这一切确是对土地极度痴迷,视土地为自己生命的狗儿爷所不能接受的。与其说狗儿爷是人生命运的悲剧,不如说是个人的人生悲剧而已,只是偏激的狗儿爷唯一认定的传承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在此变化之下,自己并不能接受儿子陈大虎所赓续的“地主梦”导致的个人悲剧。
四、结语
狗儿爷所表现出的肉身的生死观全部依托于更为深层的精神层面的生死意识而显现,承载了父亲全部意志的狗儿爷将自身意志永生不陨地寄托于儿子身上的梦想最终破灭,成为了死亡的殉道者,完成了自我的升华。《狗儿爷涅槃》之所以能够长演不衰,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正是刘锦云着力塑造出的狗儿爷表现出的生死意识,已然不是单纯的肉身的生死,而是全人类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所追寻的精神层面生死意识的永生不死。刘锦云已然不是在讲一个农民,而是在讲述整个人类社会所共有的问题,在人性探究的基础上,反映出整个人类共同的问题,透过狗儿爷的人生悲剧,探赜人类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即对生的向往,死的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