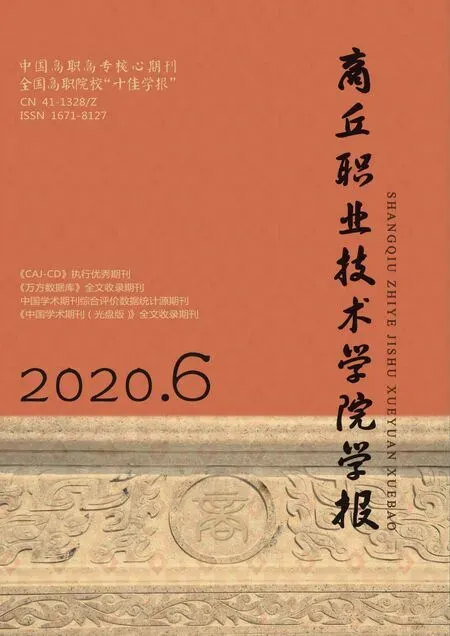由“我”到“吾”的历程:庄子修身意蕴
——以《齐物论》为例
聂 磊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庄子哲学有其独特的语境,在其哲学思想研究中,以往的研究者多关注于庄子哲学精神层面的研究,对其现实层面中个体存在的研究有所忽略,这不利于对庄子哲学思想在现实层面中的修身意蕴的解读和对现实层面中个体价值的研究。庄子修身意蕴是庄子哲学中的独特体现。庄子关注人本身的问题,从人自身的存在出发,发觉“我”的存在,进而使人自觉到“吾”的层面。本文拟从“我”到“吾”历程中的三个层面,即“丧我”之否定之我,“以明”之肯定之我,“逍遥”之回归之吾,来分析解读庄子《齐物论》中的修身意蕴。
一、“丧我”:否定之我
“丧我”出自《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1]39这里,笔者取“丧我”二字,旨在论述“丧我”之“我”与“吾”有何区别,“吾”与“我”有何关系,以及为何是“吾丧我”不能是“我丧我”。若从文本来看,大致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分析解读这段材料,即从身体生理层面的维度、精神心理层面的维度和时间存在层面的维度三个维度来具体分析。先把这段文字的意思梳理一下:南郭子綦靠着几案而坐,仰着头向天缓缓地呼吸,进入了超越对待关系的忘我境界。这时,颜成子游侍立在跟前,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呀?形体安定固然可以使它像干枯的枝木,心灵的寂静固然可以使它像熄灭的灰烬吗?你今天凭几而坐的神情和从前凭几而坐的神情不一样。”从颜成子游对南郭子綦的“行如槁木”,“心如死灰”所表现出来的身体和心灵变化特征的疑问中,可以看出,这分别是从生理层面中的身体角度和心理层面中的精神角度来分析南郭子綦的变化特征的,进而说明了南郭子綦的变化;从颜成子游对南郭子綦的最后感叹“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可以看出,这是从时间维度的层面来分析的。由此可以看出,南郭子綦在“吾丧我”之后,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表现出的特征是不同于“吾丧我”之前的。
“吾”“我”之间究竟有何不同,何以使得南郭子綦有着“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的差异?关键在于“吾丧我”。庄子认为,“吾丧我”是对自我的一种否定,这样的否定不是一般意义的否定,而是通过“吾”作为认知的标准来否定现实之中的“我”,也就是南郭子綦对“昔之隐机者”的否定。通过“吾”与“我”的对比,使得现实意义上的“我”或者说世俗意义上的“我”得到一个深刻的认识。“丧我”是认识这个世俗意义上的“我”,并且要摒弃这个世俗的“我”。这个世俗的“我”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我”呢?在通过“我”与“吾”的转换上即可得出“我”是什么样的。成玄英疏曰:“丧,尤忘也。而子綦境智两忘,物我双绝。”[2]从成玄英疏中可以看出,“丧我”之后达到的是什么境界,通过这样的境界显现,亦可看出“丧我”之后的“吾”是什么样的。换言之,“吾”才是庄子所要追求的真正本来面目。“境智两忘,物我双绝”才是“吾”的本来面目。陈鼓应先生说:“‘丧我’的‘我’指偏执的我,‘吾’指真我。”[1]41由此可见,“丧我”的“我”是一种“境智”达不到两忘的“我”,是一种物我无法双绝的“我”,是一种偏执的“我”,是一种丧失了真我的世俗之“我”。
这样的“我”正是庄子所要摒弃的“我”,庄子修身思想中对这样的“我”是加以否定的,故而,庄子提出“丧我”。因为,现实中的“我”已被经验性的、感性的一面所遮蔽,“我”其实就是一种对于自我的意识,这种意识将自己和世界区分开来,同时也按照自己的标准把世界区分开来,换言之,“我”就是一种执着于自我的心,一颗有“己”的心[3]。这样的“我”早已沉浸在经验、感觉、技艺之中而无法自拔,超经验性的、超感官的亦即智慧的、理性的一面更是无从探求,这与庄子所追求的“吾”的境界,达到 “境智两忘,物我双绝”的境界相差甚远。
庄子对“我”以他者的身份做出了一种哲学思维的分析,跳出“我”本身以他者的身份对“我”进行观照。这样的观照不像儒家的自我观照、自我反省,而是把“我”当作主体来进行观照。庄子既能够把“我”当作主体又能够以他者来观照“我”,这样的思维也只有在庄子那里才能实现。也正是如此,庄子的修身思想并不是像儒家那样将个体本身以自我为主体,同时又以自我为对象的观照;而是以自我为观照对象,以他者的身份来观照自我。这样来看,“吾”与“我”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吾”是在“我”之中又在“我”之上,超越于“我”,因为,“我”是作为一种载体来承载“吾”的存在的,“吾”不可能离开“我”而单独存在。庄子认为,“我”作为一种身体性的存在和世俗精神性的存在,这样的双重存在对于“吾”来说也必然有着一个超越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哲学的存在。这样一个否定的“我”的存在,显然不是庄子所要表达的真正的存在。庄子用哲学的思维表达了对“吾”的思考,同时庄子也对如何达到“吾”做出了分析。
二、“以明”:肯定之我
由否定之我到达肯定之我,这之中的“我”经历了什么,或者说如何才能达到肯定之我?上文分析了“我”与“吾”的含义,如何才能达到“吾”亦即真我的境界呢?如何才能达到内心与万物为一体的心灵境界呢?庄子认为,想要达到“吾”就要破除“成心”,如何破除“成心”也就是庄子所提出的方法论,那就是“莫若以明”。庄子的修身思想就是在通过对“我”的一步步解读和探究之下得以实现的。
《庄子·齐物论》中有云:“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1]58庄子认为,“成心”是人人都具有的,无论是“知代而心自取者”这样的智者,还是“愚者”,都有“成心”。那么,“成心”可以说是我执之心①,即把“我”的是非判断标准作为衡量一切的是非判断标准。这样的心就是我执之心,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成心”。陈鼓应先生认为,“‘成心’是成见之心。‘成心’在齐物论中是个很重要的观念,物论之所以以自我为中心,引发无数主观是是非非的争执,产生武断的态度与排他的现象,归根究底是由‘成心’作祟”[1]58。正是这样的“成心”阻碍了修身,无法达到“吾”之境界。“成心”使“我”与物事纠缠不清,无法以他者的态度去超越地看待“我”与物事之间的关系。世人于物事之间追逐烦恼。庄子感叹道:“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1]53-54身体上,自己的形体逐渐枯竭衰老;精神上,自己的心灵又困缚其中随之殆尽。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无穷的折磨,不仅仅我是这样,其他人和我都是这样,这实在是最大的悲哀。受到“成心”的沾染、侵袭,足以使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受到双重的折磨,而作为个体独立之“吾”则荡然无存。
因此,庄子提出,“莫若以明”使人昭然自明,那么,人所不明的是什么?是被“成心”所遮蔽的“道”“言”。“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1]58庄子如是说。道被隐蔽而无法分辨真伪,言论被隐蔽而无法争辩是非,道出现又不复存在,言论展现又不被承认。这都是因为道被“小成”所隐蔽,言论被“荣华”所隐蔽,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儒墨之辩。庄子正是看到是非的存在,而身处是非之中的人和物事又无法明白是非的争端由来,因此,庄子提出“莫若以明”的解决办法。“莫若以明”就是使人以超出是非之外的、客观的事物本然状态来观照事物本身的情形。这样的“以明”显然是对“我”的肯定,这里的“我”是真我,不是“丧我”之“我”的假我。“以明”物我之外的真我,不仅是对物事的观照,同时也是对个体本身的观照。“以明”既是对物事的本来面目的显现,又是对被遮蔽的物事的解蔽;消解“我”与物事、人我之间的是非对立,把人我的冲突、对立、紧张通过对个体本身的观照,达到一种新的境界。换言之,“以明”是观照明白人我之间的界限,“不明”的是人我之间的界限、自己和外在世界的对立。其实这都源于自我,也就是无法看到本来面目的真我,无法对真我做出肯定。也正如老庄“所讲的‘明’是依据‘道’而对事物有一个动态的、全面性的了解”[4]。从哲学层面来说这是对真我的迷失,庄子的“莫若以明”就是发现真我并加以肯定真我。
庄子通过肯定真我来对现实的种种情况做出了回答,这样的回答是对如何修身的诠释,对理解庄子修身思想的意蕴有着独特作用。在真实社会中,人的力量有限,加之“成心”的沾染、侵袭,物我关系不明。与此同时,关于产生“我”的异己力量对个体自身而言是不明的。然而,庄子看到人的自我的矛盾与人和物之间的矛盾,他认为,矛盾是由人的欲望、感情、智识、技能所造成的。因此,庄子提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1]62。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彼”,也没有不是“此”的。从他物那方面就看不见这方面,从自己这方面来了解就知道了。所以说,彼方是出于此方对待而来的,此方也是因彼方对待而成的。事物本身包括两方面,既有这方面又有那方面。“彼”和“是”是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在世俗之人的眼里是对立的、无法调和的。换言之,世俗之人即是被“成心”侵袭之人,在“成心”的侵袭之下无法认识到事物的两个方面,“故不能真有一客观之标准,已决定是非”[5],更无法站在事物两方面的“彼”“是”维度来思考问题。“尽管人与人之间时有冲突,但人可以互为主体,从而突破主体的局限性”[6]。庄子在这里看出,事物“彼”“是”的两个方面,同时也看出了,“彼”“是”之间的矛盾和“彼”“是”之间相互转换的维度之上的消解矛盾。世人往往只看到“彼”“是”的对立,认为“彼”“是”是“非彼即是”“非是即彼”的关系。这样的认识显然是境界不高的,只是现实的存在,还没有触及到矛盾的本质,庄子看到事物的对立矛盾,进而引导人们站在“彼”“是”互换的维度上来对待事物本身。这样的对待其实就是对“彼”“是”矛盾的消解,重新找到事物本身的状态,化解到人本身上就是肯定自我,对真我的重新认识。
这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1]62。“照之于天”即是观照事物本然之状态,把对事物本然状态的观念作为修身的意蕴进行阐发,这也正是庄子修身思想的独特之处,亦即不按照儒家的执着于物我关系的修身思想来阐发庄子的修身思想②。庄子认为,圣人不走是非对立的路子,而观照于事物本然之状态。这也正是因任其自然的道理。以“照之于天”为出发点,以“以明”作为观照,正是庄子修身意蕴中对事物本然的观照,对个体自身的肯定,对人本身的肯定,亦即对真我的肯定。
三、“逍遥”:回归之吾
“逍遥”是回归“吾”的最终体现。“逍遥”是一种人生境界,这样的“逍遥”之吾正是庄子修身的归宿。回归到“逍遥”的状态才是庄子所肯定的修身思想,也是庄子的修身意蕴之所在。“逍遥”在庄子语境中有着两层含义:一是在“有待”的层面上适性自足的活动;二是在“无待”的层面上“自己由之”的现实活动,即超越有待而进入无待之境。这样的“逍遥”既是一种现实活动,同时也是一种超越于现实的活动。在现实层面上,人们所处的世界是无法脱离现实的客观世界,而且必须和现实的客观世界发生互动,并在此之中达到身体的“逍遥”之境地。这也就是现实层面的“逍遥”。在超现实层面上,人们虽然处在现实的客观世界之中,但是人的精神是可以超越现实的,超越彼此的对待之上的,并达到精神的“逍遥”之境地。这也就是超现实层面的“逍遥”。
上文笔者分析了“以明”是破除“成心”认识真我,是从哲学的层面来认识并肯定真我。肯定真我是由“以明”逐步认识真我,那么,是否就可以说认识到真我的存在就能够达到逍遥之境了呢?认识到真我的存在,在庄子看来,只是回归到“吾”的思维层面,并不是最终的思维与实践的统一,即由认知深化至实践并达到二者的统一。换言之,庄子所要追求的是合乎道的认知与合乎道的实践的统一。庄子如何由合乎道的认知升华至合乎道的实践呢?庄子提出,“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1]70,“两行”是指“和是非”与“休天钧”。“和是非”从现实层面理解为不执着于现实的是非争斗,“休天钧”从思维层面理解为因顺自然天道运行的道理。一个是从形而下的现实层面解决问题,一个是从形而上的思维层面解决问题或者说是从哲学层面思考问题如何解决。“两行”即是既注重现实层面的是非争斗问题,又注重哲学思维层面的自然天道运行的道理。“两行”就是合乎道的实践,合乎道,在庄子看来即可达到“逍遥”的境界。“逍遥”的境界同时也是“达者”的境界,“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因是已”[1]69。庄子认为,“达者”是体道之士,只有通达之士才能了解这个“通而为一”的道理,因此,他不用固执自己的成见而寄寓在各物的功任上,这就是因任自然的道理。“达者”能够通达万物为一的道理,不会执着于事物各自是非之间斗争,庄子说:“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1]69“达者”能够从道的高度来看这个有待的世界,把事物彼此之间的是是非非从道的高度复归于一,这样的境界就是逍遥的境界。无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还是“恢恑憰怪”,从道的角度来看都是可通而为一的。庄子不仅从具体的事物之间的差异说明道可通而为一,更从哲学的层面将其升华到一个高度。万事有所分,必有所成,有所成必有所毁,所以,一切事物无论完成和毁坏,都复归于一个整体。庄子认为,人们都应当成为一个“达者”,成为“达者”才会做到“道通为一”地观照事物,不会拘泥于事物之间的是非,也就是说在“达者”那里事物之间是非差别都是相通的。
在“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因是已”这句话中的“寓诸庸”下句原有“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依严灵峰之说,这二十字疑是衍文[1]71-72。此虽是衍文,但对于理解现实层面的“庸”却大有裨益。“庸”就是功用通达有其所得的意思,这是从现实层面的功用角度来看,物各有其自己的用处。庄子既看到事物的现实功用,又从超越事物功用之上的道的高度层面来看事物。这样既不失事物的现实意义,又能够从哲学的高度对事物有一个“达者”的达观视角,并以此来观照事物。“庄子以追求个人精神‘无待’的‘逍遥游’为崇高理想,希望个人的精神能摆脱世间一切礼法制度、道德规范、世俗观念的束缚”[7],如此之“逍遥”才是庄子的真“逍遥”。
达到“逍遥”回归到“吾”,一切都能够从真我出发,“逍遥”之中的真我是自由的。这样自由的真我在庄子那里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80天地和“我”并存,万物和“我”复归于一体。这里不仅是齐物论思想的体现,也是逍遥境界的体现。也就是说,“人作为世俗与精神的存在,通过对自身形体、身心、情意、欲念的支离与疏解,可以消解世俗之我”[8]。庄子从“我”的存在状态追溯人的存在根源,认为人源于道,从宇宙的本体出发思考人的本质存在,即人从道汲取到本源性的存在,发现人的本质即是探求自我的本身存在意义亦即本然存在。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以道作为本源性的思考进而阐发庄子的逍遥思想,正是庄子逍遥的最终境界。同时,庄子也提出了一条圣人所处世的原则:“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1]83对于宇宙天地之外的事,圣人是存而不论的。天地以内的事,圣人只论说而不做任何议评。古史上有关先王治世的记载,圣人只议评而不与人争辩。天地之外的事是实体的存在、本源性的存在,这是不必论说的。天地之内的事物是万物为一的,不必以自己的“成心”议评。古史上已经发生的事,可以评议但不必与人争论,争论都是从各自的主观认知出发,这是没有意义的。庄子对圣人的处世原则做出了解释,庄子强调不做主观评议,目的还是避免以一己之见,陷入是非之争[9],认为一切的争论皆出“成心”、出于假我,无法认识到“吾”的存在,也没有体认到真我。“逍遥”境界在“我”的层面无法体认,只有回归到“吾”的层面才能体认到“逍遥”的境界,“吾”的“逍遥”才是真正的逍遥。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吾丧我”作为修身意蕴阐释的切入点,庄子认为,“我”由于“成心”而无法认识真我,因而需要加以否定。这样的“我”被世俗的主观我执之见所束缚,无法认识到“吾”。“吾”作为庄子所肯定的真我,需要“以明”作为观照。观照事物本然的存在,消解事物之间的是非差异,为事物被“成心”所沾染、侵袭遮蔽了的本然存在解蔽,使得物物之间彼此的差别存而不论,从物物的角度观照物物本身,而不是以彼此对立的角度去观照,进而肯定物的本身,体认到真我的存在,体认到“道通为一”,达到“达者”“圣人”之境,也就是回归到“吾”的真我状态,亦即“吾”之“逍遥”境界。
注释:
①“我执”是佛家用语,在佛家中指以自我为中心对一切有形和无形事物的执着,执着于自己的见地、知识、技能。这里试着借用佛家用语来说明“成心”。
②儒家修身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内省修身,是把事物作为对镜来反观修身。儒家这样的修身思想与庄子所提倡的消解事物的彼此对立,消解事物彼此界限的修身意蕴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