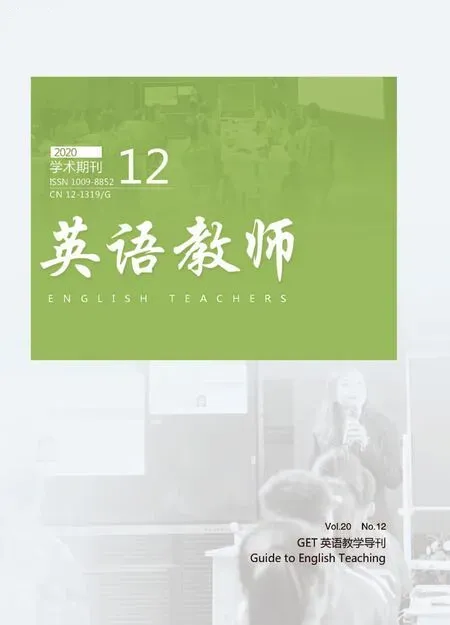基于个体意识形态操纵视角的《浮生六记》林译本研究
蔡欣洁
引言
林语堂兼具中国文化本土者和西方文化探寻者双重文化身份,由此形成了体征文化传播忠实传神同时译文达意可及的翻译观。在该翻译观的意志渗透下,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呈现出文化保留性、白描文笔和关注原文“形美”亮点三大基本特征,力求在传达原文所含文化意蕴和美学价值的同时,观照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阅读感受。
《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创作的自传体笔记,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代表作之一。1935年,林语堂所译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以下简称“林译本”)是最早的《浮生六记》英译本,也是最为经典的译本。现有对《浮生六记》林译本的研究更多关注词、句等微观文本层面,如汪宝荣(2016:43)以实证方法定量统计了《浮生六记》林译本中的地名翻译情况,经统计发现林译本地名翻译以“音译、音译加注、音译辅以范畴词直译”等翻译策略为主,以此留存原文异质性,从而带给读者异域文化体验感;王焕池(2004:104)考察了《浮生六记》林译本中地名、姓氏称谓和习俗词语的翻译,认为上述类别词语的翻译“损失了大量的文化信息”。诸如上述类型的研究多关注译本语言表达的优劣、得失,而鲜少探讨影响《浮生六记》林译本生成的译者因素和历史文化语境因素。鉴于现有研究在文化语境方向上的考察存在不足,本研究以操纵理论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操纵为视角,以林语堂的个体意识形态为切入点,分析林语堂所具有的个体权力意志风貌及该种权力意志对《浮生六记》林译本翻译特征的塑造。
一、操纵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概念
操纵理论由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提出,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时期发轫而生的代表性翻译研究文化视域理论。操纵理论包括三个核心概念:改写(Rewriting)、操纵(Manipulation)和制约因素(Constraints)。其中,前两个核心概念是勒菲弗尔对翻译本质属性的定义。在勒菲弗尔(1992b:7)看来,“翻译即改写,改写即在各种力量因素作用下的操纵”。最后一个核心概念划分并阐释了翻译活动中施加操纵、导致译文改写发生的主要权力意志体,其中包括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大类最为基本而核心的权力意志体。在上述三大核心权力意志体中,勒菲弗尔尤其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活动的操纵作用。勒菲弗尔(1992b:41)认为,“意识形态控制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选择、对翻译涉及的原文论域问题和原文语言问题的处理方式等”。
在操纵理论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定义域不仅涵盖社会意志,还包括群体意志和个体意志,“是社会环境中某一个体或群体持有的看法、观念和信仰网络”(Lefevere 1992b:48),这一意志网络“不仅包括政治,还包括影响人们行为的范式、习惯和理念”(Lefevere 1992b:16)。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翻译行为的直接践行人,其实践过程贯穿译前理解直至译后定稿的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是极活跃的翻译生产链主体参与人,因此,“译者自身所具有的翻译目的和翻译观会影响他们自身的原文本选择倾向和后续的翻译方式”(Lefevere 1992a:14),上述影响最终折射成像为译文呈现出的翻译策略选择和整体翻译风格,彰显出译者个体权力意志在生成译本中的渗透、融汇。
译者的个体权力意志来源于其天然具有的文化身份起源、长期生活的文化环境浸透和个人变迁的人生经历涤荡。在上述三者历时性、累积性、潜移默化的合力塑造下,民族、国籍、受教育情况、家族传统、所处文化圈、宗教信仰、人生阅历等层次文化现实、社会现实相互交织、积淀,哺育了译者根植于自身文化身份之上的个体意识形态。另外,积淀而生的个体意识形态反作用于译者本身,指导译者的各项文化行为、社会行为。具体到翻译活动,译者或基于自身权力意志,发挥译者主体性介入译文生产,指向性明确地操纵译本生产;或不自觉地在自身意识形态的无形引导下,有所倾向性地引导译文生产,在译文生产中留下个体权力意志痕迹。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都使译者的个体意识形态渗透其生产的译文,使译文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操纵,最终打上译者的风格标签和目的烙印,彰显出译者的个体权力意志痕迹。
二、林语堂双重文化身份下的译者意志
林语堂出生于传教士家庭,早年受教于教会学校,后前往美、法、德等国游历求学,开阔眼界,学成后回国任教于多所大学,因此其文化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林语堂以中华文化为骨,是原生于汉语语言文化圈的本土文化者,寻求着中华文化的自我彰显,诉求着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发声、绽放;另一方面,林语堂兼容西方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对英美文化具有探寻情结。他曾自我评价“两脚踏中西文化”(转引林太乙,2011:308)、“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林语堂 1994:21)。以上自评在表明林语堂文化身份双重性的同时,也体现出了其文化身份的结构性。即在这双重文化身份中,中华文化人、本土文化者这一身份是核心、根基,是林语堂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源动力和行为准则基线;西方文化受教者、探寻者这一身份为表,是林语堂实践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武器库”。
具体反映在翻译观上,林语堂(1984:422-426)在所著的《论翻译》中提出了“忠、顺、美”的翻译标准和“句译”优于“字译”的翻译方法。林语堂所提倡的“忠、顺、美”的翻译标准与中国传统译论所倡导的“信、达、雅”虽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同质化。林语堂所呼吁的翻译之“忠”,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比较忠实”,而非桎梏于原文牢笼的“绝对忠实”。他强调以句或句群作为基本的翻译单位,不拘泥、桎梏于字词的逐对译介,在翻译中注重通过对句或句群语义的整体理解、把握和转换,从而在译文中传达原文的语义、意象和神韵风采。林语堂主张的翻译之“顺”,是指行文流畅,具有好的阅读体验感。他倡导译文在表达上应符合目的语的写作习惯、行文规范和表达传统,贴合目的语读者所具备的阅读能力、所具有的阅读习惯,避免译语在表达上的生硬、佶屈聱牙或晦涩难懂,以流畅、地道的译文行文为译文语义的精准传达服务。林语堂所倡导的翻译之“美”,要求译者传达原文之魂,将原文所蕴含的美学意境、所承载的文化感、旨在体现的精神内涵传达给目的语读者,使目的语读者跨越时空、地域,感受到原文的内核意蕴。
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首版于1935年,后经多次修改润色,再版于1939年。林语堂既是《浮生六记》译本翻译的发起人,又是执行人,因而其兼具译者和赞助人双重身份。林语堂选择《浮生六记》进行翻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其作为本土文化者和爱国者常怀的文章报国、文化外译使命感,希望借由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向西方介绍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展示真实的中国文化风貌,打开中西文化对话交流的窗口,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西方文化圈对中国文化僵化、失真的原有印象。对林语堂而言,“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无一不是以译介传播中国文化为最终目标”(冯智强、庞秀成 2019:12),文章报国可谓其不改之初心。另一方面是这一时期林语堂的人生际遇。1935年前后,林语堂的侄子林惠元和好友杨杏佛相继遭暗杀身亡,其自身寓居上海期间也颇多拮据困厄,郁郁不得志。而《浮生六记》中所描绘的沈复和其妻子芸娘之间虽朴素、艰苦但深情、恬适的生活,正契合林语堂本人一直以来所信仰的抒情哲学和闲适生活态度,令其感受到“那种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沈复1999:preface),令其心境受到一定慰藉。故此,选择《浮生六记》进行翻译,也是出自林语堂本人对此书的偏爱。
三、林语堂个体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浮生六记》英译
在《浮生六记》的翻译上,林语堂的“忠、顺、美”辩证翻译观引导其对译文生产施加了潜意识操纵。林语堂文章报国、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引导其有意识地主动介入译文生产,同时其翻译活动发起人、译者赞助人的双重身份又使其具有较大的译介自由,增强了其个体意识形态发挥操纵作用的权力资本和影响效力。在上述因素的合力塑造下,《浮生六记》林译本呈现出三大基本的翻译风格特征。
其一是文化保留性,《浮生六记》林译本注重对异质文化元素的保留性转化,关注原文本文化元素在译本中的留存。在翻译中,林语堂在处理文化意象或文化信息富集的语言单位时,选择以异化翻译策略为主,辅以增译、注释、夹述夹译等翻译策略,以补足文化背景知识和文化语境信息,外显化原语言单位的隐含语义或异域知识,从而使译文在保留原文异质性的同时,观照目的语读者的概念识解图式和语义理解能力,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感受原文文化概念。此种特征在例1的处理上可见一斑。
例1:余与芸联句以遣闷怀。(沈复 1999:30)
译文:And then we began to compose a poem together,each saying two lines at a time,the first completing the couplet which the other had begun,and the second beginning another couplet for the other to finish.(林语堂1999:31)
例1中所述的“联句”,是古代文人墨客休闲嬉戏、遣怀解闷的一种常见方式,最早可追溯至汉代,指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交替出句,联结成篇,形成雅文。该概念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是一个文化缺项。因此,为更好地传达出原文中“联句”一词所具有的概念信息,林语堂在用compose a poem together将该词的基本语义“共同作诗”译出的同时,增译了each saying two lines...to finish部分,译出了该词蕴含于中华文化语境的隐信息,将该活动的具体开展方式清晰地说明,在消除理解障碍便于读者领悟原文语义所指的同时,也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更多的异域文化信息和异域文化知识资源,观照了目的语读者对异质文化的阅读期待。
其二是在行文上注重运用白描文笔,在遣词造句上简洁用语,使译文衔接流畅,表达不冗余拖沓。在翻译《浮生六记》时,林语堂以句、句群为翻译单位,对于原文中一些不便于目的语读者阅读理解且文化意象性相对薄弱、可选择性略去的概念,进行了意译处理,以使句子语义更明晰,行文更流畅连贯,贴合“行文流畅是英美主流翻译规范之一”(Venuti 1995:4)这一英美写作规范,从而带给目的语读者更优质的阅读体验感。
例2:余生于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沈复 1999:2)
译文:I was born in 1763,under the reign of Ch’ienlung,on the twenty-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 month.The country was then in the heyday of peace and,moreover,I was born in a scholars’family.(林语堂 1999:3)
如在处理例2所示的翻译时,鉴于该句语义在表达目的上重在传达人物的基本背景信息,以达意为主旨功能,且在篇章结构上该句为开篇首句,不宜过于冗长,因此林语堂在翻译该句时,将原句中的“乾隆癸末”置换处理,转换翻译为“1763”,将“衣冠之家”意译为 a scholars’family,在传达出主人公出生年份、家庭情况等人物背景信息要点的同时,避免增译或加注解释“癸”“衣冠”等词的指代对象、关联语义而导致行文过长,在开篇就造成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不适或视觉疲劳,影响其阅读热情。
其三是在译文中借由特殊的行文方式和篇章结构组织方式再现原文表达所具有的“形美”亮点。林语堂在翻译时,虽追求行文的简洁、流畅,以观照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感受,但未一味忽略原文中词句语篇在表达形式、行文结构上的美感特征,而是选择性地处理,对于一些不可忽视的原文形式亮点,在译文中也以特殊行文方式加以处理。
例3:何时黄鹤重来,且共倒金樽,浇洲渚千年芳草。
但见白云飞去,更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沈复 1999:312)
译文:
When the yellow stork comes again,
Let’s together empty the golden goblet,
pouring wine-offering
over the thousand-year green meadow
on the isle.
Just look at the white clouds sailing off,
and who will play the jade flute,
sending its melodies
down the fifth-moon plum-blossoms
in the city?
(林语堂 1999:313)
如例3的处理便体现了林语堂如何以特殊行文形式传达原文隐含的形式美。对偶性和节奏感是中国传统诗词歌赋的一大特征,赋予了汉语语言表达形式对称美和阅读韵律感。林语堂在翻译例3的骈句对联时,为保留原文所蕴含的形式美和节奏感,未将原句转译为英式散文体,而是刻意译成错落排布的诗句,将上下联部分同一位置的词形结构一一对应,从而在译文中再现了原文的节奏停顿和上下联呼应性,使目的语读者直观地感受到语句的形式对称美,带给其不遑原文读者的阅读感受。
注重译文的文化保留性、运用白描文笔和关注原文的“形美”亮点,使林语堂在《浮生六记》的翻译上既观照了原文文化意蕴和美学感受在译文中的恰当传达,又兼顾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感受、理解能力和期待视域。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极力实现上述译本翻译效果的同时,林语堂也难免在一些概念的翻译上因矫枉过正而存在过犹不及的问题。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部分中国文化概念的翻译存在误译。如在翻译原文中的“天孙”(沈复 1999:26) 一词时,直译为 the grandson of heaven(林语堂 1999:27),并加注注解其指代含义为the Cowherd(牛郎),但实际上“天孙”在中国文化意象里对应的是织女(织女相传为天帝的孙女);在翻译原文中的“巫山”概念时将其误解为长江峡谷之一的巫峡(沈复 1999:172),译为 Yangtze Gorges(林语堂 1999:173),而根据该词的词源典故“巫山云雨”,实际上原文中的“巫山”是指湖北云梦泽的阳台山(又名巫山)。另一方面是在部分原文语言表达的翻译转化上,过度偏向目的语指向,翻译顺化方式值得商榷。如在翻译原文中的“明珠暗投”(沈复 1999:92)一词时,林语堂以出自基督教典故的英美俚语“casting pearls before swine”(林语堂 1999:93)转译,虽然译文的字面语义与原文表达的字面语义相近,但在感情色彩上,相比“明珠暗投”作为事实判断词的偏中性色彩,英美俚语“casting pearls before swine”含有轻蔑、嘲讽之意,是一个偏贬义色彩的词汇,而在原文中,沈复想要表达的是对虞山游客所赠树木与庭院格局不甚相称的惋惜之情,而非嘲弄之意。
结语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Lefevere 1992a:14),作为翻译活动直接参与人的译者,其在自身文化身份所塑造的个体意识形态操纵下,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身的权力意志带入译本生产过程,从而影响译本所呈现的翻译风貌。林语堂作为中国文化本土者的内在风骨和作为西方文化探寻者的后天积淀,具有双重交织的文化身份,塑造了其兼顾中国文化外译传播的忠实、传神和目的语读者阅读接受的可及、通达的翻译观,使英译的《浮生六记》呈现出文化保留性、白描文笔和关注原文“形美”亮点三大基本特征,成为脍炙人口的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英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