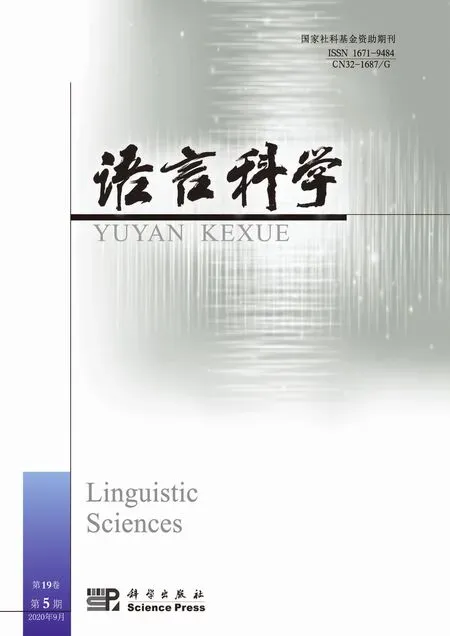从状貌词的实质与演进看汉语的分析性
张新华 张和友
1复旦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32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提要 论文建议把朱德熙(1982)所说“状态形容词”改称“状貌词”,这种改称无论从古今汉语联系还是跨语言比较,都有充分根据。状貌词的语义特征是质料性、混沌性、限定性、感叹性。上古汉语状貌范畴的典型语词形式是重言,编码理据是摹拟及语音象征,这具有高度的跨语言普遍性。总体看,从古至今,状貌范畴的典型性有较大降低,表现在:重言词改变为叠加式、形成 -bb词缀、AA功能蜕化,一些AA、AABB、ABB发展出构形用例等。状貌词由综合性向分析性的演进是控制这些发展的深层动因。
1 引言:状貌词的界定
本文所说“状貌词”即朱德熙(1982)“状态形容词”。赵元任(1968)、吕叔湘(1980/1999)称“生动重叠”、“形容词的生动形式”。学者对状貌词的分类差异很大,但多着眼于表层形式,实际上,一些表面相同的状貌词,构造方式很不一致。根据结构方式的不同,我们把状貌词概括为三大类及两个附类。
1)叠加。 这是一种构词层面的操作框架,本文称之为“词框”,相当于一种派生词缀:对基式的词义造成重要改变,得到的是一个新词。有三种形式:AA(红红、暗暗),AABB(形根:肥肥壮壮,名根:风风光光,动根:偷偷摸摸〔1〕)。大量ABB的BB未虚化,也属叠加,如“慢吞吞、水汪汪”;有些ABB就是AABB的不完全叠加。为区别起见,本文用“重叠”专指构形层面的重复。强抽象基式构成的AA、AABB属重叠,指量的增强,如“整整、认认真真”,二者都由叠加式演进形成。
2)词缀。 典型的是虚化的Abb(小写指词缀,大写指词根,下同),如“傻乎乎、直巴巴”。其他如中缀“里”(糊里糊涂)、及后缀“酸不拉几、黑不溜秋、稀了吧唧、黑咕隆咚”等,称为Abcd。一些Abb可采取Abcd,如“美不滋滋、滑不卿溜”,表明二者相通。
3)单词。 有两种,一是现代汉语的BA(滚圆、肥嫩),往往可进入AABB、ABB词框。二是来自古汉语的重言词、联绵词(幽幽、恍惚、飘渺),及“然”类词缀(黯然)等。
状貌词还有两个附类:非典型词框形式和拟态词。前者如“又羞又骚、不慌不忙、不尴不尬、虎头虎脑”,类推性不强。非典型词框的存在,表明状貌词不完全处于词的层面。拟态词是拟声词的引申用法。拟声词与状貌词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拟声词一旦失去原初的生活情景,就容易被解读成发声的动作方式,成为状貌词。古汉语有很多拟声与拟态的并存现象,这从经师注释上就可看出:对同一词语,不同学者或解为拟声,或注作拟态,如“营营青蝇”,《毛传》解作“往来貌”,朱熹(1943)注“往来飞声”。这种现象在现代汉语中仍很普遍,如:
(1) a. 屋里稀里哗啦地响起来。 (2)a. 同学们都刷刷地写个不停。
b. 那些宋军被她打得稀里哗啦,溃不成军。 b. 灯刷地亮了。
a句“刷刷、稀里哗啦”指声音,b句“刷、稀里哗啦”指状貌。
朱德熙(1993:82)认为状态形容词“是由形容词词根派生出来的各种形式”,此规则在现代汉语中成立,却不见于上古汉语:当时存在初始状貌词,但缺乏相应的性质词,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黍稷彧彧”(《诗经》),“胸中正,则眸子瞭焉”(《孟子》),“九疑缤其并迎”(《离骚》)。上古汉语词库层面存在一套与(现代汉语)性质词相对应的状貌词系统,而重言是其主要形式,其用法变迁构成状貌词演进的枢纽。
总体上,现代汉语状貌词的生动性不及上古汉语,后者的编码策略是直接描摹、综合性、基于经验感受;而前者理性分析增强。分析性和形象性往往是对立的。
2 状貌词的语法意义
“状态形容词”的称谓不能提示此类语词的语法功能。在广为接受的Vendler(1957)系统中,状态(state)、动作(activity)、完结(accomplishment)、达成(achievement)构成谓词的情状序列。其中状态指know(知道)、love(爱)之类,“状态形容词”与之差距甚大。但在动态性、时间性上,二者存在相同之处:都是弱动态性、弱时间性,是一种介于阶段谓词与个体谓词间的语法范畴,因此可把“状貌”与“状态”归为同一上位范畴。
2.1 状貌词的跨语言普遍性
本文认为,古汉语重言词及现代汉语状态形容词的语法功能可概括为“状貌”。汉代以来,学者对《诗经》状貌词常用“-貌、-状、-姿”释义,这一释义范式抓住了此类词的本质,如“肃肃”,《毛传》:“疾貌”;“窈纠”,《毛传》:“舒之姿也”;“倩”,《孔颖达疏》:“巧笑之状”。在现代汉语,各种词典对状貌词的释义也多采用“形容某某”或“某某的样子”的体例:
(3)病病歪歪:形容病体衰弱无力的样子。(《现代汉语词典》)
(4) 蓝晶晶:形容蓝得发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5) 热腾腾:热而有蒸汽的样子。(《现代汉语八百词》)
从认知特点看,状貌范畴与语言系统中其他各种语法范畴整体形成对立:前者的认知载体是感性认识,后者是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即视、听、味、触等物理感知行为,状貌词所指内容即诉诸这种认识。语言习得上,对状貌词只有实际经历过其场景,才能真切识解,如现代人很难真切体验“喓喓草虫,趯趯阜螽”的意蕴。跨语言看,状貌词也很难翻译,日语bitya指“一个带水的物体撞击一个平面,水飞溅出去”,我们容易理解这些分析性的描述,但仍然难以对bitya本身获得真切的语感。
状貌词广泛存在于藏缅、日、韩、班图及非洲的大量语言中。王辅世等(1983)对苗语、李树兰(1985)对锡伯语用“状词”;欧阳觉亚等(1984)对京语用“声貌词”。孙天心和石丹罗(2004)研究嘉戎语时把ideophone译为“状貌词”。例(6)是锡伯语的例子,形式与语义都与汉语状貌词非常相像。
那 女人 头 乱蓬蓬 (李树兰1985:21)
那个女人头发乱蓬蓬的。
国外学者对状貌词的称谓主要有三个:ideophone、expressive、mimetic,最近多用ideophone。Dingemanse(2018)认为状貌词的表意机制是描摹(Depiction),区别于普通谓词的描述(Description)。Kita(1997)认为状貌词与普通谓词的区别是:前者属“情绪-印象”(affecto-imagistic)维度,后者属分析(analytic)维度。国外对状貌词的主要研究内容涵括音义象征、句法行为、外部组合能力、表达功能等。
1) 音义象征。一些语音有很大的跨语言普遍性,如[k]指撞击、短暂,[l]指流动、延续;如英语glow、plump、splatter等,汉语嵌[l]词如嗤棱、窟窿、囫囵等。在特定语言中,状貌词所用语音往往有很高的标记性。汉语也是如此,Kennedy(1959)发现,《诗经》重言词的单音节多不常用,常用的音节却不大用于重言。重复作为状貌的语言手段,具有普遍性。状貌词与手势有紧密联系,Moshi(1993)认为状貌词即语词手势(verbal gestures),Diffloth(1972)称为手势-形象(gesture-images)。这些特征反映了状貌词在语言系统中处于原始性的地位。
2) 句法行为。在形态发达的语言中,状貌词却往往缺乏形态变化,这同样表明其范畴地位的独特性、原始性。状貌词一般可独立成句,因为它自身即指一个完整的事态。不同语言状貌词的句法功能有较大差异,日语中的状貌词可做谓语、定语、状语,上纳卡萨托托纳克语(Upper Necaxa Totonac)的状貌词则仅限做状语(Beck 2008),Doke(1935)认为班图语的状貌词很接近副词。可充当的成分多,表明状貌词远离原初性,成为成熟语词。
3) 外部组合能力。状貌词往往需引导词才能与相关成分组合,常见的引导词有言说动词如say、做类轻动词do、指“像”(like)的动词以及代词等(Güldemann 2008)。汉语状貌词往往需要“的、地”的支持,也体现了对引导词的需求。
4) 表达功能。状貌词往往构成小句中的焦点信息(Childs 2003),有正极性(Kita 1997)、叙实性(Tolskaya 2011),状貌词常带示证标记。这都表明它描写的是第一手经验材料。
前述文献都是直接以状貌词为研究对象而得到的结论,而在形态学(Morphology)的一般研究中,学者提到的下面两个概念也都涉及状貌词的表达性及音义象征性:评价性语素(evaluative morphology)、表达性派生(expressive derivation)。二者属主观范畴,语义根据是对具体形象的描摹。(1)感谢匿审专家提示我们注意这一点。编码手段上则往往采取音义象征的形式。Scalise(1984)认为,评价词缀应视为区别于屈折和派生的一种独立的语素;Hippisley(1996)指出,俄语的表达性词缀兼有派生和屈折的特征。Barbaresi(2015:40)发现在不少欧洲语言中,重叠形式是表评价的手段之一,而重叠形式总是指向状貌义的,如英语lizzy-wizzy、teensy-weensy。Auer(1989)、Dressier 和 Barbaresi(1994)、Gregová(2011)都指出,评价义在语音形式上具有临摹性。以上研究成果都显示了状貌与主观这两种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主观性的根据则是话主范畴所包含的价值内涵(参看张新华2007)。
国外学者对状貌词鲜有语义特征的分析,这方面汉语学者做了深入探讨,主要涉及:临时性/可变性(朱德熙 1956;沈家煊 1997)、程度与量级(俞敏 1957;张国宪 2006)、主观性/评议性(朱德熙 1956;刘丹青 1986;董秀芳 2016a,b)、形象性(刘丹青 1986)、有界性(沈家煊 1997;张国宪 2006)、事件性(李劲荣和陆丙甫 2016)。 临时性/可变性是一部分状貌词的重要内涵,但并非定义特征,一些典型状貌词,如“孩子胖墩墩”很难说是临时性的。形象性是整体概括,而非语义特征。有界性的刻画概括面偏高,不能指出状貌词自身的内涵。事件性强调的是场景的阶段性,这应视为状貌词的伴随特征,并非其自身的功能所在。主观性/评议性的分析有合理之处,但失之笼统。董秀芳(2016a,b)认为“汉语派生结构的类型以表达性派生为主”,其中谈到了吕叔湘(1980)所述形容词的生动形式(即状貌词)。董文认为,“所谓生动化,其实是包括程度加深以及表达喜爱或厌恶等功能”。我们基本认同这个观点,不过认为,“喜爱或厌恶”属于状貌词所反映的表层情感内涵,从更概括的范畴层面看,这种情感内涵还体现为语力层面的感叹性、成句性。对状貌词量级大、程度高之类的概括最为普遍,也最具吸引力,但存在较大缺陷。比如,状貌后缀“-丝丝、-酥酥”就专指程度低,如“凉丝丝、麻酥酥”。一些状貌词貌似指大量,实际上是混沌性带来的副产品,并非自身内涵所在,“乱纷纷”指大量的物质碎片,这是混沌性的表现,大量是派生性的。王力(1943)明确指出,“‘热腾腾’并不等于‘很热’,而是把热的情景绘画出来”。另一方面,典型指性质词量特征的是程度副词,该组合却并无状貌功能,如“很/最/极贵”。性质词自身是抽象的,程度词量化和状貌词缀都可使其具体化、现实化,这是两种不同维度的语法操作,两者有相关性,但本质不同。
2.2 状貌词的基本语义特征
2.2.1质料性
特定谓词刻画特定事物的存在情形,谓词的语义特征决定于其论元的具体物质特征。状貌词所述事物为质料,这是它与其他谓词分别的根本所在,如“圆、红”仅指物质所形成的抽象外形、颜色,“圆润、红润”则渗透着物质内部的丰富肉质及向外散发的无限气晕。一般说来,所指物理质料性越强,作为状貌词的典型性就越强。一些词典释义即提示了该原理,如“茫茫,没有边际看不清楚(多形容水)”,“红扑扑,形容脸色红”(《现汉》)。质料的特征是[+强弥散性]、[+弱实体性],所以状貌范畴在事态特征上总是表现为朦胧、纷乱、交叠。质料的具体形式涵括:气、水、光、味、声、肉、情绪,都属典型的不可数名词。另外还包括空无,空无虽没物质,但状貌词还是强调质感,与真空不同。例如:
(7) a. 空无:幽幽 深深 寥落 黑洞洞 穷光光 冷清清 孤零零 赤裸裸 空空旷旷
b. 气:腾腾 濛濛 飘飘 乎乎 喘吁吁 气冲冲 喜洋洋 醉醺醺 轰轰烈烈
c. 光:皎皎 朗朗 金灿灿 白晃晃 亮堂堂 绿莹莹 恍恍惚惚 朦朦胧胧
d. 声:瑟瑟 飒飒 缭绕 闹嚷嚷 乱哄哄 静悄悄 清清静静
e. 味:勃勃 香喷喷 火辣辣 酸溜溜 麻酥酥 甜甜蜜蜜
f. 水:涔涔 淅淅 浩浩 津津 雾蒙蒙 湿漉漉 血乎乎 油脂麻花
g. 毛发(无数线条):茸茸 绒绒 乱蓬蓬 扎煞煞 褴褴缕缕 絮絮叨叨
h. 沙土(无数碎片):纷纷 簌簌 霏霏 薄松松 花里胡哨 斑斑驳驳 沸沸扬扬
i. 肉质:沉沉 葱郁 墩实 笔直 肉滚滚 鲜润润 颤悠悠 满登登 郁郁苍苍
j. 情绪/神态:怯生生 楞柯柯 乐悠悠 疯颠颠 羞羞答答 慌慌张张 不紧不慢
上述质料可进一步概括为两大类:“肉质”是一类,其他为一类,统称“气韵”。“肉质”和“气韵”都指混沌连续的物质,与清晰离散的个体相对。“情绪/神态”是肉质和气韵的加和,如“懒洋洋、娇滴滴、悲切切”首先体现为肉质上的物理状貌,其次暗示向外蒸腾的气息。
在ABB式状貌词中,少数A是名词,一般属上面的质料,如“水莹莹、汗津津、毛楂楂、气乎乎、意切切、雾茫茫、光闪闪、火辣辣、面团团、肉嘟嘟”;早期汉语中出现的“花灼灼、石嶙嶙”之类只是主谓词组,而未词汇化。“眼巴巴/睁睁”似乎属例外,其实它强调的是目光的意蕴,仍是质料性的,从“口巴巴”被淘汰就能明白这一点。学者多把“铁铮铮、虎彪彪”视为名词,其实它们形容词化了,比较“铁铮铮-铁铁的、虎彪彪-虎虎的”,一般名词就无此用法。
古汉语不同时期都有很多状貌词缀,如“-悠悠、-漫漫、-浸浸、-滴滴、-溜溜、-丝丝、-腾腾”等,都具有典型气韵性。一些词缀可用于多种质料,显示状貌词缀的多重语义功能。以“-乎乎”为例,例(8)呈现其在多种质料上的功能相通性。另外,同一性质由于所施用的质料不同,就表现为不同的状貌,如例(9)。
(8) a. 气:喘乎乎 b. 水:粘乎乎 c. 味:酸乎乎 d. 色:白乎乎
e. 光:明乎乎 f. 情绪:臊乎乎 g. 毛:绒乎乎 h. 肉:腥乎乎
(9) 水:绿油油 丝:绿依依 土:绿魏巍 肉:绿萋萋
从更高层面看,上述例(7)中所列的十种状貌词,可概括为下面三大类:
(10) 体状:矮胖 笔挺 滚圆 稀溜溜 厚墩墩 满登登 密麻麻 粗粗壮壮 空空荡荡
貌色:漆黑 崭新 粉扑扑 醉醺醺 娇滴滴 傻呵呵 文绉绉 白白净净 精精神神
触感:阴凉 酸疼 甜蜜蜜 硬邦邦 热辣辣 暖融融 空落落 清清爽爽 粗粗糙糙
体状指由事物全部物理质料堆积而形成的样态,貌色则撇开物质堆积,指事物在意识中的映像,触感编码事物对感知者的及物关系。体状、貌色基于视觉,可加“显得”,触感用“觉得”;“显得”、“觉得”都属系动词。这表明状貌词在大类上确实可与形容词归在一起。
质料性所带来的语法后果是:状貌词与所述事物有很强的个体选择关系,组合面不大,即特定状貌词仅限于描摹特定事物质料的呈现方式。极端形式如“四牡騑騑”,毛传:“马行不止之貌”;“骍骍角弓”,《诗经集传》:“弓调和貌”;“禾役穟穟”,《诗经集传》:“苗美好之貌也”。“騑、骍、穟”本是名词,在远古是人们生活中的常见事物,以其典型形象而被感知,后来就衍生出状貌用法。状貌词组合对象的扩大是由感知上的迁移、通感引起的,如“骍”显然本用于形容词马(《玉篇》:“马赤黄”),后用于弓。
2.2.2混沌性
性质词抽象性强,在量上的体现是模糊性;状貌词具象性强,在量上的体现是混沌性、驳杂性:事物内部分化为无限多的物质片段,却又无法准确离析。在混沌态中,外部整体与内部片段之间是直接渗透的,体现为“部分-整体”通贯,即同时做逐点扫描与整体扫描。性质词“直、香”虽也指要素汇总形成的貌象,但毕竟是抽象性的,状貌词“直溜、喷香”则聚焦内部无数质素对整体的通贯。古代学者对状貌词常用“盛貌”注释,虽没能揭示其具体内涵,却体现其部分-整体通贯的语义特点,如“ 赫赫南仲”,《毛传》:“盛貌”,《叠雅》(史梦兰 2015)对“堂堂、漉漉、英英”等70多个叠音词都释为“盛也”。在上古汉语,一组联绵词以同样的混沌方式而用于相近的质料,就很容易形成同源关系,如“蔽芾、觱沸、觱發”(均见《诗经》)指草木之盛、泉涌之盛、风烈之貌(朱广祁 1985:115)。
体状、貌色两类状貌词可与“一片/团/派”组合,是其混沌性的形态标志。触感类状貌词一般可用“一丝”,但不如“片、团、派”自由。这些数量词结构都有摹状性、区域性、混沌性,并与状貌词语义一致。
(11) 一片/团通红 一片/团黑沉沉 一片/团郁郁葱葱
(12) 漆黑一片/团 白茫茫一片/团 眼中漠然一片/团
(13) 一派从容/优闲 一派荒芜/蓊蓊郁郁 大厅一派庄严、肃穆
(14) 一丝阴凉/甜蜜蜜/热辣辣/空落落
一些指颜色的性质词前加“一片”也会状貌化,如“眼前一片白”。缺乏外显形象的词语就不接受上述数量词,如*“一派公公平平/仔仔细细”。
状貌词的[混沌]是静态性、空间性的。需注意,动作动词也有一种混沌态,如“汹涌、招展、飘荡”指无数要素的动荡,而又无法准确离析(详看张新华2020)。吕叔湘(1980/1999)生动形式表中,有不少动词构成的AABB,如“打打闹闹、拉拉扯扯、敲敲打打”,动态性还很显著,属混沌动作动词,而非状貌词。比较:“那长袍飘飘荡荡”指当下动态事件,属动词的重叠用法;“老李一生飘飘荡荡”则失去动态性,就成为状貌词。ABB有所不同,虽然不少ABB动态性很强,但人们通常对这种动态性很不敏感,而是将其模糊为静态,就状貌化了,如“光闪闪、笑呵呵、气吁吁”。这表明词框ABB比AABB指状貌的功能更强。名词、量词可用AABB、ABB模式构成状貌词,其机理也在于此:把本来清晰的物质片段,模糊化为无限大量的混沌态,如“坑坑洼洼、密麻麻、赤条条”。
状貌词的语音相似性已成共识,但多限于从语音本身观察;其实状貌词还存在更高层面的象征,即重叠形式本身:用语音的重叠、复沓,象征状貌要素的无限交织。这个原理体现在两种语言现象。一是,较之语素义清晰的现代汉语状貌词,那些语素义含糊的古汉语重言,指状貌的典型性更强,如“凄凄、婀娜、剔留秃鲁”指状貌的典型性高于“清凉、柔美、圆转”:前者词义中包含着事物存在的无限气韵,是象征性、混沌式的,后者则寡淡得多,是离析式的。二是,拟声词在体貌词组中的功能特征。体貌上,无论独立成句还是作状语,单音拟声词A都指一个瞬时性、已完成的动作,不是持续体,如例(15)a。而状语AA就既可指客观的两下动作,这时指完成体,如例(15)b 的默认读法是动作只进行客观的两下就完成了,其中“当当”之后可加上“两下”;也可指动作的无限重复,这时指持续体,即把无数动作片段汇聚为状态,如例(15)c。形式上只用两个音节,语义上却指无限重复,这是一种高效的象征。这种修饰关系还成语化,如“喋喋不休、袅袅不绝”,指动作的无限性。
(15) a. 当,他敲了一下门。
b. 他当当(两下)敲开了门。
c. 他(一直)当当地(一直)敲着门。
ABB、Abcd拟声词状语也是既可用于完成体,如例(16),也可用于延续体,如例(17),但所指动作过程比AA复杂,时间也长。
(16) a. 那鹅忒楞楞就飞去了。 (17) a. 大汉手里忒楞楞地转着两粒铁弹子。
b. 一群人噼里啪啦冲到天台。 b. 鱼儿噼里啪啦地在包围圈里蹦跳。
不同于AA状语,即便是完成体,ABB、Abcd所指动作也仍是复数性的,默认读法是包含一个复杂的内部进程,并非客观的三下或四下。这表明该形式的象征性更强。
[混沌]与[质料]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以质料方式存在的事态必是混沌的,混沌也只有通过质料体现出来。从物理学看,典型的混沌态是气、水,它们总是需要在宏观层面加以把握,该宏观状态一定由无数微粒所构成,但又不可准确离析。
2.2.3限定性、感叹性
质料、混沌是状貌范畴的构成性语义特征,限定性和感叹性则是状貌范畴在主句层面的表现。谓词限定性的实质是所述事态相对于认知主体所处时空域进行定位,即现实存在性。一般谓词在词汇层面是抽象性的,构成小句时要通过时、体、情态等成分操作为具体事态,状貌词则直接编码感知主体所面对的一个特殊情景,具有直接现实性、指示性(deixis),而无需时、体成分的支持。古汉语状貌词常直接构成主句,AABB还常单独构成一个分句,这足以证明状貌词的限定性特征。例(18)中的“穆穆皇皇”直接独立成句,例(19)中的“井井”则是对对象的直接描述,两者所描状的都是感知主体所面对的具体场景。
(18) 干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诗经·假乐》)
(19) 仍乞罢诗赋,专经学论策,条目井井。(《朱子语类》)
现代汉语状貌词在典型性上形成较大分化,在限定性的表现也相应有别。状貌性最强的是BA及来自古汉语的重言词,最弱的是后来形成的叠加式AA,ABB与AABB居中。句法上,BA可独立构成谓语,AA则需语气词“的”的支持:“地板锃亮”“地板亮亮的/*地板亮亮”。ABB与AABB对“的”的要求是非强制性的:“屋里亮堂堂/亮亮堂堂(的)”。
状貌小句的限定性虽然往往并不通过时体成分来确定,却常通过感知动词加以提示。动因是:状貌范畴内在诉诸感知行为;而感知动词提示了感知主体的存在,这样,通过联系感知动词,状貌小句也就实现了向主体定位,即获得限定性。语义上,状貌小句都是感知动词的内容宾语,强烈提示“你看、只见、只听、只觉”之类的高位感知动词,后者并往往要显性编码。将例(20)中的“你看”和例(21)中的“只见”删除,小句的状貌义仍然存在,但缺乏指示定位的完备感。
(20)你看这一大片麦子,齐刷刷,沉甸甸。
(21) 在农业园区,只见碧绿青壮的花椒树上缀满油润饱满的花椒。
上述感知动词并不限于用在状貌句,也可用于其他指具体事件的小句,但在后者并非必需,所以使用时就有强调义,而前者是内在带有的,所以反而并无强调义。
(22) a. 我来到了这个工厂,只见各车间冷冷清清,半成品车间空荡荡的。
b. 我来到了这个工厂,各车间冷冷清清,*只见半成品车间空荡荡的。
(23) 九平时,(只见)叶诚突施杀手,(只见)一记追身球从新鹏身边擦过。
例(22)是状貌句,两个小句都强烈提示“只见”,用于前一小句,可管辖后小句,所以a句成立,整个句子也不表强调;只用于后小句,就无法管辖前小句,所以b句不成立。例(23)是普通事件句,“只见”可自由用于两个小句之前,使相应的小句得以强调。
“感叹性”指状貌词内在带有情绪、赞叹的主观内涵,强烈表现了外界事物与感知者主客交融的特征。状貌词所述事物都是主体生活中的东西,与之存在显著的利害关系,形成价值态度。列维-布留尔(2009)提出原始思维有“互渗律”的特征,状貌词是语言系统中的远古留存,也体现了这一点。这在古汉语状貌词尤为显著。如“穆”,《说文》:“禾也”,由于人们喜爱、敬畏禾,这种情感就凝固在“穆穆”的状貌里。《诗经》重言词很少纯客观描写,“杨柳依依、维叶萋萋”只是普通主谓小句,却明显带有积极情感。
状貌短语内在带有语力和存在义,并且,这两个要素具有“扩散效应”,即,短语内部状貌成分所带的语力和存在义可向上扩散,使整个小句带有限定和感叹的特征。在用状貌词的小句,状貌是整个小句所述事态的语义支点。如,“碧绿的草地看起来清凉诱人。”“碧绿”不单指“草地”的颜色,还暗示感知主体当时就处于该场景。“运动衫裤空荡荡地挂在身上。”“空荡荡”提示小句事态是当下现实存在的。
做定语时,状貌词总是授予中心语限定的特征,这与性质形容词形成对比。“白茫茫的雪、热腾腾的水”表定指,而“白雪、热水”是类指。限定名词的实质也是现实性:所指事物实际存在于当下言语情景中。限定名词也可接受状貌定语,这构成同位语性质的非限制(non-restrictive)关系小句:“胖墩墩的张宇”;性质词则无此功能:“*胖的张宇”。
3 状貌词由综合性向分析性的演进
纵观汉语史,状貌范畴的编码方式发生了一个大转换。这方面的语言现象纷繁复杂,但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上古汉语重言词整体功能退化,不过并未完全消失,而是选择四个出路:进入成语、演进为普通谓词、构词语素化、派生词缀化;词缀化导致Abb形成。二是由重言词而改为普通实词构成AA、AABB,并副词化;该过程背后的语法性质改变是:重言AA是语音重复,实词进入AA、AABB就发展为构词叠加,并进一步演进为构形重叠。要之,重言是上古汉语状貌范畴的最典型形式,其功能发展也构成状貌范畴演进的根本线索。这个演进过程造成:状貌范畴的综合性降低,分析性增强。
3.1 AA重言词的演进
重言的编码策略是描摹,即“拟”,包括拟声、拟态,这是语言系统的起源之一。形式上,重言词是纯粹的语音重复,内部不存在任何语法操作,其中单字一般都可以独用,表义与重言式无别,重复的功能体现为语用加重(朱广祁1985;石锓2010等)。随着语言系统的发展,重言逐渐退出舞台,基本时间线索是:重言词在先秦极为发达,《诗经》《楚辞》是其代表。两汉魏晋仍产生不少新重言词,如“晞白日兮皎皎(王褒诗)、徨徨所欲(曹操诗)、童童苦树(白居易诗)”。唐代则不但很少产生新词,前代诸多重言词也被淘汰。唐代也恰恰是近代汉语的开始,而状貌词由综合性向分析性的演进与之正好平行,这不是偶然。
重言后来大量演进为普通语词,即状貌义丧失、“去拟态化”(Marivate 1982;Mfusi 1989等),这是语言系统普通语词的一个重要来源,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以古汉语使用频率极高的“悠悠”为例。它在《诗经》时代很活跃,如“悠悠昊天、悠悠南行”,汉语史上,这一直是“悠悠”最主要的用法。另一方面,单字“悠”也与其他语素组成“悠远、悠长、悠扬”等状貌词。宋代,“悠”形成普通谓词的用法,到清代,这种用法成熟下来。例如:
(24) 满眼新晴,歌声妆影,悠荡碧云心。(《宋·赵子发词》)
(25) 用力一晃悠,只听噗咚一声响。(《三侠剑》)
(26) 树上之人便攥住树杪,将身悠起。(《七侠五义》)
(27) 说是这等说,二叔,你老也得悠着来呀!(《儿女英雄传》)
前两句“悠荡、晃悠”是以双音节形式发展为普通及物动词,“悠”的性质是构词语素;后两句则是“悠”单独演进为动词。语义特征上,状貌词“悠悠”是混沌性、静态性的,不能带宾语,不接受体貌成分,时间特征模糊;动词“悠荡、悠”是分析性的,完全丧失状貌义,可带宾语、体貌成分,时间特征清晰。
AA由语音重复(即重言)整体性地改变为构词叠加的演化发生在唐宋。其标志是越来越多的性质词进入AA框,如“急急、连连、厚厚、短短、远远、满满、轻轻”等。即AA这个语音框本来就有,但后来人们不用于构造重言词,而是用普通实词填充。实词通过AA叠加而指状貌,其操作指向是词根自身的词汇义。叠加对词根的处理是混沌式的,“黑黑(的)”并非简单对基式“黑”本身加以强调,而是指无限黑的要素汇聚形成的整体形象;相较之下,典型构形的动词重叠“走走”就是明确表示“走”本身的一次执行。
性质词的内涵包括属性和程度两方面,属性与状貌具有关联性,性质词AA叠加式所激活的主要是基式所关联的状貌内涵,其次才是程度量的特征,而且是一种很弱的特征。因此这种AA容易接受“有点、这么”之类不典型量化成分的修饰,却难接受典型量化成分“非常、太”的修饰,更难进入比较句。AA状貌义显著、程度义弱也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可与另一个同样是叠加的AA或重言,临时组合在一起,指一种更加浑杂的状貌,次序自由,如“红红绿绿、葱葱绿绿”。
但与重言相比,叠加式AA由于存在一个清晰的基式,词框内部形成明确的语法操作关系,这就表现为分析性,而分析性提高的后果必然是状貌典型性降低:叠加式要比重言词状貌义弱得多,如“高高”的意韵性不如“巍巍”。
在观察AA的功能演变时,要把状语与谓、定、补区别开:前者会导致状貌词虚化,后三者不会。只要状貌词常规作状语,就会副词化。这有两种情形:一是重言词的述谓能力降低而直接副词化,但语义并不改变,也未分析化,这是情状副词,有成语性,如“绰绰有余、冉冉升起”,此处不讨论。二是发生分析化的演进,语义上也发生根本改变:由指事物的样貌,转而指动作进行的时间、空间、规模、程度等,量的特征显著。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早期的重言直接副词化,二是后来的叠加式AA副词化;后者的分析化、形态化程度更高。下面各取一例加以观察。前者如“悄悄、草草、忽忽、累累、泛泛”。以“忽忽”为例,它本指模糊不清,与“茫茫、渺渺”同义。作为重言词,双音“忽忽”与单音“忽”功能无大分别:
(28) 忽忽乎如将不得,渺渺乎如穷无极。(《管子》)
(29)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国殇》)
“忽忽”由指物理状貌的模糊,如例(30),转而指意识状态的模糊,如例(31):
(30) 眇眇忽忽,若神之仿佛。(《子虚赋》)
(31) 心眇眇以忽忽。(《神女赋》)
后来,“忽忽”常用于句首,指与人生相关的时间,主观体验性明显,即无意识之中,一件事即告完成。这就有副词化的迹象,但尚不成熟,例如:
(32) 日晴桑叶绿宛宛,春蚕忽忽都成茧。(《黄庭坚词》)
(33) 忽忽过了残岁, 又是建文二十年春王正月。(《清·女仙外史》)
进一步地,“忽忽”常用在主语后谓语动词前,指普通动作进行的快速。这就成为时间副词。例如:
(34) 正待回身,陶守仪已忽忽跑了出来,把周敦五拉住。(《江湖奇侠传》)
(35) 且孝服未除,忽穿色衣,忽忽归去,与父母商量。(《娱目醒心编》)
例(35)前句用单字“忽”指突发,后句用“忽忽”指匆忙,表明二者形成分工,都存在于当时语法系统中。重言词“忽忽”是混沌性的;作为情状副词,指清晰的动作进程,则是分析性的。这种分析性源自所饰动作的分析性,所谓语境吸收:“忽忽”常修饰具有清晰时间进程的动作动词,逐渐就把该进程义吸纳为自身的词义内涵。
叠加式AA的副词化往往导致更强的分析化、形态化演进。这种状貌词有“白白、大大、死死、明明”等,下面以“远”为例做一阐释。单字“远”出现甚早,甲骨文、《诗经》已很常用,但叠加式“远远”直到唐宋才大量使用,且一出现就以作状语为常,例如(36),其次是定语和谓语,如例(37)、(38):
(36) 依依向余照,远远隔芳尘。(《李商隐·离席》)
(37)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白居易·夜雨》)
(38) 桃溪近,幽香远远。(《黄裳·宴琼林》)
上述“远远”是状貌词,构词叠加,强综合性,不指程度增强,而指一种富有气韵的物理距离。表现在:一是所述事物、动作是具体性的,二是感知主体对所述事物、动作有很强的现场性。例(38)前句用单字“近”,是客观陈述,后句用“远远”,指对幽香内涵的丰富体验。
历史上,“远远”长期保持状貌词功能,直到现代汉语才副词化,并在语法意义上发生质的变化:由指物理距离大变为指纯量的差距大,物理位置、现场性的内涵完全丢失。这种变化发生在两种语法环境:一是比较句,比较就涉及一个标准,“远远”指超过该标准的幅度大,如“他们失去的远远比得到的多得多”。二是否定句,这时“远远”表现为负极词,不能用于肯定句,分析性更强,接近纯量义,例如:
(39) 债务危机远远没有结束。
(40) 这些数据目前的技术远远不能分析清楚。
(41) 他远远不了解大家的积极性。
(42) 他对你还远远谈不上爱。
否定词指对肯定成分所指实质内涵加以去除(张新华和张和友2013),该内涵总是表现为一定的量,“远远”指当前关注的对象在量上与该内涵相差甚大,可换为“完全、压根儿”。负极词的语用功能是强调,语义基础则是梯级量(Ladusaw 1996;Israel 2011等),量是分析性的典型形式。“远远”有负极词的行为,表明其分析性的特征已很显著。句法上,“远远”属构形重叠:指对基式“远”的程度加强。
3.2 AABB的演进
AABB本来是AA重言的加长版,但表述功能更为强大:可把两种不同的事态融合为一个状貌统一体,并可大量临时构造。中古以前,AABB是两个语义相近重言词的叠用,指典型状貌,强混沌性,不存在结构关系,词序随意(石锓2010等),如“渺渺茫茫、茫茫渺渺”。后来,大量普通实词进入AABB词框,分析性增强,状貌典型性则降低。有两类构造方式:一类是AA+BB加合,如“羞羞迷迷、迷迷离离”,词序仍较自由;另一类是基式为AB的普通谓词叠用。特别是,主谓、动宾、偏正等AB也可进入其中,如“肉肉麻麻、放放心心、笔笔挺挺”,语义机制是:打破基式本来的分析性特征,以造成混沌的效果。
AABB的词框大,可进行的语法操作空间也就大,这就使其更容易接受指抽象义的基式,如“地地道道、公公平平、认认真真、完完全全”等。这造成AABB的状貌功能减弱,分析性增强。重复的基本策略即相似性:通过形式增大带来量的增大,而基式所属范畴不同,重复所表增量的内涵也不同。对那些状貌特征显著的基式,重复的功能就表现为提高这些状貌的质料复杂性、混沌性,因此表现为构词叠加,状貌义也更强。抽象形容词的核心特征则是去质料化,由此形成两个语义参数:类指、程度,所以叠用就表现为量的强化,这就使其向构形重叠发展,状貌义丧失。构形、句法手段是强分析性的,构词现象的机制则主要表现为综合性、融合性。
3.3 ABB的演进
这个词框内部关系差别很大,在各类状貌词框中最复杂。首先要将A是名词的主谓式与其他形式分开:该式是ABB整体词化,如“眼睁睁”;其他形式A与BB表现为不同的语义关系,并造成ABB性质的不同改变。下面只讨论主谓式之外的ABB。
ABB整体作为一种词框,BB不一定发生虚化。A与BB的关系可概括为两种:并列,A与BB各指一种独立存在的事态,如“寒寂寂、玉纤纤、白胖胖”,该词框与AABB相通,其BB为叠加,一般不虚化;中(即“中心语”)状(即“状语”),BB在语义等级上低于A,对A起殊指化的作用,其BB易虚化,如“暖洋洋、醉醺醺”。这两种词框历史上长期并存。如元代Abb已很发达,但ABB能产性同样很强,如“深密密、翠弯弯、小弓弓”。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如“白乎乎、白亮亮”。
下面讨论词缀 -bb的形成机制,其动因在于状语后置。学者多将“红彤彤”之类分析为述补结构,我们认为应该是中状。当然,也有学者把传统述补都视为中状,本文并不是在此意义上理解,而仍在传统语法系统理解。中状结构在古代汉语并不少见,且其中心语不限于单音节,如“伐木丁丁、将其来施施”(《诗经》),“依弦度曲婉盈盈”(《南朝·张率诗》),“枫叶落纷纷”(《李白诗》),“金樽酌湛湛,歌扇掩盈盈”(《唐·陈子良诗》)。实际上,中状格式在苗、藏等语言中极为普遍,如苗语“ngit(看),bub jub(呆呆貌)”(严素铭1987:50)。
由于中状与汉语常规的状中结构差距甚大,难以相容,语言系统就会努力把它挤压为一个信息单元,所谓重新分析。这导致两个语法后果:一是ABB整体词汇化,二是BB的谓述地位下降,并由此导致语义虚化,形态上也就词缀化。这一演化的直接动因是BB失去时间特征,由动态改为静态:动态的特征是殊指,静态则是概括,由动到静就表现为虚化。“烛烟昏雾暗腾腾”(李绅诗)指当下事件,“腾腾”的实义性、状语性明显;“只貊终日醉腾腾”(陆游诗)是长时性的,“腾腾”就虚化、词缀化。由此原理可知:相比动语素A,形语素A后的BB更易词缀化,如“暗腾腾”的虚化比“终日坐腾腾”(《孟贯诗》)强。
在中状ABB中,A指类,语义特点是潜在性、一般性;BB指方式,现实性、个别性,如“急”指一般情绪,“慌慌、煎煎、攘攘”指其不同的状貌表现。BB的虚化意味着方式范畴的类化:不同的抽象性质采取同样的表现样貌,“急、乱、忙、惊”均可呈现“慌慌”的形式。性质通过状貌现实化,其机制平行于动作由体貌而现实化:都是由类转化为个别。状貌专职词缀 -bb的形成,表明状貌范畴形态化程度的提高。
Abb的发展过程所涉及的具体语法现象很多,可概括为三方面:1)A由状貌词扩大为性质词,2)bb由重言词扩大到普通实词,3)整个Abb由指具体状貌发展为指抽象属性。三者都导致Abb分析性提高。状貌词A即重言词的单音节形式,早期多由其构成Abb,bb起修饰强化的作用,这显示状貌范畴的编码策略还是侧重用原初状貌词。这种格式在魏晋诗歌很多,bb虚化很弱,整个Abb形象性、综合性很强,如“灼烈烈、婉盈盈、郁青青”。后来,随着上古汉语重言词功能的整体蜕化,越来越多实词进入ABB,这一方面导致ABB状貌性减弱,另一方面也导致BB虚化加强。相比“碧沉沉”,“绿沉沉”的综合性就差些,因为“碧”自身的形象性高于“绿”。随着BB 所组合的实词增多,必然导致BB与A的语义关系疏远,BB的虚化提高,如“静沉沉、空沉沉”比“绿沉沉”虚一些。
在词缀化过程中,上古汉语的重言词主要起触发作用,自身虚化为词缀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后来的实词演化为bb,如“-溜溜、-哄哄、-丝丝”。在具体义形容词身上,[量]与[状貌]是两个同时存在的语义维度,但对表达层面的实际语法现象而言,二者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形容词分析化程度提高的直接结果就是状貌义削弱,量义增强;反之,强状貌义的重言词就抑制量义。分析化的根据即所述事物的质料义磨损,这就造成与所组合成分之间的语义一致关系弱化,选择面扩大。重言词形成的词缀有“-悠悠、-漫漫、-幽幽、-凄凄”等,虚化程度都不高,多可作状语;虚化最强的是“-乎乎”。如,“白皑皑”形象性极高,缺乏量特征,不接受“有点”修饰;“-乎乎”的质料义完全丢失,分析性强,“白乎乎”就接受一些量化修饰,如“有点白乎乎的”。“-溜溜”早期限于指水滑的A,如“酸/滴/光溜溜”,后不再有此限制,如“窄/紫/穷/憨溜溜”。一般而言,实词bb构成的Abb式,都接受某种量化修饰。总体看,现代汉语状貌词诸格式量义都明显强于上古汉语,表明其状貌典型性降低。
整个Abb格式被用于指抽象义,显示状貌词框的语法功能发生重要改变,但这种Abb词例还很少。如“干巴巴的双唇/几句话、响当当的银元/汉子、顺当当地溜进去/赚钱”,其中Abb修饰斜线后成分时就抽象化。当A为强抽象词时,Abb物理状貌义就根本丧失,这对状貌词框是质的改变。这种Abb极少,较典型的是一个“好端端”,它有两种用法:做定语,指物质构造完整(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做状语,指无缘无故(怎么好端端地又流起泪来?);两种用法都没有物理状貌义。一般Abb中的性质词A,其抽象义更多属于统指,仍与状貌高度关联。如,“-乎乎”虽组合面很大,“A乎乎”却仍强烈指向状貌:白乎乎(颜色)、硬乎乎(体状)、香乎乎(味道)、傻乎乎(神态),但:“*好乎乎”。
相比AABB,ABB作为状貌词的词框更典型。体现在:一是ABB比AABB更难接受强抽象性质词,比较:公公平平:*公平平;?容容易易:*容易易。二是同样的基式AB,进入AABB可指抽象义,ABB则指物理状貌,如:“白天才拿到派出所的户口本、身份证,晚上便被齐齐整整/*齐整整办好。”“齐齐整整”不指户口本、身份证的物理形态,而指“办”的行为完备,抽象性强;“齐整整”更侧重指具体物理状貌,所以难做泛化动词的状语。
4 结语
本文认为朱德熙(1982)所述“状态形容词”的语法意义是状貌,并把它的语义特征分析为[质料]、[混沌]、[限定]、[感叹]。跨语言看,状貌词是个普遍现象,多采取重复及语音象征的编码策略。AA、AABB、ABB在上古汉语都属重言现象,其语法性质表现为语音、话语层面的叠用,象征性、混沌性显著,状貌义典型。近、现代汉语主要由普通谓词进入其中,性质上就变为构词叠加,成为状貌范畴的主要词框,但分析性增强,状貌典型性降低。进一步,一些强抽象义谓词也进入这些词框,就获得构形重叠的特征,物理状貌义完全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