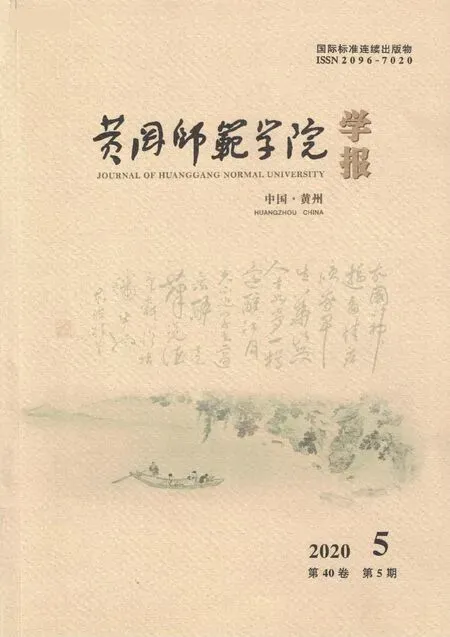苏轼古琴艺术美学思想及审美体验论析
谈祖应
(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湖北 黄冈 438000)
据《苏轼全集校注》,苏轼以琴为题材的诗、词、文计有八十余篇,内容非常丰富。北宋以降,人们对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以及经学思想都曾进行过乐此不疲的解析和极盛的赞誉,但对其古琴美学思想,却缺少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的阐析。笔者潜心阅读苏轼全集文本,从八十多篇琴诗、琴词、琴文中,披沙拣金,寻找苏轼关于古琴美学思想的阐发,撰成此篇,以就教于方家。窃以为,同他最早提出“文人画”概念并为其立论一样,苏轼有关“古琴”的美学思想及其审美追求,具有文人化审美意趣和审美体验,精妙绝伦,且独具特色,对古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丰富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苏轼古琴艺术的美学思想
古琴,是极具东方音乐特质的最佳“雅器”,古琴乐曲,是最具中国古典文人气质的书香音乐。《左传·昭公元年》:“君子之近琴瑟,以节仪也,非以慆心也”[1],这里说的是古琴修身养性之功能。司马迁指出:“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士大夫听琴瑟之音乐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2]。这里说的是,古琴乃登大雅之堂的“圣庙之乐”,其琴德最优(《新论·琴道》)。古琴与数千年来文人精神与文化血脉相连,《颜氏家训》指出,君子“左琴右书”。后来人们把琴、棋、书、画统称为“文人四艺”。在文学艺术领域,古琴与文人实为一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古琴已被文人注入了文化生命,散发着闲雅的文人气质,铸就了文人琴的美学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和理想人格的象征。儒家以“礼、乐、射、驭、书、数”六艺为教育弟子的基本内容,古琴是一项必修课。故有“君子无故不撤琴瑟”(《礼记》)之说。孔子的儒家弟子,后世的文人君子等睿圣贤达,都与古琴结下不解之缘。苏轼为“文人画”立“重意、略形、寄情、讬志”四标准,为“文人琴”而树“古意、遗形、静照、真同”四特质。
(一)“古意” 自有历史记载始,古琴就为文人君子所倚重。如上古时期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故事,说明古琴作为文人以琴言志,具有琴人合一,道艺合一,礼乐合一的“三合一”特征,是与文人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儒雅之器。古琴自古被圣贤思想熏染上了书卷文墨之气,富有古老、古意、古调、古韵的品格,和既典雅纯正,又淡泊宁静的审美意趣,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甲骨文琴字是会意字,为在木品上施张丝弦的弦乐器,说明在使用甲骨文的时代,远古先民就创造了古琴。典籍中有“伏羲作琴,神农作瑟”,“舜作五弦,此后文武王各增一弦,合为七弦”(《古史考》)之传说,这种种,赋予古琴诸多的文化寓意。
苏轼深谙古琴文化特质,对其“古意”体味最深。嘉祐四年(1059)冬,时年24岁的苏轼,九月除母服,十月在父苏洵的率领下同弟苏辙自眉州从岷江入长江,下三峡而抵荆州度岁。三苏父子行水路1680余里,舟行60日。夜行至渝州(即今重庆),苏洵江上抚琴,苏轼作《舟中听大人弹琴》诗为之记。
……
自从郑卫乱雅乐,古器残缺世已忘。
千年寥落独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阅兴亡。
……
无情枯木今尚尔,何况古意堕渺茫。
江空月出人响绝,夜阑更请弹《文王》[3]19。
这首《舟中听大人弹琴》,是作者对古老、古韵的古琴发出的第一声咏叹。该诗记叙了他们的父亲苏洵,在“江空月出”的“江浦”弹奏古琴的情景。作者整理好衣襟偷偷地静听,被“大人”清逸悦耳的琴声所“激昂”,而内心不能平静,由此引发出对古琴美学的鉴赏。其主旨是对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琴特质之“古意”给予了关注。诗中指出,千百年来古乐器多残缺寥落,唯古琴累代不绝。诗人用了不死的“老仙”作譬,道出了古琴存世年代古远的事实,此其一。对后世“独反古”的浅薄之士,强以浮浅新曲和拙劣技法与古琴抗衡的行径提出讥评。赞赏《风松》《玉珮》等琴曲之“太古自然之妙”,此其二。琴之为器,“系政教之盛,关人心之邪正”(《琴学正声》)。范仲淹有言:“将治四海先治琴”(《听真上人琴歌》)。苏轼亦指出:“无情枯木”“琴独在”“有如老仙不死阅兴亡”。是的,相传春秋晋国乐师师旷,以《楚辞》中《宋玉答楚王问》典故所作的、我国著名十大古曲之一的《阳春白雪》;据传蔡文姬在归汉途中,以胡茄音调创作的琴歌《胡笳十八拍》;魏晋时期思想家、音乐家嵇康,为司马昭所害,临死前抚弄的琴曲《广陵散》;晚唐著名琴师陈康士根据同名抒情长诗《离骚》所作的,抒发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惨遭奸谗迫害的忧郁和苦闷的琴曲《离骚》等等,都演绎出“千古兴亡”“百年悲笑”。
欧阳修对古人与“古琴”有过评说:“古人不可见,古人琴可弹。弹为古琴声,如与古人言”(《弹琴效贾岛体》)。这里指出从“古琴声”中,可以得闻“古人言”。苏轼同样对古琴之古调古韵颇有研究。元丰四年(1081)六月二十三日,他的老朋友陈季常来黄州造访,会客有喜琴者出所藏宝琴弹之。苏轼为之作《杂书琴事十首》,又作《杂书琴曲十二首》赠陈季常。对乐府《子夜歌》《凤将雏》《前溪歌》《阿子歌》《团扇歌》《懊农歌》《长史变》《杯拌舞》《公莫舞》《公莫渡河》《白紵歌》《瑶池燕》等古曲,逐一进行评点。
嘉祐八年(1063)春,苏轼在凤朔任上作《次韵子由以诗见报编礼公借雷琴记旧曲》诗,对“琴中古意”又作阐解。诗曰:
琴上遗声久不弹,琴中古意本长存。
苦心欲记常迷旧,信指如归自著痕。……[3]295
“编礼公”,即苏洵,他曾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太常礼书,故称其为编礼公。诗中说父亲大人“久不弹”古琴,但“琴中古意久长存”。也就是说,古琴的古调古韵、古雅古趣是永久长在的。苏洵有的古琴曲虽久未弹奏,但曲调的古意未忘。因其“迷旧”(迷恋古老旧曲),他“苦心欲记”其旋律,有时不依旧曲,信手而弄,自由发挥,但曲调古意的遗韵不减。这说明:三苏父子,对古琴“古意”特质了然于心。
(二)“遗形” “古意”,是作者对客体(古琴)的认识;“遗形”,是作者对主体(琴人)的体认。苏轼约于熙宁二年(1069),在开封为文与可所作“琴铭”中便有推阐,其“琴铭”曰: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萧然,如叶脱木。
按之噫然,应指而长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遗形而不言者似仆。——《文与可琴铭》[4]2108
该“琴铭”共四句,前两句写琴,用自然现象描摹琴声,“如水赴谷”“如叶脱木”形容古琴的音色,让人产生丰富的诗意联想。后两句写人,作者用按之琴弦发出长长的噫然“叹息”,比喻文与可最为擅长的“长言”文学作品,即楚辞。第四句,引用《庄子·大宗师》:“离形去知,同于大道”[5]240之“离形”这句话,形容自己超脱形体的拘执,精神进入忘我境界。该“琴铭”把人和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是铭琴,亦是铭人。明确提出操琴的人应该进入“遗形”状态,唯有如此,“遗形得极乐”(宋·梅尧臣《长歌行》)。这种“得极乐”之“遗形”状况,作者在多篇古琴诗文作品有过描写。如元丰二年(1079)正月三十日作于徐州的《游桓山,会者十人,以“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为韵,得泽字》诗中,生动地记叙了游桓山诸君,被“春风在流水,凫雁先拍拍。孤帆信溶漾,弄此半篙碧”的泗水之滨幽静清秀的美景所“遗形”,聆听着“幽响清磔磔”的琴声,发出“此欢真不朽”的慨叹。
嘉祐八年(1063)秋,他在《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其十中,也记述了这一“遗形”的心理感受。时作者游终南山,但见满目苍翠,心随白云,梦绕山麓,心旷神怡,超脱形骸,进入忘我精神状况。这种超然自得的心境,“有如採樵人,入洞听琴筑”(同上)。于是,作者从终南山“归来写遗声,犹胜人间曲”[3]371。作者在终南山下享受这美妙的“人间曲”,其前提是在“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5]228的“遗形”状态下获得的。即遗忘身内的肝胆,遗忘外面的耳目。用超功利的审美心理让生命随着自然循环变化,安闲无系地神游于尘世之外,逍遥自在于自然的境地,从而获得人琴合一,超功利的“大美”“至乐”。
(三)“静照” 元祐七年(1092)末至八年(1093)春,苏轼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守礼部尚书期间,作《次韵奉和钱穆夫、蒋颖叔、王仲至诗四首》之《见和西湖月下听琴》:
……
半生寓轩冤,一笑当琴樽。
……
月明委静照,心清得奇闻。
当呼玉涧手,一洗羯鼓昏。……[3]4105
作者言自己半生寓身官场,常与文士嘉朋宴集。今晚月光照在大地一片娴静,心地清爽闻到妙香。此时,应当邀请庐山玉涧道人崔闲演奏一曲古琴曲,用以洗涤去昏恣的外夷羯鼓声。该诗描述了苏轼和几位朋友,于西湖月下听琴的审美感受。因为“月明”,方得“心清”,因有“静照”,尤得“奇闻”。幽静安逸的审美环境,营造出奇妙的审美享受。
元丰七年(1084)正月,苏轼在黄州作《减字木兰花》词,对营造古琴审美环境表达得更为充分,词曰:
神闲意定,万赖收声天地静。玉指冰弦,未动宫商意已传。……[3]457
神情闲逸,心境淡定,大自然万物寂静无声,天地一片凝静,这就是苏轼营造的欣赏古琴雅乐的审美环境。这种静雅的文化环境,前人多有记述。如: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王维《竹里馆》
闲坐夜明月,幽人弹素琴。忽闻悲风调,宛若寒松吟。
白雪乱纤手,绿水清虚心。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
——李白《月夜听卢子顺弹琴》
鸟栖鱼不动,月照夜江深。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
——白居易《船夜援琴》
从王维、李白、白居易三首诗中,可以寻到三个有共性的关键词:“明月”、“闲坐”、“心静”。这说明演琴、听琴多选择在月色之中。夜闲人静,月色如水,琴声悠悠,撩拨人心,弹古琴俨然像参禅时的静寂。故北宋琴家成玉说“攻琴如参禅”。苏轼的“静照”,正是琴人对古琴审美环境的准确写照。
(四)“真同” 元祐七年(1092)四月二十四日,苏轼知守扬州,为恩师欧阳修《醉翁吟》作《书醉翁操后》。该题跋曰: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应。今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作诗,而与琴会,此必有真同者矣。……
有能不谋而同三合无际者,……[4]8047
两样的水放入同一器皿中,两水不相渗入;一人弹两架琴,两琴调声不相融合。太常博士著名琴师沈遵君信手弹奏的琴曲,而与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描写的琅琊山水情景十分契合。欧阳修居士纵笔作诗,而与古琴趣会,这里必有古琴音乐艺术“真同”的契机。这种“真同”,就是能做到“三合”,即手与琴、琴与景、诗与琴曲三者之间意境融合,情境协调。这种“三合”之“真同”,当是古琴艺术美学的最高境界。
说到琴师沈遵为欧阳修《醉翁吟》谱《醉翁操》曲,琴界盛传一段佳话。苏轼在贬谪黄州的元丰五年(1082)冬作《醉翁操并引》,记述了这一故事。在“引”中,作者叙说欧阳修于“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安徽滁州。滁州“琅琊幽谷,山水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亭记》)。欧阳修陶醉于山水美景,与民同乐之中把酒临听,欣然命笔写下著名的《醉翁亭记》。十年之后,好奇之士古琴大师沈遵,时为太常博士,因慕欧阳修《醉翁亭记》之盛名,特意到滁州探访,被琅琊山水美景所陶醉,于是归而以琴寄趣,作宮声三叠的《醉翁操》琴曲。其“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醉翁操》)。沈遵寻机为欧阳修弹奏此曲,欧阳修大为感动,作《赠沈博士歌》酬谢,诗曰: “子有三尺徽黄金,写我幽思穷崎钦”,并应沈之请求为该曲作词。醉翁自是大手笔,虽为此曲作歌,“然调不主声”,与琴声不合,不便于吟唱。沈遵的《醉翁操》曲传开后,有好事者为其填词,但都不理想。三十年后,欧阳修、沈遵相继去世。曾拜沈遵为师的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精通琴曲,多次由庐山前往黄州拜访苏轼。崔闲恨沈遵之琴曲无有佳词,乃请苏轼填词。苏轼不但诗文高妙,而且精通音律,于是乎,一边听曲,一边谱词。词云:
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唯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前。曰有心哉!此弦。醉翁啸咏,声如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同巅,水有时而回渊,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曲在人间,试听徽外两三弦[3]5586。
苏轼谱词后的第九年,即元祐七年(1092)四月二十四日,苏轼知守扬州。在与时为秀州本觉寺守一法真禅师的沈遵之子沈济的书信中,谈起《醉翁操》创作的话题(事见《书醉翁操后》题跋)。于是便有了琴与人“相感”,琴声与自然“相和”,歌词与琴曲“天成”,生命的存在与大自然的旋律交融相和之“天人合一”,形成审美主客体的相契统一的阐绎,这便是苏轼所提倡的古琴艺术的“真同”境界。
其实,在元丰四年(1081)六月,苏轼在贬谪黄州时期,便写下著名的《琴诗》。该琴诗是在与黄州府彦正判官的尺牍中,以偈的形式出现的。故外集题作《题沈君琴》。其辞曰: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3]2269
该诗讲的是产生古琴审美的主客观关系。作者受《楞严经》卷四“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的启示而引发的问话。意在说明“琴弦”与“妙指”乃琴乐产生之关键,若两不互动,则无由发声,必妙指拨琴,琴声乃起。这里引申出一哲理:琴、指,是弹奏出“天籁之音”的客、主观条件,两者相互依存,对立统一。世上万事万物,无不靠对立统一而达“真同”境界。作者借物寓理,言近意远。
二、苏轼古琴艺术的审美体验
(一)以琴悟禅 琴,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之化身,集儒释道禅思想于一身。明代古琴理论家李贽指出:“琴者,心也”(李贽《焚书·琴赋》)。他还认为:“声音之道可以禅通”(《焚书征途与共后语》)。说明文人在古琴的音乐声中感悟心灵与自然合而为一的人生奇妙的精神世界,达到心灵之解脱。明末著名琴家徐上瀛认为:古琴乐“修其清静贞正,而藉琴以明心见性”(《溪山琴况》)。古琴乐追求意境之深远娴静,讲求与心之虚静配合,达到琴悦。琴之高雅,化境在禅;禅之高妙,融入琴韵。古琴与禅悦相结合,为古代文人追求之旨趣。
苏轼一生与古琴相随相伴,对古琴有着特殊的爱好,并视为人生的知心朋友,甚至连做梦也《书仲殊琴梦》。他给后世留下不少独富个性特色的咏写关于古琴美学方面的诗文。可以这样说,古琴伴随他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人生,直到元符三年(1100)十月二十三日,即他去世的前一年,当他北归经广州时,还与广南监司王进叔交流古琴艺术,即兴《书王进叔所蓄琴》。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苏轼在谪居黄州五年间的文学艺术审美活动,出现了其诗词文书画琴,几乎是同步登顶艺术高峰的奇妙而伟大的文化现象。应该说,“乌台诗案”后的苏轼,一时间人生走向低谷,然而却在文学艺术领域,创造出世人公认的绝世精品。其时间均在元丰五六年间,其地点都在偏远小郡黄州。而其古琴论,亦罕见其列。细数苏轼在黄州撰有古琴论的诗词文有29篇,其中有著名的《醉翁操并引》《琴诗并序》《记阳关第四声》《减字木兰花》《杂书琴事十首》之《家藏雷琴》《欧阳公论琴诗》《张子野戏琴妓》《琴非雅声》《琴贵桐孙》《戴安道不及阮千里》《琴鹤之祸》《天阴弦慢》《桑叶揩弦》《文与可琴铭》。《杂书琴曲十二首》之《子夜歌》《凤将雏》《前溪歌》《阿子歌》《团扇歌》《懊憹歌》《长史变》《杯柈舞》《公莫舞》《公莫渡河》《白紵歌》《瑶池燕》《书士琴二首》之《赠吴主簿》《题与崔成老诗》《记游定惠院》《与彦正判官》,等等。
苏轼在上述诗文中,阐释对古琴之道的见解和古琴美学思想的要义。他在黄州期间,像他的恩师欧阳修在《送杨寘序》中所说的那样,有“幽忧之疾”不能治,后学琴于友人,则“心而平,不和者和”(《欧阳文忠公集》)。苏轼亦如法炮制,在黄州与庐山崔成老等琴家习琴论琴,以琴自娱,陶冶性情,以诗释禅,以禅喻琴,通过古琴阐发他的人生哲思和美学境界,极大地拓展了文人琴思想。
(二)以琴寓怀 中国古代文人,一向遵循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凡不得志之文人士子,多以琴乐寄寓情怀,为“穷”时之精神支柱。如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在宦游江湖的旅途中,于旅舍、扁舟,或置身月下江驿,或身处净室禅房,常乘兴弄琴,听琴,以此放逐心情,寄寓文人君子的凌风傲骨和豁达超然的情怀。
《庄子》借孔子之口讲了颜回不仕,以琴自娱,以道自乐的故事:孔子问颜回,你家境贫穷,居室卑陋,为何不去做官呢?颜回答道:我不愿做官。因为在城外我有五十亩田,足够喝稠粥;在城内我有十亩田,足够织丝麻。我有琴可弹,足以自娱。我学有先生的道理,足以自得其乐。所以我不愿意为官[5]874。庄子通过颜回的自述,既说明有吃有穿的重要,又说明“鼓琴自乐”的不可或缺。颜回的可贵之处,不回避卑微俭陋,而内心豁朗充实足以自得。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在诗中说:“闻弹一夜中,会尽天地情”(《听琴》)。阮籍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将内心的愤懑、悲苦之味,情寄于古琴之中,“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咏怀诗》)。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六月作《破琴》诗,以琴寓怀,“更忆前生后生事”,以发“破琴之慨”。
苏轼的“破琴之慨”源于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自杭州还朝宿吴淞江之夜梦。他在叙中说:“梦长老仲殊(注:北宋僧人)携琴过余,弹之有异声,就视,琴颇损,而有十三弦。”于是在诗中吟道:
“破琴虽未修,中有琴意足。谁云十三弦,音节如佩玉。新琴空高涨,丝声不附木。宛然七弦筝,动与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堕流俗。悬知董庭兰,不识无弦曲。”[3]3706
该诗中的“十三弦”指的是“破琴”;“七弦”,指的是“新琴”,一“破”一“新”,所譬之对象,即苏轼与刘挚。刘挚比苏轼年长七岁,两人都出生在儒士之家。刘挚北宋嘉祐四年(1059)中甲科第一名,开始步入仕途。熙宁三年(1070)四月,七品推官的刘挚与从凤翔府回京候职的苏轼相识。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官员,苏轼和刘挚等调京重用。苏轼官至三品的翰林学士,授礼部尚书。刘挚官至正二品中书侍郎,成为大权在握的副宰相。“元祐更化”不久,旧党领袖司马光于元祐元年(1086)病逝。刘挚乘时崛起,招纳羽翼,排除异己,成了朔党的领袖。在苏轼眼里,当权前后的刘挚判若两人,自己做了权臣,竟然变得如此丑恶。真乃私欲使人堕落,权力使人腐败,于是后来便有了“破琴之梦”。按照琴的规则,古琴是七弦,筝是十七弦。而现在则如朝中新旧两党人事颠倒一样,“琴”便成了十三弦,“筝”却成了七弦。苏轼指出,十三弦的“破琴”,虽然形象有点怪异,但“音节如佩玉”,其音韵节奏戛然尚在。刘挚,“宛然七弦筝”,却“丝声不附木”,只是一张“空高涨”的所谓“新琴”罢了。想当年新法倡行之际,苏轼与刘挚因反对新法,同为“破琴”。如今刘挚虽“新”之,而他却变怪反复,丧其本质,故与苏轼分道扬镳。元祐八年(1093)九月,一直支持旧党的高太后病故,被外放的章惇拜相,为了报复旧党,将刘挚、苏轼、苏辙等人,贬斥到更为偏僻的岭南。1097年12月3日,68岁的刘挚卒于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过了四年即1101年7月28日,66岁的苏轼病逝于常州。天地逆旅,人事代谢。苏轼《破琴诗》,托物言志,抒发了北宋元祐更化期间新旧两党的争斗,使原本为政治上的同道,却有了“琴”“筝”之别。
古代文人以琴寓怀的,最闻名的还是陶渊明的“无弦琴”。所谓“无弦琴”,意指没有弦的琴。此语出自南朝萧统《陶靖节传》。传说陶渊明不解音律,家里却置了一张无弦的不加装饰的古琴,每逢朋友聚会,便会意地抚弄一番,以寄寓闲适归隐之情趣。后来许多文人,都把“无弦琴”这个词作为隐遁的高洁品格的代名词。苏轼在他的诗里亦常提到陶渊明的“无弦琴”,但是他对“无弦琴”境界有独到的阐释。他认为陶渊明十分理解琴中之趣,所以他不拘泥手指在琴弦上拨弄,只取之“琴趣”,而不在意“琴声”,要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意境,诚如苏轼在《与彦正判官一首》诗中指出:陶公所言,“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苏轼推崇陶渊明得“无弦琴”之真趣,但对陶渊明的“无弦琴”和“无弦琴”之境界提出异议:
旧说渊明不知音,蓄无弦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此妄也。渊明自云“和以七弦”岂得不知音?当是有琴而弦弊坏,不复更弦,但抚弄以寄意,如此为得其真[4]7334。
这里,苏轼澄清陶渊明并非真的随身带着一张无弦的琴,而是一时因琴弦崩断,没有更换新弦,顺便抚弄以寄意趣而已。苏轼的解释,更正了千百年来关于陶渊明“无弦琴”之讹传。
苏轼还对“琴趣”一事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渊明非达者。五音六律,不害为达,苟为不然,无琴可也,何独弦乎?”[4]7284陶渊明在琴趣的理解上并不算通达之人。因为真正深谙五音六律,就不妨碍人们通达琴之真趣,如果这样,没有琴也可以,何必独在有弦无弦上摆样子呢?苏轼对琴之真趣的阐释,显然比陶渊明进了一步。陶渊明还停留在琴弦有无的阶段,刻意以无弦表示自己的超俗隐逸之态,这种姿态,反而是不达的表现。苏轼超脱古琴之形状,超然于琴指之技巧,以“寓意于物”的超然心态,强调“以琴寓怀”,从而体味琴乐之真趣。
“高情闲处任君弹,幽梦来时与子眠。彭泽漫知琴上趣,邯郸深得枕中仙。”[3]5534所谓“琴枕”,指形制如琴的竹枕。作者在《琴枕》诗里,把自己描述成超然物外“闲处”的“居士”,陷入忧愁之梦境的“逐客”。既能像陶渊明那样在无弦琴上寻到“真趣”,也能在“琴枕”上找回“邯郸之梦”的快意。“无弦琴”也好,“琴枕”也好,都是苏轼籍以寓怀的手段。元祐九年(1094),遭御史虞策、来之劭弹劾,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责知英州军州事。南行途经京城时,晚辈晁以道(说之)为其摆家宴饯行,苏轼垂情于话别,感慨地唱起《阳关三叠》古琴曲,表达“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浓郁深挚的惜别之情怀。
(三)以琴洗心
至和无攫醳,至平无按抑。
不知微妙声,究竟从何出。
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
此心知有在,尚复此微吟[3]1151。
作者从昭素僧人古琴的“微妙声”中,听到了最为和谐安顺,平正悠柔极致的古韵。它驱散了我心中郁积的不平之气,洗濯掉我不平和的心绪。
古代文人视古琴为内省式的通灵性之器,将情感寄托于音乐,音乐的这种调和情绪,安抚心灵的作用,古人早有论及。《礼记·乐记》云:“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
白居易的“人身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夜琴》)。欧阳修曰:“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赠无为军李道士》其一)。苏轼在元祐六年作于颍州的《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中指出,“观月听琴”,俯仰之间,“使我冰雪肠,不受曲蘖醺。”苏轼自元祐六年(1091)二月,改翰林学士承旨从杭州召还京师。六月一日再入学士院。七月贾易、杨畏以驱“二苏”为事,上疏论浙西灾伤不实,其朋党之祸甚炽。苏轼为避党祸连上乞外任劄子,最终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颍州,欧阳修曾知是州。离开是非之地,来到“土风备于南北,人物推于古今”(《谢上任颍州表》),公事湖中了,官闲事亦无的颍州西湖观月听琴。自感“悬知一生中”,道眼无由浑,其抉择真伪的眼力累增,明辨是非之眼不会浑浊。就像陶渊明那样“心闲手自适,寄此无穷音”(《和陶贫士七首》其三)。让在京城郁积的“不平气”“不和心”,在这微妙的琴声中得到疏解平复。苏轼的审美思想,与他的人生哲学关联。他把琴乐置于“乐”这一环节中,只要有“乐”,就能“游于物外”,就会“无往而不乐”。正是他采取这种超功利的观照态度,将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达到和谐一致,即称心适意,就能获得审美的满足和快乐。
元祐六年(1091)八月中旬,苏轼自感“得颍藏拙”之幸,故作《行香子》词,其词曰: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6]643。
该词表达了作者逃离是非之地,归隐田园,对着一溪云雾,弹着七弦古琴,饮酒以乐,以琴洗心生活的向往。
(四)以琴觅音 “高山流水,得遇知音”。先秦时期的著名琴师俞伯牙和樵夫钟子期,因一曲《高山流水》而成为知音的故事千古流传。苏轼以琴交友,以琴寻觅知音的故事,在琴界亦成千古佳话。
元丰二年(1079)正月三十日,时苏轼为徐州知守。在“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春风在流水,凫雁先拍拍”的春日(《游桓山会者十人,以……》),作者同朋友和晚辈后生十余人,去徐州城北十七里泗水畔作桓山春游。他们登上桓山,进入石室,听道士戴日祥弹古琴曲《履霜》。这是一首反映周朝上卿尹吉甫长子与次子争夺嫡位的故事。同行十余人在“幽响清磔磔”的琴乐声中,感到“此欢真不朽”(同上)。作桓山春游的十余友人,他们在古琴曲《履霜》里得到了心理共鸣,觅到了知音。苏轼把此次桓山之游,石室听琴,譬作陶渊明的斜川之游。
苏轼名满天下,朋友遍天下。他以诗交友,以书聚友,以画结友,以琴觅友更是他的交友之道。元丰六年(1083)二月,庐山道人著名琴师崔诚老(名闲,号玉润道人),从庐山来访,客住雪堂,一直住到苏轼离黄。崔闲工于琴,给苏轼的贬谪生活带来不少欢乐。苏轼用诗记述了他与崔闲的琴缘;“夜来一笑之欢,岂可多得,今日雪堂得无少寂寞耶?……少许夜琴一弄,谁与同者”(《送酒与崔诚老》)。
元丰七年(1084)三月三日,苏轼“与参寥师二三子”游定惠院。“后往憩于尚氏之第。……醉卧小板阁上,稍醒,闻坐客崔成老弹雷氏琴,作悲风晓月,铮铮然意非人间也”(《记游定惠院》)。
元祐六年(1091)九月十五日,时苏轼为颍州知守,在“白露下众草,碧空卷微云”(《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的秋日之月夜,在颍州西湖观月听琴。“尚恨琴有弦,出鱼乱湖纹”(同上),只怪琴声引鱼跃出,而搅乱湖中水纹,打破湖面平静,苏轼有感于“哀弹奏旧曲,妙耳非昔闻”,即兴赋“观月听琴西湖”一首,以呈随行坐客友人。
前面说到苏轼应著名琴师崔闲之邀,为《醉翁操》填词。自苏轼填词后,词与曲相谐,珠联璧合,使琴曲更显光芒,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琴曲之一。北宋琴家成玉,记述演唱这首琴歌的感受。他说“如与子瞻抵掌谈笑尔”(成玉《琴论》)。这种弹琴听曲,恰如“抵掌谈笑”的情状,正是苏轼提倡的“真同”效应。有趣的是,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陶醉于山水美景作《醉翁亭记》;十年之后,即至和二年(1055),沈遵作宮声三叠的《醉翁操》琴曲。二十七年后,即元丰五年(1082)庐山玉涧道人崔闲,请于苏轼补《醉翁操》词。苏轼谱词后的第九年,即元祐七年(1092)四月,应沈遵之子沈济之请书《书醉翁操后》题跋。从而使《醉翁操》古琴曲,在经仁宗、真宗、神宗、哲宗四朝,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尘埃中,传唱不绝,以至于千年后的我辈学人仍津津乐道,乐此不疲,演为千古传奇。若问个中秘诀,便是苏轼所提倡的古琴艺术的“真同”境界,使文人与琴人的友谊达到同气相感,同声相应,同趣相通,同道相知,方达以琴觅友,成为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