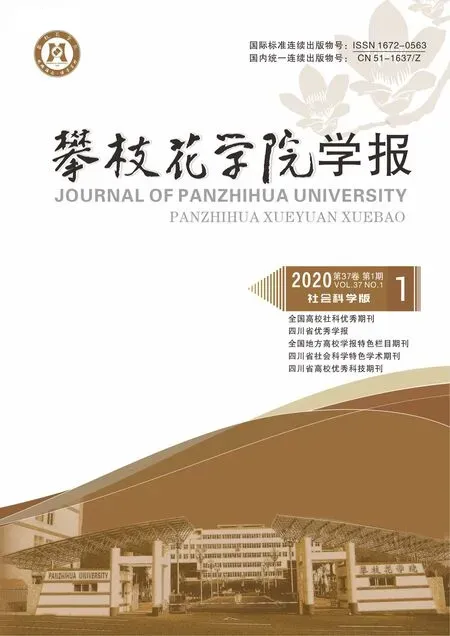《山海经》中猴类形象与金猴面具之渊源
唐世贵,唐晓梅,李仲先
(攀枝花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如果要论《山海经》中猴类形象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猴面具之渊源,首先得确证《山海经》的地缘文化。《山海经》开篇即曰:“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郭璞注云:“在蜀伏山山南之西头,滨西海也[1]1”。“伏山”,即“汶(蜀)山[2]1”,也就是盆地西部的岷山,古羌族分支蜀山氏的发祥地。西汉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3]188。”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仍然称《山海经》相传“作于禹益,述于周秦[4]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开始有人仅仅就“述于周秦”提出《山海经》的作者是战国时代的齐人、燕人、秦人、楚人、印度人和巴蜀人等各种地缘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袁珂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战国初、中期楚地楚国人。不管怎样,这些说法却无法否定《山海经》中2/3的内容直接或间接记载的是巴蜀地理人文的无争事实(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及此经《南山经》以下三十四篇,《尔雅》云‘三成为昆仑邱’。”东汉王逸、宋洪兴祖认为“昆仑”即“岷山”),这在先秦典藏中是唯一的[5]43。司马迁在《史记》开篇就叙述了中华民族的开端即黄帝与巴蜀的关系,但不给巴蜀列传却写了《西南夷列传》。试问中原文人会写《山海经》吗?把都广之野写成“天地之中”吗?《山海经》的地望原本就是由《中山经》和《海内经》构成了其地标(中心)的,这个地标有人企图扯到中原或者山东半岛,甚至云南和广西。虽然《中山经》因大禹故以中原的薄山为之首,但《中山经》的山系竟主要记载的是盆地及其周边的山脉。而太行山原本是中原王朝的象征,华夏之龙脉,竟被作者写到了《北山经》;泰山作为山东齐国、鲁国的标志,却被作者弄到了《东山经》;华山原本是秦人的发祥地标,没想到作者随便扔到了《西山经》,而衡山虽然有两次被写入《中山经》里,但同时又被放入到《海内经》中[5]548。有人认为《海内经》是汉代作品,按理说汉王朝统一了天下,就应该以汉王朝的都城长安或洛阳为“海内”,可《海内经》并没有直接记载中原王朝及诸侯,而恰恰记载的是巴蜀人文始祖帝俊,而帝俊本是《山海经》的主神(蒙文通语)[6]。这“海内”指的是哪里?旱在西汉,淮南王刘安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7]848-545。”这是继秦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后中原文人再次认同,西南都广之野(今成都双流境)为天地中心。郭璞《山海经》注亦有同样的论述。
《山海经》中各种猴类图像及其寓意与华夏文化必然有一定联系,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文物(岩画)上就出现了猴类的图形(如图1-1),猴类造型在后世文物(岩画)还多有展示(如图1-2)。

图1-1贺兰山史前岩画“猴脸”神像 图1-2“红山文化猴神玉面”
在远古时代,古人最早将“猴”写成“夒(náo)”,甲骨文中的“夒”字像是一只正要搔首弄姿的猴子(如图2)。东汉许慎在《说文》中的解释是:“夒,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8]。”甲骨专家李孝定认为“此字在甲骨文中写为猴形,既代表殷人的某位高祖,也代表猕猴和神祇”[9]1903-1917。除了“夒”字,“猴”在“《诗经》中出现过‘猱’,《左传》中出现过‘玃’,《国语》中出现过‘夒’,《庄子》中出现过‘狙’,《楚辞》中出现过‘猨’和‘狖’,《山海经》中出现过‘狌狌’和‘白猿’[10]147”等文字。《山海经》中“狌狌”和“白猿”之猴类形象大体为“人兽结合”的“人面猴身”或“猴面人身”。这种“猴形神人”或“猴祖神”的形态,形象的表现了“人”是由“猴祖”衍变而来的。在“猴”的上述称谓出现的同时,“猴”字亦被创造了出来,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11]。”但是,“在汉代以前,‘猴’字是从不单独行用的[10]147。”而“猴”取代其他称谓,那是约定俗成的。

图2 “夒”字像是一只正要搔首弄姿的猴子
一、《山海经》中猴类形象
(一)狌狌形象
《山海经》开篇对狌狌描绘道:“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12]1”。依据前人的注释,我们得知:招摇之山即蜀山,蜀山即岷山。在那里的兽类就是狌狌,长相很象猕猴(禺),却长着一双白色耳朵,而且这种动物有一种特点,就是时而是四肢着地爬行,时而人立行走。袁珂先生对于狌狌的注解:“王念孙云:‘类聚兽部引作有兽人面,名曰狌狌。’珂案:狌狌即猩猩。”另外,《山海经》中对于狌狌(猩猩)的描述还有几处:《海内南经》:“氾林方三百里,在狌狌东[12]275。”《海内南经》:“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12]275”。《海内南经》:“狌狌西北有犀牛,其状如牛而黑[12]276”。《海内南经》:“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状如龙首,食人[12]278”。《海内经》:“有窫窳,龙首,是食人。有青兽,人面,名是曰猩猩[12]452”。《海内南经》中有“夏后启之臣孟涂司神于巴[12]277”的记载,夹在犀牛和窫窳的记载中间,因此,可以确定《海内南经》对于此处的描述亦是古代巴蜀地区,那么,古代巴蜀就是一个聚居着大量猴子(猩猩)的地区,多到人们一说到猩猩,就能够想到说的就是这里。
(二)白猿形象
猿类一般为黑色或者棕色,白猿则极少见(如图4)。《南山经》:“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棪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12]2。”再往东三百里,是座堂庭山,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棪木,又有许多白色猿猴,还盛产水晶石,并蕴藏着丰富的黄金。人类对猿猴类的过分关心便越来感觉神秘,让人觉得更为神秘奇妙的是竟然发现了一个“白猿”,这种神奇的白猿人们自然就赋予它更大的力量和神通。由此“白猿”就能代表人类深层次精神愿望,成为人类美好理想的载体新形式,例如《太平广记》卷四四四引《吴越春秋》云:“越王问范蠡手战之术,范蠡答曰:‘臣闻越有处女,国人称之,愿王请问手战之道也。’于是王乃请女。女将北见王,道逢老人,自称袁公,问女曰:‘闻子善为剑,得一观之乎?’处女曰:‘妾不敢有所隐也,唯公所试。’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枯槁,末折堕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处女应节入之三,女因举杖击之。袁公飞上树,化为白猿[13]。”
《山海经》中猿之同名为“蝯”与“猨”。如《中山经》:“又东南三百里,曰丰山。有兽焉,其状如蝯,赤目、赤喙、黄身,名曰雍和,见则国有大恐[12]165。”这种如蝯之兽,名称雍和,其赤色的眼睛,赤色的嘴脸,一身黄毛,人们见了非常惊恐。其实,雍和就是“赤秃猴”,在中国已经灭绝,现生活在南美洲,其拥有令人震惊的红脑袋。又如《南山经》:“又东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其中多怪兽,水多怪鱼,多白玉,多蝮虫,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12]3。”“猨”即猿。其实,在古人心目中“猴”和“猿”是有区别的。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宋代柳宗元提出的“猿静猴躁”说。事实上,早在《说文》中“猿”和“猴”就有所区别——玃、犹、狙、猴从犬,猿则写作蝯,从虫——《说文》归部有区别义类的功能,蝯、猴分部[8],就说明它们不是同类。
(三)禺类形象

图3蒋本 狌狌 图4胡本 白猿 图5蒋本 禺强(京)
《南山经》曰:“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12]1。”郭璞注:“禺似猕猴而长,赤目长尾。”《说文》曰:“禺,母猴属,头似鬼。似猕猴而大,赤目长尾,亦曰沐猴[8]。”禺这种神异怪物“在《山海经》中常用作神名,例如东海神‘禺号’、北海神‘禺京’。总之,它们所描写的与其说是作为动物的猴子,不如说是猴类动物的某种奇异功能”,也就是说《山海经》表达的是猴类神异形象的功能,而不是其本身。“《山海经》中的‘其状如禺’以及‘禺京、禺号、禺彊、禺水、禺谷、禺中之国’等等,乃是周边民族猴祖神话在华夏的遗存。这些民族对猴祖的崇奉造成了猴在华夏文化中的神化[10]167。”猴类图像不过是周边民族崇拜的图腾。鲁迅在《故事新编》说,出自于岷江上游西羌的大禹的“禹”,其实就是“禺”,也就是“大猴子”变来的[14]。
二、金沙遗址出土之金猴面具
三星堆遗址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的历史,曾出土了4件金人面罩(如图6),而在3000年前的金沙遗址出土的不同规格的金面具中,最为奇特的是一件金猴面具(如图7),这是世界考古史上唯一的金质猴面具,用纯金来打造猴面具,说明其时猴子是极为尊贵的称号,成为古蜀国黄金文化最具特色的代表。我们可以把古埃及3300年前图特卡蒙法老的金面罩(如图8)与辽陈国公主金面罩(如图9)作一比较。首先是用途不同,古埃及法老金面罩与陈国公主金面罩是作为随葬品,而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却是远古蜀人在祭祀活动中,巫师表演的道具。其次是工艺与文化内涵不同,作为随葬品的金面罩表征的是崇高的地位,而作为巫师表演的假面具象征的却是对猴祖神的崇敬,尤其是巫师头带的金猴面具更进(敬)一层。因此,其虽各具特色。但其共同点则是远古人类对黄金的崇拜。

图6三星堆遗址出土金面罩 图7金沙遗址出土金猴面具

图8埃及图特卡蒙法老金面罩 图9辽陈国公主金面罩
从世界范围看,古埃及和西亚地区早在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大量的黄金饰品交易,通过商业贸易开始向地中海沿岸、中亚、南亚等地迅速传播黄金制作技艺。然而,都广之野古蜀黄金文明却自成系统,有着自身的渊源和发展演化轨迹,无疑《山海经》中的古图(包括猴类图像)便是他们的艺术创作参照对象。
三、从古蜀(羌)人对猴的崇拜到祭祀巫舞表演
《山海经》中的猴类形象暗示出远古巴蜀人对猴祖神的崇拜,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猴面具正是在祭祀活动中的偶像化——巫师头带金猴面具的巫舞表演。黄金稀缺而珍贵,金猴面具是古蜀人对黄金和猴祖神的双重崇拜。因此,远古巴蜀相信戴上假面(道具)具,手握木椎打敲着石磬,那有节律的敲击使玉石发出清脆优美的声音,给观众一种余音绕梁之感,人与猴祖神在这简单节奏的音乐中便开始了交通。金沙遗址出土的石磬,石磬尚能发出来自3000年前的天籁之音!石磬是古蜀王国举行盛大祭典时使用的特殊乐器。在金沙遗址这一大型滨河祭祀场所,在石磬和陶埙合奏的音乐中,参加的观众跳起蜀地巫舞,而这种巫舞在人们心目中是可以驱除恶鬼消除瘟疫的。这种思想意识早在《山海经》成书之前的黄帝时代即已出现,并且一直流传到当今社会。尤其是在长江以南地区至今还依然还有傩戏存在,这种傩戏也具有同样功效。然而,《山海经》中体现出来的巴蜀巫术祭祀活动和中原竟然不同,其实巫术活动竟然成了一种娱乐活动,所以人神共欢,敬而近之与神融为一体。中原巫术祭祀活动对神灵却是庄严、肃穆的,如同孔子说的与神鬼敬而远之。所以,金沙遗址金猴面具是人神之间相沟通的媒介,那金光灿灿的面具一是通神,二是娱神具有这两种功能。在祭祀活动中,戴上假面具就是半人半神。带上金猴面具就会给人一种神秘感,一种震慑力。
司马迁在《史记》开篇即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15]4。”司马迁叙说了黄帝与盆地周边的巴蜀部落的姻缘关系,蜀山氏就是居住在江水(岷江)中上游,后迁入都广(成都)的古羌族部落分支。任乃强先生对古羌族的族源有过系统的解说:“当猿类由泰缅地区向北移进、开始向人类进化时,缘横断山猎食而进的一支在康、藏、青大草原的顶部停留下来,形成了一个自呼为羌的民族。我国西南、西北的各游牧、农业部落,基本都是羌族的分支或与其有血缘关系”[16]6-18。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大量以猿类为图腾的祖先传说,这可能意味着这些群体的共同母族,即古羌人最初居住的地区(即喜马拉雅山北麓),曾经拥有过广泛的猿类图腾崇拜。在羌族的巫术中,与鬼神相沟通的祭司被称为端公(羌语称为“许”)。据说端公的法力来自于对猴王的祭拜。只有祭拜过猴王的端公才是真正的端公。这种风俗的起源在1941年出版的《边疆论丛》一书中有描述:白羊偷吃了睡着了的端公的经书,没了经书端公竟然就这样哭了。这时一个金丝猴(金丝猴古即称娀)来问端公为何哭泣,金猴了解到实情后告诉端公杀了白羊,吃了它的肉,用它的皮做成鼓,敲击这个鼓能背诵出经文来。端公照办了,真的十分灵验。端公为了感谢金丝猴的大恩大德,世世代代不忘金丝猴,从此,端公便以猴子皮为帽,猴子尾为帽子三尖,任何时候都恭敬地称猴子为祖师、老师傅。显然,猴子不仅成了端公(巫师)的保护神,而且端公还直接装扮成猴子的形象来娱神[17]。古羌族是《山海经》中的“蜀”,或《史记》中的“蜀山氏”的母族,其分支“蜀”在4000多年前从岷江中上游迁入都广之野定居,一代代王国承传了《山海经》之猴类形象文化寓意,并同时开创了三星堆、金沙辉煌的黄金文化。
总之,《山海经》有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既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写的一时一地,所以其先有图画,而后有文字,最后图文并存,流传至今[5]78。上述其开篇便记述了巴蜀之地的猴类形象狌狌和白猿,说明古巴蜀之地曾经是猴类聚居之地。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猴面具,证明古蜀人为了祭祀猴祖、巫舞表演的需要,依据《山海经》中猴类古图形象,制作了金猴面具。但这一金猴面具既不是当时猴子脸谱的模仿,亦不是《山海经》中猴类古图形象的照搬,而是远古蜀人艺术性的夸张再创造出来的崇拜半兽半神偶像,因此,不论是三星堆,还是金沙的黄金面具都是自成体系的巴蜀黄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