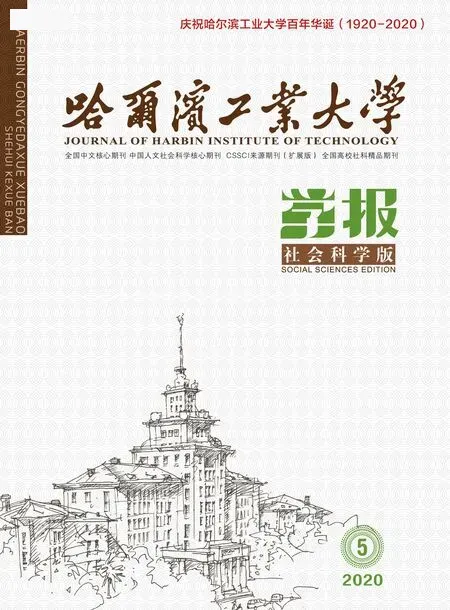《东池诗集》的故国之思与板荡之悲
种梦卓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150025)
《东池诗集》目前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不见流传于世,故研究者甚少,笔者所见为其影印版。集中诗人多为明代遗民,其中不乏陈忱、吴楚、张隽等江南名士。据《东池诗集》所载,东池诗社的五次集会,始于“庚子上巳后五日”①文章所引《东池诗集》叙文及诗文皆见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抄善本,文中随文标记所引集数,不再另注。(《东池初集叙》),即公元1660年暮春,终于“壬寅初秋”(《东池第五集小序》),即公元1662年。每次参与雅集的诗人不尽相同,累计有二十三人,共留诗七十九首。
一、东池遗民诗人群像
《东池诗集》中对于诗人的介绍只有字、号,他们是陈忱(字遐心,号雁荡)、吴楚(原名心一,字敬夫,号西溪)、李向荣(字新夫,一字晋美,号云门)、沈旭(字亦颠,旧字书圣)、黄瀚(字长文)、释净灯(字千光,号幻云)、释清晖(字祖亏)、许峙(字羽佳,号洪崖)、纪镐(字武京,号雍庵)、汤有亮(字孟明,一字海林,号天民)、张隽(字文通,号西庐,别名僧愿)、张肩(字尔就,号弁樵)、张鲁龙(字御六)、张道升(字仲曙,一字旦苛)、沈讷(字静生)、姚徵(字玄斥,一字石紸)、庾明允(字人皋)、王广和(字天俔)、龚鼎铨(字张仲)、释愿桂(字香谷)、沈在(字文兹)、张翼(字负青)、潘开甲(字东阳,一字红霞)。由于集中诗人多声名俱隐,故考其生平确有难度。笔者据所阅古籍资料,考部分诗人如下:
(一)东池诗社核心成员
根据集中各序、参会次数及所存诗歌数量来看,陈忱、汤有亮、张隽和吴楚四人应是诗社的重要组织者,也是诗社中最有名望的诗人。
陈忱,字遐心,号雁荡。在东池诗人群体中,陈忱是最受关注的文人。对于其生平、字号等,学术界早有讨论。胡适先生假定他“生于万历中叶,约当一五九零年”[1];谭正璧先生认为陈忱“约明思宗崇祯三年前后在世,年约八十岁”[2]315;郑公盾、袁世硕先生认为“陈忱当生于1615年”[2]319,众说纷纭。但其中多数研究仅限于当前所见已有文献,缺少有力的史料证据考辨,难以证实。至《东池诗集》的面世,证实了郑、袁二位先生之说当为确实。《东池初集叙》开篇即云“崇祯甲戌予年二十”,此叙结尾有“默容居士陈忱题”,可见由陈忱亲笔所写,更具真实性。“崇祯甲戌”即公元1634年,陈忱“年二十”,其出生年当为1615年。学界探讨的另一问题是陈忱是否是《水浒后传》的作者,对此顾颉刚、胡适、徐扶明等先生皆有详细论述,此从小说方面探究,与本文联系不大,故此不再赘述。
汤有亮,字孟明,一字海林,号天民。集中除对其字、号的介绍以外,各序中反复记述了汤有亮对于诗社雅集的重要性。陈忱在《东池初集叙》中即对与汤有亮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描述:“举世弃绝”之际,得其“不摈斥,时得泛游”,可见汤子对于陈忱的重要意义。张隽在《东池再集小序》中提及“庚子夏,西溪、雁荡两兄邀余赴汤子海林之约”以及《东池五集小序》“汤子复为东池之集”,杨文熺《东池雅集后序》中亦有相关言语“夫东池者,乃汤子海林养晦处……海林吟咏于斯,几不知有人世,每遇良辰必燕集西庐诸君子,即分韵唱和,时有弁言……”,可知汤子即为诗社集会地点东池草堂的主人,也是诗社最主要的组织者和核心人物。因无更多资料,其生平等暂不可考。汤海林之诗作目前只见于《东池诗集》,共有六首。
张隽,字文通,号西庐,别名僧愿。张隽为诗社的第二集、第五集作有序言,也是诗社的组织者之一。清人节庵所辑《庄氏史案本末》有载:“张非仲,隽,一名僧愿,一名文通。为博士弟子员……所著有《西庐诗草》。”[3]卷三十七《二西遗诗》(上海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清抄本)首页即有“识语”:“张隽,吴江人,一名僧愿,字文仲,又字文通,明诸生。积书甚富,南浔庄廷鑨聘修《明史》,为作有明理学诸儒传,名《与斯集》。史案未兴,恐不负延于僧;会后史狱发,就逮于杭州被诛。有《三部略》《易序测象》《西庐诗草》《石船存草》《西庐文集》。”引文出现的“史案”是考察张隽生平的重要证据。杨凤苞《秋室集》中“记庄延鑨史案本末”载“十八人:归安毛元 铭……乌程吴楚、唐元楼、严云起……吴江张隽、董二酉……皆凌迟处死”[4]。按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载“是狱从顺治辛丑发生,至康熙癸卯判决”[5],康熙癸卯年是公元1663年,即其卒年。而清同治修《苏州府志》云“居湖滨吴楼,去南浔最近,死年六十余”[6],可以推算,其应生于万历二三十年间。张隽的著作颇丰,已有多位专家学者考证,甚为详实,本文从王洪军先生之说作简要介绍[7]。亡佚之作有《三藩略》《与斯录》《象历》《九洛序》《卖菜言》《四三韵略》;现存之作有《西庐诗草》《西庐文集》《石船诗稿》《古今经传序论》。在《东池诗集》中存其序言两例,诗六首。
吴楚,原名心一,字敬夫,号西溪。在东池诗社中,吴楚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位人物,与陈忱、张隽相交甚好。前文提及的“庄氏史案”,吴楚与张隽就同为判处,且有《西溪诗集》《西庐文集》合录为《二西遗诗》留存于世;而陈忱在其入狱之后并不像他人一样避之不及,可见《二西遗诗》首页有题语“吴楚授雁宕叙”,毅然完成好友之托,二人亲密关系可见一斑。杨凤苞《秋室集》卷五记“吴楚”云:“吴楚,字敬夫,西林村人,乌程诸生。耽吟味,好钟谭派,董说称之。尝偕闵声选唐诗《岭云集》,吴江吴宗潜序之行世。及楚预史祸,声、宗潜悉下狱。时以史案系累者多文士。诸人锒铛狴犴,慷慨赋诗,互相酬答,皆无困苦乞怜语。后各免归,声合诸家诗钞为《圆扉鼓吹编》云。”[8]可知吴楚事迹概况。其卒年当与张隽同为史案处死之时为康熙癸卯年,其他暂不可考。其参加了东池雅集的前四次,留《东池三集小叙》一篇,诗四首。
(二)其他可考诗社成员
李向荣,字新夫,一字晋美,号云门。在东池诗社中,李向荣与诸人所交甚笃。其《云门诗集》也被收录在《二西遗诗》(上海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清抄本)中。其中有诗《次张西庐韵咏东池》《寄怀张西庐,即用西庐监字韵》等与张隽唱和之作,张隽在《西庐文集》中亦录有《〈云门语录〉序》;《云门诗集》中有《留别汤海林》一诗,可知其与张隽、汤有亮均交好。其与陈忱之间亦是往来甚密。陈忱有《答李云门》《春日同天民、长文过云门别业》等诗,而《云门诗集》中有《赠陈雁荡》《东池初咏,补和陈雁荡韵》等诗,二人唱和甚频。《东池诗集》收其诗两首。
黄瀚,字长文;王广和,字天俔;沈旭,字亦颠,旧字书圣。此三人均与陈忱情谊非常深厚,皆在陈忱诗作中出现多次,如《立春前一日病中乐长文见过》《春霁同石耕、长文、亦颠过海林东池草堂分赋》《寄怀黄长文兼呈汤海林》《亦颠移居得北同天俔、长文过赠》以及《春日同天俔长文过云门别业》等诗[9],可见四人常结伴交游,往来频繁。《东池诗集》中收黄瀚诗五首、王广和诗两首、沈旭诗六首。
张肩,字尔就,号弁樵。范铠所著《浔溪纪事诗》[10]320引范颖通《研志居琐録》有载:“张肩,字尔就,康熙间人。处石澥溪,年三十始读书,善画竹,筑远偏庐,傍多栽竹,以诗酒自娱。”大致知张肩生平。《浔溪纪事诗》中《鸿飞集》亦有《挽张尔就》:“翰墨称当代,风流幕昔贤。携来双屐雨,归去五湖烟。笔下生云气,胸中有渭川。伤哉随羽化,无复见张颠。”[10]321虽不知作此诗者何人,但足以见得张肩的书画声名。张肩的诗作他处并无可见,《东池诗集》收其诗一首。
纪镐,字武京,号雍庵。民国时期周庆云《南浔志》有其传:“纪镐,字武京,号亦山,一号西村逸圃。县学生,识见明卓,受业湖滨张西庐,时同有构造逆史者,征集文士。镐以大义责之,杜门谢客。事觉,张西庐被逮,镐独不与其祸,及张受戮,往其收尸,哭而殡之。”[11]可见纪镐是张隽之学生,且二人感情相当深厚。范来庚所纂《南浔镇志》中“艺文志书目”对其著述有所提及,“国朝纪镐《亦山诗集》”[12]。又有《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载,清顺治十六年,“吴江孙英(商声)、纪镐(武京)合选宋苏轼文,编为《苏文近》刊行”[13]。《东池诗集》收其诗四首。
释愿桂,字香谷。汪曰祯《南浔镇志》载:“荫在,字香谷,一字愿桂,号桤庵,吴江皇甫氏子。顺治丁亥年,十一,为僧于叶港妙华庵。丙申来浔,住明义庵。从张隽游授以诗,诀始以诗鸣。参南潜(即董说)于补船村,遂师事焉……乙巳,随南潜作楚游,以病目先归复至双林,尝主菁山常照寺,以患症结归,刺舌血写华严经,未竟,卒与妙华年三十八。”[3]卷十五大致可知其生平事迹,于顺治丁亥即公元1647年其十一岁时出家,其应为1637年生人,卒于三十八岁,即应为1674年。且先后师从张隽、董说。超永所辑《五灯全书》记其作有《桤庵集》《菁山客话》[14];潘衍桐所编《两浙輶轩续録》及其作有《香谷集》[15],今皆佚。《东池诗集》收其诗一首。
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将遗民定义为:“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故遗民之称,视其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乎终身之显晦。”[16]简言之,“遗民”是处于江山易代之际,身历两朝,且不仕新朝之人。根据上文对部分东池诗人生平事迹及相交情谊的考据,可大致确定该诗社群体均属明代遗民。
二、东池诗人的故国情思
清初,由于去明不久,且不少遗民与南明政权联系紧密,反清复明是大多遗民的梦想,遗民的结社活动意在联络明知、鼓舞斗志,因此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如上海人朱襄孙等人于顺治二年(1645)所创立的怀忠社,《南汇县志》载:“乙酉九月,与诸生方用悔等创立盟社,名怀忠,示不忘故明也。”[17]只见其名即可想见其宗旨。又如成于顺治七年(1650)有“吴社之冠”之称的惊隐诗社,由于诗社成员大多与清初太湖地区的抗清运动有关,顾炎武、归庄更是昆山起义的直接参与者,所以他们对于爱国情思和民族气节的抒写则更加直白,吴宗潜、顾炎武、归庄、王锡阐、顾有孝等文论家,直抒以天下苍生为责的感情,大胆揭露山河破碎给人身体、精神的强烈冲击,如顾有孝的《自伤》一诗:“暮宿投何处,惊闻战马嘶。窜身憎犬吠,匿迹畏儿啼。天地恩真少,英雄气己低。煌煌一社提,回望使人迷。”[18]反映亡国之后心无所依、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彷徨与报国无门的失落之情,言辞激荡。再如王锡阐的《拟谒孝陵作呈匡庐先生》一诗中所作:“忽睹天威咫尺中,暂收零涕拜穹窿。宝衣秋化离宫火,石马晨思寝殿风。恨入松楸凝做柏,血干杕杜染成枫。心苏复道瞻云物,嘉气钟山正郁葱。”[19]作为明代遗民去拜谒明孝陵在清初所代表的政治意义无需多言,这是一种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行为。总体而言,“惊隐诗社”的诗作无论是抒发浓厚的眷念故国之情还是表达不满新朝之恨,都是情感激昂的,显示其顽强的斗争性。再如成于顺治九年的侯方域宜兴诗会,在结会时曾言:“今之江左,视昔日又如何,诸君而绎余言,其尚亦可吟而啜、当醉而醒也哉!”[20]与会人员中的陈贞慧、任源祥都是坚定的遗民。他如假我堂诗会、江干五老会等,虽活动时间较短,也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斗志[21]。可以说,清初、尤其是前十年,遗民的结社活动都明显展现了昂扬的斗争精神。
直至清顺治十七年正月(1660年),清廷从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上疏严申结社订盟之禁:“朋党之患,酿于草野。欲塞其源,宜严禁盟社,请饬学臣查禁。”[22]且在疏中直接把苏、杭、嘉、湖列为社禁的重点地区,要求“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得上旨:“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以后再有此等恶习,各该学臣即行草黯参奏,如学臣徇隐,事发一体治罪。”[23]江南地区的遗民结社活动因此受到了空前的打压,并转入低潮。正如杜登春所言:“自是家家闭户,人人屏迹,无有片言只字敢涉会盟之事矣。”[24]当然,江南社事并未完全消歇,只是此后的遗民结社斗争性大大降低,这当中既有清廷通过科举考试或任职被大多数士人接受的原因,也与复明的大势已去、新朝定鼎已成事实有关,更主要的是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老去,很多遗民的斗志大不如前,由此,他们从抗争转向潜隐,结社的目的也更趋于纯粹的文人唱和以及倡举文化,更具休闲性。
而东池诗人群体作为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诗人,虽不乏抒发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诗作,但观其初集时间为公元1660年暮春,去清廷实行社禁不久,使得诗人们的集中之作不敢大肆论思前朝,只敢稍微表现国破易主的无奈与悲哀。
在《东池三集》中,张隽、陈忱、黄瀚、王广和各有诗一首以抒家国。张隽有诗:“雨坐空楼罢卷帘,故人洛社寄新占。自携颂橘偏多泪,想到荨羹未下监。稧帖更博觞咏乐,鹤魂虚觉岁时添。春风惨淡都无主,犹如君主芍药檐。”
诗中提及“颂橘”,即是借此以比屈原。屈夫子是一位忠于故国、人格崇高的伟大诗人,诗人与之自比,其目的便是学习其砥砺志杰的坚定意志、缅怀其九死无悔的爱国精神。而三月春风正应是生机勃勃之时,诗人此处却认之为“惨淡”,渲染清冷的氛围,又借春风自比,表现自己无国无主的悲戚。
陈忱有诗:“高阳旧侣不须招,柳色春深暗野桥。漫谓草来多逸兴,只怜风雅久萧条。山中人往呼裴迪,渡口风回载郑樵。遗老自知耽酒癖,斜阳遮莫话前朝。”
在春深柳色之中,漫步草间虽颇具兴致,但远不能附及“风雅”。“遮莫”一词有不同释义,任凭、不管之义或莫要、不必之义,在此处应为前者。作此诗时诗人已近知天命,自知无力改变世事,只能借酒劲忆议前朝。陈忱和其他东池诗人相比,在感念旧国方面似乎更加勇敢,如他的怀古诗《咏史》其一“汉鼎何尝一日迁?南阳发迹便相传。义师四集登台际,新莽空称十八年”,通过王莽篡权之史事,抒发了对异族入侵的愤怒,并表达了只要众志成城,就会收复江山的坚定信心;再有如《康王寺》一诗:“南渡銮舆驻跸多,只今疏磬出烟萝。遗民不识中兴主,犹唤康王是九哥。”[24]诗人借咏南宋旧史,却句句透露对南明王朝的期待。宋末与明末的境况如出一辙,皆是异族入侵、王朝中兴,虽大宋王朝在南渡后经历了许多波折与动荡,但仍保有半壁江山,这便是诗人对南明王朝的企盼所在,期待能与清廷抗衡而复国!另有其效仿屈原而作的的组诗《九歌》,痛感故国之灭亡,令人无限动容。
黄瀚有诗:“东桥有信艰江皋,还泛看花旧小船。岂意乱离频次会,敢因贫贱辍称高。论交有道思端复,即事同吟拟谢陶。莫话故山薇蕨老,一春风雨梦空劳。”
诗人信步江边,归来路上颇有闲情地泛舟赏花。虽在乱世之中,亦与同道好友相约集会,是想学习谢灵运、陶渊明般高洁立世。在闲聊中无意间提及故国山间的薇、蕨过了采摘的季节已经老了,转念间却倍感无力,一切都是空梦一场。
亦有王广和在《东池五集》中的《六麻》一诗:“一棹苍茫溪路斜,枫林炯火隔渔家。风生远凉堵归草,日落垂杨影带鸦。但使隐沦怀故国,不须避地到天涯。草堂旧以田新咏,把酒相看鬓尽华。”满腔对故国的思念只化为一个小小的期待,那就是不用逃到天涯海角才能表达,但这终究也是奢望!
东池诗人的诗歌中甚少抒写对人事的关切,甚至对故国的情思也不直接表达,只是表现自身对于家国易变的无能为力之感,并无出世为之奋斗的决心,而几乎全然沉浸山水、隐居草莽。这也是自清廷实行社禁之后明代遗民结社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生存际遇与人生悲歌
在清代经济、政治、文化三层高压下,即使隐于山野,东池诗人们的处境亦相当艰苦,但他们不抱怨,不悲观,身处乱世依然不懈追求安身立命之道、自得其乐之趣,或躬耕于田,或跌荡文酒,傲然立于世!
(一)乱世之苦,生存之难
《东池初集叙》中陈忱即有言“适膺时难,闭门扫轨者垂二纪,竟成皤皤贫叟,又苦病耳聋,须画字,欲焚笔砚,举世弃绝”,可见生活之艰。在诗集中,有多处关于生存境遇的描述。有陈忱“世运艰危际,君能赋如初”(《东池初集》),即使世运艰难,亦希望能抱有初心!有吴楚“有此偷闲地,几忘行路难”(《东池初集》),在东池草堂寻度过的悠闲时光,让人暂且忘却世道之艰难!有沈旭“垂时聊寄意,斯世敢求安”(《东池初集》),在垂钓时闲聊起人生愿望,在如此世道,连安定都是奢望!有张隽“履遇同坏衲,倾底换尘襟”(《东池再集》),衣破鞋破,要倾尽家底才能换掉脏破不堪的襟带,生活多么贫困!有沈旭“心愁贫病裹,风雨满江皋”(《东池再集》),心有愁思又身染病疾,满城风雨似乎无所立身,可怜可悲!有黄瀚“越溪人寂寞,南国思踌躇”(《东池四集·六鱼》),孤独寂寞,徘徊犹豫,不知前路在何方!有沈讷“迂路采莲穿幽径,侧身何地不徘徊”(《东池五集·十厌》),即使身处幽静的莲池旁,亦忧思前路茫茫!有张翼“应怜世故逢多难,短发萧萧半是僧”(《东池五集·十蒸》),生在多灾多难的世道,很多人不得不遁入空门,削发为僧,可见生活的艰难。
(二)窃念家国,物是人非
经历了易代的兵荒马乱,诗人们心中虽惶恐,但心底仍抱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并不敢大张旗鼓的表达,只能借他人自比。诗歌中多次出现杜甫。杜甫亦生活在唐朝衰乱之际,但其始终心怀家国天下,受千万文人敬仰。对于东池诗人来说,杜甫也是一个精神标志。沈旭有“少陵居未空,正是乱离初”(《东池初集》),将杜甫所处时代与今时相比,表明了今时之乱、之苦、之悲;释清晖“杜陵天宝没,怀抱尔犹今”(《东池初集》),杜少陵虽早已逝去,但其胸怀抱负至今仍然延续当今;吴楚“瀼上萧疏地,真堪娱少陵”(《东池再集》),身处破烂萧条之屋,但诗人仍师杜甫安于陋室、作诗自娱。
江山易主,时过境迁,如今只剩一声感慨!如许峙的“平生山水癖,指点昔非今”(《东池初集》),素爱山水,但如今山不是故山、水不是故水,感念昔非今比,人事变化令人扼腕;吴楚“君不见去年看花暑方炽,今年看花落又零”(《东池四集》),花开年年似,不同的是看花的心情。
(三)田园隐居,自得其乐
由于生活艰难,又无力改变现实,诗人们始终安贫乐道,亲自播耕。有张肩“十亩闲闲地,耕桑无古今”(《东池初集》)田地荒芜,便不管古今之事力耕桑田;王广和“情依苔石欲思隐,业在菰田且力耕”(《东池三集》),想要归隐,便只能以耕田为业;汤有亮“漫疏草径自携锄,聊次喜迎竹外车”(《东池三集》)颇有闲情,锄径外杂草;龚鼎铨“花飞钓艇通渔渚,绿绕溪门种葑田”(《东池三集》),赏花、垂钓、躬耕,亦别是一番生活情趣。
饮酒是另一种排忧之法。黄瀚“世故何须问,当歌算放杯”(《东池初集》);许峙“潦倒樽前饮,相携复论心”(《东池初集》);纪镐“把酒话幽事,长歌谢素襟”(《东池初集》);庾明允“胜概古今期不负,且携斗酒醉携柑”(《东池三集》);纪镐“遁世欲寻千日醉,看花能复几回闲”(《东池三集》);释清晖“时多感慨称诗史,杯到淋漓署醉侯”(《东池三集》);沈在“溪翁乘晚霁,池上醉吟兼”(《东池四集》);黄瀚“醉濯苔矶晚,清唫意自如”(《东池四集》)、“对酒只谈风月事,分题又感别离难”(《东池五集》);汤有亮“那堪料理愁中事,杯酒微吟讬共长”(《东池四集》)、“潦倒忘怀聊竟日,櫂歌声起又黄昏”(《东池五集》)。自古文人好酒,尤其是处于如此悲苦惆怅的境地,醉饮能让其暂时忘却世间烦心之事,沉迷诗文、沉迷美景,追寻快意人生。
《东池三集小叙》云:“兰亭修禊,千古美谈。彼时晋室虽微,犹得福安江左似觞咏娱情。”故诗集中不乏将东池集会比照兰亭雅集之作,且向往先贤激昂洒脱,许峙“永和年间事,感慨昔非今”(《东池初集》);吴楚“分得韵牌同玉律,遥知觞咏续兰亭。群贤醉后凭栏否,远岫何如隔岸青”(《东池三集》);龚鼎铨“寂寞漫伤天宝没,风流还似永和年”(《东池三集》),心态积极,即使世道乱离,依旧风流。亦有表现自己高洁立世,沈讷“世路只今逋白发,冷睨野马骤空江”(《东池三集》),即使白发苍苍,毅然敢于冷眼看这乱世。
可见,东池诗人的大部分诗作看似表现隐居生活的悠然自在,实际上,却处处透露着无奈,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他们既是为保全气节而隐,亦是无力生存于世而不得不隐,另有一番沉重忧郁。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东池诗人群体作为亡国未亡人的遗民情结与复杂心态:一方面对明朝故国心怀依恋,却连提及都要避讳;另一方面,不敢也无力改变现实,只得苟活于世,内心却依旧带着悲愤、自责的挣扎矛盾。在清政府高压严厉的社禁政策下,东池诗人群体虽没有组织反清的现实斗争活动,但其抱志守节,绝意仕进,亦应为人所敬仰。明末之际的遗民隐居者虽多,其中不乏将隐居作为终南捷径,以耸动流俗之义求扬名。而东池诗人们,正如《南浔镇志》所载陈忱“居贫,卖卜自给,究心经史,稗编野乘,无不贯穿,乡荐绅咸推重之,身名俱隐,穷饿以终”[3]卷十二,纵有经世之才,却入山唯恐不深,全然归隐!即使穷苦一身,亦不丢失文人风骨,抛却世俗名利,选择终身贫困自处,完成了遗民的全节,为国守贞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