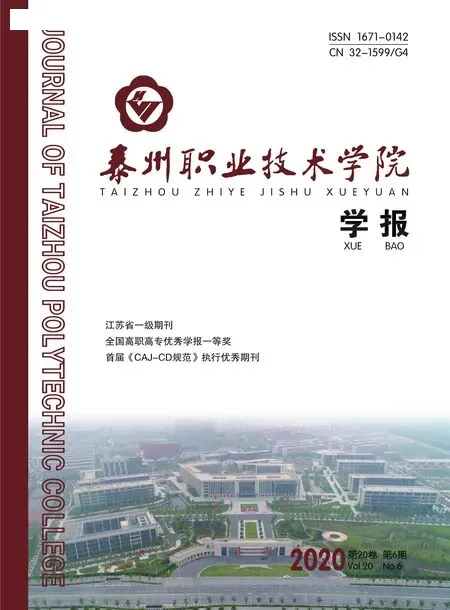论存在论的自明性问题
祁海军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河南 郑州 450018)
“Ontology”以前译成“本体论”,现在改译成“存在论”,据说这是为了破除传统“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以及“本质—现象二分”的深层模式,并且追随海德格尔,坚持存在问题在存在论上的必要性和优先地位。那么,人们这样做有没有超越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围?当然,关键是这里的“超越”应当如何理解,传统形而上学的范围是一个很宽泛的领域,我们在此不妨就传统存在论这个领域来展开论述。这里,从海德格尔对问题的提法入手,简要阐述存在论的困难以及可能的出路,存在论又何以转变为生存论。
1 自明性:存在论与认识论的内在关联
传统的形而上学谈论存在问题大多时候并不是直接谈到,它通过对“在者”的谈论来涉及存在问题[1]。借用海德格尔的表述说,只有这样才能“上手”,就存在者来谈论存在。传统本体论认为存在是存在物的本质,既然存在不可“看”,不可证明(涉及到“存在”的定义问题,而存在是不能定义的,那就涉及到系词“be”。从逻辑上说,定义具有严格的主谓结构,这也与传统逻辑把关系看作内在的有关),那么只有从其显现出来的现象来研究。由此开启了现象与本质、殊相与共相的研究传统。
即使有些专门研究认识论的哲学家,有时也不得不研究存在论的问题,认识论的存在化和存在论的认识化可以说是传统和现代的两种不同的路向。认识论之所以存在化,是因为认识论要求认识真理,那么,证明从什么样的前提出发才是正当的呢?只有从自明性的东西出发。而自明性的东西就在存在本身而不在存在之外,这里存在表现为最初出发的和最后达到的东西,即黑格尔著名的“圆圈”。
而存在论之所以认识化,和人的“反思”有关,即把“存在”首先和经常当作对象来研究,这样存在问题实际上被排除了,因为它把“存在”和存在的显现拆开了。然而存在和它的证明是一致的,不可分离的,这才是关键所在。“在自明性这个要求下,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分界将消失掉”(赵汀阳语)。海德格尔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存在论和认识论结合在一起,而坚持认为两者不可分离。运用现代语言学和逻辑学发展取得的新成果来看问题、分析问题才有可能获得一种新思路。即不仅把作为系词的存在和实存分开,而且把命题逻辑的句子当作分析的单位而不是把单独的词项作为分析的单位,才有把认识论和存在论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海德格尔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做出了出色的阐述。
那么,当我们说“存在就是存在”,这意味着什么?就这句话本身来说,存在(being)去在(to be),同时才存在(being),存在(being)本身初步显露出时间性,表明其不是一种“现成存在”,即“当前”在我们的追问下不仅“来到当前”,而且具有了一种“未来”向度,在这个来到的当前和它的未来那里,存在才开始浮出水面,进入我们的视野(展开境域)。当前好像具有一种“时间深度”,这种深度仍然没有说出真正的“存在”,只是说出了抽象的“存在”。就象我们说出“存在就是存在”这句话那样,并不表明存在问题已经得到正确理解。存在本身还必须展开,因此要获得对存在问题的真正理解,就要获得展开的存在视野。而获得可能阐释存在的视野就要从一种历史的存在者开始,这个历史的存在者追问存在的问题把这个普遍、空泛的问题变成这个历史存在者特殊问题的问题。这个历史的存在者就是“此在”。“此在”这里被表明是一种非现成存在的存在者。存在论的问题显露出具有认识论的性质。因此,海德格尔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于对此在的烦琐分析[2],与传统存在论不同,存在的问题从“存在是什么”变成“存在是谁”。也就是说,Being之为Being,正是“在起来的不断生成”,是作为自由的理念的被抛与沉沦,同时也是此在的投射和筹划。存在论转化成生存论。生存论问题不过德尔斐神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罢了。这样,存在论问题变成日常生活的生存问题。这里,“什么”一词是一个指物的范畴,“谁”这个词则是一个指“人”的范畴,从而显示出海德格尔对此在问题的关注,或者说对人的存在状况的担心,说到底,所有问题变成了道德和价值问题。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
2 见证:存在及其追问
在海德格尔追问存在问题之初,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他的出发点,那就是如下基本的判断:“这里所提的问题如今已久被人遗忘”[2]以及“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的问题”,这个判断造成了他对问题的提法不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重新“唤起”。这里的元问题是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和传统认知方法之间的判断取舍,而这正是一个价值问题,方法与要研究的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割开来。“让存在如其所是地呈现”,这是现象学方法的目的。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如果我们不再先抱有这个目的?对于存在问题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存在问题没有从“遗忘”中被唤起,被重新领会,那么最终我们也将错失存在的问题。
海德格尔对问题的提法已经决定了他的方法是描述性的,对“什么是存在”形而上学的解释还是不清楚。其原因是我们对问题的提法不正确。谈论“存在之为存在”就是谈论“无”,如果不是这样,“存在”就是一种“在者”。所以在语言中“存在”被“在者化”,这是最根本的,由于“什么是存在”的问题已经误解了“存在”,所以在存在论上就不是一个“合法的提问”。
既然人们不能这样提问,那么什么样的提问在存在论上是合法的?实际上,“我们已经先行活在对存在的领会中了”[2],存在就在于这种“问之所问”。这种“问之所以问”和此在具有本质相关性。这也是为什么此在在存在问题上具有优先地位的原因。对于存在问题只有指引,认识论这里表现为追问,而追问并不是要得到对象化的概念知识,追问本身是一种指引,指引我们领会存在问题,存在问题本质上不能对象化为概念知识,因此,我们的追问不仅具有认识论性质,而且具有存在论的性质。
这里,海德格尔抓住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存在和它的自明性是一致的。这也是对此在分析的出发点。那么自明性在哪里?就在此在的生活世界里。至此海德格尔才转身真正返回日常生活世界。在那里发现此在的“被抛”、操心以及沉沦诸状态——一个被技术知性平均化的世界,一切都被平均化,历史变成小报风格的日常叙事,哲学成为常人的茶余饭后,诗歌沦为日常语言的工具,这一切都具有亲在性,指出这种状况是表明一种本真能在的此在式见证。
比较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对存在论的解决办法,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差别是对自明性的理解不同。对胡塞尔来说,“自我思其所思”是自明的,是现象学还原的全部结果[3]。而海德格尔则持相反观点“让存在如其所是显现”。还原到“先验自我”与追问“存在问题”都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自明性。人们认为自明性是不需要加以说明的,因为人人都有关于“自明性”意识。与人们认为的相反,困难在于:“自明性”这个概念的自明性恰恰是依赖自明性的,或者说“自明性”这个概念本身并不自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一位“超越者”。需要说明的是海德格尔似乎意识到了这个循环,他把自明性等同于见证(去看,亲历)。这样,海德格尔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传统存在论,处在通往“实践”的途中。
此在及其追问本来的意义不在于获得关于存在的知识,而在于表明一种生存态度:向死而在的此在在被抛与沉沦中筹划着、操心着、烦着。这是生存的本真状态,也因此进入对“存在”的拯救。
3 本真建制:作为自由的此在
此在的沉沦状态和马克思所论及的异化状态有似曾相似之处,但是海德格尔和马克思仍然大异其趣。首先没有一种本真状态的建制,就无法有意义地谈论此在的沉沦和异化。在海德格尔那里,本真此在的建制表明是一种新神学(就象“亏欠、罪责、良心、召唤以及呼声”这些概念所崭露的那样,本真的此在是“向死而在”),在马克思那里,本真状态则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即异化劳动的克服以及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其次,此在的时间性建制不同,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的空间,这是在人类作为历史的存在物这个意义上而言的。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时间性分析着眼于时间内状态(海德格尔用“……到时”这一概念表示),作为“……到时”,对此在来说实际上已经是“向死而在”了。最后,理论指向不同,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论是“思”之事业,拒绝承认存在论可以对象化。而马克思则是要求实践,承认实践是对象化及其克服。
把海德格尔和马克思联系起来的不是两者旨趣相同,倒显示出我们自己的“先行具有”,即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的在先理解,正是这种在先的理解决定了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方式,这说明马克思在我们对于存在论的理解上的优先地位。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是作为“思”存在论,马克思的存在论则是“实践”存在论(固然马克思没有专门详细论述)。两者的历史性差别不可忽视。
就“存在”自我呈现这个意义上而言,存在的问题可以看作自明性的问题,而自明性问题之解决将意味着存在论在生活中的实现,或者说存在论在专门哲学上的终结。终结这里成为可能的出路。而上面谈到的生活世界,为解决存在论问题提供了可能。生活具有历史性,而历史性是人的实践的出发点、过程和结果。人通过感性活动得以见证历史(生活)。生活是最终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元科学,元科学的元科学……”这一无穷倒退的永久终止)。因为任何思想、语言、行动都不在生活之外。我们出生、成长、衰老以及死亡是自明的,因为这就是生活。
自明性问题作为生存论问题,对海德格尔而言,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主体的“被抛在世”又是主体的“投射筹划”。对马克思而言,则意味着共同体-主体的“物化异化”和“革命实践”。对于传统哲学的体悟方法而言,则意味着冷暖自知和将心比心的类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