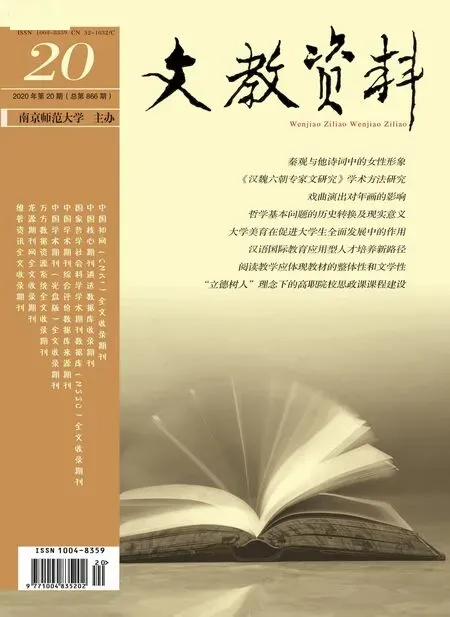《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学术方法研究
胡 楠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723001)
方法是活动的手段,是人类为获取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行为方式。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自然包括治学研究方面。学术方法的重要性自古便有所认知,在《论语》中便有许多对孔子讲述治学方法的记载,“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等语录皆耳熟能详。钱穆在《中国学术通义》中对学术方法的重要性也有所提及,所谓“凡属讨论或指导学问,最高应是道术兼尽”[1](5)。道自是道德,术便是方法,治学研究的最高准则即为“道术兼尽”。方法是治学致知的起点,也是引导思维、规范思维、把握事实、处理事实的重要工具,各学术大家在学术研究中都有独特的研究方法,此仅以《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为对象进行论述。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是刘师培对自两汉以迄唐初之间的断代文学史的研究文章的合集,论述了汉魏六朝文学变迁特点与诸家文章优劣得失,褒扬藻韵,推重美文,严辨“文”“笔”二体之别,为声偶之文争正统。除此之外又有《学文四忌》《论谋篇之术》《论各家文章与经子之关系》《洁与整》等篇目。在这本小书中,刘师培运用了多种学术研究方法对诸多问题进行论述,对现今的学术研究有诸多借鉴意义,现将其整理如下。
一、时代法
正如刘勰所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每一时代之人都必然有当时时代精神的烙印,每一时代必然会有相应时代风气的文章,每一时代必定会有独具特色的学术研究。苏轼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恰是此意。所谓时代法,即“乃以断代为史之法,以论一代之学术,凡一代之史,一代之学术研究,均系此一方法之应用”[2](230)。
杜松柏在《国学治学方法》中认为,时代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在《魏晋六朝专家文研究》中的体现全面且鲜明。首先是在划分时期方面的应用:时代的分期必然有其理由,必须合乎事实,有合理之处。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的《绪论》中将两汉至唐初之间的文学史分为了六期,并给出了合理的依据:“两汉(此期可重分为东西两期;东汉复可分为建安及建安以前两期)、魏、晋宋、齐梁、梁陈(梁武帝大同以前与齐同。大同以后与陈同,故可分隶两期)、隋及初唐(初唐风格,与隋不异,故可合为一期)。”[3](110)刘师培对汉魏六朝的六期划分使六朝文学史更细化,更易于研究者进行探索和专研。其次,时代法的运用在于注意时代背景的研究,学术的形成和发展,与时代背景、时代风尚有关,凡政治、世变、思想、风气,都有着莫大的影响。这一点正如刘师培在《论文章宜调称》中论述的那样:“夫文因时代而异,亦犹人因面貌而殊。”[3](147)文章因时代而有所不同,若同一时代有数派文字并存,则不过是时代的承上启下而已,而文章为何因时代不同,则是时代背景的不同造就的。最后,时代法的运用体现在注意其时的特殊贡献、特殊成就。《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囿》中便涉及了这一点:“一代杰出之文人,非特不为地理所限,且亦不为时代所限。”“于当代因袭旧体之际,倘能不落窠臼,独创新格;或于举世革新之后,而能力挽狂澜,笃守旧范者,必皆超轶流俗之士也”[3](140)。杰出文人是不会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特殊贡献和特殊成就反而随着时代历久弥新,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二、批判法
人的学术积累到达一定程度后,便会有评定是非优劣的情况。这种对作品进行评定,进一步发现真实,建设一系列系统观念的学术研究方法,便可以称之为批判法。通过批判法所建设的观念,会更正确,更会引起较大的反响,更能推动学术思想的成长。
批判法的运用并非空口无凭、信口开河,而是要求批判者在态度上秉持公正,不偏不倚,不含成见,才能尽量避免判断过于武断或仅出于主观臆断。且批判研究法也有相应的原则:(一)依据信证,绝不能口说无凭。批判研究法的可信之处正在于其依据的可靠性,若资料本身不可靠,则批判结果的可信度自然大打折扣。(二)有明确的依据标准和原则,而非朝令夕改。(三)具有历史的观点,溯古追今,而非囿于时代的观点,仅论当时当世。(四)批判应有所结果,裁断优劣,以明真实。这些原则在此书诸多篇章中皆有所体现。如,在《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一篇中,刘师培对今之论者辄谓“六朝文学只能空写而不能写实”这一论断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汉魏六朝各家之文学皆能写实,其流于空写者乃唐宋文学之弊,不得据以概汉魏六朝也”[3](137),并对汉魏六朝的论著并非空写进行了有依据的论证,多引《史记》《汉书》《晋书》等为据,得出“汉魏六朝之文学,皆能实写,非然者即属‘拟其形容,象其物宜’一类”这一观点。又如,《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囿》一篇中,刘师培在论述“文学不可为地理所限”这一观点时,对《隋书·文学传序》中关于“南北朝文体不同”这一观点的论述展开了批判并进行了论证。《隋书·文学传序》秉持中国因地理南北不同而文体亦不可强同的观点,但刘师培就各家文集观之认为并非如此。他由潘(岳)北陆(机)南而潘清绮、陆质实为切入点,指出南北不同而文风不同的说法并非定论,“若必谓南北之不同,则亦只六朝时代为然”[3](139),又以南北各朝文风之演变为例,力证此观点。除此两篇外,在其他诸篇中批判法时有所见,此处不多赘述。从这两篇中亦可管中窥豹,其论证证据皆有所考、标准皆有所靠、批判皆有所辩,结论自然有道理。
三、归纳法
所谓归纳法,即由个别到一般的推理,它是由一定程度的关于个别事物的观点过渡到范围较大的观点,由特殊具体的事例推导出一般原理、原则的解释方法。基本原则是以实验和观察材料为基础,经过分析、比较、选择、排斥,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归纳法由特殊之事物,推普遍之理,由个别之事例,以推知共同之通则,所明白可见者为现象,所隐微难知者为事理,在归纳时应注意事物之因果关系和变化因素,这在此书中亦有所体现。在《论谋篇之术》中,刘师培借刘彦和之言推理文章构成的基本要素:“夫立人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3](118)由此,刘师培先生归纳出文章构成的几个要素:命意、谋篇、用笔、选词、炼句,必先树意以定篇,始可安章而宅句。又以《史记》《汉书》诸多篇章为例,实证谋篇之要。这是最简易的由个别说法推至普遍道理的论述。又例如,《论文章有主观客观之别》一篇,开篇即“文章有主观客观之别”,后以各家之文为例论述,又分为学说与文体两部分阐述。在论述《史记》之主客观时,更明确指出其归纳法的运用——“《史记》则意在题先,借题发挥,属于唯心的文学。唯心只能归纳,唯物只能演绎”。也就是说,若命题在前,而例证在后,便是归纳,不然则为演绎。与今世所言的“由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正是同一个道理。刘师培在此书中运用归纳阐述了很多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除所例两篇外,在《学文四忌》《论文章之转折与贯穿》等篇中亦皆有出现。通过对归纳法概念的深入了解和刘师培在此书中的具体而大量的应用,不难发现,归纳法在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体现众多事物的根本规律和事物的共性,对验证文学研究的一般规律起着重要作用;但采用归纳法时应注意事物变化时之因果关系、变化因素和相应之变化,才能规避不完全归纳之过。
四、比较法
自审美观念和价值判断产生之时,人类便对自身条件、外部环境和周遭事物等都有所比较,这是人类的天性,自是不可避免。这种比较有时是为了对比优劣一分高下比长较短明辨是非,有时是为了比较出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及各自的特点特质。当比较法应用于文学领域之时,作用便主要为后者,将两种及以上的学术思想、文人或文章进行比较推量,以求出共同点及各具之特点特质,非仅以见其优劣、长短、是非。
在学术研究中,比较法的目的多样,但杜松柏在《国学治学方法》中主要将其归纳为五点:(1)得出共同之处;(2)决定个别事物;(3)知相同相异之处之所在;(4)知同中之异,异中之同;(5)知优劣是非之所在。在《魏晋六朝专家文研究》一书中,比较法出现的频率较高,在诸多篇章中都有所运用。例如,其中有的篇章中比较的目的是阐述问题,《论文章有主观客观之别》一篇中,便是将各家文章及各类文体的主观客观之别进行对比,其中运用大量举例加以论证,以论清“夫文学所以表达心之所见,虽为艺术而颇与哲学有关”[3](131)这一论点。又如《文质与显晦》一文,其中将文和质、显与晦进行比较,并非为了一求文质显晦之高下,而是为最终求得“盖文章音调,必须深浅合度,文质适宜,然后乃能气味隽永,风韵天成”的结论。另外,一些篇章将二者进行比较以分析各自特质,如《蔡邕精雅与陆机清新》,此文中将蔡邕和陆机之文作比,非为评优劣较高低,而是分析各自文章特点并对后世模拟者进行了评述。但此书也不妨有对两相比较者一较高下的,《论文章之转折与贯串》一篇中,即将《史记》《汉书》与后代史官进行对比,指出其高于后代史官之处,恰在于其善于转折。自《晋书》以下,都是意图在一传之内叙述多件事件,便只能加以浮词使得文意贯通,或是拆分段落以使层次分明;《史记》《汉书》中,虽叙的是两事而文意依旧贯通,即使未有分段也还不至于界限不明,《史记》《汉书》与后代史官之书在叙事成就上高下立见。通过此书中比较法的运用再结合其他文献,不难发现比较法的应用也有应注意的地方,即二者近乎相同的不必比较,二者性质不同品类完全相异的也不必比较,以及在对不同文化系统中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时,要对历史背景和语言文字进行深入了解,以避免解读不当的问题。
五、学术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书中采用多种学术研究方法,非能一言以概之。除了列举的例证鲜明的时代法、批判法、归纳法、比较法之外仍有其他学术方法,但囿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列举,如演绎法、宗派法、问题法等。
在文章的阅读过程中和对种种研究方法的分析中,不难发现一个问题——研究方法的运用并非单一的,而是综合的。也就是说,一篇文章并不是只能选取和应用一个研究方法,而是可以综合性运用,有时学术方法的综合运用会使论述更完整、更有逻辑。例如,《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一篇采用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综合方法。在文章的总论方面,为证明“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这一论断而采取了归纳法,由个别事实到一般真理,由特殊到普遍,刘师培列举了大量文献事实证明这一论断。“例如东汉文章,以蔡伯喈所传独多,而《艺文类聚》所引,宋人刻本《蔡中郎集》已未全收。……盖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3](141);而在借前面所言结论来论述钟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中对《隋志》记载的可信性时,则采用了演绎的方法。由已知推未知,由普遍之理推特殊之事物,即为演绎法之所用。二者相辅相成,使得论述的逻辑更严密。再如,《文质与显晦》一篇是归纳法与比较法的综合运用。与上一篇相似,此篇归纳法的运用仍是在对论断的推论上,但不同之处在于论证过程,通过文与质、显和晦的种种比较,最终完成推论。归纳法和比较法的结合使论述内容更充实,论据更加丰富,论断更使人信服。由此可见,学术方法的综合运用并非是单一的,甚至不局限于某两种或某几种,而是多种研究方法共同使用、共同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任意搭配,而是根据各个研究方法的目的、特点及注意问题合理应用,以避免出现前后矛盾的组合情况。
六、结语
学问为要研究其对象,无论如何都非根据方法不可。所谓方法便是到达对象之途。方法的重要作用在诸多方面可见一斑,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要作用在相关文献的研读、学术论文的写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采用的多种研究方法颇具借鉴意义。归纳法、比较法、批判法皆是常见的学术方法,这在阅读相关文献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思考方向,“为何会归纳出此种论断”“为何此二者可以比较/为何比较”等问题都有助于阅读时思考;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若是掌握了这些研究方法,则更是事半功倍,论文的内容将更充实、逻辑更严密。但在具体应用中,要注意结合相关选题,采取合理的学术研究方法,关注目的、特点及注意问题,以免陷入唯方法论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