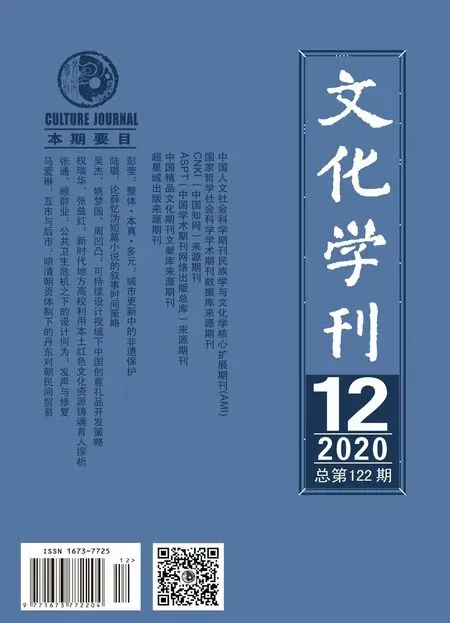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群体性事件态度的转变
李传玺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封建专制程度亦随着军机处等机构的设立而不断提高。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专制制度,对于民间的群众聚集是警惕的,对于民间的群体性事件更是坚决地镇压,这在清王朝前期的矿业政策、乾隆六年(1741)户部宝泉局工人罢工事件和乾隆十三年(1748)顾尧年请愿事件中均可见一斑。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不断加深,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清政府发现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在谈判桌上使得列强让步。为了在外交上挟制西方列强,清政府便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群体性事件,逐渐转变对民间的群体性事件态度,从单纯的打压群众聚集、群众情愿,转为有意识地引导甚至放纵涉外事件中的群体性事件,这在广州反入城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都有所体现。
一、鸦片战争前清王朝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态度
清王朝建立之初,由于担心统治下的汉族群众反抗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所以对治下民众的群体性活动十分敏感。清王朝在开矿与禁矿政策上的反复便是明证。
有清一代,清王朝从未完全禁止矿产开采,但清王朝的矿产开采主要分布于云南及其周边地区,而其他地区的矿业政策则是反复不定的,且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矿业政策。总的来说,康熙朝的矿业政策是以禁为主,禁中有开;雍正则是进一步强调禁闭;乾隆又一次变为以开为主,开中有禁[1]。但是,无论是哪一个时期,清王朝从未真正对矿产开采放下戒备之心,清王朝对矿产开采如此不放心的一个原因便是开矿“易聚难散”,由于开矿工作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协调合作,矿场便成为一个人群聚集之地,这种地方最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雍正二年(1724),户部的一份奏折中就直白地提到:“当矿沙盈溢之时,日得工价,借为衣食之资。及苗脉渐微,采按无获,商人工本既亏,夫役环视,给之既无其力,散之又无所归。聚此饥寒之人,欲不流为匪类,其可得乎?”[2]乾隆七年(1742),浙江巡抚常安上疏乾隆帝:“浙省遂昌县之小纲源,天台县之天封山,青田县之朱山等处,俱有铁矿砂坑,愚民无知,纷纷具呈恳求开采。臣因其地或涉临海澨,或僻在深山,俱易滋匪,一并严行禁止。”[3]这些官员主张禁矿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开矿容易聚众生事,也就是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康、雍、乾三朝,力主禁矿的官员奏折史不绝书,即便开矿事关国计民生,但是清王朝出于维护自身专制统治的需要,对于开矿一事仍十分警惕,清王朝根深蒂固的维稳观念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帝主政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了顶峰。乾隆六年(1741),清朝人口为14 341万,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清朝人口达到了29 696万,人口总数逼近3亿。随着人口的激增,耕地资源也越来越紧张,清王朝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阶级矛盾愈演愈烈,各地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乾隆六年(1741),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就发生了一起工匠罢工事件,户部宝泉局2 000余名工匠因工资纠纷竟然罢工停炉,“七月间各匠因工价不敷应用,四厂全部停炉,经监督及各厂大使说服,西、南、北三厂匠役开炉鼓铸”[4]3363。但是,当年七月,宝泉局工匠再次罢工,据户部尚书陈德华等奏:“北厂匠役忽于本月初七日仍复停炉,要算本年秋季新帐,并要找算两年旧帐。至十八日西厂匠役忽上房呐喊,抛砖掷瓦,要照北厂重与炉头找算旧帐。”[4]3363双方协调无果后,步军统领衙门出兵镇压,俱舒赫德奏称:“遣派官兵赴厂弹压,并施放空枪数声,工匠稍知畏惧。”[5]但是,乾隆帝却嫌镇压力度不够,他要求继续追查为首之人,务必斩草除根。乾隆帝批示到:“此等刁风甚属可恶,京师之地且如此,何以示四方。著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务必重处,以警其余。”[6]乾隆十三年(1748),苏州米商哄抬米价,导致民众不满。苏州布衣顾尧年代表民众去官府请愿,请求官府调控粮价以保障民生。为了证明自己无意挑战官府权威,顾尧年“自缚双臂,插竹粘纸,上写‘无钱买米,穷民难过’等语,前赴巡抚衙门喊诉,欲求勒令米铺减价出售,从而和者甚众”[7]。但是苏州地方官并没有理睬顾尧年的诉求,反而将其押往长洲县(今属苏州市)审讯。苏州百姓一时间群情激奋,纷纷来到官府前,要求释放顾尧年,苏州官府随即镇压请愿百姓,又相继逮捕了39人。此事上奏乾隆帝后,乾隆帝对此事作了如下处理,“今江苏一省,因米价昂贵而奸民遏粜滋事之案,不一而足,如苏郡顾尧年之自缚以煽动众心,其尤著者,将来辗转效尤,何所底止?此数案现在作何办理,地方官曾否宁怗,督抚大史当妥协经理,方不负简任封疆之意,非徒以一奏了事,遂谓可谢己责也。”[8]可见乾隆帝是高度重视这类民众抗议物价事件的,但他的着眼点不在于解决百姓诉求,调低物价,而是担心将来“辗转效尤,何所底止”。
在清王朝专制的鼎盛时期,清朝统治者绝不允许民间有任何挑战王朝权威的事情发生,对群体性事件也是持零容忍态度,乾隆帝之所以“盛世用重典”,就是要将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事情扼杀于萌芽之中。
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态度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对治下民众说一不二的专制政权,却难以应对来自欧洲列强的挑战。为了在外交上更好地与列强周旋,清政府在一些涉外事件中开始鼓动民众“聚集闹事”,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有所松懈。
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但《南京条约》的规定只是笼统的原则,具体细节并没有交代清楚,这就为中英双方的入城争端埋下了伏笔。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向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了入城要求,但是耆英并没有同意璞鼎查的要求,他所依仗的是《南京条约》的第二条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9]根据条约规定,“英国人只能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显然城内是没有港口的,所以英国人只能住在通商口岸的城外;而且中英双方对条约中的“城邑”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英国人认为城邑就是指城内,但清政府方面并没有具体规定城邑是指城内还是城外。最终,耆英既未同意英国人入城,也未彻底拒绝英国人入城,而是在广州城外的珠江边上替英国人租了一块地供其居住,入城一事也就被搁置了下来。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人再次向耆英提出入城要求,耆英与英国人往来公文数十次,仍不能打消英国人入城的念头,于是将该事上奏道光皇帝。道光帝向耆英指示到:“该督等惟当持以镇静,俟其续请时,即告以贸易之事,期于彼此相安,今欲更改旧章,人心必为疑怪,粤民素称强悍,且恐良莠不齐,傥或滋生事端,彼此均为不便。”[10]由此可见,道光帝对英国人入城一事也是十分无奈,只能搬出“民意”这块挡箭牌,但这也未尝不是搪塞英国人的绝好借口。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二月十六日,耆英与广东巡抚黄恩彤联衔贴出告示,宣布允许英国人入城,希望士绅百姓“务各破除畛域,蠲释猜疑,勿再仍前阻挠,以敦和好”[11],但此举随即遭到广州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有谣言称刘浔府中藏有英国人,愤怒的广州群众随即火烧官署,又将刘浔的朝服朝珠烧毁,刘浔只得翻墙逃跑。“广州府刘浔出,尝杖双门市民之未避前驱者,行道讹言骤起,以谓府署藏纳英夷。万喙如潮,假虐责良善为繇,遽相聚而火其署。掷物火中,虽贵玩丝毫不取,与夷馆受毁时相似。浔越后垣,走匿藩署。”[12]耆英随后将这一消息告知英方,英方在“民意”面前果然却步,不得已暂停入城一事。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利用群体性事件来对列强施压的案例远不止“广州反入城斗争”一例。“以民制夷”可以说是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交涉的一大外交手段。同治年间,醇郡王奕譞曾提出过一招对付洋人的办法:“饬下各督抚设法激励乡绅,设法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13]奕譞这一招摆明了是要在涉外事件中故意制造群体性事件,从而扶民自重。同治九年(1870),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此时奕譞又上奏朝廷称:“事之操纵困难,理之曲直自在,虽不能以之喻彼犬羊,正好假以励我百姓,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以鼓其奋发之志,激其忠义之气,则藩篱既固,外患无虞。”[14]奕譞的这些想法,与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何其相似。
而1899年至1900年在中国华北大地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起初也只不过是一些规模较小的群体性事件,如梨园屯教案便是当时常见的一桩教案,这场运动之所以走向失控,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不当处置。在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之下,靠清政府自身的实力是无法与列强周旋的,所以清政府只能靠所谓的民心来自保,毓贤曾说:“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沓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15]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二十九日,给事中胡孚辰上奏表示:“岂知今日时势,不仗兵力而仗民心;各国之觊觎而不敢遽动者,亦不畏兵力而畏民心。”[16]《恽毓鼎庚子日记》记载,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三日召开的仪鸾殿御前会议上,作为清王朝实际当权者的慈禧太后也曾说过:“法术虽难尽恃,人心自有可凭,此时若再失了民心,真不能立国了。”[17]但是,清王朝作为一个专制王朝,本能地对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感到恐惧,且清政府的统治者并非不知道群众一旦被煽动起来有多危险。早在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就曾说:“明知小民随势为转移,不足深恃,而犹藉之以仇强敌,是已自涉于夸伪,适为彼所笑耳。时名之不足好,公论之不足凭,来示反复阐发,深切著明,鄙人亦颇究悉此指。”[18]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光绪帝也曾说:“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19]但是,羸弱的清政府要想靠自身的力量来对付气势汹汹的西方列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通过制造群体性事件的方法来给列强施压了。
三、结语
清王朝对待群体性事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态度,大概可以鸦片战争为界。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对群体性事件绝对是十分警惕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手段也是以镇压为主。而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对群体性事件不再一禁了之,甚至在涉外事件中故意煽动百姓反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清王朝无法以自身羸弱的实力去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只能寄希望于组织起来的民间力量去对抗西方列强。而从根本上讲,清王朝对群体性事件态度的转变,也是封建君主专制走向没落的信号,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晚清封建统治者无法再对治下的百姓说一不二了,他们只能将百姓拉入其与洋人的对弈之中,从而在“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循环之中尽力与列强周旋。但清政府这种“以民制夷”的策略并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可以说正是由于清政府在涉外群体性事件中的不作为与乱作为,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失控。当然,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一个连司法权都不能独立自主行使的清政府,又怎么可能指望它合理公正地处理民众的涉外纠纷呢,所以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与失控也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