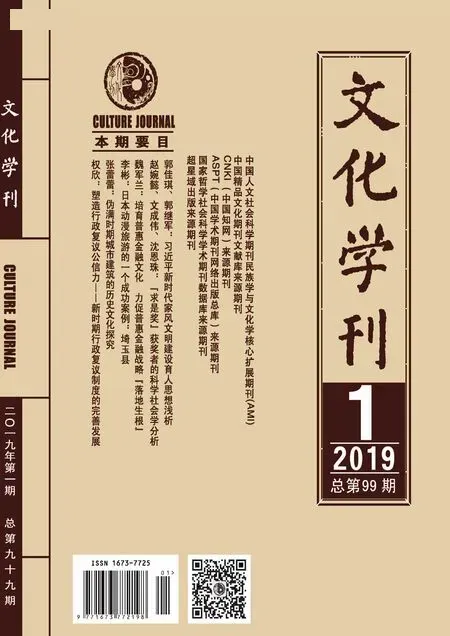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视角及其文学效果
杨培源
一、《红高粱家族》不同的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是文本中对讲述的文本内容进行察看和叙述的角度,根据讲述人察看故事内容中情景的立场而区别。热奈特使用“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三种类型来区别不同的叙述视角。下面结合聚焦与人称的概念分析不同叙述视角在《红高粱家族》中的运用及其不一样的文学效果。
(一)零聚焦叙述
“零聚焦”指在叙述过程中没有统一视角的全知道的述说,其特点是叙述者所了解的比旁人了解得更多,即全知视角。《红高粱家族》以“我父亲这个土匪”作为讲述故事的开始,与“我爷爷”“我奶奶”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爱恨情仇相呼应。“我”是一位处于当代的述说者,“我”的视角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视角。文本中的内聚焦叙述者“我父亲”年纪尚小,“我”不可能对“我奶奶”临死前的心理活动知道得那么清楚。显然,“我”并不参与故事的构建,只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光辉岁月的转述者。因此,“我”的叙述拥有全知视角,并在故事的叙述中充当隐含作者的传声筒。“我”有了解全局的视野,身为“作者”的“我”是处在《红高粱家族》文本内容事件之外的人物,“我”是“父亲”、“父亲”心中的“爷爷”及“奶奶”发生的事情的书写者。一般情况下,在《红高粱家族》中出现拥有全知视角的“我”,会使读者感觉他们在被“我”指引着阅读文本与理解主题思想,会使读者失去自主阅读和选择的主动性[1]。然而,作者莫言似乎故意不断地在提醒读者,有一位拥有全知视角的零聚焦叙述者站在读者与文本内容之间,那就是全知叙述“我”。
通过全知视角对《红高粱家族》的全景透视,使叙事可以充分运用各种故事情节和内容,灵活地调整文章结构和布局,梳理繁多的人物事件和复杂的人物线索,表现当时山东高密生活的广阔性和复杂性,为读者认识和理解当时战火纷飞、兵匪横行的现实生活提供一个恰当的认识角度。
(二)内聚焦叙述
“内聚焦”的特点是叙述者只叙述个人知道的情况,即从某个人的单一角度讲述故事。《红高粱家族》由“我”担任叙述者,以故事发生的旁观者的身份,讲述自己爷爷余占鳌和奶奶戴九莲的故事。在关于难以触及的战火年代的历史叙述中,故事内人物“我父亲”对自身经历的叙述拉近了叙述与故事的距离,消除了作者的叙述痕迹。《红高粱家族》中有关“我父亲”这一内聚焦贯穿全文。
内聚焦视角虽然没有展示出全知视角那样广阔的历史场面,却增强了无所不知的全知叙述的可靠性[2]。此外,《红高粱家族》中采用的第一人称“我”易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拉近了与故事读者的距离,往昔峥嵘岁月恍如昨日,历史的叙述有了较为强烈的现实感,并唤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三)外聚焦叙述
“外聚焦”叙述的特点是叙述者知道的比当事人知道的少。从人称而言,也是第三人称叙述。由第三人称外聚焦叙述表现的人物对话是叙述文本中进行详写的常用手法。莫言在小说中很好地运用了这种叙述方式,比如说“我爷爷”为“我奶奶”受辱找花脖子报仇的经典对话:
“我要见当家的。”爷爷说。
“是烧酒掌柜的?”花脖子说。
爷爷说:“是。”
“你来干什么?”
“拜师学艺。”
此处的外聚焦视角的叙述者没用使用任何转述语,完全采用非介入性客观立场,干净利落而又完整地再现出人物的对话。零聚焦的叙述者“我”不置一词,似乎暂时放松了对人物对话的控制,任由人物自己的对话顺畅进行,却又准确地传达出“爷爷”为“奶奶”报仇的急切心情。
二、多种叙述视角的文学效果
(一)视角的越界现象
《红高粱家族》中,零聚焦叙述、内聚焦叙述和外聚焦叙述的相互交融和越界的现象很常见。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叙述视角越界产生的一种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这种视角的“越界”兼有几种视角的优势,可以达到原来单一叙述视角难以表达出的艺术效果[3]。《红高粱家族》的外聚焦全知视角是贯穿全文本的“我”,是事件外的一个叙述者,即外聚焦叙述,使“我”有了了解全局的视野。作为孙辈的“我”不可能对发生在数十年前的对话如此了解,更不可能对于“我父亲”的感觉了然于胸,“我”跨入了文本叙事的主要方面,出现了零聚焦,“我”的视角在不断地切换,跨越不同的叙述内容。
《红高粱家族》有的场景中叙述者采用较为灵活的第三人称限制视角来描述人物的话语,和内聚焦叙述视角形成交错而使叙述话语更加丰富,例如余占鳌因要吃狗肉而和胖老头产生的对话:
“掌柜的!”余占鳌喊。
“用什么下酒?”余占鳌问。
“狗头!”胖老头恶狠狠地说。
“我要吃狗肉!”余占鳌说。
“只有狗头!”胖老头说。
“狗头就狗头!”余占鳌说。
此处叙述者只是对人物对话进行转述,第三人称的限制视角叙述的痕迹并未破坏作品的真实感。第三人称描写的全景内容,避免了第一人称叙述时的主观情绪和眼界的限制,具有比其他限知视角更开阔的观察视角和更广大的叙述空间,因此可以灵活自由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状况。
(二)架构多元复合叙述模式,增加作品的历史深度
《红高粱家族》中的多元复合叙述模式,增加了作品的历史深度。为了表述作品的多元历史内容,莫言在《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过程中破旧立新,采用多层立体叙述的框架,与故事的多重历史时空形成对应,进行了层层递进的历史叙述。
第一叙述层,故事外的作者式的全知视角的叙述者“我”对那个战火年代的全景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局面的动荡,为“我爷爷”“我奶奶”故事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背景。全知叙述者通过透视视角既能游离于故事之外对人物进行外部观察,又可自如地切入人物意识进入心理透视,关照其内心感受,如对于“奶奶”临死时的描述。通过这种透视,可以看到在生逢乱世、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的疏离感,也可以看到“奶奶”对这个世界的不舍,“奶奶”留恋这个世界、不忍离去的心理读者一览无余,莫言将这种手法运用得恰到好处。
第二叙述层,内聚焦叙述者“我父亲”的关注内容以及所叙说的具体内容。“我父亲”以感性的叙述回忆“奶奶”的传奇人生,这在不自觉中为故事涂上了浪漫色彩。《红高粱家族》中对“奶奶”的死的叙述就说明了这一点。“我父亲”作为《红高粱家族》文本故事中的一位人物,在对“奶奶”的死的叙述中,以孩童的视角展示了“我奶奶”死去的过程,亲历了生命与死亡的瞬间。在作品中,作者采用“我父亲”这种内聚焦的叙述方式有效地延长了叙述时间。与此同时,作者也采用了零聚焦的叙述方式描述奶奶即将离去时的心理活动:“这就是死吗?我就要死了吗?再也见不到这天、这地、这高粱、这儿子、这正在打仗的情人?”通过零聚焦的内心透视,展示了一位敢爱敢恨、真实可感的女性。同时,借助视角转换的场景延长叙述时间,这一时间远大于故事时间,放慢了叙述节奏,令人对“我奶奶”的叙述印象深刻[4]。
第三个叙述层,全知全能视角的“我”所叙述的内容,以及“我”对“爷爷”“奶奶”的故事的叙述。由第一叙述层到第二叙述层再到第三叙述层,是一个完整的追溯式等级序列。作者通过有规律的叙述层的交错,将叙述视角一步步延伸至历史的深处。相互交错的叙述层赋予文本以内在统一性,三种叙述视角“爷爷”“我父亲”“我”频繁地改变而自如切换,交织和融合,在文本中组合自然。各个叙述视角所叙述的内容自成章节,可分可合,众多的文本片段看似形散,实则神聚,相互关联[5]。不同视角的三部分内容各自独立,形成横向叙述,分别表现不同视角的历史内容。平行的三个横向叙述又串联起来形成纵向叙述,反映出“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发生发展的演变进程。纵横相交,构成《红高粱家族》的叙述内容的经纬线,同时体现出历史内容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赋予作品的叙事内容以深度和广度。
三、结语
在《红高粱家族》的创作过程中,莫言突破了传统的叙述视角模式,以视角越界这一独特的叙述手段开创了当代小说叙述的新方法,尤其是多种叙述视角的有序切换及其架构的多元复合叙述,增加了《红高粱家族》叙述的历史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