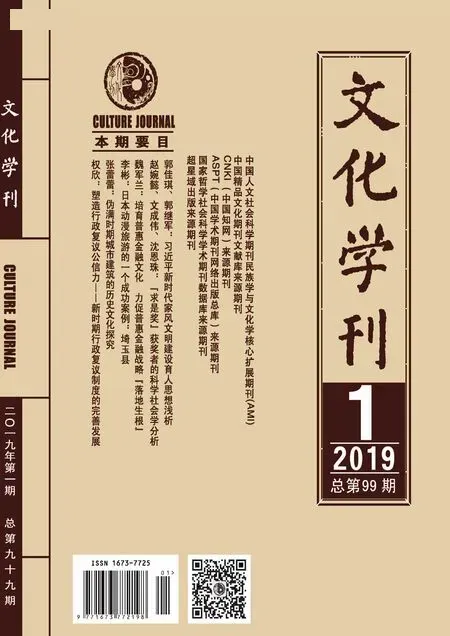“诗绝字绝画绝”,印亦绝妙:
——读板桥印存散札(之一)
艾 珺
说起人谓“绝世风流”“文化怪杰”的郑板桥,世人至为津津乐道、耳熟能详的话题,往往是“诗书画三绝”“难得糊涂”“吃亏是福”,以及种种令人百听不厌的传闻逸事。即如启功先生《论书绝句》八八《郑板桥》所咏:“坦白胸襟品最高,神寒骨重墨萧寥。朱文印小人千古,二十年前旧板桥。”诗后自注云:“二百数十年来,人无论男女,年无论老幼,地无论南北,今更推而广之,国无论东西,而不知郑板桥先生之名者,未之有也。”“当其休官卖画,以游戏笔墨博鹾贾之黄金时,于是杂以篆隶,甚至谐称为六分半书,正其嬉笑玩世之所为,世人或欲考其余三分半书落于何处,此甘为古人侮弄而不自知者,宁不深堪悯笑乎?”
是否可行,首先在板桥印章作品的本身。那么,如何客观评价板桥印章艺术呢?
迄今为止,纵观所见和各类文献著录的板桥印章总有大约近百馀方。如上海博物馆《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文物出版社,1987)收录95方,《郑板桥印册》汇集了板桥印章94方(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也有人说,“现在我们知道的郑板桥用于书画作品上的印章大约有一百三十方左右”(杨谔《试说郑板桥的篆刻艺术》,南京印社《印说》2002年创刊号)。还有的“经过多年寻访,并参以旧闻所见,得板桥印鉴152方”并且“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姓名字号斋馆籍贯’‘苦难身世’‘政治抱负幽默诙谐’‘修身养性’及‘艺术追求’等类”(党明放《郑板桥》,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在本人这样一个喜爱书画和传统印章艺术的业余爱好者眼里,评价或鉴赏印章艺术无非有三。一是印技,二是印文;三则是无论其前两者优劣入眼与否但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如印章作者,印文内容,印章的文物品性,等等。
大略说,中国印章作为独立的艺术,可以追溯到秦汉。书画艺术使用印章,滥觞于唐,兴于元,盛于明清,直至融为一体。在很多书画家兼擅治印的同时,也涌现了许多专擅治印或以治印为主的印家,并形成了诸多著名的流派和大家。板桥时代,业已是书画艺术与篆刻艺术异彩纷呈,互赠书画、刻赠印章,成为文人层面的一种交际习俗,一种雅事。板桥用印亦然。如黄学圯《东皋印人传》载,“板桥道人图章,多出凡民手,时有《四风楼印谱》。凡民而外,则胶州高西园凤翰,天台潘桐冈西风,江都高翔风岗也”。徐兆丰《风月谈余录》卷六亦载,“板桥先生印章,半出沈凡民、高西园手”。可窥一斑。
由于向喜板桥艺术及其性情,因而多年关注、赏析板桥印章,也有一点小小心得,且不揣浅陋述请方家指正。
首先,板桥可谓印家,并由其板桥风格,板桥艺术应涵盖其印章艺术。以诗书画三绝饮誉一时文坛的郑燮,虽亦以“三绝”自诩,但在印章艺术方面绝非弱项或“短板”。就迄今可见和文献著录所及,板桥印章,太半系自己奏刀,少半为友人所刻赠。板桥擅于治印的较早记载,是清末著名学者乾嘉学派领军人物阮元的从弟阮充《云庄印话·印人诗事》所记:“板桥曾为先祖制‘学圃’石印,井绘赠墨竹巨幅,题云:‘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来年更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风池。’惜未入集中。”板桥自道书法“字学汉魏、崔、蔡、钟繇;古碑断碣,刻意搜求”(《署中示舍第墨》)。板桥题项怀述《伊蔚斋印谱》中曾自道,治印“追踪两汉入先秦,较古堂中集印人,那晓风流开下相,波斋穆倩是前身”。其《题程邃印谱》又云:“周栎园(亮工)先生《印人传》,八十余人,以何雪渔、文三桥为首,而往复流连,赞不容口者,则为垢道人,可谓知人特识矣。其《赖古堂印潜》近千颗,分为四册,然皆方硬板重,如道人之浑古流媚者,百不得一。想道人亦深自赏重,不轻为人捉刀耶?”清末集书画篆刻家与书画理论家于一身的秦祖永,其著名的画论专著《桐阴论画》,谓板桥“印章笔力朴古,逼近文、何(文彭、何震)”。秦祖永《七家印谱》辑其印章十二方并印跋。西泠印社仰贤亭《印人画像》中《板桥道人小影》的题跋评价板桥“道人刻印,兼书画之精补,而直追汉与秦,其醇厚与疏宕,殆仿佛其为人,宜乎业不多觏,是固希世之珍”。而且,板桥位居所集刻的二十八位著名印家之四。凡此,可知板桥所追随的格调高古的印风,凝重挺拔的刀法,独具其“六分半”(“板桥体”)书法风格的印文印款和章法结构布局,凸显着鲜明独到的印艺特色,可谓一时印坛翘楚。
其次,板桥本人的态度和印章艺术在其艺术活动及技艺中的分量。“诗书画”之三绝,也是郑燮自诩自得之事,可由其一方《诗绝字绝画绝》用印为证。若总论板桥艺术成就和显著特点,“三绝”显然恰如其分。世人公认,艺术家生前即自况自诩,堪谓盖棺论定的历史结论。据《试说郑板桥的篆刻艺术》考察,“在篆刻上,他对自己没有很高的要求,他刻印不是很多,一生中也没有惊世之作出现,也没有形成他自己独特的较为成熟的篆刻浯言,但他扎实精深的学识、超乎常人的艺术天份、深厚的诗书画造诣,使他在篆刻艺术上,迅速登堂入室,成为当时篆刻名家,本可以成为大家的,但他好象不着意于此,篆刻在他眼里.是‘雅事’,跟‘诗书画’相比,又只不过是供人‘遣兴’的,始终是一件‘余事’而已”。所言甚是得当。
第三,板桥作品诗书画印艺术融为一体,四种艺技集于一身。坊间或谓能否将板桥的印章艺术亦视为“一绝”,与其他“三绝”合为“诗书画印四绝”呢?这动议,实非“妄议”古今有目共睹的板桥艺术成就的谤言,而是期望锦上添花,将其评价得更完美的美言。在明清印坛宏观视野下,以用比较的视点综观板桥印章艺术,总体存量有限,似乎又少有令人惊艳之作,亦即“没有惊世之作出现”。或言之,非要以“诗书画印四绝”相誉,实为苛求的过誉,既非板桥自家所愿,亦欠实事求是。
板桥印章艺术的价值何在?愚以为,板桥印章艺术之“希世之珍”,不在于印技如何,而是包括他人刻赠印章在内总量有限的用印所体现的历史文化价值。透过诸如印章作者、印文内容所印证的情趣、追求、交游、履历,尽可从一特定的微观展现板桥乃至“扬州八怪”群体的文化活动,甚至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风貌。至少,会提供可供再现当时生活现场的众多线索,这也是其印章的文物品性。以今存有限的百馀方板桥印章为文本,研究探析板桥“绝世风流”的人生轨迹,“文化怪杰”的艺术成就,于是便设想撰著一部附有《郑燮印谱》的《郑燮印传》,亦不失为一个颇有情趣和价值的事情。藉此来了结几十年喜爱板桥艺术及其为人品性而一直未得仔细品鉴的宿愿,岂不快哉!
于是,以板桥印存为话题,将一向品读板桥的心得拉杂付诸札记文字,求证于方家。
板桥一生是在坎坷的愤世嫉俗中“风流”着的,之所以“风流”得起来,是其积极向善的生活态度,总能感受生命的春色。这一点,在板桥用印中时时可见。《郑板桥印册》辑有一方长方朱文印“春风欲起锦浪初生”,未标示自刻还是他人刻赠?但用在板桥书画或印册里,终归是板桥用印。再如一方“甘露被野嘉禾遂生”,亦然。两方用印勘谓其内心生命律动的写照。因而,困苦甚至是潦倒一生的板桥是快乐的。落拓而不沉沦,狂宕而不狷戾,放浪而不无羁,淡薄而不沉寂,板桥可爱的底色也。
“春风欲起锦浪初生”,“甘露被野嘉禾遂生”,且以此开篇。